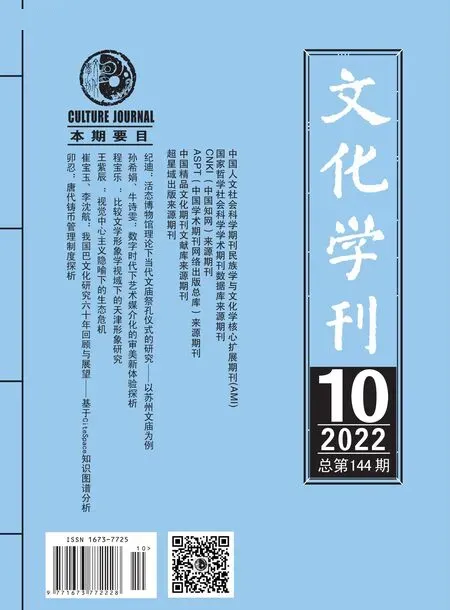三重结构对立下的深层话语
——以“行动元模型”观照谭恩美小说《接骨师之女》
刘林怡
《接骨师之女》是美籍华裔作家谭恩美创作的小说之一,也是她最具自传性质的作品。小说沿袭了作家一贯的写作风格,与《喜福会》《灶神之妻》《沉没之鱼》共同构成了书写华裔女性在男权主义和种族主义双重压迫下的生存困境及寻求自我和话语权道路的史诗系列。格雷马斯《结构语义学》结合行动元类型与普罗普的民间故事叙事理论,建立起一种抽象的“行动元模型”。格雷马斯提出根据行动元之间的接合,三对互相对立的“行动元范畴”即主体、客体,发送者、接受者,辅助者、反对者。本文试图从小说文本的情节中抽离出三对互相对立的行动元并加以剖析,寻求构成意义的深层话语结构。
一、愿望先导性的话语重奏
主体与客体是第一对相互对立的行动元,二者是由一种逻辑先设的语义投入即“愿望”结合关联的。主体是带有一定欲望性的存在物,欲望要想实现,必须以寻找、追求的方式进行。相对应的客体是被主体所想望的存在物。
(一)从失语到发声
《接骨师之女》中,带有一定欲望的主体是第二代华裔女性露丝(杨如意),被人向往的存在物的客体是露丝母亲茹灵的家族历史。从全文来看,露丝与茹灵之间恒定存在矛盾,随之茹灵在医院被查出表现出老年痴呆的症状,为了了解母亲的病情,露丝此时才想起母亲记载着家族历史的文稿,通过文稿,露丝终于重新理解了母亲,“也是一种母女关系‘回归’的过程。”[1]值得注意的是,主体对于客体的追寻并不纯粹是出于自动自发,而是在偶然的情况下不得已转向的寻求,也正是这种偶然性使得露丝最终获得的不仅是表层上对母亲茹灵的谅解,更是其自身一直以来苦苦追寻的文化之根。“阅读母亲过去的历史,才知道母亲心中装着的是对女儿最好的愿望。”[2]文本的第一部开篇就是“八年以来,每年八月十二日起,露丝·杨就开始失声,说不出话来”,这种失语现象的产生看似偶然,却也带有某种强烈的暗示意味。由于第一次失语是从“露丝刚搬到旧金山亚特的公寓里”开始的,它表明这种沉默是自我缺失的开始,因而寻求发声的过程也是追寻自我形象和话语权的经过,露丝作为主体展现追寻客体的欲望也是寻求自我的欲望。“又到了八月十二日,露丝仍然呆在她的小书房里,静静地坐着。雾角划破夜空,迎接行船归港。露丝没有失声。她讲话的能力并不被什么毒咒贼星或者疾病所左右。这一点,现在她非常清楚。可她不需要开口说话。她可以写作。此前,她一直没有一个理由为自己写作,只是为他人做嫁衣,如今,她找到了为自己写作的理由。”第二年的八月十二日露丝不再失声,这意味着追寻的达成,露丝也决定不再为他人代笔,她要下笔写出自己家族的历史。
(二)叙述的重章叠唱
《接骨师之女》文本的一大特点是出现了大量关键情节、意象的同义反复,散落和跳跃在历史与现实、中国与美国之间,犹如音乐的重章叠唱,彰显了作为家族历史的客体被叙述时在文本中的音乐性回环和丝丝渗透。比如,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流星”一词,茹灵的小叔(亲生父亲)写给宝姨的情诗中“倏忽唇启流星语,灿若晨曦掩日华,转瞬日落寻不见,愿逐星迹至天涯。”情话“想听听你飞星般的话语”“她的话语犹如流星,稍纵即逝”“狗吠月升。星恒烁夜。鸡鸣日出。天光星散无痕。”这些话语都大量反复出现宝姨的真实姓名谷鎏信的谐音词语。更在深层次上暗示宝姨本人也正如流星一般拥有绚丽而短暂的生命。宝姨原先“相貌超凡脱俗,一双吊梢杏仁大眼,目光深邃,眼神仿佛无所畏惧。她眉毛朝上挑着,显示出多思善问的个性,而饱满的双唇显得非常性感,在她那个时代却很不讨喜。”这似乎定格成永恒的照片与自残后的相貌形成极端对比,在后来的文本中反复出现。
再如“穷途末路”与“天涯海角”。刘家房屋伫立在悬崖边,“刘家先前房子后面有二十亩地,可是几百年来,一下大雨崖壁就坍塌,山水轰鸣,水土流失越来越严重,崖沟一年比一年宽,一年比一年更深了。每过十来年,那二十亩地就变小一点儿,直到最后,崖壁直逼到了我们家屋后面”。而崖沟底下是被人们当作丢弃各种杂物的垃圾场和死孩子、自杀的女人、流浪者的露天葬场。“穷途末路”本是刘家人对逼近自家屋子崖沟的戏称,“说什么时候悬崖边到了我们房子边上,我们家也就走到‘穷途末路’了,意思是说我们的好运道就完了,我们家就完蛋了。”露丝从与高灵姨妈的对话中得知老房子在1972年就全部陷下去被黄土掩埋了,刘家和仙心村也真地走入了穷途末路。而“穷途末路”还有一个另外的名字是“天涯海角”,与茹灵在旧金山住的地方“Land’s End”又构成意义的巧合和同义反复,而旧金山的住处是露丝无意间浮现在脑海中的,暗示着一次逃避性质的搬家在情节上将主体推向了客体,是意义和历史的双重回归。
再如,楔子开篇“这些事情我知道都是真的”,在第一部露丝第一次试图破译文稿时再次出现。楔子中宝姨告诉茹灵“永远不要忘记这个姓氏”和第二部开篇“这些事情我不该忘记”。这些话语与刘家老宅作为历史被黄土掩埋消失,而仅存留于人物记忆中却因痴呆症恶化即将永远消散构成对抗性的反复。
二、历时存在基础上的结构交叠
第二对“行动元范畴”中,发送者是茹灵的亲生母亲和保姆宝姨,接受者则是茹灵。发送者与接受者之间相联系的客体也是第一对范畴中的家族历史。
(一)双层嵌套结构
发送与接受的过程表现形式从文本来看是一种双层嵌套的结构。双层嵌套是指部分呈现的文本是其他部分中某一具体事物的历时存在物,与历时语境下的文本共同构成完整的文本结构。在《接骨师之女》中,楔子“真”是以第一人称叙述的刘茹灵所写文稿的开头部分;第一部以第三人称视角展示了第二代华裔女性露丝与母亲茹灵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以及露丝在西方环境中生存的种种艰难;第二部是以茹灵为第一人称的家族故事回忆,第三部又回到第一部的语境中以第三人称视角描述露丝通过茹灵的手稿与母亲达成理解和平衡。文本的第一部、第三部和尾声是现实与回忆交织的延展,楔子和第二部共同构成茹灵的文稿,包括真(Truth)、心(Heart)、变(Change)、鬼(Ghost)、命运(Destiny)、道(Effortless)、骨(Character)、香(Fragrance)八个小标题,此为文本的第一层嵌套。从手稿中可以看出茹灵的命运与宝姨人生经历的无数暗合,茹灵人生中第一次经历剧变就与宝姨有直接的关系。茹灵的手稿是与露丝关系缓和的重要媒介,相似的是宝姨写给茹灵的书卷也成为茹灵用一生的时间去理解宝姨和赎罪的中介,此为文本的第二层嵌套。茹灵在宝姨生前由于自身的叛逆任性未能与她母女相称,反而是在宝姨自杀后的岁月里不断忏悔和追忆,并在晚年记忆不断剥离的过程中坚守了对宝姨“母亲身份”的认同,如在中秋家宴上反复说明宝姨是自己的亲生母亲和手稿中提到的“我是茹灵,你的女儿”。
(二)三重历史的球形聚合
楔子和第二部的文稿以茹灵和宝姨为核心人物,每一个小标题与情节都构成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连缀成茹灵的成长史、刘家制墨店兴衰史和仙心村近代变迁史。这三重历史从个人、家族和国家三个层面共同构建,以龙骨为核心意象成球状聚合。“这是一个华人移民家庭三代人的历史,也是作者自己家庭史的真实写照。”[3]茹灵个人的命运牵动着刘氏家族的兴衰,刘氏家族的起落又同仙心村近代的变迁一起被历史的洪流裹挟着,三重历史由微观到宏观重重包裹,共同勾勒出近代中国硝烟四起的历史画卷。龙骨作为核心意象,是宝姨与刘沪森结婚时的嫁妆,却被棺材店张老板抢夺,直接导致新婚当天的惨案和宝姨悲壮毁灭肉身的行为。龙骨的丢失对于宝姨而言不仅意味着最有价值的财富的丢失,更是父亲毕生心血和家族赖以生存的根基的失去,宝姨吞食墨浆是精神极度崩溃下的疯狂,其后果是人人望而生畏的丑陋相貌和失语。龙骨后来被考古学家证实为甲骨而身价倍增,挖掘龙骨也一度在仙心村兴起,并给仙心村带来经济上的繁华。也是由于龙骨,当抗战全面爆发后给仙心村招致了无尽的灾祸。茹灵的第一任丈夫潘开京正是在坚守考古现场中被抓以致后来不幸被杀害。为了报复刘家人不顾自己被张老板迫害的现实而坚持把茹灵嫁到张家的冷漠,宝姨在死前对刘家也展开了致命的报复,让制墨店在大火中烧得干干净净,刘家也从此家道中落一蹶不振。
三、华裔生存夹缝中的异质文化天平
第三对行动元是围绕主体露丝的辅助者和反对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称这一对行动元是为“制造文本的幻觉”而设置的,没有了这一对辅助元关系,文本将会极其简单。格雷马斯认为它们的作用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有助于欲望实现,利于交流;第二类阻滞欲望的实现,妨碍交流。这两种力量使得文本变得复杂化,意义也更丰富。
(一)时空维度的统一体
辅助者是在露丝追寻家族历史中起到帮助作用的人,比如高灵姨妈。高灵作为茹灵名义上的亲妹妹、血缘上的堂妹、社会关系中的妯娌,与茹灵的关系一直处于微妙的竞争状态,茹灵在手稿中和晚年生活中时常透露两人互相攀比的嫉妒心理,二人如同双生花在乱世中分散又相逢,有着相似的命运。高灵在茹灵从开始发病到确诊为老年痴呆症的几年中,时常帮助露丝照顾茹灵,也是茹灵备感无助时首先求助的对象。高灵是除了茹灵的文稿之外,连接露丝和茹灵母女的纽带。露丝和茹灵的家族姓氏在文本中由于人物无意识的遗忘处于空缺位置。楔子中“我知道这一切,但有一个姓氏我却记不起来了。它藏在我记忆里最深的一层,我怎么也找不到。”茹灵的手稿中也进行过多次徒劳的尝试,就在露丝几乎以为自己再也无法知道家族姓氏时,高灵却为露丝几经辗转终于打听到了家族的姓氏和宝姨的名字,在结尾时经由高灵的电话最终揭晓。追寻历史的句点似乎只能由高灵亲手画上,高灵不仅是露丝与茹灵之间联系的重要媒介,也是家族历史的参与者,她是身上烙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一代华裔,是第二代华裔记忆深处的寻根所在,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统一体。
(二)破局“他者”
谭恩美作为华裔女作家,在以白人和男子为中心的美国社会一直面临着双重被边缘化的“他者”地位,“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与繁荣,表达的就是华裔作家从边缘走向中心的向往和努力”[4]。反对者如亚特、亚特的前妻米莉安、亚特的女儿菲雅和多丽等人,这一群体掌握了西方主流文化和话语权,是露丝失声的主要原因。这一群体具体又可以分为两类:其一是以亚特、菲雅、多丽等人组成的西方家庭成员,他们代表着西方主流文化;其二是以雅嘉琵、吉蒂恩、泰德等构成的工作伙伴,这些人代表着西方主流话语权。第一部的七个小部分多角度展示了露丝融入西方社会的不断努力和频频受挫。在家庭生活中,她与亚特九年的同居生活导致关系遭遇瓶颈,与亚特女儿们的关系也矛盾重重、从未缓和,这些不协调都在中秋家宴上达到了顶峰。“她想,最起码今天晚上的菜不会叫人失望”看似闲笔,实则写出了露丝对家宴的深层感受,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失望即将压垮她,她以自嘲的方式来化解。在工作上,“在跟人合作的这些书上,‘露丝·杨’这个名字总是用小字体印在重要作者后面,有时甚至根本不出现她的名字。”她对自己工作的真正态度是“她提醒自己,总的来说,她帮忙写成的这些作品还算有趣,倘或作品无趣,那么想方设法让它变得有趣正是她的职责所在。”露丝俨然行尸走肉般麻痹了自己,她以失去自我为代价努力求得占有西方话语权的一席之地,而结果却是遭客户辞退。实际上,看似神坛的主流话语权也并非充满着崇高与权威,与露丝解约的客户的书很快被摆放在减价书柜台,“荧光绿的标签上写着特价三块九毛八,醒目地贴在书的封面上,这标签就像是死尸脚趾上的牌子一样,宣布这些书的价值就此完结”,因为露丝的客户一味追寻主题的流行,而主题更新换代速度太快,书的价值只能像通货膨胀般一贬再贬。
露丝是华裔女性在男权主义和种族主义双重压迫下艰难生存的个体代表,不断在夹缝中寻求自身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平衡状态。从文本来看,只有发出自己的声音才能获得话语权从而达到二者的平衡,露丝也最终同母亲和白人男友达成了双方的相互谅解。而这样的结局也是作者作为美籍华人在异乡走出身份对立,接纳自我身份的一种表达,借露丝体现“可以容忍和异族文化的差异性和独特性,追求多元文化的和谐平等相处”[5]的意识。
四、结语
谭恩美的《接骨师之女》自传性地展示了作为华裔女性在美国主流文化中的融合与生存的历史与现实,通过露丝的生活现状关照着特有的身份焦虑,这种焦虑感的追寻也必须从历史中寻找答案。三重结构对立下的格雷马斯行动元,是文本流动下的深层话语,推动着主人公露丝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使其最终回归家族的历史和血脉。作为承载历史的语言面临的重重“失语”,也是作为华裔的三代母女无法表达自我和不被家族、异乡接纳的隐喻。文本中对于三代人姓名含义的追溯也饱含着家族过往的记忆与联系,是前辈的苦难史和生存在当下对于幸福的渴望。而在当下生活的露丝,接纳自己和母亲之后也能够从自己家族与文化的身份中汲取力量,并以一种开放的善意看待华裔女性生存的困境,融入于多元化的异质文化中。尽管作为他者的身份,这条道路还很漫长,但是至少露丝已经拥有了不可磨灭的身份根源记忆,能够用更积极的态度面对自己、母亲、爱人等差异化的情感,面对未来和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