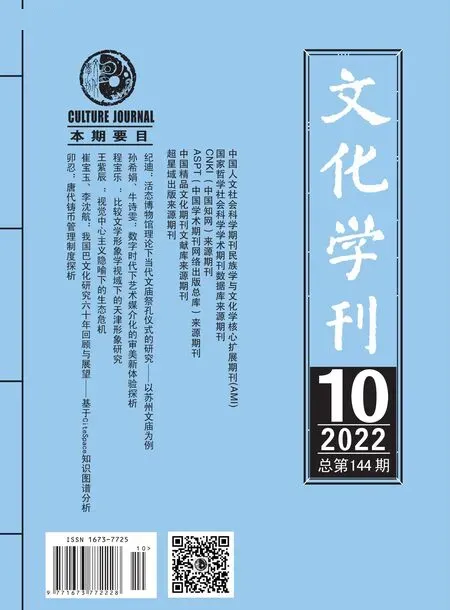有限与无限之间:聚焦于爱情的存在之思
——以小说集《好笑的爱》为例
李 琳
米兰·昆德拉笔下的人物在偶然、微妙的具体生存中筹划出无限可能性。他的小说集《好笑的爱》聚焦于现代人的爱情,除了象征永恒的“大写的爱情”,还有除去“严肃”的爱情,他将承载宏大意义、界限分明的“爱”消解于个体于具体存在中复杂、飘忽不定、矛盾且虚无的旋涡,对立于理性主义的超越抵达无限,呈现了个体存在的有限。“大写的爱情”扮演着个体超出自身有限性的媒介,是此在抵达无限的桥梁。除去严肃的爱情看似消解了爱情的形而上意义,却是对无限的另类想象。
一、哲学背景及对存在的探索
昆德拉认为现代人陷入“存在的遗忘”这一状态。海德格尔对“存在”一词进行词源学意义上的考察,认为自柏拉图以来,西方哲学史便将“存在”的问题等同于“存在者”的问题。他提出的人的存在形式,即“在世界之中的存在(in-der-Welt-sein)[1]45”。在此基础上,昆德拉通过审美的艺术形式,将栖身于经验世界中的人及其生存的真实境况呈现出来。由此,人的具体存在(concrete being)扎根于大地,作者在具体的生存情景中追溯人的存在,探索人“将是”的多元可能性。
(一)西方理性传统:被遗忘的“存在”
在胡塞尔看来,欧洲人文危机根植于欧洲科学的片面本性,它将人存在于其中的具体世界作为不断征服的“他者[2]3”。这可回溯到希腊哲学,它意不在人类如何更好地在实际生活中生存,而是发乎于一种认知激情,诸如发现普遍事物、脱离时间性的抽象本质,将理性“完全从无意义的原始水准超拔出来[3]86”。笛卡尔将人拔高为自然的主宰者,而面对超越性的利维坦,包括技术、政治、历史等力量,人只是作为单一客体而存在[2]4,人的具体存在即“生活世界[2]4”被预先遮蔽和遗忘了。在马克思看来,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一切事物的价值都被抽象为了符号-货币的关系[4]。现代科学的迅速发展,将人局限于专业化的领域内,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专家没有灵魂[5]”。昆德拉同样发现:现代知识在专业化、精确化层面日益深入的背景下,是人们对整个自然以及人自身的遗忘,人的存在陷入被海德格尔称作“存在的遗忘[2]4”这一状态。在此基础上,昆德拉主张,人物与其周围世界都应考量为“一种极限的、未实现的可能性[1]54”,在无限可能性的领域中认识你自己。
(二)存在的多元可能性
存在问题的本质以关键词的形式在行动与情境中逐渐显示出来[1]38。不同的存在情景以“复现模式[6]6”流动在小说集《好笑的爱》中的多个故事中。复现,顾名思义:某个现象或某一事件再次发生或重复出现,现代文学中与循环形式相关的理论可追溯到“德国文学中抒情诗歌的循环[6]4”,该作品研究了德国浪漫主义诗人采用的循环形式,对这一形式的基本特征进行了界定。Forrest L.Ingram在此基础上将“故事循环”定义为“一组相互关联的故事,由此来维系每一故事的独立性或个性与大的单元之间的平衡[6]5”。《好笑的爱》中强调的“复现”,呈现为同一主题或情景在多部小说之间流动辗转,“不断经受着形式或者意义的改变[7]332”,因此,读者可从不同的视角沉浸思考。
昆德拉对“存在”的探索,指向对人类生存可能性的探索。这可能性并非由人的本质决定,而是在具体的存在中理解,正如海德格尔所述:此在是什么,依赖于怎样去是,而怎样去是依赖于它将是什么[8]42。他用“生存”来规定此在的存在,怎样去是先于是什么,此在总是在意识中先行于自身而存在(being),并筹划(envisage)出各式各样的可能性,此在总是以不是其自身的方式(mode)去是其自身。此在的“所是”是它去存在的种种可能方式,即此在“作为它的可能性存在[8]42”。昆德拉进一步主张“存在包括着现实的各种可能性[9]”。他笔下的人物被赋予极大的象征意味,不同个体与同一情景或动机,在周围世界中呈“根茎状”延展开来。
二、有限与无限之间
(一)人类建构无限以超出自身的有限
“现代哲学始自一种彻底的主观主义,主观以一种隐蔽的对抗性面对着客体[3]216”,笛卡尔以来,自我作为思想的实体被称为主体,自然是具有广延的客体世界,人立志要成为自然的征服者。莱布尼兹超越笛卡尔,提出“万物都有某种驱动力,以便及时向前运动[3]217”。克尔凯郭尔否认抽象思维凌驾于人类现实(human reality)之上,强调对“我存在”这一命题的思辨不能替代且完全不同于个体于经验中的存在,他认为生活中的“自我”对于存在的把握不是源于思想的“超然”状态,而是“自我”面对生命之有限而不得不陷入的“非此即彼[3]173”的选择中。在尼采这里,存在个体从理性的光晕中滑落,理性“主体”将人的身体、欲望即感觉世界遮蔽,将思想抽象化为超经验的理念,这种抽象概念相对于经验世界中“生成”的恒长之流,代表着永恒的“存在”。现实中的人唯有驯服或抑制人性中被理性所拒斥的部分,否定或贬抑生命本身的某些部分,在怨恨与内疚中实现社会化。尼采以“力量意志[3]217”揭示力量本身成为目标,而人类永远抵达不了至高,始终都留有对更深远处虚空的恐惧。
1.抽象对具体经验的遮蔽
昆德拉笔下的小说人物,时常追求某一抽象理论或抽象概念,妄图将具体的经验或感受列入括号悬置起来。
如《搭车游戏》中,“他”将“女友”勾勒为只有忠实和纯洁的抽象姑娘,因此,在两人共同扮演的搭车游戏中,娴熟于轻佻、淫荡的游戏角色的女友引起他对其灵魂的质疑。双重形象的野蛮混淆使他厌恶,正如拉康所说,完整统一的人是抽象物,存在于经验中的人是矛盾、分裂、破碎的人[10]。“他”意识到经验世界和以概念抽象出的系统知识与直观认知之间无法弥合的裂隙,女友的“所是”被他的欲望、抽象思维、理性傲慢所遮蔽。
对于生命有限的焦虑,往往需要人为建构种种“超越性所指”。赫拉克利特曾说,万物无法逃脱死亡与变化[3]89,而柏拉图出于对生命有限的焦虑转向永恒,使绝对理性的人成为永恒存在的“人”。昆德拉笔下“人的死亡”被消解为墓碑,而这块墓碑在时间的流逝中须让位于后死者:《让先死者让位于后死者》中,“她”丈夫的墓碑被另一陌生者的墓碑替代,这一“让位”使她愤怒于人类至高尊严受到践踏,先死者的死亡不再拥有一种“死亡之存在权”。与此同时,“她”一直被迫束缚于“寡妇”这一抽象概念,并赋予这一身份宏大的意义与价值,面对男主人的引诱,她坚守着自己设立的“青春之碑”,但于经验中,墓碑事件的荒诞使她迅速消解了宏大的意义而投向了欲望。
巴门尼德曾说:“能被思考的和能存在的是在那里的同一事物[11]”。但经验世界远非纯粹的逻辑推理或抽象理论能够直接演绎出的真理,抽象之道德理论及行为准则在界限模糊、错综复杂的现实中显得无力。《座谈会》中关于伊丽莎白被误以为自杀这一事件的归因,几人以严谨有序的逻辑思辨得出了完全相异的因与果。他们挑选和处理不同的材料,演绎出各自的完美结论,在偶然中锚定必然的决定性因素,即使推理合乎逻辑,极具说服力,但都无从定论自杀的真实动机,伊丽莎白也并非确知自身的意志。显然,存在(being)的被遮蔽才是常态,人们在分析“现象”之前往往被自己所带入的偏见和预设所遮蔽,从而在“假象”的面具下挑拣着某一可能性,正如女大夫所言:若归因的结果能拯救灵魂便试图认定它。
时间于人,并非人被抛入世后才延展开的,流俗的时间观念将时间理解为现成事物“在其中”生灭的无终或无限的时间。人操劳于世,将时间抽象为生活秩序的一部分,客观估算精准的时间,但在计量之前,时间“乃是某种做成我的东西[12]”。时间融入个体的生命,诸如对事物状态的特殊感知,对时间的特殊记忆,组成个体的存在经验。《永恒欲望的金苹果》中“我”渴望体会文化历史的缓慢,而人的生活类似于历史进程,逐渐加快实则是距离的远近。
《爱德华与上帝》中的阿丽丝将“空泛、弥漫和抽象的上帝”具体化并植入她的经验生活,成为“反通奸的上帝”,在与爱德华的相处中,她在身体上区分出一条不可逾越的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态度的转变,与爱德华近乎虔诚的爱的宣言、绞尽脑汁的理性辩论都毫不相关,阿丽丝却因披在爱德华身上的宗教外衣而主动背叛上帝,而这恰是出于偶然的谎言。
2.必然作为吞噬偶然的幻象
人类个体在充满偶然性的生存体验中,妄想以必然的先验价值将其悬置。
如《谁都笑不出来》中,“我”的意见成为扎图莱茨基先生的论文能够发表的决定性条件,“我”不愿将恭维的崇拜者变为敌人,也坚决不写该文章的阅读报告。应对他日益频繁的来访,“我”以主导者的身份开启了他企图引诱女友的游戏,这却使“我”无法将整件事从荒诞的严肃性中抽离出来,“我”和女友的关系破裂;失去了视为严肃的科研工作。“我”意识到不存在一个现成的“我”,“此在”永远都在展望未来的各种可能性来筹划自身,只有在事后,我们被解开布条审视过去的时候,才会认清“此在”的“曾在”,以及它们的意义。
《座谈会》中的哈威尔提到,恰恰在因果论不得施展之时,充满铁定规律的世界才得以留存一点儿无序的空间。哈威尔拒绝了伊丽莎白的性暗示,统计学家或大数据的结论都会指向他接受的结论,但正是逃脱了普遍的决定论之外,他得以在自身的偶然性中自由筹划各种可能性。
(二)个体存在的有限性
海德格尔表明,康德提出的关于人类理性局限性的学说,立足于人的存在的有限性[3]121。个体的生命是有限的,然而人类总是沉溺于无限,昆德拉认为:人自在世便禁锢于并非自我选择的身体,并注定要死亡[1]34。此在“被抛”在世,死亡于存在者而言,是最本己、最极端的可能性,是此在“不得不承担下来的生存可能性[8]201”。然而,“何时死亡”具有不确定性,此在于日常生活中往往掩盖这种不确定性并遮蔽死亡的确定可知,由此减轻被抛入死亡的状态。
昆德拉笔下的人物共同显现此在存在的有限性。
《谁都笑不出来》中“我”因一句“玩笑”陷入了生命的虚无,他迷恋于自己主导的历险,但事态不断违背意志戏剧化的延展,女友和工作同时抛下他,他意识到所谓的历险并非自己的选择,而是“外界”强加于我们,不知它们从何来、去往何处,被遗弃感和失落感向他袭来,我们为何于“此时、此地”被抛入世,他感受到生命的脆弱与偶然以及来自深层存在的无力。
此在“被抛入世”必然指向此在向终结存在,人类知或无知则说明了其在实际生存中如何向终结存在,而无论知或不知其将死,“首先和通常是以沉沦的方式死着[8]202”,即沉陷于常人或日常的种种事务之中,借此遮蔽向死存在。《哈威尔二十年后》中的记者从自身“所能是”之中脱落,消融于公众视野中,躲避在看似实用的普遍规范下,恐于自身在无限的可能性中作出抉择,沉溺于不自知的非本真状态。然而,这正是海德格尔所描述的“常人(das Man)[8]109”即日常生活中的此在自身,“以非本真的方式存在着[8]163”,此在抛弃自己向“常人”筹划自身,日常此在总是先行将自己与其他并非本己的一切进行比较,趋向异化,将本真的能在拒斥于心外,“哪怕只是本真地面对失败的能在[8]163”。虽然记者极度关注自我,但他惯于在他人的眼光下寻求自己的“能是”,只得躲避在所谓“大师或内行”的权威下,以免直面自身。
生命个体无法逃脱经由岁月产生的变形,在有限的虚空中身处无遮无蔽的状态,被孤独和对死亡的无限恐惧缠绕。《先死者应让位于后死者》中的墓碑,揭示出人类对生命有限的有所作为,在世者将死者的生存之“无”的存在立身于墓碑,表示哀悼和思念,耽留于死者。然而,象征生命延续的墓碑也无法逃脱时间,需让位于后死者。故事中的女客拒绝谈论死亡话题,借他物遮蔽身体的变形,将人生的意义嫁接到“人的事业”并外化到他人身上。男主人极力为自己筹划出可抵消过往经验中一切失意与不足的砝码,以此来抚慰自己面对生命消逝而一如既往虚无的心灵。
人生而有限,正如《座谈会》中主任医生所言:“我”是即将回归于大自然的灰尘。
三、“严肃”的爱情与除去“严肃”的爱情
昆德拉将“大写的爱”延展为非严肃、小写、复数的爱,“爱情的概念始终与严肃相连”,好笑的爱“是除去了‘严肃’的爱情范畴[2]43”。他于存在中聚焦爱情,爱的情感以及性欲在现代社会的陷阱中变成了什么,承载宏大意义、界限分明的“爱”在现代个体的存在中有着怎样的变幻?
(一)“大征服者”与“大收集者”的辩证关系
在文本中,“大征服者”与“大收集者”显现为爱情这一极管的两端。《座谈会》中,哈威尔大夫对“唐璜的结局”以及他的承继者“大收集者”神话光晕的消解作出一番陈述。唐璜的角色在西方的想象中是“性爱的某些非神圣化[7]338”的象征。在哈威尔看来,唐璜是一个大写的征服者,承受着“悲剧性的包袱[7]156”,在大征服者的世界中,情人之间的一瞥抵得收集者无数性爱的累积,但这崇高的意义正如唐璜最终被雷电劈死坠入地狱一样消失了。大收集者与“悲剧”毫不相关,是顺从常规与法则的奴隶,将性爱日常化和平庸化,种种激情和感情远离大地,轻如鸿毛。大收集者将重负消解为鸿毛,而这重负帮助个体克服生命有限的不可承受之轻、奔向无限。
然而,大征服者与大收集者在文本中又呈现为辩证关系。在爱情领域,大征服者赋予爱情严肃意义与崇高建构,是个体通向永恒与无限的象征;大收集者看似消解了爱情的严肃意义,反对爱情的崇高建构,而本质上是对无限的另类想象,某种意义上是对大征服者的回归。
1.“大征服者”向“大收集者”的滑落
对于“大征服者”而言,爱情不局限于双方以及双方关系问题,性爱不仅在于肉欲,还需要透过对方看到“其他东西”。《座谈会》中主任医生认为性爱是对荣誉的渴望,性伴侣作为“自我”的镜子以衡量自身的价值。当爱情从严肃的范畴滑入非严肃的领域,性爱成为日常生活中平庸的琐事时,人不得不“从反面”寻求性爱荣誉,即拒绝一个求爱者。对于拒绝者而言,通过对方的苛刻来凸显自身,实现价值的“外化”;于被拒绝者而言,作为唯一选定的人,获得“例外的荣誉”。伴侣成为自我的“镜”与“灯”还体现在弗雷什曼身上,作为一个被抛入世的少年,编织着崇高的情感之网,投注无限力量的向往并从中汲取宗教式的抚慰。形而上学式“大写的爱情”将他圈定在崇高价值的光晕下,以便逃离有限、非严肃的领域。他作为现代版特里斯丹,手握丘比特之箭,幻想极端挑剔的女大夫对自己的欣赏成为照亮他的一束强光。当他瞥见伊丽莎白美妙的肉体时,他遇见的是站立在死神之门的“爱情”,美丽或丑陋轻若鸿毛,爱情只有唯一的标准——死神,这“如死亡一般伟大”的爱使他更感强大。
“大收集者”于性爱游戏中渴求获得不可想象的刺激与不可预见的存在之轻。无论是沉溺于其中的哈威尔、马丁,还是爱德华。爱德华将爱情划入“可自行决定的”严肃范畴中,用近乎虔诚的态度对待爱情。令他困惑的是,阿丽丝对他的接受建立在自己殉道的传奇新闻上,而这件宗教外衣只是作为不得已的谎言披在了爱德华的身上,将他戏剧性地卷入生活的荒谬境况,他对爱情的严肃意义产生质疑,其重要性与他付诸实践的效力完全不相称,相反,性行为的发生如此容易和自然,显得无意义。他厌恶地赶走阿丽丝这个“漂亮身体”之后,不仅没有因此而厌恶“游戏的爱”,反而更加渴望与熟练于收集游戏,他从爱情的严肃领域滑入大收集者世界。
2.“大收集者”向“大征服者”的回归
然而,“大收集者”追寻的是欲望的永恒再生,是对无限的另类想象。
在《哈威尔大夫二十年后》中的哈威尔,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魅力光环黯淡失色,无论是路过的姑娘、还是做水疗的女护士,都对他视而不见,他总是处于“丢脸状态”。然而,当他的妻子,年轻漂亮的女演员,站在他身边并同他亲昵时,他重新获得了失去的可见度,心中便涌现对她浓郁的爱,他的身体变成著名女演员的“等同物”,再次赢得“机遇和强健姑娘们的宠爱”。然而,哈威尔在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在准备着逃脱她。哈威尔意识到自身及流传的轶事都必然会遵循衰老和遗忘的规律,恐惧自身被遗忘、被模糊。生命终将衰竭,他面对自身的有限,唯有投身于爱欲,由它们将青春与年龄连接在一起,追求永不熄灭的欲望,并在其中抵抗遗忘。
其中的记者,请求哈威尔帮他鉴定自己深爱着的女友,动机在于获得大师对自己趣味的赞许,他并不在意女伴的形象,而是她在他人眼中的评判。哈威尔具有敌意的评价,使不安询问的年轻人陷入失望,他得出女友毫无价值、无趣且不美的结论并离开她,即使他仍真挚地爱着她。他追随“高见”掀开了女大夫的裙底,滑稽地咀嚼着她平庸外表下“神秘的美”,这一称赞出自哈威尔之口。年轻人因其取胜的速度、交欢中的女人、哈威尔的才华感到心醉神迷,幻想着自己正在成为像哈威尔一样的“高手”。
《永恒欲望的金苹果》中的马丁,为自己树立一面“永远追逐女人的旗帜”,他将追逐简化为“标定”“挂钩”等卖弄技巧的行为理论,就像每日必行的宗教仪式,追逐本身成为终极目标,这面旗帜象征着马丁建构的某种生命秩序或绝对价值,他将自己装束为永恒欲望的金苹果。
《让先死者让位于后死者》中,男主人坚持引诱与之有过一次艳遇的寡妇,即使对方年长得多,他仍不惜克服自己对她身体的厌恶与其交欢,只是为自己的 “生命密度”寻找一个证据,这位女客抽象化为曾经逃脱他的一切,成为生命永恒的意义。
四、结语
昆德拉的小说聚焦于被遗忘的“存在”,在人类的具体生存和偶然性中探索存在的可能性。在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下,现代人陷入虚无主义危机,现代所张扬的乐观主义,即通过人类理性与科学改变世界与建立美好未来,其与现实的矛盾和冲突使现代人陷入生存的焦虑、破碎与虚无中。个体不再能够栖息于任何宗教的或形而上学的虚幻光圈,是彻底的无遮无蔽的状态。以往承载个体“生命之重”的先验价值成为谎言,现代人在虚无中急于寻求新的替代物。
小说集《好笑的爱》聚焦于爱情,看似现代人深陷于爱情的严肃与非严肃范畴的二元对立,实则是在有限与无限之间挣扎,爱情扮演着个体超出自身有限性的媒介,成为此在抵达无限的桥梁。昆德拉在文本中演绎着现代人在爱情领域如何面对有限与无限的终极悖论。在此悖论下,小说人物呈现为“大征服者”与“大收集者”的辩证关系,前者向后者滑落的同时,后者在悄悄回归前者,展现出对无限的另类想象。尼采自理性主义传统转向对现世、此岸、现时的关注,前者是对于“美好的未来世界”的虚幻建构,对超越、来世的关注;而后者认为个体只能认清和直面自我的处境,不再包庇、辩护和自怨自艾,立足于自身去寻求自我超越的可能性。海德格尔认为本真的存在应先行到死,认清此在“丧失在常人之中的日常存在[8]210”,不再沉沦于日常种种事务的操劳或操持,“面对由畏敞开的威胁”确知它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