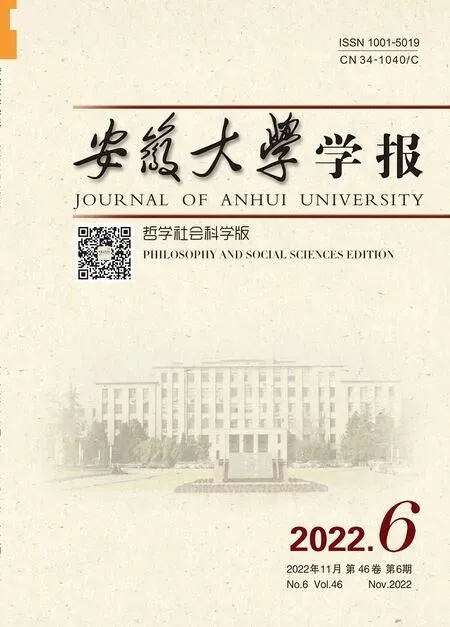论布鲁德尼的青年马克思之“证成难题”
——兼对其的批判性回应
钟晨宁
当代西方马克思研究中作为资本主义批判新支点的自我实现(Selbstverwirklichung;self-realization)问题的凸显(1)在伍德、佩弗、埃尔斯特、凯·尼尔森等当代西方马克思学者的论域中,马克思自我实现思想的重要性逐渐得到强调,并被视为重构马克思批判性理论的重要思想资源。,是随着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对“绝对贫困现象”的大规模消除而形成的。相关学者试图重构马克思理论,将马克思谴责资本主义的根源重新锁定为“它阻碍了人的发展和自我实现”(2)乔恩·埃尔斯特:《理解马克思》,何怀远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80页。。其中,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布鲁德尼(Daniel Brudney)强调了马克思在1844到1845年的青年时期对自我实现概念的诠释,并且认为该时期的马克思遭遇了“证成难题”(The Problem of Justification)困境,即马克思使用规范性预设同时拒斥规范性证成的手段而难以自洽。布鲁德尼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把罗尔斯的“反思平衡”法“补充”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规范性批判的论证手段。然而,该方案过度描绘了自我实现思想的主观信念维度,显著忽视了马克思自身的理论特色。该难题尚未得到国内学界的关注,也缺乏对有效化解路径的讨论。基于此,本文一方面将致力于阐释青年马克思“证成难题”的逻辑理路,这是当代国外马克思学试图将“罗尔斯要素”引入马克思主义的新型案例;另一方面,本文将从三条路径对布鲁德尼的解答方案进行批判性回应,从而拓宽源自马克思本人“历史辩证法”的解释深度,将马克思的自我实现思想纳入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资源。
一、何谓青年马克思的“证成难题”
在论述人的本质的思想史传统中,劳动的作用曾长期被低估甚至忽略。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凭借异化劳动概念批判资本主义是其思想发展过程中重要的闪光点。马克思创造性地看到了劳动对实现人本质的关键作用,通过自由自觉的劳动,人实现了自己的真实本质。“类本质”由潜能转化成了现实性,这就是自我实现的过程。然而,资本主义私有制系统性地扭曲了劳动过程,使其在现实生产活动中表现为一种与人类本质相违背的异化劳动。异化劳动构成了对人的“类本质”的违反。任何从制度上阻碍恰当地实践自由自觉劳动的社会,都将是一种坏的社会。既然青年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阻碍了人的自我实现并由此断定它是一个坏的社会,那么他必然拥有一个对真正本质的规范性预设。但问题是,我们在资本主义社会环境中如何证成这一真实本质的合理存在?这构成了布鲁德尼提出“证成难题”的理论背景。
布鲁德尼认为1844年的马克思侧重从“必要劳动”的角度论述自我实现。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主要指向的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的必要劳动遭到了强烈的异化,因此,马克思在此时“强调的重心在于改变主体与必要劳动的活动和产品之间的关系,而非削减主体所必须从事的必要劳动量”(3)丹尼尔·布鲁德尼:《马克思告别哲学的尝试》,陈浩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74页。。可见,1844年的马克思认为人在本质上是某类与物质世界打交道的存在,而且我们要通过特定的劳动方式才能实现我们真实的类本质特征。同时,布鲁德尼凸显了这一时期马克思自我实现概念中所蕴含的“主观信念”维度。马克思所认为人的自我实现活动,是指从事必要劳动的活动。但是对于这一活动的准确描述不能仅仅局限于劳动者的客观劳作过程,还应当强调劳动者所秉持的特定目标和信念。正是后者,才构成布鲁德尼意义上马克思自我实现概念与资本主义异化劳动过程的核心区别。马克思在描述人的自由自觉劳动时,确实侧重于将其描述为作为“类成员”身份的生产活动。例如,马克思在《穆勒评注》中批判异化劳动只是个体追逐私人利益的手段,使得市场主体陷入相互竞争与欺骗的主体间关系中。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下“我是为自己而不是为你生产,就象你是为自己而不是为我生产一样”(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4页。。个体生产的目标是积累财富,他人的需求能否通过我的生产而得以满足,对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个体是无关紧要的。这使得劳动生产出来的产品也只是物化的、异己的私利,而不是证明人与人之间存在类本质联结的共同生产与共同消费,这就造成了“不是人的本质构成我们彼此为对方进行生产的纽带”(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34页。的现象。这也是《手稿》中人同人相异化的一面。
由此,布鲁德尼尤其强调青年马克思自我实现概念的一个重要面向:真正的劳动中主体必须秉持着“为他人生产”的特殊信念,他人对该产品的消费是“成全”(complete)我“类本质”的必要环节。在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条件下,尽管生产者同样是为他之外的他人生产商品,但是他人仅仅是我谋取私人利益的对象,并不构成协助我实现“类本质”目标的群体。但是,在共产主义自由自觉劳动的条件下,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必然存在一个相互关联起来的“类意识”,即他们秉持着“类成员”身份而进行生产。因而并非是我谋取个人利益,而是他人是否从我生产的产品中获得享受与愉悦才是我从事生产劳动的真实目标。布鲁德尼牢牢抓住了这一点,相比较资本主义生产下个体互不关心的社会现象,“在共产主义条件下,劳动者认为彼此之间的关系包含这些目标和信念,并将之视为相互成全的关系,是理性的行为”(6)丹尼尔·布鲁德尼:《马克思告别哲学的尝试》,第225页。。类本质的实现并非依靠主体的孤立行动,而是仰赖社会中劳动主体的相互配合。布鲁德尼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这类“为他人生产”的特殊信念很可能是自然而然就存在的,因为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中的个体将自觉且清晰地认知到他所处的社会关系。但是,布鲁德尼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主体,如何才可能获取这种“为他人生产”的特殊主观信念?
在这一点上,布鲁德尼认为青年马克思将会面临论证手段上的无力,其根本原因是马克思在这一时期持有“告别哲学”的立场。青年马克思从青年黑格尔派脱离出来的关键特征是,他拒绝采取一种抽象的思维方式来解答理论问题,转向消解问题的客观根源的实践方法论见解。这也是布鲁德尼意义上马克思“告别哲学”的尝试。然而,布鲁德尼认为马克思告别哲学的做法迫使其在这段时间内无法完成对资本主义的规范性批判。他认为,马克思预设了一个与资本主义劳动个体的生活经验所完全不同的人本质理解,其蕴含了“为他人生产”的特殊主观信念。同时,马克思认为人可以在与资本主义异化劳动不同的自由自觉的劳动方式中去实现它。但是,马克思杜绝了借助哲学思考来改变劳动个体信念的方式,认为人的主观信念只可能来自当前存在的社会生活经验。悖谬的是,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虽未表现为马克思意义上人的自我实现过程,但对于劳动个体而言这是唯一的真实经验。
这就出现布鲁德尼意义上的“证成难题”,马克思无法合理地说明自己对劳动和未来共产主义的“本质”设定,对于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个体而言是可信的。由此布鲁德尼认为马克思在1844年对自我实现的设定,对于身处资本主义中的个体而言会产生如下效果:“如果他所说的是对的,其将显得不那么令人满意,并且还可能是武断的。”(7)丹尼尔·布鲁德尼:《马克思告别哲学的尝试》,第241页。马克思意义上人的自我实现观念,由此对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个体是完全不可信的。需要补充的是,布鲁德尼认为马克思的“证成难题”不止发生在1844年,即便是在引入“实践”概念的1845年《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问题仍然是存在的。布鲁德尼认为,我们常常认为“实践”就是联结当下资本主义与未来共产主义的桥梁,但问题依然是,推动劳动阶级决定参与革命的“第一步”(first step)的动力在哪里?(8)布鲁德尼借助了布坎南的“集体行动难题”来说明这一点。布坎南认为革命也面临着“搭便车”(free rider)现象,因此深受资本主义社会影响的理性和私己个体没有迈出革命活动第一步的动力。Cf. Allen Buchanan, Revolutionary Motivation and Rationality, Marx, Justice and History, eds. by Marshall Cohen, Thomas Nagel and Thomas Scanl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264-287.如果说劳动者能够认识到并且能够在非利己的状态下激发这一步,那么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异化是不够深的。但是马克思的目的正在于说明社会存在对主体信念的“深层次”异化作用,因而,“如果异化确实是深层次的,那么劳动者就永远不会(如果他们是理性的)迈出必要的第一步”(9)丹尼尔·布鲁德尼:《马克思告别哲学的尝试》,第278页。。在布鲁德尼看来,“证成难题”是青年马克思整体思想论述中的重大困扰。
事实上,布鲁德尼关注的是个体信念转变的机制和动力问题。他的“证成难题”并不削弱马克思对当前资本主义的批判效力,只是质疑未来共产主义信念的证成问题;其并不担忧共产主义社会中共产主义信念的自然生成,只是质疑资本主义社会中如何可能产生“近共产主义”信念;其也并不评判马克思方案本身的合理性或非合理性,只是质疑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体向共产主义信念转变的机制和动力问题。可以说,这是一个来自马克思主义学者“内部”的且严肃的理论挑战,而不是某种意识形态的片面攻击。然而,布鲁德尼的推断设定了马克思在道德信念上的特殊立场,这也令其最终转向对马克思学说的道德哲学补充。
二、布鲁德尼的方案:罗尔斯式的道德哲学的“补充”
对于布鲁德尼来说,青年马克思陷入了借助“规范性”又否定“规范性”的困局。在他看来,马克思缺乏足够的手段去敦促当下存在的个体合理接受并认同他关于人性本质及自我实现的积极设定。布鲁德尼声称,马克思的证成难题“源于他既想批判资本主义,同时又想避开渗透在日常生活表象之下的那种抽象理论,还想宣称当下日常生活中所显现的人的本性与人的真正的本性完全不同”(10)丹尼尔·布鲁德尼:《马克思告别哲学的尝试》,第18页。。但是,布鲁德尼如此诊断其实包含了一个重要的预设:他将马克思理解为在“道德信念”方面的“强决定论”者,即道德信念很难摆脱社会制度的影响而拥有独立转变的动力。在许多道德哲学的讨论中,不偏不倚、排除了任何个人私己意见和偏见的影响的观点,才会被严肃地视作正当的道德信念的构成部分。这一见解认为人很大程度上是在与社会影响相隔离的情况下,通过理性进行独立判断。布鲁德尼将这类道德主张称为“隔离式立场”(insulated standpoint)。但是,马克思不可能接受“隔离式立场”。根据他的判断,道德信念不可能脱离社会影响,甚至本身就是制度操控的产物。在《形态》中,马克思犀利地指出:“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0页。。这是一种对主体信念的社会学解释立场,即我们的信念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社会制度的影响。
由此,布鲁德尼根据这种影响程度的深浅,区别了两类观点:“结构性论点”(the structural thesis)与“社会学论点”(the sociological thesis)。而后者又可以被区分为“强社会学论点”和“弱社会学论点”。“结构性观点”认为信念没有任何独立存在的依据,信念仅仅是对客观社会存在的“反映”而已,类似于某种程度的“机械反映论”。因此,人们的信念并不具备对社会现象的真理判断能力,它只不过是一种“副现象”(epiphenomena)的表达。而“社会学论点”则认为,人们的信念受到了社会的“歪曲性”影响。这种论点只是揭示了信念的社会影响要素,但并没有否认信念摆脱社会影响的可能性。事实上,如果人意识到自己的某种信念是不正确的且是遭到社会制度操控的,就仍有能力去改变它。在“社会学论点”中划分强与弱的标准就是:“强社会学论点”会认为,“所有的道德信念都可能是制度性洗脑的结果”(12)丹尼尔·布鲁德尼:《马克思告别哲学的尝试》,第362页。;而“弱社会学论点”会认为,“由于人们目前的信念是社会制度的产物,因而是可疑的”(13)丹尼尔·布鲁德尼:《马克思告别哲学的尝试》,第362~363页。,但部分独立的道德信念仍然是可能存在的。
那么,马克思应当属于哪一类呢?布鲁德尼认为,马克思认可的是“强社会学论点”。一方面,马克思不能被错误地理解为持有“结构性论点”。布鲁德尼认为,马克思的哲学显著区别于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他不会接受观念仅仅是客观存在的机械反映。但是另一方面,马克思确实认为道德信念是受到社会存在最强烈影响的观念要素,在《形态》中,马克思总是将道德与意识形态、宗教等观念并列,把道德信念看作资本主义制度下系统性扭曲的产物。如此一来,我们就能够更加清晰地表达“证成难题”中的症结:马克思一方面认为存在着与资本主义社会中表现的现实人性所完全不同的真正的符合人本性的“类本质”;但另一方面,马克思又强调人的道德信念受到当前社会制度的“强”影响。布鲁德尼据此推导,处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体只能接受资本主义现实经验的“强”影响,而没有动机和动力开启向共产主义信念的转变。正是在这里,布鲁德尼才最终说出马克思“告别哲学”的失败。青年马克思“告别哲学”的立场,导致他拒绝“隔离式立场”的合理性,转向对道德信念的“强社会学论点”解释;但也恰恰由于这个转变,导致他无法为共产主义信念提供有力的规范性证成手段,他难以说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体接受他对类本质的哲学设定。皮特曼(John Pittman)在为布鲁德尼这本书写的书评中也点明了这一点:“这本400页的书回答了布鲁德尼的题目中隐含的问题——马克思告别哲学的尝试成功了吗?——答案是不。”(14)John Pittman, Review: Marx’s Attempt to leave Philosophy, Science & Society, vol. 66, no.2(2002), pp. 282-287.在布鲁德尼笔下,青年马克思似乎陷入了“自我吞噬”的危机,他在给出规范性预设的同时又反对任何证明规范性的手段。
进一步,青年马克思有什么办法完成对资本主义的规范性批判呢?布鲁德尼给出了他的方案,即注入包含“隔离式立场”在内的道德哲学的抽象证成手段。布鲁德尼认为,最合理的是采纳“弱社会学论点”。该观点既可以提醒我们应当谨慎留意制度的影响,必须要清楚地识别我们的道德信念受到统治阶级利益影响的歪曲可能;同时,该观点也认可人仍然保留了道德信念反思的余地,正是借助“隔离式立场”的抽象思考,我们迎来了使自己的道德信念摆脱资本主义社会错误观念影响的契机,并由此才能完成对资本主义的连贯性批判。这一方案在布鲁德尼的另一部作品《罗尔斯与马克思》中得到更清楚地表达。作为罗尔斯的亲传弟子,布鲁德尼比较了罗尔斯和马克思在证成“人的观念”上的区别,他认为在马克思那里存在“证成难题”,而当罗尔斯将人在本质上设定为自由和平等的理性存在者时,他也面对着类似的困境:如何说明这种对人的本质的设定,不也是人们在一个特定社会中成长而带来的特殊信念,或不也是一种被扭曲的结果。但是,罗尔斯可以利用“反思平衡”的方法成功应对这一难题。布鲁德尼认为“反思平衡”的方法旨在消除社会中受到阶级利益影响而扭曲的私人判断,最终确保所有的不一致之处都能被消除,以达成一个所有人可以接纳的、更佳的道德信念。“反思平衡”法是一种“弱社会学论点”的充分体现,它既警惕来自社会影响的扭曲信念的干扰,又可以赋予主体抽象空间去思考真正合理的道德信念。所以布鲁德尼在比较了罗尔斯和马克思之后,自信地认为“反思平衡最终是一种可接受的证成方式”(15)丹·布鲁德尼:《罗尔斯与马克思》,张祖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46页。。
布鲁德尼最终开出的“药方”正是,利用罗尔斯道德哲学的资源去“补充”青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规范性批判。他想让马克思重新回归“道德哲学”的思考领域。布鲁德尼的这一做法实际上代表了近些年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很重要的发展动向:在检视马克思自身的伦理学资源的基础上对之加以重构。作为英美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接棒人,布鲁德尼延续了这一学术群体的理论自觉:在大规模贫困业已消除的当代西方社会,“普遍的贫困”这类传统批判资本主义的支点不再可能的情况下,我们应当依靠怎样的信念推动我们持续批判资本主义。由此,以柯亨(G. Cohen)为代表的分析马克思主义者转向了对马克思道德信念的重视与重构。
布鲁德尼的特色在于,他挖掘出青年马克思对自我实现的重视,并认为资本主义阻碍人的“善好生活”(good life)的实现可以成为当代批判资本主义的新支点。然而,这一新支点的竖立必须借助一些规范性工具的使用,而青年马克思持有的“反对哲学”的激进立场让他无法拥有这些工具。所以从结果上来说,将罗尔斯“反思平衡”方法“补充”进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似乎是一个“完美”的融合。对于布鲁德尼来说,青年马克思对于哲学方法论上的革命存在失败之处,让马克思重新回归被他抵触的“隔离式立场”,看起来是更佳的学术选择。但是,布鲁德尼的讨论停留于青年马克思1844到1845年的自我实现概念,这种戛然而止的失败宣判恰恰错失了这一概念在马克思思想史发展语境中更深刻的特性。
三、喧嚣中的回应:反驳“证成难题”的三条理路
既然布鲁德尼提出了一个尖锐的学术问题,那么我们同样需要认真且严肃地给予回应。对于布鲁德尼“证成难题”的回应方式有三种:第一种是质疑布鲁德尼在“证成难题”中的推论“预设”,即怀疑马克思是否如布鲁德尼所说支持“强社会学论点”,进而否定任何意义上道德信念的独立性;第二种是质疑布鲁德尼的“证成难题”的“适用性”,即布鲁德尼对自我实现的规范性理解并不适用于青年马克思,他忽略了青年马克思自我实现思想的理论特色;第三种回应是质疑布鲁德尼的“证成难题”错失了马克思自我实现思想的“发展性”。青年马克思“告别哲学”的尝试不是失败的,而恰恰为他以后解决“证成难题”提供了有益的启迪。本文接下来力图说明:第一种回应虽有效但不够充分;而第二种回应和第三种回应将会有力反驳布鲁德尼的“证成难题”。
(一)“预设”回应
第一种回应实际上指明的是,马克思可以是“弱社会学论点”的支持者,马克思自身的学术资源也可以提供一套规范性工具的连贯使用。这一思路的关键在于证明,马克思仍然对部分道德信念持有非意识形态式的认知,肯定部分理性的道德信念能够摆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束缚而推动个体的信念转变。这一思路与约翰·麦克默特里(John McMurtry)、凯·尼尔森(Kai Nielsen)等人对马克思伦理学的构建有暗合之处,他们均认为马克思虽然是从“社会学”的角度解释道德信念,但并非所有的道德信念都是负面义的意识形态,并牢固地受制于当前的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例如,麦克默特里指出将人的意识等同于意识形态是错误的,他切断了将意识形态等同于道德信念的理解模式。麦克默特里认为意识形态“不是人的意识本身,而是公共模式”(16)John McMurtry, The Structure of Marx’s World-view,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127.,是关于我们自身的公共观念和公共表达。尼尔森则进一步沿着麦克默特里的思路,认为社会中既可能存在受制于资本主义阶级利益的公共观念表达(即意识形态),也可能存在其他私人的道德意识,这并不等同于意识形态(17)凯·尼尔森:《马克思主义与道德观念》,李义天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53页。。尼尔森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有能力理性地评价道德规定并相信道德进步”(18)凯·尼尔森:《马克思主义与道德观念》,第159页。。我们可以识别“被蒙蔽的”意识形态观念和“没有被蒙蔽”的其他道德信念,部分道德信念可以拥有非意识形态的特征。
然而,这种回应思路在表面上可以反驳布鲁德尼的“预设”,但在结果上却陷入了将马克思与罗尔斯“同构”的误判,它在实质上并没有超出布鲁德尼的理解视域。例如,尼尔森承认在所有社会中都可以具有一般性同意的“普遍的善”和“普遍的恶”原则,这可以借助“反思平衡”的方法识别出来(19)凯·尼尔森:《马克思主义与道德观念》,第152~153页。。在《从事实非敏感性中拯救政治理论》中,尼尔森甚至推崇罗尔斯的“反思平衡”法(20)凯·尼尔森:《从事实非敏感性中拯救政治理论——对G. A.柯亨政治哲学方法论的批评》,《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5期。。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与罗尔斯的方法存在着不容忽视的根本性差异。其一,马克思不会同意存在脱离社会背景的抽象思考的可能;其二,马克思的“抽象的方法”是对现实经验的结果的提炼,而非反过来是思考社会的前提;其三,马克思理解的普遍性绝不是脱离“特殊性”的“抽象普遍性”。考虑到马克思和罗尔斯理论性质的差异,“反思平衡”法很难融贯地置于马克思的名下(21)李志、汪志坚等国内学者也反驳了西方学者将马克思与罗尔斯融合的倾向。参见李志《论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方法——基于对分析法与反思平衡法的批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17年第2期;汪志坚:《对融合限度的反思——驳近年来西方学界融合马克思和罗尔斯的倾向》,《哲学研究》2019年第7期。。马克思与罗尔斯在道德哲学上生硬的融合,无法凸显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在解释道德信念上的特性与优势。
(二)“适用性”回应
由此我们转向对第二种回应思路的考察,即布鲁德尼的“证成难题”究竟是否适用于青年马克思?2002年第1期的《政治理论》(PoliticalTheory)杂志,刊登了露丝·阿贝(Ruth Abbey)与布鲁德尼在该问题上的两篇交锋文章。布鲁德尼在回应中进一步凝练了自己的核心关切:“在社会革命之前,马克思有什么理由相信这种目前未实现的潜力是一种真正的人类潜力,并确实揭示了善好生活的内容?”(22)Daniel Brudney, Justification and Radicalism in the 1844 Marx: A Response to Professor Abbey, Political Theory, vol. 30, no. 1(2002), pp. 156-163.但是也正是在这点上,阿贝“言中”了布鲁德尼“证成问题”中的要害:当布鲁德尼过度强调“为他人生产”这类主观信念是区别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的时候,他割裂了“善好生活”的主观信念和客观条件之间的关系。自我实现及其所实现的“善好生活”的主观信念和客观条件并不是像布鲁德尼所言是“分离”的,对“善好生活”的主观信念的改变不能脱离客观条件的改变。进一步,阿贝认为布鲁德尼忽视了1844年马克思关于“私有财产”的讨论,认为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区别的主要特征并非是“为他人生产”这一主观信念,而“私有财产,资本主义的一个客观和基本特征,使得资本主义成为对善好生活的诅咒”(23)Ruth Abbey, Young Karl Does Headstands: A Reply to Daniel Brudney, Political Theory, vol. 30, no. 1(2002), pp. 150-155.。令布鲁德尼感到困惑的新的主观信念的获取,实际上并非是青年马克思本身的困惑。对社会经验条件的首要关注,是青年马克思“告别哲学”的重要理论效应。沿着这条批评路径出发,我们就会发现布鲁德尼对青年马克思的自我实现概念存在相当程度的误读。
第一,布鲁德尼错判了马克思自我实现思想的规范性含义。布鲁德尼并未仔细甄别的是,青年马克思的自我实现是一种特殊的规范性立场,它与思辨哲学的传统道德规范性不同。在《手稿》中,马克思的自我实现指向的是可供经验检视的人的需要和感觉的丰富,以及人在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中能力的增强。一方面,马克思“类本质”概念的潜能性,指向的并非是理性或道德信念的进步,而是作为感性存在物的需要和感觉的丰富。资本主义制度阻碍自我实现,在于它阻碍了人的需要和感觉的扩大,甚至将其限制在极其狭隘、粗陋的需要和感觉之下。另一方面,马克思“类本质”概念的现实性,指向的是人在物质生产的发展过程中力量的增强。马克思经典的表述,“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92页。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但是,资本主义的工业体系造就的是人的力量的片面化与机械化的发展,最终使得“机器迁就人的软弱性”(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26页。,人的力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遭到了压抑,甚至于会退化。伍德在这点上抓住了马克思自我实现概念的关键性质。在他的分析中,马克思的自我实现应当归属于“非道德善”(nonmoral goods)的行列,它并不首要指向美善、权利、正义、义务或道德品质,而是指向我们通常与道德评价没什么关系的愉悦、幸福。伍德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基础在于它毁灭了许多重要的非道德性的善,如人的自我实现、生存保障、身心健康、资源共享与自由”(26)W. Allen, Karl Marx,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 129.。马克思的自我实现概念在内容上指向的是处在社会经验视角中的人的需要、感觉、力量的增长,这是与马克思“告别哲学”的方法论变革高度适配的,并不需要“隔离式立场”的道德哲学的反思证成。
第二,布鲁德尼低估了马克思自我实现的客观性条件。布鲁德尼关注的是个体信念转变的机制和动力问题,这导致他将主要的注意力放在了如何证成主观信念的转变维度上。但事实上,青年马克思“告别哲学”的理论动机在于:他认为主体在资本主义制度中面临的是社会制度施压造就的“客观幻觉”(objective illusions),而非通过自己主观能力即可改变的“主观幻觉”。“客观幻觉”不是一种通过理性即可矫正的“认知型”错误,而是与“错误”的社会制度相匹配并在该社会制度下主体自然相信其是公正合理的社会认知状态。青年马克思意识到共产主义信念的获得,恰恰需要消除“客观幻觉”寄居的社会条件。在《形态》中马克思概括了自己理解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9页。皮特曼指出布鲁德尼在整本著作中对这段话保持令人困惑的沉默现象。事实上,皮特曼认为《形态》告知我们由资本主义“这个体系所产生的‘客观幻觉’不能被哲学公式的条用所驱散”(28)John Pittman, Review: Marx’s Attempt to leave Philosophy, Science & Society, vol. 66, no. 2(2002), pp. 282-287.,马克思“告别哲学”的立场使他避免犯下意识形态家们的错误。青年马克思在《手稿》中开启对“私有财产”的批判,从而深入到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如此才真正掌握了消除资本主义对自我实现的客观阻碍的理论方法。所以说,布鲁德尼并没有抓住马克思自我实现思想的客观性向度,这导致他对马克思缺乏规范性证成手段的批判,实际上并不适用于青年马克思的思考语境。
(三)“发展性”回应
我们最后来考察第三种回应,布鲁德尼的“证成难题”是否准确描述了马克思自我实现概念的发展过程?布鲁德尼认为在青年马克思的思考语境内,存在对资本主义阻碍自我实现的两个谴责。第一个谴责来自写作《手稿》时期的马克思,这一时期的马克思谴责“资本主义培育灌输了关于人的本性和善好生活的错误观念,并使得正确观念完全无法实现”(29)丹尼尔·布鲁德尼:《马克思告别哲学的尝试》,第375~376页。。资本主义是在“完全意义”上阻碍自我实现,我们可以把它称作资本主义对自我实现的“完全反对”的一面。第二个谴责来自1845年写作《形态》时期的马克思,这一阶段马克思主要是从“自主活动”(self-activity)的角度来论述自我实现。马克思侧重于强调在共产主义生产条件下个体将会打破“被迫分工”的局限性,在任何活动领域中都可以充分自主自由地发展自己的能力。布鲁德尼认为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批判转向了经验性的层面,即资本主义社会在现实中只实现了少数人而非所有人的“自主活动”。布鲁德尼将这一批判称作“资本主义违背了分配正义的要求”(30)丹尼尔·布鲁德尼:《马克思告别哲学的尝试》,第376页。。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作资本主义对自我实现的“局部性反对”的一面。在这两个谴责的转换中,布鲁德尼暗示了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效力的下降,他显著偏好1844年马克思的规范性批判。在布鲁德尼看来,马克思由规范性转向经验性的视角,这使得“《形态》对于善好生活的论述,与非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之间并无本质的不同”(31)丹尼尔·布鲁德尼:《马克思告别哲学的尝试》,第396页。。1844年的马克思由于对与资本主义社会完全不同的规范性预设的强调,显得更有特色。布鲁德尼因此也认为“1844年的马克思将会成为哲学上最为恒久的马克思”(32)丹尼尔·布鲁德尼:《马克思告别哲学的尝试》,第396页。。同时,布鲁德尼认为两个谴责难以避免“证成难题”。第一个谴责需要道德哲学的规范性证明以推动道德信念的转变,第二个谴责需要借助“分配正义”等政治哲学概念证明资本主义的分配不正义。但是,马克思对“道德”“正义”等抽象理论的激进反对,导致他无法完成对资本主义的规范性批判。虽然布鲁德尼没有着墨于1845年之后的马克思,但他明显偏爱于强调规范性的马克思,甚至认为马克思在《形态》后向“经验性”视角的转向是一种哲学上的退步。
然而,布鲁德尼错误理解了马克思的经验性概念,他将马克思的经验性原则矮化为“依靠日常经验和对日常生活的最为简单的观察”(33)丹尼尔·布鲁德尼:《马克思告别哲学的尝试》,第305页。这类直观式理解。在《形态》中,马克思通过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为经验性注入了历史性的向度,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对传统哲学的重要突破。布鲁德尼对马克思经验性理解上的错置,使得他忽略了马克思自我实现思想中最为深刻的历史性向度。在笔者看来,马克思对自我实现最合理的解答是它的历史性向度。自我实现的历史性向度表明,一方面资本主义对于个体的需求、感觉、力量的扩大与丰富是有一定历史积极意义的,这使得马克思突破了《手稿》时期认为资本主义对自我实现只有“完全反对”的一面;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仍然不能满足个体对更高层次的需要、感觉和力量的欲求,这导致资本主义在根本意义上仍然是个体的充分自我实现的阻碍。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体实现“更高需要”的手段匮乏,我们可以将之称为资本主义对自我实现的“充分性反对”。
这一思路最早在1847年《雇佣劳动与资本》中得到体现。马克思将无产阶级的生存比作小房子,而将资产阶级的生活比作宫殿。资本主义社会也许会提供甚至还会改善小房子的生存环境,但旁边的宫殿则会更快地扩大,从而令小房子的居住者感到无比压抑。因此,当我们衡量需要和享受时,不是以满足它们的基本物品为尺度,而是以社会为尺度。马克思凸显出需要和享受的“相对性”,从而第一次揭示出它们的历史性向度:“我们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会性质,所以它们具有相对的性质”(3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729页。。
自我实现思想的历史性向度在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得到了更加充分的体现。马克思肯定了资本主义对于自我实现的历史积极意义,他谈道:“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不就是在普遍交换中产生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3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7页。这是对资本主义条件下个人需要、感觉等的扩大的描述。马克思继续谈道:“财富不就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的统治的充分发展吗?”(3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37页。这是对资本主义条件下个体与自然之间物质交换的力量增长的描述。另外,马克思在论述“社会三阶段论”的过程中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可以为“自由个性社会”提供前提和基础,这也是因为以交换价值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也将生产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对比马克思在《手稿》时期将资本主义视作自我实现的“完全反对”,马克思此时已经充分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历史积极性特征。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塑造了一个更充分的自我实现的潜能。
然而,这一更为充分的自我实现的潜能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无法转化成现实性,这才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更深刻的批判。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写作时期已经可以熟练地透过“剩余价值”概念批判资本主义的实质,它指出资本主义创造人的需要、感觉和力量扩大的手段恰恰是劳动阶级处在剥削状态下的剩余劳动。正是社会中居于大多数人地位的劳动阶级源源不断地为社会提供剩余劳动,导致社会虽然迎来了更充分的自我实现的潜能,但这一群体充分实现自我的手段仍然是匮乏的。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并没有使得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的福利分享给所有人,人本身发展的光明景象的背后隐藏着血淋淋的剥削事实。资本的增殖逻辑导致资产阶级不断占用工人的剩余劳动,拒绝工人拥有供个性发展的自由支配时间。所以马克思明确表示,只有在“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一般财富发展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发展的条件”(3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97页。下,个性才可能得到真正自由的发展。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并且降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使得所有人都享有发展个性的自由支配时间,是马克思意义上达成更充分自我实现的必要条件。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可以摆脱片面发展的制约,“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3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37页。。
基于以上分析可见,“完全反对”“局部性反对”“充分性反对”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阻碍自我实现的三个视角。它们加总在一起构成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整体诊断。在其中,“充分性反对”呈现了马克思自我实现的历史性向度,这也是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体现。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生成了更充分自我实现的潜能与其实现之间的矛盾,这是我们当代仍然反对资本主义的重要理由。同时,这也形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下频频遭受自我实现失败的个体产生转向共产主义信念的客观动力。布鲁德尼擅长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令其倾向于给出一个“完全肯定”或“完全否定”的二选一式答案,因而他错误地陷入了对1844年马克思规范性批判的过度强调中。可以说,马克思透过自我实现概念批判资本主义的力度不是下降的,而是渐进深入的。自此,我们可以充分地回应布鲁德尼的青年马克思“证成难题”: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体信念的转变,并不是受道德哲学的规范性论证所激发,而是源于资本主义社会在自我实现层面上的历史性矛盾。马克思不需要任何意义上“隔离式立场”的道德哲学补充,青年马克思的方法论转变恰恰推动了他对自我实现的客观性和历史性向度的发现。
四、结 语
本文引介了当代分析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中的一个新型问题。与此同时,布鲁德尼的“证成难题”在西方马克思伦理学研究中具有特殊的“推进”地位。在表面上,布鲁德尼的批评与波普尔的批评高度相似,他们似乎都指向了马克思关于人性假设的“非证成性”或“武断”的特征。然而,布鲁德尼与波普尔的出发点是截然相反的。波普尔借此否定了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科学性,但布鲁德尼对马克思的未来设想持有肯定的态度。在其2013年发表的《两种公民友谊的类型》一文中,布鲁德尼甚至认为1844年马克思所构想的“平等的关心/欣赏社会”(an equal reciprocal concern/appreciate society)是比康德“平等相互尊重的社会”(an equal reciprocal respect society)更为可欲的公民伦理方案(39)Daniel Brudney, Two Types of Civic Friendship, Ethical Theory and Moral Practice, vol. 16, no. 4(2013), pp. 729-743.。布鲁德尼的“证成难题”质疑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体的信念转变问题,这是当代西方学者在重构马克思理论的过程中提出的重要学术挑战。这充分反映了当代部分西方学者认真面对马克思文本的一面,这类学术上的探索与争鸣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然而,布鲁德尼对马克思有着较深的误解。布鲁德尼在一次讲座中表示“在规范性思想家这个层面上,马克思在很大程度上被低估了”(40)丹·布鲁德尼:《罗尔斯与马克思》,第86页。。与其说马克思作为规范性思想家的地位被低估了,不如说布鲁德尼没有看到马克思思想中规范性与历史经验性结合的深度。布鲁德尼的“证成难题”之所以不构成马克思的思想困境,原因正在于: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生成是同时蕴含在世界历史的生成与发展之中的。资本主义是历史性的,而人的自我实现也是历史性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贯穿着的自我实现的客观矛盾,使得个体无须“隔离式立场”的道德哲学推动就可开启对共产主义信念的认知转向。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体遭遇的自我实现的失败,源自更充分自我实现的主体潜在形象和在现实中大部分个体缺乏实现手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既是客观性的,又是历史性的,更是当代性的。它会随着资本主义的日益发展而日趋尖锐。马克思对自我实现概念的批判性分析绝不是纯粹道德哲学式的,而是深刻地与其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结合在一起。马克思得益于他在青年时代杜绝“隔离式立场”的态度,坚定不移地在受社会影响的具体的个体境遇中找寻自我实现的可能。自我实现的客观性和历史性向度给出了布鲁德尼“证成难题”的科学答案,我们可以自信地回应:青年马克思告别哲学的尝试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