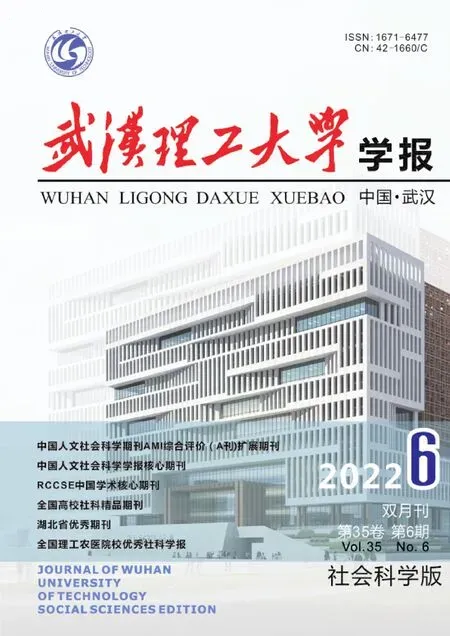尼采是形而上学的完成者吗?
——基于海德格尔释义的权力意志与永恒轮回视角
王一楠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0872)
一、 “尼采”作为海德格尔反形而上学的最终形象
海德格尔在其著作《尼采》中,将尼采的“权力意志”与“相同者永恒轮回”思想释义为“存在者的存在特征”和“存在者的存在方式”,至今仍对国内外学界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海德格尔再创作的尼采解释,一方面,确实让尼采以一位严肃哲学家的身份进入哲学的“体系大厦”,开始让后来的学者们认真对待他的思想,另一方面,海德格尔将尼采的权力意志解释为“无条件的主体形而上学”,让其作为“形而上学的完成者”,也就彻底失去和误解了尼采哲学“超出”传统形而上学的部分,海德格尔的这一解释也饱受后来法国哲学家们的批判。不论是海德格尔“捆绑”尼采,还是法国哲学家们“激活”尼采,尼采无疑都在他们的思想中发挥着“工具箱”①的重要作用。海德格尔虽没有明确承认过尼采对其思想所产生的影响,但尼采在海德格尔思想进程中,“工具箱”的地位却显而易见,即便这个“工具箱”大部分时间是海德格尔拿来批判形而上学的工具。在海德格尔的视域中,形而上学的本质以颠倒的形式出现在尼采哲学中。尼采哲学以最极端的无条件主体形而上学完成了形而上学中最后一种形式,尼采成了西方形而上学终结处所显现出来的那个形象。
那么,尼采又是怎样把形而上学带向了完成呢?在尼采的意义上,他指出西方形而上学的历史就是欧洲虚无主义的历史,形而上学所规定的最高价值自行贬抑,进而消解了由最高价值规定的一切价值。既然最高价值其规定作用的“真实世界”失效了,那么被规定的“虚假世界”也不应当存在了。尼采需要解决的是,虚无主义被其揭示出来,并将延续数百年所带来的等级秩序与价值秩序的问题。简而言之,尼采自认为首先指出了形而上学的虚无主义本质,形而上学随之解体,而着眼于形而上学解体后的“超善恶”和“未来哲学”的重建问题;而海德格尔则着眼于尼采作为“形而上学完成者”。值得注意的是,海德格尔给予尼采“形而上学完成者”的这个“称谓”,本身就充满歧义,既然海德格尔把尼采作为形而上学的完成者,那么尼采是形而上学的终结者,在某种程度上,尼采哲学就必然超越和克服了某种形而上学的本质。可从海德格尔释义的整个尼采哲学来看,“形而上学完成者”的这个“称号”对尼采而言可谓是“明褒暗贬”。虽然海德格尔认为尼采把形而上学带向完成,形而上学历史的本质在尼采哲学那里穷尽了最后的可能性。但海德格尔依然认为尼采哲学根本上并没有克服形而上学,其思想仍然限于形而上学的基本逻辑,主要表现为:(1)尼采的哲学是对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的回应;(2)尼采的哲学是“颠倒的柏拉图主义”;(3)尼采的哲学是主体性的形而上学。本文以下将分别简述这三个方面。
第一,关于尼采的哲学是对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的回应。海德格尔说:“从一开始,相同者的永恒轮回与权力意志就被把握为关于存在者整体的本身的基本规定,而且,权力意志被把握为历史终结处对“什么—存在”(Was-sein)的烙印,而相同者的永恒轮回被把握为对“如此—存在”(Daβ-sein)的烙印[1]697。按照海德格尔给予尼采的形而上学立场,尼采给出的这两个答案是对西方思想中主导问题的回应。权力意志规定的是存在者之相态(是什么),相同者永恒轮回规定的是存在者之存在方式(如何存在)。其分别回应了形而上学开端中以巴门尼德“存在者存在”和赫拉克利特“存在者生成”的两大基本问题。在“存在者存在”中,存在者以权力意志的相态被固定以来从而获得存在;在“存在者生成”中,存在者以相同者永恒轮回的方式存在。二者本质上是共属一体的,因为它们表述的是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存在者以何种相态和何种方式存在。上述海德格尔的解释,只能表明海德格尔是基于存在者整体的角度来思考和解释尼采的“权力意志”和“相同者永恒轮回”。
第二,关于尼采的哲学是“颠倒的柏拉图主义”。海德格尔说道:“无论是尼采还是尼采之前的任何思想家,也包括那个在尼采之前首次在哲学上思考了哲学历史的思想家黑格尔,都没有进入开端性的开端之中”[2]492,因为海德格尔认为尼采的思想依然植根于形而上学的基本立场(柏拉图主义)当中。海德格尔认为尼采用他惯用的“颠倒”方式来反“柏拉图主义”,看上去是对这样一种形而上学基本立场的反对,实则这样一种“颠倒的柏拉图主义”依然植根于“柏拉图主义”当中,这种“颠倒”的方式不仅没有消解柏拉图主义的基本立场,反而加强了这种立场。那如何加强了这种立场?海德格尔经常引用尼采《权力意志》的第617条:“为生成打上存在之特征的烙印——这乃是最高的权力意志。一切皆轮回,这是一个生成世界向存在世界的极端接近——此乃观察的顶峰”[2]21。在此,海德格尔认为,权力意志给“生成”打上了“存在”的烙印,把生成“存在化”了,权力意志赋予了永恒轮回存在特性,这就是尼采观察的顶峰。海德格尔基于“柏拉图主义”的立场,认为尼采颠倒了“存在”与“生成”的位置,变成了“生成”与“存在”,这种“颠倒”不仅没有消解“柏拉图主义”,反而是发挥了“柏拉图主义”基本结构中的另一种可能性,巩固和完成了“柏拉图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的《权力意志》617条完整部分,其实被海德格尔有所修改②。海德格尔有意省略了夹在上述两句之间的一句话,其内容为:“精神和感官的双重伪造,以保证这个世界的存在、令人容忍、等同……”。虽然《权力意志》是尼采的未竟之作,其在内容的编排上有一定的任意性,但其每一条表述的意思还是具有一定完整性的。结合尼采权力意志617条的内容,可以明确地知道,精神的伪造指“存在”,感官的伪造指“生成”。能够洞察到这个世界的存在是依赖这双重伪造的尼采,显然不符合海德格尔释义下对尼采是“颠倒柏拉图主义”的“形而上学家”的设定。在这个意义上,尼采提出“上帝死了”,就可以视为对西方形而上学终结的宣言,即在所有领域起规范和约束作用的最高价值失效了,它不仅指向了人类精神伪造的“存在世界”失去了作用,与这个“存在”相对,由感官伪造的“生成世界”也不存在了。尼采在取消“真实世界(存在)”的同时,也取消了“虚假世界(生成)”,根本上取消了柏拉图主义中二元对立的结构。进一步,尼采在解构形而上学的同时,又拒绝再次重建形而上学体系。
第三,关于尼采哲学是主体性的形而上学,可以说是海德格尔释义尼采哲学的根本问题。海德格尔将尼采的“权力意志”视为主体性的形而上学最后一种形式,这个思想标志着形而上学的完成和终结。作为海德格尔批判尼采哲学的最终结论,这个批判必然汇聚着海德格尔所理解的形而上学根基,以及海德格尔理解的权力意志在何种程度和意义上是植根于这个根基的。
海德格尔在此选用了古希腊哲学的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和现代哲学开端的笛卡尔“我思故我在”来证明二者与尼采“权力意志”的内在关联性,认为它们暗含着人类主体性的形而上学从有条件到无条件,再到绝对无条件的演进③。“人是万物的尺度”是有条件的主体性形而上学,人虽是在场状态和无蔽的尺度,但这里的尺度还有节制和限制人类主体性的意思,并没有自以为是地否认最遥远的闭锁之物,也就是说海德格尔认为,在普罗泰戈拉所处的那个时代,人还能对他所谓的“存在”问题有所“遥望”和“倾听”。海德格尔着重批判和释义了“我思故我在”,认为它是后来所有形式的形而上学之根基,是无条件主体形而上学的始作俑者。海德格尔将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解释为“我思我思(cogito me cogitare)”,这个第一性的认识原则成为了往后形而上学中一切反思性和自觉性主体的基础。何为“我思我思”呢?当表象活动在进行时,它在表象被知觉的对象时,被表象的对象同时保证着“我”作为“基底”的无条件存在和不可怀疑。这个原则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在认识事物之前,首先设定了理解它的条件不可怀疑,这个“我”不是事后在表象活动中认识到的,而是预先把被表象者带到“我”的表象范围之中。“权力意志”是绝对无条件的主体形而上学。在主体意义上,笛卡尔的“自我”意味着表象对象的主体,是反思和知觉意义上的主体。尼采的“自我”是身体(本能和情绪)意义上“主体”,作为身体的主体比作为“我思”的主体更具无条件和明晰性。在存在和真理意义上,对笛卡尔而言,存在就是通过主体表象对象同时表象自我的状态,真理就是对这种表象状态的确信。对尼采而言,存在就是对“生成”的固化,“存在”就是假象,通过主体表象活动进入我视域内的事物,都是如其所不是的那样显现给我的。真理就是谬误,真理意味着对“生成”的“持存化”,但这种谬误又是作为“身体”的“主体”必要的价值。在主体的有条件和无条件性上,“我思故我在”已经表明了人是一切存在者的尺度,但人的认识(表象)活动的范围依然是对主体的一种限制和条件,主体依然受制于它者。“权力意志”消除了主体表象活动范围的限制,所有事物都是权力意志的产物,整个世界都是权力意志,都被权力意志所赋形。在尼采那里,真理成了谬误,他消解了真理与非真理的界限,权力意志不仅支配着真理(限制),也支配着非真理(无限制),权力意志彻底成为了无条件的主体性形而上学。
综上,海德格尔把尼采的权力意志释义为“无条件的主体形而上学”,根源在于它植根于笛卡尔“我思故我在”所开启的现代无条件主体形而上学历史,并且穷尽了其内在的可能性。尼采作为“身体”的主体和笛卡尔作为“我思”的主体,前者象征“动物性”,后者象征“理性”,它们共同标志着形而上学的完成。真理与非真理界限的取消,也标志着人类主体对不可知领域的全面占有。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历史的解释方式,也昭示着其解释尼采哲学的基本逻辑,即“颠倒的柏拉图主义”。权力意志作为以“颠倒”方式规定形而上学的最后一种形式,必然是以“理性”主体的对立面“身体”作为主体的形式出现。暂且不论海德格尔以“颠倒的柏拉图主义”解释尼采哲学成为了另一种对主体形而上学的巩固与加强,海德格尔对尼采释义和批判成立吗?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知道,尼采比海德格尔更早指出形而上学中“主体”的表象方式无能于认识“生成”,它只能通过限制表象范围和对象的方式来如其所不是的那样来显现“生成”。形而上学中的“主体”是权力意志受到压制和限制的否定性产物,也就是说,权力意志是形而上学所虚构和伪造“主体”背后的“主体性”,而权力意志所代表的主体性作为一种源始性的能动力,跟“我思”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中受到压制和否定而产生的主体性根本不是一回事。尼采把权力意志受到压制和否定的反动力称为驱动形而上学历史运动的“复仇精神”,而对“复仇精神”的解脱,将成为尼采哲学对形而上学的克服成功与否的关键问题。这个问题进一步表现为:受到“复仇精神”压制和否定的权力意志如何在“相同者永恒轮回”思想中得到克服,这个问题将会在下面部分得到进一步澄清和阐释。
综上所述,这个时期的海德格尔在开启通向尼采哲学道路的时候,也遮蔽了通向尼采思想的道路。由于相同者永恒轮回这个思想最重要的维度——复仇精神的问题,并没有被海德格尔充分地讨论,尼采“相同者永恒轮回”的重要部分,依然对海德格尔而言是晦暗不明的,海德格尔又急于将这个思想纳入作为“形而上学家”尼采的思想统一性中来把握,从而错失了进一步追思这个思想的道路。尼采作为处于一个开端的终结与另一开端尚未开启的重要哲学家,也只有根据他的基本思想在哪种意义上是形而上学,哪种意义上是对形而上学的克服,其地位才能得到恰当的评价。
二、 相同者永恒轮回作为解除“复仇精神”的桥梁
海德格尔在1953年题为《谁是尼采的查拉图斯拉?》的讲演中,着重讨论了尼采“相同者永恒轮回”与“意志对时间的复仇”之间的关系。这里的“意志”是权力意志受到压制的产物,“时间”指遭形而上学中贬低和否定的“生成”,复仇就是对“存在者”不再存在的憎恶。在这个时期的海德格尔,对尼采“相同者永恒轮回”思想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转变,相较于之前弗莱堡时期(1936—1941年)的海德格尔将“相同者永恒轮回”粗暴地释义为形而上学意义上“存在者的存在方式”,在这里却显得相对克制,甚至愿意把尼采“相同者永恒轮回”视为一个“有待思想的思想”。这个时期的海德格尔随着对尼采哲学认识的深入,显然意识到了之前对尼采哲学的解释和定论是不妥的,因为尼采是第一个清楚意识到和指出形而上学终结的哲学家,而且其“相同者永恒轮回”的思想甚至可能是从形而上学终结走向未来哲学的“桥梁”。但正如沃尔夫冈·穆勒-劳特尔(Wolfgang Müller-Lauter)指出的那样,“海德格尔晚期对尼采思想的让步并没有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把他看作是过渡时期的思想家”[3]131。尽管海德格尔触及到了尼采“相同者永恒轮回”中超出形而上学的部分,但基于海德格尔赋予尼采的“形而上学”立场,海德格尔并不会真正聆听查拉图斯特拉的教诲。海德格尔表面上遵循尼采之思,在向一位名为查拉图斯特拉教授“相同者永恒轮回”和“超人”思想的教师请教,这其实是把查拉图斯特拉作为尼采思想中“相同者永恒轮回”和“超人”的代言人,依然以一种形而上学的先入之见来释义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形象和他教授的思想。海德格尔也没有通过领会“相同者永恒轮回”思想从“复仇精神”中解脱出来以通过这座“桥梁”,而是留守在桥的形而上学一边。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解脱”④绝非叔本华意义上对意志的解脱而遁入空无之中。
查拉图斯特拉是教授“超人”的教师,何为“超人(Über-mensch)”?超人是超越迄今为止的人,把人带向尚未具有的某种本质规定性中去,是对人类获得那种尚未具有的本质规定性的总称。这种本质规定性,就是脱离了“复仇精神”获得“最大肯定”的人。在此,我们不能把“超人”理解为海德格尔释义下“人类主体性”得到无条件发展的那种金色野兽,也不是擅长运用“黑格尔式”否定辩证法压制异己,以及利用反动力取代上帝的人。“超人”脱离了形而上学对“人类主体性”的规范,摆脱了形而上学中的否定辩证法。如德勒兹所说,“超人是通过一种新的感觉方式来定义的;他是一个与人不同的主体,不属于人的类别”[4]349。过渡到超人的桥梁本身又是什么呢?那就是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查拉图斯特拉虽然同时教授“超人”和“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思想,但要过渡到超人,首要的是通过“相同者永恒轮回”这座桥梁。迄今为止的人,只有领会了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才能通向人类的最高希望——超人。在这个意义上,并结合上述关于“权力意志”的解析,“相同者永恒轮回”成为了“权力意志”和“超人”的先行问题。
“相同者永恒轮回”之所以是整个尼采哲学的先行问题,是因为复仇精神只有在相同者永恒轮回的意义上,才能得到克服。在《毒蛛》一节中,查拉图斯特拉说:“因为人类要解脱复仇:在我看来,这就是通向最高希望的桥梁,漫长暴风雨后的一道彩虹”[5]146。人类对这种复仇意志的解除,是通向最高希望和未来的桥梁。在《救赎》一节中,查拉图斯特拉说:“复仇精神:我的朋友啊,这是迄今为止人类的最佳沉思;而且哪里有痛苦,哪里就总该有惩罚”[5]212。复仇精神之所以是迄今为止人类的最佳沉思,是因为形而上学的历史是被这种复仇精神所驱动的,哪里有时间的流逝(存在者的不再存在),哪里就有人类的痛苦,这种痛苦就会产生出复仇(怨恨),形而上学起源于这种复仇精神。值得注意的是,查拉图斯特拉把这种复仇精神称为“我的朋友”,意味着查拉图斯特拉这位教师已经学会接纳了复仇精神,这种接纳同时意味着:这位教授“相同者永恒轮回”思想的查拉图斯特拉,已经放弃对“复仇精神”的复仇,完成了由否定到肯定的嬗变,表明了查拉图斯特拉从复仇的精神解脱出来了,所以他是“相同者永恒轮回”的教师。海德格尔对这里“人类最佳沉思”的解释是:“这里所谓的沉思并不是指任何一种思索,而是指那种思想,人与存在者的关系就基于这种思想,回荡于这种思想中”[6]119-120。海德格尔一方面确实把握到了迄今为止的形而上学被尼采沉思为由“复仇精神”所驱动,以及迄今为止形而上学的本质就是“复仇精神”。而在另一方面,其又忽视了“复仇精神”是查拉图斯特拉的朋友,查拉图斯特拉不再对驱动“形而上学历史”的“复仇精神”展开复仇。那么,复仇本身和它的对象是什么呢?查拉图斯特拉说:“这个,的确,只有这个,才是复仇本身:意志对时间和‘它曾是’的憎恶。”[5]212在意志对时间和它曾是(it was)的憎恶中,作为一种纯粹运行着的流逝,“曾是”是“当下”的人所无法改变,人对时间“过去(流逝)”的无能为力,让人产生了对时间“过去”的怨恨,进而产生了对时间的“复仇精神”。
通过上述分析,意志对时间和它曾是的憎恶,在形而上学“主体”意义上,就是对无法按照其表象方式如其所是地把握“生成”而产生的怨恨。被“复仇精神”驱动的“主体”,为了逃避时间过去的事实,把握住流逝的生成,通过把“生成”量化的方式,而发明了“形而上学的时间”,其具体表现为:永恒宗教(超时间)和物理时间(线性时间),二者的“客观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源于对形而上学中“主体性”的不可怀疑。在永恒宗教中,人们在面对作为流逝和不可逆转的时间“过去”,通过虚构出一个“超时间”的永恒之物,来宰制我们的生活。在尼采看来,虔诚基督徒的信仰与殉道都是被复仇精神所驱使。因为以“上帝”为代表的永恒之物的产生,根本上源于人们对时间“过去”的憎恶。而“永恒”这一最完满的概念,实际上就是虚无主义的概念,因为“永恒”就是没有流逝的时间,在永恒中没有生成和变化。看似在发号施令,给予时间规定性的永恒不过是人们无法忍受时间“过去”的发明。当尼采说:“上帝死了!”他就是在对迄今为止的关于时间的经验与观念宣告:这个作为发明和幻象的“永恒”时间,作为最高价值,贬黜和失效了。
那么“上帝死后”,残存在“上帝遗骸”中的时间观念还剩下什么呢?——线性时间,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客观时间。在这种时间中,人们不仅没有从“复仇精神”中解脱出来,反而失去了上帝庇佑,强化了民众的“复仇精神”。随着上帝之死,人类主体占据了上帝的位置,与技术一起发动了对他者无条件的复仇和统治。技术的发展,也让技术对时间的渗透愈来愈隐蔽,技术与时间的联合统治,让人类主体身上的这副“镣铐”显得前所未有的精密与难以离开了。线性时间中,时间必然是按照从过去—当下—将来的方向来运行,过去的事物将永不复返。面对时间“过去(it was)”,人成了旁边者与无能者,人的意志成了复仇意志与否定意志。
至此,一方面,“永恒宗教”施加给民众的“永生”时间观被证明是不存在的,另一方面,上帝遗骸中的线性时间提供给人们的生存境遇又是令人无法忍受的。尼采就必须提供一种脱离于形而上学规定,同时又能避免民众再次陷入形而上学窠臼的时间观。这是尼采“相同者永恒轮回”中时间维度的基本问题。为了脱离于形而上学规定的时间架构,尼采消解了形而上学对时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规定。尼采认为,根本不存在一个固定的“过去”和最终的“未来”,如果“过去”已经形成,那怎么会有正在发生的流逝,如果“未来”有一个终点,那么它应该早已经到达,这进而解构了形而上学中的“起源论”和“目的论”。基于线性时间,回到“过去”是可以想象,却是不可能的。尼采认为,只有改变人们对“时间过去”的复仇精神与否定意志,人才能从对“时间过去”的憎恶和怨恨中解脱出来。在这个意义上,“相同者永恒轮回”对尼采而言是意志的实践原则,无论你想要什么,你都想要它“永恒轮回”,是解脱于“复仇精神”的无限肯定在“永恒轮回”。
综上,在解除复仇精神的“桥梁”意义上,尼采的“相同者永恒轮回”成为了尼采哲学的先行问题,也是其是否克服了形而上学的关键问题。海德格尔基于“相同者永恒轮回中的瞬间”来克服复仇精神。尼采则基于“永恒轮回与虚无主义的关系”来克服复仇精神。
三、 相同者永恒轮回中的瞬间
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第四十六节的幻象与谜团,通过查拉图斯特拉之口,对相同者永恒轮回的瞬间(Augenblick)作了这样的描述:“这条长路往回走:它延续着一种永恒。而那长路往前走——那是另一种永恒。它们背道而驰,这两条道路,它们恰好彼此碰了头——而且在这里,在这个出入口,正是它们会合的地方。出入口的名字被刻在上面了:‘瞬间’”[5]212。在海德格尔的释义中,如何理解和解释这个“瞬间”一直以来被视为解开“相同者永恒轮回”这个谜团的密钥。海德格尔说:“当然,只有对于一个并非旁观者,而本身就是瞬间的人,才会有一种碰撞;这个人的行动深入到将来,又不让过去消失,而倒是同时把过去接受和肯定下来。……永恒轮回学说中最沉重和最本真的东西就是:永恒在瞬间中存在,瞬间不是稍纵即逝的现在,不是对一个旁观者来说仅仅倏忽而过的一刹那,而是将来与过去的碰撞”[1]326-327。海德格尔最终认为,此在对过去肯定的决断瞬间,是从“复仇精神”中解脱的关键。可海德格尔没有更进一步的解释,在这个“瞬间”中,个体对过去由否定到肯定转化的这一过程,具体是如何发生的。在此,海德格尔对“瞬间”的解释更像是对自己“时间性到时(Zeitgung)”的再解释,“时间性到时”是时间到这个时机显现为……,是时间性的绽出,时间性作为统一整体,总是“已在”、“现在”和“将来”的共同到来⑤。在海德格尔看来,永恒轮回中的“瞬间”就是时间性的到时,是过去与将来的碰撞,以当下样式的到时。进一步来说,在海德格尔那里,“此在”作为有终结的将来,即便本真地显现和领会着“无”,也依然暗含着意志对时间的“复仇精神”。
综上,海德格尔基于自己“时间性到时”的视域,解释了“相同者永恒轮回”中的“瞬间”,这种解释虽然区别于形而上学的时间规定,可此在优先以将来维度先行领会不可逾越的可能性(死亡),依然暗含着一种对时间的“复仇”,即便此在以一种积极的方式筹划生活,也依然是在一个否定的大前提下:此在是有终的将来。尼采所批判和克服的复仇精神——意志对时间过去的憎恶——在海德格尔这里转换为了“意志对将来有终的怨恨”,意志对“过去”不可改变和对“将来”必有一死的绝望,本质上都是“复仇精神”。
四、 相同者永恒轮回对形而上学的克服
至此,作为“相同者永恒轮回”教师的查拉图斯特拉将意志从“复仇精神”中解脱出来了吗?在《救赎》一节的最后,查拉图斯特拉说:“意志已然成为它自己的救赎者和令人愉快者了吗?它已经荒废了复仇之精神以及一切切齿之恨吗”[5]214?我们看到,查拉图斯特拉——这位教授意志从复仇精神中解脱之道的教师,最后竟对自己的说教表达了疑虑。而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形象之所以能够是教师,正是因为他对自己教授的思想始终有所疑虑。但停留在对“相同者永恒轮回”传授这个思想教师的谦逊形象,显然不足以回应海德格尔的诘问。海德格尔说:“这种思想克服了迄今为止的沉思,克服了复仇精神吗?抑或在这样一种烙印中——它把一切生成都纳入相同者的永恒轮回的照料之中——不是也还隐含着一种对单纯消逝的憎恶,从而也还隐含着一种极其超凡脱俗的复仇精神吗”[6]130?海德格尔认为,相同者永恒轮回没有让迄今为止的沉思克服复仇精神,因为通过让一切生成作为相同者,进行永恒轮回,依然蕴含着形而上学的基本逻辑,即让生成“永恒化”与“持存化”。此外,海德格尔认为,相同者永恒轮回在虚无主义和瞬间的意义上得到思考之际,它才得到了真正的思考。但海德格尔对尼采哲学中虚无主义与相同者永恒轮回的关系问题的思考,却遗憾地没有更进一步,对于尼采哲学,他始终是一个“旁观者”,而非置身其中的决断者,这导致了其无法解释清楚个体对过去由否定到肯定转化的这一过程具体是如何发生的,海德格尔得出了他的最终结论:“相同者永恒轮回”并没有把迄今为止的沉思从复仇精神中解脱出来。
尼采把驱动形而上学历史的力量思考为“复仇精神”,但形而上学历史本质乃是“虚无主义”。尼采在虚无主义的意义上,思考“相同者永恒轮回”时说:“让我们想一想这种思想的最可怕的形势吧:此在,如其所是的此在,没有意义,没有目的,却无可避免地轮回,没有终结,直至虚无,这就是‘永恒轮回’,这就是虚无主义的最极端形式:虚无(‘无意义’)是永恒的”[7]!结合上述查拉图斯特拉对“瞬间”的描述,我们发现,没有目的、无始无终的生成就是虚无主义。虚无主义问题只有在相同者永恒轮回的意义上才是最极端和完整的。
复仇精神的解脱,在“相同者永恒轮回”中最终表现为:虚无意志(否定意志)和复仇精神(反动力),如何转化为肯定意志和能动力。正如德勒兹所说:“这是力的能动性和意志的肯定性同时进行的双重选择”[4]146。首先,这种转化不是在形而上学范围内(否定的前提)发生的,即否定的肯定,而是相同者永恒轮回的前提下发生的,即肯定的否定。其次,这种转化在“相同者永恒轮回”的意义上得到思考,将走向能动的毁灭,而不是能动的转化,毁灭决定了在“相同者永恒轮回”中反动力所代表的一切生成将不再轮回。
具体来说,在迄今为止的形而上学中,虚无意志(否定意志)与复仇精神(反动力),促使能动力否定并反对自身,复仇精神在逃避虚无主义的名义下取得了反动的胜利。尼采认为,只有虚无主义与相同者永恒轮回一起得到思考时,虚无主义中的虚无意志与复仇精神中的反动力之间的联盟才能解除。在“相同者永恒轮回”的意义上,最极端和完整的虚无主义意味着虚无意志的否定与毁灭,朝向了反动力本身的否定与毁灭,“相同者永恒轮回”是虚无主义克服自身和解除复仇精神的唯一途径。永恒轮回促使复仇精神(反动力)不断地走向自身的能动毁灭,让复仇精神嬗变为肯定精神,让虚无意志(否定意志)嬗变为肯定意志,在“相同者永恒轮回”中完成的双重肯定,首先意味着双重的毁灭:复仇精神(反动力)的毁灭和虚无意志(否定意志)的毁灭。那么,尼采也就完成了由形而上学中“消极的虚无主义”到未来哲学中“积极的虚无主义”的转变,这种转变不是一种“颠倒”,而是对“颠倒”的解除,因为在尼采看来,形而上学的起源(Ursprung)⑥本身就是“颠倒”的开始,这个意义上的颠倒是:否定意志和反动力对肯定意志和能动力发动“暴动”所完成的“颠倒”。
那么,曾让查拉图斯特拉担惊受怕,又让海德格尔的解释踟蹰不前,关于“相同者永恒轮回”中侏儒、复仇精神、虚无意志……也将作为“相同者(das Gleich)”一起轮回的问题,就得到了解决。无论多么强大的反动力,都将在虚无主义的永恒轮回中转化为肯定力,所有在永恒轮回中的反动力都将走向对自身的否定,走向一种能动的毁灭。在这个意义上,“相同者(das Gleich)”是有差异的“同一者(das Identische)”,侏儒、复仇精神、虚无意志……已经不再是那个绝对的“同一者”了,其经受了由否定到肯定的嬗变。在这个意义上,尼采着眼于“永恒轮回”来克服虚无主义,本质上就是对形而上学的克服。这种克服就表现在:一方面,他首先指出了形而上学的本质,以及驱动其发展的复仇精神;另一方面,他自觉地不再以形而上学的方式建构“未来哲学”。
五、 结 语
至此,我们可以回应尼采是形而上学的完成者吗?在海德格尔意义上讲,尼采“权力意志”是无条件主体形而上学的最极端和最后一种形式,它穷尽了形而上学历史运动的最后道路,而使形而上学走向完成。“相同者永恒轮回”把生成“永恒化”,依然没有把意志(权力意志)从“复仇精神”中解脱出来,它将复仇以“永恒轮回”的方式永恒不断地否定意志和生成,形而上学历史也将以“永恒轮回”的方式持续运转下去。所以,在海德格尔的释义上讲,尼采不仅没有克服和超越形而上学,反而以最极端的方式巩固和完成了形而上学。而在尼采的意义上讲,形而上学的“主体”是权力意志向外扩张受到压制和否定的产物,权力意志要消解这种否定的限制,就必然要在“相同者永恒轮回”的意义上思考虚无主义,“复仇精神”不断地否定自身并消解自身,以达到永恒的肯定(最大的肯定)。在这个意义上,尼采哲学不仅完成了形而上学,而且在某种程度上,逾越和终结了形而上学。
毋庸置疑的是,海德格尔围绕“尼采”所作的系统性讲演和论述,几乎涵盖了尼采哲学的所有问题。但当海德格尔以“尼采”为对象批判整个形而上学历史时,就必然陷入了尼采曾努力克服并驱动形而上学历史运动的“复仇精神”之中,即对形而上学中“复仇精神”的“复仇”,也就是对作为“形而上学完成者”尼采的全面批判。海德格尔对尼采的所有批评,反而成为了加强和巩固主体性的形而上学,并成为其历史的一部分。这也就解释了,在海德格尔的释义下,为什么尼采作为形而上学的完成者,却始终无法逾越形而上学的藩篱——因为海德格尔就是以形而上学的方式(颠倒的柏拉图主义)来理解和释义尼采哲学的,这也就注定了他无法真正理解“相同者永恒轮回”何以作为“最大的肯定”来摆脱形而上学中的“复仇精神”,从而克服形而上学的。
注释:
① 1972年,在吉尔·德勒兹和米歇尔·福柯的一次谈话中,两人明确提到“尼采思想”作为当代法国思想当中共同“工具箱”的重要作用。其中,德勒兹围绕尼采的创作的专著有《尼采与哲学》(1962)与《解读尼采》(1965)。德勒兹敏锐地把握到了尼采是一位拒绝编码的哲学家,德勒兹进一步把尼采形容为一位“游牧者”,这不是因为尼采居无定所的漂泊生活,而是尼采就算在固定的居所,也一再拒绝被编码的命运。福柯虽没有像德勒兹那样出版过关于尼采的专著,但在1964罗伊蒙特举行的17届国际哲学研讨会上,福柯提交了一篇名为《尼采、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论文,福柯在尼采那里发现了根除人类学的最初尝试。尼采“上帝死了”与福柯“人之死”根本上都是在最高价值贬黜后,先前的最高价值和社会规范塑造下的人将不再存在。超人的即将到来的迫近,加剧了“现代人”的消解。在福柯另一篇著名的论文《尼采·谱系学·历史学》中,福柯直言受到了尼采《论道德谱系》的影响,沿用了尼采在寻求道德起源中,用起源(Ursprung)一词开宗明义地展开了他对谱系学的讨论,并继承了尼采拒绝寻求起源的方法论。
② 在此海德格尔有意篡改了尼采《权力意志》中的第617条的部分内容,其原文为:“为生成打上存在之特征的烙印——这乃是最高的权力意志。精神和感官的双重伪造,以保证这个世界的存在、令人容忍、平等……。一切皆轮回,这是一个生成世界向存在世界的极端接近——此乃观察的顶峰”。See Nietzsche:TheWilltoPower,trans by Walter,Kaufmann and R.J.Hollingdale,Walter,Kaufmann(ed.),Published in New York by Random House,1968,P330-331.另外,海德格尔本人在他关于尼采的讲座和后来编撰的丛书中,多次引用了这个“要点重述”。但后据D.F.Krell和Walter Kafumann的考证,这个“要点重述”的标记是尼采的朋友Peter Cast后来加上去的,并非尼采本人所为。
③ 海德格尔在弗莱堡时期开设了题为“欧洲虚无主义”的讲座课程(1940年),其中详细论述了“主体形而上学”历史的演进。从普罗泰哥拉“人是万物的尺度”(14-15节),到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16-18节),最终到尼采的“权力意志”形而上学,是一种无条件的主体形而上学,主体形而上学最终发展到了顶峰,从而使形而上学走向了终结(19-22节)。参看海德格尔的著作《尼采》(下卷) 第五章《欧洲虚无主义》(孙周兴译)。另可参看Martin Heidegger:NietzscheVol.4EuropeanNhilism.translated by David Farrrell Krell,P91-149。
④ 叔本华在此所说的“解脱”,意思是从意志中解脱,不再意愿任何事物,而遁入虚无。尼采认为,意志必须总是有所意愿,就算意愿虚无,也仍然是在意愿,所以叔本华意义上的从意志中解脱,是不可能的。在形而上学意义上,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的第6节中,批判叔本华通过表象从“意志”解脱的想法,根源是对某种经验的普遍化,并没有逾越形而上学的藩篱。
⑤ 参看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第375页;另可参看黄裕生的《时间与永恒——论海德格尔哲学中的时间问题》第115页。
⑥ 尼采在某些场合拒绝寻求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起源(Ursprung),认为这是形而上学为寻求事物同一性强行外加于事物之上的发明,而在《论道德的谱系》中使用了Herkunft(起源)。具体可参看福柯的著作《尼采·谱系学·历史学》中《尼采的幽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