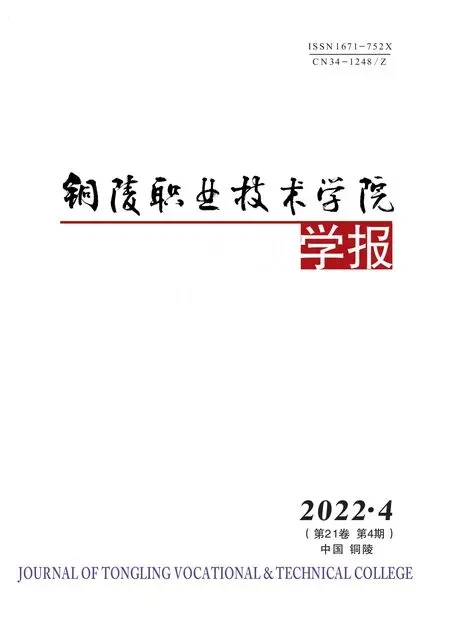中西方文学中“悲”的差异性辨微
张 磊
(四川民族学院,四川 康定 626001)
长期以来,在中国的文学研究过程中,“悲剧”这一概念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这种西方概念的中国本土化应用也得到了众多学者的认同。但是,随着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与扩展,“悲剧”这一概念逐渐显得有些不太合适。诸多学者对此也有所关注,分别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见解,诸如:张法在其 《美学原理》一书中就意识到中国的悲情与西方的悲剧是有区别的,但是这种区别是什么,却并未进一步加以说明。而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也少有人对这二者的区别进行详细地论述。在此,笔者认为,“悲剧”与“悲感”二者既有相似,又有不同。长期以来,在文学评论中这二者多是一种相互混用的情况,正是基于此,在中国文学研究的过程中对“悲感”与“悲剧”进行区别划分就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对于悲剧的研究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进行深入,其一是探寻悲剧的这种作品本身,其所探究的悲剧内容在于悲剧所反映的故事本身,中国传统作品《窦娥冤》等作品就是这一类型的典型代表;而另一种则是从悲剧之中所抽象出的悲剧精神的广泛应用,如:史记的悲剧精神、中国古代神话的悲剧意识等,这些研究过程中也多是基于对于其精神内涵的把握。
但是,悲感与悲剧相似却并非完全相同,悲剧的背后是一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悲壮,而悲感相较而言就要更为温和,它是一种能够看到希望、能够看到成功的可能性,在这种情感萌发的初期,往往伴随着人们对于成功的期盼,它使人们能够看到那个美好的、完美的结局,只是当这种可能在现实中成为不可能、成功的希望成为了泡影之后,悲感也就随之而来。然而,这种悲感是东方人们所不愿接受的,因而,在很多文学作品中出现了所谓的光明的尾巴,正因如此,很多人说中国没有纯粹的悲剧。实际上,随着20世纪初,西方“悲剧”的概念传入中国,这一概念的本土化都在不停地进行着,并成为一种广泛运用于中国本土文学研究的评论方式,在长期地使用中,或者是说在中国本土的概念运用中,更关注的是其中的“悲”,其发生于西方本土化的特点已经逐渐被忽视。
悲剧本身是西方的概念,这种概念是在西方文学体式与审美倾向之上而提出的,是西方的本土概念,用这种概念去框定中国古代文学,本身就是削足适履。中国并非没有“悲”的概念,也不是没有审悲的美学范畴,早在魏晋时期,这种审悲的风气便已经大为盛行。只是,中国文学中的悲,更多的是一种生活式的悲感,而不是美学范畴中的悲。笔者认为,中国文学悲感的基础正是基于人们生活中的悲,中国人民经历过太多的社会动荡、天灾人祸,他们以文学的方式记录着这些悲苦,这种悲苦反映在文学中,就形成了作品中那些忧生嗟叹的情感,这种情感很普通,但只有真正理解那个时代生存的悲苦,才能理解到这种悲情它是极其普遍的,却又极其深刻。王富仁就认为:“悲哀是中国文化的底色”[1],部分学者认为,悲剧与悲感之差别在于文体。而笔者认为,即使同为叙事文学,悲感与悲剧仍然有着明显地差别。诸如《史记》中所反映的悲剧精神与西方所论之悲剧依然有着明显的区别。笔者认为,中国文学中的悲与西方悲剧的差别主要体现在文化背景、表现方法、以及读者的接受方式。
一、从文化背景上来说
悲剧文化建构于宗教之上,而悲感是建构于基本的生活体验之中。悲剧从发生到其流变,其中文化背景下的宗教色彩是不可或缺的。而中国文学中的悲感,扎根于中国的文化土壤中,本身就不具备这种宗教哲学的土壤,中国并非没有自己的本土宗教,只是说,中国的宗教在长期发展中并未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再加上封建王权基于统治的需求,将自身视为天子,将自己的意识视为天命,因而中国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并未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更不用说在宗教体系上所建立起的宗教哲学精神。因而在中国文学作品之中,悲感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现实的矛盾冲突,这其中有丰富的内容,有个人理想的覆灭,有个人生命的终结,但这些都是基于现实生活层面的表达,这种悲感源于人们对生活基本诉求的表达,而没有去追究其背后深层次的宗教或是哲学含义。
(一)“天人之道”是我国悲感文化的重要来源
“天人之道”,即探寻天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先民执着探寻的重要内容,从先秦开始,我国先民对于“天”都有着虔诚的敬畏,天道观从先秦时期就已经在中国文化中牢牢扎根。人与天的关系是“天人之道”中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我国悲感文化的重要来源。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对天的论述并非少数,诸如《史记》司马迁所表达的天命观,但史记中的天与西方宗教哲学中的天有着本质的区别,司马迁对于天,是一种矛盾的复杂态度,一方面他对天道持怀疑态度,否认天命对人事的干预,认为天与人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如其在伯夷列传中所论:“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同样,在李将军列传中,司马迁也通过李广的一生,表达了对天的怀疑。李广生不逢时,尽管他一生努力,最终却也未能封侯,这与司马迁自身的经历又何其相似,他又何曾不以自己的遭遇去质问这个 “天”,“李广对天的怀疑与认命,其实也正是司马迁本人的认识。”[2]同时,司马迁又笃信天道,他在史记中也不止一次表达出自己对于天命的信服,如其在外戚世家中所言:“人能弘道,无如命何。……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终:岂非命也哉?孔子罕称命,盖难言之也。非通幽明之变,恶能识乎性命哉?”
然而以上种种对于天与人之间关系的质疑,并没有成为《史记》中悲的主体,当我们在扼惋李将军生不逢时,命运多舛的同时,却很难在这种与天的对立中激发内心的一种冲动,一种对于生命、人生的强烈情感。这也就是中西方文学中所负载的命运主体的差别。而此外,孔子、老子、庄子、墨子也从不同的角度对天进行了论述,形成了一套中国独特的天命系统。而在西方作品中,这种天命则很容易激发人们内心的情感冲动,如哈姆雷特从幸福跌入悲剧,他并没有做错任何事,却被命运无情地玩弄,但他却在抗争中让读者感受到了一种力量,引发了读者对于个中问题的思考。
(二)所愿不能实现是悲感的重要表现
西方悲剧以矛盾为悲剧的主要产生点,而中国悲感则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所愿不能实现。中国在基本的汉字构造上就表现出了对于悲的理解,《康熙字典》中“悲”字,郑笺曰:“春女感阳气而思男,秋士感阴气而思女,是其物化,所以悲也。一曰心非为悲。心之所以非则悲矣。”而西方对于悲的理解则与之不同,无论是普罗米修斯与神“巨人!在你不朽的眼睛看来人寰所受的苦痛是种种可悲的实情,并不该为诸神蔑视、不睬;但你的悲悯得到什么报酬?是默默的痛楚,凝聚心头;是面对着岩石,饿鹰和枷锁”之间的对话,还是俄狄浦斯王对命运的反抗,无论是哈姆雷特与权力之间的斗争,还是奥赛罗自身由对立情绪的斗争所产生的一系列悲剧。西方悲剧给人带来力量的核心就是反抗,这种反抗虽然无力,却贯穿于西方悲剧的始终;这种反抗虽然在命运面前是渺小的,但是却在这种反抗中展现了人的力量,这也成为了西方悲剧的精神所在。
而在中国众多文学作品中,这种反抗往往是被消解、被弱化的对象,它不像西方文学作品在反抗中表现悲,而是通过最终的结果去表现悲。例如在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与刘兰芝的爱情过程有着诸多的阻碍,但面对这些阻碍,二人并不是选择反抗,面对“我有亲父兄,性行爆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兼我怀”,面对阿母的阻挠,“阿母得闻之,槌床便大怒:‘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府吏默无声,再拜还入户。举言谓新妇,哽咽不能语:‘我自不驱卿,逼迫有阿母。卿但暂还家,吾今且报府。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取。以此下心意,慎勿违吾语。’”在这些作品中,唤起我们产生共鸣的不是其中所包含的反抗因素,而是最后的结局。东方悲往往是用一种结局去描绘它所包含的悲,并且,即使仅仅是结局的悲,中国人依然认为这是一个无法接受的设定,因而往往在结尾赋予一种光明的尾巴,“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3],这一点与西方的悲剧有着明显的差别。
(三)独特的处事哲学是悲感的独特表征
在“悲感”与“悲剧”内容的差异性背后,还隐藏着中国先民的一种处世哲学,面对必然不可战胜的对象,明哲保身、全身而退也就成为了一种智慧的表现。中国文学发展的源头——神话之中实际上就酝酿着悲剧的原始土壤。中国神话之中也有大量抗争,无论是后裔射日、夸父逐日,还是精卫填海,都是中国古代先民与自然抗争的真实写照。到了先秦,面对这种不能改变的天道,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天命观,即顺天知命。自此,同西方的抗争与改变不同,中国文化对于天的态度开始从对抗开始逐渐变成了了解与顺应。
因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文化系统中,矛盾被逐渐弱化,而同西方矛盾所引发悲剧、悲剧展现矛盾所不同的是,中国式的悲感它所关注的,并不在于这种矛盾本身。受中国文学传统意识的影响,在诸多文学作品中,我们能够看到死亡的悲、理想覆灭的悲、时代所赋予的个体价值的悲,但这些悲本身所表现的,甚至于它想要带给读者的,并不在于矛盾本身,而是在于一种生活式的悲感。生活式的悲感就是普通人所经历的一系列悲的体验,这种生活式的悲感往往能够引发人们最为广泛的共鸣。战争、流离、死亡、理想的覆灭、爱情的阻隔,这些发生在先秦时代普遍的社会现象,是当时社会先民所普遍经历人生体验,因而在作品中能够引发一种强烈的共鸣。这种悲并不是希望在悲中引发多少对于人生哲学的思考,而是在于这种悲感所引发的悲感本身。而西方悲剧则不同,西方悲剧往往是通过悲剧中所蕴含的悲剧精神或者是悲剧意识,引发人们对于哲学、生命的思考。
二、从具体的表现方法来说
中国的悲感与西方悲剧的另一区别就在于中国悲感往往是一种片段化的展现,而西方悲剧则是一种全面化的情感贯穿。中国文学作品所悲,往往表现在结局之中,而西方悲剧则是一种过程所引发的悲剧连锁。因为西方悲剧是需要突出悲,因而在作品的整个过程中,悲是其中的主线;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并不为悲而悲,而是着重塑造一种具有生活气息、真实的个体,悲只是作为众多情感中的一种来表现。
西方文学悲剧作品中对于悲的展现,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构成,一方面,这归结于其戏剧的载体形式,西方的悲剧最初是以剧作作为其主要的载体方式,它拥有着完整的故事结构、系统的思想体系,更有着其美学的表现核心——悲剧精神与悲剧意识,而这种表现核心,就是基于其剧作载体的基础上,通过情节反复渲染形成,它不是切中于结局的悲,而是更多地在过程中让人体会到那种经过反复抗争的无力,而导致的悲。另一方面,西方悲剧本来就是以悲作为其主要的表现内容,从悲剧的原始形态——酒神颂歌,到后来的悲剧,都是围绕着悲来展开的,因而从内容上来讲,悲这一内容的主体性也就决定了在表现过程中需要时刻围绕这种悲进行叙述。
而中国文学则不同,首先,以同为叙事文体的《史记》为例,《史记》的叙事结构中仍然没完全抛弃中国的诗学传统,在叙事之中仍然插入了大量的意境描写,而这些意境描写成为了读者悲感的主要来源。以其中的刺客列传为例,我们认为荆轲是一位悲剧的英雄,而引发这种悲感的最直接的片段则是在环境烘托下的人物处境,其中“易水送别”就是最能唤起我们对这种悲的体验的:“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於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荆轲的悲,通过对于环境、气氛的烘托渲染,传达给了读者。同样是悲情的人物,普罗米修斯能够带给人们战胜困境的勇气与力量,哈姆雷特能够带给读者对于生命以及生活的审视,这些作品之中的悲,不再是一章、一节或者是一段所能表现的,而是贯穿于作品始终,一段普通的描述单独列出不能看出他究竟有什么悲,但是当将它安放在整部作品之中,就能够看出它是构成悲的动态之一,这也就构成了东方悲与西方悲的差别。
另外,中国文学强调一个故事的完整性,无论是《史记》、还是乐府,只要是叙事文学,往往讲求其内在结构的完整性,其主要目的在于故事的完整性。而在西方的悲剧中,故事情节只是作为一种情感,或者说是审美的一种手段,悲剧的核心并不是在于他讲述了一个什么故事,而是透过这种故事本身所激发的情感内质,二者有着极为明显的差异。
三、从读者的接受来说
悲剧传递的是一种反抗的精神力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悲剧精神或悲剧意识,悲感则是产生同情与共鸣。西方悲剧将悲作为一个美学范畴的审美对象进行审视,因而在西方悲剧中,更多地关注如何传达悲,传达怎样的悲以及如何对悲进行接受再生成。而东方文学并不以悲为目的,悲只是作为一种气氛渲染或者情感烘托,悲是人物的一种情感,他是剧情、环境、人物的附属,而不是一种独立的目的,更不会作为独立传递的内容。例如在《史记》中,悲是读者在审视历史人物时,基于自己感同身受的情感所产生的一种情感体验,但是,这种情感体验无论是从创作本事还是作品的旨意上来看,都是一种次要的附加品,它不强调在这种悲中我们能悟出某些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当然,在某些作品中我们也能将其联系,但这种联系往往是过度解读中产生的,与作品本身的旨意实际上是无关的。从原始发生来说,司马迁对于作品中所出现的悲并不关注,如对于一个失败的英雄项羽,司马迁并未对其中的“悲感”作出任何关照,而是以一个历史的角度进行人物评判,其论曰:“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面对项羽的失败,司马迁不像西方的悲剧思想建构下那样在这种悲剧的一生中看到命运的不公、看到人生的坎坷,激发对于人生命运的深刻关照,而是在这种失败的人生体验之中,总结失败的经验与教训,作为一种后世历史的参照,而不是将其视为一种审美对象去关注。诚然,我们对这些历史人物进行品读的过程中,确实能够关照自己的社会经历,产生一种共鸣或者是人生体悟,但这种体悟一来不如西方悲剧那样来得深刻,二来亦不是《史记》的目的所在,因而在《史记》之中,悲感的体验往往是个人历程与史记人物之中的一些情感的共鸣,而不是一种以悲为手段的人生开悟或者说是哲学的情感升华。
而与之相反的则是西方悲剧所传达的读者对于作品审视背后所激发的情感以及对生活的哲学思考与态度。西方的悲剧作品多讲求其启示性,不同读者可以产生不同的理解,这与其独特的文化环境与背景是密切联系的。结合具体作品来谈,就很容易能够看到这之间的一些差异。如西方文学中 《等待戈多》,这部作品所传达的文化内涵极具代表性,它既是描写生活本身,又传达出了高于生活本身的文化内涵。在作品中,等待什么以及为什么等待不是作品所关注的重点,从生活层面上来看,这部作品是毫无意义的存在,它所描写的现实世界与中国古典作品中那些生活有着显著的差异,“表面来看,等待戈多的描写似乎毫无意义。”[4]但是,当我们去审视这种现实生活背后的深层文化内涵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部作品所涵盖的内容远远高于其内容本身,它所传达的悲感是深入每个人内心的哲学范畴,是探寻人的生活困境与生命意义的终极关怀。“如果从终极层面来思考人类的存在,人类的存在必然是悲剧的……等待戈多正是从哲学或终极的层面来思考人类存在的问题的。”[4]72在这种接受过程中,不同人会生发出不同的哲学思考,不同于东方文化的共鸣,西方这种悲剧作品讲求的是在这种生活共鸣之下的一种哲学审视,这也就形成了中西方悲剧在读者接受之下的一种差异性。
四、结语
无论是中国的悲感,还是西方的悲剧,都是基于各自文化背景下所产生的独特的审美方式。从文化背景上来说,西方的悲剧是在其独特的宗教文化语境下所产生的对于命运不可抗性的理解与体验。而中国的悲感则是基于我国先民现实生活体验中的一种对于现实感受的客观理解与感悟;从具体的表现上来说,西方的悲剧是通过一个贯穿始终的完整故事,在故事整体中串入悲的意识,使故事总体呈现出悲的特点。而中国的悲感更多的则是在片段的描写中体现悲的特点;从读者的接受角度来说,西方悲剧将悲作为一个美学范畴的审美对象进行审视,所关注的是悲所引发的审美体验。而中国文学中的悲感则是将悲作为一种气氛渲染或者情感烘托,是对剧情、环境、人物的附属,而不是一种独立的目的,更不是作为一种传递的内容。正是基于以上三个方面的审美方式的差异性,使得西方文学中的悲剧与中国文学中的悲感产生了诸多不同之处,也正是这种微妙的差异性,构建起了“悲剧”与“悲感”这两种不同的审美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