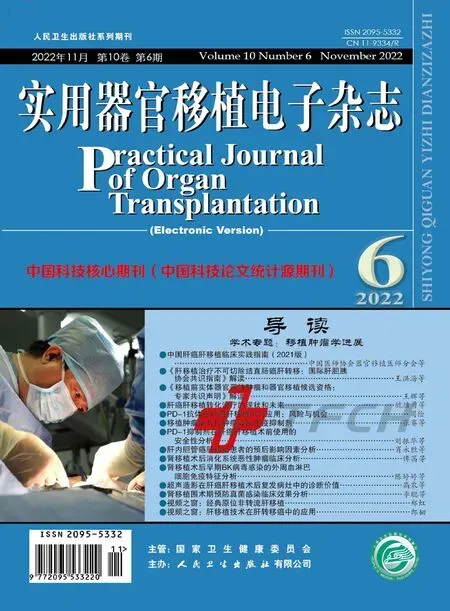PD-1 抗体在肝癌肝移植中的应用:风险与机会
周俭(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肝肿瘤外科,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上海市器官移植重点实验室,上海 200032)
程序性死亡受体-1(programmed death-1,PD-1)作为T 细胞功能的重要免疫检查点信号,其通路的激活可抑制T 细胞抗肿瘤活性。使用PD-1 单克隆抗体可阻断该通路、恢复T 细胞功能而形成治疗癌症的免疫机制。近年的临床数据显示,PD-1 抗体能显著延长晚期肝癌患者的生存期,其应用范围已从晚期不可切除肝癌的二线治疗向术后辅助、术前新辅助及转化治疗等场景拓展。作为治疗肝癌的重要手段,肝移植使大量患者获得根治和长期生存。由于激发患者的免疫功能可能引发致命的排斥反应,PD-1 抗体在肝癌肝移植患者中的应用受到特别关注。近年报道肝移植术前及术后使用PD-1 抗体的文献屡屡可见,与此相关的研究、讨论和认识也在不断地积累和加深。
1 肝移植术前PD-1 抗体的使用
肝癌患者在肝移植术前使用PD-1 抗体治疗大致分以下3 种情况:① 符合肝癌肝移植适应证的患者在等待供体期间作桥接治疗。② 不符合适应证的患者使用PD-1 抗体进行降期治疗,在达标后接受肝移植。③ 肝癌患者在经过包括PD-1 抗体的综合治疗后出现进展而选择肝移植(类似于挽救性肝移植)。近两年,全球发表了多篇关于经PD-1抗体治疗的肝癌患者接受肝移植的病例报告或文献分析研究,共报告了25 例患者[1-9],有3 例患者肝移植术后短期内出现致死性的肝脏坏死,移植肝穿刺病理检查提示,其中1 例符合急性排斥反应诊断[7],另2 例与典型的排斥反应表现不相符,但根据移植肝组织内炎细胞浸润以及血清细胞因子水平等判断,其与PD-1 抗体引发的免疫效应相关[8-9]。25 例病例中另有2 例诊断排斥反应,经治疗后恢复。这些患者切除的病肝内癌灶坏死率高,截止报道时均未发现移植术后肿瘤复发。
目前,描述性的研究不能提供高等级的证据就排斥反应(尤其致命的排斥反应)发生率以及抗肿瘤疗效等得出准确的结论。但研究者们就一些热点问题做了讨论,比如肝移植术前最后一剂PD-1 抗体与移植手术之间的时间的间隔问题。一些作者认为在肝移植前短时间内使用PD-1 抗体会增加术后排斥反应的发生率,建议根据所用单抗药物的血清半衰期设定6 周到3 个月的“洗脱期”[10-11]。然而也有研究提出,PD-1 抗体使用后与其靶点的结合率可以维持很长一段时间,其血清浓度的下降不直接影响其效能。例如,纳武利尤单抗的血清半衰期为12 ~20 d,但在单次输注2 个多月后仍能在循环T 细胞表面观察到70%以上的PD-1 分子被持续占据。在一些重复输注的患者中,最后一次给药后200 d 时PD-1 分子的被占据率仍可保持在50%以上[12-13]。另外,PD-1 抗体阻断其自身主导的免疫检查点信号通路可改变免疫细胞间对话机制,可能使整个机体产生持久性的免疫反应重编程。因此,即使设定了“洗脱期”,PD-1 抗体仍可能对肝移植患者的机体免疫产生复杂的影响[4]。目前的初步数据提示,“洗脱期”的设定反而可能是不必要的,Tabrizian 等[1]报告的病例系列中有3 例患者在移植后1 周内接受PD-1 抗体治疗,并没有发生排斥反应。目前报道的案例数据也表明肝移植术前使用PD-1 抗体后发生移植物排斥反应的比率并不很高。
总体而言,尽管PD-1 抗体可能会增加术后急性排斥反应的风险,并有发展为致命性移植物失功的案例,但其发生率较低。考虑到PD-1 抗体带来的显著抗肿瘤疗效获益,将其应用于肝移植术前的肝癌治疗正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美国器官分配网络(United Network for Organ Sharing,UNOS)根据目前的初步数据做了政策更新,明确指出使用PD-1 抗体等免疫治疗不影响肝癌患者获得肝癌特例评分[14]。由于缺乏严格设计的大样本临床研究,诸如是否设定“洗脱期”等临床关心的问题尚无定论。目前,已经有数个相关的临床研究(NCT05185505、NCT04035876、NCT04443322 及NCT04425226 等)在进行之中,将来仍需要更多的临床试验以更清楚地了解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等待肝移植的患者中使用的最佳方法,以及移植术后免疫抑制方案的最佳选择,以便更好地预测风险、评估疗效,最大限度地减少移植物丢失率。
2 肝移植术后PD-1 抗体的使用
肝移植术后免疫抑制剂的使用增加了肝癌复发风险,一旦复发,肿瘤生长迅速,极易出现多脏器转移,预后非常差。在常规的局部治疗或靶向药物等系统治疗失败的情况下,肿瘤进展很快危及生命,PD-1 抗体是这些患者最后的治疗选择。根据目前全球数十个相关案例的报道[3,15-19],肝移植患者使用PD-1 抗体后急性排斥的发生率约为28%~38%,发生排斥反应后的病死率超过60%。但也在一些病例中观察到良好的耐受性和显著的抗肿瘤效应,针对肿瘤的疾病控制率在21%~29%,疗效甚至不劣于非移植患者[15-19]。Luo 等[15]回顾分析了近些年肝癌肝移植患者复发后使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相关报道,发现死于排斥反应的比例仅占23%,远远低于死于肝癌进展的比例(77%),说明在疾病进展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死亡的情况下,免疫疗法针对这类患者是个可选方案。
理论上,PD-1 抗体的抗肿瘤机制与免疫抑制剂的抗排斥反应机制恰恰相反[20-21],但目前的数据表明这两者间可能并非是直接完全的拮抗关系,当同时应用于肝移植术后肝癌复发的患者时仍然能在治疗肿瘤和控制排斥反应间取得一定的平衡,使部分患者获益。我们应该思考如何更好地控制两者间的关系,探索免疫抑制和免疫治疗同时使用时的优化用药方案[15]。目前尚不清楚哪种免疫抑制能最有效地降低PD-1 抗体治疗带来的排斥反应风险。有数据显示,为了避免引发排斥反应而预防性地使用高剂量类固醇激素不会影响抗肿瘤疗效[21]。还有报道提出,调低他克莫司的剂量不会增加排斥反应发生率,同时不影响PD-1 抗体的抗肿瘤活性[20,22-23]。mTOR 抑制剂(西罗莫司或依维莫司)因在抗排斥反应的同时具有抗肿瘤特性而备受关注[24]。有一项回顾性研究[19]和一项荟萃分析[25]分别提示,在引入PD-1 抗体治疗时接受mTOR 抑制剂的患者排斥反应的发生率更低。临床上,许多患者接受了免疫抑制药物的组合治疗,目前缺乏高等级证据提出相对优化的免疫抑制方案。很多学者提出,预防性使用皮质类固醇以及低剂量的他克莫司和依维莫司的组合可能是值得考虑的策略[15,26]。
Munker 等[21]发现3 例出现排斥反应的患者移植物穿刺活检程序性死亡因子配体1(programmed death ligand 1, PD-L1)染色阳性,而4 例无排斥反应的患者则均呈阴性,因此提出移植肝组织穿刺活检评估PD-L1 的表达可作为使用PD-1 抗体后排斥反应发生的预测指标。笔者单位报道的初步数据也支持这一假说[27],我们已在此基础上发起了一项小型的临床试验对此做进一步的验证(NCT03966209)。DeLeon 等[18]的研究数据也支持移植物组织内PD-L1 表达可以预测排斥反应的发生,并进一步提出患者肿瘤组织内PD-L1 的表达联合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umor infiltrating lymphocytes,TILs)状态可能是PD-1 抗体抗肿瘤效果的预测因子。
接受免疫疗法的肝移植受者发生的急性排斥反应主要由T 细胞介导[28],容易与免疫相关性肝炎混淆。后者是一种PD-1 抗体药物引起的免疫相关不良反应[19,29]。当根据临床表现无法做出明确诊断时,应进行移植物活检病理检查[30]。免疫相关性肝炎的主要特征是以急性小叶性肝炎为特征,伴有孤立或融合性坏死,以淋巴细胞浸润为主,而同种异体移植物排斥反应的主要特征是门脉炎症、胆管损伤和内皮炎[28]。但有时两者似乎存在相似性,甚至单个肝活检可能同时呈现2 种病理特征,难以确定疾病进展中潜在的相互作用。Nguyen 等[31]研究发现,约有21%的排斥反应是抗体介导的。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病理表现往往有显著的毛细血管炎症及C4d 阳性染色,并能在患者血浆中检测到供体特异性抗体[32]。
接受PD-1 抗体治疗的肝移植受者发生急性排斥反应后进展为移植物失功并致死的比例很高。Gassmann 等[28]于2018 年总结的11 例肝移植中4 例发生急性排斥反应的患者全部导致死亡(100%)。Delyon 等[19]于2021 年回顾分析了21 例相关病例中8 例患者发生急性排斥反应,其中导致死亡5 例(62.5%)。与未接受免疫疗法的肝移植受者不同,使用PD-1 抗体引发的急性排斥反应只有29%对大剂量激素冲击治疗有效[28,33]。其他被尝试的药物包括英夫利昔单抗、抗胸腺球蛋白等[34],但都没有明确的疗效报道。虽然血浆置换术被认为主要是减轻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而不是细胞介导的排斥反应,但它可以加速循环中PD-1 抗体药物的清除,因此也可以考虑试用[15,28,35]。在已经报道的大多数患者中,上述治疗并不能导致临床改善,通常会出现快速的临床恶化最终因移植物失功而死亡。
综上,目前在肝移植患者使用PD-1 抗体治疗肿瘤的数据还很有限,但在引发排斥反应及抗肿瘤疗效这两个关注点上已有了初步的认识。目前还没有关于肝移植受者中使用PD-1 抗体的指南或共识,需要更多的前瞻性研究来确定其用于肝癌肝移植患者的指征和管理。目前情况下,应根据治疗目标以及其他治疗方案的可用性等对肝移植患者进行个体化评估,在移植物丢失风险和抗肿瘤疗效之间进行权衡取舍后做出是否使用PD-1 抗体治疗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