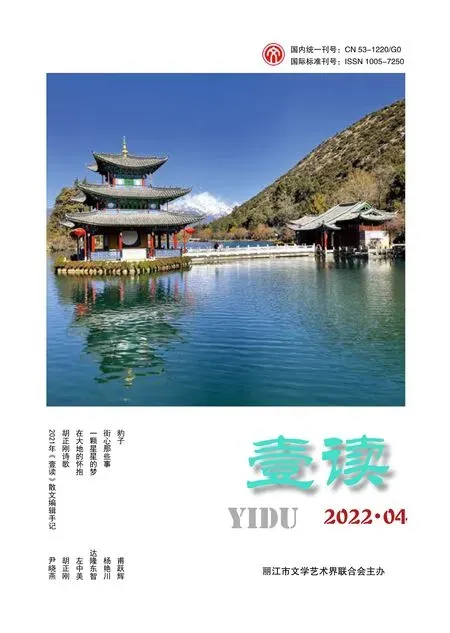徐老(外一篇)
◆赵振王
在我崇拜的偶像古今圣贤名流人群里,明代地理学家、旅行家和文学家徐霞客永远排在第一位。他弱冠之年许下“大丈夫应当走遍天下,朝临烟霞而暮栖苍梧,怎能限于一地终老此生”的誓言,用双腿丈量了大半个中国,一册《徐霞客游记》的皇皇巨著,足以名垂千古光照后人。我对他的崇拜,正是他那远征山水的矫健之腿和握笔书写“游记”的巨手。
我经常会幻想,自己能穿越到1639年,或者他阔步来到2022年。那么,我一定要在家乡永平,痴等着见一见他,亲手给他炒一盆黄焖鸡、煮一锅酸辣鱼、备一壶木瓜酒,在拉家常似的对话间,毛遂自荐做他陪同前行的挑夫或仆人。与他走几天路、涉几条河、翻几座山,就是此生至高的夙愿。我是“徐粉”、“金牌徐粉”。历来习惯呼他为“徐老”。这么一喊,便觉得他就在跟前,与他同坐在彝家土木结构的瓦房火塘边烤着火、煨着茶、喝着烧酒、促膝长谈。
此君始不负山青,意以青山作户庭。
著屐知渠能几量,褰裳访友自重冥。
闲图五岳为游钞,醉依三峰是寝屏。
莫笑东方多志怪,见随夸父逐圆灵。
这是徐老的生前好友、明末殉节官员——陈函辉盛赞徐老的诗歌《集吴澹人斋头为谈江上徐霞客游兴》。每读此诗,我就想起徐老那双朴实奋力的腿脚,曾搅动了那年的山水风雨。他孤身一人出门在外,风餐露宿、食不果腹,历尽了艰辛和危险,身后的家中还不时地发生着这样那样意想不到的变故。行走在滇西坎坷崎岖的山路上,他已是地道的中年人。此时此路听风看雨,他的心中竟有几多新意?
如果史料不出错的话,那么徐老穿行我的家乡永平境内的时间,满打满算也就五天。五天,于他个人精彩的一生而言,实在算不得什么。但对永平来说,就举足轻重了。
徐老路经永平,留下了《滇游日记二十九》这宝贵的篇章,足以让永平人世代光彩和荣耀下去。因人在旅途之故,徐老没有像桂馥先生那样长驻永平任职,细心感悟博南古道上东来西去的马蹄声和永平的厚土浓情对个人视角的冲击与心灵的洗礼,否则,永平在他笔下,必是一本大部头的书。
然而,徐老是厚爱永平的:
登其峻处,回望东山之上,露出层峰,直东而近者,乃狗街子、沙木河驿后诸脊,所谓博南丁当也;东南而远者,宝台圆穹之顶也。内平处亦有两三家当峡而居。循之西入,坞底成畦,路随涧北。二里,涉涧而南,盘南峰之腋而西。一里,透峡西出,则其内平洼一围,下坠如城,四山回合于其上,底圆整如镜,得良畴数千亩,村庐错落,鸡犬桑麻,但有灵气。不意危崖绝蹬之上,芙蓉蒂里,又现此世界也,是为水寨。先是闻其名,余以为将越山而下,至是而知平洼中环,山顶之水,交注洼中,惟山达关一线坠空为水口,武陵桃源,王官盘谷,皆所不及矣。此当为入滇第一胜,以在路旁,人反不觉也。
熟悉永平的人,一读此段便知徐老所记述的具体位置。“博南”、“宝台”这些字眼,如今已是永平的金字招牌,众所周知、家喻户晓。我之所以尊崇徐老,就与他写永平的游记文字有着天然的关联。字斟句酌地细读,真切感受着徐老笔下永平的奇山秀水,作为一个永平人的骄傲与自豪,无须夸饰就自然溢于言表。
“此当为入滇第一胜。”这是徐老“修辞立其诚”的肺腑之感,并非我狭隘区域主义者的瞎“爆料”。在我有限的想象空间里,徐老途经永平时,南方“丝绸之路”博南古道,一定以超乎想象的锦绣山水和胜景奇观,迎接过这位遥远的烟雨江南的才子游圣。否则,在他匆匆的步履下,那一字千金的《滇游日记》绝不可能留篇幅给永平。便是有,也绝不可能把他在永平境内的徒步细节,写得那般细腻耐读,如霁虹桥的大铁链般环环相扣,链接起自然与历史的漫漫时空。
徐老给永平留下了六千余的珍贵文字,让本来就有着悠久历史的永平,在他的浓墨重彩下“重量级”地凸显着绚丽的光芒,弥漫着悠远恒久的芳香。近四百年来,推崇徐老书写风格的人,不亚于崇拜他如风行走大地的数量。其中,最权威最有代表性的评价,就是明末清初江南文坛的盟主——钱谦益。他认为,徐霞客所作游记,贵在据景直书,文字直朴真实,不与古人游记争文章之工,是真正的游者之山水,是世上罕见的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看他写的游记,就像跟他一起,游走在各种山川奇景之中。
我相信,徐老留给永平的,就是“真文字”、“大文字”和“奇文字”。透过徐老写永平的文字,我似乎看到久远的博南古道上那位边走边看边琢磨、姓山姓水姓无畏的勇者,对苍茫远方的痴迷和对足下土地的热情。徐老一生的时间,基本都放在了旅行考察上,游历云南就达三年之久。我所以崇拜他,正被他“生于足下,死于足下”的不屈性格和勇于探险、敢于征服和求证求真的精神所折服。他这种刚毅坚卓的精神,给了我一个相对稳定的“运动”半径和奔涌不息的生命氛围,对后人的激励产生了难以估量的价值。
1639年7月29日,徐老结束“极边第一城”腾冲的考察,踏上重返鸡足山之旅。但他折返保山却没有再经永平,而是若南高原天空里一朵无比动人的彩云,由保山往东南方款款而去,沿枯柯河经右甸(今昌宁),循澜沧江而下顺宁(今凤庆)、云州(今云县)再折返顺宁,又过蒙化(今巍山)、迷渡(今弥渡)、洱海卫(今祥云),最后风度翩翩地归附于佛教圣地——宾川鸡足山。
徐老另择这条行者极少涉足的险途,是为了考察怒江、澜沧江及礼社江的水系源流。经他实地踏勘,不仅澄清了保山东河往南为枯柯河,再西南会勐波罗河入怒江而非“东下澜沧”,还否定了《明一统志》所谓澜沧江东合礼社江于定边(今南涧)入元江的说法,得出澜沧江南下车里(今西双版纳)直流入海的结论。
徐老回程没有复经永平,是他对澜沧江流向科学求证的一种使然,并非他在永平期间受了怠慢故意“绕道而行”。后来,他在写顺宁的文字里再次提到永平:
顺宁者,旧名庆甸,本蒲蛮之地。其直北为永平,西北为永昌,东北为蒙化,西南为镇康,东南为大侯。此其四履之外接者。
直北即正北,此“永平”即他曾途经的彼“永平”。徐老牵引着后人在遥远的回望中珍存于心间的那条漫漫旅途,他的足迹铺垫出缭绕了近四百年的美妙音符,是他留给神州大地的传世杰作。
徐老对三迤大地饱蘸浓情的赞美讴歌,馈赠了今人丰富多彩的旅游资源和旅游文化独特的科学内涵。尽管他终究只是过客,而且离我们也越来越久远了。但他的精神和文化价值,却更加熠熠生辉。
老屋
那是容纳我第一声啼哭的老屋,它看着我紫红色的肌体,脱离母体,被潮湿的红土温情地接住,山村的又一个小主人就这样降生了。
老屋,生长在遥远的澜沧江边,是典型的“三坊一照壁”结构,土墙、木架、竹子和茅草,或者青瓦构成。老屋不耐看,却耐住了几百年岁月之风的吹拂和袭击,至今迎着日月星辰岿然屹立于滇西的崇山峻岭之中,在西南丝绸古道旁遥望着远方盘坐着,回味着古代马帮进进出出时吹着的响鼻,留在历史小路上的生命冲击力,对现代文明血脉相依的精神牵连。
老屋,永远在我魂魄最悠远的制高点上微笑着,大青树和凤尾竹犹如一把把扇子,被老屋悠然自得地摇来摇去,笑听澜沧江滚滚南去时留下的涛声。
老屋,是我爷爷的爷爷王金壮年当马锅头时,从夷方(缅甸)驮回来的,一驮驮进出,又一趟趟来回,来得漫长而艰辛,充满了血汗质地的颜色和光泽,照耀我们祖祖辈辈生生不息的生命体,一如既往地顽强前行在生命的历程之中。
在一条千年古道上形成的整个马帮文化的构成要素里,马锅头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生命符号,成为一枚岁月的风铃随意地在风中叮当乱响。在那些极度分散各自占山为王的特定环境里,做茶叶、布匹、食盐生意的马锅头们,要行走自如地“穷走夷方”,换回翡翠玉石等建设自己的家园,没有过人的体力和超人的智力,那是绝对的天方夜谭,空话连天,永远只可能是悬挂在村口大青树上的幻想。如果我老祖王金没有一个人独抓两百多斤的驮子轻松自如上下马背的绝活,那也就不可能有我家现在这座让我们家族引以为自豪的老屋了。
在口头传承的家族光荣史实的王金老祖这一环,里面饱含了起伏跌宕的故事情节。王金在一次走夷方翻越高黎贡山的时候,被强盗拦路堵住要王金的马帮也要王金的小命。
“拿去吧。”我仿佛听到这么一句不温不火的话语的同时,猛然间看见王金一个人抓下一溜马驮子并整齐地摆在驿道上。“拿走。”耳边又有两个字像刚响过的火药枪,充满了冒烟的火枪味道。瞬间里确实伴有一声枪响的,老树丫上的一只憨斑鸠(野鸽子)应声落地。可以想见这种表演之后的效果是一个什么样子,落荒而逃的强盗“唰”一下就在王金的眼前消失殆尽,留下的是一条光滑得发亮的马帮路在王金的身前身后延伸着,往西直入缅甸再通南亚各国,朝东经大理、楚雄之后过金沙江,一直连着蜀国四川。
西南丝绸古道的发现是经过一番周折的。著名使者张骞在到达阿富汗后,发现那里已经有中国出产的茶叶和丝绸等等物品,他疑惑不解并断言肯定还有一条其它路径连通南亚。他回到祖国后,就专题给皇帝汇报了自己的惊人发现,皇帝高兴地听完张骞的陈述并派出队伍向预测之中的西南方向查访,查访那条未知的民间商道,是如何披荆斩棘开山过河地越过苍茫大地,最后抵达遥远的异国他乡的。终于水落石出了,中国真实地存在着第二条丝绸之路,而且,是靠民间的力量自发地走出来的。
我无法想象皇帝和朝廷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是如何的情不自禁又是如何的欣喜若狂,一条由国内起始连着涉过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三条大江以及无数山脉的漫漫商业道路,那是多么荣耀的旅途和辉煌的政绩啊,每一段路程、每一个蹄印、每一座驿站,霁虹桥、惠人桥、双虹桥,南(北)斋公房,花桥、蒲缥和杉阳古镇……哪一处都是血汗的凝结,尸骨的堆砌和生命的延续啊。王金留给我们家族的老屋就坐落在古道旁,老屋及我们家族的后人,都深受古代马帮文化的熏陶和洗礼,喜欢行走,用自己的双脚去探寻外面的精彩世界,并创造了混合兼容的边地文化。
老屋,是王金用马帮用青春用热血用生命驮来的换来的,也是他一生可以用来标榜人生价值的看得着摸得着的不动产。我是王金的孙子的孙子,又是老屋的儿子的儿子。
我的胎衣,是有出处也有去处的,它被埋在老屋屋檐外的一棵香椿树旁,紫红的香椿叶也该是我彤红胎衣的一种变化和延伸吧,老屋一直像一位慈祥的守灵老人,虔诚地为我守候着浓香的胎衣。胎衣还在,老屋还在,我心灵的呼吸声还在,看得着也听得见啊,我至今在远离老屋的一座警营里仍然可以看到自己的胎衣,在高原的烈日下发出山羊一般的咩咩声。
那些屋檐下的燕子窝,陈旧而富有生命力。燕子,曾经与我一样,是老屋最动感的主人。我们一起为老屋的兴衰而努力地酿制欢声笑语,乳臭奶香马粪的混合味道,曾经使老屋飘逸地走过了岁月最美好最经典的那一段。
老屋被我们渴望光宗耀祖的不屈的生命欲望推动着,一如阿妈每天推着的小石磨,可口的豆浆源源不断地流淌着,生命就这么在深山里延续,没有人回避和逃离,都深爱着大地上那些乳汁般白色的液体。血液和生命注定与山有缘,除却山,我们彝族就会觉得无依无靠,是山给了我们依托,有山也就有了生命的基础。
就说苍茫的高黎贡山吧,它对马锅头王金很重要,对王金的孙子的孙子也很重要,所以,高黎贡山永远是我诗歌创作的闪光点和支撑点:“男人/是高黎贡山/一生拖不垮//女人/是澜沧江/永远流不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