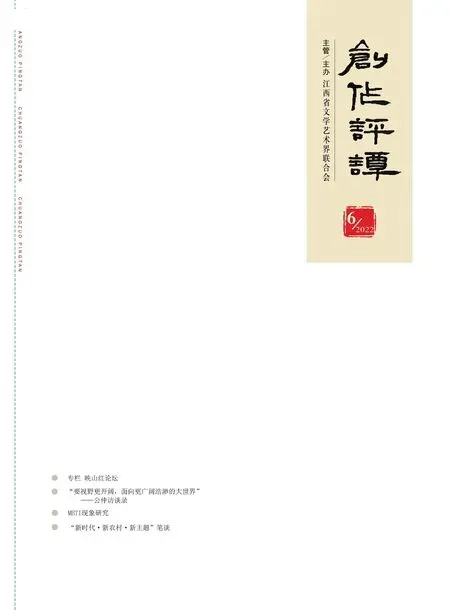“美善相乐”的陶艺追求
——袁乐辉访谈录
◎ 访谈人:刘飞燕
刘飞燕(以下简称刘):袁老师您好!首先祝贺您的个展成功举办。此次您展出的陶艺作品全是运用泥条盘筑的古老技法造型,并赋以妆彩,这使您的陶艺创作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与风格。此次展览的人物造型都半眯着眼睛,或歪着头,或伸展着颈脖,或沉浸于云朵,他们有着松弛又美好的状态,层叠斑驳的妆彩给人一种时间的沉淀感和静谧感,并能感受到一股从土里生长出来的自然与质朴气息。请您谈谈此次展览作品的灵感来源、制作工艺以及您的创作历程。
袁乐辉(以下简称袁):此次展览作品的创作来源是多方面的。一是跟我的生活经历有关,它有年少的记忆及当下的生活积累,也有我对艺术、生活的种种思考;二是表达艺术与生活之间的关系;三是关注自我生活的追求。我以前更多从观念、形式等方面进行创作,现在的创作更关注本心,本心能更自然、真实地呈现个人的审美观念。此次展览的作品是近三年的创作表现,主要围绕生活叙事,以生活叙事的情景方式融入东方诗意的情境描绘。正如您刚才所说,我的作品中有云朵、小鸟等元素,它们表现了中国田园式的、唯美、浪漫的生活形式。这种生活形式也是我个人所向往的。我认为陶瓷艺术既要讲究工艺,也要讲究内涵,这种内涵应体现在观念、形式、艺术价值等方面,给人带来一种美的感受、美的认知及对美好的向往。
灵感有时也是偶然获得的。有一天,我陪孩子午休,看到孩子在睡梦中轻合的双眼,以及他胖嘟嘟的脸庞,这让我体会到睡梦中的惬意美感,以及眯着眼睛的松弛感。类似这样的日常生活感受,让我逐渐形成了一个概念——艺术要更多地去反映生活本身,反映自己对生活的一种感悟。
此次展览作品的创作工艺是泥条盘筑技法和化妆土技术。泥条盘筑是一种古老的手工技法,它让我在后期创作中可以脱离模具。在使用模具成型时,通常会形成一种思维定式与认知惯性,只要做出一种模具样式就可以随意复制,但泥条盘筑的技法让创作更具挑战性,并有唯一性。泥条盘筑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通过泥条堆叠、粘贴成各种各样的形态。我塑形时不会刻意保留泥条盘筑的痕迹,刻意地保留手工痕迹会让人陷入一个过度强调工艺技术的旋涡。艺术的表达不是表现技巧,或是炫耀技术如何精湛。我选择泥条盘筑的原因:一是技术的古老,二是泥条盘筑技艺本身就富有一种现代的美感,三是它让我的艺术创作有随性轻松的捏泥状态。我预想在不刻意强调泥条盘筑技艺的同时做出具有时代感的作品。
化妆土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在新石器时期作为彩陶的护胎功用,后来到唐宋时期广泛应用。我以化妆土作为现代陶艺创作的表现语言,从白色化妆土的配比、彩色土的融合等工艺深入研究、拓展。我认为陶瓷艺术语言不必束缚在某种概念、某种工艺美术的特定范畴内。在工艺技术上,我跳出景德镇传统工艺中“有瓷质、玻璃质感”的审美观念,换以捏塑、涂抹化妆土的哑光肌理质感。由于带色化妆土的色彩过于明亮,容易刺激我们的视觉感官,所以我以哑光的质地表现,使作品具有内敛的特质。我认为制陶技艺要不断地从“瓷内瓷外”的维度来丰富和拓展。我的陶艺作品也不全用瓷泥,也会用粗陶泥。我选择带有沙粒感的粗陶,而烧制温度依然达到瓷的温度。
我的创作历程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2005年硕士毕业到2012年,这期间我一直在探索陶艺语言的表现形式并寻找适合自己表达的主题,这也是我早期创作风格多变的原因。在不断地创作中,我体会到陶瓷材料、工艺技术及创作者三者是相互交融的。同时也在思考陶艺如何从传统转化到现代,并立足于中国当下的文化语境,融入现当代艺术的潮流中。无论是我的构成形式,还是情色主题观念形式及综合装饰形式,都是这个阶段不断探索的结果。早期的作品主要有构成系列、镜子系列及青春期系列,这三个系列对我现在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并让我对陶艺有更深远的思考。
第二个阶段,我开始思考如何在艺术的形式和内容上有更好的表现,并以中国式的符号语言进行表达。2016年我去韩国访学,半年的访学生活彻底改变了我的创作手法,同时也是我创作历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我曾经的创作手法是通过景德镇的模具创作,即选择模具成型的方式并结合不同的装饰语言,如青花、粉彩等技法装饰。而到了韩国后,一切就回归到了自己最原始的混沌状态。在韩国,如果通过模具翻模创作,需要很高的成本。而韩国又没有类似景德镇的粉彩、青花等装饰形式,同时绘画方面也较缺乏,其整体的装饰风格也比较单纯。这些因素促使我选择以手工捏塑的形式——泥条盘筑技艺创作我的陶艺作品。正是这种创作的转型,让我回归到陶瓷艺术接近自然本身的艺术表现。手工捏塑的表现更加单纯、简练,简洁的形式语言可以清晰地表达我的创作主题。
第三个阶段是从韩国回来之后,我的陶艺创作又有一些变化。2018年,我以中国传统戏剧题材《牡丹亭》的人物故事申请到了国家艺术基金。这个戏剧故事的创作融入了一些概念,以生活叙事的方式创作,并通过情景再现的方式增强艺术感染力。这对我来说也是一次创作转变,是由形式美感过渡到生活叙事,再到一种精神内涵的表达。我过去的作品更多强调形式感,现在则回归到中国传统美学的含蓄与内敛表达。
刘:纵观您的陶艺创作,会发现您一直在形式、材料、主题等方面都有不同的探索。从您最早的构成形式到观念性形式,再到综合装饰创作及现在的捏塑妆彩创作,能看到您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关注点。如此次的展览作品,它们除了有外在形式美感,更有内在的精神表达。您一直以来的陶艺创作路程,可否看作是由外在形式逐步向内在精神转化的过程?
袁:这个讲得非常到位,这是一位艺术家从最初的艺术探索到艺术风格成熟的过程,也是生活阅历积累的过程。每个艺术家对艺术都会形成自己的认知,从形式到内容的填补,从外在到内在的表现,最后都需要往精神层面靠拢。我的作品精神是以叙事的方式去描述、再现不同人群的生活状态。艺术源于生活,说的是艺术需要用诗意的、叙事的方式再现当下的生活。创作早期,我不会过多地考虑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很多时候在关注观念与形式,现在我更多的是思考作品的精神内涵,因为艺术需要与他人的精神情感产生共鸣。我的“精灵系列” “云游系列”等作品,有些灵感源于《山海经》,有些则源于“90后”某些荒诞、怪异的审美取向。这些唯美、超现实主义、富有幻想又荒诞的作品,都离不开中国传统的文化内涵。它是东方诗意的显露,也是东方诗意的一种生活叙事。
我认为艺术最伟大的妙处有两点:一是富有想象力。富有想象力的作品是有内涵的。二是有中国传统艺术中的写意。写意讲究的就是内在的精神传达。我做“游梦浮生”这个主题展览的时候也是以中国写意的方式呈现。捏塑不是一种刻意的写实,而是一种本真的写意。我的《丛林之歌》《林鸟》《晨曲》等系列作品都有中国式的田园情结。这种田园情结是中国人的审美情结,也是中国人内在精神的诉说。当然,我的陶艺作品是有外在形式美感的。我是学院出身,受过专业的艺术训练,艺术的形式美法则在捏塑造型的过程中会自然而然地融入进去。
刘:相较于传统陶艺,您的陶艺作品有很强的现代感。请问您如何看待传统陶艺与当代陶艺?
袁:传统与现代是一个伪命题,也是一个永恒的命题。如果用时间概念去划分的话,肯定有传统与当代的区分,但是用 “美的、好的、高级与低级的概念”去概述的话,传统与现代则只是个相对的概念。我们来看中国传统造物,不管是陶器还是其他艺术形式,很多放到现在来看还是很当代;反过来,我们现在做的虽是现代,却不一定有当代性,还是很具传统韵味。艺术要往向前看,向前看就会有时间的概念。无论是传统陶艺还是当代陶艺,它一定要有时代感。时代感是要面向当下的,没有时代感的东西我们自然会把它划分到传统陶艺中去。反之,有时代感的作品或者在这个时代有创新的作品自然会把它划分到现代陶艺中去。我认为艺术家应该有使命感,要向前、向未来做有创意的作品。假设作品没有未来性,二十年、五十年、一百年过后,人们再去看会觉得很传统。我认为传统陶艺更多的是在延续中国传统的工艺体系,而现代陶艺更多的是面向未来的陶瓷艺术。
我认为当代陶艺需要包含“过去、现在、未来”这几个词。“过去”是指要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解,对东方文化美学有认知。“现在”是指要关注当下的社会现实。不管是具有批判精神还是材料的探索,都是对现代社会的一个关注和表达。“未来”则是说当代艺术如果不关注未来的发展,就不能叫当代艺术,因为当代艺术是放在历史的高度往前看的。我认为传统陶艺是支撑现代陶艺的基础,现代陶艺则把传统陶艺往当下延伸、繁衍,这也是面向未来的一个过程。无论是传统陶艺还是现代陶艺,一定要立足本土文化创作,要有中国式的表达。陶艺创作要博古通今,既要厚古更要有当下的文化立场。从工艺美术的范畴来看,传统陶艺支撑着工艺美术体系;从艺术思想性来看,当代陶艺更强调思想的表达。陶瓷艺术应是以思想为主,以工艺为辅,只有这样,中国陶艺才能走向未来,生生不息,并不断地形成新的艺术语言,产生新的造物美学。
刘:陶瓷材料是一个古老的创作媒介,一件陶艺作品的诞生需要水和火的介入,并经过由软变硬的物理形态变化。这其中既有技艺的必然性,又有窑火的偶然性。一件陶艺作品还未出窑之前,都有不可知性。在陶艺创作中,您如何看待这其中的必然性与偶然性?
袁:必然性是指任何艺术家都需要接受专业的训练,没有专业的训练是不可能对艺术语言、主题内容、题材选取等有足够的把握。偶然性则有点像道家思想中的启悟关系,也可以说是一种敏感性,艺术家无论是对生活还是对艺术都会有自己的敏感点;有了这种敏感性,自然就会对艺术有偶然性的表达,这是一种水到渠成的双向关系。当然偶然性里还带有时代机遇,当下很多艺术家的风格会有趋同性,想要在趋同的风格样式里脱颖而出,必须建立在必然性的基础。在必然性的历练中,随着时间慢慢推移,渐老渐熟,自然会形成自己的风格。必然性与偶然性也像艺术中感性与理性的关系,如果艺术家过于理性的话,他会太拘谨、不自然,恰是感性的成分补偿了他理性的认知世界,从而有了自然随性表达,所以我觉得必然性与偶然性是相辅相成的一种关系。以我个人的创作历程来讲,正是我近二十年在陶艺语言上的不停探索才形成了当前的艺术风格。一位艺术家如果没有探索的精神,就无法去感悟艺术的真理。也只有不断地探索,才能在哪天就“顿悟”了。我认为“顿悟”需要三个字,首先是“学”,第二个是“悟”,第三要“修”。最后是“我”的造化,即从这三个过程中慢慢地形成“我”的状态。这个“我”无论是“大我”,还是“小我”,甚至“自我”,都是在慢慢地形成必然又偶然的艺术内驱力。
刘:下一阶段,您是继续陶艺捏塑妆彩的研究、探索,还是会有新的创作计划?
袁:近五六年,我肯定还会用泥条盘筑技术继续陶艺创作,以人物肖像的方式去实践表现,用以小见大的方式去描述生活场景的关系。在未来我也会去做全身像或半身像或跟其他的动物结合的作品,等等。这是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妆彩的运用仍然是一个探索的过程,但是会更加地丰富。近两年形成的妆彩风格,可以说是自己艺术探索的积淀与风格式样的孵化。一种风格的积淀或一个系列的延伸,从成熟期到深入突破,可能需要十年左右。至于十年以后,我可能还会继续突破自己,因为一种新方式的形成,需要以“过去—现在—未来”的文化立场来支撑。只有适合我的艺术形式,我才能把它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果不适合我,并让我感到不轻松不自然,哪怕再好的表现形式,我也不会再深入下去。未来的陶艺创作,我将更遵从自己的内心,让自己开心。这样我才能更精细入微地创作,对艺术形式的表现也更得心应手。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对任何一种艺术语言的表现,我都会坚持“真、善、美”三个字。无论我走得多远,走得多长,“美善相乐”都将是我的陶瓷艺术走向生生不息的最重要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