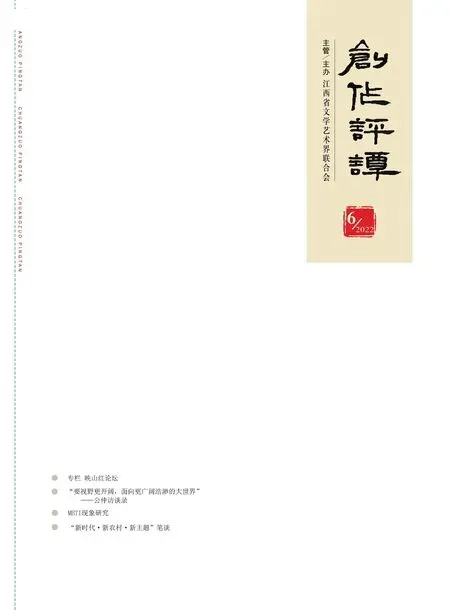新乡土写作的三种形态及其评价问题
◎ 余 凡
随着土地流转、现代集体经济成为农村发展的新景观,农村在生产方式、社会形态、文化观念等方面皆发生着新变迁。用文学书写这类农村现代变迁和观念变革,书写处于其间的农民的精神底色,是新时代乡土作家创作的重要主题。在新时代新理念的引领下,作家以过去或当下的某一固定时间段的记忆为叙述支点,或书写旧时乡土的美好时光,或书写新时代乡土的新主题和农民的新处境,这类创作即“新乡土写作”。以观照当下农村现实和理念表达的不同方式为划分标准,新乡土写作在写作风格和美学追求上主要呈现出三种形态:乡土的诗意歌咏类;文化人类学视角下的乡土纪实类;乡土问题的即时性诠释和出路想象类。这三种形态侧面反映出乡土作家观察时代的不同姿态。多文体形式的加入,也使得旧有的乡土写作形式、边界和观念发生着位移。
其一,乡土的诗意歌咏类书写。创作者以侨居者身份追忆故乡的生活点滴,倾心于书写故乡的旧时印象和今日新变,诠释乡村人渐趋裂变的世俗伦理,歌咏着现代乡村的风物与民俗文化。这类书写十分注重表达的文学性,代表着乡土写作的理想样态。如付秀莹的“芳村长篇小说三部曲”(《陌上》《他乡》《野望》),作者以远离者的视角回望乡土的常与变,探寻故乡人的婉转心曲。情绪情感表达上的恬淡与从容,是付秀莹新乡土写作的重要特色。付秀莹乡土写作的散文化、诗化倾向,使其创作具有“诗化现实主义”的特质。付秀莹以《红楼梦》那种贵族生活细节铺排的方式写现代乡村生活,是以精致写庸常的典范。
其二,乡土纪实即非虚构类书写。这类书写建立在走访现场、深度交谈和理性辨析的基础上,生成关于乡土的个性化“问题”。这类书写对乡土日常生活经验的描摹和乡亲的心理刻画是新鲜的。此时,作者充当着底层代言人的角色,打破了底层不可代言的“神话”。而这背后关联着的文献伦理学问题、社会调查的研究伦理问题、启蒙姿态的傲慢问题、先验的语言编码对非虚构表述影响的问题等,是纪实类新乡土写作被质疑的核心问题。如梁鸿的非虚构创作“梁庄三部曲”(《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梁庄十年》),梁鸿以归乡的“外来者”身份实录故乡社会关系与规则的新变,关注于时代进步语境下城乡对立甚至紧张关系、家乡人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境况,痛心于乡土的破败与人心的异变。梁鸿的这类写作,强调了社会学和人类学作为认识当下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方法价值。通过访谈对话,梁鸿获得了转型时代农村现状、农民精神处境的一种真实声音、一份精神证词。通过抵近梁鸿的学术资源和方法,可以看出,乡土纪实类创作有着很明显的向《忧郁的热带》《面具》《乡土中国》《中国士绅》致敬的特点。
其三,乡土问题的即时性诠释和出路想象类书写。这类书写往往对农村未来发展作积极乐观的想象,努力表现出在时代变迁语境下农民与土地关系的复杂面貌。由于其对农村的叙述是即时性的,因而,这类创作对农村发展过程中诸多新问题皆有较为真实的展现。如关仁山的“中国农民命运三部曲”(《天高地厚》《麦河》《日头》),以及《金山银谷》和《雄安雄安》。关仁山的新乡土写作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收获。关仁山往往以“先行者”的姿态对农村新面貌进行记录和歌咏,对新时代新农村建设作理想化的期许,这也使得其书写本身有着未来探索的性质。新时代新农村的发展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主题在关仁山的小说中都有所涉及,如土地流转、农业的集团化合作、生态农业和乡村文化重建等。关仁山的创作整体上揭示出关于农民命运的一个道理:农业塑造着农村新人的品格,然而,非农产业却是农村新人实现自我价值、带领乡亲脱贫致富的唯一路径。在《日头》中,金沐灶为改变农村局面提出了两个建议:一是建设集体农业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二是注重文脉建设,重塑传统文化,从人心人性重塑角度来推动乡村文明和道德的重建,以文化重建换来农村发展的知识、眼界和胆识。金沐灶对阻碍农村发展的主要障碍有清晰认知:资本进入农村,看似为农村带来了好处,实则与农民的利益无关;更为长远地看,则为农村和农业带来长期的伤害。《麦河》对农村未来的书写是积极的、理想主义的,农村改革之路前景光明。而《日头》则更多地呈现出农村发展过程中的矛盾与困局,叙述腔调是悲观的,对农村的发展有着深深担忧与焦虑。
三种形态的新乡土写作在展现乡村生活的新经验、乡村发展中的新变革上是相似的。如付秀莹在《陌上》中对农村选举腐败、皮革厂污染问题、猪瘟发生后的农副业合作社以及农民职工化等现象的书写,《野望》中对于返乡创业大学生的歌颂、对网络主播的赞美等,都与关仁山笔下所揭示的新现象、新问题相似。再如,梁鸿对转型时代乡村人心人性的书写、对乡村生活志与风物志的书写,与关仁山笔下所展现的状况相似。与第一种形态注重文学性的写作相比,后两种形态在直接而鲜活地展现农村问题上具有相似性。在阅读过程中,能够很明显地感觉到梁鸿与关仁山这两类书写在记录转型时代的中国故事、中国经验和中国问题上的自觉与创造。基于创作观念和价值立场的不同,对不同形态新乡土写作的评价存在着诸多差异。在呼吁和倡导“主题性创作”[1]、避免书斋式空想、杜绝不及物创作的时代语境下,影响三种形态新乡土写作评价的首要因素在于如何定位问题导向的乡土故事讲述方式上。
王春林对关仁山的创作有一个很典型的评价,恰恰指向乡土故事讲述方式的优劣评价。王春林曾基于思想和主题表现的文学性标准,指出关仁山关于“三农”问题的即时诠释和出路想象类写作的一个不足,即创作上存在着“理念过于直露”的“席勒式”倾向,而“古往今来,大凡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趋近于‘莎士比亚化’”。[2]所谓“席勒式”创作,即有着显著的主观主义倾向、直接的理念预设、强烈的民族经验投射在其中的创作形式,其体现出较强的思想性,极力追求表现时代现实问题和人的精神处境,而非与时代相背离的创作模式。所谓“莎士比亚化”创作,是建立在对言之不尽的莎士比亚创作的丰富思想艺术特质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即强调文学性、注重思想理念的间接而非直接传递、注重文学内在规律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就王春林的评价语境而言,“席勒式”与“莎士比亚化”的冲突即创作强调理念还是强调文学性的冲突。由于新时代的乡土写作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揭示新乡村发展中的问题,所以对“席勒式”与“莎士比亚化”作优劣判断与取舍,比概念的理想化区别下的取舍要复杂得多。
首先需要肯定的是,王春林对关仁山创作模式的批判是有道理的,站在文学内部评价标准上审视,理念直露确实是关仁山创作的掣肘。一旦乡土作家试图揭示新农村的新问题时,就很容易滑入为新而新、理念先行的陷阱。
然而,从非虚构角度、从记录中国乡土真实问题的角度出发,“席勒式”创作的价值与意义反倒需要被呈现和照亮。关仁山通过“三部曲”记录新农村新主题,进而表达其对“三农”问题的哲思,为理想的现代农业发展作鼓与呼,是关仁山创作目的之所在。作品中的人物和故事是表现“三农”思考的载体,这必然会出现“理念过于直露”的现象,揭示现实问题必然会造成文学性的削弱。换言之,关仁山对乡土的挖掘、探索和建构所立足的角度并非单单是文学,更主要是表达文学之外的目的,即对农村、农业和农民未来出路的一种认知和设想。此时,文学的内在标准显得不那么重要。且在非虚构写作日益凸显其价值的今天,“理念过于直露”对于表现新农村的新主题而言,恰恰是值得称道的。也因此,“席勒式”倾向恰恰是新乡土写作表现当下农村现实的必然选择。这表明,关仁山这一类型创作原本就不追求“莎士比亚化”的目标,这一目标亦不是其抱负之所在。注重文学性的评价逻辑会造成对关仁山创作理念的误识与误判。有学者指出:“在现代性的历史语境中,当代乡村作家对‘新乡’的书写,已不仅仅是一种文学性和艺术性的创作,更是对乡村现代性的一种深刻反思与有益补充以及对当代中国乡村未来的一种文学设计和艺术想象。”[3]这就凸显出文学性和艺术性之外的目的的重要意义。显然,关于乡村的“文学设计和艺术想象”,审视的中心在于文学之外的如社会学等学科门类。因而,当我们责难反映乡土现实问题的写作不够“莎士比亚化”时,我们的乡土文学观念可能是偏颇甚至缺失的。
对“席勒式”创作倾向的辩证认知,给我们提供了诸多关于如何放置新乡土写作中理念的位置以及新乡土写作的批评路向的重要启示。其一,作家创作倾向与作家的创作理念、精神追求有着密切关系,对不同创作形态的评价最终要回到对作家创作心理的阐释上。理念化写作往往注重对问题的揭示。在这一点上,乡土纪实即非虚构类创作与乡土问题的即时性诠释和出路想象类创作有着相似的逻辑理路,梁鸿的“梁庄三部曲”与关仁山的“中国农民命运三部曲”在注重农村现实问题揭示上具有相似性。对于关仁山而言,从“现实主义冲击波”到新乡土“三部曲”,注重现代意识的传递、注重文本的穿透力和注重对现实问题的洞察是其一直在坚守的方向。其二,虚构文学在表现新时代新农村新问题上的孱弱,凸显着“席勒式”创作甚至问题意识较强的非虚构写作的社会历史纪实意义。非虚构写作的兴盛是时代文学发展的悲哀,而“悲哀”的背后,是创作界和批评界对虚构创作所能达到的对社会现实问题揭示的深广度的失望。因此,乡土作家重视乡土问题的即时性诠释和出路想象这类凸显主题性的创作甚至非虚构创作的价值,以此来直观观照即时性的当下,充当时代前行中的“书记官”角色,参与当下历史的建构,就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作为转型时代乡村变迁的亲历者甚至是参与者的乡土作家,记录乡土“超稳定文化结构”的松动,为社会学家抵近乡土中国提供了一份鲜活的精神档案,更为多年后的研究者抵近时代历史现场提供了有效史料。在未来研究者那里,任何对乡土的及物书写,都会受到“敬惜字纸”般膜拜。记录转型中国乡村发展变迁的作品属于在场叙事,当我们将梁鸿和关仁山作为新乡土的新支脉时,就意味着突出了后两类写作形态对于乡村发展变迁的在场叙事作用。其三,新乡土写作在把握新时代的新气象和农村新时尚时,唯有对农村现实问题保持审美距离,才能确保作品的文学性;唯有注重“席勒式”创作,才能更直接地揭示乡村发展中的问题。这就形成了摆脱理念直露与及时捕捉时代新主题之间的悖论。孟繁华指出,由于中国现代性的复杂性,作家在表达乡村变革时呈现出多样的形态,且“某些书写乡村中国问题的作品,本身也构成了‘问题’的一部分”[4]。即新乡土书写内容、如何书写、书写形态及其背后的评价,也是时代乡土书写问题系统中的一部分,“席勒式”的、非虚构的书写为新时代“新乡土写作”内涵与外延的增殖提供了具体语境。
注释:
[1]李云雷:“‘主题性创作’是新时代下产生的一种新的创作类型,即用文艺的方式去表达国家的重大的主题。”见邵宏华、王佳雯:《新时代赋予文学以新的使命——专访青年文学批评家、〈小说选刊〉副主编李云雷》,《团结报》2022年8月13日。
[2] 王春林:《乡村大地的沉重忧思——评关仁山长篇小说〈日头〉》,《中国文学批评》2016年第1期。作为文学批评领域的两个重要概念,“席勒式”与“莎士比亚化”源于马克思、恩格斯评析拉萨尔剧作《弗兰茨·冯·济金根》所提出的观点。马克思说:“这样,你就得更加莎士比亚化了,而我认为,你的最大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54页)
[3] 彭维锋:《“新农村”镜像的文学建构:当代“三农”题材文学中的乡村书写》,《学术交流》2016年第1期。
[4] 孟繁华:《历史合目的性与乡土文学实践难题——谈乡土文学叙事的局限与合理性》,《光明日报》2017年3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