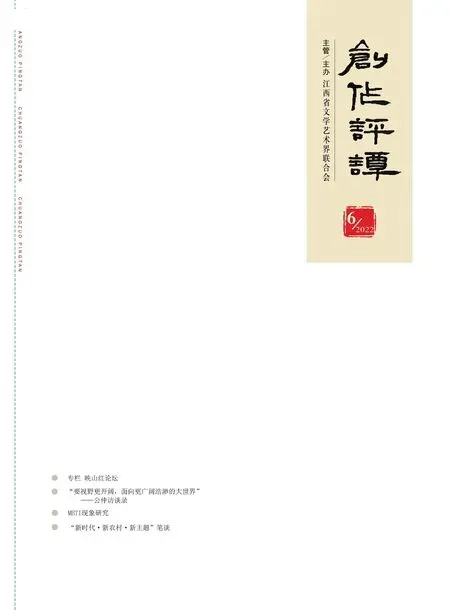“文学是我心甘情愿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
——公仲论
◎ 李洪华
在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华文文学研究领域,公仲都应该是一位格外值得钦敬的学术前辈。如果从1954年第一次以“公千里”的笔名发表文学评论开始算起,公仲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已逾六十年了。无论是在思想解放的新时期,还是在继往开来的新时代,他始终都以矫健的身姿穿行在学界与文苑,从当初在海外华文文学领域的筚路蓝缕,到后来对世界华文文学的整体探究,再到晚近对新移民文学的新思考,公仲在世界华文文学研究领域与时俱进,矢志不渝,不断提出新观念,搭建新架构,发掘新材料,扶持新作家。笔者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期在先生近旁学习、工作和生活,耳闻目染间,深切感受到先生的睿智卓学和人格魅力,其为人之真、治学之诚,无不为后辈学人之楷模。今年正值先生米寿之年,笔者在此试图对先生的治学之路做一管窥,既向先生致意,也为后学垂范。
一、当代文学研究的个性与创见
公仲最初耕耘的园地是中国当代文学。以敏锐的触角,及时捕捉当前文学新现象,大胆提出富有创见的文学新观念,是公仲在新时期进行文学评论和理论研究的风格。“文革”结束后,新时期伊始,文学创作并未完全摆脱“思想钳制”时期的理念化倾向,一些写作者大多以说教姿态揭露“伤痕”,“反思”过往。有鉴于此,公仲及时撰文,从文艺创作的本质出发,呼吁创作应该摒弃理念说教,注重形象思维[1],文章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后引起了广泛关注。随后,公仲多次在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上发表演讲,主张文学创作应该解除束缚,放下包袱,贯彻“双百方针”,遵循自身规律。公仲初期对当代文学研究的勇气和热情既表现在对某一时期文学现象和文学思潮的探讨上,也落实在具体作家作品的评论上,他的第一部文学评论集《当代文学纵横谈》便是最好的见证。1980年代初,当蒋子龙、陆文夫、贾平凹等作家的改革文学引来文坛一片喝彩时,公仲却不失时机地提醒人们,文学不能停滞,创作力避俗套,“改革文学要振兴,无论什么样好的‘套子’、‘模式’和‘框框’,都非破除不可”[2]。1980年代中期,当李延国、钱钢、麦天枢等作家的全景式报告文学潮头涌动时,公仲冷静地指出,报告文学要避免“非文学化、非艺术化的倾向”,谨防“大笔墨写事件而忽视了对人物的刻画”,“作品强调信息量和反思元素”时,不能“超过了甚至取代了文学的审美元素”[3]。无论是已有盛名的老作家还是新近出现的文坛新秀,公仲总是一视同仁,及时关注他们推出的新作品。在评论壮族作家陆地的长篇小说《瀑布》时,公仲并不因其获得当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一等奖而一味赞赏,他在肯定小说描绘时代风云和民族风情方面成就的同时,也坦诚指出作品在人物描写、情节发展和语言运用方面的不足之处。[4]对于曾经以革命历史小说创作实绩并提出超越“五老峰”口号而蜚声当代文坛的江西本土作家杨佩瑾,公仲则主要是站在中国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高度,把握杨佩瑾革命历史小说创作的发展历程和当代意义,分析其创作的三个阶段即生活原型向情节型过渡、从刻意追求情节向潜心塑造人物转向、从以人物为中心向思想内涵深层开掘,指出作者不断自我超越对当代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具有重要启示。[5]陈世旭是新时期登上文坛并引人注目的江西本土作家,公仲一直对其密切关注,1984年10月在《文学评论》“文学新人评介”专栏率先发表了《陈世旭创作个性的发展》。在文章中,作者从“真诚的心”“深邃的眼”“老辣的手”三个方面描述了陈世旭正在发展中的创作个性,指出陈世旭“有外科医生的沉着冷静”,思想“深沉而感情尤烈”,文辞“简练而内涵极丰”。[6]可见,公仲的评论可谓是外举不忌“贤”,内举不避“亲”,都是从文本出发,褒扬针砭无不落到实处。
公仲早期治学并不只是甘于对当代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进行散点式的“扫描”和“掠影”,而是怀有更大的“企图”。1981年6月,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在庐山召开学术年会,作为大会副秘书长的公仲竟然在会议期间向来自全国的专家学者散发了他编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纲要》。在新时期乍暖还寒的“早春”时节,公仲终因《纲要》提出了一些“大胆”的文学主张,“美化”了一些“有问题的作品”,而遭到公开点名批判,并被责令检查。直到四年后,公仲才把《中国当代文学史纲要》充实扩展为《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编》,交由江西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获得了该年度江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一等奖空缺)。《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编》本着“理清脉络,提供史料,阐明观点,引导思考”的指导思想,以文艺思潮为主线,以作家作品为基础,分“开拓”(1949—1956年)、“发展”(1957—1966年)、“曲折”(1966—1976年)、“复兴”(1976—1984年)四个阶段梳理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进程,分析总结了不同时期当代文学的成就与不足,尽量做到“思想解放些,观点鲜明些,条理清晰些,提法新颖些,史料充实些”。譬如,在总结三十五年来当代文学发展时,著者认为,“社会主义时代新文学的发展,三起两落,形成了两个马鞍形,其经验教训是极其丰富和深刻的”;在讨论文艺与政治关系时,著者提出,极左思潮“搞乱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忽视了文艺的特殊规律,助长了对文艺工作不合理地进行行政干涉的错误做法”,使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文学批评中的简单化、庸俗化有所抬头;在分析作家队伍时,著者强调,“文艺界的宗派主义由来已久,早在三十年代就有所表现,解放后,来自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两支文艺队伍也出现过一些问题,特别是在批判胡风文艺思想和反右斗争中,宗派主义滋长”。[7]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编》在分析主流文学的同时,还对每个时期的少数民族文学、儿童文学和电影文学单列章节,梳理分析。这部由姚雪垠题字、丁玲作序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编》不但是新时期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第一批著述之一,而且首开了个人主编的先例。正如丁玲所言,公仲“居然敢大胆地”编写出这样一部“有个性”、“有一定创见的当代文学史”来,尽管其中不免“有不尽妥当、完善之处”,但“这种尝试,这种精神”,应该是值得“肯定的”。[8]
二、华文文学研究的“筚路蓝缕”
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语境中,海外华文文学日益成为中国当代文坛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经历了1980年代的蹒跚起步、1990年代的开拓进取和21世纪的繁荣发展。
文学需要创新,研究更需要开拓。众所周知,公仲主要是以研究海外华文文学而广为学界称道的。作为国内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的最初拓荒者之一,公仲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便开始把自己的主要精力转移到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了。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编》的“后记”中,公仲曾如是交代:“限于条件,台港文学未能编入,只有待来年了。”[9]其后,公仲便真的身体力行起来。一方面,他借外出开会、讲学的机会,大量查阅、收集海外华文文学资料,并尽可能与相关作家、学者交流,下决心先把台湾新文学史写出来。另一方面,公仲以“但开风气不为先”的勇气在他任职的江西大学(现为南昌大学)开设“台湾新文学史”课程,集思广益,发动学生参与课堂讨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988年8月,历时四载、批阅多次的《台湾新文学史初编》终于问世了。这部由公仲和汪义生撰写的《台湾新文学史初编》,是国内最早的台湾文学史著述之一。著者尝试改变以往文学史的编著体例,以史论为主,把代表作家作品按历时顺序展开,分别在各个时期各个章节分期论述,对研究对象采取广义视角,凡与台湾有渊源关系,对台湾文学有一定影响和贡献的作家,均囊括进来。《台湾新文学史初编》全面综合论述了台湾自1920年代至1980年代60年间的文学发展历程,视野开阔,资料翔实,从广泛的横向联系和纵深的历史发展中把握台湾新文学的整体状貌和基本特征,无论是对影响较大的乡土派文学和现代派文学,还是对过去关注不够的通俗文学和儿童文学,都力求进行客观、公允地评价。正如艾青在给该书所作的“序言”中所说,该著“虽说初编,却已是那样完整、颇多独立见解的史书”,“宁要观点新颖,个性独特,也不要人云亦云”,“中国新文学史,没有台湾,怎能算完整?怎不觉遗憾”,“这本书算开了一个先例”。[10]这部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台湾新文学史初编》在当时引起了较大反响,《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文汇报》等都作了专门报道或评介,冯牧称之为“同类著作中的上乘之作”[11]。
虽然《台湾新文学史初编》获得了学界广泛的赞誉,但公仲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全力以赴地继续“开疆拓土”,把研究视野拓展到整个世界华文文学领域。1990年代末至新世纪初,相继推出《世界著名华文女作家传》(公仲任执行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和《世界华文文学概要》(公仲主编)。五卷本的《世界著名华文女作家传》以罕见的勇气和规模第一次整体展示了欧美、台湾、港澳、东南亚等世界各地区三十五位著名华文女作家的生活历程、创作成就和艺术风格,其中包括谢冰莹、苏雪林、张爱玲、林海音、於梨华、聂华苓、欧阳子、龙应台、张晓风、施叔青、李昂、三毛、琼瑶、席慕蓉、亦舒、梁凤仪等等。丛书内容丰富翔实,收录了大量访谈传主的第一手材料,语言生动活泼,观点新颖独到,对传主的成就与不足,不虚饰,不隐讳,既富于学术创见,又极具审美价值。毫无疑问,这套华文文学史上的拓荒之作填补了世界华文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空白,也因此获得了华东地区优秀文艺图书奖一等奖。《世界华文文学概要》是公仲对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又一重大突破,无论是在广度还是在深度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这是第一部关于世界华文文学系统、整体研究的专著。它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大陆的世华文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层面”[12]。著者大量运用第一手翔实材料,充分吸收最新研究成果,既从宏观视角,以时间为经,以地域为纬,厘清基本概念,确定研究范畴,辨析内涵本质,梳理主要线索,整体把握世界华文文学的发展状况及其与母体文化之间的联系和差异;又从微观角度,结合不同国家、民族、地域的历史文化语境,以华文作家作品为对象,分析台港澳、东南亚、欧美澳等不同地域、具体作家的创作个性,而且还十分注意对各地华文文学报刊、文学社团的介绍与分析。无论是在宏观架构、整体规模上,还是在编著体例、学术理路方面,这本书都可以名副其实地冠之以“世界华文文学史”了,但公仲却说:“编写文学史是一件很严肃的事,世华文学研究领域如此宽泛,我们的研究还存在许多不足,怎么能贸然打出‘史’的招牌呢?世界华文文学史以后迟早会有人写出来,我们这本《概要》对别人写史能有所帮助,内心就感到很欣慰了。”[13]从《台湾新文学史初编》到《世界华文文学概要》,既彰显了公仲不断开拓创新的学术精神,也体现了他治学严谨的学者品性。
三、新移民文学的新发现与新思考
在学界或坊间曾经流传这样一种说法,“古代”行不通,走“现代”;“现代”行不通,走“当代”;“当代”行不通,走“华文”。今天看来,虽然这种戴着有色眼镜的“学术等级论”已不再需为之多费口舌了,但是由来已久的“文人相轻”的倾向仍常露端倪。针对学界关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质疑和世界华文文学繁荣发展的现实,公仲既充满学术自信地提出“不必妄自菲薄”,也保持学术自省地告诫要警惕评论和研究的“滞后”。在回顾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三十年发展历程时,他以大量的研究成果和充分的学理依据反驳外来质疑:“三十而立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可以说,作为一门学科的建设,已经相当成熟、完整,发展的前景,也令人乐观。这与文学类的其他学科的建设相比较,是绝不逊色的。”然而,“与其他各门学科一样,我们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也并非尽善尽美,还存在不少问题。三十年的研究史,史论研究的不多,作家作品研究的不少。大多研究,未能突出海外华文文学特点也是优势的‘多元文化,多重视角’来研究,显得平板而老套”[14]。对于有学者提出,“华文文学研究的现状堪忧”,要从“语种的华文文学”转向“文化的华文文学”的研究,公仲不同意“现状堪忧”论,反对“偏执一端”的研究倾向,主张“华文文学研究应该有开放宽容的意识”,“方法论体系的建立,绝不在于提出了什么个口号,贴上了个什么标签,而是要实事求是地从文学本体的内在规律出发,细读大量的文学文本,不断深入地研究探讨,逐步地提炼、总结”。[15]
新世纪以来,作为海外华文文学生力军的新移民文学已成为繁荣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新移民文学的茁壮成长和繁荣发展当然少不了那些为之呕心沥血的培育者和助威呐喊的倡导者,而公仲应该是其中“最具成就和影响,也最值得钦敬的学者之一”[16]。早在20世纪末,公仲就提出:“新移民文学是世界华文文学的新生长点,它为世界华文文学注入一股新鲜血液,并正逐步形成了一支新生的主力军。它所创造的欣欣向荣的文学新景观,必将成为世界华文文学走进新世纪的新成就的新标志。”[17]新世纪以来,公仲更是以老骥伏枥的不已壮心不遗余力地关注、推介和研究新移民文学,《“万里长城”与“马其诺防线”之间的艰难突围——现当代欧洲华文文学新态势》《论新世纪新移民小说的发展》《华文文学新世纪的辉煌——华文文学之我见》《海外华文文学之我见——兼谈“落叶归根”和“落地生根”》《离散与文学》《八零后文存》,以及大量关于新移民作家作品的评论,都是他对新移民文学倾注心血的见证。在《“万里长城”与“马其诺防线”之间的艰难突围——现当代欧洲华文文学新态势》中,公仲主要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一批来自中国内地的欧洲新移民作家作品为对象,分别以“万里长城”和“马其诺防线”指代中西不同文化语境,论述并展望了海外新移民文学的创作现状和前景。他认为,新移民作家在中西两种文化观念的比照下,表现出与大陆作家和前辈移民作家不同的文学新质:与同时代的大陆作家相比,他们“创作基调积极乐观,表现了更多的奋斗精神与理性思考”,“在某种程度上……视野更为高远,思考更为深沉”,“已远远超越了当年的‘伤痕文学’”;与前辈移民作家相比,他们“更多关注生活本身的品质”,作品中更多“洋溢着智趣和理趣”,风格更“自由而感性”。公仲最后认为,新移民文学在中西不同文化之间来往冲突、彼此融合,“形成了一道独特的世界文坛上的风景线”。[18]这篇视野开阔、见解独到的长文发表后,很快被《新华文摘》转载。《论新世纪新移民小说的发展》是国内第一篇对新世纪新移民小说进行整体考察的评论文章。作者从题材广度、思想深度和艺术高度三个方面分析论述了新世纪十年来新移民小说的发展状况和创作成就。公仲认为,新移民小说在新世纪的发展,首先体现在它对历史文化的掘进和开拓,它不是“一般的平面意义上的开拓”,而是更关注“立体意义上的历史深层的掘进”,更具有“历史的纵深感和史诗的厚重度”;其次,对人类人性更广泛深入的探幽析微,是新移民小说深度掘进的又一重要标志。新世纪新移民小说常常“将人的生物性、生理性、心理性因素和家庭、社会、历史的影响紧密地有机地结合起来”,“将人性开掘得深入透彻、细致入微”,“弘扬人性的光辉,升华人的精神,净化人的灵魂”;第三,新世纪十年,新移民小说把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尤其是红楼梦技法和西方现代小说的手法“巧妙有机地结合起来”,“在艺术手法、叙述方式和结构技巧方面日臻成熟”。[19]在《华文文学新世纪的辉煌——华文文学之我见》《海外华文文学之我见——兼谈“落叶归根”和“落地生根”》中,公仲在对新世纪老中青三代华文作家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进行总结的基础上,以无可辩驳的文学事实提出“华文文学前景一片光明”[20]。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公仲以其敏锐的目光和宏阔的视野提出了他的新发现和新思考,即华文文学的“世界性寂寞”及其超越问题。他认为,新世纪以来尤其是新冠疫情肆虐时期,海外华文文学普遍存在一种“世界性的寂寞”,这一方面对于华文文学创作打开视野、拓展思路,大有裨益;但问题的另一方面,也许是更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如何超越这“令人烦恼的寂寞”,走向积极、乐观、更有意义的人生。公仲从中西文化观念差异进行追根溯源后进一步提出,在当今全球化的网络时代,我们的人生观念也要与时俱进,开通开放,主张落叶归根的,是正常健康的情感,我们支持欢迎,期待拥抱他们;由于主客观的种种原因,愿意滞留异邦,落地生根的,我们同样也该尊重他们的选择,祝愿他们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为人类也为祖国,做出应有的贡献。爱祖国,不看身在何处,要看心在何方,我们海外的作家们要放下一切思想包袱,摆脱无尽寂寞的困扰,轻装前进,为我们的华文文学创造出更多更好更美的优秀华章来。[21]公仲的这些发现和思考绝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建立在他对新移民作家作品的长期关注和大量阅读基础上的,仅上述两篇关于新世纪海外华文文学的综论文章,所论及的作家作品就包括王鼎钧、痖弦、林楠、严歌苓、张翎、虹影、周励、林湄、苏炜、沈宁、陈河、刘荒田、卢新华、少君、陈九、陈瑞琳、沈宁、叶周、薛海翔、陈浩泉、王威、孙博、戴小华、章平、曾晓文、施雨、沙石、陈谦、秋尘、曾晓文、黄宗之、朱雪梅、余曦、李彦、王瑞芸、吕红、融融、施玮、江岚、邵丹、曾宁、高淇、洪梅、山眼、梓樱、杜杜、秋尘、瑛子、休休、赵廉、饶蕾、郑南川、北奥、林婷婷、沈家庄、任京生、朴宰雨、顾月华、梅菁、陈屹、吴玲瑶、华纯、南希、美英、庄雨、张惠雯、孙宽、二湘、虔谦、杨慰慰、董晶、刘松、王哲、张棠、夏婳、安静、昔月、方丽娜、张琴、阿心、朱颂瑜、朗莉、冯玉、青洋等八十余位名家新秀及其创作。
《离散与文学》《八零后文存》《八八文存》是公仲晚近推出的文学评论集。在此之前,他还出版过《当代文学纵横谈》《文学徜徉录》《“万里长城”与“马其诺防线”之间的艰难突围》《文学新思考》等评论集。这些评论集主要反映了公仲在不同时期关于文学尤其是海外华文文学的审美感悟和理性思考。作为世界华文文学研究领域德高望重的前辈和长者,《离散与文学》入选首批“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文库”,应该是实至名归的;然而公仲却在《后记》中既表达了“荣幸”,又流露出“惶恐”,体现了他一贯为文大胆、为人谦逊的风格。书中虽然收录了作者前期的一些评论,但主要还是新世纪以来发表的有关新移民文学的研究文章。在《寄厚望于世界华文文学——兼谈四种思想意识的深化加强》中,公仲在肯定新移民文学成就的同时更进一步指出,当下新移民文学要提升品位,超越自我,必须深化加强“全球意识”“忧患意识”“批判意识”“忏悔意识”等四种思想意识。在《请以更多的热情关注海外华文文学——兼谈海外华文作家文化身份》中,公仲在呼吁学界以更多的热情关注海外华文文学的同时,对海外华文作家的文化身份进行了新的思考和界定,他提出:“凡祖籍中国,用中文创作(外语创作只要有中文译本的),对中国文学有帮助有贡献的作家,都可以算是文化中国的作家。”[22]在《新移民文学的新思考》中,公仲对新世纪以来的新移民文学进行了新思考,在分析优势和局限的基础上,指出其出路。他认为,大多数新移民作家在文化、阅历和思想上具有自身优势,但却也有难以摆脱乡愁情结、不甘位于边缘位置、消极表现文化差异等局限。因此,新移民作家应该发挥优势,体现世界公民意识,乐于边缘,在多元文化的交汇点上博采众长,表现文化新质,开创出“新移民文学的新生机、新出路”。[23]《八零后文存》《八八文存》之所以用了这样有些“直白”的书名,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书中的文章基本上是在八十岁以后所写,所收存的文章主要是对新世纪和新时代新移民作家作品的评论。在《新时代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的长文中,公仲将新时代海外华文文学的总体状貌概括为“遍地开花,群星璀璨”:一是从地域上来看,华文作家的分布越来越广,在原有北美和东南亚两大板块基础上,又增加了南美、东亚、澳洲、欧陆等新景观;二是从作品出版和发表园地来看,越来越开阔,既有国内的名社名刊,也有海外众多报刊和出版机构,更有广阔电子媒体;三是指新时代海外华文文学名家辈出,譬如“三驾马车”(严歌苓、张翎、虹影)、“陈氏四杰”(陈河、陈谦、陈九、陈瑞琳)、“五朵金花”(董晶、王哲、刘松、杨慰慰、张棠)等。作者最后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已经进入到一个鼎盛时期。[24]在《欧洲华文文学新景观》的长文中,公仲对长期被忽视的欧洲华文文学进行了整体梳理和重点评析,提出“欧洲华文文学是世界华文文学的重要发祥地和独特风景线”的重要论断,评析了“欧洲华文作家协会”、“荷比卢华人写作协会”、虹影、赵淑侠、吕大明、陈平、林湄、章平、余心乐、刘瑛、老木、余泽民、张执任等欧洲华文作家团体及其代表作家作品。[25]毋庸讳言,这些关于新移民文学的“新发现”和“新思考”,充分体现了公仲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和开放包容的治学思想。
四、文苑学界的拳拳之心与殷殷之情
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先生在《离散与文学·序言》中开篇便说:“公仲是我尊重的学者和兄长。我认为,他不仅是著名的教授,而且是充满活力的文学活动家和组织家。”[26]我想,大凡曾经接触或了解公仲先生的人,都应该会认同雷达先生的这番发自内心的真诚表白的。在学界同人中,公仲先生对于文学活动的组织能力和参与热情是有目共睹的。我们不妨以“管中窥豹”的方式来略举一些公仲在参与和组织文学活动方面的精彩片段。
1979年6月,在庐山,公仲以江西大学中文系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的身份参与筹备了全国十六所高校当代文学教材编写会,并当选为新成立的中国当代文学学会筹委会委员。1980年7月,在庐山,公仲以大会副秘书长的身份参与筹备、组织召开了“全国文艺理论学术讨论会”,陈荒煤、王若水、丁玲、吴强、徐中玉、钱谷融、王元化、公刘、白桦、梁信等文坛学界的大家名流,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四百多名专家学者欢聚一堂,共同研讨。这次“文革”后全国性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学术会议,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史乃至文化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981年6月,公仲以大会秘书长的身份筹备组织了“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庐山年会”。1993年8月,公仲以副会长的身份在庐山主持召开了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第六届国际研讨会,此次大会首次把“海外华文文学”更名为“世界华文文学”,会后公仲主编出版了研讨会论文集《走向新世纪:第六届世界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1999年6月,公仲在南昌主持筹办了中国小说学会第四届年会,并在年会上当选为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会后主编出版了年会论文集《面向新世纪:中国小说学会第四届年会论文集》。2004年9月,公仲在南昌筹划召开了首届新移民作家国际笔会,海内外六十多位著名作家与会,研讨了新移民文学发展的现状和前景,会后在南昌大学设立了新移民作家国际笔会联络处。2010年7月,公仲更以罕见的勇气和热情在南昌成功策划、筹备、组织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小说节。会议期间,举行了“中国当代小说高峰论坛”和“首届小说节颁奖晚会”,来自海内外的一百多位著名作家和批评家汇聚一堂,就中国当下小说创作状况、各自的创作体会以及文学教育等诸多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小说节引起了海内外文学界和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会后主编出版了《中国小说学会首届小说节文集》。
公仲对文学活动的热情并不只体现在组织各种创作和学术研讨会,把国内外的作家、学者请进来,共襄盛举,而且更多的是积极主动地走出去,与世界各地的华文作家和国内外的学界同人进行对话、交流,尽可能地获取第一手材料,拓宽学术视野,提升研究水平,为世界华文文学奔走呼告。20世纪80年代初,公仲领衔江西当代文学研究所(后随校名更改为南昌大学当代文学研究所)打算主攻世界华文文学时,就曾清醒地意识到,“我们在地域环境、物质基础等方面客观条件之不足”,“只能是隔岸观花,靠难以得全得详的间接资料来分析研究”,“故往往难免于失之全面准确”。[27]因此,随着中国内地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公仲和他的研究所同人们便开始致力于加强与海外的学术交流,一方面热情邀请海外作家学者来南昌讲学,另一方面尽可能争取甚至创造机会外出访学,出席相关的国际学术研讨会。1987年8月,公仲应邀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出席第三届台湾研究国际研讨会,并在大会上宣读论文《海峡两岸当代文学的异同》,引起很大反响。1999年9月,应邀访问奥地利、丹麦,并在维也纳大学和哥本哈根大学进行学术交流。2003年11月,应邀访问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并作题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现状和问题”的主旨演讲。2005年10月,赴美参加纽约皇后公共图书馆举办的“北美华人移民文学的历史与未来”国际研讨会,并作“新移民文学应深化加强四种思想意识”的主题演讲。2005年11月,应邀赴加拿大多伦多进行学术交流,并在多伦多大学和约克大学发表“新移民文学的新思考”主题演讲。2006年12月,应邀赴台湾清华大学讲学,主讲内容为“中国大陆当代文学现状及新移民文学”。2007年8月,应邀赴加拿大温哥华出席加拿大华人作协创会二十周年暨第八届加华文学研讨会,发表“离散与文学”的主题演讲。2008年5月,出席洛杉矶美中海外华文文学高峰论坛,发表“文坛两热点透析”的主题演讲。2019年5月,赴德参加法兰克福欧洲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发表“欧华文学新视野”的主题演讲。以上虽然只是公仲从事文苑学术活动的部分举要,但足可窥其“一斑”。事实上,长期以来,公仲常常利用出国探亲的机会,大量拜访北美、欧洲、东南亚等各地华文作家及其团体组织,而且还组织研究所其他成员出国进行学术交流。也许,在当前全球化日趋加深的背景下,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学者们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走出书斋组织和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已经成为学界的一种常态,似乎并不值得怎样的夸饰;然而,当我们把上述研究成果和学术活动与一位年近九旬的长者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就不由得肃然起敬了。
近来,耄耋之年的公仲仍然与文苑学界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一如既往地大量阅读,笔耕不辍,时而通过书信的方式与作家及时交流阅读新作的感受,时而通过写序的方式表达对新人的鼓励和对故交的激赏,时而直接投笔著文发表自己的见解,时而通过寄语的方式表达对世界华文文学的美好愿景和期待。在《给虔谦的一封信》中,他告诉作者:“我感到你的确很有一种钟情于历史书写的情结,而且那是与你的寻根问祖、念故乡恋宗亲的情怀分不开的。这是一种高尚的情操,足以使你的作品更显亲切动人、恩爱善良。”[28]在《给宗之的一封信》中,他坦言道:“这篇小说,我倒似乎觉得还不够到位,尚未能达到那种使人激情冲动的满足感。”[29]在《序王哲〈落叶飘飘〉》中,他称赞作者谦虚谨慎、精益求精的写作态度,肯定这部长篇“相当完整严谨,而且还很有些特色,很有可读性,叫人读之会爱不释手”。在《“当往天地间一展胸怀”——序浩泉〈阅读地球〉》中,他不无溢美地赞叹:“这部旅游文集可以说,是一部全球的旅游指南、深度的文化导读。亲爱的浩泉老弟呀,我会将你这部旅游文集,搁置案头,安放枕边,不离不弃,伴我终老。”[30]在《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创办20周年寄语》中,他动情地寄语:“我以为这个学会真是来之不易,应很好珍惜敬重。正因为我们国家还是要进一步改革开放,我们的学会也必将会更加发展繁荣。为此,我认为我们学会仍要坚持我们的民间性、学术性的原则,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坚持创新包容的气度,在这伟大的新时代做出更大的贡献。”[31]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如今,米寿之年的公仲仍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白自己对文学事业的不舍、对华文作家的钟爱:“文学是我心甘情愿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评论则是我为文学事业作贡献的一种手段。尽管是为他人作嫁衣裳,我也无怨无悔。只要自己尽了一份力量,对作家、读者能有一丁点儿帮助,我就心满意足了。”[32]“我不敢高高在上,对作家作品指手画脚,评头论足,只想与作家读者交个知心朋友,掏心掏肺,促膝谈心。”[33]“我所追求的是乐观、开朗,精神不死。进入耄耋之年,也当有所信,有所求,有所用,有所为,而后有所终。”[34]“生命有限,来日无多,一种紧迫感和使命感叫我不能停歇。”“我只能快马加鞭,勇往直前,在我的余生之中,为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事业,再尽最后一份力量。”[35]流溢在字里行间的无不是公仲对世界华文文学的拳拳之心和殷殷之情。值得欣慰的是,在所有朋友的印象中,“公仲很年轻”。当然,说他年轻,不仅仅是因为他仍然每天坚持游泳和散步,“浑身上下依然洋溢着一种年轻人特有的朝气与活力”[36];更多的是,因为他仍然活跃在各类学术报刊和学术活动中,为人和为文时常会率真地流露出些许可亲可爱的“偏激”[37]。是的,公仲先生永远都怀着“一颗年轻的心”。
注释:
[1]公仲:《从看图识字说起》,《文汇报》1978年2月23日。
[2]公仲:《当代文学纵横谈》,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第25页。
[3]公仲:《当代文学纵横谈》,第179页。
[4]公仲:《当代文学纵横谈》,第94页。
[5]公仲:《当代文学纵横谈》,第95页。
[6]公仲:《陈世旭创作个性的发展》,《文学评论》1984年第5期。
[7]公仲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编》,江西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1、177、672页。
[9]公仲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编》,第673页。
[10]公仲、汪义生:《台湾新文学史初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页。
[11]陈公仲:《离散与文学:陈公仲选集》,花城出版社,2012年,第319页。
[12]潘亚暾:《筚路蓝缕的拓荒之作——评〈世界华文文学概要〉》,《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1年第1期。
[13]公仲主编:《世界华文文学概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612页。
[14]公仲:《灵魂是可以永生的》,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4年,第205页。
[15]公仲:《灵魂是可以永生的》,第177页。
1.2 细菌孔蛋白表达缺失伴产ESBLs和AmpC ESBLs和AmpC的产生均由质粒编码并常见于肠杆菌科,有学者[6]认为这与诱导型或去抑制型染色体基因酶的高表达有关。孔蛋白属于革兰阴性菌外膜上的蛋白质,由跨膜蛋白形成孔道,可允许抗菌药物通过。当其改变或丢失,同时伴 ESBLs和(或)AmpC高产时,可致抗生素在细菌外膜上的扩散速率减缓以至于药物不能进入细菌内部从而产生耐药性。
[16]陈公仲:《离散与文学:陈公仲选集》,第1页。
[17]公仲:《文学新思考》,江西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60页。
[18]公仲:《“万里长城”与“马其诺防线”之间的艰难突围——现当代欧洲华文文学新态势》,《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19]公仲:《论新世纪新移民小说的发展》,《小说评论》2010年第2期。
[20]公仲:《八八文存》,美国南方出版社,2022年,第16页。
[21]公仲:《文学新思考》,第57—59页。
[22]公仲:《文学新思考》,第80页。
[23]公仲:《文学新思考》,第60页。
[24]公仲:《八零后文存》,美国南方出版社,2020年,第33页。
[25]公仲:《八零后文存》,第44-70页。
[26]陈公仲:《离散与文学:陈公仲选集》,第1页。
[27]公仲、汪义生:《台湾新文学初编》,第390页。
[28]公仲:《八八文存》,第75页。
[29]公仲:《八八文存》,第72页。
[30]公仲:《八八文存》,第27页。
[31]公仲:《八八文存》,第20页。
[32]公仲:《文学新思考》,第1页。
[33]公仲:《八零后文存》,第4页。
[34]公仲:《灵魂是可以永生的》,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4年,封底。
[35]陈公仲:《离散与文学:陈公仲选集》,第322页。
[36]张渝生:《永远的青春——公仲印象》,《创作评谭》1991年第3期。
[37]汪义生:《一位有真性情的学者》,《世界华文文学论坛》199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