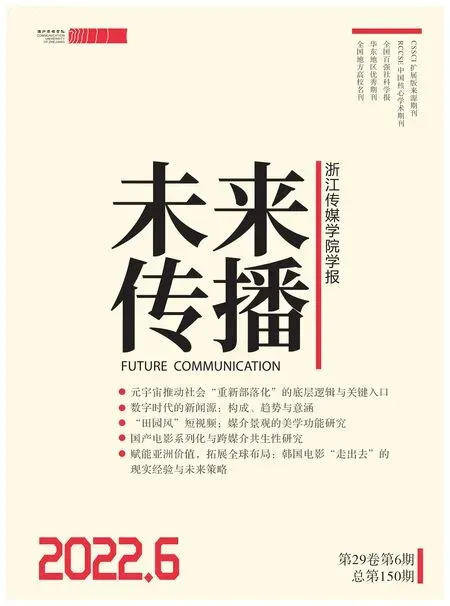赋能亚洲价值,拓展全球布局:韩国电影“走出去”的现实经验与未来策略
张 燕,张 亿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北京100875)
对亚洲乃至全球电影市场而言,韩国电影的组合拳“韩影—韩星—韩国文化”的威力始终不可小觑。21世纪以来,洪尚秀导演携演员金敏喜先后拿下4座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杯;2019年韩国电影百年之际,奉俊昊凭借《寄生虫》(Parasite)一举拿下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棕榈奖,随后横扫美国电影奥斯卡奖最佳影片、最佳国际电影、最佳导演、最佳原创剧本四项大奖。《寄生虫》扬名世界之后,在世界范围内极大程度地推升了韩国电影的创作影响力、韩国影人的关注度以及韩国电影产业的全球振幅效应。2022年6月初,朴赞郁凭借《分手的决心》(DecisiontoLeave)赢得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宋康昊斩获影帝,成为韩国首位获得三大国际电影节影帝的演员。韩国在电影方面的文化输出以及产生的综合效益,不可谓不盛况空前。即使在全球文化消费跳水萎缩的2021年,韩国仍创造了年度观众人均观影4.22次的傲人数据,虽较2019年4.37次的历史高位有所下降,但这一电影强国的重要指标已然连续三年稳居世界第一。自2018年以来,韩国已经实现了2003年卢武铉政府提出“让韩国进入世界第五电影强国”的远景规划,目前已成为排名第四的世界电影大国,并持续推动韩国电影进一步高质量发展与全球化拓展。
安危相易,辉煌之时危机亦相时而现,韩国电影“走出去”的难题更加凸显:一则,韩国本土电影市场基本饱和,电影消费能力强弩之末,内需扩展前景有限;二则,韩国电影对外依赖的瓶颈劣势越发明显,亚洲占比过重,欧美则一如既往高筑文化壁垒;三则,韩国电影抗击意外风险的硬实力亟待增强。在新冠疫情肆虐的情势之下,全球文化产业同此凉热,身处困境的韩国电影“走出去”能开辟多少市场空间、发挥多少艺术效能、反馈多少商业价值与文化影响,无疑是韩国电影能否在全球性的文化博弈中行稳致远的关键。
事实上,作为东亚地区的中等发达国家,韩国的经济基础、文化资源、区位优势等并不明显。与亚洲其他国家相较,5200万左右的人口总数比较少,更遑论基数红利,然而韩国电影却屡创电影佳片高票房收益的“汉江奇迹”。这种“小大之辩”引起了诸多国内电影研究机构和学者的广泛关注。自2015年以来,北京师范大学亚洲与华语电影研究中心通过《亚洲电影蓝皮书》系列和“亚洲电影论坛”的联动形式,在亚洲电影的宏观学术视野中,检视韩国电影历年的产业数据、文化现象和代表作品;华中师范大学亦举办“中韩影视国际论坛”,对韩国电影进行广泛观察,产出相当体量的学术成果。研究韩国电影的代表性学者专研之处各有千秋:学者张燕锚定内容生产、传播机制、话语创作、身份意识等维度,从史论、理论、本体、现象剖析韩国电影的历史与当下;学者范小青从产业分析、类型创作、导演研究等角度对韩国电影展开详实研究;学者李道新、彭涛对韩国电影的研究涉及影史研究、艺术话语生成、意识形态博弈;学者峻冰、石川从美学风格演变、艺术思潮、跨域翻拍等角度研究韩国电影等等。
通观国内韩国电影的研究,多集中于文化现象、导演研究、类型研究、个案分析和明星研究,至于从亚洲乃至全球语境出发,全景观照韩国电影“走出去”的流程,即产业创立、行业发展、宣发运营与国际传播的全生态研究,仍属于热研究中的冷思考,并不多见。本文基于韩国电影“走出去”的历史脉络与现实经验,展望韩国电影发展的未来策略,以期在梳理与比较中,助力中国电影讲好中国故事,完善国际传播矩阵,建成电影强国和文化强国。
一、 韩国电影“走出去”的经验总结
针对“第三世界亚洲电影”(1)此处的“第三世界”应依照詹明逊的个人定义:“我不认为诸如此类的表达方式能够表明在资本主义第一世界、社会主义集团的第二世界以及受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其它国家之间的根本分裂”。詹明逊“本质上是描述的态度来使用‘第三世界’这个名词”。具体释义可参见Fredric Jameson. Third-world Literature in the Era of Multinational Culture[J].Social Text.1986.的理论研究,学者弗雷德里克·詹明逊(Fredric Jameson)提出了由“地缘政治美学”[1]进入的观点,并由此得出结论“就其外在形式与内在本质而言,(亚洲电影)必定是一种意识形态”[2]。尽管詹明逊的观点是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美苏对垒的冷战末期以及检视中国、韩国、印度等亚洲国家电影跨越式发展的具体语境中提出的,但“地缘政治美学”这一概念的提出,为深掘韩国电影“走出去”的缘起及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配套措施,确实提供了新的切入点。
韩国电影“走出去”的历程,伴随着韩国政府对文化产业自上而下的统筹规划,在作为文化产品的商业盈利属性和作为意识形态功能性工具的政治治理属性之间,韩国电影实现了微妙的平衡。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民选政府的陆续上台,韩国政府与国家领导人推进韩国电影的产业发展与强国建设,各届领导人为不同时期的韩国电影在政策层面规划出阶段性发展的多元方向,这些与施政理念融合的电影发展方向,自然也具有相当鲜明的阶段性和理念先行特征。
1986 年,全斗焕政府提出“文化与国家的发展同步化”,包括电影在内的韩国文化产业得到合法性重视,文化不再单一作为统治手段,转而向新自由主义经济转轨;1993年,金泳三政府确立“文化立国”策略,并发表年度总统报告,剑指“好莱坞电影《侏罗纪公园》(JurassicPark,1993)的收益相当于售出150万台现代汽车的索纳塔所获取的利润”[3],趁着四野震动、国民骇然之际,顺势出台《电影振兴法》,吸纳民间资本,将影像业划至制造业,以工业标准减税降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在被美国的“开放市场”胁令,韩国进入全面民营化、脱离管制化时,金大中政府以“扶持但不干涉”的理念推动韩国电影产业转型,出台《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著作权法》《影像振兴基本法》《广播法》《演出法》等配套法律,自由与统制并举,竭尽所能咬定了本国电影配额不低于40%的生命红线。在政治与文化的双重博弈中,韩国电影寻找到了自身发展的攻守策略——开启以配额制保护国产电影、提升本土市场竞争力的防御机制。同时,广泛借鉴好莱坞营销制片模式,师夷长技建构自身,渐次筹谋完成“走出去”的攻略布局。
进入21世纪,韩国电影产业发展取得了史无前例的优异成绩。2001年,在韩国电影本土市场占有率超过50%,国民观影人次超4000万人次,《生死谍变》(Swiri,1999)、《醉画仙》(StrokesofFire,2002)、《我的野蛮女友》(MySassyGirl,2001)等类型电影成功“走出去”的向好局面出现后,卢武铉政府对电影产业结构重点布局,在其任内公布的《电影产业中长期发展计划(2007—2011)》中,六大主要建设课题之一即“扩大韩国电影海外输出范围”。李明博政府上台后,“韩流”已在亚洲乃至欧美地区风靡。李明博政府继而加大力度进行韩国电影的海外市场拓展,深度融合韩国电影与韩国文化,韩国电影的国别特色和类型特征愈发明显,同时,投资数千亿韩元扶持电影技术产业,特别是CG(computer graphics,计算机动画)技术发展,贯通了电影业全产业链。朴槿惠政府制定三大国家政策方针,即“经济复兴、国民幸福和文化繁荣”,着力促成韩国电影产业发展繁荣和韩国电影世界化,2016年文化与体育部专设CG/VFX基金,鼓励优秀人才投身高端电影技术研发与创作。文在寅政府在延续往届文化政策的同时,更加鼓励韩国电影的全产业发展,身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文在寅甚至亲自下场为韩国电影造势。例如2020年2月10日《寄生虫》拿下奥斯卡四项奖项的当天,文在寅在推特上发文祝贺,其中“《寄生虫》以最韩国化的故事打动了世界人民的心”“韩国电影与世界电影媲美,开始了新的韩国电影100年,非常令人振奋”“为了让我们的电影人尽情发挥想象力,无忧地制作电影,政府也会一起努力”等表述,无疑是其对韩国电影发展秉持积极支持态度的最佳注脚。
立足本土,布局全球,韩国政府完成宏观政策的顶层设计后,韩国电影“走出去”的战略实现,转而仰赖于官方引领、业界实施与民间认同的常态落实层面。政府部门的宏观统筹与资本公司的商业化运营推广和韩流文化的社会性消费推广多线并行,着力保证“走出去”成效显著。
韩国政府的电影职能部门分工精细,专设帮助韩国电影吸引外资,减少税收,加强内容企划、创作和流通,支持国际传播并提供对外翻译全额补助等措施的文化体育观光部。此外,设有大力推动本国文化企业外向型发展,注重内容建设和人才培养,发掘和扶持本土文化创意,为韩国文化企业定制投资融资金融辅助服务的文化产业振兴院。二级下辖执行部门中,隶属于文化体育观光部的韩国文化中心亦为韩国电影“走出去”出力良多,其在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大洋洲的28个国家设立了33个韩国文化中心,便于实时洞悉各大战略市场的消费常态与文化动态,同时,肩负寻找并资助韩国有潜力的文化事业海外落地生根、项目在地孵化的保障任务。
以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为代表的行业性专业机构得到顶层下放的部分权力,一方面,搭建日常性、规律性的电影交易渠道,每年在威尼斯、戛纳、柏林等国际性电影节展中,借助重要专题活动“韩国电影之夜”将优质韩国电影推广到世界影坛。另一方面,通过参与制定相关福利政策,吸引国外资本对韩国电影、韩国市场、韩国技术与场景的关注,变相强化韩国电影的跨界合作。例如提供相当份额的税收减免,鼓励来韩拍摄,再如广泛设立办事处,反哺完善国际交流合作机制等。与此同时,市场规划层面,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建有票房系统KOBIS(Korean Office Box Information System),便于独立采集、评估市场数据并预测类型电影发展趋势;宣传推广层面,韩国文化和信息服务网KOCIS(Korean Office Culture and Information Service)与韩国影像资料院(Korean Film Archive)双管齐下,向全球观众免费提供线上搜索并观看韩国电影的资源,因地制宜举办文化周、文化月、文化展等推广活动,吸引观众沉浸式体验韩国电影,育成韩国电影消费习惯。
伴随政策的有的放矢和职能部门的有效联动,有利于打造韩国电影品牌、服务韩国电影发展、树立韩国文化形象的各类电影节也应运而生。其中釜山国际电影节、全州国际电影节、富川国际幻想电影节、济州国际电影节等都已成长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区域性电影节展;而首尔独立电影节、釜山亚洲短片电影节、首尔亚洲国际短片电影节、首尔青少年电影节等也为艺术电影、独立制品、内容创新、人才引进、技术升级发挥了独特作用。
韩国电影企业建成专业集成度极高的文化全产业系统。希杰(CJ)、乐天(Latte)等财阀辖制娱乐业,纯商业集团管理,依靠敏锐的商业嗅觉和灵活的市场策略,精准弥补方向性政策条款中“肉食者鄙”的偶然漏洞;纯资本导向专业运作,以小博大,引导外来资本耦合韩国本土的基础条件和文化特质;纯效益考量评估,从投资和开发,从制作到发行,从建设院线到线上平台,多措并举。韩国电影企业的垂直运作和系统体系,为韩国电影的进一步发展带来源头活水,持续为“走出去”的形式和内容供能续航。特别是在全球消费主义盛行之下,韩国电影配合“韩流”的文化攻势,韩国料理、韩国服饰、韩国文学、韩式化妆品乃至生理性的韩国整容医疗相互策应,一度呈现亚洲乃至世界范围的爆发式消费性文化推广的利好局面,利好的消费又反哺了韩国电影的生产,进而增幅其文化影响力和潜在市场引导力。
就韩国电影的发展成效而言,自20世纪80年代末至21世纪初,韩国电影向上发展态势始终如一,在政商合力强化的输出路径、韩国影人的持续努力与优秀影片及剧目的井喷等三重积极因素累加之下,单一影片出口转向技术服务类乃至全产品出口,海外运营结构得到后续保障,逐步趋向于好莱坞的成熟工业体制;内容创作杂成其大,吸收亚洲在地经验,迎合国际竞争趋势和当代艺术潮流,创造韩国电影自身具有“地缘政治美学”特征的艺术风格;攫取丰厚经济效益之余,技术链、产业链、传播链、价值链充分延伸,实现了韩国文化的“走出去”和韩国意识形态的对外输出。
然而,韩国电影“走出去”属于典型的输出型经济结构,偏向“买方市场”的乙方身份,无疑受到区域性政治变化和世界性经济波动的影响。2005年韩国电影海外出口曾创下7599万美元的空前佳绩,盛极而衰,纵享贸易逆差进而席卷亚洲的“韩流”立刻被亚洲乃至欧美地区其他国家以各种保护性防御措施加以抵制。2006年韩国电影海外收益断崖式回落,负增长68%,锐减至2451万美元,随后一路走低,直至2010年后方才重新上扬,[4]苦心孤诣十年,步步为营至今才恢复元气。而这样任海外市场和文化强势方拿捏的“小冰期”窘境和“过山车”波动,恰恰暴露出韩国电影“走出去”的诸多问题。
二、 韩国电影“走出去”的问题透视
波德莱尔在研究艺术的现代性时指出,“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与不变”[5]。作为创下世界纪录的所谓“电影强国”,韩国电影的发展难以脱离地缘,其瓶颈与“地缘政治美学”的现代性“变与不变”问题实则一般无二:囿于短促的执政周期,韩国电影政策连续性差,纵使电影发展大局向好,但长效措施往往保障无力,甚至间歇性出现因党派政见不合而相互掣肘的情况;创作内容层面,盲目秉持韩国文化为主为尊,核心吸引力和竞争力不足,类型单薄,大片有量无质,头部大片稀缺;市场统筹层面,国内宏观管理能力欠缺,文化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趋于饱和的国内市场为电影生产雪上加霜,海外市场布局缺乏良性均衡的调整技巧和长远成熟的经营智慧,亚洲市场被过度依赖,与其他地区相比严重失衡。
就政局与政策变化而言,1987年韩国完成宪法修订,标志着韩国社会民主化转型。1993年以来,国家权力始终由保守党与进步党两派轮流坐庄,受到地域主义、代际变迁和民族主义极大影响,随着政权更迭,电影政策也在偏“左派”或偏“右派”中反复横跳,甚至会因政治阵营不同,强行扭转前任的施政方针。例如朴槿惠政府上台后,一度将前任李明博政府的电影政策收紧,20世纪90年代韩国把中国放在海外市场的龙头老大位置上,寻求循序推进、密切合作,但由于朴槿惠政府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对美国的诉求,例如韩美军事基地萨德问题严重损害中方利益,导致中韩电影交流与合作出现长时间的中断与停滞,继而痛失中国市场。继任的文在寅政府对韩国电影“走出去”实施了相对积极的施政管理,但因此前军事外交影响导致的被动局面无法解决,韩国电影对中国的海外输出被迫向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两地迂回寻求合作。
韩国电影具体发展极大依赖于综合电影投资发行公司——希杰、秀宝(Showbox)、乐天、Next Entertainment World(简称NEW)、Cinema Service等,这就使得韩国在全面学习美国好莱坞模式过程中埋下显著隐患——资本财团全面地把持电影全产业环节,集团化垄断情况愈演愈烈,商业集团的长期规划与政府政策的频繁易帜并不合拍,两者存在携行之难。同时,自2009年以来,名列韩国电影发行排行前列的三大公司(希杰、秀宝、乐天)占据市场份额常居50%以上,伴随电影企业的话语权水涨船高,“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尴尬局面间或发生,从韩国电影向来勇于抨击政治黑暗而对财阀攻讦无力,即可窥见一斑。
就创作而言,世纪之交,韩国著名导演姜帝圭曾用其最初的三部商业电影,努力在规划自身发展方向的同时,也契合了韩国电影“走出去”的三步走策略:其独立执导的处女作《银杏树床》(TheGingkoBed,又名《隔世情缘》,1996)通过类型化高概念的精良制作,以最易共情的爱情元素叠加奇幻类型作为突破口,为韩国电影探索建构了商业类型创作的理念与方案,立足本土成功获得韩国本土观众认同;紧接着《生死谍变》(Swiri,1999)聚焦朝鲜半岛南北分裂的历史创伤,以谍战、爱情等类型杂糅模式与借鉴好莱坞高概念运作的商业经验,成功开辟韩式大片的创作路径,引领韩国电影快速走向广阔的亚洲市场;其后《太极旗飘扬》(Tae-guk-gi,2004)再次以兄弟情隐喻朝鲜半岛的民族创伤,影以载道恢弘民族主义,深化韩国文化标签,助力韩国电影成功走向世界。此后在2003年康佑硕电影《实尾岛》创下韩国国内超千万观影人次的超级卖座纪录之后,至2019年新冠疫情暴发之前,韩国已拥有超本土五分之一人口观看的“千万人次以上”的现象级影片19部,涉及犯罪、黑帮、悬疑、动作、灾难、战争、政治等类型。与此同时,洪尚秀、金基德、李沧东、奉俊昊等导演在国际重要电影节展中屡获大奖,进一步多维度、多向度地激发了韩国电影整体面貌的变革——从散兵游勇到大片制作,类型化的艺术创作形成群体性的效应。
韩国电影百年之际,奉俊昊电影《寄生虫》斩获了全球电影节展上数十个重要奖项,很大程度上激扬了韩国电影“走出去”的能量,带动了韩国电影极大体量的世界输出和商业价值跃升。《寄生虫》作为奥斯卡历史上第一部非英语最佳影片,为所有非英语国家和地区的电影进入欧美主流话语体系鼓舞士气。单片在超过30个国家和地区上映,根据北美票房网站Boxofficemojo统计,截至2022年1月31日统计数据,《寄生虫》的韩国本土票房是5336万美元,海外票房是2.09亿美元,全球票房超过2.63亿美元。继该片获Netflix投资进行长线运作开拍剧版后,Netflix更是追加5亿美元投资韩国影视项目。事实上,Netflix作为已在全球130个国家或地区落地发展、具有全球发行优势的流媒体平台,其加大与韩国之间的跨界合作,希冀以本土化策略将自身平台与韩国内容进一步深度绑定,从而获取海外内容的优先权与主动权。与此同时,韩国电影内容、影人以及技术也在依托Netflix具有的流媒体发行平台优势的“借船出海”策略下,希望获得亮相于世界电影市场、最大限度争取全球观众与商业收益的机会,从而进一步有效推进韩国文化的海外传播。
就市场运营管理而言,韩国本土市场已近文化消费临界值,产业升级放缓,出口产品种类单一,附加值低的完成片出口比重大,技术和服务出口少,除去CG技术和VFX· DI两大拳头产品,3D、音效、特效、装备等品类出口占比低,甚至有持续走低趋势,部分出口额为零,存在明显短板。与此同时,外片输入的竞争压力有增无减,自2006年韩国政府调整电影银幕配额制后,美国、日本持续发力,而近几年伴随国际金融资本注入,Netflix、Disney、HBO等跨国电影集团进一步染指韩国的线上市场。
海外推广方面,过度集中于亚洲,尤其依赖中国和日本的偏颇格局,始终是韩国电影“走出去”必须面对的结构性问题。2005年韩国电影海外收益7599万美元中的6614万美元来自亚洲(占总海外收益的87%),6032万美元来自日本(占亚洲收益的91.2%、占海外总收益的79.4%)。[4]十余年过去,检视2021年韩国电影海外收益情况,这一比重失衡的局面并未改善,亚洲市场仍雄踞75%。过度依赖东亚市场的同时,没有及时开拓后备补充的欧洲、北美、中南美、非洲、东南亚、大洋洲等其他多元市场,[4](21-24)2021年韩国电影在美国销售占比4.8%,略高于中国香港的3.6%,远不及日本的14%和中国台湾的17%。同时,比较欧洲、北美地区的所占收益比例变化可知,欧美市场更加难以进入。欧洲从2016年的24%断崖式锐减至2021年的4.9%,北美地区从2016年的9.4%下降至2021年的4.8%。究其原因,一方面与欧美地区的单边保护主义和文化中心主义密不可分,另一方面,类似《寄生虫》批判资本主义、抨击阶级固化、反思人性异化的相似创作内容,欧美市场已经屡见不鲜,《寄生虫》作为文化和审美的“他者”,在海外影坛满足猎奇的昙花一现已成定局。配套设施的基础建设上,传播覆盖面的不足仍是硬伤,海外观众接触韩国电影的机会少,对外来文化的陌生感强,也从接受群体层面将“走出去”的韩国电影拒之门外。
三、韩国电影“走出去”的策略升维
2020年后,新冠疫情致使全球电影发展一度停摆,缓慢复苏之后,内容生产阻滞、观赏热情下降、行业信心不足、整体票房遇冷等问题渐次又在“后疫情时代”缓施重手。全球性的危机挑战需要全球性的携手合作,在完成经验积累和症结把脉之后,韩国电影“走出去”也在危机之中应时调整,未来策略初见端倪——内容策源发力,升级生产模式,市场规划与国际传播深度协同。如能落实以上三条通路及其配套举措,保证具体细节到位,那么针对韩国电影国内的市场赋能、消费升级以及激活亚洲乃至世界电影市场的区域协同效应,都将取得可预见的理想成效。
创作内容方面,优质商业生产应着力增加竞争价值,完成片的精品化和内容为王的专业化生产策略并驾齐驱。一方面,电影作为文化商品“走出去”,拥有观众熟悉、喜爱且有票房号召力的演员和导演固然重要,作品本身的文化感染力同样不容小觑。每一部承载着韩国文化标签的完成片登陆海外院线都实属不易,为了保证海外观众能看到最优质的韩国电影以及海外片商能接触到最具价值的韩国影片,眼下的韩国电影,正如詹明逊指出的“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6],将类型电影、普世价值、平民叙事、全球景观、特色题材进行序列性组合,延伸“民族寓言”的创作内容。例如《兹山鱼谱》(TheBookofFish,2021)围绕儒文化的文野并立、雅俗共赏,借助三兄弟的不同立场展开多线叙事;《摩加迪沙》(EscapefromMogadishu,2021)取景海外,利用国际景观完成奇观营造,以恐怖袭击作为核心事件,弥合意识形态双向分歧;《出租车司机》(ATaxiDriver,2017)借助外国记者完成视角转换,讲述特殊题材,增幅文化代入感;《雪国列车》(Snowpiercer,2013)从生存危机和阶级异化出发,实现类型融合,传达善必胜恶、希望永存等普世价值。
另一方面,韩国电影应在文化接受与心理认同上,充分权衡普世通约性和在地异质性,最大限度地建构影像叙事与文化共通的表达空间。这种把握创作与接受的规律机理,以“这种相应物本身就处于本文的每一个永恒的存在中而不停地演变和蜕变,使得那种对能指过程的一维看法变得复杂起来”[6]的导向变化,实现了电影主题的凝练、格局的扩张和技巧的升级。例如,《局内人》(InsideMen,2015)、《国家破产之日》(Default,2018)、《南山的部长们》(TheManStandingNext,2020)、《摩加迪沙》等跨越了经验性的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政治隐喻,转向直面全球各国家和地区普遍面临的时代问题——反腐和反恐。再如,网剧《鱿鱼游戏》(SquidGame,2021)直白使用西方在《生化危机》(ResidentEvil,2002)、《饥饿游戏》(TheHungerGames,2012)等电影中已然普遍熟稔的游戏滤镜和升级系统,透视“下克上”的逆袭心理,效仿好莱坞之余,矫正了既往邯郸学步的错误,体现出当下的韩国创作者正在逐渐生发出强调自身特色的形式和内容的主体意识,对精神层面的文化消费品进行区别化创新。
此外,韩国电影致力于以创作关注和迎合社会潮流,将时代议题纳入核心主题。例如,在“ME TOO”运动后,韩国电影对女性电影的创作和电影中的女性意识传达更为重视,在现实主义的指涉之外,将性别议题与女性遭遇绑定,金度煐、金涵洁、朴努利、李钟言等女性导演为女性发声,“逐渐构造出具有自身完整性的女性经验世界。她们的态度,一边探索、丰富着全新电影题材,一边开辟、细化着电影表达的新场域,为韩国电影寻找着新的突破口与美学方向”[7]。再如,尊重多元电影思潮涌流,形成电影专业人才阶梯层级,保证多类别片种与专长人才羽翼渐丰,养成以奉俊昊为代表的谙熟商业大片的类型特征和叙事技巧、兼具作者性的人文思辨的进入好莱坞体系中的反好莱坞创作者。另辟独立电影和艺术电影的创作扶持基金和专项人才计划,遵循艺术电影和独立电影的行业传统,支持不同类型的电影人才进入一线发光发热,并对他们的优秀作品持续进行孵化和海外发行。
生产模式方面,通过区域性官方贸易协议,IP转化率和附加值大幅提升,分账模式细分升级。2014年11月,经过四轮谈判,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简称FTA)签订,中日韩自贸区成为继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欧盟之后的世界第三大经济贸易区,该协议联动东亚地区协同发展,辐射亚太地区贸易迭代,于韩国电影而言,通过共同体绑定,有效降低行业风险,也保证了项目海外落地后接受空间的潜在市场。路径反作用于创作,区域形势变化配套了携行的内容变化和渠道变化。以韩国的文化思维和逻辑话语创作,兼具国际视听与民族特色的《奇怪的她》(MissGranny,2014)、《七号房的礼物》(MiracleinCellNo.7,2013)、《极限职业》(ExtremeJob,2019)等全球性优质影片面向海外出售版权和翻拍权,“一源多用”(One Source Multi Use,简称OSMU)的 IP 使用方式遍地开花,在地改编版本的类型、形式、价值观都被移植“融梗”杂糅再生,融汇了潜在市场自身文化底蕴与审美偏好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完成“再书写”“再塑造”“再生产”,促成了韩国高附加值IP成熟转化,并为规避IP转化周期长,孵化项目质量良莠不齐,文化隔膜导致海外观众接受无力的困境制造窗口效应。
韩国电影“走出去”着力保证更加合理化的产业金字塔结构,追求将电影、电视、音乐、演出、游戏、特效等多样媒体产业多种经营,有力协调并充分运筹优势资源,嵌合策划、立项、投资、制作、发行等多个产业环节,保持全产品的统一调性和竞争活力。正如取材中国文化的《花木兰》(Mulan,1998)和墨西哥文化的《寻梦环游记》(Coco,2017)之于美国电影,韩国电影不断借地缘优势,保持类型电影内容覆盖的丰富性和创意性,不断以他山之石攻玉,弥补商业电影套路感强的观赏劣势。近年来,丧尸片《釜山行》(TraintoBusan,2016)、奇幻片《与神同行》(AlongwiththeGods,2017)系列、灾难动作片《极限逃生》(Exit,2019)、科幻动作片《徐福》(Seobok,2021)等影片,都非既往韩国电影擅长的内容,但都与此前成熟的韩国悬疑片、动作片、爱情喜剧片等相关,可视作重新加入东方式文化色彩和时代性文化底蕴之后的焕然一新的创作探索。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韩国电影“走出去”开始充分重视分账比例,在与欧美等国合作时,切实提高地位和收益,提升电影附加值,争夺衍生品开发权,在疫情、资本、地域等考验之下,保持良好健康的产业生态。新冠疫情中,由于线上流媒体扩展模式被广泛应用于电影宣发,短期来看,于中低成本电影而言,线上点映增容了市场,然而,锚定实体院线且投资高昂的商业大片没有动摇立场。因为尽管流媒体正值风口,票房的固有优势和衍生红利仍是立足之本,哪怕以延迟档期等方式“弃车保帅”,也要保证精品头部电影的全额价值。与此同时,还需警惕流媒体配套的分账模式与版权保护给高投入大片带来的后续挑战。
传播路径方面,韩国电影重新进行国际化布局和创新性发行,以“点的突破”“线的链接”“面的辐射”组成三维的传播矩阵。
点的突破,即准许个别企业率先突围,发挥个别影人明星效应。例如,出身三星集团的希杰公司作为韩国全面从事投资、制作、发行、海外出口以及演出制作等娱乐业务的最大的综合性文化企业,[8]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秉持着“没有文化,就没有国家”(No culture,no country)的经营信条,与相关的海外电影机构进行合作,先后打造了《杀人回忆》(MemoriesofMurder,2003)、《实尾岛》《海云台》(Haeundae,2009)、《熔炉》(Silenced,2011)、《双面君王》(Masquerade,2012)、《鸣梁海战》(RoaringCurrents,2014)、《国际市场》(OdetoMyFather,2014)、《奇怪的她》、《老手》(Veteran,2015)、《极限职业》等超级影片以及斩获美国电影奥斯卡奖4项重要大奖,获得包括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棕榈奖在内数十个奖项的《寄生虫》[9]。至于从“韩流”中跃然升起的裴勇俊、李英爱、元彬、崔智友、宋慧乔等知名韩国演员与林权泽、奉俊昊、朴赞郁、李沧东、金素英、崔岷植、宋康昊、李秉宪等实力影人,更是韩国电影“走出去”的文化面孔和票房灵药。
线的链接,即延续区域性的攻略概念,摒弃一城一国的个体经营模式,节省准入成本。例如,借助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东南亚国家联盟组织、日本政府的“酷日本”国家品牌等,通过与组织中心机构和核心单元直接商务洽谈,获得庞大组织的认同接受,跳过各个击破的繁冗周期,一次性获取该组织内所有成员国的市场准入资格。再如,跻身亚洲最强力的电影融资平台之一的香港亚洲电影投资会,联动覆盖中、美、韩、意、荷等在内的 35 个国家和地区的电影行业组织。
面的辐射,即合理产业结构,调整市场中心。一方面,全产业链深化推进,技术赋能,深耕厚植韩国文化品牌,为韩国电影“走出去”推出“双保险”:前置的内容创作服务——大力发展技术服务出口,后置的放映发行联动服务——以CGV为代表的院线布局全球。
技术服务出口增强了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同类电影服务竞争时韩国电影特色业务的优势。以VFX(特效制作)技术出口为例,在中国市场取得良好反馈的《狄仁杰之神都龙王》(2013)、《西游记之大闹天宫》(2014)、《西游记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2016)、《西游记·女儿国》(2018)、《美人鱼》(2016)、《湄公河行动》(2016)、《红海行动》(2018)等作品的VFX制作均来自韩国的DEXTER、Macrograph、Digital Idea等公司。即使在2020年韩国电影技术服务出口同比减少近 50%,3D 和音效收益清零的不利情况下,VFX后期依旧揽件20项工作,收获976万美元,完善了韩国电影应对突发风险的防控体系。
而CGV作为韩国最大的影院投资管理公司,全球第一家资本上市的专业影院公司,自身定位为“超越韩国的世界市场”。截至2019年,已在中国、韩国、越南、美国、印度尼西亚、土耳其等8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超过530家高端影城和3900多块高品质银幕。CGV院线所到之处,韩国电影剑及履及,优先享有最佳放映档期和最优资源,不仅保证精品类型片释放单片效能,还开展明星见面会、电影首映式、韩国电影节、韩国文化节等主题活动,增加市场受众对于韩国电影的良好观感,制造连锁反应。
另一方面,在地缘政治背景下,韩国电影发展的顶层设计配套着韩国的全球战略布局,放大地缘要素,探索共同发展的全新伙伴关系;提供覆盖海内外的全流程专业化服务,建立覆盖全球市场的商会组织;进一步引入民间资本,创新融资合作模式;发挥政府机构智能,建立文化智库,深化人才专业化培养和国际化交流;完善线上版权保护,策应流媒体分账模式;加速“走出去”的总体效益在投资制作、团队管理、市场推广宣传、产品衍生开发等环节的回流效率和完成质量,再以效益反哺技术转型革新、服务体验和基础设施的升级,形成闭合的良性生态。
四、结 语
身处新百年伊始的时代节点,面临疫情以来的现实困境,尽管既有电影产业基础扎实,但韩国电影要继续“走出去”开疆辟土仍是巨大挑战。因本土市场空间的饱和性与有限性,未来韩国电影务必继续开放性、国际化地坚持“走出去”:首先,需要从大局层面完善全面的文化服务和政策引导,健全保障创作环境,提高项目孵化成活率,激发创作群体活力,吸收世界性创作资源;其次,应深耕提升电影内容高品质创作,并转化类型、形式、内容与价值观,追求优质的商业类型,生产完备的普世价值话语,增强韩国电影的市场吸引力和文化感染力;再次,合理规划产业结构,创新多渠道经验与获利模式,把纯粹单一的完成片产品属性出口最大限度转为多元的高专业程度、高艺术品质、高商业附加值的服务与技术出口;最后,调整全球产业、经营与传播布局,深度铆合全产业链条,深化全球生态圈层,保持亚太市场的优势,均衡内部获利板块,翻越欧美市场保护主义的高墙,跨越中南美与非洲地区的市场低谷。唯有在危机之中与世界同甘共苦,追求骨落神秀的结构升级,才能实现全产业活性循环与多向性、差异化运营,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和创新链,继续开辟韩国电影“走出去”的现代化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