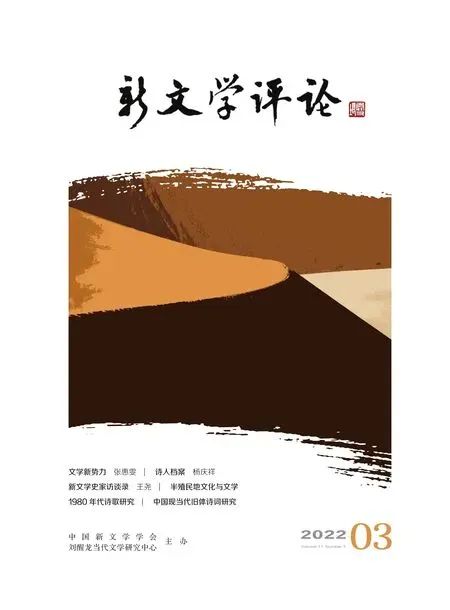石一枫作品中中层青年的成长叙事
□ 白秋华
“中层青年”即中间阶层青年。国内对“中间阶层”的界定最初只以经济水平为标准,有学者认为“中产阶级或中间阶级(中间阶层)是指生活水平、财产地位处于中等层次的社会群体”①。而随着理论的发展,社会学对“中间阶层”的界定更加完善:“中间阶层不等于中等收入群体,应该从收入、职业和教育多个维度分析我国中产阶层的规模与结构”②;“中间阶层介于富有阶层和贫困阶层之间,其划分的标准主要是收入水平和财富拥有量,同时兼顾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文化程度、社会心态、价值观念等因素”,“他们多数从事行政管理、工程技术、商业营销、教师、律师、医生、秘书等职业,一般受过大专以上教育,在技能、职能、阶级、社会地位或权利等方面都居于‘中间地带’”③。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国内对中间阶层的界定总体上趋向于遵循马克斯·韦伯的三位一体多元分层方法,着重从财富、权力、声望等几个指标上来界定中国的中间阶层。所以本文所讨论的中间阶层是指在财产收入上处于中上等水平,从事非劳力职业,能够保持较体面的生活,具有一定话语权、受过高等教育、追求较高层次的生活质量与享受的社会群体。
石一枫笔下的中层青年享受着父辈创下的功勋与成绩,不需要关心普通市民的生计和生存问题,养成了懒散与寄生的生活习惯。于是当席卷而来的消费文化冲击他们的生活时,他们感到不适与无助,疲于挣扎后,深陷颓靡的生活之中无法自拔。从他们身上我们能够看到过快的都市国际化发展带来的孤独、麻木、疏离的精神异化现象。石一枫作品书写中层青年在转型时期的普遍精神生活:一方面,中间阶层处于高层和底层之间,是维系社会稳定最重要的社会力量,借中层青年能够透视整个社会青年在转型时代的精神状态,给新时代青年精神危机的文化应对提供参考;另一方面,石一枫曾提到过作为写字人的责任:“通过一斑是可以窥全豹的,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资源与不足,可以帮助我们对时代发出应有的声音。”④石一枫拥有的资源就是自己的生活阅历与文化积累,他处于中间阶层,以自身经验与视野书写故事,展现中层青年“新时代的新史诗”,以及他对于新时代中层青年精神困境的思考。
一、漫游在路上:走向成长的尝试
石一枫在《世间已无陈金芳》后记中谈到,他作品中的青年“缺点在于犬儒主义,优点在于还知道什么叫是非美丑”⑤。中层青年在颓靡之后还有一定的价值判断,意识到当下生活状态的不可行性,因此他们有脱困的诉求并进行脱困尝试。这种尝试的形式有两种:一是出走路上的反省,二是回归之后的慰藉。
(一)出走:路上的反思
鲁迅提出“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后,“出走”在现当代文学中就被赋予特殊的意义,并且在不同的时代有所发展,出现了出走现象的普遍化、形象的多样化和主题的多元化。五四时期的出走最初带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与革命色彩,是对封建家族束缚的逃离与反抗。《伤逝》中的子君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第一个出走者形象,而鲁迅对于子君这一形象的塑造,也符合了他对“娜拉走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结局的预示。与子君为爱出走失败有所不同,《家》中的觉慧在受到新思想的洗礼和旧传统的戕害下决然出走显得更有革命性和成熟性。抗战时期作家们塑造了新的战争语境下的出走者形象,更加强调了民族意识和家国情怀。当代文学中的出走又显现了在新时代里对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复杂探索。
石一枫也继承了出走模式,描绘中层青年在路上的姿态。在他的作品中,出走被赋予逃避或者追寻的内涵。这既是中层青年的出走之路,也是他们的成长之路。中层青年们通过真实的出走这一行动逃避当下的生活现状获得精神自由或者是在动身的路上寻找答案,在路途中不断自省。
《红旗下的果儿》中的陈星就是这样一个漫游在路上的出走者。陈星沉默寡言,周身笼罩着与这世界格格不入的孤独感:“这个沉默寡言的年轻人,仿佛一生下来就做好了承受孤独的准备。”⑥为了逃避孤独,陈星开始了周而复始的漫游。最开始他是无聊而行走在路上,有时候“连休息都顾不上,就继续游荡起来”。这时候他并没有感受到“浪剑走天涯”的快乐,只觉得自己在流浪,在周而复始地围着一块无聊的地方乱转。但是久而久之,他却喜欢上了走路,“走到哪里都无所谓,只要能走就好”,因为走路对于他来说似乎就能忘记一切悲伤,只要能走,就还有自由。让他迷上走路的原因不是路上的风景,而是走路的状态,出走不仅能够让他逃离孤独,还能够获得精神自由。陈星漫游式的出走是他走出孤独与悲伤状态的一种逃离式的尝试。
而《借命而生》中的杜湘东的出走则是另一种状态:主动思考与追寻。杜湘东的刑警理想破灭后陷入憋屈,之后又因为一次失职导致一名罪犯死亡一名罪犯逃跑,他愧疚不已,从此一蹶不振,成为自暴自弃的边缘人。在老婆刘芬芳的抱怨和咒骂中,杜湘东的愧疚感愈加强烈,也在思考自己的个人价值所在。在一次巧合,杜湘东踏上了追击逃犯许文革的漫漫长路。在这段长途中,杜湘东发现了姚斌彬和许文革逃跑的真相,也在与其他刑警侦查的对比中认识到自己追击和监视方式的老套与过时。他非但没能亲自抓到许文革,还成了徐警官的优秀侦查能力的烘托者。但是这场出走并非没有意义,最终他寻找到了个人价值的答案,“男人战斗,然后失败,但他们所为之战斗过的东西,却会在时间之河的某个角落恍然再现”。救出欲自杀的许文革的那一刻,“杜湘东觉得全世界都在为他庆功。他还觉得不止许文革,就连自己的这条命也是借来的,向姚斌彬借,向许文革借,向刘芬芳借,向警察老徐和崔丽珍借,向这世界的所有人借”⑦。获得新生的不仅仅是许文革,还有杜湘东,他对自身个人价值的重新认识也是他的一次新生,所以伴随他多年的憋闷一扫而空。他追寻式的出走让他明白,在复杂多变的时代里,就是要满腔热血,紧跟时代步伐,而不是成为时代的旁观者,被时代遗弃。
石一枫的其他小说也出现了出走者形象。《恋恋北京》中的赵小提受音乐梦想与爱情的重创后又面临咖啡厅营业的失败,由此陷入了抑郁的困境。于是他选择跟随b哥和小保姆一起周游世界,进行一场流浪式的出走,来重新认识生活。《我在路上的时候最爱你》中的陈俊在辗转几个岗位后,经济状况越来越差,在彻底弹尽粮绝之时,通过母亲的关系得到一份旅游摄影的工作,于是陈俊踏上了漫游全国各地的出走之路,暂时忘记了爱情和生活给他带来的痛苦。《心灵外史》中的杨麦在对进入传销组织的大姨妈的拯救之路上,进入了自己内心深处,重新审视了信仰问题。他们的出走无论是逃避式的还是追寻式的,目的都在于想要摆脱此前的颓靡状态,从失败、空隙、焦虑的负面情绪中抽离,获得短暂的精神自由与自省。第一种状态中的青年完全只关注出走这一行动本身,将一切现实生活中的烦恼统统抛到脑后,让自己的心灵有一次短暂的放空。而第二种状态中的青年则心无旁骛地只追寻着自己的目标,忘记牵绊自己的其他因素,在出走中寻找到人生的价值得到了答案。
(二)回归:亲情的慰藉
出走使青年获得短暂的精神自由,可在孤独和茫然的现代社会中,青年仍然需要找寻精神的寄托和归宿,于是家成了他们在现代社会中漂泊无依之时的救生圈。家在现当代文学中的含义之一就是作为人们的寄托与归宿。鲁迅的小说有故乡情结:在小说中,主人公不断地回乡却又不断失望而最终离乡、去乡,形成了“离去—归来—再离去”的小说模式。他在小说《在酒楼上》中透露了他渴望回归却又无处回归的无奈:“北方固然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无论那边的雪怎样的纷飞,这里的柔雪又怎样的依恋,于我都没有什么关系了。”⑧他的这种故乡情结揭示了众多长期在外尝遍人间悲凉和痛苦,尽受世道炎凉与人情冷暖的疲惫游子归返故园寻求温暖港湾的普遍心理。之后当代文学中的家扩大到家族、民族、国家上来,开启了寻根之旅。当作家们将家扩大到宏大含义上来时,也同样有作家仍然从微观出发,观照转型时期存在颓靡心理的个体的家庭亲情关系。石一枫便是如此。
在石一枫笔下,中层青年的家庭关系都是破碎的,父母各自再婚组成家庭,于是他们有了亲情缺失的无归属感和漂泊感。在出走的这一过程中更是感受到了这一点。所以这些中层青年试图通过同母亲的关系缓和来重获心灵依靠。
在《心灵外史》中的杨麦的印象中,他的童年“基本上是在狂风暴雨中度过的”,童年记忆只剩下“辩论、揭批、指桑骂槐、阴阳怪气”。《我妹》中的杨麦去南京寻找妹妹小米,时间正值春运,卷入归家大潮的杨麦觉得自己似乎也在归家途中,“在此时的中国大地上,与我共同奔波的浩荡人流里,每一个赶路的人都在遥望着自己心里的那个‘家’吧。哪怕容颜已改、故园残破,他们仍然默默无声地赶回去,虽百死而不折”⑨。尽管杨麦心里明白,自己的家园早已残破不堪,但是他仍然对此有所向往。所以之后杨麦多次来到南京,试着跟母亲沟通,终于两人冰释前嫌。母子二人相互关心,杨麦多年以来缺失的母爱终于在多年以后得到补偿,由此获得了慰藉。《心灵外史》中杨麦父母双方又各自再婚,他清楚地认识到“父母两边的家都不再是我的家”,于是“只好尽力在脑海中删除了对于‘家’的一切依恋与期许”⑩。长时间缺少家庭带来的温暖和安全感,杨麦患上了焦虑症,心理医生彭佳亿建议他试着与母亲和解,尽管母亲控诉过杨麦,但是之后她得知杨麦患病,决定前往北京照顾杨麦。虽然母亲并没有改变杨麦邋遢的单身汉生活,但是杨麦“终于过上了有人陪伴的日子”,在母亲的照顾下,杨麦有了重新生活的底气。在《我妹》和《心灵外史》中,处于两种不同故事线的杨麦,都经历了家庭的破碎但最终都回归到了家庭亲情之中,重获了来自母亲的温暖与慰藉。出走路上愈感强烈的孤独感与漂泊感在他们回归亲情时消散,心灵的港湾得到了重建,颓靡的精神状态也有了缓解之状。
出走与回归构成了石一枫作品中中层青年由颓靡走向成长的一个路程,家的回归意味着希望与寄托,它让中层青年们在长久的无可归属感和漂泊感之后获得了心灵的慰藉,颓靡的困境有了挣脱的可能,颓靡也不再是终点与尽头。
二、路途有指引:引路人的对照
关于主人公成长的小说被称为成长小说。艾布拉姆斯曾对这一小说类型进行定义:“这类小说的主体是主人公思想和性格的发展,叙述主人公从年幼开始经历的各种遭遇。主人公通常要经历一场精神上危机,然后长大成人并意识到自己在人世间的位置和作用。”因此单从人物由颓靡到脱困的成长过程来看,石一枫作品也带有成长小说的痕迹。而在成长小说中除了有精神成长历程的主人公,还有对主人公成长具有极大影响作用的人物,这个人物一般被称为“引路人”。苏珊娜从叙事学的角度分析了引路人在成长小说中的地位和价值:“成长小说主人公独自踏上旅程,走向他想象的世界。由于他本人的性情,往往会在旅程中遭遇一系列的不幸,在选择友谊、爱情和工作时处处碰壁,但同时又绝处逢生,往往会认识不同种类的引路人和建议者,最后经过对自己多方面的调节和完善终于适应了特定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的要求,找到了自己的定位。”由此可见,引路人是成长小说主人公成长路上的启蒙者,在青年成长的过程中直接或间接给予意见和建议。
石一枫作品中中层青年由出走再到回归,都是对摆脱颓靡状态的一种在路上的尝试,这得到了暂时的精神自由并找到了脱困的希望。石一枫在小说中又设计了引路人的角色,为中层青年寻找自我提供指引方向,中层青年在引路人的对照中发现自身缺陷,由此最终确认自我,获得成长。小说中中层青年受到指引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受到美善者的正向指引,一是受到失败者的反面对照。
(一)美善者的正向指引
中层青年还懂得是非美丑的,当他们还在自我舒适圈中沉沦之时,他们身边出现了一些仍怀赤子之心、在社会中始终保持自我的美善者。这些美善者对中层青年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为他们挣脱困境指明了方向。
《我妹》中的小米是一个美善兼备的理想人物。小米不甘现实阻碍,坚持新闻披露,还在老家创办了接收色弱、色盲等病弱人群的俱乐部,并且在跑新闻的途中找到了失踪已久的哥哥大帅。小米对于一切事物都勇敢探索的精神让杨麦重新认识自我,唤醒了他对新闻行业坚守初心的职业操守,让他认识到作为媒体工作者的担当与责任:“自从小米来过之后”,杨麦的精神“就已经受着一个‘妹妹’的影响了。她近在咫尺的时候是这样,她远在千里的时候也是这样”。小米和杨麦身上有很多共同之处,比如年轻之时都拥有新闻梦想并揭露过社会黑暗。但是小米身上“多了一份从凡俗生活里挣脱出去的力量”,所以小米能够克服重重困难坚持新闻梦想;而杨麦却信念单薄,在现实中无法坚持初心,只想过安稳的小日子。因此在寻找小米的过程,实际也是杨麦寻找自己的过程。寻到了小米,杨麦也寻到了新闻初心与自身价值,不再颓废也不再刻意地以愤世嫉俗来标榜自己,而是勇敢迈出脚步,同小米一起动身去揭露社会黑暗,揭露“幻象背后真实的世界”。
《地球之眼》中像安小男这样执迷于道德问题的人在庄博益看来是一种另类的存在,但他却也是深深地影响着庄博益。庄博益本来是一个社会的随波逐流者,但他仅有的微薄的羞耻感与道德底线让庄博益存在转变的可能。安小男孤军奋战,一直坚持于道德追问、不肯向社会现实低头,他对于道德的理性坚守唤起了庄博益内心的良知。尽管庄博益经常提醒自己不要再被安小男的情绪所蛊惑,尽量把自己调整成漠然的、就事论事的心态,但“安小男那冥顽不化的‘道德感’”令庄博益“感到疲惫和无所适从”,“每当看到有什么关于母校的新闻,甚至在夜阑人静无法入睡之时,安小男那张老丝瓜般的脸总会无声无息地浮现出来,不动声色地搓着庄博益心里某个污痕累累的部位,搓得他的灵魂都疼了”。久而久之,他对安小男的态度由轻视、误解转变为理解,甚至最后对他产生敬佩之意。在这态度转变的过程中,庄博益自身的灵魂也接受了一次次洗礼,道德底线得到加强,他不再以麻木消极的态度对待世界,而是重新思考道德的底线和力量,认识到社会中无处不在的道德约束与道德榜样,甚至思考“社会能否变好的”问题,因此最终他也能够坦然地面对监控,步入人生的新路程。
这些美善者形象,被赋予了石一枫的希望与寄托,他们是十分理想化的人物。但作者希望有这些人的存在,从文化的角度为人们指点精神突围的迷津。
(二)失败者的反面对照
从生活真实来看,石一枫作品中的失败者或许更能作为当代社会的普遍人群。这些失败者沉迷于自己的世界里,要么以金钱为价值标准,完全失去荣辱,要么沉溺在自己的世界里追寻虚无缥缈的事物。他们的结局都是失败的。这些失败者在小说主人公身边上演着他们的失败故事,为中层青年提供了一种反面教材,从他们的对照中否定了他们的道路,由此走向相反之路。
《心灵外史》中的李无耻以金钱为信仰,一头扎进世俗物欲的沼泽之中,过于追求权钱利的世俗目标,精神世界一片荒芜,并出现了病变和异化。小说中李无耻世故圆滑,八面玲珑,他靠各种手段大发横财,最终却破产仓皇而逃。杨麦透过李无耻在金钱的世俗信仰上快速成功,却又迅速走向失败的经历中,意识到严重的利己主义和无常的人际关系让世俗信仰显得十分不可靠。大姨妈是以群体为中心的宗教信仰者,她一直在寻找心灵的归宿,经历了革命、气功、传销、上帝的信仰路程。其实大姨妈对这些信仰都有怀疑,但她长时间受到来自社会他者的审视,从他人的否定中看到自身差异与社会对她的隔离与伤害。她“脑子是满的,心却是空的”,觉得心一空就会觉得孤单和害怕,所以“每当听到那种特别有劲儿的话儿,尤其当他们说是为了我好,为了我身边人好,为了所有人好,我就特别激动。我觉得只要信了他们,就能摆脱世上的一切苦……”。大姨妈她无法拒绝一个具有强大融合力与感召力的群体召唤,因为这些群体让大姨妈感受到了被指引与被接纳。杨麦从大姨妈的信仰追寻史中看透了她的信仰的盲目性,但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缺少宗教信仰,内心长期空虚的大姨妈也不得不依靠外物作为精神支柱,扭曲的信仰方式最终也导致了大姨妈的悲剧。李无耻的失败与大姨妈的悲剧都让杨麦有所反思,无论是以金钱为核心的世俗信仰还是以群体为中心的宗教信仰,它们都是不可靠的,不能真正给人心灵的慰藉与依靠。然而,“信仰迷途后的归宿究竟在哪”这个问题是复杂的,杨麦没有找到答案,这也是石一枫留给读者乃至社会的问题。
在其他作品中,石一枫也塑造了以金钱为中心的极端利己主义者,如《地球之眼》中的李牧光,在大学时期就弄虚作假,找“枪手”写论文以获得到美国上学的机会;在美国时答应同林琳假结婚是因为他想利用林琳清白的身份洗钱,在国内办厂也是为了这一目的。这种毫无道德可言的行径的最终结果只能是失败。“我”——庄博益作为一个旁观者,尽管开始是以事不关己、冷眼旁观的态度,但最后仍然受到了道德冲击与震撼,守住了道德底线。同名人物李无耻在《我妹》和《心灵外史》中是相仿的形象,同样也是失败结局。杨麦从中吸取教训,得到对照,选择跟随妹妹小米追寻初心,探索新闻真相。
失败者与美善者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物形象似乎是石一枫小说的一种普遍书写,二者的强烈对比,更衬托出美善者的道德品质,从而让成长的主人公自然而然地选择美善的一边。尽管这种书写仍是浅层次的表现,但也仍然寄托了作者的思想价值以及对美善者的呼吁,给青年在精神成长提供借鉴与反思的榜样。“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或许是石一枫为当代社会青年走出时代困境、自我反思提供的一种方向。
结 语
石一枫作品主要书写青年们在转型时代的个人命运和价值,尤其集中展现了中层青年的精神面貌,揭示了青年颓靡的时代精神症结。作品中的中层青年经历了颓靡—脱困尝试—获得成长的精神历程,他们在复杂的社会中通过自我尝试与他人指引,不断反思自己的价值与追求,从而摆脱颓靡状态,完成了个人成长与精神救赎。
石一枫的写作观是作品能够表现“某个情感线索下的时代故事”,讲出“独属于这个时代的中国人的命运”,对社会和人性做出“聪明的判断”,因此他的作品也的确以繁复的故事展现了社会的复杂性。他在写作中继承了问题小说与成长小说的创作思路,以文学反映现实和思考现实,通过中层青年的精神状态展现了时代变迁下整个社会青年的生存图景,发掘了当下青年颓靡的这一时代症结,引起我们在精神层面的深入追问与思考,为当下颓靡青年提供了精神脱困的参考案例。
注释:
①李强:《关于中产阶级和中间阶层》,《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②李强、王昊:《我国中产阶层的规模、结构问题与发展对策》,《社会》2017年第3期。
③肖文涛:《中国中间阶层的现状与未来发展》,《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
④李云雷、石一枫:《“文学的总结”应是千人千面的》,《创作与评论》2015年第10期。
⑤石一枫:《世间已无陈金芳》,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232页。
⑥石一枫:《红旗下的果儿》,九州出版社2009 年出版,第 61 页。
⑦石一枫:《借命而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65页。
⑧鲁迅:《鲁迅全集·卷二·彷徨·在酒楼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65页。
⑨石一枫:《我妹》,外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137页。
⑩石一枫:《心灵外史》,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