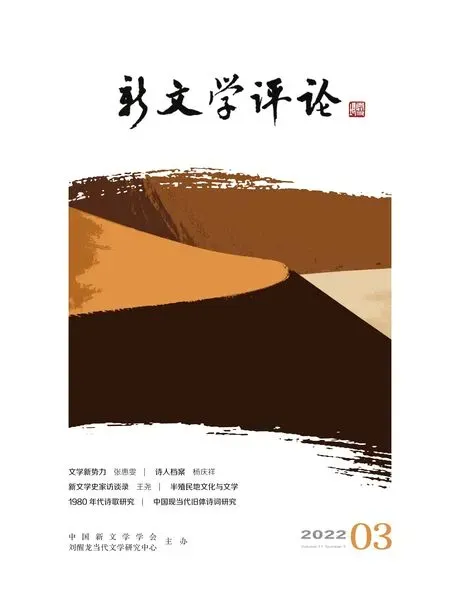半殖民文化语境下的服饰、性别与民族
——旗袍与1930年代留日女学生的身份政治
□ 张惠娟
至1920年代末期,在有关留日学生的文学书写中,知识分子作为弱国子民的身份“焦虑感、悲怯感和不确定性”①明显减弱,文化立场和民族身份认同向本民族回归,他们通常以一种平视的姿态去观赏和体验东洋文明。与此同时,日本侵华带来的民族危机又让身处战争策源地的留日学生,在精神上、心理上遭受着殖民文化的侵袭与裹挟,身份体验更为敏感、复杂和深刻,留日学生的形象塑造、文化身份建构和民族情感表达呈现出新的样态。相比于清末和1920年代,1930年代的留日学生生活书写和形象塑造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在国族叙事和殖民叙事之间嵌入了性别因素,给予留日女学生独特的观照。
只关注清末和1920年代留日男学生的生活书写和形象塑造,难以触摸不同历史语境中留日学生的精神世界和心理现实,概览现代留日学生群体的全貌。在这个意义上,留日女学生的生活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在现代中国作家笔下,留日男学生和留日女学生的着装表现出明显的区分:留日男学生的着装以日本的学生装和洋装为主,着重呈现的是日本衣服与中国身体之间的紧张关系;留日女学生的着装以旗袍和洋装为主。这些都决定了留日女学生文化身份建构的路径、方法与留日男学生迥异,服饰的叙事功能也必然有所区别。日本的女学生装就是西式的洋装。在留日女学生身上,洋装不再是带来文化冲突的主要因素,文化身份问题的复杂性主要由旗袍来完成。1930年代流行于中国的旗袍是中国女性大众与国民政府建构民族国家中心意识相互协商的产物。随着留日女学生的身体“越境”进入日本的文化空间,旗袍牵动的是中国衣服、中国身体与日本文化空间之间的对抗。旗袍和洋装不仅表现了留日女学生对自我民族身份的体认,还参与调配了男留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民族情感和审美心理。另外,留日女学生生活的书写和形象塑造与男留学生构成了对照与互补,提供了性别视野中的留学生形象。考察这一特殊现象,能够让我们窥探到现代知识分子留日生活的堂奥,触摸到1930年代中日战争语境中知识分子民族身份的特殊形态。
服饰是“人的第二皮肤”②,不同种族之间,民族身份首先是以肤色来区分,在同一肤色的不同种族之间,服饰是区分我族与他族的视觉“符码”。旗袍是1930年代留日女学生区别于日本女学生的重要标志。但在历史现实和文学书写中中日女学生的服装并非是那么泾渭分明的,留日女学生也有穿洋装的习惯,加上男性审美视角的参与,留日女学生的身份问题在旗袍与洋装之间也变得更加暧昧。旗袍与洋装都是时尚虚拟链条上不同的几何形状,二者在中国女留学生身上的互换和分布(个体选择偏好的差异),“指向一种力量的汇集、冲突与布置”,这种力量是性别之力、速度之力、战争之力、殖民之力、都会之力、摩登之力等复数力量③。
一、承认的政治:旗袍的时尚衍化与“旗袍—中国”话语象征的形成
民国时期流行的旗袍脱胎于清朝的“旗装女衣”④,与男性的直筒长衫、五四时期的“文明”新装、20世纪20年代的西式长裙有着密切的关联,联系着民国初年的社会生态和女性的身体、精神世界。民国时期女性穿旗袍不同于清兵入关时“男降女不降”的文化现象,是清朝覆灭、民国建立这一社会生态的结构性变动背景下中国女性的集体文化选择,体现着推翻帝制,缔造共和的政治变革给予民国女性实际生活的意义。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对一切旧制做了彻底清扫,旗袍在辛亥革命以后几乎销声匿迹。1920年前后,在“文明”新装高调宣扬文明、进步、民主、自由之时,旗袍却在上海女性身上悄然复活,由老大帝国的遗物摇身变为沪上女子的新宠⑤。旗袍在俏女、徐娘身上重新绽放时,也招来了维新与复辟的声讨。但是从隐匿到现身,旗袍引发的喧哗与骚动不止于历史线条上的反常,它的突现也带来了文化身份上的结构性变化。西化的穿着搭配、从妓女到妇女大众的流行路径,以及与男式长袍相似的视觉观感等都将旗袍嵌入了新的表达方式与配置关系之中,使旗袍具有了新与旧、中与西、男与女、良家与妓女等二元混合的文化特征。朱鸳雏写作的小调《旗袍》⑥可谓是对这种变化最为敏锐的观察,首当其冲的就是性别的“出线”:“玉颜大脚其仙乎?拖了袍儿掩了襦。婆婆年老眼模糊,笑姑姑一半儿男一半儿女。”放了脚的女子穿着前拖后掩的一截式旗袍,形象酷似青年男子,造成了女着男装的视觉混淆。在一个穿长袍是男子的专属形象的社会里,女子对旗袍热衷的意义就越过了出风头的内心冲动,演变为一种由分化走向统合的性别政治。时装“也是女性表达自我的方式之一”⑦。旗袍被突然翻牌,一反常态地风靡开来,其实是女性在利用旗袍直筒一截的形式特征,回应和对抗流行的“文明”新装,以寻求改善上下两截的穿衣传统,从而获得与男性共享一截穿衣的权力。可以说,“性别革命的质变”⑧是满人旗女之装向民国旗袍演进替嬗的核心动力。女子选择一截式旗袍,与剪发、放脚有着同等的价值追求,首先是“泯灭性的区别”⑨,便于争得与男子共享教育、参政的权力。
与一截穿衣的视觉诉求相应的是,女子旗袍在款式、形制上也呈现出去满族化和民国化,或者说是去封建和现代化两个方向。首先是去除带有满族印记的繁镶阔滚、雕花刺绣,下摆由宽变窄,颜色以碎花、纯色、格子取代华丽艳彩,面料不仅限于细绸锦缎,土布、棉布也可制作,穿着者无年龄、身份之别,花季俏女、半老徐娘同穿旗袍上街。这些具体而微的细节变化让旗袍彻底改头换面,也打破了皇权时代森严固化的社会身份等级区别。其次,当旗袍成为一种时尚,与其他审美活动一样,可以被看为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具有想象性地解决难以解决的社会矛盾的功能”⑩。1920年代,除了表达男女平权的诉求,旗袍也是女性身体与现代建国理想等国族政治交锋的舞台。旗袍的民国化可以说是两个“民族”之间的转换,是一种去旧布新、旧貌换新颜的文化翻新,意味着祛除前清印记之后的再次民族化。初兴的民国旗袍虽然符合了现代化国族论述中去繁从简的需求,但依旧保持着宽大、方正、严肃的流行趋势,强化着中性化的审美和生活实践,和“文明”新装一样,仍然不能体现民国女性服装的现代性,以及由此而来的女性新形象。也就是说,只有明确了旗袍在中华民国的现代国家体制之中如何完成从封建落后向现代文明的形象跃升,如何成为中华民国新的国民身份的象征,才可以理解女性在现代共和制国家建设中的地位和角色。
旗袍的流行实质上是妇女解放的思想现代性与时尚现代性的一场接力。五四新文化运动退潮之后,思想解放、女性独立、男女平权的启蒙呼声不再是女性服饰变革的主要动能,时装的潮流更仰赖于女性时尚意识的增强。比起报纸杂志的思想说教,妇女大众更愿意沉浸在大众传媒制造的幻想中,她们对新闻、广告和摄影照片呈现的穿旗袍的生活方式趋之若鹜,在模仿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一种无意识的身份认同。就像张爱玲所说:“中国的时装更可以作民意的代表”,设计灵感皆出自不谋而合的“公众的幻想”,进而“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洪流……裁缝只有追随的份儿”。旗袍在民国的流变也是对女性气质不断的重新定义。经过十多年的蝉蜕,旗袍就像一个经过磋磨、淘洗,再重新上釉的花瓶,中性化(男性化)色彩彻底脱落,焕然而成专属于女性的新时装,已“无真正与男装相等之旗袍者”。至1930年代,旗袍的款式和造型基本固定,呈现凹凸有致、宽窄有距的立体流线型,“烘云托月忠实地将人体轮廓曲曲勾出”。在此期间,妇女解放思想、西化摩登的时尚潮流、简洁自由的现代审美黏合在一起,捏成了一个完整的身份,重塑了现代女性的身体和形象。
1929年4月,国民政府颁布的《服制条例》对女子的服制做出了规定,女子常礼服在原来上衣下裙样式的基础上,还增加了一种“长至膝与踝之中点”的袍式。即使服制中没有明确说明甲种袍式礼服就是旗袍,但齐领、右掩的前襟、衣长、袖长等特征的描述,以及当时旗袍的流行普及程度,都足以说明服制中的袍式礼服就是彼时的流行女装——旗袍。至此,旗袍作为民国女性的身份标识从政令上被确定下来。同时,作为女公务员的制服,旗袍也具有了公共性的社会意义。1930年代中期,国货运动和新生活运动的集结带来了国家权力意志对旗袍颜色、面料的统一规范,进一步强化了旗袍的文化合法性,使之成为全民族“广泛团结和群体认同”的标志,具有了国族符号象征的政治意义。
身份是群体在个体构成中的沉淀堆积,是个体的明确表达中改变特性的结构呈现。民族身份在个体的自我表达中蕴含着向内和向外两个维度:在民族内部,民族身份需要被承认、被接纳;在异族环境中,民族身份需要被发现、被认可。服装是支持身份认同的“物质的和象征的资源”,是身份认同的标识条件之一。旗袍作为国族符号的象征,同时也是一种“承认的政治”,经由“旗袍”这一符号,表现出女性与中华民国政体之间承认的关系。在中华民族内部,女性与政体的承认关系被纳入更大的国族论述范畴,旗袍所起的中介作用会被弱化。如:张若谷在《战争·饮食·男女》中对“一·二八事变”之后摩登时尚服膺于抗战动员情形的描述,就体现了旗袍在承认关系中的弱化倾向。“一·二八事变”的炮火,让上海的摩登女郎和女学生们“回忆到那有声影片《璇宫艳史》中的婚典礼炮……他们于是都感兴而起”。“许多城里的小姐,她们都脱卸五颜六色的长旗袍,短大衣,和高跟皮鞋,不再搽脂搽粉,穿了黑短裤、白衬衫,在公共体育场,和男学生们同受军事训练。”脱下旗袍,换上戎装或医护服的摩登小姐将会成为与男性比肩同齐的“摩登花木兰”。在战争动员的催化之下,围绕女性的性别论述从属于国族论述,不仅承认女性可以和男性一样可以共同构成强大的抗敌力量,也承认穿旗袍的摩登女郎和女学生有着爱国抗敌的激情和勇气。在这套承认的关系之中,旗袍不仅不具有象征意义,而且成了障碍,只有脱下旗袍,这套关系才能真正实现并发挥作用。也应该注意到,战争刺激下摩登女郎改头换面的自觉意识和行为选择充满了罗曼蒂克式的浪漫幻想,是不牢靠的,难以成为残酷战争中强大的精神支撑。建立在幻想和摩登时尚基础上的承认关系也是单向的,摩登女郎这个群体还没有形成“抗战救国”的认同感。
当有异族文化观念、文化立场参与其中,或者走进异质的文化空间时,这种承认的关系发挥的效用会更为显著,旗袍的象征性会明显增强。进入异质的文化空间之后,附着于旗袍上的性别基因就淡化了,旗袍获得了与中国女性民族身份同义替换的价值功能。女性与国家政体之间的承认关系由旗袍来完成,并转换为旗袍和中华民族、中华民国政体、中华民国国民之间的亲密关系。主要体现在旗袍与异族服饰在同一主体身上的互换和对峙,进一步来说就是旗袍与洋装的交锋。洋装在中国和日本具有混淆、改换和重塑民族身份的功能。男留学生通过学生装和洋装使得民族身份模糊于中国和日本之间,洋装和旗袍也同样可以让留日女学生在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随意切换。换装的故意为之有时也是为了维护本民族的国族尊严,有着正向、积极的意义。庐隐1930年寓居日本期间,为了近距离观察娼妓生活,去柳岛时特意脱下中国服装,换上西装。在日本,只有“不守妇女清规”的摩登女子会在娼妓聚集的胡同漫游,她们都是身着西装、长筒丝袜、皮鞋搭配起来的洋化装束。庐隐正是通过换装的方式,以日本摩登女子的身份进入娼妓生活圈,有意识地维护了中国的国族尊严。更为普遍的是,留日女学生会通过穿旗袍的方式表达“华夷之辨”的排外心理,对异邦文化、异邦民族的劣势加以指摘。在留日学生的民族身份叙事中,不仅旗袍的民族性得到强化,还产生了排他性。“中国”与“旗袍”的拓扑联结更加稳定,“中国”成为“旗袍”的限定语,形成了“中国旗袍”的偏正结构。在留日学生中间,“中国旗袍”不止于表达上的自觉,在精神心理层面也是一个敏感的信号,厘定着本民族与异族之间的界限。
二、旗袍的表意功能与逆写文明优劣的反殖民话语
在留日女学生的民族身份建构中,旗袍的叙事功能,是在与人物的性格气质、传统的审美标准以及留学生面对日本的文化心态等紧密串联来实现的。大革命之后,中国殖民话语由“矮化中国转向‘逆写帝国’”,留日知识分子通过强调和突显中国文化的优越感,以中国传统审美观念区分中日女学生之美等策略,来逆写文明优劣,构设反殖民话语。
首先,旗袍具有标识中国人身份的表意功能,是中国留日女学生能够引发身份认同的“共享的特点”。集中讲述旗袍与留日女学生民族身份故事的是崔万秋的《新路》。小说中冯景山在火车上与林婉华初次相遇时,洋装干扰了冯景山对林婉华民族身份的判断,当林婉华开口说话时,她的民族身份才得以明确。而旗袍就像一个自动发声器,它的标识性打破了留日女学生民族身份的神秘感,免去了猜测和打量的解密过程。这样一来,留日女学生穿上旗袍,就等于出声宣告自己是个中国人。林婉华与柳庆荇在东京街头也都因身穿中国旗袍而引起对方的注意。林婉华“一看见中国旗袍知道是中国女留学生”,她“辨出那穿中国旗袍的是柳庆荇。柳庆荇见有穿中国旗袍的女子,也特别留心看”。这种表意功能还体现在旗袍与洋装在同一主体身上的选择和替换。林婉华、金秀兰、梅如玉三位留日女学生对旗袍和洋装的选择有着不同的偏好。旗袍是林婉华的主要社交服饰,洋装只是居家的常服。在公共场合,她通常“借旗袍表示中国女子的骄傲,她不惟访友出游要穿旗袍,就是早稻田大学上课,也穿旗袍”。舞场、晚宴之类的地方更不消说,就算是和房主的女儿一同去逛公园,她也要脱下洋服,特意换上一件海蓝色方格子夹旗袍。金秀兰只有在家这个属己的空间时才穿旗袍,“出门时从来不穿旗袍”,惟恐往来的人“生出奇异之感”。在外出游玩、参加聚会或者去学校上课的时候,她总要换上“颈项胸脯都可露出来的柠檬黄色的上下一体的洋服”,唯一一次穿旗袍出游还是在与男留学生冯景山在公园约会的时候。而梅如玉自从来到日本,再也没有穿过旗袍,无论在家还在外出均是各色洋装相搭配。应该注意的是,留日女学生服饰选择上的偏好与民族身份意识之间并不能完全对应。尽管林婉华乐于享受旗袍带给她的高贵的、积极的身份体验,但也不忘在东洋寻找故国的熟悉感和舒适感。东京街道平坦光滑,街路树排列两侧,“好像上海霞飞路一带的样子”,甚至路况比上海还好,汽车从这马路上走,不惟速度甚高,而且没有颠簸得难过之忧。洋房前贴满商业广告的松坂屋让她“不由得联想到上海的永安公司”。她寄宿的公寓也有上海法租界福熙路一带西洋住宅的风味。东京的道路和住房让她的内心涌动着他乡亦故国的归属感。
旗袍不仅具有标识留日女学生文化身份的功能,还具有表现留日学生文化心态、民族情感的功能,二者构成了一个镜像结构。当女留学生的着装意愿与留日女学生的民族身份意识不一致时,叙事者的文化立场就显得尤为重要。林婉华积极的身份体验是日本文化空间和中国服饰两种因素联合带来的。在描写冯景山的欢迎宴这一情节时,崔万秋借助中日青年混杂的舞场空间来铺陈意境,对林婉华的出场进行了影像化的慢镜头式的描写。“旗袍姿的中国美人林婉华出现在这舞场时,正是一支华尔兹的曲子刚完,电灯恢复了亮度的时节,全场的视线,都集中在她一人身上。”舞曲结束,狂躁的舞场回归平静,灯光恢复正常亮度,人的意识如梦方醒,一个旗袍姿的中国美人缓缓步入,吸引了众人的目光,占据了被观赏的中心地带。叙述者通过对时间的把控,来精心布置场景,为林婉华的出场渲染了一种严肃而隆重的氛围,也衬托出她的漂亮和高贵。这一切都在提醒和强调林婉华的身份非同一般,而“旗袍姿”和“中国美人”就是她最核心的形象修辞。当在场的日本舞女被这位中国小姐的美深深吸引,并议论不断时,叙事者的目的似乎达到了,即立足民族本位,通过在异质的日本空间树立中国女留学生的中心位置,表达自我民族身份的优越感。在这个过程中,旗袍在其中起着结构性的作用。事实上,这也正是1930年代留日学生民族身份叙事的重要特征。
身份是“通过差异与区别”建构的,“只有通过与另一方的关系、与非它的关系、与它正好所欠缺的方面的关系以及与被称为它的外界构成的关系”。留日学生的民族身份的认同是在与日本国族形象的相互建构中完成的。留日学生在定位和找寻自我的同时,也在发现和塑造着日本。他们通常把中国和西方提到同等的位置,以现代人和文明者的眼光来打量日本,发现了一个既传统又现代、既文明又专制、既先进又落后的矛盾重重的日本。崔万秋的《新路》是通过发现落后于中国的“日本时尚”来表达民族身份优越感的。冯景山在去往东京的途中,两次发现与中国同步的“日本时尚”。第一次是火车到三宫站,他洗漱完回到座位上时,对面来了一位短发的女性,他联想到中国的“披发鬼”,“原来‘披发鬼’不是中国专利,在日本的火车中也可以发见得出来”。第二次是在火车经停御殿场时,车上上来一群女学生,她们“穿着衫裙连在一起的制服”,坐定之后与周围的男学生大胆打闹,他惊讶地发现“原来中国和东洋是一样的”。林婉华也发现东京的夜生活不如上海热闹,最豪华的舞场停业时间竟早于上海,还未尽兴就要打烊。“她想,若是在上海十一点半钟,正是热闹的开端,一直可以跳到明天四点,东京真是太乡下气了。”而旗袍作为中国女性的常服,是中国社会时尚现代性的重要标志。当它跟随留日女学生进入日本时,在其流行中留日女学生也发现了落后于西方和中国的“日本时尚”。日本摩登女郎铃木信子对中国女留学生穿旗袍的美态艳羡不已,她邀请金秀兰去舞场时,建议金秀兰穿上旗袍:“我希望你今晚穿那身华尔纱的旗袍去,一定可以把全舞场的羡望吸集在你一个人身上。”但金秀兰不愿惹人注意,羞于穿旗袍,还是选择了乳白色的洋装和茜色的领带。当铃木信子惊异于金秀兰不穿袜子时,金秀兰“对这位半熟的日本摩登女子感到一点轻蔑之意,她心里想不穿袜子在巴黎和上海早就流行了,而这自以为很摩登的信子女士竟引以为异,实在好笑”。谢冰莹1930年代留学日本时,在电车里发现了一个文明、有序、励志的日本,同时也发现了一个男尊女卑、大男子主义风气盛行的落后帝国。“如果你是一个女性的话,走进电车里,不平之气就会整个地占满了你的脑海。舒舒服服坐着的大半都是男人,攀着圈子随着电车的摇摆的,不是老态龙钟的老太婆,便是背上驮着孩子,手里抱着大包袱的少妇。”中国知识分子欧化程度较高,在电车上男子会主动给女子让座;而在日本的电车上,日本的男子只会偶尔给小孩和六十岁以上的老太婆让座。在男女平等的现代文明秩序里,中国是优于日本的。谢冰莹相信,日本女人要是看到中国电车上的情形,一定会心生羡慕,“而叹息自己太可怜了”!“每遇到中国女人自由地和男子挽着手一同在大街上走,或者坐在车上很自由地笑着谈着……她们的表情是含着无限的羡慕和感慨的。”萧昔生的《留日漫记》则是通过借日本之势,贬低矮化异族留学生形象,在日本下女和菲律宾留学生的身上寻找自我民族的优越感。他在《留日漫记》中讲述自己下课回到住所,看到日本下女富季桑“穿着一件中国式藻皮红色的中国旗袍”,既惊讶又好奇。“我真不知道她何以忽然要穿着一件中国衣服!又不知道她是由何处寻来了一件中国衣服穿的。”虽然他对旗袍的来历百思不得其解,但认定这件旗袍一定来自中国留学生之手。很快他就将这份惊诧和疑问迁移到中国男留学生的人格品性,并以菲律宾留学生作为参照。“凡中国留学生的男子,据说都是对于日本女子特别殷勤,特别表示亲切与有礼,尤其中国男子,普通都是堂堂仪表,决无如菲律宾人之粗暴野蛮鼻突脸陷满面青须者可比。故超达如富季桑者,于无意之中,对中国男子特别爱慕,因而打破国家观念,喜好中国式衣服而求取好于人亦未可知。”萧昔生将菲律宾留学生塑造为面相凶恶,品行低劣,蛮横粗暴的野蛮人,来凸显中国男留学生的高洁、端正的人格品质。故而,日本的两位下女对中、菲两国留学生会产生异样的感情,“均似对于中国人有一种特别的感情,而对于菲律宾人多加歧视”。
旗袍同样也是留日男学生彰显民族主义文化立场,向本土文明和民族传统寻找文化认同根基的触媒。《新路》中,冯景山的文化立场和叙述者是一致的,他的文化身份可以定位为“理想的民族主义者”。他企图通过林婉华和金秀兰两位留日女学生的服饰与身体在她们身上寻找民族印记,辨识中华文化的特征,达到民族身份认同的内在与外在的完全融合。冯景山在火车上初遇林婉华时,他的审美观念随着林婉华国族身份的明确而产生变化:生出日本健康美和中国阴柔美的双重标准。当时,林婉华穿着藏青哔叽学生裙、白衬衣和蓝底红花上衣,衣领上打着茜色领带,手中提着西式小包,是一个短发洋装的日本女学生形象。匀称的身姿、丰润的肌肉、嫩红的面颊和水汪汪的大眼睛,体现出一种健康美。确定林婉华是中国人之后,叙述者的审美修辞立马转向中国文化内部:“她的眼睛和嘴唇最是动人。中国旧话上有句‘脉脉含情’,冯君以为这四个字正可形容她的眼睛了。至于她的嘴唇是怎样的美,冯君觉得现下名传天下的中国女明星胡蝶的唇,长得和这位林婉华很相像”,并在体形相貌上刻意与日本女子做出区分:“她的腿,不像日本女子那样粗,她的脚,不像日本女子那样大,长筒丝袜,黑色皮鞋,与她上身的洋装非常相配。”当林婉华脱下洋装换上旗袍,带给冯景山的是欲望化的吸引。在欢迎宴上,身穿黑色旗袍的林婉华甚是惊艳,身段体态娇而不媚,气色可人,冯景山立刻被打动。在樱花跳舞大会上,两人在孤灯下对坐畅谈,林婉华因旗袍加持由内而外透露出来的优雅气质,令他感佩。旗袍塑造出来的身体丰姿更是“给他以诱惑”。旗袍的美丽同样在金秀兰身上也风韵难掩。和金秀兰同游井之头公园时,看到金秀兰的旗袍丰姿,冯景山再次心神荡漾。他从侧面看去,旗袍包裹下的身材楚楚可人,“她的细长的脸庞,是那样红润,两个乳房轻轻的鼓出一点来,藏在铃兰花样的轻罗之下。两支肩膀的曲线,又是那样丰满优美”。把公园内所有的日本女子都捆在一起,也赶不上她的可爱。等到站起来,“长身玉立的她,步法非常婀娜,铃兰花的旗袍直垂到脚跟,一阵风过,衣裾飘动,好像仙女的仙翼。从后身看她的两肩的匀整,背脊的挺直,以及腰身的纤细,都是异常轻灵洒脱,一点儿笨重处也没有,至于面部,则更充满了青春的光明”。即使是穿洋装的时候她的脸庞、身段、姿态,也“是代表的中国传统美人;尤其是传统的苏州美人,与日本的女子迥然不同”。同样是穿旗袍的中国女留学生,在感性层面,她们对冯景山的诱惑力难分伯仲,但在理性层面,他仍然以中国传统的审美标准来作出区分,并在她们身上寻找中国的地域文化基因,以此来给她们进行文化身份定位。来自长沙的“林婉华是现代美人”,有着蜀湘女子的执拗、强韧、聪慧、热情、爽快,在她身上甚至可以看到湖南女作家丁玲、白薇、谢冰莹的影子,她们都“是‘楚国情调’的产儿”。来自苏州的“金秀兰是中国传统的美人”,有着江浙女子的才气、精巧、温婉、含蓄、内敛、绵软。就连她们恋爱的方式也是大异其趣:“江浙的女子对于恋爱的态度,是欲擒先纵;蜀湘的女子对于恋爱的态度,是一往情深。”而“冯景山喜欢古典的”,喜欢金秀兰“蕴藏乎中的”才气和她的温柔、顺从、纯洁。留日男学生定位异性同胞也是在表达自我。以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作为参照对留日女学生做出民族化的文化身份定位,隐含着男性视角下的民族主义文化立场。他们通过给本国女学生服饰和身体的传统赋意,实现了对自我民族身份意识的表达。
三、作为他者的旗袍:国族论述里的殖民纠葛
“作为身体的延伸、却又并非身体一部分的服饰,就不仅连接了身体和社会,更清晰地区分了它们,成为‘我’与‘非我’的边界。”旗袍作为国族符号的象征,划定的是“我族”与“他族”的界限。半殖民地文化语境中,当服装的社会批判功能指向日本的殖民策略时,就产生了殖民性的社会话语作用,具体表现为被殖民和自我殖民化的表意功能。1930年代,“旗袍—中国”的话语象征也屡屡被日本殖民者所征用,实行文化殖民策略。为了制造中日亲善的幻象,日本社会提倡让本国妇女着旗袍。如:1930年代“在银座常可见到穿旗袍的日本女人,中日战后这种打扮即告灭迹”。又如:1934年长崎国际产业观光博览会和1937年日本东京博览会都为伪满洲国设专馆,并让日本的女招待穿上中国旗袍,双手拿着日本国旗和伪满洲国的旗子,以表示中日之“友好”。当身体“跨境”时,服饰引发的国族论述张力,不仅包含不同民族的服饰在同一主体身上的“文化互换”,还包含同一民族服饰在不同主体身上的“文化易界”。在后者的视野中,殖民话语对“旗袍—中国”隐喻结构的征用,还体现在旗袍作为相对于另一种服饰的他者而存在。
进入一个国家,就是进入一种文化。1930年代,旅居中国的日本侨民同样也需要用中国服装来掩盖自己的民族身份。小说《娟子太太》中,旅居上海的娟子太太为了生存需要,只有通过换装频繁改变民族身份,呈现了殖民时代的民族身份矛盾。娟子青年时期,与中国留学生相恋,跟随恋人来到上海。在恋人死后,为了保障日常生活,她不得不穿上中国旗袍,将自己伪装成中国人。只有到了深夜,她才能穿上和服和木屐,享受做日本人的短暂时光。两套服装,两种身份,娟子太太的民族身份由白天和黑夜来操控。白天她是面容白皙,穿灰色旗袍的中国教员,晚上她是“穿和服拖木屐的日本妇人”。日军占领上海后,她被聘为日本宪兵队的翻译官和治安维持会的顾问,脱掉了灰色的旗袍,做回真正的日本人。当战火熄灭,日本撤兵,她又重新过上了昼夜分裂的生活。此时的她就如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在回不去的祖国和扎不了根的异国之间漂浮、游荡。纵使旗袍会给她带来生活的便利,让她受到中国民众的认同,但她难以在情感上认可自己穿上旗袍的中国人身份。旗袍在她的精神世界始终难以跨越“我”与“非我”的民族边界,一直是相对于和服和木屐而言的他者。换装给娟子太太带来的身份之累既是主动选择,也是被动接受的结果,隐含着殖民时代的历史创痛。不知“到什么时候,用什么法子,才能够将那可怕的火的记忆忘掉,将那尖锐的仇恨的狠刺拔去呢”?
围绕旗袍展开的国族论述和殖民纠葛,在崔万秋的《新路》中,通过“九一八”国难叙事、日本殖民叙事和留学生民族身份叙事的含混表达来实现。来自东北殖民地的留日女学生梅如玉是主要叙事焦点。刚到日本时,她还是一个“半城半乡的姑娘”,“势利眼的女孩子”,“身上穿的也是一件朴素的旗袍”。在日本不到三个月,就完全换了副模样,她变得“有些像美国女明星葛莱泰嘉宝那样的女性。她的脸上浮现着一种近代的锐敏,鼻梁笔直,眼睛大而有光。乳白色的皮肤,红莓似的嘴唇,头发漆黑”。朴素的旗袍被形形色色的洋装所取代,变成了她生活世界中的“他者”。与她的旧装束一起被遗弃的还有资助她的爱人和民族身份。中国同她的爱人方潜亭一样,“只是多余的赘瘤,已不是可恋慕的对象”。文化认同和身份体验的错乱是日本在东北进行殖民教化的直接后果。她从小接受日本的殖民教育,日本文化深刻进她生命的底色,习文断字都是日本式的。长时段的殖民教育截断了原生民族文化对梅如玉的浸润和供养,扰乱了她的根源认同和价值认同,带来文化认同和民族身份的错位。“她自幼受的是日本教育,她心目中本没有中国”,也“从来没有意识到她自己是中国人”,甚至对中国的认知也是久远的,且充满了殖民色彩。她的意识里,“没有中国,只有一个腐败的支那,这支那是人人吃雅片,各个女子都缠小脚,各个男子都拖着长辫,读书人都是弯腰驼背的老迂腐”。与本民族文化的隔膜,和对日本文化的熟悉,为她脱下旗袍换上洋装,获取新的身份创造了条件,同时也意味着自我殖民化。她的身上充满了悖论,在厌弃、漠视本民族身份的同时,又利用本民族身份之便从留日同胞周星庵、刘维廉等身上获取生活资本,还同时给深爱着自己的方潜亭写信敷衍,表达虚假爱意,骗取生活费。寄生于男留学生时,她又对威胁、挤压自己生存资源的中国女留学生充满了敌视和嫉妒,甚至以耍弄男留学生作为报复手段。事实上,对梅如玉来说,与情感危机、生存危机相伴而生的还有悬置于本民族和异族之间的身份危机。在她与男留学生的寄生关系中,在满足男留学生情欲需求的同时,梅如玉也遭到了他们的排挤、蔑视和嘲讽,被称为“烂熟的妖星”。小说着意淡化甚至抹除梅如玉对日本殖民统治的体验和记忆,反之以深刻的受殖体验剖析她的文化根源,在揭示日本殖民策略的彻底性和破坏性的同时,为旗袍的缺席找到了合理的根由。
《新路》中,九一八事变激发了留日学生休戚与共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事变发生之后,日本当局加强了对留日学生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控制。留日学生界为日本的殖民野心和侵略行径而愤慨,他们因为“九一八这样的国耻,而在日本身受种种刺激”。清脆急切的号外声就像一个个魔爪,将他们从狂欢的梦境拖回冷酷的现实。文化根源的改变必然带来民族情感的疏离。当留学生界热火朝天地召开会议,筹划运动时,很晚得知消息的梅如玉“既不愤慨,也不激怒”,唯一诧异的是“她没想到竟发生得这样快”。看到沈阳沦陷的报道,她首先想到的是“她们一县的学生就又扩大了做事的地盘,于她有益无损”,所以她对此事并不感甚大的痛苦。在日本资本主义享乐原则和金钱诱惑之下,梅如玉慷然接受了殖民势力的收买,答应日本政客向他们提供留学生内部的情报,以赚取优渥的生活资源。这种神秘的工作性质,让她精神振奋,甚至认为自己接受了一项庄严神圣的任务,与好莱坞电影中嘉宝饰演的国际间谍有着同样伟大而高尚的意义。一个人民族身份的根源一旦改变,文化认同一旦缺失,残酷的殖民现实就失去了感召力,更无休戚与共的民族情感和国家观念可言,直至与殖民势力联合,走向汉奸的歧路。当她激怒方潜亭而被杀害的时候,也意味着她对同胞和自我民族的叛离受到审判和裁决。
结 语
“近代的半殖民境遇使得中国臣服于欧美对‘文明’‘现代’‘进步’的定义,中国固有的文化价值系统和文学观念被‘西方中心主义’拆解,中国在模仿(或对抗)殖民帝国的现代化的过程中陷入了‘自我迷失与重拾’的怪圈。”旗袍在民国的时尚衍化以及“旗袍—中国”隐喻结构的形成,凝聚着大众审美、民族国家观念、政权意志的力量,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模仿(对抗)西方殖民帝国现代的过程中重拾自我的表现。在留日学生的民族身份叙事中,旗袍是留日女学生和留日男学生表达民族身份认同的共有媒介。随着留日女学生的身体“跨境”,旗袍的表意功能超出了本民族的社会文化范畴,更多受制于日本的文化空气。中国普遍流行的旗袍在日本成了一种张扬的个性表征,标志摩登、欧化的洋装反而是一种内敛、保守的选择。在民族外部,旗袍是留日女学生的身份标识;在民族内部,旗袍塑造的女性身体又对男性同胞构成了情欲引诱,也是进一步定位留日女学生文化身份的重要参照。
也需要注意到,经“旗袍—中国”的隐喻结构建立起来的民族认同逻辑,有一定的限度。留日女学生的身份意识是在追求物质现代性的快感和刺激中逐渐感知的,功利性的诱惑是主要动力。当身着旗袍的留日女学生进入日本的舞厅、公园、街道等公共空间时,她们的身体也并没有实现由个体到民族国家的文化转换。作为中国民族身份象征的旗袍无法换来日本民众对中国国族本身的认同和尊重。以旗袍作为国族象征,重建民族自信的愿望只能在日本的普通民众和部分中国留学生那里有效。因此,崔万秋《新路》结尾大致可以作出这样的理解:林婉华加入冯景山等男留学生的反帝宣传运动,并一起被遣返回国,既宣告了留日女学生难以承担起现代知识分子身份重建的任务,也说明了中国知识分子民族身份的建构和反帝、反殖民的抗争也需要在国内的战斗实践中来实现。
注释:
①李永东:《身份焦虑、民族认同与洋装政治——以创造社作家为例》,《文艺研究》2018年第3期。
②玛丽琳·霍恩著,乐竟泓、杨治良等译,卜文校:《服饰:人的第二皮肤》,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③张小虹:《时尚与现代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221页。
④漱石:《京剧物类名称表·衣履类》,《繁华杂志》1914年第1期。
⑤根据当时报载的记录,旗袍在1920年前后开始流行,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光绪帝逃难,宫中的细毛皮货、书画珍宝流散宫外。辛亥革命之后,散入上海的竞卖市场,旗袍被衣装商人收买,受到戏子和妓女的青睐,上海妇女求新趋异,以为穿旗袍为出风头之事,旗袍在老少之间流行开来。参见一动:《新闻拾遗 新年新装束之怪现状》,《申报·自由谈》1920年2月20日;独鹤《闲话·大衣与旗袍》,《天津益世报》1921年1月17日;病鹤画并注:《旗袍的来历和时髦》,《解放画报》1921年第7期。
⑥凤兮(朱鸳雏):《旗袍·调寄一半儿》,《礼拜六》1921年第101期。
⑦伊丽莎白·威尔逊著,孟雅、刘锐、唐浩然译:《梦想的装扮:时尚与现代性》,重庆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3页。
⑧张小虹:《时尚现代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230页。
⑨许地山:《女子底服饰》,《新社会》(北京)1920年第8号。
⑩Jameson, Fredric(1981),ThePoliticalUnconscious:NarrativeasSociallySymbolicAct, London: Methuen, p.79.转引自伊丽莎白·威尔逊著,孟雅、刘锐、唐浩然译:《梦想的装扮:时尚与现代性》,重庆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