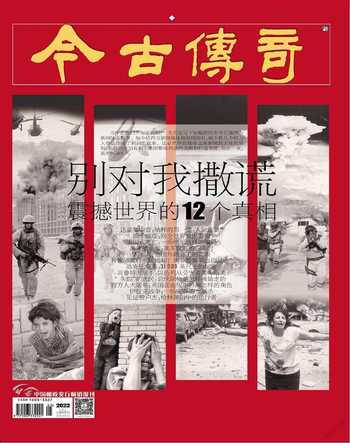伊拉克战争一场安静的大屠杀



海湾战争后,伊拉克癌症、白血病和恶性肿瘤的发病率上升了70%,原因和美英部队使用的贫铀武器有关,这种武器在伊拉克全国都留下了放射性尘埃。据专家介绍,这些尘埃已经通过地下水和土壤进入了食物链。
费莉西蒂·阿巴思诺特曾在文章中写道:“巴斯拉正在进行一场安静的大屠杀。饥饿、多重先天畸形、癌症、心脏缺陷、麻风病、各种饮水传染的疾病和死亡,从巴斯拉儿童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尾随在他们的后面了。”
伊拉克儿童的大量死亡作为20世纪的重大罪行,跟纳粹大屠杀、1945年盟军轰炸德累斯顿和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的暴行一样令人发指。
小诗人贾西姆,愿你安息
2月份的时候,在巴格达一家医院,我遇见了13岁的贾西姆。他得了一种致命的白血病,无精打采地躺在那儿,用他又大又黑的眼睛看着病房,这个他的小小世界。他的眼睛在他美丽、苍白,几乎透明的皮肤的反衬下显得更大了。他一头浓密的黑发打着小卷,像是特地打理过一样,让人难以相信他的健康状况已经是朝不保夕。
在生病之前,贾西姆在伊拉克南部的家乡巴斯拉街头卖香烟。巴斯拉是伊拉克古老的第二大城市,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遭到无情的轰炸,成了“沙漠风暴”行动名副其实的“风暴眼”。美英联军在战争中使用了包裹核工业废料“贫铀”外壳的导弹和子弹,现在已经被证实和伊拉克儿童患癌症人数成6倍的增长有关。这种弹药的使用造成了伊拉克全国残余着大量放射尘埃,而巴斯拉是这场灾难的正中心。美国陆军环境政策研究所指出:“贫铀进入人体之后可能会对健康造成严重的后果,它会从化学和放射性两方面给人体健康带来危险。”残留的放射性尘埃会随着风传播,其影响要持续45亿年之久。
对伊拉克实施的制裁禁运让童工问题成了这个国家特有的悲剧,要知道,教育从前在伊拉克可是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父母如果不把小孩送去上学,会被处以罚款。我坐下来跟贾西姆谈话的时候,医生告诉他我是以写作为生的。
情况立刻发生了转变。贾西姆坐了起来,满脸现出活泼激动的神情。他从枕头底下拿出本练习簿。封面上是米老鼠,里面是一笔漂亮的阿拉伯语,都是他每天写的诗。贾西姆长大了想当诗人。他的诗在技巧、才华方面都很不凡,有一种远远超过他年龄的洞察力。
有一首叫《身份证》,是这样写的:
姓名是爱,
班级是无心,
学校是苦难,
省区是哀伤,
城市是叹息,
街道是悲惨,
门牌号码是一千次叹息。
他还特别收集了一些他喜欢的格言。“生命不会考虑我们的热情,”这是一条,还有:“我问死亡,有什么能够大过你?和爱人分手更大过死亡。”他仔细地望着我的脸,想知道我对他这本小诗集的反应如何。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最后我说:“贾西姆,你一定要尽最大的力量和疾病斗争,赶快好起来,因为你真的是一个才华惊人的诗人。如果你在13岁就能写出这样的东西,我都无法想象你到20岁时能有多么大的成就。”我告诉他,他将会成为伊拉克伟大而古老的文学传统的一部分,最初正是这个国家为人类带来了写作。他高兴起来。我问他知不知道一句谚语:“书是在埃及写的,在黎巴嫩印的,在伊拉克被阅读的”,还问他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人只有通过不断阅读,搜集特别的句子、事实、文字,才能学会写作,就像他正在做的那样?他说没有听说过。尽管他病得很重,还是听得很投入、很专心,还仔细地把我说的都记了下来。我向他介绍了几位诗人和他们的生平,还背给他听了一些我喜欢的诗句,他把这些也写了下来,脸上洋溢着喜悦,那是因为有人能够理解他的激情,心灵的语言和他相通。
我写了很多关于贾西姆的报道,他的诗也登到了很多报刊上。贾西姆的生命悬于一线,他需要进行一种化疗,欧洲的一个救援机构必须在10天之内赶回巴斯拉才能救他。
就在3个星期之前,一个朋友去了伊拉克,我把写贾西姆的文章的剪报特别装订起来交给他,嘱托他带给贾西姆,让他看看自己的诗作第一次被印刷出来——我都想到了他的小脸又一次神采焕发的样子。
昨晚朋友从伊拉克回来了,打来了电话。“贾西姆怎么样?”我问他。救援机构没有及时赶回去,贾西姆一次次在病痛中挣扎搏斗,他弥留了一段时间之后,在我的朋友到达之前败给了死神。贾西姆再也看不到自己发表的诗了——现在,他只不过又为对伊制裁中“附带损害”的统计增添了一个数字。
我曾经告诉贾西姆,诗歌能够永远活着,我还引用了英国诗人詹姆斯·艾尔罗伊·福莱克的诗:
因为我从未见过你的脸,
也从未牵过你的手,
我穿越时空传送出我的灵魂,
向你问好。
你会明白的。
福莱克传送出送信人一样的文字,走过我不会走过的道路。他要求一位从未见过、尚未出生、也不认识的朋友,独自朗读我的作品,在夜里。
那时我是个诗人,那时我很年轻。
就像你一样,贾西姆。
愿你安息,小诗人:生于1985年,死于1998年。
巴斯拉来信
在美丽却被无情地打垮了的巴斯拉,伊拉克第二大城市,这座在时间的迷雾中建立的古城,这个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交汇成为阿拉伯河的地方,伊拉克在制裁下的困苦,以及这个国家近来的历史都被封存了起来。高耸的铜像排列在河畔,它们是两伊战争的英雄,每尊铜像都伸出右臂怒指着伊朗的方向。持续8年的两伊战争造成的损失几乎不亚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巴斯拉到处都能见到这场战争带来的破坏。破坏之上又添破坏,在这之后3年不到又爆发了海湾战争,去年12月美英两国又进行了连续4天的轰炸。一位居民自嘲地说:“我们有句俗话说,就算法国和德国打仗,巴斯拉也会遭到轰炸。”
海湾战争后,癌症、白血病和恶性肿瘤的发病率上升了70%,原因和美英部队使用的贫铀武器有关,这种武器在伊拉克全国都留下了放射性尘埃。據专家介绍,这些尘埃已经通过地下水和土壤进入了食物链。在巴斯拉我们目睹到一场安静的大屠杀。饥饿、多重先天畸形、癌症、心脏缺陷、麻风病和各种饮水传染的疾病——死亡从巴斯拉儿童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尾随在他们的后面了。
伊拉克儿童的大量死亡肯定会作为20世纪的重大罪行载入历史,跟纳粹大屠杀、1945年盟军轰炸德累斯顿和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的暴行并列。去年7月辞去联合国伊拉克人道事务协调员一职的前联合国助理秘书长丹尼斯·哈利戴指出:“每个月有6000到7000名5岁以下的儿童因为和禁运有关的原因而死亡。”哈利戴辞职就是为了抗议这种“对整个国家的毁灭”。
巴斯拉的病例有的已经超乎了人的想象。一位医生的论文比较了巴斯拉和原子弹轰炸后的广岛在婴儿先天畸形上的异同。杰南·侯赛因医生记下了所有先天畸形的病例。他拿出1998年拍摄的照片展示了足月出生的婴儿发育不全的情形,这种情况又叫“葡萄串综合症”,让人想起1950年代原子弹试验后太平洋岛屿上出现的症状。还有其他种种婴儿畸形——没有脸、没有眼睛、四肢扭曲、没有四肢、没有大脑。
“如果你不会昏过去的话,我可以给你看看一小时前刚出生的一名婴儿,”杰南医生说。这个小东西发出细小、颤抖的叫声。它没有生殖器,没有眼睛、鼻子、舌头、食道和双手。扭曲的双腿从膝盖往上的部分都被一张厚厚的“肉网”连在一起。医生说:“我们见过很多相似的婴儿。”当地的植被显示出高达正常值84倍的辐射。
唇腭裂發病率也出现了令人吃惊的增长。“过去我们很少见到唇腭裂病例,我每星期有两次手术,现在平均每次有两个唇腭裂。有一家人生了3个女儿都是唇腭裂,她们的父母求我在一天里把3个手术都做了,因为他们没有钱再回来一次了。”面颌外科医生穆斯塔法·阿里这样说。他曾经在英国的爱丁堡、格拉斯哥和邓迪工作过,两伊战争开始以后回到伊拉克,战争中难以想象的伤病大大磨炼了他的医疗技术。可是即便是两伊战争时期的情况也无法跟联合国制裁9年之后的生活之差相提并论:“有些孩子的父母只有够用来做手术的钱。他们到医院时我们没有氧气,没有麻醉药,他们只好走了,但再也没有回来。”
巴斯拉附近有一个村庄,幼小的孩子们在水沟里玩耍,贫穷是当地最大的特色。在那里我们找到了两岁的维迪安。维迪安的母亲离家出走了,他是祖母带大的,家里空空荡荡,一件家具也没有。维迪安身体瘫痪,双臂萎缩,腿部畸形,连呼吸都很痛苦。他长着一张虚弱的小精灵般的脸,只有眼睛能动,警觉地张望着。巴斯拉总医院的费萨尔医生认为他最多再活一年。听专家说,这些畸形儿无论是在哪里出生,都有一些共同特性。要不就是家庭所在地区在海湾战争期间遭到猛烈轰炸,要不就是父亲曾参加过被轰炸地区的部队。
25%的新生儿因为营养不良和环境因素早产或者体重过轻。医院里的早产婴儿保育箱都不能全效运转;因为没有氧气,没有鼻胃管,没有净化和卫生设备,就连消毒剂也被联合国制裁委员会禁止进口。早产婴儿病房有17个婴儿。医生说:“1994年后没有一个早产儿存活下来过。”我注视着那17个新鲜生命的小脸,现在他们几乎可以确定都已经加入了和禁运有关的统计数字里。
我们离开的时候,阿里医生问道:“如果巴斯拉再遭到轰炸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拿这么多伤亡怎么办?”我们沿着巴斯拉一条公路朝北驶去,那条公路就是海湾战争时美军总司令诺曼·施瓦茨科普夫将军指挥的“猎火鸡”大屠杀的现场,已经成了那次大屠杀的代名词。一路上还有被烧毁的车辆,仿佛是对那场难以想象的恐怖的不断提示。那是个星期天的晚上。
第二天早上9时30分,巴斯拉又遭到轰炸。
巴斯拉有一个伊拉克航空公司的纪念碑。上面刻着:“伊拉克航空公司,1947年至1990年。”它可以作为伊拉克的一个隐喻,象征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提出的“儿童的权利”,和每个月那7000名5岁不到,并没有“违反联合国决议”的死亡儿童。
(来源/《别对我撒谎·23篇震撼世界的新闻调查报道》,约翰·皮尔格选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第一版)
责任编辑/周津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