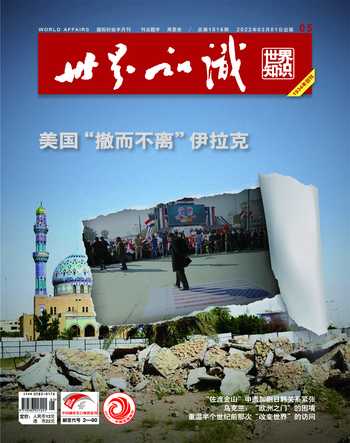美国“角色转变”后,伊拉克困境会有所改变吗
唐恬波
2011年12月,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把美国从伊拉克撤军称作“胜利时刻”,声称美国留下了一个不完美但“主权独立、稳定、自力更生”和“拥有民选代议制政府”的国家。十年之后的2021年12月,美国宣布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作战任务,并将剩余驻伊拉克的2500名美军转变为“培训和顾问”角色。但此次美国总统拜登没有发表胜利演说,而伊拉克离独立、稳定和自主也更加遥远,其政治、安全与经济困境也很难因美国的“角色转变”而有所起色。
美国因素导致原有问题不必要的激化
美国研究伊拉克历史的著名学者菲比·马尔曾言,伊拉克自古就以“难以治理”闻名,而这一名声甚至被保持至今。近代以来,伊拉克可以说基本上遇到了中东地区存在的所有典型国家治理难题,包括但不限于教派民族冲突、部落文化、恐怖主义、非政府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坐大、经济结构畸形和外来力量干预等。美国在2003年对伊拉克的入侵、占领和改造,尤其导致了该国原有问题不必要的激化。
2003年后美国在伊拉克建立的政治体制并非是所谓的“美式民主”,而是以黎巴嫩模式为蓝本、以教派分权为特征的议会制。这一政治模式强调伊拉克国内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族这三大阵营对自我身份的认同,而这既损害了各教派民族对伊拉克的国家认同感,又破坏了该国的治理能力。在缺乏主流意识形态且政党政治也不成熟的情况下,三大阵营都惯于以族群身份进行选举动员。这导致许多人逐渐淡忘了国家概念,转而以族群利益为先。占伊拉克人口约60%的什叶派惯于从地区宗教领袖处寻求指示,占伊拉克人口约18%的逊尼派试图依靠外援乃至极端势力弥补其政治劣势,库尔德族约占伊拉克人口的15%,他们则渴望从自治走向“建国”。三方阵营都有离心倾向,这使得建立统一的国家认同观念“难上加难”。
身份政治对伊拉克国家治理能力的冲击同样不容忽视。一是造成冗官冗员现象并拉低伊拉克政府的执政效率。伊拉克自上而下地贯彻教派族群分权,意味着国家各级职位都必须“三方有份”。例如,若議会议长来自逊尼派,那么第一与第二副议长则分别来自什叶派阵营和库尔德族阵营。二是限制了对政治人物的问责,恶化了腐败问题。伊拉克国内政客执政表现糟糕时,往往以自己“为族群争取了利益”作为开脱,而所有对政客的腐败指控,则多数被批为来自政敌的“陷害”。于是,身份政治成了一些腐败行为的庇护所,而部分政客通过腐败行为集聚了大量资源,以雇佣团队、收买人心等方式限制后来者对自身的挑战。三是“老面孔”垄断政坛,民众日益“政治冷漠”。伊拉克政坛被舆论普遍认为存在“老面孔”垄断领导层与“裙带关系盛行”的问题,民众选来选去也无法改变现状,因此对选举乃至政治本身日益失望。

2019年10月,伊拉克爆发大规模抗议示威,民众呼吁推翻现有政治体系及其领导人。
与政治领域相比,美国对伊拉克安全领域的破坏也不遑多让。2003年5月,美国完全解散了萨达姆时期以逊尼派为主导的伊拉克军队。之后迫于严峻的安全形势,美国力求快速组建包括军队和警察在内的伊拉克安全部队,因此大肆成建制地吸纳来自什叶派和库尔德地区的民兵,给该国埋下了民兵武装组织不断发展壮大甚至“尾大不掉”的伏笔。2014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伊拉克攻城略地,美军重返伊拉克进行反恐。此番美国只肯采取“空中干预”行动,拒绝在伊拉克部署大规模地面部队。因此,在伊拉克军警部队大部溃散的情况下,美国只得借助库尔德族乃至什叶派民兵武装力量在地面进行反恐作战,导致民兵力量再度膨胀。库尔德民兵武装组织与伊拉克中央政府一度武装对峙,有了搞“独立公投”的基础;什叶派民兵武装力量在打击“伊斯兰国”期间,通过伊拉克政府间接获得了美国的军备、资金和作战支援,人数扩张到十万以上。民兵势力强大,导致伊拉克难以在国家层面合法垄断暴力。可以说,目前令伊拉克国家主权受损且被美国描绘为该国“万恶之源”的什叶派民兵武装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国自身政策的产物。此外,美国还使伊拉克军警部队日益“空心化”。在2011年美国撤离伊拉克前,伊拉克军警部队曾长期参与反恐和“平叛”作战,但由于情报、指挥、后勤和空地协同等“高端”作战任务均由美军垄断,伊拉克军警部队得到的锻炼较为有限,再加上腐败的侵蚀,伊拉克军警部队日益“空心化”,这导致的直接结果之一便是2014年伊拉克军队面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攻城略地时“一碰就碎”。
伊拉克经济对石油的畸形依赖同样与美国的胡乱作为有关。2003年,美国曾对伊拉克经济推行加强版的“休克疗法”,取消了该国的所有贸易保护政策,这导致大量廉价进口产品蜂拥而至,一下子冲垮了伊拉克本土孱弱的制造业。此外,美国将大量战后重建项目交给了美国企业,却不进行有效的监管,这导致支出大量资金后,拟建的道路、医院与发电厂等国家发展必须的基础设施不见踪影。非石油产业被美国简单粗暴的政策严重破坏,叠加基础设施的大量缺乏,导致伊拉克难以依靠石油反哺非石油产业,因此该国经济对石油的依赖越发加重。
政治混乱,安全风险上升
2021年10月,在民众持续不断地进行大规模抗议示威,呼吁推翻现有政治体系及其领导人的压力下,伊拉克依据2019年12月新通过的国民议会选举法,提前举行了议会选举。其结果是什叶派宗教领袖萨德尔麾下政党“萨德尔运动”拿下最多议席,赢得了议会329个席位中的73个,伊拉克前总理马利基领导的“法治国家联盟”、国民议会议长哈布希领导的逊尼派政治团体“进步联盟”和库尔德民主党(简称库民党)所得议席数量也在30个以上。亲伊朗的什叶派政党“法塔赫联盟”整体得票数与“萨德尔运动”不相上下,却因选区划分和内部竞争(如什叶派民兵武装组织“真主旅”坚持单独组党参选)等因素,导致所赢得议席数量不足20个,相比上届选举结果减少了三分之二。因此,一些不服选举结果的民兵武装力量转向通过暴力来“抢夺选票中未能获得的利益”。同年11月,看守政府总理卡迪米遭遇未遂无人机暗杀。2022年1月,哈布希的住所被火箭弹袭击,其幼子受伤。一时间,政治暗杀在伊拉克迅速蔓延,“萨德尔运动”和亲伊朗的什叶派民兵武装力量中均有高级指挥官被杀身亡,未遂暗杀更是“家常便饭”。在如此混乱的局面下,萨德尔选择与哈布希及库民党组成联盟。该集团通过吸纳一些小党和独立议员,已手握组阁所需的165个席位,哈布希也因此成功连任议长。同时,萨德尔还在试图邀请其他什叶派政党入阁。
然而,无论如何组阁,伊拉克的政治痼疾恐怕都难以缓解。首先,教派分权仍是该国政治底色。在伊拉克政坛“翻云覆雨”的仍是萨德尔、马利基等“老面孔”,政治体系的“基本游戏规则”和“主要玩家”都没有发生变化。其次,从过往政绩看,“萨德尔运动”的执政能力尚待证明。萨德尔旗下政党的高级成员在过去长期执掌电力、卫生等部门,但其施政表现都不理想,此外部分高级成员还屡涉贪腐大案。总而言之,伊拉克更需要一个拥有广泛民意支持且权力足够集中、能力令人信服的政府来“医治”其政治衰败,但短期内具有该特征的政府难以出现。
政治上的混乱和真空使伊拉克的安全风险上升。自2021年12月美国将伊拉克驻军转变为“顾问”以来,什叶派民兵武装力量仍在继续攻击包括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在内的目标,但同时也在避免造成美国人的伤亡,从而引发美国的激烈报复。而美国也在加强防卫,力求避免出现大规模人员死伤以致于不得不回师美国的局面。同时,大部分民兵武装组织都涉嫌卷入了政治暗杀,与伊拉克军警部队一样或忙于保护要人,或致力于报复与反报复。而上述各方恰是伊拉克反恐的主要力量,反恐阵营的一片混乱使“伊斯兰国”有了蓄力和重组的空隙。该极端组织继2021年多次在巴格达及其周边地区发动大规模恐袭后,还曾在2022年1月攻入位于巴格达东北方迪亚拉省的一处军事基地。在美国的支持下,伊拉克军警部队虽在大体上能够完成“打地鼠”式的反恐作战,但若美国逐渐减少投入,同时极端组织继续坐大,那么2014年大溃败的历史不是没有重演的可能。
在经济方面,2020年下半年以来国际油价的回升,使伊拉克财政暂时获得了喘息空间。但由于政府治理能力欠缺,该国只能靠增加公共岗位、提高工资等“发钱”的方式与部分民众共享石油财富,难以将其用于必要的投资与建设。
伊拉克的国内态势走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中东地区国家整体情况的缩影。教派民族矛盾是伊拉克国家良治的绊脚石,也是治理失败的遮羞布。民众若没有强固的国家认同感,所谓的“民主选举”只会助长该国的内部分裂,并进一步冲击民众的国家认同感,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同时,政治上的失能会迅速传导至安全与经济领域。而这些问题部分来自美国引入的“新自由主义”,若要克服这些问题,则有待于伊拉克和其他中东地区国家痛定思痛的自主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