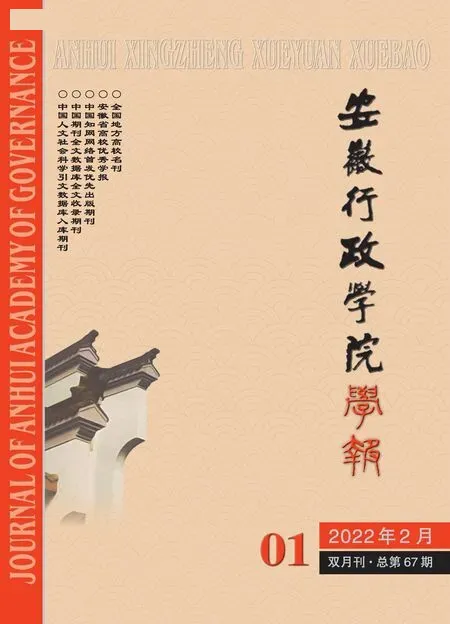嵌入性视角下城市社区居委会“内卷化”困境及成因
李艳丽,张紫菁
(武汉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社区居委会作为连接政府与基层民众的桥梁,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随着城市社区治理实践的不断深入,居委会行政化色彩日渐浓厚。2015年,民政部和中央组织部发起减负改革运动,旨在缓解社区治理压力,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1)。但时至今日,居委会的治理效能不仅未见明显提升,反而引发“边缘危机”“行政回弹”(2)等一系列问题,陷入“内卷化”的治理困境。导致这一困境出现的原因有哪些?纾解这一困境的可能路径是什么?综合学界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发现学者们主要从基层治理和路径依赖理论两个角度出发,论证了居委会“内卷化”困境产生的原因。从基层治理的角度来看,组织内部资源约束、政府干预过多、居委会成员主观倾向[1-2]、法治建设不完善[3]等都是社区居委会治理“内卷化”的原因;从路径依赖理论出发,认为我国的传统文化、宏观政策、社会情境、组织构架等诸多元素共同作用导致居委会“内卷化”[4-6]。也有极少数学者以经济社会学的嵌入性理论为出发点,指出居委会在社区治理中的行动逻辑受“双重网络嵌入”的影响[7]。嵌入性理论作为一种分析框架,为城市社区居委会的治理提供了全新的探索视角,更为系统直观地揭示了居委会在政—社治理格局中的地位和各主体间的关系特征。为此,本文同样基于社会嵌入理论的分析框架,探讨居委会在政—社关系网络中的弱连带特征,并以此为出发点阐述居委会“内卷化”治理困境的成因,提出纾解社区治理“内卷化”困境的可能路径。
一、何为“内卷化”
“内卷化”由拉丁文“involutum”演化而来,用以形容某种盘绕起来的繁乱事物(3)。最早使用这一概念的美国学者亚历山大·戈登维泽将“内卷化”描述为某种事物在到达最终形态时,既无法停止运动保持稳定,又不能继续突破成新的形态,只能向内转化,让内部结构变得更加复杂[8]。之后,美国学者格尔茨[9]和黄宗智[10]进一步延伸“内卷化”概念,将其引入农业经济研究;杜赞奇则从政治角度,用“国家政权内卷化”来描述国家机构不合理扩张的现象[11]。现如今,“内卷化”作为一个开放的学术概念,已经被广泛运用于社会、经济等各学科领域。通过提炼亚历山大·戈登维泽等四位学者的主要观点,可以对“内卷化”概念进行一个大致界定,即内卷化作为一种状态,描述的是当某种系统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由于外部条件的制约无法继续扩张,只能转向精细化内部,但在总体上呈现停滞不前、无实质性的增长。
二、行政回弹与边缘化:城市社区居委会的“内卷化”危机
结合当前各地区城市社区治理改革实践,发现居委会“内卷化”困境总体呈现“行政回弹”和“边缘危机”两大趋势。
(一)行政回弹
1.行政倾向突出
居委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在实际生活中却往往承担大量政府下派的工作,从办公场地、行为做派到工作内容都有着突出的行政化倾向。部分地区试图通过推行整合服务窗口、取消社区挂牌、简化公章使用等举措改善这一局面,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社区工作负担,却未能触及社区居委会行政化的实质。一些上级政府不深入基层、不了解辖区实际情况,为了便宜行事,在城市管理过程中仍将各类具体事务抛给作为基层治理单元的社区。与此同时,事务下沉并未带来相应的权力下沉,居委会缺乏足够的权威,在大多数时候只能选择打“人情牌”,履行职能的过程中还要顾虑“担责”问题。这些现象加重了居委会日常工作的压力,导致社区自治成本激增。
2.身份定位模糊
2015年,减负改革前的社区居委会具备强烈的“类行政化组织”特性,即成员并非国家公务人员却承担一定社会管理职能的非行政性组织;改革后,由于居委会类行政化实然性质与自治组织应然属性之间的矛盾未得到有效解决,其身份定位模糊的问题仍然存在,如将居委会看作是政府机关或办事处,忽略其社区内组织的性质。社区居民甚至某些居委会工作者都对自己所在社区居委会的职能、日常事务、工作地点不够了解等。
3.事务包揽过多
城市社区居委会的群众自治性质要求其应与社区居民构建友好关系链,形成良性互动。但在实际生活中,作为治理主体的青壮年群体更多活跃于工作区域或学习区域,在城市社区内往往呈现“不在场”的情形;缺乏自治意识的老人或学龄前儿童成为社区生活的主体[12]。无论改革前还是改革后,城市社区居民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均普遍偏低,社区自治活动的开展难度较大[13]。为了提升治理效率,节省治理成本,缓解工作压力,本该和居民双向配合的居委会往往只能采取“大包大揽”的方式推进社区建设,缺乏与居民的有效沟通。虽然从表面上看,社区发展速率得到了短暂提升,却在无形中助长了居民的“政治冷漠”,甚至导致“懒治”,不利于培养社区内生治理活力。
4.社区治理资源不足
改革前,社区治理资源短缺、政府财政供给不足几乎是多数城市社区普遍存在的问题。居委会治理资源受限,社区办公设施落后或不全,无法支撑工作人员完成日常工作,拉低效率;社区经费拨给不到位,治理活动难开展,居民日常生活未得到实质性改善;工作人员薪资待遇低,福利补贴不到位,限制了社区人才培养,阻断了新兴力量的注入,使社区居委会整体出现“老旧化”“高龄化”趋势。为此,中央提出“权随责走、费随事转”制度,要求各地有关部门在开展需要居委会协助配合的工作时,应及时划拨经费并为其提供有效的工作条件。但在推进改革实践的过程中,部分地区并未将这一制度完全落实到位。经费“迟拨”“不拨”,社区工作人员薪资待遇得不到提升,工作热情被大大消磨。社区缺乏其他资金来源渠道,只能被动推进工作,活动开展依然受限。
(二)边缘危机
1.组织架构被迫裁撤,内部趋于“空心化”
居委会结构科层化现象是对自治组织属性的削弱和对政府基层管理单位属性的强化与迎合。实行减负改革正是为了改变这一局面,但在改革以后,居委会在“政府—社区”结构中的定位反而变得更加尴尬。部分地区通过设立社区工作站,实行“议行分设、居站分离”的模式帮助居委会分摊事务,这一举措虽减少了居委会的工作负担,却也在无形中削弱了居委会在社区治理中的地位及居民的信任度。一方面,居委会承担的工作量减少,社区群众对居委会的需求和认同也随之减弱;另一方面,政府如果拨出资源以支撑社区工作站的运转,就必然要削减对居委会的财政补贴或人员技术支持。如此一来,居委会不得不精简组织架构并裁减成员,导致内部“空心化”的出现。
2.生存空间遭受挤压,地位呈现“边缘化”
减负改革前,政府管理重心下移导致大量社会行政事务下沉至社区,居委会日常工作负担重,行政事务繁多,为了完成任务不得不减少处理社区日常事务的时间,居民自治空间遭受挤压。除此之外,居委会还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处理各类报表等工作,以应付繁复严格的考评制度,甚至为了达成指标,出现弄虚作假、只顾形式不顾质量的“面子工程”,大大影响社区治理的成效。为了解决居委会工作事务过于行政化的问题,一些地区采取行政职能和自治职能相剥离的措施,试图让居委会复归基层群众自治的领域。虽然这一举措让居委会的行政负担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却也进一步削弱了其作为治理主体的话语权。失去行政职能的居委会无法维系与政府的紧密联系,也无力再处理社区居民对政府的意见和诉求,甚至难以动员居民配合日常治理活动,由此在社区结构中呈现“边缘化”的趋势。
3.民众缺乏参与热情,陷入治理“无力化”
从总体来看,减负改革之后,部分地区政府有意减少对城市社区的管控,试图通过“议行分设”、建立社区工作站等方式引导居民实现自我治理,让居委会摆脱“万能居委会”的称号,然而这些举措未能从根本上有效激发居民的自治意识。一方面,政府管理和居民自治并非处于“此消彼长”的态势,政府放权并不意味着居民自治就能实现相应的“弹性增长”,催生居民自治活力,得从居民自身抓起;另一方面,受传统体制影响,居民的自治意识和自治能力稍显不足,政府在这一前提下贸然“放权”,可能会形成社区事务无人管也无力管的尴尬局面。既无法调动辖区居民的参与热情,又缺乏“大包大揽”社区日常事务的能力和资本,部分城市社区居委会在减负改革后反而陷入“孤掌难鸣”的困境。
综上所述,可将居委会的治理“内卷化”困境概括如下:出于减负改革等目的,虽然居委会的组织架构、工作职能有所改变,但其实然属性与运作机制却未能从根本上得到优化,导致居委会仍然陷入治理乏力的困境之中。
三、弱连带嵌入与脱域:居委会“内卷化”困境的形成原因
(一)弱连带嵌入下的居委会生存处境
作为新经济社会学的核心理论,嵌入性(em⁃beddedness)理论最初是由匈牙利学者卡尔·波兰尼提出的,用于反驳当时经济学界流行的理性经济人假设,认为市场必然嵌入于社会[14]。在他之后,美国学者格兰诺维特构建了一系列嵌入模型,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弱连带优势”说,他认为,个体之间的双边关系以“关系性嵌入”的形式体现,且可以根据“认识时长”“互动频率”“情感亲密(彼此推心置腹)”“互惠性服务内容”四个要素将关系区分为强连带、弱连带和无连带。通常情况下,弱连带关系由于信息传播广泛,往往能给人们带来更多的社交或就业机会,便于个体融入社会[15]。随着嵌入性理论被引入国内经济、社会等研究领域,“弱连带优势”似乎呈现出全然相反的本土化特征。纵观社区居委会在政—社网络中的嵌入状态,发现居委会成员与其他主体成员的弱连带关系恰恰是导致居委会治理改革乏力的重要原因。
1.认识时间短,个体角色遭受符号模糊
根据格兰诺维特的理论定义,关系性嵌入涉及“双边”个体,且主体双方的“认识时长”特指“两者在一起时耗费的时间量”,暗含着深层“熟知”及“互动”含义(4)。在以基层治理为载体的实际工作中,居委会成员、政府人员乃至社区社会组织成员都被模糊为“机器”符号(行政机器或自治机器等),个体角色特征被淡化。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以理性主义的工作交接为主,互动关系悬浮于组织表面,并未达成深层“熟知”的条件,因此认识时间短。而在和社区居民的交流中,一方面,社区居民基数大,居委会成员在有限的人力精力条件下很难与他们构建普遍的“一对一”熟识关系;另一方面,社区居民乃至某些居委会成员自身均存在“不在场”现象,亲密互动关系受人员流动影响,难以长期维持。这都导致日常生活中居委会成员与社区居民认识时间不长,互动不够深化。
2.互动频率低,“事缘”交往倒逼行动压力
政府与居委会的互动多以“工作下达—成果反馈”的上下级工作交流为主,即纯粹的“事缘”型互动,这类互动伴随着理性工具主义,难以促进情感的升温,政府成员与居委会成员的对接中同样采取“公事公办”的理性态度,双方“无事不联系”,这其实就是个体互动频率低的表现。居委会与其他社区组织同样以“事缘”交流为主,职能划分较为明确,平时各有分工,互动机会较少。高频率互动通常出现在社区应急治理时期,这时的互动具有紧急性、高压性等特征,成员承载情感过于负面,不属于良性交流的范畴。改革后,一些新型社区组织,如社区工作站的出现,进一步挤压居委会的生存空间[16],更加影响双方的连带关系。相比政府和社区组织,居委会和社区居民之间的交流多了一层“地缘”或“情缘”的色彩,但实质上仍以“事缘”为主。居委会成员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会主动采取“打人情牌”的方式与居民拉近情感关系,吸引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活动,但这种方法耗费成本高且无法完善有效激励机制,成果也不尽如人意。居民碍于人情不得不短暂地参与社区活动,久而久之还会对此产生反感情绪。居民的主观能动性未得到提升,仅把居委会成员看作是敷衍应付和寻求帮助的对象,对居委会的工作配合不足,互动频率低。
3.情感关系弱,负向情绪滋生矛盾
根据前文可知,“事缘”型交往容易滋生负面情绪。居委会和政府互动过程中,繁重的行政负担、过多的绩效考评往往会导致居委会成员产生焦虑和逃避心理,影响其工作积极性,而政府成员由于要对接多个社区,自身事务繁忙,在能直接通过“事缘”互动达成任务目标的前提下,同样缺少与居委会成员构建亲密情感关系的动机和条件,双方情感联系薄弱。居委会成员与社区组织成员之间,一方面互动频率较低,情感关系匮乏;另一方面受主体利益导向影响,社区组织成员“事缘”互动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权责和利益纠纷。如部分物业公司将自己定位为社区事务管理者而非服务提供者[17],利用社区设施和资源为自己谋取商业利益,由此引发与社区的矛盾冲突,导致情感关系恶化。在与社区居民交往的过程中,出于社区义务感和利益驱动,居委会成员倾向于与社区居民建立亲密情感关系,希望以此提升居民配合度,营造和谐友爱的社区氛围。但实际工作中居民对社区治理持“冷漠”态度的现象较为普遍,居民仅在有需求时才会主动与居委会沟通,居委会成员很难与居民建立起紧密的双边情感联结。
4.互惠内容少,理性互惠淡化人际关系
居委会与政府之间存在明显的互惠服务,具体表现为居委会为政府分摊行政类事务,政府为居委会提供存续资源,但两者间的互惠规范以基于理性的政治性互惠为主,并由于地位、资源的不平等导致了单边依赖倾向。居委会必须依靠政府提供的资源才能保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失衡的理性互惠规范可能会加剧居委会成员的心理和行动负担,容易淡化甚至恶化双方的互动关系。社区社会组织所需资源通常也都是由政府或者市场来提供,他们和居委会之间很少存在互惠性服务内容,除非社区发生突发性公共事件,需要各治理主体共同参与、协作配合,利益共谋现象才会产生。但此等情境下的互惠服务同样基于理性或社区义务性,很难进一步催生出情感联结,更不用说协作配合通畅,若社区组织之间出现推诿塞责现象,还会反向滋生矛盾和冲突。居委会的自治组织性质决定了居委会在日常生活中必须为社区居民提供惠利。而居民给予居委会的惠利则往往以价值回报为主,如帮助居委会完成工作指标,形成良好自我认同等。但在实际生活中,居民的社区参与感淡薄,居委会成员收获的价值回馈往往不对等。长此以往,居委会成员很容易在心态上产生动摇,导致社区义务感的消磨。
根据格兰诺维特的嵌入性理论,正式的组织及工作环境通常是弱连带关系的主要来源。居委会成员与其他治理主体以“事缘”为主的互动决定了其关系连带基本仅存于工作场合,与私人生活场域几乎割裂。而在我国特有的特殊主义导向下,传统的“熟人社会”本质决定了以强连带为主的嵌入关系是帮助个体依托人情往来,从而获取更多社会资源的优势途径。这就使居委会成员在弱连带关系中无法获得充足且流动顺畅的社会资本,面临资源匮乏的困局。与此同时,受弱连带关系影响,顶层政府与基层社会未能构建亲密有效的联结,居委会不得不作为政—社关系网中的“桥”而存在。虽然这在某种程度上防止了政府和居民的“身份越位”[18],但也为居委会增添了较为沉重的负担。减负改革不仅没能强化居委会成员与其他主体成员间的连带关系,甚至通过削弱其职能地位等方式将连带关系进一步弱化,使得居委会逐步退让到无连带的边缘,由此更加陷入社区治理“内卷化”的困局。
(二)脱域:社区居民自治动力缺失之根本
居委会与其他治理主体的弱连带关系是催生居委会治理“内卷化”困局的重要原因。但仔细分析当前的社区治理改革会发现,即便国家将权力触手抽离基层社区,在政府、居委会和其他社区组织的多方努力下,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主动性也很难得到有效提升,居委会带动下的居民自治仍然乏力。社区内生性治理动力缺失,究其根源,在于现代化城市社区的“脱域”,如图1所示。

图1 嵌入性理论下居委会“内卷化”治理困境研究框架
“脱域”(disembedding)一词是由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最早提出的。他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将“脱域”解释为“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19]。与原有单位制不同,现代化城市社区的大部分居民由于生活方式、工作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日常活动区域远离社区居住地,并且主要以学习区域或者工作区域为依托,围绕自身构建了一个更加广阔自由且不受居住空间限制的社会关系网络。
在这样的脱域机制下,社会资源从先前由单位内部集中分配转向社区外自由流动,带动了社会关系网络的外移。异质互嵌取代了原先单位制时期的同质生活[20]。高流动性和强异质性逐渐成为现代社区的常见生态。社区失去了以往包括交互、实践、资源整合及分配等功能,仅仅体现纯粹的居住意义,再加上社区通常为居民提供的是维持性资源而非发展性资源,居民需求在社区之外的场域能够得到满足,导致他们对所在地域社区的依附性大大降低。与此同时,社区成员的价值观念、生活习惯、文化水平等差异过大,很难形成有效沟通。大家不愿花费时间精力与陌生邻里建立亲密互动关系。一方面,受情感关系淡薄和低认同度的影响,现代社区内多数居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不强,对社区活动抱有“冷漠”或抵触情绪;另一方面,由于工作、学习等原因,社区居民中占比较多的青壮年群体基本处于“不在场”状态,社区建设主体缺失,加剧了居民在社区治理中的边缘化色彩。
由此可见,现代城市社区的“脱域”大大削弱了居民参与社区自治的主观动机和客观条件,是导致基层自治发育不足的根本原因。若“脱域”问题不解决,居民自治水平始终无法提升,无论社区如何实行治理技术创新变革,也难以走出基层社会治理乏力的困境。
四、总结与反思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基层民主作为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关键领域,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经过长期探索,我国现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逐步形成一套相对稳定且有效的基层治理制度,在党和国家的带领下,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中国特色基层治理制度优势得到充分展现。当前基层社会治理改革实践的重点,是进一步拓宽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范围和途径,提升群众参与感和幸福感。本文从嵌入性视角分析城市社区基层自治组织“内卷化”困境的成因,为解决社区治理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式。既然治理改革的核心在于促进民众参与、提高自治能力,就应当将“自治”贯彻落实到具体实践当中去,解决城市社区最根本的“脱域”问题,强化基层自治组织与其他治理主体的连带关系,解除基层自治组织、社区居民等多元主体面临的资源约束、权力约束、利益偏好约束,从而发挥公共服务和社区自治应有的理念和价值,通过激发地方自治主动性,实现社区复兴[21]。不能把未来治理领域的前景全部寄托在行政运作之上,也不能全然抛弃政府引领。当前学界诸多学者呼吁社区治理改革需要“去行政化”,但结合我国的特有国情,在国家基层社区自治基础普遍薄弱的情况下,实现行政与自治的有效衔接才是最为合理的方式。在这里“自治”(self-governance)并不指代“绝对自主”(absolute autonomy),其更多体现的是社区在政府的操作范围内自行管理自身事务[22]。要构建“以行政引领自治,以党建推动协同”的社区治理新格局,建设多元主体协同合作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从而推动城市基层治理工作有效开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阔步前进。
注 释
(1)见《民政部、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开展社区减负工作的通知》(民发〔2015〕136号)。
(2)“边缘危机”和“行政回弹”作为居委会减负改革失败后陷入“内卷化”治理困境的两大趋向,前者是由于地方削弱居委会职能和结构,却未能帮助居委会顺利实现在社区治理格局中的地位转变,导致居委会组织转型与职能变动脱节,从而陷入无事可做,无力为治的边缘化局面;后者是由于地方减负流于形式,只精简社区挂牌、公章、工作平台等,却未有效缓解大量行政事务下沉的事实,治标不治本,使得居委会依然未能摆脱行政负担沉重的困局。
(3)“Late MiddleEnglish(in the sense'(part)curling in⁃wards'):from Latin involutio(n-),from involvere(see INVOLVE)”源自2013版《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The New Oxford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13)。
(4)在《The Strength of Weak Tie》这一章的原文中,格兰诺维特用“the amount of time A spends with B”解释个体间的认识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