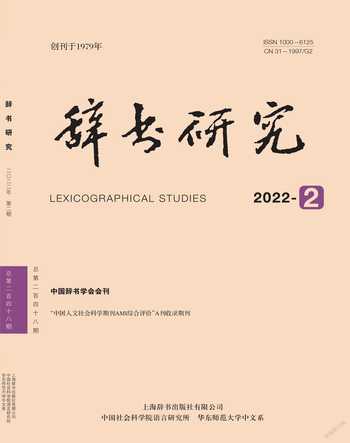“卢鹊”与“卢鹊喧”
李尔钢 李灵玢
摘 要 《汉语大词典》对“卢鹊”条的部分释义因对书证的误解而出现偏差。该词的使用始于春秋战国,而作为典故,则源于敦煌残卷所录汉诗。词典修订,除纠错之外,还须另立典故词条及其副条,原因有二:其一为大型语文词典词条分工之故,其二因“卢鹊喧”作为贪官恶吏重赋扰民之典,直至唐代仍在使用。展示用例,有助于“卢鹊”条正误,亦或有助于揭示语言中“断流典故”的来龙去脉。
关键词 卢鹊 卢鹊喧 词典修订
一
《汉语大词典》(以下简称《汉大》)第7卷1472页“卢鹊”条:
卢鹊①古代良犬韩卢、宋鹊的并称。亦泛指良犬。晋 葛洪《抱朴子·释滞》:“繁弱既韬,卢鹊将烹。”又《广譬》:“高鸟聚则良弓发,狡兔多则卢鹊走。”②鸟名。唐 李绅《闻里谣效古歌》:“莫令太守驰朱轓,悬鼓一鸣卢鹊喧。”
该词条义项①释义及所引《抱朴子》两例,没有问题。相比之下,义项②就隐隐让人担心。首先,其释义“鸟名”过于简洁以至于粗略。与《汉大》其他鸟雀类词条相比,“卢鹊②”的释文缺少对于所释鸟毛色、形貌、生活习性等更为细致的描述。说明原释义撰写者或许并不清楚卢鹊是一种什么鸟,有望文生义的可能。其次,不同于义项①有两条书证支持,义项②所引《闻里谣效古歌》例只是孤证。这违背了除非理据充分,否则孤证不立的注释一般原则,也说明“卢鹊”作为鸟的意义在文献中绝少使用,原释义撰写者难以找到其他佐证。再次,在作为孤证的唐代李绅诗句“莫令太守驰朱轓,悬鼓一鸣卢鹊喧”中,太守飙车敲鼓与卢鹊这种鸟的喧叫之间,似不存在什么必然的联系,这使我们进一步怀疑,原释义者对于孤证是否过于轻信?是否是断章取义?对于所引李绅原诗的理解,是否没有做到知人论世、字斟句酌?是否没有做到通过整体来把握该诗引作证据的部分,从而产生了偏差?
考《新唐书·李绅传》,《闻里谣效古歌》诗大约作于唐大和六年末,李绅时由寿州刺史任改授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在离开寿州前闻民谣而效古歌,以一名虚构的“乡里儿”为主人公创作了该诗。《全唐诗》卷四八〇李绅《转寿春守》诗序云:“太和庚戌岁二月祗命寿阳,时替裴五墉终殁。因视壁题,自墉而上或除名在边,坐殿,殁凡七子,无一存焉。寿人多寇盗,好诉讦,时谓之凶郡,犷俗特著。蒙此处之,顾余衰年甘蹑前患,俾三月而寇静,期岁而人和,虎不暴物,奸吏屏窜。”《闻里谣效古歌》诗起首,描述主人公“乡里儿”无忧无虑、有吃有穿、夜不闭户、饮酒踏歌的静好图景,应该就是李绅对自己治理寿州三年后所得太平景象的文學性概述。诗的中间部分突出地指明“使君”的关键作用:“使君为我剪荆棘,使君为我驱豺狼。”说明正是由于刺史李绅的刚严治理和爱民仁心,才迎来寇静人和、奸吏屏窜,虎不暴物的太平景象。而接下诗句转折,以东家父老的口吻奉劝乡里儿要知晓贤明仁慈地方官的护佑之恩,说如果刺史接替者贪婪残暴,静好岁月将被打破。这与诗的结尾部分安慰乡人,说朝廷一定会选择好官继任,而自己将廉洁无私、两袖清风地告别寿州前后照应。
以上李绅《闻里谣效古歌》诗中含有词目且与其释义最直接相关的,就是以东家父老口吻假设贪暴刺史接任情形的以下诗句:
莫令太守驰朱轓,悬鼓一鸣卢鹊喧。恶声主吏噪尔门,唧唧力力烹鸡豚。
其中,“太守”为汉制,禄二千石,是一郡的最高长官,李绅用以称代唐代的州刺史。其“朱轓”亦为汉制,将两边车耳涂成朱红色,为汉代太守车乘的标志,李绅亦借指唐代州刺史之车。其衙门“悬鼓”亦始汉制,《汉书·何并传》“使奴剥寺门鼓”颜师古注:“植木而旁悬鼓焉。县有此鼓者,所以召集号令。”唐刘禹锡《龙阳县歌》:“县门白日无尘土,百姓县前挽鱼罟……沙平草绿见吏稀,寂历斜阳照悬鼓。”(《刘禹锡集》卷二十七)说明唐延汉制,于政府衙门之前仍置悬鼓,用以召集号令。
引诗中的“卢鹊”,也是延用的汉代典故。敦煌残卷法藏部分,伯二五三七《略出籯金》县令子男之篇第二十四“庭鹊喧”条引汉诗:“卢鹊何喧喧,有吏来在门。披衣出户看,吏言欲得钱。”伯二五二四《类书残卷》刺史门“卢鹊”条引此诗作:“卢鹊何喧喧,有史来到门。问史何所以,已言欲得钱。”文字小异,而其内容皆在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中有更加翔实的扩展和印证:“孝桓帝时,河南李盛仲和为巴郡守,贪财重赋,国人刺之曰:‘狗吠何喧喧,有吏来在门。披衣出门应,府记欲得钱。语穷乞请期,吏怒反见尤。旋步顾家中,家中无可为。思往从邻贷,邻人已言匮。钱钱何难得,令我独憔悴。’”常璩不仅更详细完整地记录了诗的内容,还记载了诗的创作背景——东汉恒帝时国人为讽刺当时贪财重赋的巴郡太守李盛(字仲和)所作。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常璩的晋代引诗,已经将敦煌残卷所存汉诗中的“卢鹊”,替换为更加通俗的“狗吠”,这就证实了在与太守和胥吏相关的语境中,“卢鹊喧”应当理解为犬吠而非鸟鸣。《汉大》“卢鹊”条义项②释为“鸟名”,误。李绅诗“莫令太守驰朱轓,悬鼓一鸣卢鹊喧。恶声主吏噪尔门,唧唧力力烹鸡豚”,实为上所引敦煌残卷汉代佚诗的唐代翻写,意为如果贪婪的刺史接替者乘车奔驰而来,敲响衙前悬鼓发布催租政令,乡下就将闹得乌烟瘴气、鸡飞狗叫。奸吏重新上门讨要租钱,乡里儿哀声叹气地宰猪杀鸡款待。因此似可断言,李绅《闻里谣效古歌》诗中之“卢鹊”的意义并非“鸟名”,与汉诗一样,指的就是狗。它用在这里一语双关,既实指乡人用以看门护院的家犬,因恶吏到来而狂吠;亦指狺狺喧哗的讨钱恶吏,在乡人眼中,他们正是贪腐太守派来的凶残走狗。
“卢鹊”狗的意义,来自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名狗韩卢和宋鹊。《战国策·齐策三》:“韩卢者,天下之疾犬也。东郭逡者,海内之狡兔也。韩卢逐东郭逡,环山者三,腾山者五。”《礼记·少仪》“乃问犬名”汉郑玄注:“谓若韩卢宋鹊之属。”三国魏曹植《鼙鼓歌·孟冬》描写冬猎场面:“趯趯狡兔,扬白跳翰。猎以青骹,掩以修竿。韩卢宋鹊,呈才骋足。”晋张华《博物志》卷六:“韩国有黑犬名卢,宋有骏犬曰䧿(笔者按:“䧿”,“鹊”之异体字)。”说明韩卢、宋鹊本为春秋战国时名犬,“卢”“鹊”为犬名,“韩”“宋”为其所产国,而“韩卢、宋鹊”经省略之后,以“卢鹊”代称良犬,亦常见于文献,《汉大》“卢鹊”条义项①即已列举《抱朴子·释滞》:“繁弱既韬,卢鹊将烹。”又《抱朴子·广譬》:“高鸟聚则良弓发,狡兔多则卢鹊走。”除此两例之外,我们还可以再增补两例,宋苏籀《知人》:“绁刍狗而求卢鹊之功,架鸡鹜而责鹰扬之效。”(曾枣庄 2006)清凌廷堪《任运说》:“狡兔之避卢鹊也,恃其捷也。”(《校礼堂文集》卷十七)说明自晋代开始,直到清代,学者们都一直认可韩卢宋鹊作为良犬的意义,并且在省略之后将“卢鹊”作为良犬代称在语文实践中自如运用。由于李绅诗中“卢鹊”之义亦为吠犬,与义项①基本相同,《汉大》“卢鹊”条原义项②的错误释义就失去了孤证支撑,其原释义和义项也就都应予取消。
二
《汉大》“卢鹊”条的纠错部分上文已述畢,而与之相关的修订工作却并未完成。这首先是因为宋代晁补之文章《医言》中的另一条书证:
以国观身,理自此知。不有圣人,人谁则医……卢鹊 秦和,王佐可蹈,鹊犹伊训,和比虺诰。(曾枣庄 2006)
按,《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扁鹊者,勃海郡郑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张守节正义引《黄帝八十一难序》注曰:“秦越人与轩辕时扁鹊相类,仍号之为扁鹊。又家于卢国,因命之曰卢医也。”说明为了与黄帝时同名的扁鹊相区别,以“家于卢国”为依据,名战国时的扁鹊曰“卢医”。又《汉书·艺文志》“中世有扁鹊、秦和”颜师古注:“和,秦医名也。”是卢鹊即扁鹊,与“秦和”一样,皆为古代名医,又皆因其所在之国“卢”“秦”而得名“卢鹊”与“秦和”。由于晁补之文例的存在,“卢鹊”于是又有了一个“扁鹊”的意义;而《汉大》“卢鹊”条也应该在补充晁补之例的同时,重新再补一个义项②:“春秋时名医扁鹊的别称”。
修订工作还须继续的另一个原因,是需要增补以下“卢鹊喧”条及其副条:
卢鹊喧汉桓帝时期,巴郡太守李盛贪财,重赋税搜刮人民,国人作讽刺他的诗曰:“卢鹊何喧喧,有吏来在门。披衣出户看,吏言欲得钱。”见敦煌类书残卷刺史门“卢鹊”条引汉无名氏《刺巴郡郡守诗》,又敦煌残卷《略出籯金·县令子男篇二十四》“庭鹊喧”条。“卢鹊何喧喧”,晋 常璩《华阳国志·巴志》引作“狗吠何喧喧”。是“卢鹊喧”本谓狗吠。后用为贪官恶吏重赋扰民的典实。唐 李绅《闻里谣效古歌》:“莫令太守驰朱轓,悬鼓一鸣卢鹊喧。恶声主吏噪尔门,唧唧力力烹鸡䐁。”唐霍孝恭《霍处士墓志》“褰帷广视,百城息卢鹊之喧。露冕遐临,十部绝豺狼之暴。”唐 皇甫冉《答张刘方平兼呈贺兰广》诗:“复有故人在,宁闻卢鹊喧。”亦作“卢鹊吠”。敦煌残卷唐 李峤《杂咏》诗注引无名氏《钱》诗:“不闻卢鹊吠,贪吏绝来求。”
卢鹊吠见“卢鹊喧”。
之所以需要增补以上“卢鹊喧”词条及其副条,首先是因为大型历时性语文词典对名物性词条和典故性词条的分工。如果说“卢鹊”条释义“古代良犬韩卢、宋鹊的并称,亦泛指良犬”具有名物词释义的性质;那么“卢鹊喧”“本谓狗吠,后用为贪官恶吏重赋扰民的典实”则为典型的典故词条释义。名物词条与典故词条需要分立分释。
增补“卢鹊喧”词条的一个次要原因,则是进一步坐实上节对“卢鹊”释义“鸟名”为误释的判断。“卢鹊喧”条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因为唐代文献中存在不少将“卢鹊喧”作为典故使用的实例。例如以上引例中,霍孝恭的《霍处士墓志》就述其曾祖为官清静,故民间无如豺如狼的凶暴之吏。皇甫冉的诗则恭维同为官员的老友贺兰广等造福一方,能约束奸吏,百姓免于侵扰。[1]李绅诗例从原“卢鹊”条移入新建的“卢鹊喧”词条,其内容含意上文已经细析,亦谓刺史贪婪,派恶吏骚扰地方百姓,兹不赘述。而李峤诗注所引《钱》诗(徐俊 2000)364-365则更直接地将卢鹊狂吠与贪吏上门讨钱挂钩。所有这些唐代用例,全都源自汉代无名氏那一首《刺巴郡郡守诗》,这就进一步说明在唐人心目中,“卢鹊”为犬名而非鸟名,而“卢鹊喧”为贪官恶吏重赋扰民的典故。从这个意义上说,增补有时或有助于纠错。
须特别指出的是,增补条所列使用这一典故的全都为唐代诗文而无后代用例,让人推测在唐代之后,出于某些原因,人们忽然集体丧失了对在唐代曾经十分流行的这一典故的正确理解,不再使用这一典故,这或许也是导致《汉大》原编纂者误解误释的原因。这一点新建词条的释文中并未加以说明,仅以止于唐朝的引例让词典的研究者和读者感知。而通过更深入地研究其停止使用的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原因,或许能为揭示语言中存在的此类曾经活跃却在历史的某一时刻忽然消失的许多“断流典故”的来龙去脉提供帮助。
增补“卢鹊喧”词条,佐证“卢鹊”条的纠错,拂去岁月的积尘,让历史上曾经流行且具有正能量的典故重新熠熠闪光,被今人理解,亦应是今天《汉大》修订者的责任。
附 注
[1] 贺兰广,唐玄、肃、代宗时人。从皇甫冉《答张、刘方平兼呈贺兰广》诗中“屡枉琼瑶赠,如今道术存”之句看,其时贺兰广与皇甫冉文字赠答颇多。贺兰广有《对屯田佃百姓荒地判》存世,其判文针对当时诸畿县屯田官霸占逃民荒地拒不归还业主的行为加以否定,要求归还土地,以维系战乱后归来的流民。是其约束官吏,维护百姓利益之实例。其文曰:“人散久矣,地广大荒。开都护之屯田,辟天子之县内。且耕且战,岁取十千以饷农;足食足兵,武有七德以威敌。殊管氏之见夺,异周制之不颁。且运属中兴,人多复业。惟桑与梓,诗人兴敬止之辞;安土重迁,县司敦仁人之礼。请从地著之业,无俾流萍之叹。”见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四百八·贺兰广·对屯田佃百姓荒地判》:“诸畿县置屯田,佃百姓荒地,主令复业,请自耕种,屯司不与,县司执申,若不还地,人即却逃。”(中华书局,1983年11月,第1版,第4181页)。
参考文献
1. 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编纂处编.汉语大词典.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1994.
2. 徐俊纂辑.敦煌诗集残卷辑考(第1版).北京:中华书局,2000.
3.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版).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武汉 430062)
(责任编辑 马 沙)
37615005892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