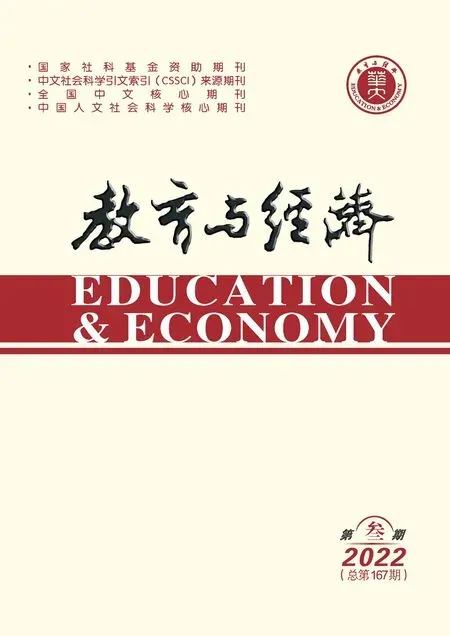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及其公共教育政策的呈现
李永春, 刘天子
(1.东北石油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 黑龙江 大庆 163318; 2.首都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学院, 北京 100048)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对劳动者知识与技能的要求越来越高,而劳动者知识与技能的形成又不得不回归到讨论人力资本理论的内涵以及对教育的着重关照上来。纵观历史,不难发现人力资本理论从建立之初就独树一帜,可以说它率先摆脱了经济增长的“唯物论”,开始更多地关注到“人”。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通过对自己的投资不仅使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上更具竞争力,而且还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宏观经济的增长。随着时代的变迁,人力资本理论的内涵也在不断扩展与演变,这使其更具有解释力。但不论人力资本理论内涵如何演变,理论转化为现实教育政策,自始至终都与教育部门有着密切联系。于是一国的教育政策俨然就成了提升本国人力资本的纽带,其重要程度不言自明。本文意在通过梳理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脉络和伴随人力资本理论发展而带来的国家层面公共教育政策的演变,来探索理论的动态演进与政策的互动变迁之间的关系。
一、人力资本理论的雏形期
人力资本理论的诞生虽然是在几十年前,但人力资本的思想却源远流长。早在公元前,柏拉图(Plato)就曾在《智术之师》一书中指出数学、几何学等文化知识对于生产工艺及国家管理的重要性[1];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也曾多次提到知识与技能在生产活动与决定个人社会地位中的重要作用[2]。我国先秦时期的思想家们也非常重视关于人的培养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孔子对知识分子的价值实现曾经说过“学而优则仕”,管子也说“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早期的这些哲学家虽然认识到某些专有知识对生产的巨大作用,但由于在漫长的前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形成庞大的劳动力市场,同时也没有出现国家层面的教育体制为这些专有知识的产生提供平台,所以,虽偶有人力资本思想的显露,但还并不足以称之为人力资本理论的雏形,直到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Adam Smith)于1776年出版巨著《国富论》开始,人力资本理论的雏形才开始显现。
(一)古典经济学时期的人力资本思想
早在亚当·斯密之前,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就在其《政治算术》一书提出了劳动是财富之父、复杂劳动比简单劳动能够创造更多价值,对人口货币价值进行计算以及提高人口素质,培养技艺高超的人等观点;法国重农学派代表人物弗朗斯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认识到“构成国家强大的因素是人……人本身就成为自己财富的第一个创造性因素”[3],如果国家政策失当,社会将休想从他们及其子女身上获益;而作为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则在《国富论》中首次较为系统地赋予了人力资本以内涵,他说:“社会居民或成员习得的、有用的能力,这些才干的获得,需要获得者在教育、学习或学徒期间支付生活费用,因此通常存在一个实际花费,而这笔花费是一个固定的、已实现的资本,如同储存在他自己身上”,“学习一种才能,须受教育,须进学校,须做学徒,所费不少……但这笔费用,可以得到偿还,并赚取利润”。[4]可见,亚当·斯密把人“习得的、有用的能力与才干”看作人力资本的内涵。这些能力与才干的形成被看作是一个投资过程,而这种投资是需要教育与培训的,而教育与培训是有成本的。他的这些思想对后来人力资本理论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我们认为亚当·斯密奠定了人力资本理论的雏形;同时,亚当·斯密明确指出人的才能的养成与获得是需要通过在相关部门学习而获得的,劳动者素质低下对经济发展会起到明显的阻碍作用。他还认为国家对于国民的教育应引起足够重视,这不仅将使国民受益,“国家也可受益不浅”,接受教育的国民不仅更懂礼节、更守秩序,而且还能免于狂热与迷信的蛊惑,使国家的政治与经济得到稳定的运转。在古代的中国,很多思想家都非常重视通过教育提升受教育者的价值。《礼记·学记》上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学习才能提升自己,从而实现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二)相应的公共教育政策
亚当·斯密时代正处在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初期,原有的生产方式和狭小的地方市场已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资本积累和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为公共教育政策的发展提供了可能。不过市场上的劳动者多为廉价的低端劳动力,以手工与纺织业为主。此时各国还没有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公共教育体制以对其国民提供有针对性的正规教育,所以也就没有国家层面上相应教育政策的统一呈现。此时的学校多以“学在教堂”或“贵族学校”为主,教堂学校虽也讲授其他知识,但宗教目标仍是首要任务。贵族学校的首要任务则是培养“精英”与“绅士”,以便随时接手整个国家,普通民众则很难进入。当时普通民众对个体人力资本进行投资的合理选择便是“学徒制”。正如埃泼斯坦(Epstein)所说:“人类获得技术知识的第一阶段是以长期的、正规或非正规的约束为基础的学徒学习为主的,这是人类社会创立的家庭之外的传输技术知识的最普遍的安排。”[5]亚当·斯密也认为“学徒就是仆人在被授予这一行业的技艺的条件下,必须在一定年限内,为主子的利益而工作的制度安排。”[6]如果用后来形成的人力资本理论来阐明的话,“学徒制”可以看做是一种交易,即学习者(徒弟)通过在一定期限内为施教者(师父)的利益努力工作,来换取被授予行业技艺的机会。而“学徒制”是“行会制”的雏形,徒弟跟随师傅学习技艺是需要缴纳费用的,正如加入行会也需要缴纳一定费用才许入行一样,而“行会制”又被现代一些学者认为是西方大学制度的雏形。可见,在亚当·斯密时代,民众已经意识到对个体人力资本进行投资非常有必要,但囿于公共教育体制不够完善,更多的人是以“学徒制”来自发地进行个体人力资本投资,于是向师父缴纳的费用以及一定时期内为师父免费工作就是投入成本,而未来自己学会某门技艺能够挑摊立户独立谋生则是预期收益,这正符合亚当·斯密本人对人力资本内涵的界定。
在中国,孔子之前,教育也曾经被贵族垄断。孔子开设私学,实施有教无类的招生策略。自此,平民也开始享有了受教育的权利。尽管如此,由于当时条件限制,实际上还是“精英”教育。孔子非常重视通过教育提升个人素质,提升个人能力,进而实现社会价值。他认为一个人必须通过教育来修身,然后才能具备安人、安天下、安百姓的能力。孔子认为教育能给个人带来经济价值。他说:“学也,禄在其中矣。”荀子也肯定教育在“功力”“聚财”“和群”“安势”等方面的功能,他说:“百姓之力,待之而后功;百姓之群,待之而后和;百姓之财,待之而后聚;百姓之势,待之而后安;百姓之寿,待之而后长。”西汉时期,汉武帝非常重视儒学,在朝廷上设立五经博士学官,到东汉时期又开设了太学,到了隋唐时期又开科举取士。以上教育政策都是意在通过教育培养具有社会价值的人,以服务于政治统治。唐代颜之推曾明确表示教育不但可以“多知”“明达”“为己”还可以“利世”。
二、人力资本理论的诞生期
自亚当·斯密之后,又有不少经济学家在其著作中发表了包含人力资本思想的论述。庸俗经济学代表人物萨伊(Say)认为劳动是后天取得的一种能力,需要由每年用以教养他的款项累积而形成;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List)提出了精神资本的概念,他说“(精神资本)是个人所固有的或个人从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得来的精神力量和体力”[7],这对现代意义的人力资本概念的确定具有很大启发性;新古典学派在关于把人看作资本方面也有讨论,代表人物马歇尔(Marshall)曾说:“以一种抽象的和数学的观点来看,人是资本;但在实际分析中把他们当作资本与市场的实际情况是不相符的”[8],可见他已经认识到人的知识与才能的资本属性,但在实际分析中又不愿把人视为资本;同为新古典学派的瓦尔拉斯(Walras)则是较早使用人力资本概念的经济学家,但他认为人力资本与土地一样是自然资本,而不是人工所产生的,并把人力资本等同于人本身,在数量上等于人口的数目,这显然有失恰当。总之,各家学派的经济学家对人力资本的内涵都进行了不同层面的探讨,他们对人力资本理论的产生都起到了推动作用,但对之前亚当·斯密所述人力资本的“习得的、有用的能力与才干”的内涵却没能持续跟进。直到20世纪60年代,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索罗(Solow)在对美国经济增长的研究中,发现了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索罗残差”。“索罗残差”也称“现代经济增长之谜”,即美国的产出增长率远远超出了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率,各经济学家纷纷对此问题进行回应,舒尔茨勇敢而且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并给出了“索罗残差”的解释,认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国民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加之同时代贝克尔(Becker)和明瑟(Mincer)等人对人力资本的开创性工作,致使人力资本理论正式诞生。[9]
(一)人力资本理论的产生
1960年12月28日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T.w.Shultz)在第73届美国经济学年会上发表了题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讲,这标志着人力资本理论的产生。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是指“凝结在劳动者身上的,后天习得的,具有经济价值的体力、知识、健康、技能和能力”。他运用自己建立的人力资本理论对“索罗残差”做出解释,计算出美国1929—1957年间经济增长中有33%的增长,应该归功于教育,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手段。之所以说舒尔茨勇敢,是因为之前主流经济学家们认为教育是一种吸收高雅文化、传递普世价值的东西,把教育当成创造资本、获取经济收益的手段是不道德的,而舒尔茨认为教育具有文化与经济上的双重意义,教育不仅能发展文化,更能提高人的各方面能力,增加未来的收入。舒尔茨认为既然人力资本是把人作为资本来进行投资的,那么凡是提高劳动者质量的投资都算人力资本投资,他把人力资本投资分为五大类:学校教育、在职培训、成人学习、医疗保健、就业迁移。[10]
人力资本理论自产生后便沿着两条路径推进:一条路径便是舒尔茨人力资本的宏观研究路径,该路径主要解决宏观经济增长之谜等宏观问题;另一条路径则是以贝克尔(Becker)为代表的人力资本的微观研究路径,即用经济学方法对个人及家庭的行为进行分析。他把教育、婚姻、生育、健康、迁移等都纳入“成本-收益”的分析框架,从而解释人类行为选择的内在规律。这两种研究路径的逻辑基础是一样的,即都认为人力资本投资可以提高一个人的生产能力或配置能力。但在结果上存有一定差异,这种差异表现在是提升了个人的个体收入,还是推动了一国整体经济的增长。生产能力偶尔也被称为劳动生产率,英国经济学家韦尔奇(F.Welch)发现,接受教育不仅能提升一个人的生产能力,还能提升其配置能力,舒尔茨则把人的配置能力概括为“处理不均衡状态的能力”,这些都包含在个体的人力资本当中,而接受教育则被认为是人力资本投资的最重要手段。自此,一国的教育水平被提升到空前的高度加以重视。
(二)相应的公共教育政策
人力资本理论产生之后,各国纷纷认识到教育对一个国家长远发展的巨大作用。同时自19世纪以来,各国基本上都建立起了以政府干预为主的非完全市场化的教育体制,就连最崇尚自由放任、市场行为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英美国家,亦不例外。所以教育作为人力资本形成的主要渠道,尤其是一国的公立教育,若没有有效的教育政策作保障,那么这个渠道就不可能畅通,甚至会被堵塞。一旦这个渠道被堵塞,一国国民的人力资本存量将长期不足。这将导致整个国家经济的停滞甚至综合国力的落后。于是各国根据本国国情相继出台了各种相应的教育政策,教育政策作为提升一国人力资本的着力点已经成为“天下共识”。
该时期,发达国家普遍实行了通过加大教育投入来改善教育质量的教育政策。比如美国在这段时期先后颁布了《国防教育法》《中小学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卫生专业教育资助法》等法规。与此同时,美国等发达国家开始鼓励学生接受高等教育,资助优秀贫困学生,加强数学、自然科学、外语和职业培训的教学。随之而来的是美国经济的全面增长以及个体收入的快速增加,而美国也在这个时期,彻底超越苏联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日本在当时也发表了白皮书——《日本的成长与教育——教育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日本也是通过加大教育投资来积累人力资本,这使二战失败后的日本迅速崛起;教育对于发展中国家更为重要,舒尔茨在《穷国经济学》中说道:“改进穷国的福利之关键因素不是空间、能源和耕地,而是教育、健康和培训。”但发展中国家由于资源受限,所以着重实行了普及初等教育,降低文盲率的教育政策。世界银行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资金不再一味投向基础设施建设,而是更多地转向了各国的教育部门。1974 年世界银行曾发布《教育部门工作报告》,报告里明确指出用于援助的资金“应该首先投资能够促进经济生产的教育项目,或是为经济发展提供所需要的各类人才”。[11]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争取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农村普及小学五年教育,有条件的地区普及七年教育;1974年,中国又提出大力普及农村小学五年教育、农村有条件的地区普及七年教育、逐步在大中城市普及十年教育。
总之,20世纪60至70年代中期以前,世界上许多国家把人力资本理论作为教育改革与教育政策制定的重要理论基础,把一国的经济增长寄希望于教育。也就在那个时期,无论全球的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都是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
三、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期
随着人力资本理论的诞生,人们长期以来对经济增长、工资结构变化和个人收入变化等方面的疑惑,由于人力资本概念的引入而变得迎刃而解,教育的经济价值被人们空前重视,提供教育的学校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投资。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变得缓慢,美国经济甚至出现滞涨,对教育的大力投资并未获得如期而至的经济大发展,甚至在一些发达国家出现了“过度教育”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批评人力资本理论的理论流派应运而生,其中以斯宾塞(Spence)的筛选理论、多林格(Doeringer)和皮奥里(Piore)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鲍尔斯(Bowels)和金蒂斯(Gintis)的社会化理论最有影响,甚至筛选理论大有与人力资本理论分庭抗礼之势,筛选理论作为信息经济学中的重要理论,[12]认为教育的主要作用不是提高人的生产能力,而是把不同能力的人区分出来,供雇主选择,以消解员工能力的信息不对称。同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计算机为代表的互联网信息技术开始在市场上广泛应用,熊彼特(Schumpeter)的创新理论再次被人所重视,技术创新也开始越来越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引擎,经济学家开始重新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理论。以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 Romer)和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也称内生增长理论。该理论以技术内生化为特征,把人力资本纳入经济增长的模型之中,从经济增长模型中阐发人力资本理论,显示出与人力资本理论诞生期以劳动力要素分析为中心所不同的研究思路,较好地解释了知识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13]
(一)技术内生的人力资本理论
1986年,斯坦福大学教授罗默(Paul Romer)发表了《收益递增与经济增长》一文。他把知识作为独立变量纳入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同时将知识区分为一般知识和专业知识,把人力资本区分为原始性人力资本和专业性人力资本。[14]专业性的人力资本会产生专业知识,各国经济增长的不同在于知识和人力资本导致的技术进步不同;1988年,芝加哥大学教授卢卡斯(Robert Lucas)发表了《论经济发展的机制》,他把人力资本理论和技术决定论的增长模型结合起来并加以发展,形成了人力资本溢出模型。他将人力资本直接引入经济增长分析,假定在全球经济范围内存在人力资本的外部性,认为该外部性是由人力资本的溢出造成的,这种外部性的大小可由全社会平均的人力资本水平来衡量[15];1990年,罗默(Paul Romer)又建立了一个包括最终产品、中间产品和研究与开发三部门在内的增长模型,克服了他本人(1986年) 和卢卡斯(1988年)模型中没有微观基础的缺陷——即后两者把技术进步视为总生产函数的一个变量,对技术进步投资的溢出效应被追加到其他所有企业的投入要素上。
在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浪潮中,人力资本理论被纳入增长模型,成为技术产生与技术创新的决定因素。[16]同时由于人力资本能够通过技术创新这一中间变量而最终影响经济增长,于是人们开始强调特殊知识与技术创造所需的“专业化人力资本”。这使得人力资本的研究更深入、更具体、更数量化了,不仅极大发展了人力资本理论,而且使各国重新认识到教育与培训的重要作用,同时开始特别重视科技创新以及专有人才的培养上。
(二)相应的公共教育政策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人力资本理论面临来自理论与现实的双重挑战,一些发达国家的政府对教育投资的热情开始下降,教育支出开始减少,政府开始更多关注现有教育投入基础、教育体系本身利用教育资源的效率以及教育质量提升等问题。美国政府基于对当时公立学校教育效率过低、教学质量不高的判断,于1983年颁发了《国家在危机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政策性报告,进一步引导教育改革,提升教学质量。并于1991年发布了《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开始赋予学生与家长更多的学校选择权利,如开放入学、设立特许学校、引入教育券等政策,鼓励学校竞争,提高教育效率。
新经济增长理论产生后,技术作为内生因素直接影响着国家经济产出,而人力资本作为技术创新之源再次凸显出其重要作用,而专业化人力资本较强的科技创新人才则被各国格外重视,他们往往主导了技术创新,其结果是技术外溢使得整个经济增长,人民收入水平提高,正如舒尔茨在1993年《人力资本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价值》一文中再次重申的“提高人民收入和国家财富的决定性因素是人力资本,而绝不是空间、能源或其他物质资本”[17],此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对高科技人才的重视程度史无前例。仍以美国为例,美国于1994年签署了《美国教育改革法》,该法案意在引导中小学教育除了强调基础知识,要更多关注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系统解决问题的技巧;2001年“9·11”事件以后,布什政府把高等教育改革培养高技能人才作为整个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增强美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转年布什就签署了《不让一个儿童落后法案》,主抓基础教育改革,同时于2006年出台高等教育的配套改革计划《美国高等教育行动计划》。[18]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自从1978年确定了国家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发展路线起,便实施教育改革,从教育现代化任务的提出到恢复高考选拔制度,从重点校制度的恢复到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从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到高等院校的扩招,从学硕为主到大力发展专硕,中国教育部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教育政策,希望通过教育政策的实施进一步把简单的、潜在的“人力”转化为高端的、现实的“生产力”。中国的教育政策确实做到了这一点。自改革开放以来,就高等教育而言,为中国培养了9900多万名高素质专门人才。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所取得的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政府因时制宜的教育政策。通过实施惠及亿人的育人工程,从根本上提高了人们的素质,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从而实现了由“人力”到“生产力”的转化。
总之,在人力资本理论发展期内,教育作为提高人力资本的着力点再次被赋予了极为神圣的使命。不过,由于不同国家之间国情的不同,这个阶段内其教育政策也略存差异,有些国家集中力量发展高等教育,希望重点培养一批高科技人才;有些国家则从基础教育阶段入手,从小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不过,两者都认识到培养专有性或异质性人力资本的重要性。
四、人力资本理论的突破期——新人力资本理论的崛起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社会对劳动者个体人力资本,尤其是对不可替代的专有性人力资本的要求越来越高。同样是在学校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个体,其能力却表现出了极大的异质性,于是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之前建立起来的人力资本理论。首先,传统人力资本理论强调教育对一个人能力与技能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又把人接受的教育进行同质化处理,并把人力资本简化为受教育年限。而现实情形中却是即使是接受相同教育的个体,其能力也会表现出极大的不同。不同个体的先天禀赋所带来的后天市场化收益差距,越来越悬殊,于是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人与人之间先天能力的差别;其次,传统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能够提高个体的能力,进而影响到该个体的收入。但传统人力资本理论所提到的个人能力仅仅被局限在认知能力范围内,而现实社会中,随着现代服务业逐渐替代传统大工业,与人打交道的工作越来越多。而与人打交道所需要的“乐观”“情感”“自律”“意志力”和“真诚”等非认知能力,对一个人收入的影响也变得越发重要;再次,传统人力资本理论把一个人技能的形成多归功于学校教育,从而忽略了学前抚育与职后培训。但努森(Knudsen)等人经过研究发现,人的技能形成像动物一样是存在生命周期的,有些技能在某一阶段比其他阶段更易形成,有些技能则只能在某一特定阶段形成。[19]对人的技能形成的投资也应该考虑到阶段性的差别,如一个人的认知能力(IQ)在10岁左右就基本上稳定不变了,但非认知能力的持续可塑性则较强;最后,传统人力资本理论把先天能力与后天习得二分处理。库尼亚(Cunha)、赫克曼(Heckman)和斯肯纳克(Schennach)几乎同时发现了先天禀赋与后天环境因素之间有着重要联系。这种联系可以表述为基因的表达需要合适的环境作为土壤,后天习得则受先天禀赋的制约,二者交互发生作用。后天环境又是可以通过投资创造的,后天观察到的表现已经是先天和后天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表明传统的人力资本的研究方法已显得有些不大适用。[20]
(一)基于能力的新人力资本理论
基于上述原因,传统人力资本理论内涵亟须扩展。2010年美国经济学年会专门以人力资本新进展作为其中一个小组议题进行了学者讨论。其中,汉纳谢克(Hanushek)明确提出为了更好地了解个体在经济社会中的表现,我们需要制定一个基于能力的新人力资本的研究议程。议程中所提到的新人力资本理论与传统人力资本理论相比,仿佛打开了能力的“黑箱”。他构建了一个多维能力、生命周期的人力资本理论框架。人力资本的内涵不仅包括认知能力,还包括非认知能力。能力的形成因素不仅包括正规教育因素,也包括先天禀赋与环境作用、学前抚育与学后培训。新人力资本理论框架存在着两条互为补充的研究主线:一条是探讨能力(1)“能力”在此也可作“技能”,由于先天禀赋与后天习得存在交互发生作用,所以现有经济学研究中已经不再做严格区分。形成与开发的机制。另一条是研究个人能力对个人最终经济社会行为产出的影响。[21]两条主线可以分解为四个板块:一是认知能力的形成机制,二是非认知能力的形成机制,三是认知能力的社会经济回报,四是非认知能力的社会经济回报。[22]这四个板块基本上囊括了新人力资本理论所有研究的问题。由于非认知能力的引入,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与人格心理学家开始跨学科合作。在学界,随着“大五人格”量表对非认知能力测量上取得的一致共识,非认知能力的研究也取得了一系列进展。赫克曼和洛克纳(Lochner)发现,总体来讲非认知能力比认知能力更容易形成,且可以形成的生命周期更长。同时非认知能力与认知能力对于社会经济回报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对于女性而言,其非认知能力对于社会经济回报甚至起到更重要的作用。[23]与此同时,库尼亚和赫克曼发现技能存在自我生产效应,即一种技能的形成可以增加下一时期获取技能的能力。这不仅意味着上一期所得技能产出可以持续到下一期,也体现了技能的自我增强和技能与技能之间的互相促进效应。[24]一个阶段非认知技能的形成也有助于提高下个阶段认知技能的形成,例如孩子早期集中注意力的能力培养会影响他们青年时期的学习测验成绩。而邓肯(Duncan)等人发现大学入学率只在极小程度上取决于入大学时期的家庭收入情况,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孩子成长早期的家庭收入情况,家庭早期的预算情况对于孩子成年后的能力和学业表现,具有持续效应。[25]这与早期人力资本学者贝克尔的发现并不相同。他们给出的解释是:由于家庭早期的资金约束导致孩子早期投资上的不足,直接导致了孩子早期能力(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的缺失。由于能力的自我生产效应,这种能力的缺失,持续作用到未来孩子是否能够读大学。[26]
基于新人力资本理论对于技能形成的内在规律的发现,可以看到,不论是单个家庭还是公共教育体制,都应该尽可能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对弱势儿童进行早期实验性干预和长期跟踪研究发现,单个家庭如果能够提高孩童时期的父母时间投入,以及家庭的资源水平,就可以显著地提高孩童成年后的经济社会生活表现,同时也会给公共教育投资提供了借鉴。[27]对弱势家庭子女的经济援助更应该提前,避免其早期的人力资本投资的不足。后期的人力资本投资对个体认知能力的提升非常有限,由于非认知能力的长期可塑性,后期的人力资本投资应多关注非认知能力。[28]
(二)相应的公共教育政策
新人力资本理论产生时间还不长,学者们仍在不断丰富和完善这一理论。基于“能力”这一黑箱已经被人们打开,我们有理由相信,促使能力形成的各种教育投资将会更加具有针对性,而且针对能力形成的公共教育政策将会更加完善。同时,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世界各国教育部门非常重视在中小学开展人工智能教育,注重培养青少年交叉融合和跨界思考的能力。2013年美国就曾制定《联邦STEM教育五年战略规划》,2016年日本则发布《日本再兴战略2016》,该《战略》提出中小学必修课要包括人工智能等相关课程。2017年我国国务院印发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该《规划》提出“(要)在中小学阶段设置人工智能相关课程,逐步推广编程教育”[29]。自此之后,人工智能教育在我国中小学逐渐铺开。根据现有研究结果,我们不妨为我国公共教育政策提供一些建议:一是政府的教育调节政策应该基于个体能力形成的内在规律,着重关照弱势群体,对弱势家庭的教育干预适当提前,如学前教育以及家庭抚育支持等。这样有助于弥补孩童由于家庭资源不足而造成的早期能力缺失,为他们储备能够进行自我生产的早期能力存量;二是鉴于非认知能力对个体在未来经济社会方面的巨大作用,对人力资本的后期投资应以非认知能力为主[30],如可在大学阶段开展针对性较强的社团及社会实践活动、开展职业培训等,在社会上广泛宣传职业素养与职场道德等;三是教育评价方式不要再追求一维的认知能力,如考试成绩与升学率,非认知能力也应纳入我们的评价体系之中,从而建立起更为多元、更加全面、更加公平的教育评价机制。
五、结论
人力资本理论作为教育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在解决一个又一个社会问题的过程中,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与此同时,人力资本理论的出现,也影响到了一国公共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通过梳理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史,可以清晰地发现其内在运行存在着这样的逻辑:即“时代需要→理论先行→政策跟进”,这其中理论的发展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具有根本性的指导作用。事实上,每个政策的出台,其背后都有理论思想支撑,正如伟大的经济学家凯恩斯(Keynes)在《通论》结尾所言:“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干家自认为不受任何理论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学者之奴隶。”[31]未来,我们应该站在前人肩膀上,继续丰富人力资本理论,追问其理论思想,扩展其理论内涵,以便更好地解释伴随知识经济时代到来所产生的各种生存疑问,为政策的制定提供强有力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