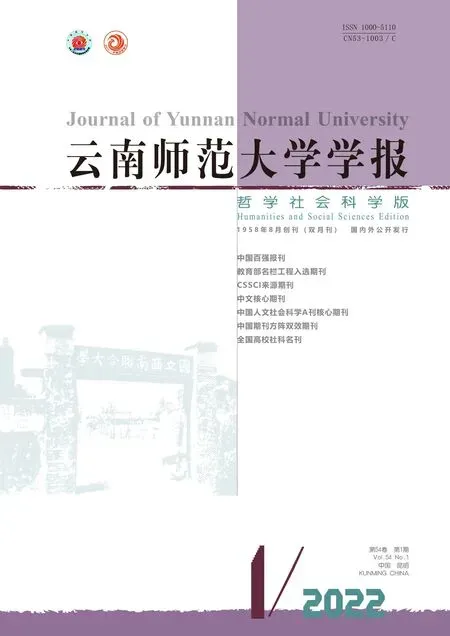旅游者隐喻:西方旅游人类学的认识论困境及其反思*
赵红梅
(云南师范大学 地理学部,云南 昆明 650500)
一、引 言
西方人类学史上曾出现过一股微弱的研究旨趣——对旅游者隐喻的讨论,即批判性地看待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行为,并对田野作业的主观性提出质疑。该旨趣受到文本主义的直接滋养,并衍生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即:民族志者与旅游者之间在哪些方面存在相似性或相异性?克里克·马尔科姆指出,对人类学家与旅游者之间相似性的拷问严重威胁到人类学家的自我认同。然而,人类学家与旅游者的角色重叠不单给人类学家带来肤浅的身份认同困扰,更对民族志文本的科学性、专业性和权威性形成挑战。这一滥觞于“文化科学”反思运动的人类学原生烦恼,在旅游人类学家那里变成复杂的多重烦恼,比如:旅游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行为与某些旅游者的旅游行为有何区别?旅游人类学家如何应对复杂的研究对象?旅游民族志是旅行游记吗?这些问题反映了西方旅游人类学对旅游知识生产的集体反思,同时折射出西方主流人类学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对旅游人类学发展的桎梏效应。然而,国内学界在西方旅游人类学视野的引介与本土化过程中,忽视了其主流人类学与旅游人类学之间的关系背景,未能从真正意义上就该视野的实践性外推与文化上的可外推性(1)黄光国.社会科学的理路[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338~340.进行探讨,导致对西方旅游人类学的盲从与虚化。鉴于此,文章以文献研究法与参与观察法为基础,以旅游者隐喻为线索,一方面透过西方主流人类学的反思浪潮来反观旅游人类学的认识论困境,揭示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与社会事实之间永恒断裂的真相,另一方面为国内旅游人类学树立一面反思之镜,激起对中、西语境下旅游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再探讨。
二、人类学家,还是旅游者?
(一)田野现场的文化接触与情感回避
在人类学150多年的发展史上,他者一直是学科标识和人类学家身份认同的重要内容。不同的人类学理论赋予他者不同的角色:他者即我们(普世论)、他者即以前的我们(比较论)、他者非我(特殊论)。(2)威廉·亚当斯.人类学的哲学之根[M].黄剑波,李文建,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5.人类学家眼中理想的他者是“文化岛屿”,一种与世隔绝、同质、有清晰边界的小规模社会,以静止和稳定的状态等待人类学家的参与观察。这种简单的“我者-他者”二元关系堪称完美,作为我者的人类学家是他者的唯一诠释人,其知识权威的角色无与伦比,以至于他所付出的金钱、时间、精力与情绪代价倒不值一提。然而,完美的他者是人类学自己描摹的幻象,托马斯·埃里克森提醒人类学家,现代化的社会进程几乎已经“侵染”地球上所有孤立隔绝的地方,“文化岛屿”不再是一种社会类型,“岛屿”对于人类学家的象征性内涵已失去意义。(3)Thomas Hylland Eriksen.In Which Sense do Cultural Islands Exist?[J].Social Anthropology,1993,(1B).田野现场的文化接触变得越来越复杂多元,从20世纪初可能碰到的殖民官员、传教士、商人、旅行者、探险家等,到20世纪中期以来怀揣不同目的的移动者,以及无处不在的旅游者。
克利福德·格尔茨在1960年代就告诫说,绝大多数社会科学研究都会直接遭遇现代生活的细节,而且多少有些恼人。(4)Clifford Geertz.Thinking as a Moral Act:Ethnical Dimensions of Anthropological Fieldwork in the New States[J].The Antioch Review,1968,(2).对人类学家而言,最恼人的体验莫过于在田野现场碰到自己以外的陌生人,面对这些“非我族类”,人类学家表现出相当复杂的情绪。早期人类学家小心翼翼地与传教士、殖民官员和商人等人群保持距离,以免被混为一谈。人类学“教主”马凌诺夫斯基创建了“英雄主义”的田野工作传统,确立一手资料搜集的专业与非专业之别,赋予田野调查尊严,同时将出没在田野地点的其他人排除在外,他本人也身体力行,绝口不提特洛布里恩群岛上的白人商人。自20世纪40至5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旅游的空间扩展,西方新生代人类学家越来越多地在第三世界国家的田野现场撞见自己的同胞,这些披着旅游者外衣的西方闯入者前所未有地挑战了人类学家的自我认同。像早期人类学家回避殖民官员或白人商人一样回避旅游者,是新生代人类学家做出的第一反应。因此,纵使人们普遍认为旅游应是人类学轻车熟路的研究对象,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多数人类学家兀自撰写民族志,仿佛没有旅游这回事,旅游者也根本不存在。应当如何解释人类学家这种不可思议的“情感回避”?马尔科姆对此提供了一系列设问式回答:是不是旅游者大多来自人类学家自己的社会而无法将其界定为“他者”,所以只好忽视他们?人类学很难将玩耍、休闲和娱乐视为严肃的研究论题?人类学家普遍对旅游怀有文化偏见,仅仅是因为和田野调查相比旅游(旅行+观察)显得不够权威?(5)Malcolm Crick.The Anthropologist as Tourist:an Identity in Question[A].Marie-Francoise Lanfant,John B.Allcock and Edward M.Bruner.International Tourism:Identity and Change[C].London:SAGE Publications Ltd.1995:205~223.但克里克认为,关键原因还在于人类学家已经意识到自己与旅游者之间的亲缘性和相似性,这导致他们的集体焦虑,宁愿将旅游束之高阁。历史上人类学家曾被印第安人比作骗子、傻瓜、窥探狂和小气鬼,但都不如被看成旅游者这样令人不安和难以面对。那么,人类学家是某种形式的旅游者或旅游者是某种程度的人类学家吗?换言之,人类学家的旅游者隐喻在何种意义上是成立的呢?
(二)人类学家与旅游者的相似性
在一般意义上,人类学家与旅游者同属西方世界的转喻,都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产物和西方文化的特定代表。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人类学是欧洲帝国主义对全世界的一种“赎罪”方式,(6)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M].王志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48~486.人类学家这个物种对他者的“悲天悯人”立场则是对殖民暴行的弥补性逆转。丹尼森·纳什道出人类学家的历史心结,即旅游导致一种类殖民的文化接触,旅游者是休闲移民,是文化帝国主义的产物。(7)Dennison Nash.Tourism as a Form of Imperialism[A].Valene Smith.Host and Guests:The Anthropology of Tourism[C].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89:37~52.这样,人类学、旅游、殖民主义是同一个出身,产生于相似的社会结构,都是空间扩张的变种和权力的延伸。(8)Edward Bruner:Of Cannibals,Tourist and Ethnographers[J].Cultural Anthropology,1989,(4).迪安·麦坎内尔笔下的旅游者是现代人的西方代表,从现代性的疏离中出走,到他者那里寻找真实性,这种近似研究者的诉求使旅游者肩负社会学家或科学革命的职责。(9)Dean MacCannell.旅游者:休闲阶层新论[M].张晓萍,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6.在此意义上,旅游者就是研究者,旅游行为就是一种元调查,这正是哈罗德·加芬克尔所说的“每个人的行为都像社会学家”(10)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第十一版)[M].邱泽奇,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38.。撇开个人动机不谈,寻找文化真实性的旅游者与寻找文化差异性的理论家/人类学家有什么本质区别呢?从词源上看,希腊语中的“理论”一词与“景象”“奇观”同义,据此类推,作为理论家的人类学家和作为观光者的旅游者大致是一类人。(11)George van den Abbeely.Review:Sightseers:The Tourist as Theorist[J].Diacritics,1980,(4).
在文学和隐喻意义上,人类学家和旅游者都是“侵扰”异文化的陌生人,在离家旅行、短暂逗留、搜集信息与纪念品、回家后讲述旅行故事等行为特征上,二者没有质的不同。20世纪70至80年代的一些人类学家都认同这一说法。西敏司认为人类学家是“严肃的旅游者”(serious tourists);(12)Sidney Mintz.Infant,Victim and Tourist:the Anthropologist in the field[J].Johns Hopkins Magazine,1977,(27).皮埃尔·范登伯格怀疑人类学家是“深度旅游者”(in-depth tourists);(13)Pierre van den Berghe.Tourism as Ethnic Relations:a Case Study of Cuzco[J].Peru.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1980,3.帕特里夏·阿伯斯和威廉·詹姆斯则将人类学家定义为“兼职旅游者”(part-time tourists);(14)Patricia Albers,William James.Tourism and the Changing Photographic Image of the Great Lakes Indians[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83,(1).此外还有“精英旅游者”(refined,sophisticated,elite tourists)(15)Jean-paul Dumont.Review of The Tourist[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77,(4)“三等旅游者”(third-order tourists)(16)Donald Redfoot.Touristic Authenticity,Tourist Angst and Modern Reality[J].Qualitative Sociology,1984,(4).之说。至少在“外来者身份”“旅行”“长驻”“无知”这4条上,人类学家与后现代旅游者没有太大不同,后者对异文化的好奇心和了解程度丝毫不输人类学家。20世纪70年代,当菲利普·科塔克在巴西一个小渔村发现嬉皮士群体时,他憎恨他们对社区文化谙熟的事实,却又不得不承认自己对“天真的土著”的浪漫想法和他们对“简单生活方式”的追求是殊途同归。(17)Phillip Conrad Kottak.Assault on Paradise:Social Change in a Brazilian Village[M].New York:Random House.1983:40~41.在“后现代世界的旅游与人类学”一文中,弗雷德里克·埃林顿等二人揭示了人类学家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遇到自称为“旅行家”的实验型旅游者时所感受到的身份危机和职业挑战。(18)Frederick Errington,Deborah Gewertz.Tourism and Anthropology in Post-Modern World[J].Oceania,1989,(1).
在和他者的关系上,人类学家和旅游者都与他者形成了某种二元关系,分别是文化意义上的“他者-自我”关系与交换意义上的“东道主-游客”关系(简称“主-客”关系)。这两对关系都隐含“文明-原始”“现代-传统”“中心-边缘”“先进-落后”等二元对立结构,人类学家和旅游者所象征的“文明”“现代”“中心”“先进”等文化内涵成为他者衡量自己有无价值、特征或共同人性的标尺。(19)威廉·亚当斯.人类学的哲学之根[M].黄剑波,李文建,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5.对于人类学而言,他者是反思现代文明或人类学家自身文化的镜像,因而他者在人类学家角色认同中的作用就很关键。同样,在他者眼里,人类学家也是一种他者,所以将作为研究对象的他者的看法纳入认知框架,既是人类学家角色认同的一部分,也是凸显主位观、平衡客位观的学理依据。也就是说,人类学家的自我是由他者的兴趣、态度和理解塑造而成。然而,这种取决于语义学上的他者的自我是脆弱的。保罗·拉比诺在摩洛哥经历了6任报告人和一个对等的他者之后,意识到人类学家和他的报道人都生活在一个经文化调适过的世界里,都陷于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20)保罗·拉比诺.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M].高丙中,康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144.克里克·马尔科姆对被当地小沙弥误认作嬉皮士这件事耿耿于怀,他甚至不确定自己的报道人是如何理解这段“他者-自我”关系并制定相应规则的。那么,他者对于旅游者又意味着什么?迪安·麦坎内尔眼中的现代游客是对原始民族、贫困人群以及其他少数民族怀有好奇心,在不同程度上渴望介入异文化和社会的人,他们刻意使自己处于象征性的非我状态,以此重新定位自己。这一点与人类学家何其相似,他们堪称和社会学家一样是“完整的人”。(21)Nelson Graburn.人类学与旅游时代[M].赵红梅,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355~364.以对他者的好奇和了解程度作为潜在标准,旅游者身份也存在内部分化。丹尼尔·布尔斯汀眼中享受“伪事件”(pseudo-event)的旅游者,和埃里克·科恩笔下躲在“环境空气泡”中的旅游者,(22)Erik Cohen.Toward a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Tourism[J].Social Research,1972,(1).看到的是文化碎片或假象,他们是“不完整的人”。爱德华·布鲁纳在带完一个“泰国-缅甸”旅行团后,收到一位富豪游客发来的“游客聚会”邀请函,这是一位饱览异域风情的中产阶级游客,他想向同团的游客展示自己多年来搜集的旅游纪念品(23)Malcolm Crick.The Anthropologist as Tourist:an Identity in Question[A].Marie-Francoise Lanfant,John B.Allcock and Edward M.Bruner.International Tourism:Identity and Change[C].London:SAGE Publications Ltd.1995:205~223.,布鲁纳作为大学教授兼导游,也荣幸地在受邀之列。他发现这些旅游者返家后之所以能够再聚,是基于“去哪里-他者”和“收集什么-文化差异”这两项认同内容,游历的他者越原始越偏远,见识的文化差异越奇异越稀罕,就越能获得其他旅游者的认同,也越能彰显社会地位与身份。这是符号型旅游者的显著特征。
威廉·亚当斯说:人类学从来都是生存于、也只能生存于大众接受和期待的框架之内。我们应该,而且必须占据一个地位,并扮演一个角色。(24)威廉·亚当斯.人类学的哲学之根[M].黄剑波,李文建,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5.但假如报道人将人类学家预设的“他者-自我”关系理解成“主-客”关系,人类学家将如何建立自己的研究者身份,如何满足大众对人类学家的行为期待?或许在他者眼里,民族志者、殖民主义者和旅游者看上去都是意识形态融合大背景下出现的有钱有权和有特定需要的另一种他者。尽管今天的人类学家与旅游者看上去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身份,在与他者的互动方式和对他者的表述策略上存在极大不同,但在动机和追求上,二者仿佛一根线上的两个蚂蚱。(25)Michael Harkin,Modernist Anthropology and Tourism of the Authentic[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95,(3).参与观察与旅游行为这两种看似没多大关系的文化实践,共享的不仅仅是起源、地域和他者,还将显示出更宽广的相似性。
(三)与旅游者划清界限
对于人类学家与旅游者的相似性,包括旅游人类学家在内的人类学家都怀有潜在的忧虑、敌意和排斥。没有哪个群体像旅游者一样,对人类学家关于文化多样性与复杂性的认识论优越地位形成如此之大的挑战和威胁,因此很多人类学家竭力寻找二者之间的差异性,以撇清自己和旅游者的关系。
从性质和角色上看,旅游者是在玩耍,追求世俗的感官愉悦;人类学家在工作,追求关于人类状态的知识。布鲁纳认为,旅游者是屈从(surrender)的精神隐喻,民族志者是奋争(struggle)的精神隐喻,(26)Edward Bruner.The Ethnographer/Tourist in Indonesia[A].Marie-Francoise Lanfant,John Allcock,International Tourism:Identity and Change[C].London:Thousand Oaks,1995:236~239.这一差异既体现在过程上,也体现在结果上。这是人类学家理想中的区分边界,但它至少在两方面有懈可击:其一,正如维克多·特纳所说,“工作-玩耍”的二元分立是后工业社会的特征,在前工业社会(或传统社会)二者之间的边界很模糊。(27)Victor Turner.From Ritual to Theatre:the Human Seriousness of Play[M].New York:Performing Arts Journal Publication,1982:28~36.其二,人类学家所谓的工作,是指人类学家带着学术敏感性、尊重与勤勉的态度对当地人进行“严肃的”参与观察,但事实上很少有人类学家能做到完美的内在转换或“经验接近”,(28)Clifford Geertz.Local Knowledge: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M].New York:Basic Books.1983.他们依赖翻译或报道人的程度不亚于旅游者依赖导游和领队。因此,托马斯·埃里克森才戏谑说从文化观光到完全的人类学研究,可能只差一小步。(29)托马斯·许兰德·埃里克森.什么是人类学[M].周云水,吴攀龙,陈靖云,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5.从行为上看,旅游者与旅游对象之间的互动基本上是视觉基础的,感知是选择性的、碎片的和即时的;人类学家与研究对象的互动主要是口头式的,到田野现场只是漫长地做笔记、分析、写作、修订与呈现过程的开始。若要人类学家承认有些旅游者懂得并不比人类学家少,无异于在宣布整个人类学信仰体系没有合法性。(30)Tim Wllace.Tourism,Tourists,and Anthropologists at Work[J].NAPA Bulletin,2008,(23).因此,“东道主-游客”关系必须是一种肤浅短暂的交换关系,“他者-自我”关系必须是一种深刻长久的文化关系。人类学家和报道人往往结成终生朋友或亲人关系,因而有人认为与报道人的关系性质是旅游者变成民族志者的关键点,但也有人指出一个沮丧的事实,即人类学家和研究对象之间本质上是一种信息剥削关系,人类学家是有明确目的的任务者,为获取信息,他们刻意营造了与当地人的亲密关系。(31)Malcolm Crick.The Anthropologist as Tourist:an Identity in Question[A].Marie-Francoise Lanfant,John B.Allcock and Edward M.Bruner.International Tourism:Identity and Change[C].London:SAGE Publications Ltd.1995:205~223.人类学家需要建立身份意识以获得可靠的信息,因此他们清醒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旅游者对自己是现代性的建构者这一点茫然无知,原因在于社会科学家是在实践中生产理论(Theory of Practice),而旅游者是将理论付诸实践(Practice of Theory)。(32)George van den Abbeely.Review:Sightseers:The Tourist as Theorist[J].Diacritics,1980,(4).因此“有无意识”是麦坎内尔为区别人类学家和旅游者而提出的另一个标准。但正如爱德华·布鲁纳所言,所有科学家都不会有一个不变、同一的自我,自我永远是历史时代的产物,学科视角、生命情境以及相关历史社会因素都会影响研究者的产出。(33)Edward Bruner.The Ethnographer/Tourist in Indonesia[A].Marie-Francoise Lanfant,John Allcock,International Tourism:Identity and Change[C].London:Thousand Oaks,1995:236~239.如此看来,人类学家那点清醒意识也没什么大不了,不比旅游者的无意识高明多少。
在一些极端的“反旅游者”(anti-tourist)人类学家眼中,旅游者是敌人、造谣者、新殖民主义的后备军以及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的危害者。他们众口一词:旅游者非我族类,其生而有劣根性,是现代性背景下繁荣富足社会衍生的文化碎片。(34)Nelson Graburn.人类学与旅游时代[M].赵红梅,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355~364.他们如此急切地与旅游者划界限,本质原因还是旅游者的在场冒犯到民族志者的权威和优越地位。参与观察是一种要求研究者运用其社会自我作为主要研究工具的方法,(35)林恩·休谟,简·穆拉克.序言:尴尬的空间,创造性的场所[A].林恩·休谟,简·穆拉克.人类学家在田野:参与观察中的案例分析[C].龙菲,徐大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10.人类学家的知识生产有多依赖这种方法,他对这个自我的重视程度就有多高,无论他下意识还是有意识排斥旅游者,都不仅是在维护他者的纯洁性和自我身份的权威性,而且也是在捍卫学科知识的可靠性与神圣性。
另一方面,在旅行者、人类学家与旅游者这三个角色之间存在微妙的历史关联。旅游者被看作古典旅行者的现代变种,人类学家也与古典旅行者有不解之缘。在18至19世纪的欧洲,旅行是一门科学,旅行家在旅途中洞悉人类社会与历史,人类学的形成正是科学旅行家与摇椅理论家合作的结果,因此约翰尼斯·费边揶揄说,人类学是借旅行家和探险家而上位的学科。(36)Johannes Fabian.Time and the Other:How Anthropology Makes its Object[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6~7.这样,人类学家和旅游者的原型都可上溯到旅行家和探险家。到20世纪60至80年代,嘲笑旅游者变成西方社会的文化时尚。这种社会情绪本质上是对古典旅行艺术逝去的反面表达,用保罗·富塞尔的话来说,现代旅游业存在的前提是真正的旅行行为已不复可能,(37)Paul Fussell.Abroad British Literary Travelling between the Wars[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44~45.旅游者之滔滔和旅行者之寂寂正是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断裂的双重标志。在西方智识传统里,旅行者与旅游者是两个具有不同文化内涵、历史隐喻、社会表征的概念。丹尼尔·布尔斯汀指出,现代旅游者与古典旅行家在旅行艺术上有霄壤之别,为此他做了系统的比较:第一,旅行者是为正事而旅行的人;旅游者是为愉悦而旅行的人。第二,旅行者是主动的,他自找苦吃地探寻他者与差异体验;旅游者是被动的,他希望有趣的事情如期而至。第三,旅行者的旅途要冒未知、挫折、健康、生命的风险;旅游者的旅途由旅行公司或现代科技保驾护航。第四,旅行者往往单枪匹马展开旅程,旅游者往往结伴、结群而行。第五,旅行是一项活动,包含体验与担当,对旅行者具有真正的吸引力;旅游是一件商品,批发零售均可,其核心吸引物是“伪事件”(pseudo-event)。(38)Daniel Boorstin.The Image:A Guide to Pseudo-event in America[M].New York:Harper & Row.1961:77~117.显然,把旅行者替换成人类学家,对比结果也基本成立。在穿越地理与文化边界上,探险家、传教士、殖民官员、士兵、移民、逃亡者、帮佣者、人类学家、旅游者等都有相似或相异的旅行故事,但除了探险型旅行家,人类学家竭力与其他旅行角色保持距离或划清界限。“没有痛苦的人类学”就没有分量和说服力,田野工作本质上是冒险实践,经历身体和情感创伤在所难免,古典探险旅行者光辉厚重的英雄形象正好有力地诠释了人类学家田野作业的神圣性质,关于其动机、行为与体验的故事正是对田野调查中“苦劳”这一部分的“深描”,这一点是现代旅游者无法比拟的。站在民族志者的立场上,旅游者是私生子、旅行者的可耻简化版和冒名顶替者,这也是人类学家宁肯在旅行者这里认祖归宗而不愿与旅游者结亲的深层原因。
“西方旅游者”这一角色类型得以普及的背景原因是全球化进程与现代性传播,直接原因是20世纪中后期以来国际旅游的扩张式发展,人类学家执迷的“文化岛屿”也在这一过程中趋于消解,因此很难说旅游者在某种意义上不是人类学家宣泄失落情绪的替罪羊。考虑到主流人类学对人类学家与旅游者之间相似性的回避以及对差异性的强化,因此很有必要建议人类学家有一颗平常心,承认自己的一部分旅游者属性。克里克·马尔科姆甚至认为,人类学家与旅游者之间的区别在于程度而不在类属,比如在逗留时间长度、语言能力水平、地方互动的本质、讲述故事所使用的媒介与语言等方面,二者只有程度之别。(39)Malcolm Crick.The Anthropologist as Tourist:an Identity in Question[A].Marie-Francoise Lanfant,John B.Allcock and Edward M.Bruner.International Tourism:Identity and Change[C].London:SAGE Publications Ltd.1995:205~223.因此,人类学家与旅游者身份重叠的程度并不取决于回避或强化的态度,而取决于以哪种类型的旅游者作为参照比较对象。当民族志作为一种方法或活动时,受过专业训练的人类学家并不比一些后现代旅游者更有资格和话语权,后者在对异文化的参与长度和体验深度上甚至超过前者。当民族志作为一种文本时,人类学家的比较性、系统性表述风格是否有压倒性优势,他的身份认同是否最终将系于写作?如果民族志文本是人类学家区别于旅游者的决定性物证,那么一些优秀的旅行游记将对这种文本形成另一种挑战,人类学家也将面对这二者之间的相似与差异,而这本质上仍然是旅游者隐喻的延伸。
三、民族志,还是文学作品?
(一)“不科学”的民族志
狭义的民族志是指一种以表达整个世界或生活形式的事实为目的的写作模式,是建立在田野调查基础上的叙事。在几代人类学家的努力下,民族志基本确立了科学、专业、权威的知识角色和文体地位。前马凌诺夫斯基时代的人类学处在从业余向专业化发展的状态,人类学家尝试将民族志建构为人类学自己的方法,1874~1912年间连续四版的工具书——《人类学笔记与询问》是这种努力的标志性事件。该书的目标读者从初版针对旅行者升级到第四版针对受过专业训练的观察者,这一转换反映人类学对现场观察和资料搜集的地位和主体的再思考和探索,但这一时期的人类学家既自己撰写民族志,也利用其他人的民族志,并未获得民族志的定义权与专属权。在马凌诺夫斯基时代,民族志以科学和专业为标签,通过与广义民族志大家族的其他成员,比如游记、个人回忆录、报刊文章以及传教士、移民、殖民地官员、朝觐者等人的随意记述形成鲜明对照来进行自我定义。(40)Mary Louise Pratt.寻常之地的田野工作[A].周歆红,译.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C].高丙中,吴晓黎,李霞,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56~80.1922年出版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正式确立“科学人类学的民族志”准则,它通过一套有效的科学规则把资料员和研究者的身份完美地合二为一,(41)高丙中.《写文化》与民族志发展的三个时代(代译序)[A].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C].高丙中,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6~17.使专业的资料搜集与业余的资料搜集彻底区分开来,给人类学家的民族志打上“田野作业基础上的民族志”这一标记。
然而,科学民族志就真的科学了吗?20世纪80年代初文本学派对民族志进行“文学治疗”的运动揭示了三个真相:一是人类学者关于调查对象的知识具有相对性,这种相对性与人类学者的主观性密切相关;二是人类学者使民族志表现出科学性的手法往往是文学性的;三是民族志通过与其他文体的对立来确立自身的合法地位,做法如此过火以至于遮蔽了一个事实,即民族志本身的话语方式通常源于这些所谓的其他文体(比如小说与旅行游记),而且至今也依然与之共享某些写作经验。(42)Mary Louise Pratt.寻常之地的田野工作[A].周歆红,译.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C].高丙中,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56~80.实际上,田野调查并不是一次次可供复制的“实验”,每一本民族志专著都意味着一次特殊的田野经历与体验,很多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以时间长度或语言能力而著称,但即便这两项指标都超额完成,也无法彻底消除调查者在面对他者时的主观性磨难。想想《人类学家在田野》里那些关于脆弱、移情、信任、依赖、情感依附、互惠和责任等的议题(43)林恩·休谟,简·穆拉克.序言:尴尬的空间,创造性的场所[A].林恩·休谟,简·穆拉克.人类学家在田野:参与观察中的案例分析[C].龙菲,徐大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10.,就知道要在个性的自我与社会的自我之间划清界限有多难。几乎每个人类学家都要完成“感性-理性-主观-反思”的民族志循环过程,期间必然会面临伦理、政治、理论乃至方法论上的困难与调适。
(二)科学民族志的调适
民族志史上的先锋调适者是格雷戈里·贝特森,他的《纳文》一反提供权威和概括的信息以说服读者的民族志常态,而是很不专业地直接向读者“报告”自己对材料的思考过程。乔治·马库斯认为《纳文》虽然不守规矩,却给后学树立了在写作和解释形式之间“玩耍”的榜样。(44)George Marcus.Rhetoric and the Ethnographic Genre in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J].Current Anthropology,1980,(4).其中,以保罗·拉比诺的《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和让-保罗·杜蒙的《头人与我》玩法最为彻底,将调查过程解剖给公众看,即布迪厄所说的“把对象的研究作为研究对象”,(45)保罗·拉比诺.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M].高丙中,康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144.从而真正触及田野作业的相对性问题。这种打破“主观-客观”平衡的实验主义民族志令经验的客观性修辞让位于自传和反讽性的自我写照,不仅刻意破坏对异国风情的幻想,而且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到民族志权威的建构和他者表述的客观性上来,导致提供文化事实的传统民族志成为一个疑窦丛生的概念。可以说,这些反常态的民族志培育了一种对人类学家自身处境进行清晰思考的特性。
詹姆斯·克利福德说,在人类学领域,只提少数人的名字,颇有影响的如克利福德·格尔茨、维克多·特纳、玛丽·道格拉斯、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让·迪维里奥以及埃德蒙·利奇,都对文学理论和实践有兴趣,他们各自以不同的方式模糊了艺术和科学之间的界限。(46)詹姆斯·克利福德.导言:部分的真理[A].吴晓黎,译.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C].高丙中,吴晓黎,李晓,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29~55.马凌诺夫斯基对一些作家的追捧众所周知,弗朗兹爸爸的几位爱徒同时把自己看成人类学家和文学艺术家。当代人类学家又有几个能完全避免民族志的文学性呢?如果缺乏隐喻法、形象表达、叙事等文学过程,又有哪些民族志能被誉为是有风格的或好的民族志呢?所以,打造民族志是一件手艺活,它与写作这样的世俗之事相关。(47)詹姆斯·克利福德.导言:部分的真理[A].吴晓黎,译.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C].高丙中,吴晓黎,李晓,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29~55.正因为如此,乔治·马库斯和迪克·库什曼才将民族志作为文本分析的对象,揭示马凌诺夫斯基及其跟随者的科学民族志是一种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本质。通常,如果一部民族志专著在描述事实之外还被认为是生动的或构思精巧的,那么其表现力和修辞功能应该是装饰性的,即便是为了更有效地帮助事实的分析或描述,那么这样的事实内容至少也应该与传达事实的方式分离开来。但实际上民族志事实与文学修辞已经紧密结合在一起,难以剥离。文学手法变成传达民族志的专业性和权威性的一种策略,这也是马库斯和库什曼二人所针对的问题,即民族志是如何说服读者相信异文化知识的?二人指出,实验民族志文本权威的树立取决于确立叙事在场、谋篇布局和对素材表述的事前编码这三大策略。(48)George Marcus,Dick Cushman.Ethnographies as Texts[J].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1982,11.至于实验民族志的真实性和合理性则是一个修辞学问题,它自身引发与现实主义民族志类似的反思,比如以客观性之名的主观性、以直白坦率之名的修辞、以事实之名的虚构等。
可以将这类民族志的认识论焦虑看成一种哲学调适,它反映公众对民族志者的前理解和预设的极端置疑。(49)詹姆斯·克利福德.导言:部分的真理[A].吴晓黎,译.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C].高丙中,吴晓黎,李晓,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29~55.20世纪80年代当人类学家终于将民族志当作一种写作方式来解释、审视、反思与修正时,他们无法否认无论哪种类型的民族志都是一种有文学品质的写作,而由于民族志对自身科学、专业、权威的追求与定位,导致文学性在民族志文本中的吊诡功能:一方面是有意无意的文学手法强化了民族志的专业权威、叙事真实性与知识可靠性;另一方面是文学策略在民族志中的“制度化”使之无法彻底区别于其他文学体裁,反而引致民族志知识的真实性危机。
(三)民族志与旅行游记
通过承认民族志知识是一种有承诺的、不完全的部分真理,是一种混合的文本活动,人类学家可以在总体上应对民族志的文学性困境,但却无法解决民族志与旅行游记之间的隐喻烦恼。旅行游记作为一种文学体裁不仅给予民族志以书写启迪,而且将“旅行者-旅行游记”与“人类学家-民族志”这一组对照关系补充完整,使人类学家的职业身份认同陷入更深刻的危机之中。
在对象和内容上,民族志与经典旅行游记的指向基本是一致的,作者都是民族/异文化的好奇者与探秘者,文本都反映一个地方的地理与文化景观。在前马凌诺夫斯基时代,旅行话语、传教士著作与殖民官员报告等均可视作民族志的前身,艾尔弗雷德·劳奇甚至认为民族志就是旅行者故事的合集,并非马凌诺夫斯基想象的那么专业。(50)Valerie Wheeler.Travelers’ Tales:Observations on the Travel Book and Ethnography[J].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1986,(2).在民族志与旅行游记的亲缘关系上,玛丽·路易丝·普拉特指出了游记与民族志之间的有趣类同点与延续性。第一,民族志中个人性叙述和客观化描述相结合的手法源自16世纪的欧洲游记。在个人性叙述方面,马凌诺夫斯基的原则是既彰显民族志者的个性化理想形象,又抵制个人化叙述的地位与分量。早期民族志者(如马林诺夫斯基和雷蒙德·弗思)往往将自我建构成漂流者形象,因为漂流者或俘虏在很多方面实现了参与观察者的理想,其欲显还掩的表述方式使民族志者被神秘化为一个极富理解力却非常不系统的文本人物,大概是介于科学家与国王之间的一种形象。到爱德华·埃文思-普里查德这一代,民族志中的人类学家成了受难的勘探者和冒险家形象,但这种形象建构也受益于19世纪非洲旅行家和探险家的游记。第二,现代民族志对研究对象的表述偏好与18世纪晚期的旅行者游记话语之间有着内在延续性,二者都存在两种倾向,即一方面倾向于把对象当作欧洲帝国主义的“幸存者”和“受害者”进行历史化,另一方面倾向于把他们当作未受历史影响的原始人进行自然化和客体化。普拉特认为人类学家要从这样的自我审视中获益,从而选择适当的修辞或创造新的修辞以诠释民族志的专业性和科学性。(51)Mary Louise Pratt.寻常之地的田野工作[A].周歆红,译.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C].高丙中,吴晓黎,李晓,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56~80.
然而,比起相似点,民族志与旅行游记之间的区别要明显得多。瓦莱丽·惠勒从角色感、讲故事、自我表述、权威与虚构、矛盾与读者5个方面比较了民族志与游记的异同,但她更强调显而易见的相异性。(52)Valerie Wheeler.Travelers’ Tales:Observations on the Travel Book and Ethnography[J].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1986,(2).瓦西里奇·盖纳尼-蒙塔菲则在迪恩·麦坎内尔的基础上对旅行者、民族志者和旅游者进行了再比较,她认为民族志是人类学家的个人层面和文化层面与他者相接触后的产物,人类学家从有意识的民族志写作中、从异文化神话的建构中、从对他者的内省式表述中,获得了完整的自我;深度旅游基础上的游记即便能触及旅行的内在维度,也不可能运用人类学自我反思性的写作方式。(53)Vasiliki Galani-Moutafi.The Self and The Other:Traveler,Ethnographer,Tourist[J].Annals of.Tourism Research,2000,(1).诚如迈尔斯·理查森所说,如果人类学家不去描述关于人类的神话,那么谁能做这件事呢?旅游者吗?当然不是。(54)Miles Richardson.Anthropologist—The Myth Teller[J].American Ethnologist,1975,(3).
1995年,《当代人类学》(Current Anthropology)组织了一期主题为“民族志权威与文化解释”的特刊,全面反思民族志者角色、民族志方法、民族志话语与“文化崩溃”的关系,这是民族志反思在主流人类学中告一段落的重要信号。今天的人类学家研究整个世界,并不局限于某个遥远的角落,尽管人类学的传统兴趣仍在延续,但它的研究实践、它与研究对象的关系、它的论题多样性和结构与20年前迥然不同。民族志方法嵌入在当代世界一系列更为复杂的关系丛中,超出了它的殖民历史、马凌诺夫斯基范式,甚至旅游者隐喻。在复杂的文化接触过程中,民族志方法发展出新的生存方向,比如“关系的民族志研究”(ethnographies of encounter)一文所提倡的跨国资本主义、空间与地方、“人-非人”关系等主题。(55)Lieba Faier,Lisa Rofel.Ethnographies of Encounter[J].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2014,(43).在当代,许多人类学家花大量时间写期刊论文、论文集论文和会议论文,传统民族志成了偶尔为之的作品,这样,当传统民族志不再作为当代人类学的主要认同根据时,人类学的学科意识也松懈了下来。因此,当人类学家进入一些其他领域时,就不可避免地被裹挟着与其他话语和实践形成尾随或派生关系,虽然他们也运用田野调查方法,但调查对象、主题和内容都与传统民族志甚至实验民族志有了较大的区别,这些象征性的民族志研究能提供关于对象的什么知识呢?将遭逢怎样的反馈和评价呢?西方“旅游人类学”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发展历程在很大程度上诠释了这些样态和问题。
四、解释主义,还是实证主义?
(一)民族志方法的旅游反思
主流人类学的反思之光在20世纪80年代末辐射到旅游领域,拉开旅游学界对民族志方法与社会科学表述风格的再思考序幕。其中,以两篇文章作为标志性和总结性的时间节点:一篇是1988年的“旅游研究的方法论”一文,文章指出,旅游研究中“掩盖理论和方法的问题,未能意识二者间的内在关系”的不幸倾向,导致了3种病态研究路径:1.没有实证基础的理论话语;2.印象和轶事材料组装而成的描述性文章;3.缺乏理论支撑的数据分析。文章批评人类学家、历史学家与政治学家所偏好的民族志理路是一种低方法论成熟度和低理论意识的研究范式。(56)Graham Dann,Dennison Nash,Philip Pearce.Methodology in Tourism Research[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88,(1).另一篇是克里克·马尔科姆所撰的综述论文,文章指出,由于对待旅游现象的随意态度,使得旅游社会科学文献混杂了大量关于旅行、旅游者的感伤主义文化意象,而之所以将这种写作风格称作“表述”而非“分析”,是因为它充斥着模棱两可、草率归纳与模式化的语言。亦如哲学家尔弗雷德·劳奇所说,认识论层面的人类学离科学状态还很远,人类学家毋宁将自己看成讲述旅行故事(说教类)的人。(57)Malcolm Crick.‘Tracing’ the Anthropological Self:Quizzical Reflections on Field Work,Tourism and the Ludic[J].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and Cultural Practice,1985,(17).克里克置疑以这种文字风格为载体的知识体系的确定性,认为案例研究必须突破这种禁不起检验的文献形象,创造出有别于文学表述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从而对旅游的复杂性做出值得尊重的学术研究。(58)Malcolm Crick.Representations of International Tourism in the Social Sciences:Sun,Sex,Sights,Savings,and Servility[J].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1989,(18)此后,人类学视角下的田野调查和民族志反思逐渐告一段落,而代之以旅游研究方法论的大探讨。据1998年统计,《旅游研究纪事》(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以方法论为主题的论文数量排名第四,(59)Margaret Byrne Swain,Maryann Brent,Veronica H.Long.Annals and Tourism Evolving-Indexing 25 years of Publication 25(Index1)[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98,(25).到2013年(Annals的40周年刊庆)已跃升第一。(60)Honggen Xiao,Jafar Jafari,Paul Cloke,John Tribe.Annals:40-40 Vision[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13,(40).实际上,作为方法与文本的民族志一直在旅游研究方法论中被品评、改进、保留和应用,这股势头一直持续至今。
2000年世纪之交,丹尼森·纳什分析了3篇基于民族志方法的旅游人类学文章(主题分别为旅游影响、“主-客”互动和旅游者),结果表明民族志研究虽然提供了旅游世界的部分真相,但很难评估民族志者理解文化的使命完成得怎么样。他总结了旅游民族志研究的一些基本要素,即:1.小规模社区、一手资料、密集式和探索性的人群研究;2.客观性与同情性的理解观;3.控制性的参与观察;4.明智选择报告人,等等。但纳什也坦承,正是由于这些要素要求才使得民族志描述性文字的信度不那么容易获得。(61)Dennison Nash.Ethnographic Windows on Tourism[J].Tourism Recreation Research,2000,(3).旅游民族志研究也成为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之间争辩战的一个焦点。2005年,旅游人类学的一部重要著作《文化之旅:旅行民族志》(Culture on Tour:Ethnographies of Travel)出版,评论性文章至2010年仍连续不断。以纳尔什·格雷本为代表的人类学家是肯定赞美派,认为该书线索清晰,内容紧凑,理论明确,是近20年来“旅游人类学”的代表作。以珍妮特·钱为代表的学者是否定批评派,指责书中大量使用作者自创的、连学界人士都难以读懂的术语,接连不断的反思与评论性叙事使全书难以卒读。该书著者爱德华·布鲁纳于2010年做出统一答复,他首先针对两派尖锐对立的意见,指出此次争论是“旅游研究”中长期存在的科学的、实证的、定量的研究路径与质性的、人文的、民族志的研究路径之间紧张关系的爆发;其次针对旅游研究的方法,认为不同的研究问题就应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最后布鲁纳宣布,自己的研究理路是人文主义与解释主义的,这是一种广义的科学,一部上乘的民族志是可以无限接近旅游现象的“真相”的。(62)Edward Bruner.The Two Reviews:Science and Humanism in Tourism Study[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10,(3).
(二)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之辩
在国际旅游学界的三大权威期刊——《旅游研究纪事》《旅游管理》和《旅行研究》中,《旅游研究纪事》发表质性文章的数量居首位,但也仅占其总量的28%。(63)Roy Ballantyne,Jan Packer,Megan Axelsen.Trends in Tourism Research[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09,(1).《旅游研究纪事》的创刊人兼总编贾法·贾法里在任的35年间(1973~2008),作为人类学博士的贾法里提倡不拘泥于方法,因而《旅游研究纪事》对质性的旅游人类研究表现出最大的接纳度。但第二任总编约翰·特赖布更倾向于实证主义范式,特赖布认为以定量方法为核心的实证主义至少可以提供有前提的旅游真相,原因在于:1.实证主义能够施用有效研究方法的领域是有限的,因而其知识供给不会泛滥;2.实证主义有严格的方法论规范,其研究方法无法脱离知识力场中的概念、学术规范、研究技术等规则的操控,它没有选择自由。相较而言,以解释主义为核心的质性研究是将“旅游复杂性需要不同视角的研究”当作信条,虽然竭力在寻求“翻译”旅游现象的自然主义声音,却往往提供一些矛盾、含混且需要复杂语境界定的凌乱叙述。实证主义者认为,这些知识“真相”是缺乏信度或效度的,但解释主义者却发明像可证实性(confirmability)、可信性(trustworthiness)、透明性(transparency)之类的标准来为自己辩解。(64)John Tribe.The Truth about Tourism[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06,(2).在旅游学领域这场从1980年代末持续至今的方法论大讨论中,实证主义的定量方式看起来已经取得重大胜利,而解释主义的质性方式仍在为“生存”而战。
21世纪初,西方旅游研究处在重要的转折点上,进入约翰·特赖布所谓的“新旅游研究”时代。这一时期与旅游人类学相关的学术事件有3个:其一,《旅游研究》(Tourist Studies)与《旅游与文化变迁》(Journal of Tourism and Cultural Change)两家期刊先后于2001年和2003年创刊,这是两家主要提倡和支撑质性研究的期刊。其二,2004年《旅游中的质性研究: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Qualitative Research in Tourism:Ontologies,Epistemologies and Methodologies)一书出版,该书标志学术界对旅游研究新路径的思考。其三,2005年第一届旅游“批评转向”会议在克罗地亚的杜布罗非尼克举行,自此掀起旅游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反思浪潮,“杜布罗非尼克效应”(Dubrovnik Effect)表明旅游研究亟待创新性理论与方法的知识贡献。(65)John Tribe.New Tourism Research[J].Tourism Recreation Research,2005,(2).一些批评者趁势提出,在实证主义长期居于压倒性优势背景下,应该给予解释主义和反思性研究一些合法的空间。(66)Irena Ateljevic,Candice Harris,Erica Wilson,Francis Leo Collins.Getting ‘Entangled’:Reflexivity and the ‘Critical Turn’ in Tourism Studies[J].Tourism Recreation Research,2005,(2).这三大事件是旅游民族志知识回潮的契机。在新近一篇题为“旅游知识体系”的文章中,约翰·特赖布纠正了自己对“非商业性旅游知识”(包括艺术与人文等知识类型)的态度与看法,他承认,缺乏艺术与人文知识、价值观导向知识与土著知识的旅游知识体系是营养不良的,目前旅游研究面临的基本挑战是旅游知识认知的多元化,而不是任由某一类型知识独霸天下。(67)John Tribe,Janne Liburd.The Tourism Knowledge System[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16,(51).如果旅游想告诉我们一些关于现代世界的重要事情,单纯的经济、统计、地理、社会、文化维度都不足以囊括旅游复杂性,正如单一的文本表述风格亦不足以表达研究对象复杂的客观维度与主观维度一样。
五、学科坐标与研究契机
在西方主流人类学史上,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在这一时段,基于田野调查的民族志知识生产与它的研究对象——他者(民族与地方)之间发生了深刻的断裂,在意识到关于研究对象的所有多样性和后殖民转变后,文化人类学内部爆发了系统的认识论反思运动。这股反思浪潮指向田野调查方法与民族志文本的深究与修正,从两个方面进行自我批判:一是以人类学家自身为调查工具的参与观察法的主观性缺陷与有效性;二是民族志文本的表述策略如何维系了学科知识的科学、专业与权威地位。这两个方面合二为一,就是人类学家必须面对的两个核心问题,即:田野调查基础上的民族志文本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研究对象的真相?民族志是一种再现文化还是发明文化的文体?旅游者隐喻就是这场关于民族志“写作”反思运动的派生物。首先,它带着复杂的目的反诸民族志的田野调查基础,争辩人类学家与旅游者之间的异同,激起方法论上的人类学反思;其次,民族志与旅行游记的延伸类比暴露出民族志文本的文学性与个人性话语风格,它促使人类学家承认民族志知识的局限性,从而激起修正与完善的热情。西方旅游人类学的兴起与确立基本坐落在主流人类学这个突出的断裂时段,在某种意义上,旅游人类学的产生也是主流人类学内部变迁的产物之一。因此,当主流人类学的反思风潮波及人类学家的旅游研究时,自然就激发了对旅游者隐喻的多重反思。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这种以旅游人类学家身份认同与文本表述为核心的反思支流被逐渐整合到“旅游研究”领域关于解释主义理路与实证主义理路的方法论争锋之中,导致旅游学界对民族志方法长时间的“爱恨交织”。
近年来,西方旅游学界也开始反思论文表述的边界,以及旅游知识是否是对旅游现象的真实反映的问题。(68)Honggen Xiao,Jafar Jafari,Paul Cloke,John Tribe.Annals:40-40 Vision[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13,(40).戴维·哈里森记述了这样一件事,一位英国高级旅游顾问偶然看了一本《旅游研究纪事》之后惊叫起来:谁写的这些东西?谁会看?(69)David Harrison.Anthropologists,Development and Tourism Networks Encounters and Shadows of a Colonial Past[J].Tourism Recreation Research.2010,(2).显然,旅游现象的知识生产和参与应用脱了节,但哪一个阵营更接近旅游真相呢?从旅游研究共同体的立场看,这是知识效度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给予质性研究方式更多的机会与信任,因为好的质性研究是知识效度的保障。自西方旅游人类学被引入国内学界以来,出现了不少旅游民族志与本土案例的研究,为国内旅游学贡献了一种有效度的知识类型。但国内旅游人类学存在两个短板,一是对西方旅游人类学的发展了解不充分,二是尚未建构起一个基础扎实的研究共同体。这使得它在国际旅游研究呼唤有效度的旅游知识时无力回应,在应对国内复杂的旅游文化现象时因缺乏理论和方向而未能发挥民族志方法的优势。事实上,西方主流人类学的方法论反思在前,为旅游知识生产的认识论困境提供了认识和分析的元话语,同时也提示国内人类学界卸下旅游者隐喻的包袱,将旅游世界看成田野调查的一个实验场,去尝试一些创造性的知识生产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