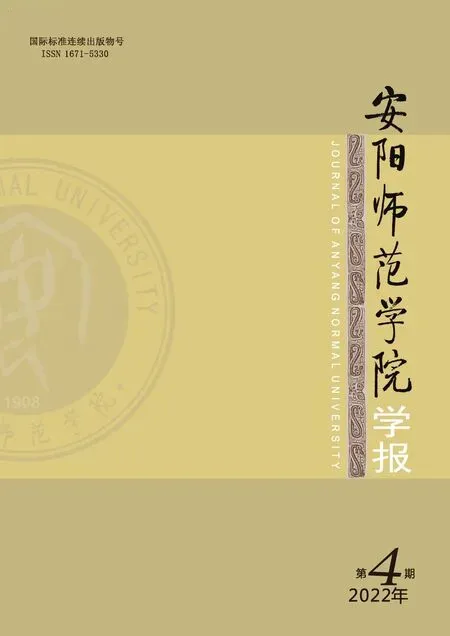《周易》人格美学研究引论
张 齐
(南京审计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0)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每一民族都拥有以自己心血铸就的伟大经典,而愈是处于源头的经典,就愈是散发着奇异的光芒,吸引着后世的探索者不断地溯流而上,一探究竟。对于中华民族而言,《周易》便是这样一种伟大的经典之一。众所周知,《周易》一书可进行多维度多层次的研究,而伦理学美学乃是其中十分重要的面向。不过,《周易》论著虽多,而未见有从人格美学角度来对其加以系统探讨。文章在梳理了《周易》及人格美学研究的派别及状况的基础上,试图指出《周易》人格美学研究的可行性,以就正于学界大雅。
一、《周易》哲学及美学研究述略
现在通行的《周易》一书,是由《易经》和《易传》两部分纂合而成。“经”部分由六十四卦及系属于其后的卦辞、爻辞构成。而《易传》则是为解释“经”之大义而作,其中《系辞》《彖传》《象传》皆有上下篇。此外,还有《文言》《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总共十篇,犹如经文部分之羽翼,故又有“十翼”之称。此一部分原是后起,不属于《易经》,一般认为是汉代儒者将其合并,便于学习参照。《周易》一书的创作,号称“人经三圣,世历三古”,相传为伏羲、文王、孔子相继著成。由于尊经崇孔的传统,此说长期以来几成定论,直至宋时欧阳修《易童子问》出,方启疑窦,后世疑古之风愈盛,此说已遭普遍怀疑,诸家研究所得结论亦不一致,然皆大多认同经文部分作于殷末周初,而传文部分作于春秋战国时期(亦可能延至秦汉)。既然如此,此书绝非一人一世所作,而是经过了漫长的年代,由多人修撰纂集而成。
若作一横向比较,《周易》经文部分的形成,恰在所谓“轴心时代”之前,而其传文部分的形成,则在“轴心时代”即将结束之时[1](P7)。横越于这段历史之间的,则是诸子辈出、百家争鸣的思想高峰。毫无争议的是《易经》开启了华夏文明乃至诸子百家,《易传》的思想则对诸子百家进行了高度的提炼和升华,其主体学派归属虽有争议,但这些争议也恰恰表明了其思想的丰盈复杂。倘为《周易》在思想史上的地位下一断语,对于中国的轴心时代而言,《易经》是凿破濛鸿的开启者,而《易传》则是金声玉振的集大成者。
千百年来,对这部被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的著作,人们或穷本极源,或推陈出新,或穿凿附会,或精思巧构,形成了极为复杂的易学研究流派,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易学诠释著作。鉴于此书地位的重要和思想的复杂,研究者自先秦以迄于今,代不乏人。清乾隆时期修撰四库全书时,针对易学研究,学者们总结出了“两派六宗”之说,以概括其流变(两派即“象数”和“义理”,象数派有占卜、禨祥、造化三宗,义理派有老庄、儒理、史事三宗)。《周易》本居六经之首,其自身所蕴道理又极渊深博大,再加上后世衍流附会,皆好援易为说,又自引其学附于易之名下,遂使易学日繁,几至无所不包。鸦片战争之后,尤其是辛亥革命以来,西学东渐之势甚大,其科学精神与方法亦渐渐渗透至易学研究领域,学者多援引近现代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理论,从不同角度切入易学研究。与此同时,传统的经学式研究不绝如缕,而后起的哲学研究则继承“义理”一派,融合西方哲学的思辨传统,愈趋精密深邃,使之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
易道广大,对中华文化的各个领域皆有深刻影响,而在文学、艺术、美学领域,更是如此。周易美学的研究,自朱谦之、宗白华、方东美诸先生启其端,其后刘纲纪、王明居、曾繁仁、陈望衡、王振复、张锡坤等人承其绪,又有其他诸多专业学者探颐索隐,再加上最近二十多年来国学热的推波助澜,遂使这一方面的成果层出不穷。大体来看,这些研究已经涉猎美学的形上与形下各个层次,涵盖了各种具体艺术门类。
先秦时期的文化创造型态往往是综合的,并没有现今如此细致的专业分工,许多著作既是文学作品,又富有哲学意蕴,还记载着若干历史事实,《周易》一书亦是如此。因此,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将此书当作文学作品来进行品鉴和钻研的,或将卦爻辞视作歌谣,试图从中发现其类似《诗经》的“比兴”手法;或将其视作叙事,考究卦爻辞中的叙事特色;或追溯它与当时其他作品之间的交融;或爬梳其中典故对后世文学作品的辐射。严格来说,这些都不是针对《周易》美学思想的研究,而是将《周易》作为文学作品对其体裁、风格、技巧进行研究。
当然,更多的人是将《周易》视作伟大的哲学著作,依据其运思方式、概念体系以及历代诠释,尝试从美学的立场出发,发掘其中所蕴含的审美观念,一方面观其历史沿革,另一方面探究其如何有益于当今时代的审美风尚。他们或以周易哲学思想为根基进行美学原理的构建;或对《周易》的某些卦象如《贲》《离》《观》《复》《咸》等作出独到的阐释,分析其可能含藏的美学意味;或阐发《周易》经传中某些典型的观念如太极、阴阳、刚柔、文、含章的美学义涵;或探讨这些极富美学意蕴的卦象和观念在漫长的文化传统中对于建筑、音乐、绘画、诗歌、舞蹈乃至包装设计等具体艺术门类的渗透作用;或针对著名易家如王弼、孔颖达等人的易学思想加以美学的观照。
此外,随着三十多年来西方美学理论强风的持续披拂,也有学者运用符号美学、身体美学、生态美学(或环境美学),对《周易》也作出了较为新颖的诠释,于人颇有启迪之义,于学亦有开拓之功。最近一些年来,美学领域出现了一些令人眼花缭乱的“转向”,如美学的日常生活化转向、美学的政治学转向、美学的情感转向等等,这些“转向”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周易》美学的诠释。
二、人格美学研究述略
关于“美”的论著汗牛充栋,关于“美”的重心言人人殊。对于《周易》而言,其中所蕴含的哲学、美学思想无疑是深刻而丰富的,可以从多个角度、多种层面来加以探讨。鉴于笔者个人兴趣,所关注的问题始终在于人。但人是什么?人应当怎样才能更好地生存在这世上?在哲学上对这两个问题进行探讨,必然涉及道德和审美,所谓“人格美学”的研究域就是对这一问题的集中统摄。然而,不单“美”的观念众说纷纭,“人格”概念的界定亦莫衷一是。那么,究竟何谓“人格”?人格何以配得上“美”的冠冕?
“人格”的使用,往往关联着对某个具体的人的价值评判,这种评判不管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今,都极为盛行。然而考诸典籍,先秦时未曾出现“人格”一词,正如日本学者今道友信所说:“在西方近代才有的作为做人的道德的责任,在东方的古代世界就已经存在了。但是……在东方却没有‘人格’这一概念。”[2](P167)汉语中的“人格”一词是从日文中引入的,对应英文中的Personality。此词起源甚早,早在拉丁文中便已有之,作Persona。在古罗马,当时戏剧所使用的假面即Persona。之所以要戴假面,乃是表示演员须得适应该角色性质,尽力贴合戏中人的角色特征,这当然要有理性和意志的作用。“Persona是根据理性和意志,用语言并且通过决断把角色的性质演出来的主体。因此,所谓人格常常被认为是根据理性和意志的决断乃至判断的主体”[2](P164)。其实,不仅是在戏剧表演时如此,在实际的人生中也是如此,人都因着特殊的境遇以自己的理性和意志而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依此角色与他人进行应对并承担责任和义务。在此意义上,人若完全无责任地行动,便意味着此人人格的失堕,甚至不足以称之为人。今道友信通过考察指出,东方虽然人格概念缺乏而晚起,但很早便有义务与责任的概念(如儒家所倡与“仁”对举的“义”);“人格”概念虽然出自西方,但“责任”在西方世界只是近代才产生的。因此,正是由于美学上的这种东西方互补性的状况,奠基于责任的人格概念理应成为东西方的共识。
然而就学界现状来看,对于人格问题作出深刻而广泛研究的,还是西方学界。由于人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人格问题持久地引起了哲学家们——尤其是心理学家们的兴趣。事实上,心理学家们对于“人格”的定义迄今为止仍未有定论,据此而作的研究便分化成不同的派别,在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建立了形形色色的人格理论,形成了六大流派。“它们是精神分析学派、特质学派、生物学派、人本主义学派、行为主义和社会学习流派以及认知流派”[3](P3)。犹如盲人摸象一般,学者们也是各执一词,每个流派都立足于其所探触到的人格的某一方面,建构出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根据不同的立场,他们对人格类型都有独特的归纳,依据其划分的基础来看,大体上可归为四类:或依生理特质,或依心理特质,或依社会取向,或依行为特质。这些区分都只是具有大体上的普遍性,而不具有绝对的普遍性,原因在于这些不同的人格理论只是心理学家们自己职业身份、生活背景、人生经历乃至人格特质的外显和投射。而且,他们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思潮的渗透和影响,而在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之间表现出某种侧重。根据考察,从西方心理学的发展潮流(近代人本心理学以及超个人心理学)来看,“西方的心理学家对人的探讨已从自我转到超自我,从身心的层面提升到灵性的精神层次……西方目前极力开显的新典范和人格类型,正是我们先秦古代先哲的擅场”[4](P51-52)。
为了论述的必要,基于前述考察,我们姑且对“人格”作出这样的界定:所谓“人格”,就是人们在现实的生命活动中,依据理性、情感和意志所作的价值判断并恒久地施之于实践历程而形成的较为稳定的性格特征和类型。应该说,“人格”更多地与伦理学、心理学相关,人格的完善意味着人的正向价值尽可能完满地实现,就其根本性质来看,主要偏重于善而不是美。然而,众所周知的是,在中国古典美学中,美的问题是绝不能脱离善而单独进行讨论的,这不仅在今之所谓的文学、艺术作品中是这样,在人的评判中更是如此。而且“人格”不可能只是一种静态的呈示,对它也不能仅作抽象的思辨式提炼。“人格”的形成和发展,必定是在具体境遇中的深刻而持久地实践才最终实现的,对这些实践行为的评判,不仅可以是道德的,也可以是美学的。当然,人们在讨论某个人美不美时,一般多着眼于其形体、容貌等外在的特征,但这种评判只是一种静态的评判。而人是生存于特定时空的活生生的东西,他可供人评判的美不会也不应只是其形体、容貌,其言行举止、所作所为亦复涵括在内。
大体上来看,人的存在关涉到两重维度:价值与境遇。人之所以为人,其所具有的诸种价值并非只能为境遇所决定,也以其认知、情感与意志,挟带着个人独特的价值观念进入境遇之中,深刻地改变着外在境遇,并使价值得到恢拓,也使得处身于价值与境遇之间的人塑造出其独一无二的人格型态。无疑,我们可以把天地间的这些人格类型当成艺术品,对他们的形态样貌、气度风韵进行审美观照。倘以“生命”为原点,以康德“美的理想”为坐标,便可以根据人各自的价值抉择确定其格位,这便可以大致勾勒出人格美学的曲线图。
康德的美学思想颇为精深,他的论述构成了人格美学的经典表述。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区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美:自由美和依附的美。前者又称作“流动之美”,后者又称“固着之美”。前者之所以是自由的,乃是因为它不与对象“应是”的概念相结合,而后者之所以不自由,乃是因为它以其概念及概念的对象所具有的完善性为前提。康德认为,只有针对自由美的鉴赏判断才是纯粹的,因为它没有预设目的的概念。相反,若以目的概念为前提的对象的美,由于笼罩在“完善性”之下,所以只是固着之美。置言之,“善与美的结合”会对鉴赏判断的纯粹性造成损害,所以康德又称这种鉴赏判断为“应用的鉴赏判断”。按照康德的标准,纯粹的鉴赏判断是非常严格的,所以符合这种鉴赏判断,能够冠之以“自由美”之名的对象非常之少,他也只是列举出了如下之物:花朵、许多鸟类(鹦鹉、蜂鸟、天堂鸟)、海洋贝类、卷叶饰、线描以及无标题的幻想曲、无词的音乐。
虽然如此,康德更为推崇那种并不是作为纯粹鉴赏判断的“美的理想”。他提醒人们“要想从中寻求一个理想的那种美,必定不是什么流动的美,而是……固定了的美”[5](P69)。在此,康德否定了其他事物能够拥有“美的理想”,而认为“只有那在自身中拥有自己实存的目的的东西,即人……才能成为美的一个理想”[5](P69)。也就是说,只有把人作为审美对象,才有可能从中寻求到“美的理想”。
康德认为,对人的审美,有性质不同的两方面:一是审美的规格理念,一是理性理念。我们可以将前者称之为“人体美的理想”,将后者称之为“人格美的理想”。前者表明了人作为某一特殊的动物物种,在形体外貌上所可能达到的最为完善的美;后者则是从人作为人的立场出发,使“人类目的”成为评判人的形象的原则。鉴于康德以“作为一个道德存在者的人”为创造的终极目的,所以,他认为“美的理想……就在于表达道德性”[5](P72)。康德是以道德价值在人的形象中的呈现作为“美的理想”,而所谓“美的理想”,其实就在于人格美。应当承认,康德以其创建的精密美学理论体系为人的审美奠定了不可移易的基础,但先验哲学对于经验世界中丰富多彩的人格型态尚无充分的解释效力。此外,康德所论道德价值的类型却比较单薄,他谈到的道德修养的诸方法,也显得过于僵硬而没有弹性,故不切于实际的人生践履。然而,这些恰恰是注重工夫论与境界论的中国哲学所擅长的。
在中国近现代哲学或美学史上,方东美先生点出了弥贯在中国形上学之中的三大人格类型,他说:“儒家是以一种‘时际人’(Time-man)之身分而出现者(故尚‘时’);道家却是典型的‘太空人’(Space-man)(故崇尚‘虚’‘无’);佛家则是兼时、空而并遣(故尚‘不执’与‘无住’)。”[6](P141)此说颇富诗人情怀,然以时空作为划分人格类型的依据,则有失偏颇,且未触及根本。佛家姑置不论,儒家之观象于天、观法于地,未尝不重视空间,而道家如老子、庄子亦未尝不重视时间。说到底,人格的区别应当只在于价值取向的性质及价值实现的程度,时间、空间之格套,毕竟是外在于人格本身的。方东美在其他场合也指出了这一点,突破了以时间、空间界定人格类型的局限,昭示出人格美学的高妙境界,他说:“中国文化传统的人格理想是圣人,圣人是各方面精神能和谐圆满发展至极致的人……中国文化中之理想人格是含音乐精神与艺术精神之人格……中国之最高人格理想正是化人格本身如艺术品之人格。”[6](P2-3)方先生此说固然高妙,可惜只聚焦于“圣人”人格。
此外,若论具体的人格美品鉴,宗白华先生是绕不开的。宗先生发现,在《世说新语》中有诸多篇章都是鉴赏和形容“人格个性之美”的,“美学上的评赏,所谓‘品藻’的对象乃在‘人物’。中国美学竟是出发于‘人物品藻’之美学。美的概念、范畴、形容词,发源于人格美的评赏”[7](P269)。如前所述,人格的品藻不是始自魏晋时期,早在先秦便已有之,以晋人风姿为纯美的标准,只是宗先生一往情深地钟爱所致的结果。可惜如同古代诗文论一样,宗先生妙悟虽多,但在人格美学的系统理论方面并无太大建树。不过,他毕竟开辟了一个可引发后人思致的人格美的世界,后来者大可以在此领域深耕细作,从现有的研究来看,“魏晋风流”的人格世界无疑仍是学者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当然,也有学者也在尝试探索其他历史时期的文化或政治名人,通过考察具体历史境遇中的人物行谊以彰显其人格美。这样,王侯将相、贩夫走卒、仁人志士、才子佳丽,也都相继进入其视野。这种研究可以视作文学赏鉴的变种,然而系统的理论建构则仍然付诸阙如。
事实上,一般是在文学作品(尤其是抒情类和叙事类)中,人格之美才能得到透彻集中地呈现,但这种呈现只是一种感性的、具体的方式,即使对人格的情感、意欲以及生存状态进行了细致入微地刻画,并形成了所谓的典型形象,但毕竟不是以一种理论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此外,在与之相应的文学批评鉴赏中,“人格美”几乎是一个用滥了的词语,但论者多是“拿来主义”,在还未对何谓“人格美”作出清晰界定的情况下便直接使用。实际上,他们基本上是将“人格美”等同于人物形象、人格魅力,尤其是人的道德品质,并运用此概念去评价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人物,或借此窥视创作者的精神世界。从“人格美”的意涵上来讲,这也是其题中应有之义,但毕竟并没有在理论上建构出完整的“人格美学”体系。近年来,在文艺理论界及美学界,学者们也注意到这一问题,有人痛感于美学中“人”的缺席,提出了“审美向人回归”的口号,尝试建构人生论美学体系[8](P2837)。也有学者意识到“人的美学”理论建构的诸多不足,在不同程度上主张回归传统,从已有的经典著作和思想家中汲取可借鉴于当下的资源,例如,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占据主流的儒家。
儒家对人格美学的认识上,《孟子·尽心下》说:“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此言道出了人格美的生成逻辑。所谓“可欲”者,自然是人们所认可为“好”者,亦即“价值”。人们在切实的生存践履过程中,将此价值尽可能充分地实现于其所接洽的世人和世事之中,这便臻促了人格美的生成。然而,孟子更多地是从内在心性价值层面去体悟,而对外在境遇缺乏足够的关注,他对价值的理解也更偏重于纯粹道德性的一面。因此,新的人格美学的建构,便有必要从上述两个方面再加以充实,既尽力使养润人的基本价值需求得以实现,也要尽可能地描述在不同境遇下人的通权达变的多样抉择,这样才能使得人格美学的建构既虚灵而又笃真,既普遍而又具体。在这方面,《周易》经传恰恰可以补足这些缺失。可惜的是,长期以来《周易》人格美学的研究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三、《周易》人格美学研究的现状与未来
作为中华文化的元典,《周易》的主旨即在于“究天人之际”,人的趋吉避凶、求福免祸以及迁善改过、穷理尽性而至于天之所命,是它永恒的主题,故而人的美善问题不能不进入其的视野。诚然,《周易》中并无“人格”这一概念,甚至也无系统的美学思想,但在《周易》这部“忧患之书”中却隐藏着不少人格修养的方法,这些方法以性情的涵养为核心,以礼乐的调节、律法的规范为具体手段,辅之以风气的陶冶、典范的感化,以与天地相融通、与时节相合拍为最终境界。它致力于使内在心性和外在秩序都达到最大的和谐,这种和谐是动态的和谐,而非静态的;是在时间的无穷历程中都追求的,而不是一劳永逸、一成永成的。如此成就的人格,在伦理意义上为善的,在审美意义上为美的。对于人格审美而言,这是真正的美善和谐之途。
其实,在既往的《周易》美学研究中,已有不少前辈学者或多或少对《周易》人格美学的问题都有所触及。刘纲纪的《〈周易〉美学》一书,应该是最早对《周易》美学思想做出全面系统研究的著作。此书经过缜密扎实的考证,厘清了《周易》中与美学相关的观念,并从天地、阴阳、文、象数四个方面探讨了其与美学的关系。在具体美学问题探讨方面,涌现了诸多颇具启发性的提法,如《周易》的生命美学、《周易》中的“观象制器”与古代技术美学。而《周易》中一些本来不属于美学范畴,但含有美学意蕴的概念,如“太和”“阳刚与阴柔”“变化”“交感”“文”“卦象”等也都作了美学的引申和阐发。就刘先生所界定的“美学”领域来看,虽然也有论及自然美学,但主要还是侧重于《周易》与文艺美学思想的关系。倘追本溯源, 《周易》中谈及“美”,原是作为人格典范的“君子之美”。此外,所谓“阳刚与阴柔”原非指作品风格,而是指事物的两种相对偶的性质,后又引申到人的道德品性。而“交感”在起初是指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至于“文”自然包括了“物相杂”之谓,其所谓“天文”主要是指天之日往月来、星移斗转、春秋迁移、昼夜改换,而所谓“人文”则指人之习俗、典章、礼法、制度等,原非狭义的文艺作品。既是探讨《周易》美学,却不重视“人”的美学,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当然,刘先生也认为,“就美学而论,生命之美的观念在《周易》中是居于主导地位的。这是《周易》美学最重要的特色,也是它的最重要的贡献”[9](P69)。可惜这包蕴了人的生命在内的美学,在《周易》之中又是如何得以具体展现出来的,该书并未花费太多篇幅论述。其后他与范明华合著的《易学与美学》延续了此一立场,进而探讨易学美学原理在工艺、建筑、书法、绘画、文学、音乐、舞蹈等领域的应用,尽管论域相较之前有了大规模拓展,却仍未及于“人格美学”。
王振复立足于文化人类学立场,对《周易》的美学智慧进行了尽可能周全的探究,并辟专章探讨《周易》中“人格美学智慧的超越”。他注意到了蕴含于《周易》中关于人格的丰富思想,认为这些思想“无疑具有强烈的伦理色彩,却也典型地体现出中华古代伦理学与美学互相包容、统摄的特点……是美的伦理学或伦理的美学,也是关于求善兼审美的人学、人格学”[10](P367)。此说当然是极富洞见的。然而,在王先生看来,《周易》中所谓“人”,并非指一般普通人,而主要是“巫”和“圣”两种,《易经》卦爻辞所呈现的是前者,而《易传》(王先生称为“《周易》辅文”)呈现的主要是后者。“《周易》的人格审美智慧,是在从《周易》本文到辅文、从巫到圣的文化转型中形成的。”[10](P367)衡之以《周易》文本的实际情况,其说有欠妥当。《易经》中“巫”只出现于一处,《巽》九二“巽在床下,用史巫纷若,吉,无咎”。而且,这里的“巫”也是就其作为神职人员的身份来命名的,并非某种人格类型。而在《易传》之中,固然出现了大量论述“圣人”处,但就其数量来看,除了《系辞》之外,在《大象》《小象》《彖传》及《文言》中,都远不如“君子”。此外,《易传》中还出现了多处与“君子”并列的“仁人”“贤人”以及对举的“民”“众”“百姓”“小人”等称谓,亦不应说与普通人无关,这些都需要纳入人格美学的框架中,作出尽可能准确地分析和厘定。
张锡坤等人所著《〈周易〉经传美学通论》是近年来研究《周易》美学思想的一部厚重之作,该书出于对百年易学中经传分观的不满,提出从“经传贯通”方法对二者中所蕴含的美学观念进行整合式的理解。该书除了探讨前人业已述及的《周易》美学的精髓如生命、象数、交感之美,亦探讨了他人甚少置喙的审美观照方法以及忧患意识与中国诗学的“以悲为美”观念。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此书集中论述了“含章”与“明”所具的审美意蕴。在探讨“含章”之美时,其亦论及《周易》中的理想人格,但不占太大比重。而且,他们认为:“《易经》的美学意蕴应该定位为坤地含章之美……含章之美也代表着人格之美的最高境界。”[11](P61)此说不敢苟同。《坤·文言》释六五“黄裳元吉”时,的确呈示了“美之至也”的“君子”,但《乾·文言》释九五“飞龙在天”时,更呈示了与天地、日月、四时、鬼神均相合无碍的“大人”。另外,其释上九“亢龙有悔”也呈示了“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的“圣人”,这两者境界均是高于“君子”的。就《周易》中乾坤两卦关系来看,虽曰乾坤并建,但《乾》为阳刚健动,《坤》为阴柔巽顺,《乾》居于主导创始地位,而《坤》则居于顺从终成地位。因此,《周易》中的理想人格境界,不能说是仅体现于《坤》卦之中,必须将其置于与天地共生的宏阔格局中,才能得到谛当的认识。
通过以上考察可以发现,总体上前辈学者的研究都颇具开创意义,但因其并未完全从人格美学的立场出发去对《周易》进行探讨,故虽有触及,不免有浅尝辄止之憾。正是基于这种考察,文章认为,对《周易》作人格美学的研究与审视,不仅有其必要性,而且在理论上是可行的,有着较为广阔的开拓空间。《周易》一书通过卦象的排列、爻位的变化,深入地展示了人生在世“价值”与“境遇”之间丰富复杂的辩证关系,从而提升了人格完善、境界升华以至天地太和的广大愿景,在此种意义上,甚至可以把《周易》看作一部人格美学的经典著作。针对《周易》的人格美学的研究,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尝试从价值哲学的视角出发,结合康德的美学、伦理学思想,以人的虚灵而真切的价值认取及其见之于境遇的笃实而又灵动的践履作为人格美学的核心,并进而探讨《周易》所呈现的变动不居的世界之中,人是如何将种种价值理念融摄于具体的境遇,从而以其独特的践履方式铸就了阴阳合德、刚柔并济的人格类型,这些人格类型又是如何可以从美学的角度予以审视。通过这些方面的探讨,庶几可以建立较为整全的人格美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