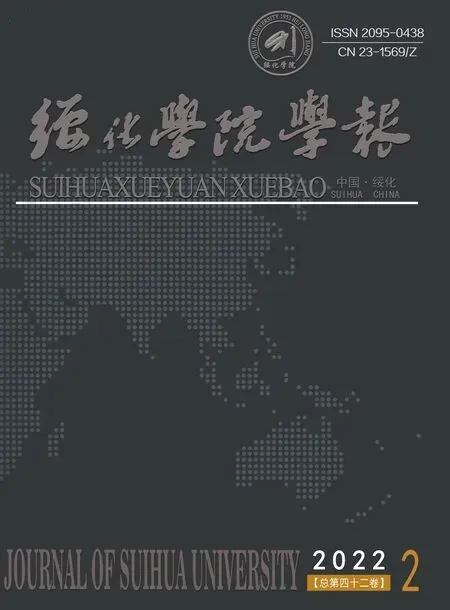宋代田产交易“先问亲邻”规则适用纠纷浅析
艾萌萌 张丽霞
(郑州大学法学院 河南郑州 450000)
一、田宅交易“先问亲邻”规则的制度设计
“先问亲邻”指的是在田产交易过程中,顺次先后取问亲邻是否有购买意愿,同等条件下,亲邻具有优先权。若亲邻均无购买意愿,业主方可与他人交易。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优先权,指的是顺位上优先,而与购买价格无关。若亲邻与第三人出价相当,则亲邻具有优先权,若第三人出价高于亲邻,那么业主可根据“房亲着价不尽,亦任就得价高处交易”规则,选择出价更高的买主进行交易。
“先问亲邻”最早出现在唐代中后期的民间契约中,如唐乾宁四年“敦煌张义全卖宅舍契”中,提到“先问亲邻”的内容:“其舍一买已后,……已仰旧舍主,不买舍人之事。”[1](P227)五代后周时期,先问亲邻制度在法律层面出现,“如有典卖庄宅,准例房亲、邻人合得承当,若是亲邻不要及著价不及,方得别处商量……。”[2](P2312)《宋刑统》:“应典卖,倚当物业,先问房亲,房亲不要,次问四邻,四邻不要,他人并得交易。”[3](P207)尤其在南宋时期对亲邻法的解释更为周密详实,这一时期的律令规定行使亲邻优先权的主体是既亲又邻,而不是以往的“亲”或“邻”。元朝时期,对亲邻的范围进一步作出限定:“应问邻者,止问本宗有服亲及墓田相去百户内与所断田宅接者……”[4](P47)该律令进一步缩小了行使亲邻权的主体范围,对那些因贫困急于出售房屋的业主大有裨益。明清时期先问亲邻直接在律典层面消失,清朝的司法实践中也否定这项权利,在《光绪会典事例》中甚至出现了政府直接干预,禁止行使“先问亲邻”权的规定,认为这项权利损害了卖方的利益。但该制度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已经在民间成为约定俗成的固定模式,因此明清时期先问亲邻制度仍广泛存在于民间田宅交易中。
先问亲邻规则的行使方式是“以账取问”,以书面的形式向亲邻人询问是否行使该权利,若亲邻人无意购买,则需及时批退。该权利的存续期间为三天,超过三天,不得再行使。《元典章》记载:“令文:“……若不愿者,限三日批退,愿者限五日批价。”[5](P313)亲邻权受到侵害之后诉讼于官府的时间也是受到限制的,亲邻请求官府救济的时间应在自典卖田宅之日起三年之内。后期又有官僚谏言,认为三年时间太长,引发的诉讼过多,建议缩短为一年。[6](P7471)整体而言,各朝律令对讼于官府的时限规定呈现缩短趋势。
“先问亲邻”规则的设立,恰恰反映了古代中国重视血缘关系,维系地缘关系,避免宗族财产外流的这种传统宗法思想,如南宋法官范西堂所言:“……墓田之于亲邻两项,俱为当问,然以亲邻者,其意在产业,以墓田者,其意在祖宗。”[7](P37)该规则能维护亲邻间的和谐关系,最大限度地减少交易风险,有利于田宅的方便管理以及经济效益的提高,敬祖保宗的宗族伦理和对财产便于管理这两个角度,是先问亲邻制度持续存在的生命之源。
二、田宅交易“先问亲邻”规则的适用纠纷
(一)因不问亲邻而引发的诉讼。先问亲邻规则自五代时期正式入律以来,就作为田产交易程序的第一个环节而存在。亲邻人明确放弃先买权,在问账薄上着押签字为证,业主方可与亲邻人以外的第三人进行交易。然而在实践中,由于与“邻里骨肉,不相和协”[8](P5901-5903),从而不问亲邻擅自与他人交易的业主不在少数。此外,民间为了规避田产交易向国家缴纳的土地交易税,而故意不办理手续,避开亲邻人,私下交易,最终因违反“先问亲邻”规则引发争端,诉讼于官府。
《清明集》中“吕文定诉吕宾占据田产”一案,弟文先死后,无子嗣。兄文定讼于官府,状告叔父吕宾占据田产。经判官审理发现,涉案田产是文先于嘉定十二年典卖吕宾,嘉定十三年八月进行投税印契,事实清楚,程序正当。但是依据宋律堂叔吕宾却不能合法拥有该田产。因吕文先在典卖田产时,未曾公开取问亲邻,吕文定未进行批退以放弃亲邻权,官府最终判决田产收赎为业主所有,交易无效。此案的判决结果反映,交易中规避先问程序交易的,其交易无效,双方各自返还财产,这一规定,与现代合同法中确认买卖合同无效的处理方式完全一致。
(二)因未尽问亲邻引发的诉讼。宋太宗雍熙三年二月下诏,典卖产业时,“据全业所至之邻皆须一一遍问,侯四邻不要,方得与外人交易”[8](P5901-5903)。这表明在典卖田产时应将所有“房亲”“四邻”遍问,如果在同等条件下所有亲邻主动放弃权利,方可与第三人交易。《五代会要》与《宋刑统》都仅仅是规定了亲邻人享有的先买权,但是对哪些人属于“房亲”的范畴?哪些人又属于“四邻”的范畴未做出进一步的规定。据《清明集》记载:“诸典、卖田宅,四邻所至有本宗缌麻以上亲者,以账取问。”[9](P308-309)根据相关判词可以得出,宋时的“房亲”指同宗族缌麻以上的亲。“四邻”的范围受到的限制较“房亲”更多,享有亲邻权的“四邻”必须同时满足多个条件才可,首先必须带有一定的亲属关系,即与业主属于缌麻以上亲属或者墓地相毗邻的地邻关系,其次,邻人应毗邻典卖的田产,且田产之间无河道、公路等阻断连接。
遍问亲邻的正规做法也是“以账取问”,逐个询问适格亲邻人是否有购买愿意,当所有的亲邻都“着押批退”后,该房产方可与外人交易。若有人未在账上批退,则代表其要行使亲邻权,同等条件下,该人就具有优先购买权,这一权利若遭到侵犯,就会诉至官府,产生纠纷。
《清明集》“执同分赎屋地”[7](P111)一案中,毛永成诉毛汝良将田产典卖与陈潜,应无效。毛汝良承认,当时交易这些土地田产时,没有向享有亲邻权的毛永成询问,也未让其在写有亲属名字的账上批退,判决结果是毛永成原价赎回已交易田产,这一判决显示未尽问亲邻,仍然导致双方买卖合同无效这一结果。
(三)因问亲邻的执赎期限而引发的诉讼。《五代会要》等律令未对亲邻人行使先买权进行期限的规定,宋代官员敏锐地察觉到先问亲邻这一规则对于那些贫困伤病等急于出售的业主极其不利,提出“限日以节其迟”[4](P48)。据《清明集》记载:“诸典、卖田宅满三年,而诉以应问邻而不问邻者,不得受理。”[9](P309)也就是说,亲邻权超出一定的期限,权利就归于消灭,官府也就不再保护这项权利的行使。据《清明集》记载,宝庆元年间,余焱状告黄子真未经批退程序,就购买了其叔父余德庆的田产,并引亲邻之法请求官府允许他回赎田产。官府审判之后认为余焱与余德庆属于是缌麻以上亲属,且陈诉之日距离典卖之日未超过三年期,不管是在主体上还是诉讼时效上均符合相关亲邻之法的规定,遂判决允许余焱回赎其叔的田产,即叔父余德庆与黄子真的买卖合同无效,双方各自返还财产,再次典卖之际需按照符合亲邻之法的程序进行。
关于亲邻权的诉讼时效,纵观而论,每个朝代的法令均逐渐缩短了诉讼期限。宋绍兴二年就有官僚谏言:“依绍兴令,三年以上,并听离革。又缘日限太宽,引惹词诉,请降圣旨,并限一年内陈诉。”[6](P7471)元代,时限缩为百日,“业主虚抬高价,……,仍听亲邻典主百日收赎。”[10](P487)先问亲邻的时效从三年减为一年,又从一年缩为百日的主要原因是,该制度随着不断的发展演化与实践应用,其弊端越来越明显,需要对时限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来减少诉讼案件的增加,同时这个规定也能加快田产的流转,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增加赋税。还有一类是亲邻人在业主典卖房屋之际“批退”时间的缩短,由五日缩短为三日,后文“亲邻人利用先问亲邻规则压价”一部分会详。
(四)因伪造证据问亲邻而引发的诉讼。宋人在田宅交易中存在通过伪造契约文书来规避亲邻的现象,在两宋史料记载中常有发生。太宗八年,开封府赵孚就曾言:“庄宅多有争讼,皆由衷私妄写文契,……,狱讼增益。”田宅交易极易引发诉讼,主要原因是欺骗邻居,伪造契约,私下交易,导致诉讼案件日益增多。这种不规范的交易使诉讼增加,也会导致税收流失,所以建议政府应该制定产权交易的标本,在全国实行。以此来防范虚假的契约文书,从而减少此类官司的出现。
太子中舍牛昭俭言谈及自己处理的亲邻争讼案时说:“……虚构词讼。其上件契,并行毁抹。所争物业,各有结断……”[6](P5902)根据法律规定,典卖田宅时,如果当初交易之时,没有亲邻着押批退的文契,给百日期限供认罪行的予以免罪,只收取若干的抽贯税。牛昭俭自天圣四年十月到任,处理的诉讼事务,争夺田产的十余件,大多都是属于造伪文契所引发的纠纷,他同时发现民间手中的契约文书又多为伪造,邻里乡亲之间不相互和睦协助,暗自交易,虚抬价格。争论出现时,拿出很久以前的文书,等朝廷颁布法律,将超出时限的契书送去税务那官印的契书作为凭证,官府将其作为依据,临时判断,很难区分真伪。这反映了当时在田宅交易中业主恶意伪造契约、虚构讼词、私相交易的情形,不仅加大了审理难度,而且会造成曲直不分的状况。前文吕文定吕文先一案,未问亲邻而仍能办理交割,应为伪造了相关批退文书。遗憾的是未能找到官府对这种情形的裁断,无法窥知违法的处理结果。
(五)业主滥用亲邻优先规则而引发的诉讼。在宋代涉及亲邻权相关的诉讼中,有一类是业主将土地卖出后,田产的价格比卖出时有所上涨,业主便谎称有亲邻未行使批退,意图赎回已典卖的田产,由此而引发的诉讼,此种又称“妄执亲邻”,这种情形显然源于违反亲邻规则导致交易无效,是业主对这一规则的滥用。南宋高宗绍兴二年四月户部言:“迩来田价增高于往昔,其卖、典之人,往往妄称亲邻及墓田邻不曾批退;……引惹词讼。”[8](P6601)田价比以往的高的时候,典卖业主往往谎称典卖田产时亲邻或墓田邻未着押批退,主张典卖无效,赎回田产,再高价转卖与他人,由此引发诉讼。另高宗绍兴二年八月臣僚又上言:“近年以来米价既高,田价亦贵,遂有诈妄陈诉,或经五、七年后称有房亲、墓园邻至,不曾批退。……引惹词诉。”[8](P5905)这两段谏言可看出,当时利用亲邻法部分漏洞以达到占据田产的现象颇多,导致诉讼于官府的案件增加。
《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妄执亲邻”一案,陈子万与杨世荣合谋,利用亲邻之法的漏洞,取赎30年前出卖给陈定僧父亲的田产,被判“妄执亲邻”。杨世荣资助陈子万赎回田产,同时又唆使陈子万行使亲邻权,助纣为虐,同样是罪恶深重,判将田产还于定僧,陈子万与杨世荣各杖责一百。该判决体现了判官使用情法并用的审判方法,并且可知违反亲邻规则,不仅仅是交易取消,归还田产,还可能会受到刑罚处罚。
(六)亲邻人滥用亲邻优先规则而引发的诉讼。还有一类事后置业指的是业主所典卖土地与自己后置的土地相邻,这种情况不能行使亲邻赎回权,否则也属“妄执亲邻”。但需稍作区分,这种情形是亲邻人(事后)行使权利所引发的纠纷。《清明集》中“干照不当”一案中说道:“知县谓徐六三得产之后,吴元昶方买邻地,又起屋在上,所不应退。”[7](P17)县尉认为吴元昶的土地与徐六三的土地毗邻,判令徐六三按照亲邻之法收回交易费用退还所买土地。知县认为徐六三购得土地之后,吴元昶才买得邻地,然后在上面建造房屋,所以徐六三不应该退回土地。显然知县说法在理,判决结果是官府监督吴元昶秉公对照核准土地交易款项,索取双方契约呈报监司、知州照会。这也说明法律不支持事后置业者主张亲邻之法,这一案件说明官府援理入法,虽然法律规定存在缺陷,但是根据公理道理,吴元昶的做法都得不到支持,也说明官府开始关注亲邻人何时成为有效的权利人这一时间节点的问题,法律制度通过实践逐渐趋于完善,在处理具体个案时不断地弥补法律漏洞。
(七)因利用亲邻优先规则压价而引发的诉讼。先问亲邻以程序性规则来保障优先购买权行使,但不免有无良之人利用此规则谋取私利,其中压价购买即为一种典型行为。亲邻在行使优先购买权时,通常压低价格,而业主则抬高价格,双方就价格达不成一致,亲邻又基于这一身份主体意图行使优先权,从而引发诉讼。《宋刑统·户婚律》规定:……房亲著价不尽,亦任就得价高处交易。[3](P207)法律规定如果房亲给的价格不合理,业主也可以与第三人交易房产,但是如果业主、牙人勾结第三人弄虚作假,虚抬价格,则根据所欺瞒的金额等具体情况进行论处。
在现实交易中,有一些业主,或是生活困难或是病魔缠身等现实原因,急于出售田产,解决燃眉之急。但是亲邻却故意迟迟不进行批退,刻意压低价格,从而导致矛盾丛生。这也是前文讲到亲邻人批退时间从五日减为三日的原因之一。南宋士大夫袁采曾说道:“……不可恃其有亲有邻,及以典至卖,及无人敢买,而扼损其价……。”[12]官府审理业主与房邻因价格无法达成一致,业主意与第三人交易,而房邻又想行使亲邻权的案件时,会在断案时优先考虑业主出卖房产的紧迫性,业主是否虚抬价格,房邻是否恶意延迟,若是房邻恶意延迟,官府不仅不会支持亲邻的优先购买权,甚至会受到刑罚处罚。这种援情入案的审理方式能够很好地弥补法律漏洞,同时情法并用也是法律工作者最高的价值追求。
三、宋代“先问亲邻”规则适用纠纷的解决经验
(一)依法审判。在代表宋代诉讼审判制度发达的《名公书判清明集》的判词中,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依法”“引法”“揆法”“准法”“酌法”“参法”等,故各律、令、格、敕等法律是断案的主要依据。通常而言,田宅纠纷一经诉讼程序,须由县令进行亲自审理。审理事实的过程主要就是对诉讼证据的收集与认定,以便根据事实作出正确的判决。在涉及“先问亲邻”的田产诉讼中,法官首先主要以契约、文书为核心物证,判断契约是否系伪造或有涂改痕迹,核实当事人身份,是否属于当下法律规定的“四邻”“房亲”的范畴;其次是核实交易时间,看田产交易是否超出法定的收赎时间,这些有法律明文规定的纠纷类型,一般都会依法判决。由“先问亲邻”引发的纠纷大多都是由诸多违法行为导致的,比如应问而不问、虽问但未尽问、伪造契约等,这类案件如果案情属实,法官多为依法裁判,比如吕文定诉吕宾占据田产的判决是“听收赎为业,并给断由为据”。正是因吕文先在典卖田产时,作为房邻的吕文定不知情未曾着押批退,所以法官依法判决,该田产收赎为业。从现有存世判决看,依法依律而判的为常态。这种常态也使得宋代先问亲邻的制度体系更严谨。对判例整理可见,第一,不问、问而未尽、捏造批退文书等直接违反先问程序,导致交易无效;第二,业主滥用亲邻规则的,不仅相关交易无效,行为人亦受刑罚处罚;第三,亲邻权人的权利行使也受到限制,不能违反时效,不可事后置业。这些规则极大地丰富了“先问亲邻”制度,也为后世优先购买权制度的设计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援理入法。涉及“先问亲邻”的案件,法官们的审判依据多是“依法判决”“揆之理法”,那么“理”与“法”又有什么关系呢?通常认为,“理”与“法”同属于行为规范。真德秀对“理”和“法”的基本区分是“是非有理,轻重有法”。他认为,“理”的性质和功能是判断行为是非,“法”则是衡量行为轻重。“理”侧重于对事实的价值判断,“法”注重对行为情节的裁量。未署名判例《改契书占据不肯还》有“揆之理法,无一而可”之语。这表明“理”和“法”属于不同的裁判依据。“理”意在论说理据,“法”重在据法判决。无论论说理据,还是据法判决,都离不开说理。说理展示的是理性,容易被人接受。在涉及到“递问亲邻”的纠纷解决时,法官一方面“依法断案”,另一方面则会引入“公理”“天理”可以使断案结果更加让当事人信服,如在“妄执亲邻”一案中,陈子万败光家产很久之后,使用计谋赎回已经卖给陈定僧父亲三十年的田契,并且将案涉的田地卖给杨世荣,还凭借田产契约以亲邻优先权为由赎买陈定僧其他的田产,无耻之极,令人咋舌,法官引入公正天理,结合案情,认为陈子万赎回田产已经时隔一年,赎金未能足额交付,不应当将别人的田产卖给杨世荣,于法于理都所不容,更不应当妄自行使亲邻赎买权,后陈子万与杨国荣各杖责一百,交易款返还杨世荣,田产返还陈定僧,令各人签收领取凭证附入案卷。
“公理”“公法”“天理”“国法”等概念的建构,意在营造安定有序的社会秩序,往往意味着对私欲的抑制。人有圣仁贤愚,就私去公也是趋利避害的本性使然。常情之私与理法之公的冲突和协调是法律史上永恒的话题。他们并不局限于应付政绩考核,而是强调善政和善治,尽量做到寓教于判,兼顾判决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三)援情入案。以《清明集》中所见判词为例,判官们处理的各种案件,特别是民事案件的裁决,大多是兼顾情理和法律的审判方法。在审判中,天理人情也被修改为法律作为审判的依据。情理在中国诉讼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情理法的并用,这种具有强大审判技巧的审理方式能很好地弥补法律漏洞,兼顾情理和法理是法律工作者最高的价值追求。在涉及“先问亲邻”的案件“妄执亲邻”中,杨世荣不该资助陈子万赎回本不该属于他的田产,赔付的钱款本应该由官府没收,但是法官基于“情理”的考虑,认为杨世荣可能存在不知情的情形,将交易钱款返还给了杨世荣。受“无讼”观念的影响,《清明集》书判常以讼事“终凶”为说辞,劝人止息讼争。判中也会经常调解劝和,屈法就情的现象也比较常见,皆为止绝当事人的词讼。为此强调酌情据法,尽量施行酌中之公法,务求“情法两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