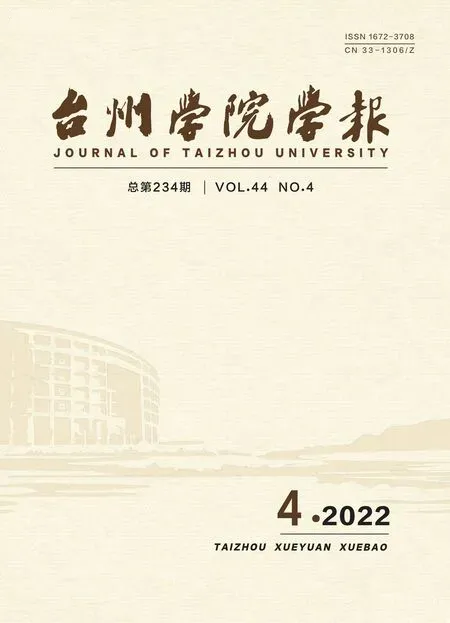塞壬主题阐释的“两种力量”
於悠然
(华东师范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上海 200333)
塞壬是古希腊神话中人首鸟身的邪恶生物,偶尔呈现半人半鱼的形象,它们通过魅惑的歌声诱惑途经的水手,使他们陷入迷狂,使船只触礁沉没。其造型渊源可追溯至公元前2000年,最早的文学形象则出现于《奥德赛》第12卷。此后,托名赫西俄德的《名媛录》交代其身世及数量,欧里庇得斯的《海伦》《希波吕托斯》和残篇,索福克勒斯的残篇,奥维德的《变形记》,许金努斯的《传说集》,阿波罗尼奥斯的《阿尔戈英雄远征记》以及波桑尼阿斯的《希腊风土记》均涉及对塞壬身世、命运的讨论。“塞壬”这一有趣又颇令人费解的形象自古希腊以来一直经历反复的阐释、重塑和改写。
由于塞壬的形象并不存在单一、确定的文本源起,其最重要的元文本《奥德赛》也未涉及过多塞壬的信息,仅在第12卷第52行“塞壬们的歌声”(ἀκoύσῃς Σειρήνoιιν)、第 167 行“塞壬们的海岛”(νῆσoν Σειρήνoιιν)通过双数所有格暗示《奥德赛》出场的塞壬个数为两位。这种模糊性使关于塞壬的自洽解释变得极为困难,也使塞壬形象拥有更多可能性,在广阔的时空中不断被赋予新意。
塞壬的形象之所以有如此宽广的阐释空间,不仅是因为元文本的简洁性与模糊性,也是因为塞壬故事的核心情节是两种力量的持续互动,这使故事结局的到来尽可能被推迟,并在阐释语境中预留了一段不能立即抵达的距离和一种不断摇摆的未完成的可能性,从而给予各个主题以争论的空间。
为佐证这一结论,本文将采用日彻维兹的提法,将有关塞壬的阐释主题粗略分为两类:一为立足塞壬形象的动物性与自然性;二为关注其人文属性[1]20。通过呈现并分析两种路径下塞壬阐释的内在共性,揭示“自然—文化”分类下出现的逻辑缺口,更清楚地解释应当如何理解塞壬主题中的“两种力量”,并恰切地诠释塞壬的形象魅力。
一、自然属性
这一主题的合理性在于,虽然后世神话中,塞壬未被赋予确定的出身,但无论依据何种解释,它都与河神、海神、地母等自然神灵存在亲属关系。《奥德赛》第12卷“白骨”“风平浪静的海面”[2]等意象,也暗示了塞壬形象中浓厚的自然属性。此外,从荷马时期的墓葬艺术可以看出,塞壬与冥世、死亡以及象征自然力的狄奥尼索斯存在密切联系[3]。当它的形象由鸟首人身过渡为人首鸟身、人首鱼身后,它也往往在雕刻绘画作品中披散着茂密的长发,呈现自然、野性、去社会化的特征。根据这一属性,塞壬的形象衍生出两种重要象征意义:女性的和感性的。
实际上,雄性的人头鸟形象在公元前5世纪就从艺术作品中消失了,这一时期的戏剧家、作家、学者如埃皮夏尔姆、埃热西普、帕拉埃法图斯也总将塞壬的魅力理解为女性的肉欲诱惑,而非不可知的魔力。考虑到此时的腓尼基人和希腊人常出海贸易,经年累月不返[4],这样的解释也许暗含对水手朴素的道德劝诫,希望水手们以意志力抵御未知的诱惑,尽早返乡。这一意义上,塞壬歌声的危险性在于对世俗家庭生活和社会秩序的破坏,此处“两种力量的互动”便体现为男性水手回归世俗家庭生活和流连途中的温柔乡之间的矛盾。
这一主题在步入中世纪后被基督教禁欲主义利用并获得宗教意义的诠释。此时,随着厌女文化的扩大,妇女的性诱惑越来越引起神职人员的忧虑,对女性的贬损和妖魔化成为其布道和著作中的标准化术语。塞壬,作为“半动物半人”的混血儿,代表不洁与卑贱,又完美呈现男性屈服于淫欲的惨烈下场——陷入癫狂,不得善终。对基督教来说,这可以恰当地指涉肉欲的危险与可耻。男性教徒潜心苦修、获得精神救赎的愿景与现世生活中切实感受到的女性诱惑之间的矛盾(也是彼岸和此岸之间的矛盾)暗含在这些言辞激烈的痛斥中。
塞壬的女性视角解读在19—20世纪发生转向。在布伦塔诺、海涅、普希金、阿波利奈尔的改写中,他们摒弃了传统解读里塞壬危险、禁忌的部分(实际上也是道德、宗教的部分),以更多笔墨描绘其美丽的外型与悲惨身世,将之置于审美语境中进行观照。但在女性主义解读中,这两类解读都无法令人满意。本质上,塞壬依然是长达千年男性垄断话语下失声的边缘化他者。塞壬的故事仅出现于奥德修斯在费埃克斯宫廷的转述,她从未言说自我,因而任由男性描摹与想象,最终也会归结为两种命运——纯粹性快感的对象(妓女、情妇)或无性的社会连结(妻子、主妇)[5]61-63。
在父权制文化下,男性往往被认为是无性的、公共的、纯精神与文明化的,是灵与肉的统一,而女性则是肉欲的、私语的、感官物质与原始的,是灵与肉的分裂。这样一种包含了等级观和统治逻辑的认识框架同样体现在塞壬的女性主题阐释中。实际上,奥德修斯的意志并没有坚定到可以无视塞壬的诱惑,但他必须确保塞壬的挑逗不会耽搁返乡的航程,影响他荣归故里的正途。因此,与其说这一主题体现的是两性间势均力敌的对抗,不如说只是男性对作为“他者”的女性单方面的“行动”——靠近或疏远、攻伐,而女性只能被牢牢囚禁在“作为意义承担者的角色”[6]563中。这是塞壬阐释中“两种力量”的其中一种互动方式。
(二)感性的。歌声作为塞壬形象最显著的特征,直接作用于水手的感官,引发他们入魔。在传统认知里,感性来自本能驱动,源于人类自然状态下的动物性,作为动物的塞壬极可能通过歌声唤起这些心灵中的“非理性”部分。因此,谈及塞壬的自然属性,音乐和感性也是重要的表现主题。
赫拉克利特曾提过,塞壬凭借美妙的歌声和杰出的音乐天赋来达到诱惑和戕害水手的目的,而这一时期的陶器装饰也出现大量塞壬与笛子、齐特拉琴的搭配。随着基督教正统地位的确立,塞壬的音乐主题常被用以攻击象征宗教异端的世俗音乐。其繁复的表现手法和对听觉愉悦的重视格外为基督教正统所不齿[7]。随着异端文化最终失势,这一主题则扩大为对一切感官愉悦与世俗享乐的批判。这既可以视为基督教正统对作为“他者”的异端文化的警惕与攻讦,也是音乐内容与形式之间,道德和感官愉悦之间尖锐的对立。
音乐净化论也是古希腊由来已久的理论传统,“歌声”又是塞壬最显著的特征,因此,塞壬在哲学中也常作为通过歌声净化灵魂的存在出场: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曾描绘八位塞壬在宇宙的八环发出和谐吟唱的情景[8];普罗克洛斯则进一步阐发,声称塞壬通过在尘世吟唱遥远的歌声,使灵魂自发地脱离世俗[9];而后,莎士比亚曾借仙王奥布朗之口,称海妖的歌声可以“镇静狂暴的怒海”[10]。这一传统并不强调塞壬与奥德修斯间尖锐的对立关系,而是关注歌声使灵魂脱离现世枷锁的神秘力量。在对启蒙理性和现代文明症候的反思中,这一主题也从某种意义上得到复兴:因为科学语言被认为是混沌、浮肿的,而音乐具有超越语言逻辑的直觉式力量,塞壬歌声的危险性被自觉隐匿,正向的精神力量被重新发现,这在乔伊斯、尼采的作品中均能找到证据。这种依靠直觉、感性而非逻辑理性的特点也使基尼亚尔、福斯特将塞壬的歌声重新与自然联系起来,并传达出对“自然成为功能性的他者,人与自然愈发疏远”这一现代文明困局的忧思。
中学阶段的统计该侧重于什么方面?是数理统计还是社会统计?两者无论是方法还是思想都是不同的,不把这个问题弄清楚,统计学的教学就可能不着要点,甚至带来逻辑上的混乱.一线教师不仅应该了解中学教材,更应该读一读大学教材中的相关内容,例如,可以读一读大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相关内容(参见文[2]).
塞壬的音乐主题看似有两类并行的传统,实际上一以贯之的就是塞壬歌声通过感性直观所唤起的原始生命力量与人类社会文化中逐渐成形的规范性、约束性力量之间的矛盾张力。
二、文化属性
随着古希腊宗教光明、理性、秩序、人格化的一面逐渐展露,塞壬身上“半人”的部分也得到更多着墨。它的歌声逐渐成为追求智识与自我反思的表征,成为歌颂人类主体性力量的背景音乐。
《奥德赛》文本中,塞壬曾直接许诺,奥德修斯在听完演唱后将变得无所不知[1]22,赫丽生指出,这源于早期希腊人和闪米特人认知里“妄图像神一样全知很危险”的观念[11]。西塞罗也结合安蒂奥许斯的观点指出塞壬歌声的魅力在于知识的诱惑[12]。与此同时,奥德修斯通过理性的策划,预测塞壬的策略,既内化了塞壬歌声中的知识,又成功保存肉身,这可以视作人类主动运用理智支配感性冲动和自然力量的胜利。
在中世纪早期,塞壬常出场于劝谕性故事,为基督教正名。亚历山大学派的克莱门特主教就曾指出,面对塞壬歌声般的异教智慧,真正的基督徒不应该抗拒接触,而应以虔诚的心,勇敢聆听希腊文化的智慧,并为己所用。但随着宗教统治地位的加固,塞壬的主题逐渐化身为攻击异教文化、异教知识的工具。这样的观念演变同样体现了基督教正统对作为他者的异端文化的单方面“施力”。
因为塞壬的故事出现于奥德修斯的自述,必然建立在对自我的深刻体认上。除了普遍性智识的诱惑,塞壬之歌对“自我反思”的诱导同样受到关注。这一传统源自柏拉图,他认为塞壬的歌声唤起灵魂对知识和自我完善的天然渴求,即德性,使灵魂自发摆脱肉身,进入纯粹的自我反思状态[5]88。这一主题更紧张胶着的版本体现在卡夫卡的论述中,通过展现沉默的塞壬向内自我持存的姿态,揭示奥德修斯胜利的真相——以放弃认识真相为筹码换取侥幸逃脱的机会,卡夫卡揭示了“为了自我保存,最终丧失自我”这一现代文明下的存在危机[13]。在这一视角下,塞壬形象所呈现的悖论,是求知和自我保存,完全屈从于“存在”与保持个人有限意志之间的尖锐关系。
与文学缪斯联系在一起是塞壬形象人文化的另一条路径。这是新柏拉图主义的传统,在彼得拉克的作品中,塞壬多次以缪斯的职能出场,传达出远离虚幻的现世,追求真正神圣和宏大事物的理想。19—20世纪的作家、学者,如马拉美、布朗肖、罗兰·巴特也借助“塞壬”表达文学和艺术上的观点,在这些论断中,我们同样能发现一些共性:马拉美在《礁石》[14]111和《致读者》[14]3中将诗歌同塞壬若即若离的特性联系起来,强调诗歌文本与读者间若远似近的距离[15]。布朗肖则指出作者在处理素材时既需要精密的控制,也需要抹煞自我,如奥德修斯般陷入迷狂,以求写下出乎意料的文字,是作者与文本间充满张力的关系造就了作品的魅力[16]。罗兰·巴特在谈及摄影艺术时,直接引用布朗肖的表述,把摄影艺术的魅力比作塞壬“若有若无的诱惑力”,一方面作品以直观、显在的方式阐述自身,直击观者的心灵深处;另一方面观者无法真正接近和言说影像的内核,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揭示了影像艺术的本质[17]。中国作家格非则用塞壬歌声比喻小说叙事,由此指出小说叙事的魅力在于“既非实质,亦非徒有其表的空壳”[18],通过反复探寻真实与虚构间恰到好处的距离,小说完成了对个体真实生命状态象征性的、抽象的解释。
上述论断尽管聚焦文学艺术研究中的不同话题,但都不约而同地关注塞壬的模糊性、不确定性,以及它和主体心灵间若即若离的动态距离,并由此表现文学艺术神秘的召唤力。塞壬和主体心灵间对立紧张的关系,在这些论断中则不被强调。
三、“自然—文化”:两种力量的互动方式
在前两节中,本文已指出,几乎所有塞壬主题阐释都出现了两种力量的互动:生存与死亡;理性、意志力与感性、欲望;自我保存与求知;自我与他者(包括男性与女性,宗教正统与异端,人与自然);虚构与真实;文学艺术与创作者,文学艺术与读者。
之所以存在这样的共性,可能与阐释的源头——塞壬故事的内在结构有关,本文将借用普罗普故事形态学的方法[19]114-124拆解塞壬故事的基本情节并分析其叙述结构,以更直观地论证上述猜测。
普罗普在《故事形态学》中曾言:“从形态学的角度说,任何一个始于加害行为或缺失、经过中间的一些功能项之后终结于婚礼或其他作为结局的功能项的过程都可以称之为神奇故事。”[19]87“塞壬故事”始于塞壬对主人公的加害行为,结束于主人公顺利经过塞壬岛,符合普氏对“神奇故事”的定义。
根据普氏功能结构,将其情节概括为“主人公的目的—禁令—加害者出场—破禁—加害者消失”。其中,“主人公的目的”对应奥德修斯渴望返乡的情节;“禁令”对应喀尔刻女神告诫奥德修斯“不可倾听塞壬歌唱”的情节;“加害者出场”对应塞壬的出场;“破禁”对应故事高潮,即奥德修斯陷入迷狂,要求水手解开绑缚,而水手充耳不闻;“加害者消失”对应奥德修斯一行人安全经过塞壬岛,塞壬自杀的情节。
在经典的塞壬主题阐释中,“主人公的目的”一般指代符合普世主流要求的正道,如回归世俗家庭生活,过禁欲的基督徒生活,过现代文明生活,自我保存,男性特权的最大化等;“禁令”指代为达成这一目的“不能做何事”的规范性力量,如基督徒不宜接触异端文化、世俗音乐、肉体欲望,不要妄图获得全知,女性不能妨碍男性的“正途”等;“加害者出场”指代社会生活中某种反规定性力量的出现,并强调这种力量如何使人类偏离普世的正道,如异端文化影响信仰的纯洁,世俗音乐引人堕落,女性诱惑影响精神救赎,求知蕴藏于人的天性,音乐能超越语言直击灵魂等;“破禁”指代前文所言两种力量的互动,如理性与感性,男性与女性,自我保存与求知,宗教正统与异端,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加害者消失”指代反规定性力量的陨灭,如世俗音乐被边缘化,女性被驱逐出宗教生活,异端文化被剿灭,音乐传统衰落等。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主题都涉及上述五个功能项,如现代文学艺术主题的阐释就仅仅围绕“加害者出场”和“破禁”两个功能项,讨论艺术作品这一“反规定性力量”的生成性、模糊性、意会性和内在真实性,并由此探讨创作者、读者与作品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一策略暗含了这些主题与前人阐释不同的观点倾向。为说明这一差异,首先需要解释奥德修斯的“破禁”何以是塞壬故事最关键的情节,以至于没有任何一组主题省略了对此的阐释。
在神奇故事中,一个禁令设下,往往意味着即将被打破。当喀尔刻女神警告奥德修斯“倾听塞壬的歌声会带来危险”时,富有经验的读者往往能够预想到主人公必将反复试探禁忌的边缘,这种打破禁令和遵循禁令间紧张的关系,奥德修斯想要聆听歌声又害怕死亡的矛盾,处于破禁边缘时生死双重命运的叠加,不仅就故事本身而言极富张力,也构成了一组适宜被迁移、改写与演绎的神话母题。
而“奥德修斯用蜜蜡塞住水手的耳朵,并命令他们绑住自己”这一设定则让结局的到来尽可能延缓,这不仅使读者持续为之提心吊胆,也使奥德修斯与塞壬之间的关系向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转移,二者的距离仿佛无限趋近(塞壬的歌声已直击奥德修斯的心灵,使之陷入迷狂),又维持在一个安全的边界(奥德修斯的肉身被缚住,与塞壬的物理距离保持稳定),这种动态的、无限趋近又永远不可能被抵达的距离,给学者们预留了可供反复演绎的巨大空间与可能性,繁衍出众多阐释主题。
如前两节所提示的,不同阐释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如何理解这一未定的空间:在传统的解释中,学者们往往预设了一个清晰的由此向彼的线性发展过程,并将这种未定性视作力量转换过程中一个暂时的阶段,塞壬的诱惑只是人类主体性力量战胜自然力量,男性力量征服女性力量,理性力量支配感性力量的宏大叙事中一剂助兴的佐味,衬托和彰显这场战斗的荣光;随着现代时间概念的兴起,学者们逐渐关注塞壬歌声本身,并重视歌唱瞬间的生成性和由此敞开的幽远、深邃的空间,无论是马拉美的比喻“扇子的褶皱”[14]58,还是布朗肖反复言说的文学空间中的至高体验[20],都主张谛听的瞬间有丰厚的内涵,并强调一种类似“得意忘言”的精神状态。因为这种内涵具有非概念性和不可交流性,是逻辑理性无力认识、科学语言无力言说的,所以也常被认为是“空无的”,但正是因为不需要借助逻辑、语言等间接工具,它能够在发生的当下直击奥德修斯的灵魂,抵达理性所无法触及的深刻。这两种对塞壬的认识实际上涉及理解世界方式的差异,前者体现了传统西方形而上学那种线性、进步、外在统一的认识观,后者则是对这一认识观的反思、偏离和逃逸。
以传统西方形而上学的观点看,一直牵引着奥德修斯一行人抵抗各种诱惑的根本目标是保存肉身,返回家乡,与妻儿团聚,重夺属于他们的地位与财产。沿途遭遇的各式冒险,都只是“场景的空间变化”[6]37,重要的是预言中必将实现的“到达”。在奥德修斯理性的精算下,他获得深刻的审美体验,同时安全离开塞壬岛,完成了倾听歌声和确保航行不被中断的平衡。这套阐释中,他对世界的理解和规划,呈现确定、运筹帷幄的姿态,这种姿态正源于对过去、现在、未来的同一性的笃定。诗人塞缪尔·丹尼尔(Samuel Daniel)曾借塞壬之口直言奥德修斯所追求的史诗人生是一种巨大的幻觉。换言之,这种万能理性驱使下的认识方式只是对另一种虚幻,即同一性、必然性的盲目崇拜,而塞壬的引诱正是要使奥德修斯脱离这种发展逻辑并无限期地搁置他的航行。通过揭示瞬间的未定性、不可预测性,现代时间不再被视为由无数瞬间均匀衔接的“线”,而是每个瞬间都在无限生成的“海洋”,正因为此,“到达”不再享有“优先视点”,占据支配地位,而是和每个瞬间平等地被重视。
此外,基于目的论的立场,传统解读中“加害者消失”这一情节总是比力量的对决过程得到更多着墨,阐释者往往倾向通过“塞壬自杀”这样确实的证据,佐证一类力量战胜、支配另一类力量的必然性。在这样的预设下,塞壬阐释的“两种力量”也根本没有进行任何“平等的对决”,只是西方哲学传统中那个不对称的二元模式,即主体对客体、理性对感性、男性对女性、正统对异端、文化对自然的支配关系在起作用,象征自然、女性、异端的塞壬仅被置于边缘他者的位置和贬义的话语策略中,静待奥德修斯的“行动”。通过消解“到达”的优越性和必然性,并重回塞壬歌声的瞬间,这种认识论上的“一分为二”也被“瞬间”组成的“多”打破。正因为此,这套阐释往往仅围绕塞壬歌声本身展开,几乎没有涉及“主人公的目的”“禁令”“加害者消失”的相关要素,目的不再重要,为了达成某一目的“不该做何事”的规范性力量也就不再具有意义了。由此,塞壬阐释中的“两种力量”不再深陷非此即彼的僵局,呈现紧张的对立关系,而是在若即若离的关系中,通过一种未经深思的本能反应来捕捉“瞬间”的可能性与创造性。
上述两类理解中,后者能比前者更恰当地阐释塞壬形象的魅力。这首先是因为前一理解存在根本性不足:它所采用的二元论视角与塞壬形象是相悖的。塞壬是半人半动物的混血儿,本就是自然与文化杂糅的产物,要求塞壬仅扮演二元结构的其中一个范畴而不掺杂对立范畴是极困难的。一方面,塞壬歌声所具备的魔力在人类理解范畴之外,对塞壬的人文主义解释不可能抹煞这一因素,如柏拉图不得不以“追求德性的自然天性”(而非深思熟虑的理性选择)来解释人类对塞壬的臣服;另一方面,塞壬的歌声至少是以人类能够听懂的形式发出的,包含“人化”的因素,其音乐主题阐释有时也兼具自然感性冲动的特征和人类智慧的苦心经营(繁复的指法、花哨的唱腔),塞壬本就是神话想象的产物,对自然属性的阐释自然无法避开文化的观察。在二元论视角下,学者有时不得不刻意忽视塞壬形象所呈现的混沌性和杂糅性。
后一理解的优势既体现在它没有对塞壬或塞壬歌声的象征义做出过于明确的概念化界定,从而尊重了塞壬形象中混沌、杂糅和不可言说的部分,也体现在它重新回归到“歌声”这一塞壬形象最核心的特征,以及人类在聆听瞬间所触及的高峰体验,这能更好地彰显和诠释塞壬那种若隐若现、深不可测的神秘气质和巨大的精神力量。此外,传统二元论习惯将主体与自然分离,但是当象征自然力量的塞壬歌声直击奥德修斯的心灵时,内与外之间并不存在很清晰的固定界限,后一理解能更好地揭示这种浑然一体、模糊不清的瞬间感受。
结 语
从塞壬的原始形象和渊源可以看出,它的自然属性是本质的,而人文色彩则是后天的、派生的,当人类与塞壬相遇时,感性的吸引是天然的、本能的,理性的判断则是反思的、经验的,因此,凭借下意识的本能反应来理解塞壬的歌声能更好地契合它的本质特点,理解和诠释其魅力。但对瞬间性的回归并不是回到原始、野蛮的塞壬形象和人类荒芜的精神状态,而是凭借瞬间的、直觉式体验去超越以逻辑理性的眼光无力认识的、更深刻的存在,是理性对自我的超越。
文章的主要任务不是通过塞壬主题阐释的嬗变来证明“瞬间”“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等现代哲学观点的正确性,而是希望借助主题阐释中“两种力量”这一切口,相对理性和清晰地界定塞壬形象的本质特点,并由此最大限度地挖掘其形象魅力,给塞壬形象的阐释和再书写提供些许提示和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