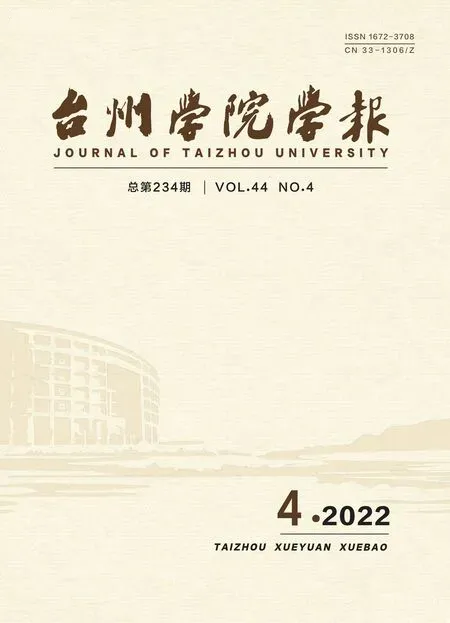《新左岸》杂志与法国颓废派的产生
李国辉
(台州学院 人文学院,浙江 临海 317000)
法国颓废主义的历史,也是文学期刊的更迭史。在颓废主义和随后的象征主义历史上,出现过许多重要的刊物,它们不但是新思潮的策源地,也是宣传和交流的媒介。颓废主义的个别刊物已经引起了关注,比如倡导自由诗和象征的《风行》(La Vogue)。《风行》之外,还有不少重要的杂志被遗忘在历史的角落里。《新左岸》(La Nouvelle Rive gauche)就是其中的代表。创刊于1882年9月,终刊于1886年10月,虽然时断时续,并曾更名为《吕泰斯》(Lu tè ce),但是这个持续长达5年的刊物,正好处在新思潮发生的关键期。它不仅几乎独自守护了颓废文学的萌芽,而且成为颓废派的促成者。多费尔(L é o d'-Orfer)曾指出:“象征主义和颓废的诞生地,是她的床。”[1]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没有《新左岸》及其后继者《吕泰斯》,就没有颓废主义和象征主义。本文尝试以颓废主义思潮史为背景,探察《新左岸》曾发挥的历史作用。
一、颓废理念的传薪者
法国19世纪的颓废文学,虽然在世纪末才真正确立,但是它的种子早在30年代就埋下了。1834年,尼扎尔(D é siré Nisard)曾将古罗马的颓废诗与当时的法国诗比较。古罗马的帝国时期,风俗的“败坏”又继之以精神的“衰落”,于是在文学中造成了对描写的热衷,以及对雕琢风格和模糊措辞的偏好。尼扎尔的结论是,“两个时期共有同样的颓废”[2]。这可能是法国现代文学首次与颓废的概念连在一起。浪漫主义以及随后的诗人、批评家渐渐接受了颓废的概念。工人运动的兴起、政权的动荡,也在道德和文艺上给颓废准备了温床。波德莱尔是随后30年中值得注意的颓废诗人。尽管以唯美主义思想为宗,但是波德莱尔诗中的阴暗形象,以及词语具有的精神迷醉效果,使他成为后来颓废派的先驱。不过,波德莱尔却曾把颓废一词赠给了雨果。他在《1846年的沙龙》中说:“这(雨果)是一位颓废的或者过度的作家,他灵巧运用工具的能力真正让人敬佩和惊奇。”[3]尽管雨果也曾用过这个词,并且是在否定的意义上使用的,但是不妨碍批评家们称他为颓废者。多勒维利(J.Babbey d'Aurevilly),一位几乎在19世纪中后期一直活跃的批评家,看到了雨果浪漫主义的缺陷:“雨果先生,他并不是一位素朴的诗人,旨在创造田园诗,但他毕竟是个诗人,一位并不纯朴的诗人,但过于精巧,完全是一位颓废者。”[4]
尼扎尔提出的颓废概念,就像一个雪球一样滚动着,经过了波德莱尔、多勒维利之手,它似乎并没有越滚越大,但也不至于日渐剥落,而是仍旧前进,等待着历史的机会。这个机会随着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缔造而到来。在工人运动和革命思想高涨的时代,以颓废精神为代表的各种悲观主义成为年轻人反抗共和国的武器。乔治·杜比(Georges Duby)指出:“掌权的共和派没有弄错,他们在悲观主义之中看到的是对现政权的直接批判。”[5]在这种背景下,波德莱尔被招魂,他成为年轻作家们模仿和崇拜的对象,成为颓废文学的“先知”[6]。古罗马颓废文学的新奇、精巧等风格,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这更多是文风自然的变化,但在世纪末的年轻人那里,对反常、病态的美的刻意寻求,不啻为一种时尚。1878年,古尔多(Émile Goudeau)在法国创办了第一个具有颓废色彩的“厌水者(Les Hydropathes)”俱乐部。除了小说家莫泊桑外,它的成员还有布尔热(Paul Bourget)、莫雷亚斯(Jean Mo ré as)。卡恩(Gustave Kahn)和拉弗格(Jules Laforgue)也参加过活动。后面四位将在未来的颓废主义、象征主义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该俱乐部成员混杂,但还是持续了几年,终于在1880年解散。1881年,特雷泽尼克(Lé o T ré zenik)和其他几位成员,创立了“多毛人(Les Hirsutes)”群体,但新的群体两年后就消失了。同时,莫雷亚斯和萨曼(Albert Samain)等人组织了“黑猫(Le Chat-Noir)”俱乐部,并出版了文学周报《黑猫》。文学小杂志在颓废主义时期具有史无前例的作用,它给诗人、批评家提供“相互发现、惺惺相惜的地方”[7],使流派的创立成为可能。《新左岸》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它的创始人是特雷泽尼克。
在19世纪80年代初期,这些群体并不具备真正流派的性质。它们只是一个松散的沙龙,既没有共同的纲领,也没有明确的方向。它们更像是不同风格、不同类型的作家的非正式聚会。拿野猫俱乐部来说,它既有左拉(Émile Zola)、都德(Alphonse Daudet)这些小说家出席,多少推崇自然主义,又有邦维尔(Théodore de Banville)、孟戴斯(Catulle Mend è s)这些巴纳斯派捧场。偏于颓废文学的作家只是其中的部分成员。因而虽然看似热闹,但这些社团只是颓废主义的预备,颓废主义并没有稳定的推动力量。
客观来看,《新左岸》创办之初,对杂志的方向并不清楚。《新左岸》创办的初衷,是让政治上的反对派发声。它也辟出一些版面吸引读者。埃尔泰(Henri Heltey)曾代表这个刊物说:“我们是独立的,不想成为特定的任何人的机关报,而只是我们自己的。”[8]但是特雷泽尼克对新的美学具有很好的鉴赏力,他逐渐发现了一些优秀作者身上的颓废元素。在1883年1月26日的《新左岸》上,特雷泽尼克评论了科佩(François Copp é e),一位在精神上与波德莱尔相近的诗人:“他希望显得被激情压垮了,或者被我们的颓废创造的病态压垮了:厌倦、忧伤、忧郁;他在呻吟中比在努力中找到了更多的魅力。”[9]从波德莱尔开始,疾病的形象成为颓废派文学的基本标识,但他并不像一些批评者说的,是“一种脱离肉体的声音”[10]。相反,肉体在颓废者那里变得更加重要了,诗人必须依靠它来寻找个人的感受。
科佩只是部分显示出特雷泽尼克关注的颓废风格,在另一个作家魏尔伦(Paul Verlaine)那里,一种更为正宗的波德莱尔主义显露出来。魏尔伦出狱后,曾加入过当时的各种社团,他曾在《黑猫》上发表诗作,1883年也参加过“黑猫”组织的文学沙龙。但与兰波(Arthur Rimbaud)的漂泊生活以及狱中服刑,让他几乎在巴黎被遗忘了。就在这不堪的处境中,特雷泽尼克站了出来,为魏尔伦呼吁:“魏尔伦,一位健在的诗人,我们把这个研究献给他。在一个许多人因为一首十四行诗就出名的时代,他在出版五部诗集后还不为人知,那里有许多杰作。”[11]引文可以证明魏尔伦当时边缘诗人的身份。特雷泽尼克对此愤愤不平,他公开称魏尔伦为“大师”。这是法国第一位将桂冠戴在魏尔伦头上的批评家。特雷泽尼克的目的并不只是称颂一位落魄的诗人,他在这位诗人身上发现了富有价值的东西:“魏尔伦是波德莱尔的直接信徒。他从这种危险的范例中得到了他闻所未闻的反常的精致、他的深刻、他的独特性;他有古怪的类比。”[11]可能波德莱尔的光芒在一定程度上遮住了魏尔伦,但“直接信徒”这个用词让魏尔伦成为波德莱尔颓废的继承人,这重塑了魏尔伦的文学声誉,对随后颓废理念的演进也是很关键的。
1883年4月6日,《新左岸》办到第62期时,开始改名为《吕泰斯》。当年8月,波德莱尔的“直接信徒”行动了。魏尔伦在《吕泰斯》上连载了《被诅咒的诗人们》,第一位出场的人物是特里斯坦·科比埃尔(Tristan corbiè re),但真正的重头戏却是兰波。兰波1875年离开法国,放弃了文学事业,但他的作品却意外地进入颓废主义的历史中。这种意外,从文化背景来看,也有其必然性。如果年轻诗人在精神上延续的是巴黎公社时期的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如果波德莱尔是这些年青人共同的灵感,那么兰波得到关注就是一个历史必然。魏尔伦看到成熟期的兰波具有这些价值:“他采用纯真的风格、特别朴素的风格写作,只运用半韵、模糊的词、简单的或者平常的语句。他成就了细腻的奇迹、真正的朦胧,以及因为细腻而产生的近乎无法估量的魅力。”[12]魏尔伦并没有明言这种做法是不是一种未来的艺术,兰波、马拉美以及他自己,分别代表着不同的道路。但是引文中模糊的用词、朦胧的风格,与颓废主义、象征主义的关系是不言而喻的;而半韵的技巧表明兰波摆脱传统诗律的渴望,这又是自由诗诞生的契机。兰波之后,出场的是马拉美,一位当时同样少有人知的诗人。魏尔伦本人没有列入“被诅咒的诗人们”中,但是他就站在他们中间。
这个系列论文的标题,着眼的还是主体精神,也就是波德莱尔使用的概念。魏尔伦并不是纯粹的模仿者,他在思考怎样给这个新群体命名。颓废是一个很不错的词眼。在1884年3月底,魏尔伦指出:“他们的表达手法是平和的,就像有点颓废的青铜艺术品,不过,颓废这个词究竟想说什么?或者彩色大理石的青铜艺术品——打倒虚假的浪漫主义,让纯粹的、顽强的(同样有趣的)诗行永存!”[13]颓废现在被理解为“表达手法”,不是古怪的、反常的手法,而是“平和的”。这里的用词颇费苦心。“被诅咒的诗人们”没有一个是平和持中的,相反,每个人都有反常性。将反常的东西看作是平和的,这意味着一场审美价值的政变,这样就可能确定颓废文学的正统性。
从1883年到1884年,不到两年的时间中,颓废的理念成功地得到了拓展,有了新的涵义,颓废者未来的大师们联袂登场,这恐怕是特雷泽尼克始料不及的。他的《吕泰斯》很快成为颓废主义的策源地。相比之下,同一时期的《黑猫》杂志始终未能在颓废理念的传播上有大的建树。莫泊桑和左拉曾一度成为《黑猫》的总管,办刊的方向也就可想而知。另外,《黑猫》不太关注理论探索,重在发表文学作品,这也把机会留给了《吕泰斯》。《新左岸》《吕泰斯》幸运地成为文学风云的搅动者。
二、颓废派的孵化器
《被诅咒的诗人》的发表,让魏尔伦成为年青诗人的偶像。有学者指出:“如果不是因为这三位,可以想象魏尔伦可能仍旧是一位长期遭到遗忘的巴纳斯诗人,等待着恢复名声。”[14]58尽管魏尔伦加上他谈到的三位诗人,已经有了四位成员,这并不代表颓废派已经成立(尽管魏尔伦后来不断续写《被诅咒的诗人》,但是后来者并未真正得到广泛认可)。科比埃尔1875年就已去世,兰波正在埃塞俄比亚东部探险,去掉这两位过去式的诗人,就只剩下马拉美和他自己。如果没有新的核心成员加入,颓废派只能是空中楼阁。在这关键的时期,莫雷亚斯向魏尔伦走来。
莫雷亚斯原本属于《黑猫》的撰稿人。他的诗作也是先刊登在《黑猫》上。可能是《新左岸》对诗学理念的关注吸引了他,莫里亚斯也加强了与《新左岸》的联系。在1883年5月第68期中,莫雷亚斯发表了《1883年的沙龙》。这篇文章可以看出莫雷亚斯是如何走向颓废文学的。文中指出绘画(画像)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忠实地、严格地、细致地描摹模特的轮廓和体形”,它允许夸张、允许抽象,以便体现“光辉的自然主义”,这种方法其实是左拉的方法;另外一种采用“色彩主义者”的方法,它更强调想象力的作用,“富有空间和梦幻”[15]。人们很容易看到这篇文章背后波德莱尔《1846年的沙龙》的影子。波德莱尔在他的文章中提出了南方艺术和北方艺术的二分法。简言之,莫雷亚斯的第二种做法,与波德莱尔看重的德拉克洛瓦(E.Delacroix)的相似。莫雷亚斯的文章暴露出他和魏尔伦相同的渊源。尽管莫雷亚斯也继承了颓废文学的传统,但在这篇文章中,一切都是不确定的:两种做法都有效,莫雷亚斯未来可以选择任何方向。
魏尔伦和莫雷亚斯亦师亦友的关系,帮助莫雷亚斯剔除第一个选项。斯蒂芬发现1884年莫雷亚斯发表在《吕泰斯》上的文章,已经受到了魏尔伦的影响[14]85。莫雷亚斯在语言和诗歌形式上,越来越显示出颓废者的特征。他在1884年第126期的《吕泰斯》上,发表了《不合律的节奏》(Rythme Boiteux)一诗,诗中说:
因为你苦恼的眼睛的毒药
我也苦恼。
你的大眼睛,绿光闪闪
把我捕到它们的罗网中间。[16]
这里反常的措辞,具有显著的颓废气息。另外,这首诗故意使用不规则的诗行,它比兰波的自由诗还早发表两年。它在象征主义自由诗历史中的地位,一直未得到注意。
莫雷亚斯很快也被打上了颓废者的标签。这是魏尔伦祝圣的三位诗人之外,第一位被认可的颓废者。特雷泽尼克不会放过这个宣传机会,他在1885年6月,专门写了《让·莫雷亚斯》(Jean Mo ré as)的评论文章。文中说:“颓废者们在这种趣味上,把一些文学信仰归功于莫雷亚斯,而莫雷亚斯也不否认。莫雷亚斯因为与他们有联系而名声不好,而颓废者们很乐意把他算成他们的一分子。”[17]这里出现了一个关键的术语“颓废者们”,它代表一个新的不同于“被诅咒的诗人们”的圈子正在形成。这种圈子就是颓废派的基础。
莫雷亚斯并不仅仅是魏尔伦的跟随者,他也对马拉美产生了兴趣。马拉美当时住在巴黎的罗马路87号,一些年轻人开始参加他每周二的晚会,他们没有刊物,也没有社团的名称,但是主要的参与者都是未来颓废主义或者象征主义的骨干。这些人中有象征主义者卡恩和吉尔(Ren é Ghil),也有瓦格纳主义者威泽瓦(Té odor de Wyzewa)和迪雅尔丹(Édouard Dujardin),后面两位后来也是象征主义的主要成员。莫雷亚斯也名列其中。在稍晚的时候,吉尔曾经把以马拉美为主体的诗人看作是一个流派,并表示:“通过象征让梦幻占据主导地位,通过‘词语在意义和声音上交替的锤炼’,让歌唱占据主导地位,这是我们这个流派的愿望。”[18]从这里可以看出莫雷亚斯学到了什么。对象征和梦幻的寻求,让莫雷亚斯渐渐偏离了主题与措辞的颓废,开始在表达手法和风格上着力。这群人的活动,在1884年引起了一家名叫《小北方》(Petit Nord)杂志的注意,它不但将这群人称为“马拉美主义者”,还造出“马拉美主义流派”的词。这个词后来并没有传播开,但是它的出现,说明流派意识正变得越来越自觉。《吕泰斯》希望保持的中立角色也随之陷入危机,《小北方》杂志曾指责道:“马拉美主义者们有一个官方刊物,这叫作《吕泰斯》。您很清楚巴黎非常简单。”[19]
在颓废派的历史上,1885年出现的伪作《衰落》(Les D é liquescences)非常重要。尽管这部诗集原本是恶作剧,目的是用来嘲弄颓废者,但是事与愿违,该诗集竟获得了成功,得到了很多喝彩。《衰落》1885年5月出版,但是诗学史家没有注意到一个现象,早在当年4月26日的《吕泰斯》中,诗集中的三首诗就发表出来了。在《行板》(Andante)一诗中出现了“象征到来了”的诗句[20]。特雷泽尼克似乎将它看作是颓废文学的新进步,而热心地将它们刊出。但很快特雷泽尼克就发现了秘密。尽管如此,他还是把出版的《衰落》的序言发表在《吕泰斯》上。这个序言原本6月28日随着新版的《衰落》问世,但是《吕泰斯》居然能抢在它之前,在6月14日就印出了,足足提前了两个星期。其中的原因可能是特雷泽尼克也加入到这个恶作剧中,他认为这个善意的恶作剧,对颓废文学的发展有利。在同样伪造的序言中,人们看到一个颓废者说出了马拉美的话:“梦幻,梦幻!我的朋友们,我们是为梦幻而着手写诗的!”[21]32这部诗集的作用不是丑化新的颓废主义,而是浓缩它的特点,把它放大给巴黎的读者。
1885年,颓废文学的影响显然扩大了。在当年5月的一篇标题为《颓废者》(Les Decadents)的文章中,人们读到这样的话:“颓废是一种时尚。人们不无偏颇地带着愉快的热情变成颓废者。我认识的一个勇敢的小孩,脸色红润,面颊丰满,正是十六岁的年华,自称自己是绝对的颓废者。”[22]《吕泰斯》给颓废派的成立,准备得还不止这些。一位年轻、有才的诗人身在德国,他注意到了这个刊物的创办,也注意到魏尔伦发表的兰波的文字,并在书信中这样写道:“我在《被诅咒的诗人们》中的几首诗中读兰波,怎么读也读不够。”[23]91这位诗人就是拉弗格。他是《吕泰斯》给颓废主义培养的真正的诗人,也是颓废主义和象征主义年轻人中唯一具有大师地位的人(如果魏尔伦、兰波和马拉美属于早前一代诗人的话)。1885年3月,在第163期的《吕泰斯》上,他发表了两首诗,都出自他的集子《悲歌》(Les Complaintes)。不但如此,《吕泰斯》中的诗歌专栏,还经常出现另外两位年轻诗人的名字。一位是洛朗·塔亚德(Laurent Tailhade),另一位是维涅(Charles Vignier),也是魏尔伦的学生。还有一位叫作雷诺(Ernest Raynaud)的人,也时不时在这个杂志上出现。一时间《吕泰斯》可谓群贤毕至。可以说,除了瓦格纳主义者之外,《吕泰斯》几乎聚集起未来所有的颓废者和象征主义者。魏尔伦的学生们和马拉美主义者们,再加上拉弗格、塔亚德等人,好像一起听到了洪亮的号角,前来迎接新诗歌时代的到来。
三、颓废派的诞生
《吕泰斯》与一群颓废诗人的关系,被批评家注意到了。《时报》的记者布尔德(Paul Bourde)对颓废者没有好感,他在《颓废诗人》(Les Poètes d é cadents)一文中指责这个流派:“它道德面孔上的特征是对大众表露出的厌恶,大众被看作是极其愚蠢和平庸的。诗人为了寻求珍贵的、罕见的和微妙的东西而离群索居。”[24]这种批评是取笑颓废者们的主体精神。文学风格的反常特征,也得到了该批评家的注意,颓废者的诗作中充斥着“公墓、棺材、坟墓”之类的形象,他们还喜欢用“罕见的节奏和翻新的语言”[24]。总之,一切都是病态的、丑恶的、奇怪的。就像《衰落》这部恶作剧最终适得其反,推动了颓废主义的传播一样,布尔德的批评文章,反而在大众中确立了颓废派的诞生。因而布尔德无意中对颓废者们做了两件好事。第一件是他第一次称这群人为流派。在之前的一些散见的文章中,“颓废者们”使用得非常多。颓废者们是一个泛称,“厌水俱乐部”解散后,巴黎就有一个不成功的社团,名字就叫颓废者。颓废派是一个特称,它指的是人员确定、多在《吕泰斯》上活动的诗人群。布尔德在谈到马拉美时曾指出:“马拉美不仅遇到了理解他的读者,而且他还找到了更加狂热的崇拜者,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的崇拜对象要难以理解得多。”[24]这里“更加狂热的崇拜者”指的就是特雷泽尼克和他的《吕泰斯》。这一点特雷泽尼克非常清楚,他在第193期的《吕泰斯》上作出回应,指出:“假如布尔德先生很了解实情,在《吕泰斯》上人们并不狂热。”[25]布尔德也毫不退让,他在来信中告诉特雷泽尼克,可能特雷泽尼克不喜欢马拉美,但是他的刊物却不是这样:“我并未谈论《吕泰斯》的文学观点,我谈论的是它的编辑部表明的文学观点。您不喜欢马拉美先生,这是我们共同的审美能力;但是所有你的撰稿人并不如此。”[25]两人的争论充分说明了颓废派与《吕泰斯》的紧密关系。
第二件事是列出了颓废派的成员名单。魏尔伦虽然列出过名单,而且后来增加了新的成员,但是他的名单是虚的。他的文章的价值,在于确立一种新的风气。从1883年以来,这两三年的时间中,没有真正的名单出现。布尔德的文章解决了这个问题。被他列入讨伐名单的,共有六人,前三位是魏尔伦、马拉美和莫雷亚斯,都是《吕泰斯》推出的名家,后面二位是塔亚德和维涅,也是《吕泰斯》的撰稿人。最后一位是莫里斯(Charles Morice),他曾在《新左岸》上最早发表魏尔伦的评论,是魏尔伦的朋友。这六个成员缺少了拉弗格。拉弗格认为未被布尔德当众批评是一件很遗憾的事,他在信中曾说:“今天的《时报》上有布尔德论颓废者的一篇重要文章,没有提到我的名字。”[23]124
针对布尔德的批评,特雷泽尼克避重就轻,竭力为《吕泰斯》洗清“罪责”,认为颓废派的产生要怪就怪像魏尔伦这类人,他们高兴写什么就写什么,与杂志无关。明眼人知道保护好杂志,就能维护颓废派。特雷泽尼克用心良苦。莫雷亚斯像拉弗格一样,也看到了这篇文章,毕竟他坐上了第三把交椅。莫雷亚斯称布尔德为颓废派第一位“严肃的批评家”[26]。他包容而又讲原则地回应了布尔德。他向布尔德保证,颓废派并不是一群凶神恶煞:“让布尔德先生放心,颓废派诗人不想多亲吗啡女神苍白的嘴唇;他们还没有吃掉带血的胎儿;他们更愿意用带脚玻璃杯喝水,而非用他们祖母的头颅,他们也习惯于在冬天阴暗的夜晚写作,而非与恶魔往来。”[26]莫雷亚斯还为颓废派的晦涩和解放诗律辩护,但这篇文章更大的意义,却在于用象征来解释颓废派。莫雷亚斯说:“早在所有人之前,所谓的颓废派作家在他们的艺术中寻找纯粹的观念和永恒的象征。”[26]这一句话已经显露莫雷亚斯想创立象征主义流派的心迹。虽然他的《象征主义》宣言在次年的9月,方才得以刊发,但是他1885年8月的这篇文章,已经预示了象征主义与颓废主义的分裂。
尽管莫雷亚斯当时还不动声色,而且他还没有使用象征主义一词,但是一位叫卡泽(Robert Caze)的批评者已经注意到了莫雷亚斯的野心,1885年8月《吕泰斯》曾选登过他的一篇文章。卡泽说:“莫雷亚斯先生,在我看来,非常好地定义了这些人们称其为颓废派诗人、他称为象征主义诗人的思想。”[27]卡泽的文章,更为重要的是列出新的颓废者的名单。在讨论特雷泽尼克等编辑人员时,卡泽说:“他们对魏尔伦的节奏、莫雷亚斯(《流沙》的作者)的诗、佩尔福尔(Emile Peyrefort)的田园诗、维涅的散文、阿雅尔贝(Jean Ajalbert)的现代性、塔亚德优美的押韵,甚至是拉弗格先生的谜语给予了热烈的欢迎。”[27]这个名单新加了佩尔福尔和阿雅尔贝,他们都是《吕泰斯》的撰稿人,两人后来淡出颓废派。在这个名单中,拉弗格得到了承认。颓废派的成员又扩大了。
进入新的一年,颓废派仍然在向前迈进,只不过曾经辉煌的《吕泰斯》渐渐丧失了荣光。1886年4月10日,巴朱(Anatole Baju)的杂志《颓废者》(Le D é cadent)创刊。这个杂志最初的支持者是资历尚浅的普莱西(Maurice du Plessys)、奥里埃(G.Albert Aurier)等人,它吸引的主要是普通的年轻作者,比耶特里称它与有名的颓废诗人只有“特别松散的联系”[28]75。但是它很快就争取到了魏尔伦和雷诺,马拉美也偶尔贡献诗作,因而它后来成为颓废派的机关刊物。巴朱不一定有特雷泽尼克的艺术眼光,但他的诗学水平远在特雷泽尼克之上。正是在巴朱那里,颓废派又发展出“颓废主义”的术语,这个术语的意义被解释为:“选择有修养的人物、罕见事件的心理状态、用语的真诚、表达上的无可指责。”[29]这种定义用某些唯美主义的思想改造了魏尔伦、马拉美的美学观。在1886年之前,颓废文学和自然主义在主题和风格上有很多相似性,作家们经常有杂处的情况,但是在巴朱的体系中,颓废主义和自然主义成为完全对立的了。他批评“污秽的”自然主义,强调颓废主义塑造的是“有修养的人物”[29]。这种区分对于巴朱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让颓废派摆脱早期由魏尔伦代表的道路。
1886年4月11日,《颓废者》创刊1天后,另一个颇负盛名的杂志也创刊了。它就是《风行》。它的负责人是卡恩。卡恩1885年参加过马拉美的晚会,热衷颓废派运动。他的《风行》一开始是颓废派的刊物,但是随着瓦格纳主义者威泽瓦、迪雅尔丹等人的加入,再加上志气满满的莫雷亚斯,这个刊物最终变成象征主义者的园地。颓废主义和象征主义的分裂发生在当年9月和10月,莫雷亚斯发表象征主义的宣言文章,并联手卡恩创办了《象征主义者》(Le Symboliste)杂志。这个杂志里,以前不少颓废派诗人未能进入。马拉美的学生吉尔同时又在新创办的杂志《颓废》(La D é cadence)上,提倡所谓的“象征主义和和声学派”,并极力攻击巴朱及其代表的《颓废者》作者群。之前《新左岸》(《吕泰斯》)时期集中而团结的颓废运动宣告结束,颓废主义和象征主义渐渐成为权力斗争的旗帜。
结 语
1886年9月底10月初,《吕泰斯》杂志黯然终刊,退出了历史舞台。《风行》杂志的编辑多费尔敏感地注意到了这个变故,他记载道,“《吕泰斯》小姐刚刚咽下最后一口气”[1]。“战国时代”的到来,不知是否让多费尔感到兴奋。以《风行》等为代表的新刊物,成为新时代的英雄。《吕泰斯》的历史作用,随着它的消失而渐渐被人们遗忘。甚至不少人抱守着后来的颓废主义和象征主义理念,来审视它的办刊水准。巴尔(Andr é Barre)曾经对《吕泰斯》不无鄙夷地说:“它(发表)的诗和散文都不太象征主义”,[30]这种执今以绳古的思维方式,自然不会尊重《新左岸》(《吕泰斯》)的历史价值。这也是今天的颓废主义和象征主义研究不太关注这个杂志的原因。不过,通过历史事实的考古,可以发现,就像后来的杂志是从《新左岸》走出来的,颓废主义和象征主义也是从这个杂志聚集的群体走出来的,《新左岸》在颓废文学的理念上、在流派的活动上确立了颓废派的基本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