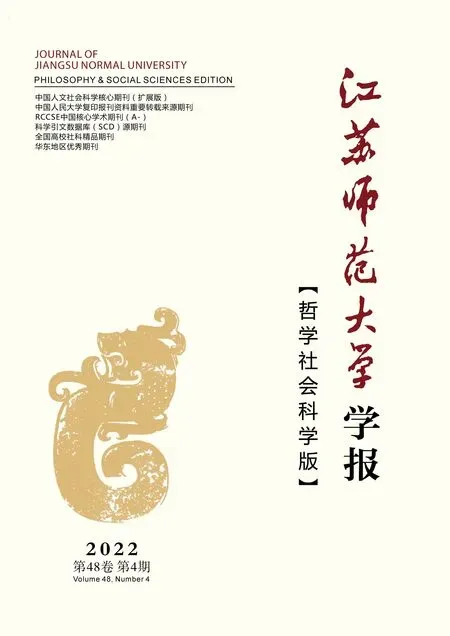文化共情:中国动画电影的跨文化传播策略
俞 睿 周 隽
(南京艺术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13)
在我国发展创意产业的大背景下,我国动漫产业近年来以40%以上的增速发展。艾瑞咨询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的泛二次元用户规模约为3.5亿,有2.19亿为在线动漫用户。截止到2018年底,我国动漫行业的总产值已经突破1500亿元,占中国文娱总产值的24%,2020年我国的动漫产业总产值有望突破2000亿元〔1〕艾瑞咨询:《2018 中国动漫行业研究报告》,2018 年 8 月https://www.iresearch.com.cn/Detail/report?id=3309&isfree=0。。在动漫产业井喷的背景下,我们仍应该看到,现阶段中国动漫的国际竞争力不足,出口动漫规模远不及进口动漫规模,出口发展薄弱,中国动漫公司在全球产业链中仍然承担着发达国家动画代工和外包对象的角色,中国动漫内容生产环节的原创性仍然不足。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动漫在技术、产业结构、发行等方面存在着问题,另外一方面则是因为,中国动漫没有在内容创新、文化传承、国际传播等方面做好准备,这也就造成了中国动画电影在跨文化传播方面未能发挥其文化影响力,也无法通过大众文化的传播方式塑造积极正面的中国形象。那么如何才能发挥中国动画的优势和潜力,加强中国动画电影的跨文化传播效果呢?我们需要通过分析比照找到解决的策略。
相比较而言,美国通过动画电影,成功地输出了一个“富裕、公平、正义、民主、美好、崇尚自由和英雄主义”的美国形象,深入世界各地观众的人心。这种文化价值的输出从某种程度来说并不完全代表美国的现实,但它以动漫的形式“虚构”和“美化”着美国的现实,从而影响了一代人,增强了文化传播力。而日本动漫也以其明快、漂亮、炫酷、世界化等特点在东亚文化圈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力,同时也帮助日本在国际社会树立了积极正面的国际形象。近年来,日本政府推出的“酷日本”战略更帮助日本动漫走向全世界。如2011年6月30日到7月3日,日本在巴黎举办的“JAPAN EXPO”活动,4天时间创下了20万人的来场记录(1)胡静、储静伟、沈靓:《东京:“酷日本”3年前升为国策,动漫游戏电影形成产业链》,《东方早报》,2013年6月5日。。从比照中我们可以看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及其文化在当今世界大行其道,而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的坐标位置还没有最终确立,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与接受度与我国的经济发展程度和综合国力地位不相匹配。因此,中国动画电影更肩负着一种文化使命,即传递中国文化的审美信息和文化价值理念,让世界更多受众理解、欣赏并认同中国文化,从而塑造中国文化的世界形象,打造中国文化影响力。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使得西方世界暴露出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西方式的民主、自由价值理念遭到前所未有的质疑,西方文明的灯塔似乎开始崩塌。在此背景下,如何审视东西方文化的对比和变化,如何审视自身文化在这一变化中所处的位置,以及如何发挥中国文化的影响力是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应该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东西方文化也已经不再是绝对的对立,而是呈现出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因此,包括动画电影在内的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应该是基于世界文化价值趋同和文化共情背景下现代价值理念的传播。从美国动画电影我们也可以看出,它不断融入世界元素,其价值观传播也在发生转向,而中国动画电影中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也在发生融合。因此,中国的动画电影的跨文化传播策略也应该基于追求文化共情背景下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动画电影经典,传承中国文化,做好内容创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打造积极正面的中国形象。
一、文化研究背景下中国动画电影的跨文化传播
纵观目前的世界格局,尽管世界正在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但西方文化对于东方及世界其他文化的包容还非常有限,西方文化霸权依然大行其道,从西方世界对伊斯兰文化根深蒂固的歧视就可见一斑,后殖民派学者萨义德提出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就是指西方人藐视东方文化,并任意虚构“东方文化”的一种偏见性的思维方式。萨义德在上世纪80年代从文化的角度解读了帝国主义的殖民行为,分析了文化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2)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London: Routledge, 1978, p.2.,以及文化如何参与帝国主义事业;而褔轲则将权力与知识的关系的论述引入了文化与帝国主义关系的研究,指出西方文化在本质上是与帝国主义事业“共谋”关系。东西方存在着一种不平等权力关系,这种不平等不仅体现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更体现在文化上。西方以美国为首,形成庞大的全球信息传播体系,以美国好莱坞、迪士尼为主导的影视娱乐体系,目前成为全球化意义生产的主宰者(3)张胜冰、徐向昱、马树华:《世界文化产业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0页。。而在后现代研究基础上的文化研究是对二元对立的拆解,在文化上则表现为:东西方文化之间打破不平等和对立关系,形成交流与沟通和融合,不再有所谓“纯粹”的东方文化或西方文化。东方文化的重建不是建立一个类似于传统西方自我中心式的文化,也不是摧毁一个西方中心后再树立一个东方中心,而是东西方文化的相互融合。1994 年霍米·巴巴在《文化的定位》中提出了著名的“杂交”(Hybridity)理论,他认为杂交属于既非此也非彼的第三空间,杂交文化是一种新的交叉文化(4)Homi K. Bhabha, "Signs Taken For Wonders-questions of Ambivalence and Authority Under a Tree Outside Delhi, May 1817".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1994, p.113.。我们从文化研究背景下学者对东西方文化的发展态势的阐述中不难看出,这种不平等关系正在经历一种转化,这种转化是一种基于文化融合、杂交背景下文化多中心的转化。
在世界多极化发展的今天,文化的多元、共存、融合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强调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的潮流不可逆转。当前,人们正在寻求文化多元背景下的文化共融。在文化多元和文化共融的背景下,中国动画电影的跨文化传播应该是在文化共融背景下寻找文化共情的基础,同时保持文化特色,加强文化传承和内容创新的跨文化传播。动画电影作为一种大众文化产品有其特殊性,其受众范围广,影响力大,不仅影响到青少年群体及部分成年观影群体的世界观、价值观,还能以轻松幽默的形式轻松跨越文化意识形态的鸿沟,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同时,其文化符号的指征性和标识性强,能够很好地代表民族文化的特征,达到塑造文化身份,传播文化影响力的效果。因此,中国动画电影的跨文化传播应该是文化共融背景下打造中国“文化名片”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一种以主体身份积极参与世界文化对话的过程,是在西方话语和本土文化传统之间寻求有机平衡的积极探索,更是不断发展和更新自我的一种文化构建。我们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认真汲取其中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同时,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我们要在不断汲取各种文明养分中丰富和发展中国文化(5)中共中央宣传部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刚要》,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46-148页。。
二、“文化共情”背景下世界动画电影的价值转向
人们一度将文化输出过程中存在的不对等性归结于文化的差异性,认为美国的文化价值观输出是某种形式的文化霸权。然而纵观美国动画近期推出的动画电影,除了将迪士尼的原创动画及对经典进行改编之外,美国动画电影的《功夫熊猫》《寻梦环游记》等影片已经显示出美国动画电影将世界不同地方的文化价值、符号、理念作为其创作的主要元素。而我们从中国近期的动画电影《大鱼海棠》《哪吒之魔童降世》等动画电影也不难看出,中国的动画电影也在寻求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植入现代性价值理念,从而寻求现代社会的普遍认同。因此,东西方文化已经不再是绝对的对立,而是呈现出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如今的文化产品的对外传播应该是基于世界文化价值趋同和文化共情背景下的现代价值理念的传播。中国的动画电影也应该基于世界文化发展的背景,在追求文化共情背景下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动画电影经典。
从上个世纪以来,美国的动画电影成功地传播了美国的主流价值取向,包括王子公主终成眷属式美国梦的实现(《美女与野兽》《阿拉丁》《史瑞克》等)、冒险与个人英雄主义(《冰雪奇缘》《海洋奇缘》《里约大冒险》《蜘蛛侠》《钢铁侠》等),以及对充满美式幽默和轻松、刺激、物质极端富裕的美国生活的刻画(《卑鄙的我(小黄人系列)》《小马宝莉》《芭比公主》等)。
随着全球化过程的推进,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动画电影中加入了越来越多的世界元素。从早期的《花木兰》到后来的三部《功夫熊猫》,再到取材墨西哥文化的《寻梦环游记》,可以看出,在世界文化趋向多元、中国崛起,而美国英雄拯救世界的动画电影已鲜有创新的背景下,动画电影取材世界化、多元化已经成为一种大势所趋,更是美国动画电影主动迎合世界市场及审美趋势的一种转向。从近期的《功夫熊猫》《寻梦环游记》等动画电影可以看出,美国的动画电影开始把视线投向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并从中取材。尤其是从《功夫熊猫》中的三部系列影片,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动画电影不仅选择了“熊猫”和“功夫”这两个文化标识,而且逐渐深入中国文化,将中国哲学、建筑、饮食、民俗等元素都进行了深入挖掘,并将西方人眼中的“典型中国”呈现在了大家面前。从《功夫熊猫》第一部来看,美国动画电影选择了两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标识”:“熊猫”和“功夫”。听到这两个词的世界观众立刻就会将其与中国联系起来,因为这就是大多数不了解中国文化的世界观众所了解的中国。“功夫”片在西方观影群中塑造了东方文化“酷”和“神秘”的一面,同时也折射出后殖民思维背景下的西方观众对中国文化的印象:中国文化是缺乏科技和现代文明支撑的“落后”的“他者”,所谓的“功夫”只不过是唬人的虚张声势和故弄玄虚。将“熊猫”与“功夫”嫁接更增加了西方观众对于“中国功夫”的“奇观想象”,带有很大的戏谑和博眼球的成分。《功夫熊猫》第一部应该说塑造了一个裹着“熊猫”外衣的美国英雄,这与《花木兰》的个人英雄主义一脉相承。然而到了《功夫熊猫》第二部和第三部,美国导演已经开始深入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内核中,向观众传达的是济世救民、和谐共生;刚柔相济、动静结合;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有无相生、修身悟道的中国哲学及处世观念。呈现出美国个人英雄主义和美式幽默与中国哲学“回归自然、寻找本我”的共情和谐。从《寻梦环游记》我们也可以看出,美国动画电影将墨西哥文化中有关亡灵节的习俗融入其中,其中更传达了阴阳往复、生死沟通、家庭价值理念与个人梦想之间的矛盾等价值理念。应该说,《寻梦环游记》中传达的家族理念是与美国崇尚的个人主义与自由理念相矛盾的,然而弥漫在整个影片的却是浓厚的家族亲情和团结,甚至类似于中国文化中对于家庭和集体的崇尚,个人主义最终屈服于家族亲情,亲情之爱最终成为影片最为动人的焦点。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美国的动画电影的取材和世界价值传播已经呈现出一种主动的转向趋势。从一开始的“美国至上”式的绝对优越转向外部世界的价值多元化和文化共情。
作为世界范围内较为成功的案例,美国和日本的动画电影已经展现出全球意识,美国的迪士尼动画和乐园、皮克斯动画、环球影视等电影公司自不必说,日本动画中也有如宫崎骏等动画大师的作品涉及人类命运、科技文明和环境保护等题材。如《风之谷》(1984)《龙猫》(1988)《幽灵公主》(1997)等。日本动漫的大量输出也使得日本的战败国形象等被明快、漂亮、酷等印象所替代,将日本塑造成为“酷日本”(Cool Japan)的形象(6)何德功、周梦:《日本力推“动漫外交”用动漫影响他国民众》,[2006-5-15]http://media.people.com.cn/GB/40606/4372544.html。。日本的经典动画形象也很好地塑造了酷、可爱、机智、平和的国家形象,很好地扭转了日本曾经的战败国形象。从美国和日本动漫取材的世界性来看,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文化产品正在寻求更为广泛的题材,更具有包容性,价值观也更加多元。
三、中国动画电影在“文化共情”背景下的传播策略
在中国动画电影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具有现代意识的作品。1941年,中国第一部动画长片《铁扇公主》成为继美国的《白雪公主》、《小人国》和《木偶奇遇记》之后的第四部大型动画影片,标志着当时中国的动画已经接近世界先进水平。1960年,中国完成了第一部水墨画动画《小蝌蚪找妈妈》;1962年,第一部折纸动画《一棵白菜》完成。新的动画形式的加入,使中国的动画事业也达到了一个顶峰。特别是五六十年代上海美术制片厂制作的《骄傲的将军》《小蝌蚪找妈妈》《大闹天宫》《哪吒闹海》《三个和尚》等影片捧回了几十个国际艺术大奖,铸就了中国动画新的辉煌。《大闹天宫》的灵感来自中国传统神话小说《西游记》,在作画时采用中国传统作画技法,充分展现了中国传统艺术。该片不仅获得了百花奖的殊荣,更是在国际电影节上大放光彩,先后获得伦敦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短片特别奖以及菲格腊达福兹国际电影节评委奖,这些都为中国动画赢得“中国学派”的美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国际动画艺术界因此称誉我国民族动画片为“中国动画学派”。从这些早期的动画电影探索来看,中国的早期动画电影较好地吸取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元素,从中国的经典传说、文学作品、艺术形式中汲取了丰富的养分,成功塑造了中国早期动画电影的民族身份、美学品味和文化标识。
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动画逐渐陷入低谷,国内原创作品缺乏创新。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外国动画开始纷纷进入中国,并占据主流市场,中国动漫逐渐被美、日赶超,动画市场也逐渐被美国、日本等垄断。在现代信息科技不断更新的浪潮下,技术上的落后导致中国动画电影在某种程度上开始朝着“伪国际化”的方向偏离。即开始崇尚模仿西方动画电影,缺少对中国动画电影传统的思考梳理,既没有很好地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从中汲取养分和灵感,更没有结合动画电影的发展趋势对我国动画电影进行现代性创新。1999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推出了史上投资最大的一部商业动画长片《宝莲灯》,在各个环节上都采取了与国际接轨的动画片制作方式,但是模仿的痕迹很明显,在人物造型方面设计得过于简单,就连“石猴”这一传统中国动画电影形象也逃不脱模仿迪士尼的嫌疑,不能不说是失败的案例。而随着近几年动画产业的发展,一些国产优秀动漫电影开始摆脱模仿的痕迹,而选择从中国古代经典文学作品或传说中汲取元素,同时也融入了现代性价值理念。事实证明,这些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相结合的作品均在艺术水准和商业上都获得了成功。如《大鱼海棠》(2016)创意源自《庄子·逍遥游》中的“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电影还融合了许多来自古书《山海经》《搜神记》与上古神话“女娲补天”等的传统元素,并基于这些元素打造了一个奇幻世界。影片虽取材自中国古典文学及传说,但却传达了爱、责任、牺牲,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现代性普世理念。该电影成功地通过中国文化中的“鲲”、“土楼”等视觉符号和意象成功地传达了中国文化中的情感和爱的模式:隐忍、牺牲、责任。这种爱有别于西方关注自我的爱,而是一种东方诗意美学语境下的“大爱”。而近期的《哪吒之魔童降世》(2019)可以说也是一个成功地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理念相结合的案例。哪吒源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为道教护法神,在《封神演义》《西游记》中均出现过,动画电影《哪吒闹海》(1979)中的哪吒延续了古代神话的叙事。然而从现代意义来看,传统神话中的哪吒的行为如“剔骨还父、割肉还母”所代表的的中国古代“孝道”价值理念,以及李靖怕天庭降罪不惜让哪吒偿命所体现出的服从权威和君权的价值观,都是与现代社会价值观格格不入的。《哪吒之魔童降世》采用了经典神话故事原型,却摒弃了原先神话中体现出的“孝道”和对“君权”的敬畏,而将哪吒与父母的关系赋予了现代家庭关系的价值理念。片中李靖夫妻知道“魔童”生来就有缺陷,却仍对他百般呵护,这符合现代社会对于天生缺陷儿童在成长过程中的人性化关怀理念,这种基于“爱”的教育理念是与现代社会,尤其是国际社会对于儿童成长的关注是完全吻合的。相反,如果仍然采取“剔骨还父、割肉还母”的情节则会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产生很大的文化误读,进一步加深西方观众对于中国文化价值理念的误解。同时,哪吒在成长过程中喊出的“我命由我不由天”所代表的反抗精神和独立意识也是与现代文明社会所崇尚的个体独立意识和价值观所吻合。《哪吒之魔童降世》也因此入围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而《大鱼海棠》也获得5.65亿的票房。因此,这种基于现代价值理念的改编是成功的,也是中国动画电影在进行传统文化故事改编时值得借鉴的。从这两部动画电影对于传统文化的成功改编可以看出,中国动画电影能够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元素赋予现代性的价值理念是全球化时代进行跨文化传播的重要一环。
所以基于对国内外成功的动画电影的分析,寻找共同的价值追求,以人类的共同情感认同作为基础应该成为中国动画电影跨文化传播的重要策略。从中国动画电影的全球化传播来看,首先是要寻找中国文化与世界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共识基础。自古至今,人类对于美、自由、公平、正义、友爱、个人梦想实现、英雄主义等追求是共通的,与其相关的主题、题材、叙事策略及价值观跨越东西古今,跨越民族、文化及意识形态。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国产动画电影应该以这些共通的母题和原型为基础,必要时要对传统文化题材中不适应现代社会价值理念的元素进行相应改变,搭建起价值传播的基础。其次,在文化共识的基础上,我们还需要坚持本土化的审美特征和视觉形象的可辨识性,并结合现代审美语境的趋向打造属于本土的文化符号,确立中国动画的世界身份。应该说,确立民族文化的世界身份不应该归结于对传统文化的一味回归,以及对于传统文化中的符号进行脸谱化传播。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只有提取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并与现代社会相适应,才能散发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从形式到内容的仿古式创作只会限制中国动画电影的艺术创新,同时让其失去艺术魅力。最后,从取材来看,中国动画电影的取材应该更广泛,应该涉及具有世界广泛意义的主题和题材,如和平、环保、老龄化、贫穷、残疾人关怀等具有人文关怀性主题,而不应局限于传统文化,同时也应该更加关注中国当今的发展和社会现实,通过动画电影折射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和人文关怀。长期以来,中国动画电影都定位为低龄儿童,而纵观世界动画电影的传播策略,都将观众定位为全龄段观众。这是因为,动画电影的传播不仅限于艺术与娱乐,更涉及国家形象的塑造。动画电影因为涉及全龄段观众,包括儿童,因此需要通过过滤现实,展现相对“理想化”的社会,并通过理想化的观念和思想方式,引导国家政治生活的价值导向,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生活的精神面貌,并以此构建正面的国家形象。我们纵观美国的动画电影,都是在理想化式地塑造一个“富裕、公平、正义、民主、美好、崇尚自由和英雄主义”的美国形象,动漫的形式“虚构”和“美化”了美国的现实,并艺术性构筑了美国的国家形象,这种理想化的美国形象深深影响了全世界的观众,使他们构建起关于美国较为正面的“国家形象”。因此,基于动画电影的传播特点,中国的动画电影不仅应该从灿烂的中国文化遗产中汲取营养,更应该关注中国社会现实和世界主题,通过动画电影这种理想化式的现代审美形式传达中国自古以来就秉承的友好、热爱和平、包容、开放、天人合一等价值取向和理念,更好地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从而打造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我们需要通过这种艺术形式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传播我国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7)中共中央宣传部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刚要》,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47页。。
纵观中国动画电影的发展趋势,中国的动画电影创作群体已经开始尝试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价值理念相结合,力图在文化共情的基础上打造具有中国文化特色,并被世界广泛认可的动画电影,这是一种基于文化多元、文化共融背景下的中国现代价值理念的跨文化传播,也是一种传播中国优秀文化的可贵尝试。但是,我国动画电影的崛起还处在初级阶段,对于中国动画电影创作者来说,基于文化共情的中国现代价值理念的传播还没有形成一种文化自觉,我们需要培育未来的动画创作者,使他们具备广博的世界文化的视野,在世界文化的体系之下反观中国文化的构成,并意识到中国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的“共情”基础,这样他们才能寻找到“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才能打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动画电影经典,并通过动画电影让更多的世界观众了解中国,喜欢中国,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优秀文化和价值理念,确立中国文化在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的主体性,从而树立良好的中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