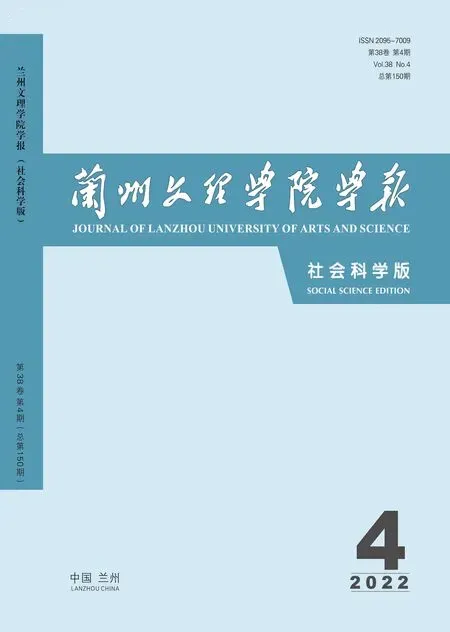秦人在陇右的早期发展与秦早期文化的面貌
牛 海 桢
(西北民族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30)
在中国历史上,秦朝占有重要地位,秦所建立的大一统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奠定了后来中国政治制度的基础,在推动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方面起过重要的作用,对历史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有着重大的影响。近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加之以甘肃礼县为代表的陇东南秦早期文化遗址考古实践的深入开展,秦早期文化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关于秦早期文化的研究,应该说有20世纪初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两次高潮。第一次以王国维、蒙文通、卫聚贤和傅斯年等人为代表,主要对秦公簋器铭、秦都城和秦民族源流进行了探讨。随着苏秉琦等人30年代发掘宝鸡斗鸡台秦墓并提出秦文化的概念,90年代以来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墓的发现,学术界把秦早期文化发源定在了甘肃东部,对秦人起源及秦早期文化的面貌进行了探讨,主要论文有张天恩《早期秦文化特征形成的初步考察》(《炎帝与汉民族国际学术研讨会》,三秦出版社2002年版);《早期秦文化特征形成的初步考察》(《秦文化论丛》1993年刊)。雍际春《秦文化与秦早期文化概念新探》(《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黄永美《早期秦文化的新认识——华夏文化中的独特地域性文化》(《秦汉研究》2011年刊),黄东旭《早期秦文化多元特质和源流问题浅析》(《华中人文论丛》2014年第1期)。上述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对秦早期文化的概念、文化特征进行了总结,给人们进一步理解秦早期文化开拓了思路。本文拟借助历史文献和考古学研究的成果,对秦人早期在甘肃的发展和文化面貌进行探讨,以期引起大家的讨论。
一、秦人在陇右的早期发展
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学术界对于秦人的来源进行过长期的探讨,主要有“东方说”和“西方说”。
其中坚持和论证“东方说”的主要有傅斯年、卫聚贤、黄文弼、徐昶生、林剑鸣、韩伟等。傅斯年曾在1934年写成《夷夏东西说》,认为“秦赵以西方立国,而用东方之姓者,盖商代西向拓土,赢姓东夷在商人旗帜下人入于西戎”[1]。卫聚贤则认为“秦民族发源于山东,至山西、陕西、甘肃然后再向东发展”[2]。
“西方说”主要代表是蒙文通、俞伟超和熊铁基等。蒙文通通过文献对比,明确提出“秦为戎族”,“秦为犬戎之一支”[3],从文献研究角度将秦与戎人联系在一起。俞伟超则是从考古学的角度,根据秦人墓葬的葬制、葬式和陪葬器皿的洞室墓、屈肢葬和铲形袋足鬲源自羌戎,认为秦人出自戎人[4]。熊铁基则认为“秦是西方戎族,变化较晚”,认为秦的早期世系是在强大以后伪造的[5]。无论是“东方说”还是“西方说”,学者们的共识是,秦文化兴起发展于西汉水以及渭河上游的陇右一带,继而东向发展,壮大强盛于关中平原地区,经过几十代人的努力,最后混一六合,统一全国,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基础。至于秦人的起源的最终定论,还需要更多的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的丰富和证明。
关于早期秦人的历史记载,目前我们所能依靠的基本资料是《史记·秦本纪》和《史记·秦始皇本纪》所附的《秦记》以及《竹书纪年》。《秦记》是秦人自己记载的历史,秦始皇焚书时,“史官非《秦记》皆烧之”[6],唯独保留下来了《秦记》,司马迁在编写《秦始皇本纪》时将其编入,因此记载非常可信。而《竹书纪年》则可以与《史记》互相印证。关于秦人早期历史,世系记载虽然非常清楚,但是不无虚构的成分且世系记载不完整。如“费昌当夏桀之时,去夏归商,为汤御,以败桀与鸣条”。鸣条之战是商人立国之战,史有明文,其意明确,说明费昌是给商汤驾车战胜了夏桀。但结合前句记载“大费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实鸟俗氏;二曰若木,实费氏。其玄孙曰费昌,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问题就出现了,大费是大禹时代人,其玄孙不可能是夏桀时代人,虽然梁云先生将“玄”字其解释为“玄而又玄”[7],但世系阙如也是不争的事实。
《史记》最早提到秦人在陇右活动的范围是从中潏开始的,周孝王以非子牧马有功,准备以非子为大骆嫡嗣,取代原来的嫡子“成”。但由于“成”为姜姓申侯之女与大骆所生,因此申侯反对改嫡,向周孝王说:“昔我先郦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潏,以亲故归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复与大骆妻,生適子成。申骆重婚,西戎皆服,所以为王。王其图之。”孝王受到申侯的反对,但是又不愿辜负非子的功劳,于是说:“‘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後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亦不废申侯之女子为骆適者,以和西戎。”非子“居犬丘”。因为善于养马,被周孝王封为附庸。根据《史记》记载,嬴人与商人有着同样的祖先记忆和族源传说,但长期僻处渭水中上游,虽然在当地有着举足轻重的力量,但族群地位很低,属于周人的部族奴隶,使之与西方戎人为伍。周人赐姓与封为附庸之国,失姓断祀的非子部族得到了一个全新的、尊贵的家族记忆,甚至改变了其族群本质,提高了部族地位,正式融入了西周的分封制体系,获得了华夏部族的身份而逐渐得到了东方诸侯国的承认。
关于西犬丘的位置,《史记正义》注引《括地志》说:“秦州上邽县西南九十里,汉陇西西县是也。”关于西县的位置,我们所依靠的文献资料主要是《史记》以及《史记》的三家注。《史记·樊郦滕灌列传》记樊哙“还定三秦,别击西丞白水北”[8]。同书注唐司马贞《索引》案:以亲故归周,保西垂,西谓陇西之西县。白水,水名,出武都,经西县东南流。言樊哙击西县之丞在白水之北耳。可见西县为秦时所设[9],汉继承之。西汉水起源于嶓冢山,从东向西又折向南流,又曾名白水。
关于秦的地理位置,就在今天的天水市清水县一带。《史记集解》引徐广曰,“今天水陇西县秦亭也”,至今在清水县东北三十公里处还有秦亭镇保留了秦亭的地名。《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秦州清水县本名秦,嬴姓邑。”[10]《汉书地理志》也记载:“后有非子,为周孝王养马汧、渭之间。孝王曰:‘昔伯益知禽兽,子孙不绝。’乃封为附庸,邑之于秦,今陇西秦亭秦谷是也。”[11]关于附庸,孟子的解释是:“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12]至于非子所封的这个附庸是附于某位诸侯或者直接附于周王,史无明文,但是秦人从此开始有了一定政治地位。那么,为什么周孝王不将非子分封到其父大骆所居住的西犬丘一带而分封到清水一带呢?周朝时期的渭河流域,周人、姜姓申侯、戎人与秦人都在这一地区错居杂处,互相角逐,其本质则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之间对资源的争夺,其中,周人与戎人是这两种文化的代表,而秦人与申侯则介于前两者之间左右逢源,首鼠两端以维护本部族的利益,以联姻等形式维系与两大势力之间的关系。非子牧马的地方在陇山以东的汧水与渭水交汇的地方。广义陇山指六盘山全部,也称“大陇山”;狭义陇山仅指六盘山南段山脉,故名“小陇山”。小陇山又称陇坂、陇坻、陇首、陇头,是渭河平原与陇西高原的分界山的界山,也是汧水与渭水的分水岭,北连朔漠,南通汧渭,呈西北——东南走向,平均海拔在2500米以上,长约一百里,东西绵亘六十余里,是关中平原地区的天然屏障。渭河在经过陇山时河沟下切,悬崖峭壁夹峙河谷,宝鸡峡至天水之间水流湍急,迂回曲折,山高林密难以行走,因此古代从关中平原向西或者陇西高原向东都是从陇山以东地势相对平缓的汧水谷地,陇山以西则是沿着清水县牛头河、长谷河河道行走的,而清水县恰好处在这一陇关要道上,所以周孝王“别子分宗”,封不是大骆嫡子的非子于秦,就是让非子部族替周王室守住这一要隘,进而把渭水流域的戎人阻隔在陇山以西,达到为周人屏藩的目的,也是周王室联络、制约西北戎人的纽带和桥梁。
自非子部族成为周人附庸而后,秦人为了部族自身的发展,在周人的支持下,不断与戎人发生战争。非子儿子秦侯在位十年,孙子公伯在位三年,到重孙秦仲时,周厉王无道,引起了戎人大反叛,攻陷了原来非子的父亲大骆部族居住的西犬丘,灭掉了大骆部族,秦仲也在伐戎之役中战死。周宣王为了巩固西垂,借予秦仲子庄公兵马七千人,收复西犬丘,庄公也被封为西垂大夫,秦人正式成为周王室直属的大夫,加上其占有的渭水和西汉水上游广大地区,开始以地方势力的地位并列于诸侯。到周幽王时期,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秦襄公将兵救周,护送平王东迁洛邑有功,平王始封襄公为诸侯,秦国遂由大夫进阶为诸侯。襄公享国十二年后死于伐戎之役,子文公继位,仍居于陇右的西垂宫,直到四年后帅军东略于汧渭之会(宝鸡县千河乡),营建新都。十六年以兵伐戎,收周室东迁之后的余民为秦所有,与周室以岐为界。五十年,文公死后归葬于西山,也就是甘肃礼县。王国维总结说“西者,汉陇西县名,即《史记·秦本纪》之西垂及西犬邱,秦自非子至文公,陵庙皆在西垂”[13]。
从以上《史记》等文献的记载可见,一直到德公徙都雍城以前,秦人的发展基地一直在陇右,即使是迁都于陇山以东关中平原之后,西垂仍然是秦人的旧都,祖宗的陵寝所在地,也是秦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并以其为中心向四周扩展。如秦献公嬴师隰(前424—前361),在未继位时曾经避据于西地,“出子二年,庶长改迎灵公之子献公于河西而立之”。《史记正义》解释说:“西者,秦州西县,秦之旧地。时献公在西县,故迎立之。”[10]200正是随着秦人势力的不断增强,秦人在巩固了西垂为中心的陇右大后方的时候,不断地东向进取,突出的表现则是都城的不断东移,正如王国维在《秦都邑考》中说:“然则有周一代,秦之都邑分三处,与宗周、春秋、战国三期相当:曰西垂、曰犬丘、曰秦,其地皆在陇坻以西,此宗周之世秦之本国也;曰汧渭之会、曰平阳、曰雍,皆在汉右扶风境,此周室东迁秦得岐西地后之都邑也;曰泾阳、曰橖阳、曰咸阳,皆在泾、渭下游,此战国以后秦东略时之都邑也。观其都邑,而其国势从可知矣。”[14]随着秦人势力的不断增强和周王室势力的不断衰微,秦人逐步向东面关中一带进行迁徙,秦迁都路线为秦邑——西垂(西犬丘)——汧——汧渭之会——平阳——雍——泾阳——栎阳——咸阳[15]。由以上秦人发展的历程加之考古发掘的甘谷毛家坪、礼县大堡子山、清水李崖遗址以及大量文物的出现,都说明秦人的早期活动轨迹一直在甘肃陇右境内。所谓的秦早期文化就是从西周孝王时非子之后,一直到春秋前期武公时期,秦人在陇右地区经历了从附庸到西垂大夫,再到诸侯的发展过程。陇右是秦人兴起和发展的大本营,在秦人发展历史中具有无可辩驳的重要地位,正是在陇右地区的文化涵养和文化积累,才为秦人后来在关中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研究秦人历史,决不能离开陇右地区而讨论秦人的发展问题,否则就是背本而逐末,忘源而逐流。
二、秦早期文化的面貌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礼县大堡子山、甘谷毛家坪等地考古发掘的不断进展,关于秦文化的关注和讨论渐趋活跃。随着我国社会矛盾转化为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文化旅游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学术界对秦文化面貌的探究进一步深入并成为潮流。如黄留珠就认为,“秦文化,具体指秦族(即建国前的秦人)、秦国和秦朝文化”。对秦文化的发展阶段进行了基本的界定,并且认为“就秦族、秦国文化而言,它们是中国的一种地域文化,其地域范围主要在今甘肃东部至陕西关中地区”[16]。葛剑雄则将秦文化概括划分为秦人文化、秦国文化、秦朝文化和秦地文化,并指出秦地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所称的秦地即《汉书·地理志》所载的地域;狭义的秦地一般指三辅和天水、陇西、安定、北地、上郡与西河等郡[17]。实际上,我们所探究的秦早期文化从时间方面来说,就是秦族文化,从空间而言,实际上是秦地文化,统而言之秦早期文化。
要探讨一个部族的文化面貌,首先需要我们对文化面貌有一个确切的定义。秦早期文化历史久远,记载漫漶不清,除过文献记载的雪泥鸿爪之外,我们只能依靠考古学文化来进行探索性的认识。张忠培认为:“分布于一定区域,存在于一定时间,具有共同特征的人类活动遗存,在考古学上,一般称为考古学文化。”[18]考古学文化揭示考古遗址的文化面貌,一般认为文化面貌应该包括一定的年代界限。其次是确定的分布地域。第三是具有群体性特征的典型遗存。秦早期文化是秦人创造的有明确的时空界限的地方文化,也经历了一个学习、创造、发展和流播的过程。对于探究秦早期文化面貌而言,考古学文化资料和文献的互相印证是较为可行的途径。考古文化是器物文化,这些器物凝聚了古人的生存状态、生存方式,记录着当时人的思想情感。同时也是古人的思想、知识、技能、信仰、追求和审美物化的结果,从而体现出一定的文化面貌和文化特色。而这种物化的系统化和体系化,则反映出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内容的不断丰富,也是嬴秦一族后来不断开疆拓土,东向发展的物质和文化基础。
(一)农牧经济的繁荣
从新石器时代以来,人类先民就创造了农业经济和牧业经济这两种基本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秦人源于山东半岛,有着悠久的农耕传统,西迁后所处的陇右地区,是黄河和长江两大流域的分水岭,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大部分是渭河和西汉水及其支流冲击而形成的河谷川原地带,尤其是河谷地带,土壤肥沃,地下水位较高,浇灌便利,特别适合农业生产。以秦安大地湾为代表的前仰韶文化是当地旱作农业的代表,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秦字的释义可以看出来,“秦,伯益之后所封国。地宜禾。从禾、舂省。一曰:秦,禾名”。段玉裁注曰:“按此字不以舂禾会意为本意,以地名为本意者。”[19]可见,正是因为秦地宜于农业生产,禾名也就转成了地名,所以段玉裁说秦字以地名为本意。王鸣盛在论及“秦”字时也认为:“秦地本因产善禾而得名,故从禾从舂省,禾善则舂之精也。”[20]说明秦地所产黍米之精良,从古代文献我们可以确定,秦人的祖先显然是以农耕为主要经济生活方式的。甘谷毛家坪遗址曾经出土有粗泥红陶平底仓和泥质灰陶三足仓各一件[21],陶仓的出现说明当时人粮食的生产已经有一定的剩余,所以才专门修建粮仓予以储存,间接说明了当时农业的发展水平。
按照苏秉琦的意见,从考古学角度而言,从渭水上游到秦安一线,是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与洮河流域的马家窑文化的分界线,也是中国西部地区与中原地区的分界线。而从陇东到陇西一线,也可以看作是西部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模糊地带[22]。秦人早期所处地区正是处于这一模糊地带,并且长期与戎人杂处。戎族之号,多冠居地,《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当时周边的戎人就有绵诸、绲戎、翟、獂戎,邽、冀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10]200。加之陇右地区遍布的梁峁、沟壑、森林和草场,地形条件限制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资源的有限性逼迫嬴秦部族被迫向戎人学习游牧和狩猎作为其经济生活的补充,养马和畜牧逐渐发展起来,秦人也逐步形成了半农半牧的经济生活方式,这种方式最大的优点是因地制宜,充分利用自然条件,宜农则农,宜牧则牧,农牧兼营,从而促进经济发展。从传说中秦人祖先的业绩,到他们的名字,大都与牧畜、狩猎有关,如嬴人远祖柏翳为舜之虞官,佐禹治水理地,掌上下草木鸟兽,能“调驯鸟兽”,曾教民种稻并发明凿井技术而赐姓赢。柏翳以后的费昌、孟戏、仲衍等都以能“御”而留名,御其实就是驾车。到非子时期,更是因为养马有功而得姓续祀,成为邦国附庸。
此外,礼县西山遗址出土的家畜狗、猪、黄牛、绵羊 (山羊)、马等动物的骨骼也说明了定居饲养业的繁盛[23]。而甘谷毛家坪遗址的动物种属出土更多,包括珍珠蚌未定种、宝贝未定种、龟、鹰科、雀形目、家鸡、雉、田鼠、兔、狗、狐、狗獾、黑熊、马、猪、梅花鹿、马鹿、狍、黄牛、绵羊、山羊等骨骼一万五千余件[24]。这些动物的饲养加快了农业经济与社会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从灰坑和地层中出现的数量不少猪骨骼,更是说明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水平。从人类学角度而言,农家散养的猪所搜寻的食物主要是野果和根茎类植物、菇菌类和野生谷粒,圈养的猪更是要以粮食来喂养。换言之,在食物缺乏的时期,猪与人处于共同的食物竞争地位[25],而养羊、牛则不同,羊牛所吃的都是人所不能直接食用的植物,因此,牛羊的养殖是人类更高层次的对环境资源的利用,是对生存环境限制的新突破,也是农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和产物。秦人早期在陇右的农牧业经济是后来东进关中进而争霸中原乃至统一六国的物质条件基础。
(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
为了适应于生产生活的需要,秦早期发展中,手工业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体现手工业发展的主要是制陶业、青铜铸造业、冶铁业和制盐业。
从新石器时代开始,陶器就伴随着人们开了定居的生活,正因为陶器反映了各个地域、各个时代和不同文化类型的工艺特征和审美风格,映射了社会的生产、生活状况和社会风习,因此被视为上古时代人类社会生活的化石[26]。甘肃境内秦早期文化遗址中,大量出土有陶器和青铜器,仅甘谷毛家坪从2012年到2015年就出土有“墓葬 199 座,灰坑 752 个,车马坑 5 座。共出土铜容器 51 件,陶器约 500 件,小件千余件(组)”[27]。根据考古发掘报告,陶器的种类主要有炊具,包括鼎、鬲、甑、釜、甗等;食器,包括盆、钵、豆等;贮藏器主要有瓮、罐和缸等[21]。从这些出土陶器制作技术来看,当时的制陶技术已经相对成熟,经历了从泥条筑成到泥条拉坯法再到轮制的发展线索[28]。
在金属器械的制造和使用方面,秦人也不输中原地区。以铜器为例,礼县大堡子山和赵坪出土的青铜器造型古朴,纹饰精美,铭文铸造精致,工艺复杂又有创新。在赵坪出土的方壶、盉、盨、方盒等器物的盖上、沿下,肩部和底座上铸接有很多圆雕的小动物,包括卧鸟、上行或下行的虎、熊等,因此梁云先生认为这些器物打破了中国古代青铜器发展到商周之际后器型和纹饰程序化、模式化,风格单调、沉闷的现象,“获得了别开生面的艺术效果”[7]124。在制作技艺上,邵安定在研究了大堡子山出土的铜器后认为,礼县出土铜器的加工和成型已采用锻造、铸造、冷加工等多种工艺,“而且还可根据器物的用途和所需的机械性能而采用不同的合金配比以及加工工艺”[29]。此外,铜器还大量用来装备军队,在陇右礼县、秦安、甘谷和秦城区博物馆收藏的大量的戈、矛、戟、殳、剑、匕、镞等兵器也说明秦早期冶铜和铸造的能力。在甘谷毛家坪还出土有铁镰,大堡子山出土有铜柄铁剑,秦人早期对铁器的使用成为秦人发展先进生产力,迅速强大起来的物质保障。
盐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古人所谓:“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30]同时,盐也是畜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含有盐分的水草可使大家畜膘肥体壮。秦人早期生息的西汉水流域有著名的盐官镇,武帝元狩年间设置盐官,也称为卤城,以产盐著称,《水经注》称:“相承营煮不辍,味与海盐同。”[31]盐味纯净绵润,畅销西北。秦人早期控制了此地,并且发展了高超的井盐生产技术,并且以盐来控制周边戎人,销售各地积聚财富。秦人在陇右的手工业有力推动了秦早期经济社会的发展。
(三)祭祀传统的继承
商人和秦人的图腾都是鸟,很可能二族同源或者二者族源相近,这一点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认可。商人有着很强的宗教祭祀传统,《礼记·表记》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商人所创造的至上神是“帝”或者“上帝”,而商人的祖先是受到“帝”的保护的。周朝建立后,商人的祭祀制度也被周人所继承,但是周人认为,人间的富贵只有祭祀自己的祖先才能得到佑护,不是自己的祖先不能祭祀。《左传·僖公十年》载:“晋侯改葬共大子。秋,狐突适下国,遇大子。大子使登仆而告之曰:‘余吾无礼,吾得请于帝矣。将以晋畀秦,秦将祀余。’对曰:‘臣闻之,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正义》解释说:“皆谓非其子孙,妄祀他人父祖,则鬼神不歆享之。”[32]因此非常强调“尊祖敬宗”,宗庙祭祀是国之大事,以对神权的顶礼膜拜来维护和加强族权和王权。这种传统也被族源相近的秦人所继承。襄公建国后,“秦襄公攻戎救周,列为诸侯。秦裹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皥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駠驹、黄牛、羝羊各一云”[33]。少皥亦写作少昊,是古代东夷部落之神,后与五方相配,为主西方之神,“少昊以主西方,一號金天氏,亦曰金窮氏,時有五鳳,隨方之色,集於帝廷,因曰鳳鳥氏”[34]。少昊以鸟为图腾,也说明了秦人与商人一样来自东夷。秦襄公立国伊始,即在西地也就是今甘肃礼县立畤祭祀祖先,其实是商周时期先民祭祀传统的延续和继承。祭祀其他神灵的祠也很多,《史记·封禅书》胪列汉代各地祠庙时说:“西亦有数十祠。”司马贞《索隐》解释说:“西即陇西之西县,秦之旧都,故有祠焉。”这些祠庙的建立也是秦人建国后从文化和精神上培育部族自豪感和凝聚力的政治与文化措施。虽然此举受到了司马迁从正统观念出发的批评:“秦襄公始封为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见矣。”“位在藩臣而胪于郊祀。君子惧焉。”[35]但是这种祭祀为秦公室统治权塑造天命观,增强秦人雄踞西北,虎视东方信念的效果却是实实在在的。
除过立祠祭祀祖先以外,秦人中间还残留着商人以来极端野蛮落后的人殉和人祭行为,陇右地区礼县大堡子山和甘谷毛家坪秦墓中人殉现象都能说明这一点。虽然墨子对这种行为进行过严厉的批评,“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36]。但是,秦国人殉现象仍然形成了一种传统,《诗经》中《黄鸟》篇就是当时秦人对子车氏三良从死的感叹,“《黄鸟》,哀三良也。国人刺穆公以人从死,而作是诗也”[37]。《左传》也说:“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38]人作为社会生产力的主要组成部分,人的生命任何时候都是宝贵的,但是,在奴隶社会时期,在宗教祭祀的传统影响之下,人们往往把生命看得很轻,有的时候人殉还被看做是一种荣耀,以至于形成了一种制度,正如祝中熹先生所说的,“其殉人之举不宜单纯归之于‘统治者的凶残’,那是一定文化背景下的社会现象,是一种特定宗教观念下的产物”[26]127。
按照现代社会学的观点来看,祭祀体系是中国传统中在行政系统之外另建的一种权威形式[39]。秦早期襄公开始的历代国君,深谙这一政治权术,他们构建了从国家到民间的包括祭天、祭祖、人殉和民间丧葬祭祀在内的一系列社会信仰体系,从而把包括戎人在内的各族百姓紧紧地纳入到秦人的文化体系当中。
三、秦早期文化的精神与特色
秦早期文化的主体是秦人,而秦人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组成和内涵。从中潏开始,初到陇右时,作为异地移民,秦人周边诸戎环伺,形势紧张,双方时战时和,互相依存。造父被封到赵城后,陇右秦人被迫依附于赵氏,以赵为姓,成为典型的部族奴隶。从秦人的直系祖先女防的三世孙非子时候,因为为周室养马有功,非子被封秦邑成为附庸后,秦族逐渐形成,其首领也逐渐被称为“秦嬴”“秦仲”“秦侯”等。周幽王十一年(前771),秦襄公正式成为诸侯,秦人不再凭借御车养马,镇守边陲,而是凭借周王室天下共主的名义,在周人支持下不断向东和向西开疆拓土,进而融合周边的戎和周余民,从而形成了秦人的文化圈层。秦人能够在落后的自然和经济社会条件下不断东进,最终统一全国,得益于其不断进取,改革创新的文化精神,从而形成了自身的文化特色。概而言之,秦人的文化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浓厚的尚武精神
秦早期文化时期,虽然秦人僻处西陲,地位较低,与中原地区各诸侯国交往不多,中原地区的战火也较少波及。但是在与戎人世代厮杀以求生存的背景下,在不断杀伐征战中,社会变革加上军事斗争的需要,秦人全民尚武,军事行为从贵族的专利变成了平民的义务,修习战备,射猎为先成为全部族的时尚。尤其是面对戎人,“秦人传统制戎之策,有力战,无退避,与周人畏戎之事异”[40]。这种尚武之风在《诗经·秦风》中表现最为突出。《诗经秦风》中的《小戎》《车邻》《驷驖》三篇章或赞美秦人的战车之精良;或铺陈秦仲时期车马的阵容和规制;或通过描写秦襄王狩猎游园的场景赞美了秦人平时的战备锻炼,但都是对尚武精神的弘扬和肯定。《黄鸟》篇更是通过对秦穆公死后“三良”人殉的惋惜与不舍,反映了对能战武士的敬重与崇拜。
最能体现秦人尚武和团结精神的则是《诗经·秦风》中的《无衣》。“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41]诗歌以问答的形式表现了秦人团结一致,同甘共苦的战斗精神和战斗意志,也是秦人尚武精神的最直接体现。正因为如此,班固在《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赞》中说:秦地“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诗,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焉”[42]。认为汉代时期陇右地区的社会尚武习气受到了秦人的影响。
秦人以陇右为基地,东进关中驱逐诸戎,占领周人故地。商鞅变法后,开始实行奖励耕战的政策,秦人的尚武精神达到了巅峰时期。“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父遗其子,兄遗其弟,妻遗其夫,皆曰:‘不得:无返。’”[43]诚然,尚武精神在秦早期与戎人作战时,起到的是保家卫国的激励作用,到后来秦国争霸乃至统一全国的战争中,则起到的是杀戮和戕害社会生产力的作用。所以马非百在《秦集史》中列举秦兵杀戮数字后说:“实自秦立国以来,战争频仍,除秦军被杀者外,其所杀敌国之军,殆有不可胜记者。”[40]1021仅仅对晋国战争中,“龙贾之战,岸门之战,封陵之战,高商之战,赵庄之战,秦之所以杀三晋民数百万”[44]。人作为社会生产力的主要因素,秦国对民众的杀戮是对当时社会生产力的极大破坏,这一点我们是必须要予以谴责的。
(二)以事功为主的学习创新精神
秦早期文化渊源于商周文化,秦人初到陇右地区,时刻处于诸戎杂居与包围之中,生产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发展阶段相比东方各诸侯国而言都比较落后。即使成为周人附庸后,也是极为艰难地在夹缝中求得生存。可以说,秦人的东向发展与崛起离不开周人的支持与利用,正是在周人的拉拢与支持下,才有了非子附庸,得姓续祀;秦仲始大,肇兴礼乐;庄公伐戎,称为大夫;襄公建国,始为诸侯,与诸侯通聘享之礼。及至文公时迁都汧渭之会,积极向周文化靠拢同时不断进行制度和文化的学习和创新。但是,秦人向周人的学习是有选择的,归根结底是因为秦人在当时是一股新兴的政治力量,充满朝气又积极进取,千方百计图谋自强。而周人内部矛盾重重,贵族势大,僵化腐朽。面对戎人的进攻,“秦人传统制戎之策,有力战,无退避;与周人畏戎之事异”[40]461。可见在生死存亡面前二者的精神状况已不可同日而语。
秦人向周人的学习和创新主要表现在政治制度方面。就继嗣制度而言,秦人在嫡长子继承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春秋时期秦国十九位国君中,康公之后的八位国君,史书没有明确记载其排行身份,康公之前(包括康公)的十一位国君中:武公、德公、成公、穆公都是兄弟继位者,襄公、出子二人是非长子继位,宪公、宣公是以长子身份继位者,文公不明嫡庶,只有静公、康公明确为太子继位。与他国子孙争立,明争暗斗甚至父子兄弟相残所不同,秦早期在继嗣方面还有礼让行为,庄公卒,长男世父(嫡长子)不立,让其弟襄公;武公卒,其子白不立,立其弟德公;宣公有子九人,均不立,立其弟成公;成公卒,子七人均未立,立其弟穆公。采取这种继嗣方式和秦人所处的环境有关,秦人历史几乎都和战争伴随,国君必须以武力服众,亲自带兵作战甚至成为秦国传统。所以《左传》说:“秦伯卒。何以不名?秦者,夷也。匿嫡之名也。”何休注:“嫡子生,不以名令于四竟。择勇猛者而立之。”[45]
在地方基层政权建设方面,秦人也有所创新,比如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武公十一年,“初县杜、郑”[10]182。这些县的确立,解决了对当地少数民族和土著的管理问题,如邽、冀是为管理戎人,杜、郑是为管理关中渭河流域的周余民,同时也打破了周朝的世卿世禄制,朝廷任命的流官代替了血缘世袭,国君直接控制地方。春秋时期秦国没有出现晋国、楚国、齐国那样窃取权柄的卿族,和秦国创立的县制密不可分。
秦人向周文化的学习还表现在史官制度的建立上,秦文公十三年(前753),“初有史以记事。”史官制度起源很早,相传仓颉即为黄帝史官,周朝时期史官摆脱了此前巫史不分的传统,出现了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等五史[46],亦即王室史官,其职守于天文、星历、人事无所不包。占卜天地、祭祀鬼神,法天行道,取鉴兴亡,兼政事与学问于一身。文公时期的史敦,穆公时期有由周入秦的内史廖,他们不仅记言记事,司马迁写《秦本纪》《秦始皇本纪》和《六国年表》就是根据秦国史官所记的史书。此外,史官平时主要备国君顾问,肩负解决问题,提供建议,弘扬学术,教化百姓的的职责。所以史书记载秦国设立史官制度以后,“民多化者”[10]179。
秦人对周文化的学习,也在考古学中有所证明,以葬俗为例,刘明科在考察了秦早期的葬俗文化后认为,秦立国后的近百年里,“从用鼎制度,器物配置组合,器物造型及装饰风格,墓葬形制及葬式等方面,全面承袭了周人做法”[47]。充分可见周文化对秦葬俗文化的影响。
(三)兼收并蓄的融合精神
秦人早期所居的秦地,《汉书·地理志》载:“故秦地于《禹贡》时跨雍、梁二州,《诗·风》兼秦、豳两国。昔后稷封斄,公刘处豳,大王徙岐,文王作酆,武王治镐,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秦人早期占据的天水、陇西一带,“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故《秦诗》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及《车辚》《四载》《小戎》之篇,皆言车马田狩之事”[11]1644。正是由于秦人早期在陇右地区所处地区诸戎环伺,所以尚武精神浓厚,又因为秦早期与西戎之间既有战争,又有被迫的融合和文化交流,不可避免的带有羌戎文化的特点。因此,王国维才说:“其未逾陇以前,殆与诸戎无异。”[14]288黄文弼也说:“秦既西迁,杂于戎狄,且通婚媾,故其俗多杂戎,如武公穆公以人从葬,赵襄子以智伯之头为领器,皆受西北民俗之影响。”[48]以至于中原地区认为:“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35]可见,秦早期文化与中原文化而言相对落后。但正是这种落后,激发了秦人兼收并蓄,不崇礼仪而崇尚实用与战功的典型文化特色,因此,秦早期文化风习中,无论戎人还是周人,只要对自身发展有利的制度、技术都积极学习。完成了宗法、祭记、文书、音乐、人殉、丧葬等制度体系,形成了秦人的礼制体系和精神文化。积极学习戎人先进牧马技术,结合本民族长于耕作的特长,农牧兼营,为本民族发展提供了丰盈的物质基础。不断吸收戎人和周余民加入本国,广泛延揽为本国需要的各类人才并加以重用。所以说,秦早期文化是秦人在继承中原文化并向西戎等少数民族学习和周文化学习的结晶,体现了一个民族在成长发展壮大过程的特有的精神气质,这种统一文化的形成,也成为了秦民族形成的标志。
四、余论
关于秦早期文化的地位,学术界讨论很多,褒贬不一,徐日辉先生认为:“秦早期文化的价值就在于它是秦文化的源头,而秦文化又开汉文化之先河,具有发祥肇起中华文化和文明发展的历史地位。”[49]但是,作为历史文化的一部分,秦早期文化既有十分可贵的财富,比如尚武进取,善于学习,不甘落后的文化精神。也有不少糟粕的成分,例如后世批评的穷兵黩武,愚民政策等等,对此,必须予以摈弃。但是,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而言,任何文化精神和文化面貌都有一定的源头,寻源探流是人类的反思文化的基本方式。我们应当承认,秦文化是一个大概念,它既有岁月积淀,不断发展的历史性,也有融汇四方,多方杂糅的多元性。秦人文化从陇右起源,到关中地区崛起,随着秦统一全国而影响波及中国大地及此后历代社会,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之一。因此,通过探究秦人的早期发展和秦早期文化的特征,进而追寻中华民族人文进化传承的人文特征和精神谱系,更是本文的题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