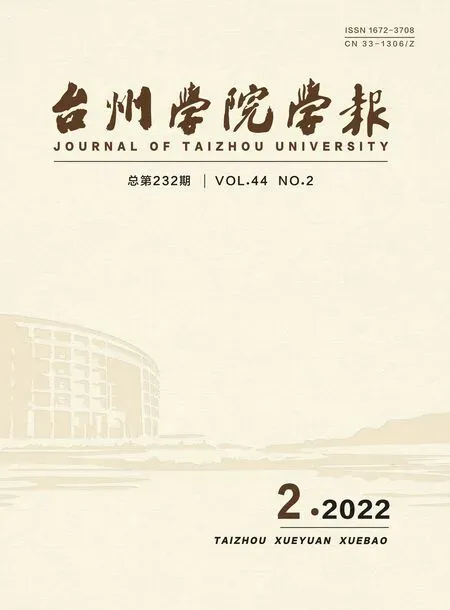互联网时代重提异化的主体性
——以生命传播的视域
刘 欣
(北京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 100871)
后疫情时代,人被推入了更加莫测的境地。新冠的持续威胁、生态危机的加剧、政治格局的割裂与对抗、心灵的贫瘠和虚无……在面临危机之时,我们试图去理解自身,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探寻其和谐与冲突的根源,力图找到解法。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重新回到了马克思。
生命传播理论启示着我们审视21世纪人类根本生存境域的改变——互联网的发明和广泛使用。正如马克思主义学者曼纽尔·卡斯特在其著作《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与文化》中,宣告了网络社会的到来。网络连接一切的逻辑延伸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改变着生产、权力和文化的运作及其结果[2]。更重要的是,人类的感觉、情绪、意识、观念、思想以及隐匿在其背后的无意识等,也前所未有地在跨越时空中快速连接、迅速交互[1]3。在这样一个复杂的、流变着的、不确定的媒介大时代中,人如何构境着自我与世界?我们又在面临着怎样的“异化”?复归的可能性在何方?本文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出发,运用生命传播相关思想,回应互联网时代的异化与复归的可能性。
一、马克思异化理论的两个维度:主体性与外部性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形成的异化思想,体现了对人本质的理解,揭示了在巨大外部性面前人的类本质的丧失。马克思在《手稿》中将异化劳动做了四个规定: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活动的异化;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人与人的异化。从劳动产品到劳动活动本身,再到作为类的人,最后是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呈现了环环相扣的递进关系。异化理论包含着两个阶段的异化:一是人作为主体的自我异化,即异化理论的主体性;二是人作为主体间存在者的交往异化,即异化理论的外部性[3]157。
(一)身心分离的自我异化,主体性的破碎。自我异化涵盖前三个规定。马克思发现了“劳动”作为人生存所必要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作用于人和自然之间,人在劳动中发挥着作为人的潜能、领有着自己劳动所得,也创造着自身的历史。但在国民经济现实状况下,劳动者不领有自己的劳动产品,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的劳动行为相分离[4]47。异化的第一阶段也就是物的异化[5]20。“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4]50物的异化上升到主体的自我异化,这种异化更深层次的影响是人类本质的异化,即人作为整体性的人的丧失。
马克思所言的类本质是人之为人的特征,是人不同于其他生物的特征。人首先是自然中的存在者。从肉体的生存角度来说,人同动物一样都需要依靠无机界生活[4]51,即,“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4]52。但与此同时,人也是有意识的存在,即,从精神方面来讲,“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同时也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4]52。更进一步来说,“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4]53。马克思认为:“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活动。”[4]54
马克思所言的人的类本质和类生活是一种身心合一的存在状态,是一种包含着“美的规律”的、和谐的、与自身和自然共生的状态。但劳动中原本应包含的人的能动的创造性,对自我的肯定,对美的规律的把握,在异化下统统消失殆尽。原初的、有着整体经验的、身心合一的人也走上了不断异化的道路。
(二)货币作为中介的交往异化,外部性显现和主体性退隐。马克思在对异化理论的四重规定进行论述时,也贯穿着对“个体的人是如何连接成社会的”这一理论难题的分析。他认为人的类本质并不是无数个个体的集合。社会中原子化的、孤立的个体如何产生连接,连接着个体的那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素,才是我们领悟类本质的关键。
马克思发现资本主义社会中,将个体连接成社会,并产生相应社会行为和社会活动的是货币。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劳动者在自我劳动的基础上获得了私人所有,然后以私人所有为前提,与他人进行分工和交换。在这一过程中,私有者发生分化:一部分人失去了自己的生产资料;另一部分人积累起自由货币。于是,一般私有者的分工、交换关系,开始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转变:劳动转变成雇佣劳动,工人开始在有产者的工厂里进行生产[3]170。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在这一进程中逐步确立。结构性的外部又反过来作用于结构中的个体。这一过程并不是凝固不变的,马克思意识到了这一巨大的外部性是在不断地发展和生成之中。
在私人所有下的交换行为必然发展到价值,价值的现实存在就是货币[3]295。在人类原本的交往活动中,相互交换的物品是劳动者个体脑力和体力活动的凝结物,物品本身蕴含着劳动主体的个性。是否交换取决于交换双方的意愿,所以物品本身无法在客观层面进行统一化的衡量。交换行为是在差异中进行,并不存在客观的、统一的、可衡量的中介物。但当某种特定的物象,如货币,进入交换活动中,凝结着劳动者脑力和体力的物品变成了可纳入客观衡量体系的商品。人与中介货币的关系开始发生颠倒。在交换中,人与人的关系也变成了物象与物象之间的社会关系。金银之类的货币拥有了支配世界的真正的权力,成为一种社会权力[3]296。
如果说私人所有是人异化的第一步,是人主体性破碎的开始。那么以货币为中介的交往异化是人的进一步异化,这种异化上升为一种绝对的、不以个体意志为转移的外部性实存,将人破碎的主体性进一步隐匿。
二、互联网时代的异化,从空间到时间
马克思之后的200年间,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纷纷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进行细致考察。对异化的揭示和探讨也从空间维度发展到时间维度。
(一)空间维度中的异化:身心的不断截除。马克思提出异化概念时,正值资本主义初始阶段,彼时人的异化源自劳动者无法占有自己的劳动产品;到了20世纪20年代,卢卡奇揭示“物化”理论时,人的异化源自近代社会理性化进程中,工具理性对人主体性造成的整体意义的肢解[5]21。在泰勒制的规训下,人变成了可计量的、抽象的、数字化的人,人的丰富性和个性丧失。不断精细化和专业化的分工,将人分散至流水线上,人的整体性被割裂。人作为主体的整体性不复存在。人被异化成社会这个巨大机器中的螺丝钉。卢卡奇“物化”的直接结果是“物化意识”,即人陷入精神领域的困境[5]27。再到20世纪60年代,福特主义得到大规模推广,组织化的资本主义确立起自身霸权地位。列斐伏尔在这一背景下,揭示了8小时工作时间以外,人的日常生活也被资本主义殖民,变成了资本主义逻辑闭环和社会不断扩大再生产的内在环节。在此基础上的日常生活,也变成了总体异化的必要中介。列斐伏尔在对日常生活的批判中发现,人们已从生产异化走向了全面异化[6]。
自此,对异化理论的探讨仍在空间中展开,更多地从人类的生产活动等行为进行考察。彼时,正处于麦克卢汉所言的印刷时代,线性的书面文字塑造着人们与之匹配的时空观,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个体的思维模式和社会的组织方式,也催生着标榜理性、逻辑、专门化、效率、个人主义的现代性。在麦克卢汉看来,口语时代的部落人是人类存在更原初的形态,也是马克思所言的进入私人所有之前的、身心合一的人。部落人生活在感官平衡和时空同步的世界之中,这是一个具有部落深度和共鸣的封闭社会[7]363。部落人的内心世界是由复杂情感构成的创造性混成体。与同质化的文字人不同,文字人以效率和实用为由,将有机和谐、复杂的通感转化成为一致的、连续的、线性的视觉感知方式。整合的人变成了分割的人。“它好像使人发生爆炸,变成专门化的、心灵贫乏的‘个体’,或者叫作单位,在一个线性时间里和欧几里得空间的世界里运转的单位。”[7]365麦克卢汉异曲同工地从媒介变迁的角度论述了精神分裂和异化是拼音文字的必然后果,也是人类感官收缩、心灵贫瘠的根源[7]367。
(二)时间维度中的“新异化”:认知方式的异化。生命传播理论认为,互联网在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连接方式。统一的、秩序的、线性的时间观念被打破,单位时间内的连接以网状的、多重的、差异化的形态急速生成。个体的生命体验较过去成倍地增长,伯格森所言的“生命时间”在网络社会中真正成为显现。学者哈特穆特·罗萨认为,传播速度加快带来的社会加速已经跨过了一些临界值,使人类的异化不仅在空间中展开,更在时间维度上与自己相异化[8]117。这种“新异化”从一定时间单位内行动者的行动事件或体验事件数量为出发点,考察人作为行动者的经验范围和期待范围的重叠速率。当我们需要在更短的时间内做更多的事情时,我们的经验与期待之间的步调逐渐失调,被称为“当下”的时间区间不断萎缩[8]18。罗萨认为,异化进入时间维度对人存在最根本的变化是使人与自身吸收世界的能力相异化[8]145。生命传播更进一步指出,隐含在“新异化”背后的是一种认知异化[9]6。
三、在异化主因的隐匿和显现中重提主体性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异化理论的目的是在此基础上扬弃异化,并探寻复归的可能性。如今,人们不仅依然置身异化之中,异化更在时间和空间双重维度上展开。复归之路何在?应辨析当代人异化的主因来自何方。
(一)个体间连接中介的改变:从“货币”到“媒介技术”。海德格尔曾在《技术的追问》中提出,招致事物发展变化的诸多因素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呈现出隐和显的关系。以生命传播的视角,将媒介技术环境放入异化理论的变迁中进行考察时,不难发现自马克思提出异化理论至20世纪末,传播速度处于相对稳定的阶段,继而人对时间的感知也保持相对稳定。此时,异化的主因是人类生产方式的所有制形式,即私有制。货币成为连接个体与个体,使个体上升为社会的中介。个体的多样性和复杂的情感结构被切割,统统以商品的价值逻辑放置于单向度的、线性的结构之中,人的主体性被抹杀。
20世纪末,一场极重要的技术革命开始在西方产生且迅速扩散。大卫·哈维将电脑和互联网技术视为人类体验空间和时间的新的主导方式。如果说前网络社会中的人们以货币为中介连接起来,那么网络社会中,人与人的缔结方式有了除货币之外的新的中介——媒介技术。具体而言,是依托电脑、智能移动终端、互联网和5G等技术为基础的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缔结,这种缔结以网状的、立体的、多重的、无序的形态存在,也重组着社会的结构。生命传播将互联网中的个体隐喻成因陀罗网中的珠宝,彼此相连、交互辉映、牵一发而动全身[1]4。曾经隐匿在现代性社会结构中的个体,其能动性在万物互联的网络社会中被释放[10]。由于媒介技术作为异化主因的显现,失落的主体性在生命传播的理论视域下被重提。这也是追问网络时代复归可能性的通路。
(二)万物互联中主体性得以可能。马克思对异化的扬弃诉诸两个手段:共产主义与人的复归。这两个手段可以看作两个维度的复归之路:前者诉诸外部实存,是前文所讲的外部性;后者诉诸人的主体性。但正如前文所论述的那般,人的异化在近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进程中,主体性消失殆尽。这也是从卢卡奇到列斐伏尔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无法真正在理论层面找到异化扬弃的根源。20世纪的学者们对复归的讨论陷入死循环,也恰恰印证了麦克卢汉所揭示的媒介环境对人的麻痹作用,就像“鱼到了岸上才知道水的存在”[11]。置身21世纪的幸运之处,也在于新的媒介技术不断应用带来媒介环境的不断变迁。我们在媒介与媒介之间“移民”,获得了“反环境”的能力。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文化的逻辑从以线性文字和语言为中心的现代性,转向以图像和视觉为中心的后现代性。作为媒介的互联网通过超链接将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媒介形态进行融合,将人们再次带入视觉与听觉同步的感官平衡的世界。生命传播强调传播中的感觉、知觉、情绪以互联网为媒介,在个体之间释放和流动。在万物互联中,无数个体之间的感觉、情绪、意识等发生碰撞,上升为大大小小的社会意识,影响和指导社会中行动者的行为,个体和群体的行动转化为社会存在,从而对社会实存进行改变。
生命传播启示着我们,网络时代的传播将人的感觉、情感、情绪重新带回到主体身上——感觉着的主体成为可能。与此同时,“传播—行动—改变”的模式也肯定着主体在网络时代的能动性——“能”动的主体改变着巨大的外部性。在这两个维度上,我们便找到了复归的可能。
四、复归的可能性:生命经验与良善生活
马克思已指明,人的复归是人异化的解药。复归是人性的全面复归,是人的感觉和感觉的人性。马克思所言的完整的人性,是包含着感性回归到他自身的人,是五官感觉被充分发挥的人[4]84。五官感觉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等构筑了人与外部相关联的基础。思维、直观、情感、愿望、活动、爱等属于人的特性的活动也应运而生。“正是因为这些感觉和特性无论在主体上还是在客体上都成为人的”,所以这种解放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4]82。
(一)从感觉、实践到生命经验。马克思所认为的五官感觉被充分发挥的人和麦克卢汉所言的“部落人”都是人的一种原初状态,即一种和谐的、身心平衡的状态。但需要指出的是,感觉或五官感觉是一种意识的内在活动。置身网络社会中,我们的感知系统、思维模式和心智结构都在被媒介所深刻地塑造着,个体如何确定五官感觉被充分发挥?正如生命传播理论警示的那样,人们在享受社交媒体带来的身心的快感和满足时,可能也会陷入更大的空虚,甚至身心失调。师曾志曾指出,网络社会中,人们的体验越多而经验越少,需要重新审视人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9]7。这种社会实践应是梅洛—庞蒂肉身意义上知觉、情感、情绪与活生生的身体一元的状态。也是本雅明笔下的“经验”。他认为“经验”有别于“体验”,经验是具身实践过程中的身心记忆,形成并留存于肉身的身体图式中,也以此生成、建构着未来的存在。而体验是一种短暂的、离身的、走马观花的,很难让人记忆[12]。生命传播主张在传播速度加快、个体卷入的同时保持对个体自身和情绪的关注,所有的情绪都是我们自身生命意志的表达,而这些终会体现、反映在肉身上。肉身不仅是本源性的空间,我们能够在身体中找到抵抗异化的种子;我们也是存在于社会的空间中,所以我们的共同体验会凝结成一种社会维度的行动。以肉身投入活生生的、具体的日常生活的实践活动中,在经验叙事中体悟身心合一和感知的复归。
(二)艺术、共鸣与良善生活。面对社会加速下的“新异化”,罗萨以“共鸣”理论来描述与异化相对立的和谐状态。生命传播理论认为,互联网通过构境人们的感觉与知觉系统,建立起个体间相互依赖与共生的“经验场”,是“共鸣”关系的基础[9]14。共鸣意味着一种主体间的和谐关系。从主体的个人经验、汇聚成共生的经验场再到产生主体间共鸣的路径中,最能达成的是艺术。因为艺术既是完整的人的内在规定性,可以实现主体感知的复归;也是存在于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统一的最高形式。换言之,艺术是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个体之间最能感受、认知、达成共识和产生共鸣的形式。
马克思在《手稿》中论述了劳动和艺术对于完整的人的意义:“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同样,从实践领域来说,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4]52劳动和艺术本身就是人生存活动的组成部分。而如今社会分工的专业化,使原本属于人在自然界自由自觉的创造和生存活动被分离,劳动变成了赚取货币的手段,艺术变成了艺术家才能进行的创造活动。当艺术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被剥离,被束之高阁,人的感知能力也同时被收缩。但谁说鸟儿动听的叫声不是艺术?清泉在山间奔流的节奏不是艺术?夏日火热的晚霞不是艺术?“让生活变成一件艺术品!”[13]回到活生生的日常生活中,体悟五官感觉——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让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的力量的感觉得到复归[4]83-84。以此为基础的精神、意志、爱等等感觉被重新丰富,让人再次成为身心统一的、占有自己全部人性的丰富的人。“只有人的心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社会才可能出现。”[14]一种合乎人性的、良善的生活才能展开。
结 语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已跨越了两个世纪,它不仅揭示了人类心灵和生存危机的内在根源,更始终关照着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道路。但回顾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关于异化理论的探讨,异化的扬弃和复归之路却陷入了死循环。其根源在于马克思所论述的人的异化是从主体性的破碎开始,而货币作为连接个体与个体的中介,是人更深一步的交往异化。货币改变着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自然的关系,货币上升为一种绝对的外部实存,使人的主体性进一步隐匿。那么复归的可能性何在?
生命传播首先启示着一种“反环境”的思维。20世纪对异化与复归的讨论陷入僵局,其原因在于置身线性文字和印刷术统治的社会和文化状况中,人们无法感知所处的媒介环境,更无从反思媒介之于人——从心智到行动——强大的塑造能力。文字和印刷术将异化的主因牢牢地锁在人类生产方式的所有制形式上。异化的主体性沦丧在巨大的外部性中。其次,生命传播强调关注新媒介赋权下的个体与自身、个体与社会的动态关系。互联网时代,人类有了除货币以外的新的缔结方式,从生产、权力、文化到社会结构也由此改变。互联网使人脱离单向度的理性人,重新成为感觉着的主体。“能”动的主体也改变和重塑着巨大的外部性。这也揭示出,互联网时代,新媒介赋权下的个体重新获得了一种主体性,复归的通路正在敞开。
在主体层面,互联网在媒介物质性上为个体提供了五官感知复归的可能。但作为主体的个体如何认知和把握这种感觉的重新回归。首先,个体要在认知层面肯定自身感觉的合法地位——快乐、愤怒、悲伤都是个体生命意志的表达。其次,在对自身主体性的把握中如何避免沦为一种彻底的“主观性”。其尺度在于个体心灵和肉身的平衡,这个平衡不是一个绝对的、凝固的状态,而是流动的、在个体的实践中不断自我校准的过程。这种实践不断作用于自身和外部世界,每一个上一秒都积累成生命经验,为向死而生的每一个下一秒提供着智慧的源泉。在主体间层面,作为人本质规定的艺术重新回归人的生存活动中。不论在个体的日常生活,还是在主体间的经验世界之中,艺术是疗愈、是共鸣,也是一种良善生活的抵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