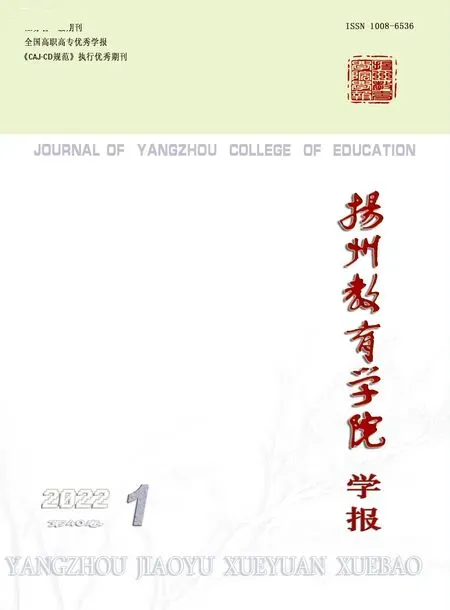十八至十九世纪西方职业生涯思想述评
屈 振 辉
(湖南女子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04)
十八至十九世纪西方思想家辈出、灿若星河,在其丰富的思想中有很多有关职业及与人生发展关系的论述,即职业生涯思想。这些思想表现在经济学、社会学、哲学、管理学等多学科领域,异彩纷呈。
一、经济学学者的职业生涯思想
斯密被称之为“现代经济学之父”,他对职业生涯思想的贡献主要在其分工理论中。他认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 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凡能采用分工制的工艺,一经采用分工制,便相应地增进劳动的生产力。各种行业之所以各个分立,似乎也是由于分工有这种好处。”[1]他认为职业分工是劳动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这种看法基本符合客观史实,也较接近马克思的观点。他还极力反对政府干预个人职业选择,这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们突破传统的职业“神定论”束缚、自由选择职业并进而规划职业生涯扫除了障碍。他将人们职业选择的动机解释为“职业的优越性”。他认为:“在同一地区中,有什么职业明显地比其余职业优越或者差劲,那么,总是有许许多多的人涌向优越的职业,避开差劲的职业。”这种“职业的优越性”既取决于工资高低,还取决于其它因素。例如是否惬意、能否容易而又省钱地学会、是否有稳定就业的保证、是否要求可信赖性以及是否提供升迁的机会等等。[2]他并未将人们职业选择的动因单纯归结为金钱,而是对其进行了多元化归因。这也比较接近现代职业生涯理论,只是其所称的因素是否全面、正确就很难说了。如在社会主义中国,青年人选择职业还须考虑到国家的需要。此外,他提出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奠定了现代职业生涯理论的人性论基础,即人们总是首先从有利于自己的“理性经济人”角度选择职业和规划职业生涯。后世学者施恩就此为基础提出了“职业锚”思想。[3]
在职业生涯思想上,李嘉图理论的贡献主要在对于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划分上。“李嘉图注意到劳动的不同性质,区别了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在相同的时间内,复杂劳动创造的价值大于简单劳动创造的价值。”[4]依据李嘉图的理论,技术性、操作性的工作属于简单劳动,管理工作属于复杂劳动,后者是前者的倍加,难度更大。青年人唯有从前者做起不断培养自己从事多种简单劳动的能力和经验,而当其“倍加”到某种程度时才能驾驭复杂的管理工作。当然,从简单劳动走向复杂劳动也是现代人职业生涯发展的普遍趋势。
斯密的职业分工论与李嘉图的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划分论存在着承续关系:职业分工是划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前提和基础。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是众多职业分工划分方式中的一种,唯有对职业进行分工划分后才能从中区分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划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是对职业分工的深化。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划分是抽象层面而非具体形态层面进行的职业分工,它对职业分工的探讨已深入到本质和规律层面,甚至也为后来马克思发现劳动的二重性并进而揭示价值的本质奠定了基础。
二、社会学学者的职业生涯思想
韦伯对于职业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学中。职业社会学是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学发展的重要分支,韦伯是其重要的代表人物。其职业思想集中体现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他批判了以路德为代表的基督教“天职”思想。他认为职业人士不是为职业而生而是靠职业谋生,职业意味着个人对生活于其中的某一领域规范约束的被迫服从,不然他就会被排除在游戏规则之外,丧失其生活和存在的方式。职业决定了职业者的生存和生活方式,并在他的内心建立起了对这种职业的“信仰”和荣耀。[5]他还阐述了职业的意义与价值。他认为职业不仅是一个人赖以生存的手段,它也成为一个人在社会上找到并保持一个位置的根本方式,成为他的安身立命之本。可见,他虽然和路德等欧洲中世纪神学家都认为职业神圣,但后者认为这种神圣来源于对上帝的信仰,而前者则认为这种神圣来源于职业者自己内心对职业的认同。这种思想具有重要意义:人们既不为上帝而工作,就更不需要固守所谓上帝的职业安排;人们为自己而工作,因而自我才是职业生涯发展与规划的中心和起点。这种观点适应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他对职业选择问题也有论述。他认为在相同社会历史地位的情况下,新教徒和天主教徒表现出的不同经济取向和职业选择更表现了宗教的重要作用。“由环境——这里指的是家族共同体和父母家庭的宗教气氛所照拂的那种教育类型——养成的心理和精神特质决定了对职业的选择,从而也决定了一生的职业生涯。”[6]他将决定人的职业选择并进而影响其职业生涯的因素归结为“环境……养成的心理和精神特质”是正确的,但他认为这是由“家族共同体和父母家庭的宗教气氛所照拂”则犯了客观唯心主义错误,而他看到人的职业选择和职业生涯受其“家族共同体和父母家庭”的影响则具有一定科学性。他还提出职业声望的概念。这是影响人们职业选择的重要动因和进行职业生涯规划须考虑的重要因素。“职业声望,是指职业在社会上的受赞誉程度,也是人们对职业社会地位的主观评价。”[7]或说是“社会中的人们对某种职业的权力、工资、晋升机会、发展前景、工作条件等社会地位资源情况的评价,亦即社会地位高低的主观评价”[8]。现代职业观虽认为职业只有分工不同而无贵贱之分,但在职业声望上体力劳动者不如脑力劳动者、手工业者不如神职人员仍然是不争的事实。
从社会学视角研究职业问题的西方近代学者中,涂尔干是又一代表人物。“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1893年发表的《社会劳动分工》中论述了分工问题,被认为是职业社会学较早的研究。”[9]他研究社会分工时提出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等两个概念。他认为前者是建立在社会分工和个人异质性基础上的一种社会联系方式。分工导致了职业的专门化,每个人都因职业的不同而发挥着不同于他人的独特能力,每个成员都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必须依赖他人,这就造成人们彼此的相互依赖感、团结感和自己与社会的联系感。[10]46从现代职业生涯理论看,这种思想具有重要意义:一是他看到了社会分工、职业的专门化与个人异质性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后两者间的联系,延伸而言就是现代职业生涯理论中的人职匹配。个人的异质性是人们进行职业选择的重要依据,它决定了人们从事不同的职业和即使从事相同职业其职业生涯历程也不相同。二是他意识到不同的职业为每个人发挥不同于他人的独特能力提供了舞台,而能力恰是人们在选择职业进而规划其职业生涯时必须考虑的因素。“能力是职业生涯发展的根本因素,它的大小决定着一个人的职业生涯发展状态,正确评价自己的能力就可以预知自己的职业生涯发展潜力到底有多大。”[11]三是他从每个人都必须依赖于他人出发阐明了社会有机团结的重要性,这与职业及职业生涯联系在一起,意味着人们在选择职业及规划职业生涯时不仅要考虑自己,同时也要考虑服务他人和社会。这在社会主义国家尤为重要。他还指明了在职业共同体思想中存在某种集体意识。他认为现代社会各种职业群体中,共同的集体意识、共同的职业活动和利益会导致一种群体内部的同质性,这种同质性将使形成共同的习惯、信仰、情感和道德伦理成为可能,这些群体的成员在他们的行动中也要受到这种集体意识的制约和指导。[10]47这种“集体意识”从现代职业生涯理论来讲即职业价值观,它在职业生涯中很重要。“只有在工作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工作才会成为一种乐趣而不是负担。”[12]
韦伯与涂尔干是同一时期的社会学家,韦伯的研究涉及到很多方面,而涂尔干的研究则较为聚焦,因而前者较之后者对职业生涯思想的启示更多。韦伯的研究批判中世纪的基督教“天职”思想并力图使职业与宗教相分离,但其中某些论述又带有宗教色彩;涂尔干的研究则摒弃了宗教色彩,他的有机团结理论中的某些观点更适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
三、哲学及政治学学者的职业生涯思想
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论述过职业选择、职业兴趣等问题。在职业选择问题上,他认为每个人的职业选择必须与其性别、年龄相应。“让每一个人有一项适合于他的性别的职业,让年轻人有一项适合于他的年龄的职业。”[13]297除少数职业外他对大多数职业都不持歧视态度,甚至认为艰苦、危险的职业都可以做。“我不允许我的学生选择不卫生的职业,但是我不禁止他去从事艰苦的职业,甚至去从事危险的职业,我也是不加禁止的。”[13]298他认为人们应在平等地对待职业的基础上进行职业选择,并已提出了“爱好和倾向”在职业选择中的重要性。“为了尊重所有一切有用于人的职业,也不需要全都学会它们,只要我们不抱着不屑为之的态度就行了。当我们可以进行选择,而且又没有什么东西强制我们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想一想在同一类职业当中,我们的爱好和倾向是适合于做哪一种职业呢?”[13]299他所说的人们在职业选择时应考虑的“爱好和倾向”,从现代职业生涯理论的话语说即职业兴趣,它对职业生涯具有很重要的影响。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从个人权利角度探讨了职业选择问题。他认为应承认个人的特殊利益、福利和权利,主张职业选择的自由,反对柏拉图“理想国”的构想,个人的职务应由官府来分配。他极为重视个人选择职业的自由。在各种个人自由中,他对于职业选择的自由给予重要价值。暂且不论他是从政治层面还是法律层面探讨职业选择权,他将职业选择上升到权利的高度予以重视,这是以往学者所前所未及的。德国哲学家费希特也论述过职业选择问题。“在他看来,人才阶层并非是享有社会特权的群体,而是指能把自我职业选择与社会责任统一起来的人。可以说,人自由选择职业的结果促成了社会阶层的产生。当然,人的秉性天赋制约着职业选择的去向……每个人都可以选择一种职业发展自己的才能。”[14]由上观之,他认为个人的职业选择应同社会责任联系起来;人们的职业选择既受其秉性天赋制约,也要以此为出发点进行考虑;人们既要选择能发挥自己才能的职业,也应在自己选择的职业中发挥自己的才能。现在来看其上述观点与现代职业生涯理论还是不谋而合的。
傅立叶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在论述分工问题时提出职业的选择应以“兴趣和爱好”为基础,因此不应受旧式分工限制而自由选择。他将他自己设想的理想社会组织称为“法郎吉”。他认为“法郎吉”中的社会成员在职业的选择上是自由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选择适当的工作,并且工作不固定,可以随着自己兴趣的变化而变动。[15]他的上述观点积极意义在于:首先,他意识到“兴趣和爱好”在职业选择中具有重要作用,这已为现代职业生涯理论所证实,“择己所爱”已成为现代人选择职业时的首要原则。其次,他提出“不受旧式分工的限制,自由选择职业”既反资本主义也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最后,他的上述观点更具有政治上的进步性,“法郎吉”是他设想的空想社会主义组织之名,是后来社会主义社会的雏形。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别说根据自己的爱好和兴趣选择职业、“随着自己兴趣的变化而变动”职业,就连择业自由都是不真实的:工人虽然有选择受雇于某个资本家、从事某种职业的自由,但是无法摆脱必须受雇于整个资产阶级的厄运;而真正的自由择业和根据“兴趣和爱好”择业,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就是他所说的“法郎吉”中才能实现。这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
较之于经济学、社会学,哲学、政治学的意识形态性更强。卢梭、黑格尔、费希特等资产阶级思想家在职业生涯思想上总体表现出明显的自由主义倾向,这较之西方中世纪无疑具有相对的进步性,但也存在局限;傅立叶作为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他的职业生涯思想尽管存在不科学等局限,但反资本主义的倾向却非常明显,如资产阶级思想家一味鼓吹职业选择自由,而他则指出只要存在旧式分工,职业选择自由就无法真正实现。
四、管理学学者的反职业生涯思想
职业生涯理论在现代更多属于管理学及心理学范畴。管理学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前期,早期管理思想家从总体上说是反对职业生涯的。管理学中职业生涯理论的出现与“人本管理”思想的兴起相联系,但西方早期的管理思想总体而言则是一种“物本管理”,其以泰罗制为典型代表。泰罗制别名“血汗泰罗制”,从这个别名就可看出其端倪。早期管理思想家仅仅将人视为“经济人”,认为人仅仅是为金钱报酬而工作,只要满足其物质需要、给其大量物质报酬就能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因此他们主张实行“物本管理”,不仅“重物轻人”,甚至把人当作工具进行管理。他们还认为必须将工人时刻置于正式组织控制下。这种以物而不以人为中心的管理自然不可能衍生出职业生涯思想,甚至是反职业生涯——连人都不顾哪还要管其职业发展。只有当管理思想演进到以人为本的时代,职业生涯思想才能真正出现,以人为本管理理论的出现是职业生涯思想产生所必备的条件。这种思想认为人不再仅是“经济人”,单纯地仅为报酬而工作;人同时更是“社会人”,因此要尊重人、重视人,即要以人为本。特别是对高级员工而言,心理上的成功感和满足感远胜于物质报酬。人本思想是现代职业生涯理论的基础,组织的职业生涯管理必须要遵循此道。“开展职业生涯规划,关键在于组织方面,在于组织要有以人为本的管理。”[16]综上所述,职业生涯思想在管理学学科内,从早期到当代历经了从反对到重视的嬗变。
五、结语
十八至十九世纪西方经济学、社会学、哲学及政治学等学科学者阐发了大量关于职业分工、职业选择等方面的思想,形成了他们初步的职业生涯思想;甚至早期管理学者的反职业生涯思想也为管理学后来进入人本时代而衍生出职业生涯思想提供了铺垫。这都是现代西方职业生涯思想的重要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