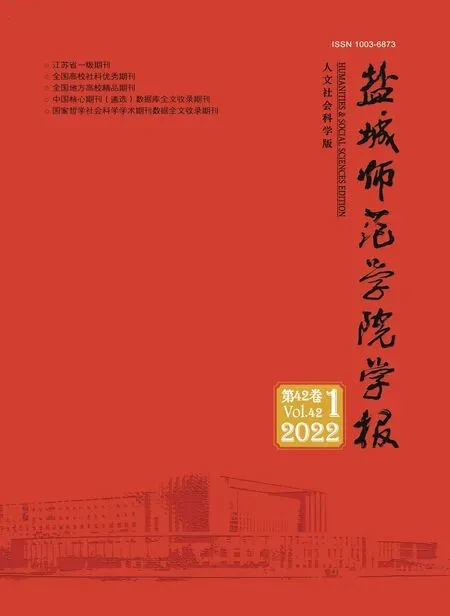沈从文《长河》谜题:“重造”的七个契机与一个可能
杨 雅,周晓风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1331)
一、《长河》的生成背景和“重造”意图
在沈从文的创作中,甚至在整个现代文学史上,《长河》都算得上是一个奇特文本。这样一部照黄永玉的话说本应写成“《战争与和平》那么厚”的小说,虽然中道夭折,又历经审查删改,仅存一卷共10万余字,但它所呈现的激进写作态度,充满现实粗粝感的美学特征,以及坎坷波折的出版经过,都值得我们予以充分注意。抗战时期,沈从文的小说写作相较于战前有所放缓,而关于文学、社会和政治的评论文章则越写越多。后者中,沈从文常常提到“重造”二字,地方“重造”、经典“重造”、民族“重造”等,不一而足。何为“重造”?纵观沈从文对“重造”的种种阐述,不难发现,“重造”的意思有两个:一是推倒不合理的旧事物,二是在此基础上重新创造符合理想和时代要求的新事物。可见,“重造”本是一种充满批判色彩的提法,它源自作家对现状的不安和不满。文学家表达自己思想的较好方式是文学作品,尤其是那些富有艺术自律性的作品,它们是一个作家“成其是”的关键所在。法兰克福学派代表阿多诺在谈到艺术自律性时曾说:“艺术的社会性并不在于其政治态度,而在于它与社会相对立时所蕴含的固有的原动力。”[1]相比于那些更直接的政论文章,《长河》这一基本上保持了小说样态的文本,也许更能见出沈从文以文学“重造”现实的实践经过和可能产生的价值。
《长河》的写作或可追溯到1934年。如《长河》的“题记”所说,早在1934年的那次回乡探亲时,沈从文便萌发了写作另一部与《边城》相对应的小说的愿望,尽管当时还仅仅只停留在构想或者说“预备”阶段:“我并不即此而止,还预备给他们一种对照的机会,将在另外一个作品里,来提到二十年来的内战……”[2]59凌宇认为这部小说是不曾被写出来的[3]219。在笔者看来,未完成的《长河》尽管未曾直接写到内战,却和沈从文预期的“另外一个作品”有很大相关性。和初次返乡被缪斯光顾一样,1937年底的那次返乡所耳闻目睹的一切,再度激发了沈从文写作的欲望。这一点从《长河·题记》与《边城·题记》的呼应上不难看出来,而沈从文于1938年7月30日写给张兆和的信里也说道:“(《长河》)与《边城》故事比肩,笔法同,人物不同。”[4]320正是因为沈从文在《长河》中刻画了一群处于战争氛围中的人,使得该小说相较于意图写成“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的《边城》而言,具有了显著的介入的意图。换个角度看,现实对《长河》的介入也是深刻的。也许,这本身就是一体两面的事情。
《长河》讲述的故事并不复杂,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所写的就是全面抗战前夕湘西地区“一些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与‘变’,以及在两相乘除中所有的哀乐”[5]。引发作者书写湘西今昔之变的原因,正是他在战时路过湘西时的所见所感。沈从文此次离京南下,实是迫于“七七事变”引发的战争威胁。日本侵略者的残暴和中国人或苟且或英勇的作为,共同为他的南行之路制造出一种紧张氛围。他在长沙八路军驻湘办事处拜访徐特立,在湘西和当地要人谈话并发表鼓励湘西人从军的演讲,种种行为都显示出他对抗日战争和湘西未来的关切。
在沈从文看来,一方面,湘西在观念上被人误认为是“匪区”,在现实中又遭受着外来势力的压迫。从湘西管窥全国,他发现整个民族亦不能团结向前。总之,一切亟需“重造”,抗战乃可胜利,民族方有未来。但另一方面,抗日战争又启发了沈从文,使他相信这场正义之战将是湘西人在血与火中证明自己的难得机遇,也是国家和民族振兴的难得机遇。1938年7月28日,他写信告诉张兆和,《长河》“用的是辰河地方作故事背景,写橘园,以及附属于橘园生活的村民,如何活”,这一点是现存第一卷所侧重表现的,而接下来将的内容是这样:“如何活不下去,如何变;如何变成另一种人。”[4]313这一部分内容按照计划亦应表现在第一卷中,但却遭遇了叙述延宕。在两天后的一封信里,沈从文又表示,《长河》将要续写“雷雨后的《边城》,接着写翠翠如何离开她的家,到……沅陵还是洪江?桃源还是芷江?”[4]317根据《长河》中关于省里往湘西地方调兵的传言来看,这里所谓“雷雨”者,应当就是指接踵而来的战争。问题就在于《长河》并不曾写到内战,更不曾写到抗日战争,仅仅铺陈开了一片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湘西社会图景,让人体会到一种来自战争的危机感。不过,我们不应该忽略,在沈从文的原计划中,《长河》应该有四卷。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长河》,只是理想中的《长河》的开头,占全文极小一部分。而这一部分,恰恰是在消解人的“重造”、民族“重造”和社会“重造”等“重造”的可能。因为这些“重造”并没有良好的效应,也未能阻止那场还未被写到的战争。然而,湘西地方如何经由“重造”来应对这场民族的浩劫,却是沈从文不得不思考的问题。或许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中,种种“重造”之路都走不通。倒是那浩劫本身,能够荡清所谓的社会历史背景。凡此种种思考,自然也被投射到文本中。
二、现实境遇中的七类“重造”
在战争还未到来时,湘西就已经处于激剧的时代变动中了。沈从文几乎是以一种歇斯底里的方式在描写这种改变,那些笑谑和讽刺的背后无不隐忍着悲恸的情绪。这种风格转变是沈从文抗战时写作特点的一个表征,即由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向。这意味着战时社会现实的疮痍和沉重对唯美文本的入侵,意味着湘西“牧歌”的丧失。但同时,就在“牧歌”乌托邦的崩析中,文本中闪现出一些具备“重造”社会现实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不仅是研究文本的有效入口,而且是为未完成的《长河》提供的待选道路。
尽管沈从文更着眼于书写湘西的新变,但《长河》中的大多数本地人,仍然保有着传统美德。这些敬天畏神的“美德”或许不那么“科学”,却显示出纯净的人性美。这也是鲁迅做出“伪士当去,迷信可存”[6]的激进论断的原因之一。在以往的写作中,这种“人性”被沈从文讴歌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并且认为这就是他建造“希腊小庙”所要供奉的偶像。“人与地”一章中,从有关买卖橘子的戏剧场面,到当地人“吃水上饭”的情形,再到妇女们的坚韧顽强,无不显示出这一群生活在沅水边的老乡们生活的淳朴、生命的严肃和面对自然时的谦卑。他们不虚伪不矫饰的生活方式,果真是一曲田园牧歌。这一点早早地便被苏雪林注意到,并且在议论中加以发挥,认为沈从文“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入到老态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廿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7]。如果苏雪林的判断是正确的话,那么,湘西人的这种“人性”一旦被发扬、被推广,中华民族便有了“在廿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的可能。这一未被现代都市文化和传统儒文化所侵染的充满原始意味的“人性”,将是“老态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得以“重造”的一种形而上的基础。这一点更明显可以从沈从文对都市文化的批判和对现代性的怀疑中看出。既然《泥途》《腐败》《八骏图》等小说中所展现的都市情况是如此的不堪,那么一种与其相异质的生存状态便被需要。也就是说,沈从文所建构的湘西原始的人性美,足以镜照以都市文化为表征的现代文化的堕落和软弱,也足以反讽它,更可以去改变它,以自身的优越性去“重造”它。可惜的是,这种美好的愿望只能存在于假想中。以弘扬“湘西式”的“人性”去实现人的“重造”和民族“重造”,这一可能性在《长河》中仅仅可以被识别——它是《边城》等系列有关湘西的书写的遗响——但还未来得及展开,便被庸俗现实给嘲弄了。比如,当地年轻的读书人本是有可能把当地人的美好品德带出去的人,但他们连自己都已经被都市所同化,遑论对湘西地方的好处加以研究和宣传。这就难怪作者在“题记”中要说:“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是的,这种美好“人性”不但难以被发扬,反而还正在消失。
原始生命的淳朴、热情和真挚固然可贵,但在现代化的语境中,那些可贵的“民族品德”毕竟已是明日黄花。罗宗宇认为,湘西地方业已显露出四种问题:动乱、落后、烟毒与统治的黑暗[8]。那么,是否可以靠引进来的模式,接受“现代化”的事实,并以“现代化”的内容,来对一个处于蒙昧或者说自在的湘西进行地方“重造”呢?从《长河》中不难看出,现代化的幽灵首先是以“纸烟”“罐头”“自来水笔”“白金手表”等物质形态深入湘西地区。这些看起来可以解决“落后”问题的东西,却如“题记”中所说的那样,“‘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可具体的东西,不过是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这些现代“奢侈品”虽然在技术上先进,但对湘西人的精神却是一种腐蚀。事实上,就连“烟毒”,也是随着现代文明一起涌入湘西的。当地年轻人在追求时髦的历程中逐步丧失了“治事做人的优美崇高风度”,生活变得轻浮而躁动,“只能给人痛苦印象”。在沈从文看来,现代商品对当地的影响更多的是负面的,而湘西人也不甚具备甄别、扬弃与自觉学习的能力。因此,他对现代保持忧惧,背后还“指涉着一个‘将来’的无爱的世界”[9]。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在近代中国行不通,同样,具备现代感的器物虽“已到了湘西”,却也不能承担起社会“重造”与地方“重造”的责任。那么,形而上的现代性是否能够“重造”湘西呢?在第二章“秋(动中有静)”中,读者将遇见一个象征性符号——“新生活”。正如一些论者所说,“新生活”是国民党中央势力的象征,但不可否认,作为一种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新生活”毕竟还具备一些积极因素。当地人对“新生活”充满喜剧性的反应,既反映出他们对那个惯于对湘西苗民实施压迫、剥削甚至屠杀的蒋介石政权的怀疑和恐惧,同时,对新名词的陌生,还意味着他们对新生事物的难以理解和出于本能的排斥。这种滑稽场面的出现,是因为政策制定者对国情对人民的不了解。不量体裁衣,不因地制宜,不从实际出发,单凭理念简单地引进现代化内容——无论这内容是形而上的还是形而下的——只能是徒劳,并且加重地方的骚乱。政府和地方的隔膜,使得“新生活”这一政策,以及“新生活”所代表的现代化生活方式,与湘西实际情况产生龃龉,再一次消解了社会“重造”与地方“重造”的可能。
保安队长的出现,拉近了《长河》与社会、时代与政治的距离。这里出现的保安队长是国民党政权里的丑恶面貌的一个典型,政治上蛮横霸道,生活上毫不检点,经济上巧取豪夺。他侵扰当地人的正常生活,掠夺腾长顺的橘子,挑逗单纯善良的夭夭。政党的权利已经侵入了这个世外桃源,而当地人却仍然处于一种蒙昧状态。那个曾经以宗法制为主要社会结构的湘西,业已经由外来势力而分裂出了对立的阶级。阶级对立,即指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压迫。文中关于乡民企图用一个大萝卜向有司请赏,却被委员所盘剥的刻画充满了讽刺意味。当地人的善良并不被长官所表彰,却反被利用,并且无处申诉。幸而年轻一代在自发的状态下萌发了反叛的意识,“气愤不过”,“火气上心”,幻想自己“当了主席,一定要枪毙好多好多人,做官的不好,也要枪毙”。这些内容集中出现在小说的最后一章“社戏”中,这似乎昭示出某种转折。总之,保安队长的不知收敛与三黑子充满挑战味道的话语,对统治者来说,都是一种隐患,而对中国现代革命历史的进程来说,则是一个极具意义的瞬间。正如列宁所说:“单是被剥削被压迫群众认识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而要求变革,还是不够的;要举行革命,还必须要剥削者也不能照旧生活下去和统治下去。”[10]正是以保安队长为代表的反动政权的荒谬,给了当地人要求革命的理由。统治者的疯狂与被压迫者的反叛意识,共同打开了国家“重造”的契机。可惜的是,在那惊喜的时刻,湘西人虽然有琐碎的反抗和言语上的挑战,却不能从根本上认识到这种压迫是统治者的阶级特性使然,也就无从把自己阶级的力量凝聚起来共同抵抗外来的入侵和压迫,也无法翻身起来打碎不合理的国家机器,而创造一个新的合理的国家。
但《长河》所揭示的问题远不止于此。倘若我们把《长河》看作一个整体,同时又把它看作沈从文所有创作中的一个新站点,就会发现《长河》本身还寄托着作者经典“重造”的愿望,当然,散文集《湘西》也可作如是观。1938年9月,沈从文在《谈进步》中写道:“凡希望重造一种新的经典、煽起人类对于进步的憧憬,增加求进步的热情和勇气,一定得承认这种经典的理想,是要用确当的文字方能奏效的。”[11]所谓“确当的文字”,应该是指语言的精确与风格的恰到好处。战争中的中国是苦难的中国,为了更准确地把握住此岸世界,作者放弃了他的“湘西牧歌”。相较于意图写成“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的《边城》而言,《长河》对现实的介入可以说是有目共睹的。同时,《边城》是一部完整——甚至可以说是一部完善——的作品,《长河》却被删改得残破。它显现出一派劲健粗粝的风格,这和《边城》的玲珑剔透大异其趣。如果说文本被删改是不得已的话,那么文风的选择则可以视为作者有意选择的一种书写策略。用席勒的话来说,这种策略使得沈从文从一个“感伤的诗人”变成了一个“素朴的诗人”。他放弃了“感伤诗人”所可能获得的那种无限性,放弃了《边城》的那种纯粹且永恒的审美价值;写作趣味则一改对“超脱和宁静”的追求,开始为战时的现实生活所激动,甚至意图用文字“引导”读者“回到生活中去”,通过经典“重造”及时地影响读者[12]。这是因为在他关于湘西的书写中,以往那种人与自然合为一体的情形,已经被战局所肢解。在现代化的侵袭之下,湘西人从一种与环境相融合的自然状态,进入到一种更富有阶级意味的社会状态之中。作者往昔的“唯美主义”式的浪漫寄托,一经战火的检验,便成为了梦幻泡影。如果说,沈从文战前包括《边城》在内的一批作品还属于凌宇所说的那种“从精神到精神的思辨”[3]195的话,那么,在《长河》中他则开始用一种更直接的方式正视现实。这也使得《长河》乃至他战时的整个创作都更富有现实主义倾向。《长河》也具有一些现代主义的色彩,但在强大的现实主义倾向面前,现代主义已经由一种思想降格成了一种方法。在今天看来,《长河》的缺陷主要在于它的未完成与被删减,许多飘浮的意义还未被文字有效地凝固下来。因此,就算《长河》寄托了沈从文经典“重造”或文运“重造”的理想,那这“经典”也是一个未完成的“经典”,而“文运”的“重造”更是因为错误的文化政策而遭遇了惨烈的滑铁卢。
三、革命战争:“重造”的必由之路
在沈从文的“重造”家族里,人的“重造”、民族“重造”、社会“重造”、地方“重造”、国家“重造”、经典“重造”、文运“重造”这七位主要成员都相继在《长河》中得到了施展本领的天地,但可惜在那些充满可能性的契机里,它们都被冷峻的现实给压抑住了。连年内战和日本的侵略都说明了这七类“重造”的功用是有限的。事实上,湘西这样一个长期处于中央势力所压迫的苗区,中国这样一个处于内战又面临着日本侵略的国家,都是缺乏“重造”之社会现实基础的。政府的反动、生产力的落后和人民对自身阶级的认识不足,共同制约着《长河》中体现的七类“重造”。
在《长河》的开篇,沈从文一如既往地营造起一个独立于主流社会以外的湘西世界。然而,这个湘西世界在第一章“人与地”中甫一完成,便开始接受来自外界的考验。这一点是《长河》比之于沈从文此前湘西书写的最大不同处。比如,《阿黑小史》的故事发生在这样一片天地:“人人各安其业,无匪患无病灾,革命也不到这地方来。”[11]232《边城》中虽驻扎有戍兵,但“除了号兵每天上城吹号玩……兵士仿佛皆不存在”[2]68。沈从文在写作《长河》时,极大地动用了他的现实眼光和经验。相较于《边城》,《长河》有明确指涉现实的痕迹。小说中写到的“新生活”,即是最显著的例子。那么,《长河》所根植的现实,究竟是怎样一种现实呢?自清嘉庆年间直至1936年,湘西苗区一直实行着“屯田制”。统治者抢夺苗民私田充公,以绿营军屯种、汉民屯丁屯种和苗民耕种屯田后交租这三种方式来经营屯田。苗民的生存资料被大幅削弱,而1934至1936年,水涝旱灾接连侵犯湘西,苗民的基本生存受到极大威胁。先前主持湘西军政的“湘西王”陈渠珍在与红军的战斗中失利,率领的一万余军士死伤与被俘三千余众。随后,他又拒绝了苗民的减租申请,这直接触发了1936年的苗民起义。苗民组成“湘西革屯抗日救国军”,要求政府“废除屯田”“抗日救国”,湘西地方自治政府由是垮台。湖北省主席何键本欲趁此机会征服湘西,却弄巧成拙,反而在战斗的失利中被撤换。1938年初,也就是沈从文正身处湘西时,国民党继续对“湘西革屯抗日救国军”进行镇压,失败后则以民族大义为幌子进行招安,将“湘西革屯抗日救国军”改编进国民军,意图假借日本人之手消灭湘西势力。根据《长河》中有关“新生活”的内容,我们可以知道小说的时间起始应该就是1934年左右无误。而这一段时间,湘西地方恰是战火频仍。
《长河》的生成既离不开战时局势和湘西现状对他的启发,而好友戴望舒主持的《星岛日报·星座》提供的平台也很重要。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沈从文全集》里读到的《长河》与其初刊本存在着出入。《沈从文全集》收录版本的底本是昆明文聚出版社于1945年出版的单行本,而这个单行本则是在6万余字的初刊本的基础上增改到10万余字后才形成的。此外,沈从文还在1944年为单行本增添了大量批注,解释了不少方言和不常见的专有名词。批注是为了消除阅读的障碍,让文本可以在更广阔地域里更顺利地流传,这可以看出沈从文对《长河》所抱有希望之大,对现实问题关注之热切。关于《长河》的版本问题,唐东堰教授和他的研究生杨熔合作的《〈长河〉版本源流与修改考释》一文做了详细的梳理。其中,初刊本与单行本之间的差别,最能说明在那个风云际变的时代里,文化政策和审查制度的状况,以及作者心理的转变和发展问题。初刊本中,作者对蒋介石政权及政权下属人员保安队长等人的描写显得较为暧昧。到了初版本中,作者却通过人物之口,表达了对蒋介石的肯定态度,同时,对保安队长的描写却更辛辣。后者或许是因为审查制度的严苛,对保安队长的讽刺和挖苦不得不有所保留,前者却似乎没有忌讳国民党手下的检察机关的理由。归根结底,这还是因为沈从文眼见了中下层掌权者的腐败,却仍然寄希望于领导者的勤恳和英明。无法从阶级斗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观照当时的社会历史,是沈从文的局限所在,使其不能从理论上把握住时代与战争的本质,自然而然地也就影响了《长河》这样一部立志于宏大叙事的长篇小说的写作。
但是,沈从文不是革命家,不是唯物主义的哲学家,而是一位作家。作家用他特殊的手段去认识和理解时代和社会。尽管上世纪三十年代末的沈从文并不具备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和阶级学说的角度研究湘西问题、中国问题的能力,但《长河》却生动形象地反映出了湘西地区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阶级与经济难题。罗杰·加洛蒂在一篇研究圣琼·佩斯的文章中注意到了圣琼·佩斯身份的双重性,他认为:“作品本身的见证比作者的意愿还要更有分量。”[13]反观《长河》对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湘西地方的书写,我们同样会发现,尽管他仍然倾心于“希腊小庙”,同情那些保有传统美德的湘西人,但现实生活的危难警醒着他,让他不得不直面一个不断瓦解的宗法社会,正视那场即将到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事实上,早在写作《记丁玲》的年代,沈从文就认识到“一页新的历史,应当用青年人的血去写成”,只是丁玲和胡也频“加入这血肉相搏的斗争里,对于某种理想的实现,常作超越历史条件以上的乐观”,因此青年左翼革命者总有“不可形容的天真”[4]141-144。但时势越发严峻,再也不给人顾虑周全一切再行动的环境。在《长河》里,沈从文终于尝试着跳出“湘西牧歌”的藩篱,从对自己内心理想和彼岸世界的描写,跃进到了对现实社会或者说此岸世界的同情和观照中。也就是说,沈从文在缺乏阶级自觉的情形下,仍然以现实主义文学的特殊手段认识到了中国现代社会进程中战争前夕的危机时刻,把握住了那一阵紧张跳跃的脉搏。七类“重造”的可能性的破碎,最终将会导出那场残酷战争。尽管《长河》的叙述在战争信号越发明显之际戛然而止,但就现存的章节而言,我们已经可以在其中感受到作家情感的悲愤和那个时代对湘西的重压。借用恩格斯评价巴尔扎克的话语来说,在《长河》中,现实主义实现了它“最伟大的胜利”。在《长河》中,宁静美好的“边城”不见了,出现的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战前社会。这里的安静是纷乱前的安静,这里的光亮是黄昏的夕照。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看来,七类“重造”得以实现的前提,是一场彻底的革命战争,一场能够创造一个合理合法的社会政治环境的战争,说到底,就是一场赶走侵略者推翻反动政府的战争。《长河》的危机,就是中华民族现代社会的危机,而当这种危机酝酿到极端时,将擦出革命的火星!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湘西甚至中国而言,革命战争都并非目的,却是实现种种“重造”目的的先决条件,是“民族的要求和需要的不可遏止的表现”[14]。这等于说,未竟的《长河》还存在着一个没来得及被写出来的契机,那就是战争,是残酷的战火所附赠的“一切的‘重造’”。当然,历史不能假设,所以我们仅仅只能根据上文所述的种种迹象,把战争带来的“重造”视为一个可能。而这个属于文本的“可能”,却是中国现代革命历史给出的唯一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