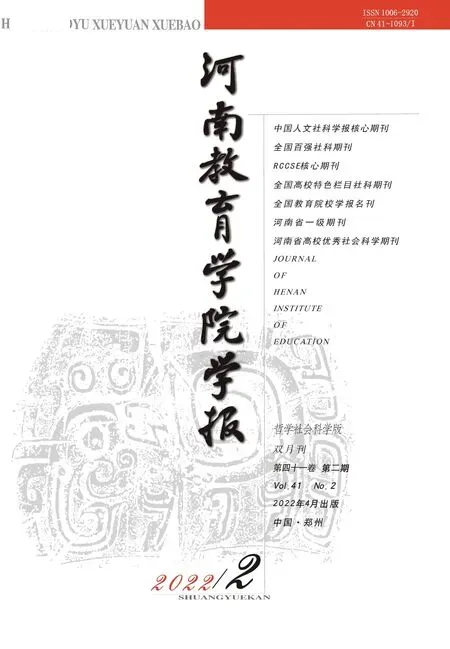性别、种族与阶级:一个关于女性主义文化理论的问题
——以电影《绿皮书》为例
吴新纶, 刘秀丽
一、引语
女性主义文化理论是不是只为并且只能解决女性问题?当波伏瓦提出“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1]8这一论断时,这个疑问就随之产生。“女性”当然是女性主义文化理论的中心,但当女性主义这种特色鲜明的文化理论从单纯的口号话语深入到社会肌理,借用“女性”视角打量和考察人类及其存在的组织、制度、现状和历史的时候,就会发现这种文化理论具有强烈的先锋性和强大的战斗力。它不仅可以作为考察性别问题的利器,而且在撕开性别的面纱之后,对于考察与性别问题纠缠在一起的阶级问题、种族问题,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这种先锋性和战斗力,在电影《绿皮书》中得到呈现。
一般来说,对电影《绿皮书》的探讨集中在种族与阶级问题层面,而不是性别层面,这与电影所要表现的主题也相符合。不管拍摄黑人还是白人、上流社会还是下层社会,电影镜头总在提醒我们:它在避免性别问题,比如托利·瓦纳朗格和妻子的友爱互动,家庭聚会中男女两性的均等,南方黑人劳作场面中男女老幼的普遍性。但女性主义的方法和视野却给我们带来奇妙的观影体验,帮我们穿透飘浮于《绿皮书》表面的迷雾,直抵影片内核,发现一片新的天地。这片天地既是影片《绿皮书》的,也是女性主义文化理论的,更是时代与未来的。
二、性别问题:唐·雪利的女性色彩
电影《绿皮书》讲述的故事很简单,意大利裔底层白人托利·瓦纳朗格被雇佣护送身份显赫的黑人天才钢琴家唐·雪利前往美国南方巡演。在一路同行过程中,二者逐渐放下对彼此的偏见和歧视,互相理解并成为彼此信赖的朋友。在南部各州的演出旅行,既是呈现美国白人对于黑人的歧视的叙事过程,也是黑人雇主和白人司机之间超越种族偏见建立跨种族友谊的过程。[2]这部电影显然抓住了这个时代美国文化中的热点问题:男性友谊、种族、阶级以及同性恋。男性间的友谊是文学史上一个长远的话题,在社会生活中也一直为人津津乐道,这和男性一直掌握着文化主动权和话语权密切相关。社会甚至对于男性之间的情爱也表现出一定的宽容度——尤其是相较对待女性间的同性爱而言。李安的电影《断背山》,就对男人间超乎寻常的关系表现得相当唯美。《绿皮书》中男主人公之间的友谊不属于一见倾心、相见恨晚型,相反,两个男人第一次见面就彼此成见颇深,特别是托利·瓦纳朗格对唐·雪利既有白人对黑人的本能憎恶,又有穷人对富人的妒恨,对“黑而富”之人的复杂情感。所以,两个男人开始的旅程并不愉快,托利·瓦纳朗格甚至吃掉了妻子为唐·雪利准备的食物。
但男性间的友谊只是影片表面的浮光。《绿皮书》好像一个包装精致的盒子,只有打开盒子才能看到里面的内核。导演在这个盒子里放置着三块具有对立共生关系的蛋糕,分别是男与女、黑与白、上层与下层,它们喻示着三层重要的关系:性别关系、种族关系和阶级关系。其中,性别关系在电影中的表现最为隐晦。
女性主义文化理论有一个预设的男女性别二元对立前提,即女性天生是弱势的,是被统治者;男性天生是强势的,是统治者。从性别到社会,尤其是注意到黑人女性的社会地位,人们发现,男女性别的二元对立,已经在语义上被置换为社会地位强弱的二元对立。贝尔·胡克斯的《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明确指出,相对于白人妇女,在白人家庭帮佣的黑人妇女才是真正的弱者。这部颇有影响力的著作的第一章就是讨论黑人妇女问题的。[3]1强弱关系对性别关系的置换,是女性主义文化理论的研究重点之一,它开阔了女性主义文化理论的研究视野。很多看似不相干的现象,看起来云遮雾罩的问题,放在这种置换视角下来看就能找到内部关联,从而寻得澄明透彻的答案。
性别关系在《绿皮书》中表现得非常隐秘,只有把钢琴家唐·雪利身上的女性气质从电影灰暗的色调中提取出来,放到光亮的地方观察才能够看清。从体格上讲,唐·雪利瘦削、柔弱,的士司机托利·瓦纳朗格孔武有力;从性格上讲,唐·雪利被动、柔弱、内敛,而托利·瓦纳朗格性格粗犷,举止豪放;从行为上讲,唐·雪利遇事隐忍、忍气吞声,举手投足投射出女性的优雅色彩,而托利·瓦纳朗格攻击性强,遇到不喜欢的情况就挥拳相向。显然,他们一个被塑造成被保护者,另一个则充当了保护者。
在二者交往的过程中,虽然在知识层面上,唐·雪利是托利·瓦纳朗格的指导者,比如他教托利·瓦纳朗格写精美的情书,但是在行动上,唐·雪利却一直在接受托利·瓦纳朗格的保护,每当唐·雪利受到欺辱时,都是托利·瓦纳朗格出面护其周全。当唐·雪利受邀演出邀请方却不准备规定品牌的钢琴时,当他在白人的酒吧被集体殴打时,当他在公共浴室赤身裸体扣着手铐时,托利·瓦纳朗格总是像英雄一样出现,影片有意识地在这些情境中将托利·瓦纳朗格拍摄得高大、强壮。影片中突出的强弱形象对比超越了人物的生理性别,总是置于解决问题位置上的托利·瓦纳朗格充满男性的阳刚气质,而总是处于被拯救位置上的唐·雪利饱含女性的柔弱色彩。
影片显然没有打算让观众一下子就洞穿这种性别角色关系,毕竟它的主要叙事是围绕两个男人展开的。但我们依然可以从很多隐晦的细节找到电影的喻指——不仅是那些女性化的柔媚的手势、在自己的处所穿着宽大而华丽的睡袍这些物理层面的明喻。托利·瓦纳朗格面对啰啰嗦嗦的唐·雪利时,用自己的妻子来类比唐·雪利在他心目中的印象,这表明唐·雪利的身上具有明显的妻性特点。而妻性,是女性诸多内涵中最具女性色彩的一种。唐·雪利对此非常清楚,他在和托利·瓦纳朗格争执的过程中说出自己“不够男人”,并据此发出对自我身份认同的质疑。这种性别上的错位,也与他特殊的性取向,与他和妻子失败的婚姻具有因果关系。
从性取向的角度来分析,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同性恋问题与种族问题一样尖锐。同性恋者比异性恋者更容易被聚焦。他们会被歧视,会受到严重的不公正对待。作为被观察者,同性恋者是被俯视的,与异性恋者相较处于社会人群关系的低端,同性恋者的社会性别处境在当时相当于男女关系中的女性性别的弱势处境。
从夫妻关系的角度来分析,在家庭内部,夫妻关系可能存在的不平等是社会性别关系的缩影。不管是先天如此,还是按照波伏瓦所言女性的第二性别是后天生成的,在一个家庭中,男性似乎有着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女性似乎是天然的弱者。影片中唐·雪利性别取向的特殊性加重了他出生即有的种族上的弱者气质,所以,面对欺凌、嘲笑和漫不经心的接待,他总是选择第二性的逆来顺受,面对美国南部警察看见他既是黑人又是同性恋者的时候歧视的目光,他习以为常,他想象不到自己可以拥有反抗的权利。特别有意思的是,唐·雪利的同性恋对象是白种人。这种跨越种族的同性恋可以理解成导演对美好未来的一种期许,也或许,是导演的一个讽刺。
因此,在电影的后半段,当唐·雪利与托利·瓦纳朗格之间建立起深厚的友谊之后,再一次面对俱乐部老板不让唐·雪利在餐厅就餐的情形,唐·雪利劝告托利·瓦纳朗格放下拳头,他说:“没关系,我会表演的,只要你让我演!”到这里,导演试图表达的是两个男人的友情达到了高潮,彼此之间的信赖充分建立起来。但是观影者也明显可以感觉到一种不适——根据爱奇艺、腾讯视频等的弹幕也可以看出,许多观众看到这里都会有类似的感觉——那就是唐·雪利对托利·瓦纳朗格呈现出的信赖不是一种基于平等感的信赖,而是一种类似驯服感的信赖,是一种孩童对于长者、女性对于男性、弱者对于强者的信服,盲目而又完全的信赖。这样轻易的、盲目的信赖,是不是可以反观出唐·雪利在此前的日常中一贯的无助和柔弱,一贯的女性性别的弱者立场?
天生的黑皮肤,加上女性化的角色自觉,让唐·雪利雪上加霜。他很难在一个白人社会中找到属于他自己的合适存在。所以,他既骄傲自负,又卑躬屈膝,对来自白人社会,尤其是白人男性的欺凌逆来顺受。这种逆来顺受是女性主义者非常熟悉而且非常厌恶的。因此,尽管影片的结尾试图用圣诞节的一杯红酒来消弭所有的问题,但我们看到加诸唐·雪利身上的枷锁极其深重,且已然成为一种自觉,事实怎么可能如影片所愿?
三、种族问题:香蕉人的女性特征
唐·雪利从种族而来的黑皮肤,是他在美国这片土地上生活的困境之源。这种肤色决定了人们认知他的第一印象,且无法改变。因为经年累月的肤色之累,所以唐·雪利才发出自己“不够白”的哀叹。这一方面来源于肤色上的无法改变;另一方面,也来自他内心极度敏感的黑人认同。他并没有以自己的黑人身份为耻,他对生而为黑人是认同的,他没有白人天生高贵、黑人天生下贱的观念,这一点难能可贵。他之所以要冒着明知存在的危险却放弃纽约更舒适、便利的生活,是想通过自己的音乐才华为黑人赢得尊敬和尊严。这一点尤其值得敬佩,并引起了托利·瓦纳朗格深深的思索,他逐渐理解唐·雪利多年来为什么主张靠隐忍来赢得尊严。刘思岑从叙事能量的角度对《绿皮书》当中的种族议题的观照也颇为有趣:“电影《绿皮书》中的‘种族歧视’主要采用的剧作模式和叙事能量为: 以喜剧形式呈现种族歧视的悲剧内容、由冲突对立转向人性回归的价值期待、由角色固化转向个体觉醒的原型能量。”[4]显然,影片中有比此更值得关注的内涵。
唐·雪利“不够白”,同样也“不够黑”。在观念上和文化上,他的黑人典型性并不突出。托利·瓦纳朗格一边吃着炸鸡一边和他探讨自己对黑人的认知。唐·雪利不同意托利·瓦纳朗格的观点,他认为黑人爱吃什么食物、爱听什么音乐这样的说法是偏见,而他自己就是和偏见不一样的人。恰恰是这种不同,让他无法融入自己的黑人种族,其他黑人邀请他一起打球,他无所适从,最后逃跑了事,乃至引出酒吧里的祸患——他无法融入自己的族群。这种和既有族群的出离状态,与唐·雪利“香蕉人”的特征有关。
香蕉人又叫ABC(American-Born Chinese),最初意指出生在美国的华裔。他们虽然在族群上是华人,但与移民赴美的上辈不同,自幼受到美国文化、美国教育的熏陶,在语言习惯、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价值立场等方面已经基本西化。现在香蕉人的使用日渐泛化,已从最初具有美国白人意识形态的亚裔人群,演化为指代所有对自身族群身份存在不同见解的人群,包括具有白人意识形态的黑人、具有黑人意识形态的白人、具有东方意识形态的白人和黑人等。按照女性主义理论的中心与边缘观念,在白人社会里,香蕉人是身份尴尬的边缘人,扮演着他者的角色。但在母族(母国)里,香蕉人也是他者,也很难找到身份的认同。香蕉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他们与自身所处环境的主流群体有着天然的族群隔阂,但在意识形态上又融入了主流群体。对于主流群体而言,香蕉人的这种他者角色,在身份和社会地位上具有天然的女性特征。
在电影《绿皮书》中,唐·雪利是典型的香蕉人,也是典型的他者。影片的主题是黑与白的隔阂,所以有大量镜头来表现他在白人主流群体里中遭遇的不公正对待和尴尬处境。但影片也注重表现他与黑人族群的隔阂,除了以上提及的他拒绝了黑人的运动邀请,《绿皮书》还设置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桥段。唐·雪利的汽车抛锚在马路上,路边是大片的种植园,一些黑人劳工在种植园里劳作,他们好奇地看着白人托利·瓦纳朗格修理汽车,为黑人唐·雪利提供各种服务。唐·雪利站在路边默默地注视着黑人劳工。有那么几个瞬间,劳工们也凝望着他。画面是静默的,却起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在表面的静默中,劳工们内心的声音被释放出来,他们为白人与黑人之间服务与被服务关系的颠倒感到震惊。唐·雪利的内心声音也被释放出来,但这种令人震惊的声音要微弱一些,因为他一直很清楚作为一个黑人钢琴家在身份上的尴尬,很清楚一个普通黑人在社会上可能的际遇。他们对望着,隔阂感、距离感滋生在无声的镜头里。所以,在那个夜晚,唐·雪利的钢琴弹奏蕴含着一股巨大的力量,他在白天没有说的那些话,作为香蕉人所承受的一切迷惘与痛苦,都在他的钢琴声中爆发出来。这一切也正如周晓航所言:“唐对自身种族身份的认同危机是黑人族群缺乏身份认同感的写照,在进行自我身份认同的征途中,他的内心矛盾且孤独。”[5]
反观托利·瓦纳朗格,他并没有这种迷茫,尽管他表示相比唐·雪利而言他更加接近黑人,但是他清楚地明白自己不是黑人而是意大利裔美国人——是白种人。李银河在她关于黑人女性主义的论述中说:“白种人在社会结构中是强势群体;白种人总要从白种人的立场看他们自己,看他人,看社会。”[6]1虽然他过着和许多黑人经济水平相差不大的日子,可是白种人的身份意识掩盖了他接近于黑人的生活方式。他不存在认知上的身份错位,只存在社会生活中的身份错位。在托利·瓦纳朗格这里,身为白人的优越感和处于社会底层的生活现状之间的错位冲突原本不明显,但黑人老板的存在凸显了这种身份错位。
从唐·雪利和托利·瓦纳朗格的身份错位中我们可以看出二者关系的滑稽之处,即白人不“白”,黑人也不“黑”。女性主义文化理论认为人们应该允许白人可以不“白”,黑人也可以不“白”,人们应该破除对族群的成见,尽管它并未提出破除成见的具体方法,尽管这对身处女性身份的群体和个人而言都是一个极其艰巨的任务。
四、阶级问题:谁在扮演男性角色
影片在偷偷把钢琴家唐·雪利置换成一个女性角色的同时,又非常机智地把他设置成一个“上等人”:他受过很好的教育,是著名的钢琴家,一个人住在如“城堡”一样的豪宅里,举止文明有度,优雅大气,是个优秀的资产阶级绅士。司机托利·瓦纳朗格则面临失业,经济困顿,靠吃热狗比赛获得50美金来付房租,是个典型的“无产阶级”角色。不难看出,电影《绿皮书》中,唐·雪利和托利·瓦纳朗格的关系,隐喻着阶级关系,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爱恨情仇。
阶级关系是女性主义关注的另一重点。当他们发现仅仅聚焦性别并不能解决女性问题的时候,开始追问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他们看到,资产阶级女性的诉求与无产阶级女性的诉求存在巨大的差别。同样在姐妹阵营里,资产阶级女性(不论黑人还是白人)对无产阶级女性(不论黑人还是白人)并没有表现出真正的同情心和同理心,资产阶级女性雇佣无产阶级女性时,一样会压榨剥削她们。资产阶级女性无法抛弃来自资产阶级的优越感,也不会主动去抵制阶级压迫,反而可能成为实施阶级压迫的行为者。贝尔·胡克斯说:“共同压迫的思想是一种错误而虚伪的说法,它掩盖和混淆了妇女们各种复杂的社会现实的本质。性态度、种族主义、阶级特权和其他偏见把妇女们分裂开来。”[3]52贝尔·胡克斯看到了女性群体的复杂性并对她们进行了分化理解。在她这里,女性主义文化理论已经超越性别关系,走向了更为深远的社会关系:阶级关系。她发现,阶级之间的鸿沟是造成女性悲剧的深层次原因。李银河在一段对女性所遭受的天生压迫的论述中也侧面佐证了阶级压迫的普遍性和根本性:“在不同的年代和不同的文化当中,男性也受压迫,但是他们是由于属于某个阶级或阶层的成员而受压迫。”[6]90
《绿皮书》中的唐·雪利带着鲜明的资产阶级气息,他富有、优雅、睿智、声名日隆,当然还有傲慢和对无产者的偏见。初见托利·瓦纳朗格时,他是一个坐在王座上的黑人。高高在上的唐·雪利昂着头,对托利·瓦纳朗格提出各种要求——这样的姿态让无产者托利·瓦纳朗格感觉很不舒服;途中,唐·雪利对托利·瓦纳朗格百般挑剔,他看不惯托利·瓦纳朗格的生活习气、嫌弃他粗鄙的语言,试图以自己为模板,教托利·瓦纳朗格学会举止优雅,礼仪得体。唐·雪利对无产者托利·瓦纳朗格的排斥、否定,来自属于他的阶级意识形态的优越感。阶级关系实际上是一种意识形态关系,来自不同阶级阵营的人往往彼此看不顺眼,就如唐·雪利与托利·瓦纳朗格,在影片的前半段,他们几乎出自本能地彼此厌恶、相看相厌。
关于阶级关系与女性关系,贝尔·胡克斯在《女性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中说:“女权主义斗争轻易地被同化并且服务于保守势力和自由女权主义者的利益不是偶然的,因为美国女权主义已经变成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3]10我们由此看出女权主义的复杂性,它已经不再是女性争取平等权益的单纯工具了。贝尔·胡克斯强调阶级和意识形态,试图以它为钥匙来打开不同阶级女性之间的关系并探寻其背后深隐的原因。如此一来,女权视角下的阶级身份也会被赋予一种性别色彩,按照社会关系的强弱相对,阶级的强弱决定了谁在社会中扮演强硬的男性角色,谁扮演弱势的他者。唐·雪利正是这样的一个角色,他与上层阶级站在一起,与统治阶级享有共同话语,并与处于话语中心的人们一道对处于话语边缘的人们施加某种影响。我们可以从影片的许多桥段里面看到这种中心话语对边缘话语的影响,例如唐·雪利教托利·瓦纳朗格写信、多次纠正他乱扔垃圾的行为、告诫他不要偷盗。在这一点上,唐·雪利是强势的男性。
唐·雪利对托利·瓦纳朗格下意识的教导隐含了某种根深蒂固且广为接受的偏见:处于社会边缘的无产者即底层民众是粗俗的、愚昧的,他们的言行举止需要接受作为社会精英的上层阶级的矫正和教育。影片毫不隐讳地将唐·雪利塑造成了一个教育者形象,将托利·瓦纳朗格塑造成一个可以被教育好的受教育者形象。托利·瓦纳朗格捡起了他随手丢在地上的饮料杯、学会了用优美的句子写信,而唐·雪利允许托利·瓦纳朗格保留那块偷来的石头以及吃炸鸡的情节则更像是一种老师对学生的一些小毛病的宽容。
贝尔·胡克斯意识到“资产阶级白人女性”这一上层女性的存在,从而发现了女性内部的不平等与分裂。资产阶级白人女性不关心底层妇女的权益能不能真正得到保障,她们只在乎在男权社会中如何利用自己的女性身份争取特权。实际上,底层黑人男性甚至在资产阶级白人女性的面前也同样在扮演着弱者的角色,而黑人女性则在剥削链条中处于最底层。女性群体本身的四分五裂,原因并不在于女性本身,而在于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阶级对立、剥削和奴役。阶级对立、剥削和奴役的存在显然不是因为性别对立。
《绿皮书》采用了一些障眼法来粉饰阶级关系,一方面是唐·雪利教育指导托利·瓦纳朗格,另一方面,是托利·瓦纳朗格实际上也改变了唐·雪利。表面上看来,这似乎只是一个上流社会精英与一个底层劳动者之间关系的改变。由于生活习惯和教养的不同,人们之间存在个人素质和行为观念的差异,这种差异看起来微不足道,甚至是可以抹平的,上流社会和底层是有沟通的通道的,影片结尾唐·雪利敲开托利·瓦纳朗格家的门,大家会心一笑便是证明。但阶级差异是否可以如影片表现的那样一笑就消失了?为什么唐·雪利对托利·瓦纳朗格的教育看起来那么天经地义?为什么托利·瓦纳朗格接受起来毫不迟疑?为什么托利·瓦纳朗格就一定粗鄙、唐·雪利就一定优雅?为什么托利·瓦纳朗格感动唐·雪利的更多的是他对后者的保护?仅仅是因为女性化的唐·雪利需要一个勇猛汉子的保护,黑皮肤的唐·雪利内心的由于“原罪”般的自卑需要白人英雄的鼓励?不尽然。阶级鸿沟并没有被唐·雪利腼腆一笑填平,他所代表的阶层,不管是白皮肤的传统资产阶级还是新晋的黑人资产阶级,仍然会对底层抱有各种偏见,比如认为底层是需要教化和修正的,他们高高在上的姿态几乎成了潜意识,随时会在某个不经意间流露出来。资产阶级不会放弃手中的特权。唐·雪利并不处于资产阶级权力中心,他不过是这个阶级的一个边缘化个体罢了。即使如此,主导他言行举止的意识形态依然是资产阶级的。
唐·雪利的后天身份是优雅的知识分子,是著名的钢琴家,是有产者,他矜持而文雅,有上位者的优越感。但他的先天身份是黑人,先天肤色具有“原罪”,几百年来面对黑人族群所承受的欺凌、压榨等不公正,他同样需要承受。况且他又具有女性化的气质,不自觉地向粗犷的同伴寻求保护。所以很多时候他是沉默的,内心风云诡谲,脸上波澜不惊。虽然他与无产者托利·瓦纳朗格来自完全不同的社会阶层,但阶层边缘人与白人资产阶级女性一样,并没有多少话语权。事实上唐·雪利也相当于扮演了一个资产阶级白人女性的角色。正如他在剧中说的那样,“他们请我去弹钢琴只是因为觉得这样很有文化感而已”。唐·雪利的尴尬在于,他的社会身份是男性,而对于请他去弹钢琴的富人们而言,他的社会身份是女性。
五、结语:三重阻隔幻梦
这样,我们看到了《绿皮书》的勃勃野心。以杨蕾为代表的一种观点认为《绿皮书》是对美国黑人生存状态的真实书写。[7]这样的评判稍微单薄了一点。从女性主义文化批评理论的角度观察《绿皮书》,它的内蕴更丰富,也更有层次感。影片通过两个男人的友谊设置了三组二元对立或者说三重阻隔:男性与女性、白人与黑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并且试图为这三重阻隔搭建沟通的桥梁。方法是聪明的,它为黑白关系中处于弱势的黑(唐·雪利)添加资产阶级符码,并赋予阶级关系中处于强势的资产阶级符码相对弱势的女性气质;反之,白人托利·瓦纳朗格却与底层黑人的精神气质相似,他身上被赋予的是无产阶级符码,但同时具有强烈的男性气息。影片以冲突阻隔开始,以一种浪漫主义的乌托邦式结尾:代表上层阶级的唐·雪利为下层的托利·瓦纳朗格开车,身为白人的托利·瓦纳朗格彻底接纳了黑人唐·雪利并邀请他参加圣诞夜的家庭聚会。王霞认为,唐·雪利通过杂糅白人文化和黑人文化,在处于白人和黑人双重边缘的生活状态中最终找到了平衡点,重新成功建构了自己的文化身份,从而探寻到生活的方向,向着新生活勇敢地迈出了新的步伐。[8]肖聪也认为,唐·雪利和托利·瓦纳朗格之间不再有“黑”与“白”的界限,他们之间不再有种族歧视和隔阂,只有可以温暖彼此的纯洁友谊。“黑”与“白”的代表人物从最初的对立转变成“黑”与“白”的真正融合。[9]但是若从女性主义文化理论的角度去思考,我们理应深入到一个更为本质的问题:导演所导的真的是真相吗?
一种黏黏糊糊的美好情景展现在影片的结尾:阶级、性别、种族差异被消解了,不同阵营的人们和谐相处,一笑泯恩仇。影片以最小的成本(两个男人的友谊)取得了无限大的收益:阶级对立消弭、性别不平等消失、种族矛盾得到化解。文源将之解读为一种身份认同的融合。[10]这是一种多么美好的憧憬!但显然,这不过是一个美好的梦境而已,是创作者的一厢情愿。
女性主义以其对社会入微的洞察,告诉人们若要彻底摆脱女性困境,首先要解决的是阶级矛盾,是种族歧视问题。否则,女性主义文化理论就不会有出路,女性,包括资产阶级女性和处于社会底层的黑人女性,都看不见前路明媚的曙光。如前所论,《绿皮书》欲盖弥彰的问题与女性主义谈论的问题高度一致,性别、种族和阶级的问题是唐·雪利的困境,是千千万万黑人女性的困境,也是所有女性的困境。女性主义文化理论对社会问题的烛照,从女性问题出发,深入到整个社会机理之下,并引发我们进一步的思考:女性的命运与前途在哪里?两性之间终能走向唐·雪利与托利·瓦纳朗格式的和谐吗?《绿皮书》采用绿色的封皮,是因为绿色代表着畅通无阻,导演希望有一天黑人能够不再受约束,去任何想去的地方。但绿色在影片里还被赋予了一种反面意义——歧视。[11]我们认为,在今天的西方某些国家里,任何试图弥合社会裂隙的尝试都只能说是在问题的表面黏着了一层鲜亮甜腻的糖衣,在糖衣之下,尽是女性主义文化理论已观照到而不能解决又亟待解决的各种问题。
“不仅是女性,也是每一个阶级、每一种性别的人都‘能拥有足够的钱,好去旅行,去无所事事,去冥想世界的未来或者过去,去看书,梦想在街头巷尾徘徊,并且让思想的钓鱼线深深地沉入到河水中去’。”[12]这种女性主义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文追求不谋而合,如果把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思想联系起来思考,未来女性主义文化理论也许会走上一条更为广阔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