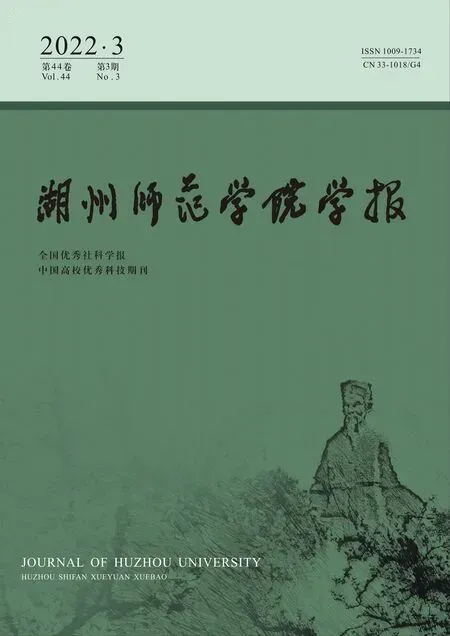子弟书《遣晴雯》作者考*
耿 柳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 沈阳 110820)
子弟书是我国北方曾流行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它首创于八旗子弟的笔下,盛行于清乾隆、嘉庆时期,衰于光绪、宣统年间,约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作为一种说唱艺术,子弟书已成绝响。但它流传下来的近五百篇曲目,有一部分仍在曲坛上流传,对其他曲种影响较大。在中国韵文发展史中,清子弟书之文本更是继唐诗、宋词、元曲、明传奇后的又一文学高峰。
一、子弟书作者考证的历史由来
子弟书的作者因为几乎不直接署名,所以,对于部分子弟书作者的认定,学界常持有不同意见。以子弟书作家韩小窗为例,其所留子弟书篇目最多,但学者们认可的篇目并不一致。随着考证工作的不断深入,被确认为韩氏的作品是逐增逐减的,一些佚名之作通过比对或佐证材料支撑,被归到韩氏名下,但是也有一些曾经被认定为韩氏的作品,经考证作者确另有其人。比如,著名子弟书唱段《忆真妃》,同名东北大鼓和易名为《剑阁闻铃》的京韵大鼓被当成韩小窗的作品传唱多年。任光伟先生20世纪50年代询问了当时在沈阳的社会名士和民间艺人,绝大多数人肯定为喜晓峰之作[1]1-2,启功先生则通过道光十五年(1835)隆文《忆真妃》序断定作者为春澍斋[2]244,对于《忆真妃》的作者,学界还曾有过缪东霖、王尔烈等观点。判定子弟书《遣晴雯》的作者虽然没有《忆真妃》那样复杂,仅集中在“芸窗”“蕉窗”之辨上,但至今尚无定论。
二、《遣晴雯》作者归属的四种观点
子弟书《遣晴雯》的作者,“芸窗”乎?“蕉窗”乎?各家学者有四种观点:(1)芸窗说;(2)蕉窗说;(3)芸窗、蕉窗或为同一人说;(4)无名氏说。
《遣晴雯》头回诗篇有“芸窗下医余兀坐无穷恨,闲消遣楮洒凄凉冷落文。”二回结尾有:“蕉窗人剔缸闲看情僧录,清秋夜笔端挥尽遣晴雯。”前后分别嵌入“芸窗”“蕉窗”,因此造成了子弟书研究者对此篇作者的不同解读:(1)标注作者是芸窗的主要出版物有:郭精锐等编《车王府曲本提要》[3]28;昝红宇等编《清代八旗子弟书总目提要》[4]450;陈锦钊辑录《子弟书集成》[5]1387。(2)标注作者是蕉窗的主要出版物有:胡文彬编《红楼梦子弟书》[6]198;关德栋、周中明编《子弟书丛钞》[7]324-327;陈新编《中国传统鼓词精汇》[8]776。(3)黄仕忠等著《新编子弟书总目》记:作者芸窗……或为蕉窗,或原即同一人[9]456;林均珈编著《古典文学丛刊:红楼梦子弟书赏读》注作者芸窗(或作蕉窗)[10]311-322。(4)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辑校的《清蒙古车王府藏子弟书》[11]332等书未标注作者信息。
四种说法并存。部分研究者撰文笃定作者为芸窗,并否认蕉窗说;部分研究者则将可能性列出。笔者此文分享所知信息、分析所得资料,以便对子弟书《遣晴雯》的作者考证得出一个客观判断。
三、“芸窗说”的学者角度
陈锦钊先生《论〈清蒙古车王府藏曲本〉及近年大陆所出版有关子弟书的资料》(1)《论〔清蒙古车王府藏曲本〕及近年大陆所出版有关子弟书的资料》原载《民族艺术》1998(4):157“海外专稿”;2018年《陈锦钊自选集》收入此文并修正了一些文字,此稿引用自《陈锦钊自选集》。:“如《红子》198-205、《丛钞》324-330所收录《遣晴雯》二回,作者均题‘蕉窗’,乃是根据本曲结尾“蕉窗人剔缸闲看《情僧录》,清秋夜笔端挥尽遣晴雯”(上句《红子》作蕉窗氏剔烛……)而来,但本曲的诗篇第七、八句,无论是史语所藏本或《曲本》305、《子集》165-166及上述两种收录本,均无一不作:‘芸窗下医余兀坐无穷恨,闲消遣楮洒凄凉冷落文。’据此可知,本曲应为‘芸窗’所作,《提要》28著录本曲,亦题‘作者芸窗’。(2)《红子》《丛钞》分指《红楼梦子弟书》和《子弟书丛钞》;《曲本》《子集》分指《清车王府藏曲本》《横滨市立大学纪要:子弟书集》;《提要》指《车王府曲本提要》。芸窗是子弟书名家,据上引鹤侣氏《逛护国寺》子弟书,可知他与松窗、小窗等齐名,乃‘俱是编书的国手可称元老’,而现存他所作的子弟书,除此曲外,尚有《武陵源》……等六种,其取材均与隐逸及弱女两种故事有关,而‘蕉窗’其人,则除《红子》及《丛钞》两书曾提及外,笔者迄尚未多见。在现存各种有关子弟书之资料中类此错误疏漏的情况仍多,若不早日予以补正,势必将徒增后人困扰。”[12]291-292
对陈锦钊先生不盲从师辈专家,生怕贻误后人的想法,笔者十分赞同。前辈研究者所留考证文章是后人研究子弟书的基石。子弟书从刻本、抄本流传而来,纠偏不易,立说更难。就陈锦钊先生《遣晴雯》作者的考证角度,笔者觉得颇值得商榷。
陈锦钊先生认定《遣晴雯》作者定为“芸窗”,强调署名“蕉窗”者“徒增后人困扰”。其论据有四:(1)诗篇嵌入“芸窗下”;(2)芸窗是子弟书名家;(3)芸窗的作品取材均与隐逸及弱女两种故事有关;(4)蕉窗只有两书提及,他处不多见。下文将讨论这四个论据可否支撑其观点。
第一,在子弟书《遣晴雯》中,诗篇有“芸窗下”不假,结尾有“蕉窗人”也真。所以,此条无法证明作者是芸窗。
第二,文中提到的鹤侣氏作《逛护国寺》原文片段为:“这是鹤侣氏新编的两回时道人逛护国寺,他说拿来我看看,坐下将书拿过来。看了两篇摇头晃脑说,成句而已,未必够板,数来保样,这是何苦来?论编书的开山大法师,还数小窗得三昧,那松窗、芸窗也称老手甚精赅。竹轩氏句法详而稳,西园氏每将文意带诙谐。那渔村他自称山左疏狂客,云崖氏、西林氏铺陈景致别出心裁。这些人俱是编书的国主可称元老,亦须要雅俗共赏合辙够板,原不是竟论文才。他批评了多时,将书扔下扬长去,马六气的眼发呆。……”[11]277这段子弟书讽刺了一个夸夸其谈、只逛不买的人,作者鹤侣还嘲笑自己创作的子弟书在这个口若悬河的人口中不过就是“数来宝”,而其他几位子弟书作者各有章法,不愧为名家写手。这确实可以证明子弟书作家中,韩小窗称魁,芸窗与罗松窗比肩紧随。但这和《遣晴雯》的作者归属无甚关联。
第三,芸窗的作品类型与《遣晴雯》题材相似。这类哀怨悲悯内容本来就是子弟书作者擅长表现的题材之一,比如《忆真妃》《青楼遗恨》《露泪缘》等曲目,所以,此条也非《遣晴雯》作者是芸窗的佐证。
第四,蕉窗在他处未多见。子弟书东调代表人物是韩小窗,西调代表人物为罗松窗,二人并称“二窗”。受他们影响,子弟书作者笔名叫“窗”的较多。除前面提到的芸窗、蕉窗外,还有竹窗、明窗、闲窗、雪窗、幽窗、书窗、梅窗、晴窗、锁窗诸位。竹窗写过《二心论玉》《绿衣女》;明窗写过《双官诰》《风流词客》;闲窗写过《女觔斗》《一疋布》《全彩楼》《梅妃自叹》等;雪窗写过《十面埋伏》《射鹄子》;幽窗写过《拐棒楼》《钟生》;书窗写过《击鼓骂曹》《赵五娘吃糠》;梅窗写过《天缘巧配》;晴窗写过《苇莲换笋鸡》;锁窗写过《走岭子》;……这些叫“窗”的子弟书作者名字,也是前人从子弟书作品中提炼而来,其是否准确,不在本文探讨之列。目前看这些叫“窗”的作者只传下来一段作品的不止一位,其他只留下一曲子弟书的写手也不在少数,为什么蕉窗就不能只留下一段呢?
四、《遣晴雯》作者的职业
关德栋、周中明在《论子弟书》[13]56-62谈到子弟书作者的社会地位时写:“蕉窗在《遣晴雯》诗篇末尾说‘蕉窗下,医余兀坐无穷恨,闲消遣,楮洒凄凉冷落文。’作者则是位医生。”关于《遣晴雯》作者从医的观点谁先,未考,倒是被多家认可并提及。
耿瑛在《红楼梦子弟书》序言里写:“仅从《遣晴雯》中‘芸(蕉)窗下医余兀坐无穷恨’一句,得知蕉窗氏乃是一位从医为业的业余作者。”[5]3《车王府曲本研究》收入黄仕忠撰《车王府钞藏子弟书作者考》一文中也有“据‘医余’句,可知本篇作者能医。”[14]435的推论。陈锦钊著《子弟书研究》文称:“据《遣晴雯》之诗篇,有‘芸窗下医余兀坐无穷恨,闲消遣楮洒凄凉冷落文’句,可知芸窗系行医为生,以医余从事写作子弟书。”[15]347在《遣晴雯》作者尚有争议的情形下,推断子弟书名家芸窗是一位医生,稍显不妥,更何况“医余”就一定指作者是医生吗?
笔者认为“医余”二字,既可以理解为此曲作者是个从医者,给他人把脉抓药后闲暇中浮想联翩,握笔成文;也可以理解为其身体有恙,看罢病症,生出烦恼,借书古人消愁遣闷,还有可能“余”指“我”,“医”本意为治疗,引申为破解。那么这句话就是说:“在芸窗下,闲消遣著文破解我兀坐的烦恼。”
既然《遣晴雯》的作者可能从医,如果能找到芸窗或蕉窗是个从医的业余作者的证据,是可以反推其人可能是《遣晴雯》之作者的。可惜芸窗所留作品虽多,身世并无考。只有唐鲁孙先生在《失传的子弟书》一文中提及:“东城调又叫东韵,是高云窗、韩小窗、罗松窗所编写。……当时‘三窗九声’是最博得人们赞赏的。”[16]49-51由此看来除了公认的韩小窗、罗松窗并称为“二窗”之外,坊间当还有高云窗、韩小窗、罗松窗并称“三窗”的传闻。这里提到的“高云窗”,当为芸窗。韩、罗二窗均为子弟书的专业作家,能与二窗并提为三窗,芸窗是业余作者的可能性不大。且通读芸窗所留其他子弟书篇章,并无其从医或因患疾去看病的句例,而蕉窗确在他处无多记载,所以无法从作者职业或身体状况这个角度来推断《遣晴雯》的作者归属。
五、芸窗的嵌名习惯
现存芸窗作子弟书,嵌名之处列出:(1)《武陵源》(一回)诗篇:幽斋雨过晚凉天,鸟语花香景物妍。小几摊书评往事,芸窗握管注新编;卷末:只因为日长睡起无情思,拈微辞芸窗偶遣一时闲。[11]144,145(2)《飞熊梦》(《渭水河》五回)卷尾:痴人芸窗把笔闲成段,留与诗人解闷题。[11]928(3)《渔樵问答》(一回)卷尾:度炎暄乘闲偶弄芸窗笔,谱新词为与知音作品评。[11]190(4)《林和靖》(一回)卷尾:只因为乘闲偶寄芸窗兴,感知音笔下传奇衍妙文。[11]151(5)《梅屿恨》(四回)卷尾:度残春芸窗偶阅西湖志,吊佳人小传题成遣素怀。[11]704(6)《刺汤》(二回)诗篇:半启芸窗翰墨香,萧萧风雨助凄凉。[17]277
可以看出,芸窗比较自如的自称方式是“芸窗握管”“芸窗偶遣”“芸窗把笔”“偶弄芸窗笔”“偶寄芸窗兴”“芸窗偶阅”,其特点是将“芸窗”换成“我”,我握管、我把笔、……表达意思完全不变。而在《遣晴雯》中,若将“芸窗下”的“芸窗”替换成“我”便不成句,相反“蕉窗人”处换成我,则完全通顺。
在芸窗作子弟书《梅屿恨》中,还看到这样的诗篇:小院春归寂寞中,海棠枝上鸟啼红。一窗冷雨三更梦,半榻愁帷午夜钟。[11]698《梅屿恨》诗篇中嵌入的“一窗”和《遣晴雯》中的“芸窗”一样,当同属景物描写。如果芸窗是《遣晴雯》的作者,那岂不是一窗也可以是《梅屿恨》的作者?实际上,《梅屿恨》曾一度被误以为是韩小窗的作品,傅惜华《子弟书总目》[18]73,122和关德栋《曲艺论集·现存罗松窗、韩小窗子弟书目》[19]134,《梅屿恨》作者均注为韩小窗,即因《梅屿恨》“度残春芸窗偶阅西湖志”句,有抄写别本为“夏日长小窗偶阅西湖志”所误。黄仕忠《车王府钞藏子弟书作者考》:“疑小窗名头大于芸窗,后人遂改芸窗之句为小窗之标识,以高声价。”[14]427这种分析并不无道理。笔者所见还有将二凌居士为《黛玉悲秋》题跋略为修改,刊印在《圣贤集略》之扉页的做法(3)见光绪乙亥季春(1875)文盛堂、盛京财神书坊、会文山坊《黛玉悲秋》及光绪丙午年仲秋(1906)盛京老会文堂《圣贤集略》。。芸窗又比蕉窗名声响亮,有无假托之嫌呢?
六、“蕉窗下”的版本情况
按子弟书署名惯例,从《遣晴雯》尾处“蕉窗人剔缸闲看情僧录”便可判定此曲作者是蕉窗,但因此曲诗篇中的“芸窗下”,才导致各家解读产生了分歧。如果“芸窗下”处是“蕉窗下”,此争议可休矣。
《遣晴雯》别本恰恰如此!中国曲艺家协会辽宁分会编的《子弟书选》[17]中,“芸窗下医余兀坐无穷恨”这句即为“蕉窗下医余兀坐无穷恨”;《中国传统鼓词精汇》[8]选本同《子弟书选》,这和关德栋、周中明在《论子弟书》[13]56-32一文中提到的“蕉窗下,医余兀坐无穷恨”高度契合。《红楼梦子弟书》虽记为“芸窗下”,204页注释云:“芸窗,别本作蕉窗。”
既然有别本“蕉窗下”,且出处多达四种,为什么笔者没有根据这些下结论认定作者是蕉窗无疑呢?因据笔者所了解的情况看,这四版是有关联的。按时间排序依次为:辽宁曲协《子弟书选》(1979),关德栋、周中明《论子弟书》(1980),胡文彬《红楼梦子弟书》(1983),刘新《中国传统鼓词精汇》(2003)。
中国曲艺家协会辽宁分会编《曲艺通讯》1980年第三期,杨(天)微先生《关于〈子弟书选〉的校订》一文记述:“中国曲协辽宁分会去年编印了一本《子弟书选》,收韩小窗等二十位作者所著子弟书83段197回(应为198回,罗松窗《秦王吊孝》从结构及韵脚看分明为两回,但抄稿未分回,姑从抄稿)。这些书段据傅惜华先生珍藏抄稿编印。1963年,春风文艺出版社拟正式出书,曾得到傅先生大力支持,凡可约略考出作者的抄稿全部献出。后出书因故中辍,不幸中之幸,在那阬火腾焰的年代里,它却得以保存下来。傅先生手中所存那一部分作者不可考的子弟书抄稿,却劫灰飘扬不复可睹了。这些资料的散失,是我国曲艺史乃至文学史研究中不可弥补的损失。”[17]35-36
《子弟书选》所录曲本为耿瑛先生1962年从傅惜华处觅得,虽然只是给研究者提供的内部资料刊本,但所选作品皆为“略考”过作者的。《子弟书选》校对并不完善,但是“蕉窗下”一处绝非录入排印错误。
笔者藏有关德栋先生写给耿瑛先生的1979年到1998年之间的亲笔信23封,最早的一封从邮戳看是1979年7月5号,对编辑中的《子弟书丛钞》多有谈论;收到辽宁曲协印《子弟书选》的回信落款11月29号夜,时间当同为1979年。而关德栋、周中明撰《论子弟书》一文初稿1979年6月18日写于合肥,7月改于上海,1980年1月重订于济南。故关德栋先生的文章极有可能是借鉴了《子弟书选》中的“蕉窗下”之文。耿瑛与关德栋、周中明等十人为“子弟书研究会”(4)子弟书研究会:1987年6月在北京成立。发起人十位:王文宝、白化文、关德栋、李万鹏、李鼎霞、陈文良、周中明、耿瑛、阎中英、程毅中。发起人,他们就子弟书作者问题时有沟通,如果《子弟书选》“蕉窗下”处排印错误,以几位的学术态度,此事后续一定会有修正。
胡文彬编《红楼梦子弟书》的校对和注释是胡文彬先生和此书的责编耿瑛先生多次探讨沟通并共同完成的。
又据沈阳曲艺家协会主席穆凯回忆,《中国传统鼓词精汇》是顾问刘英男先生请耿瑛先生代为排序并拟写的序言。
四条线索归一,笔者虽深知耿瑛以治学严谨著称,绝不会杜撰一个“蕉窗下”出来。但正所谓孤证不立,今只有找到“蕉窗下”的原抄本才能作为实证,惜傅惜华藏本早年已寄回傅惜华之女傅玲处,并未留存影印件,实为憾事。
七、现存《遣晴雯》的四种抄本
目前笔者能看到的《遣晴雯》抄本影印件四种:(1)百本张(〈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双红堂文库藏:稀见中国钞本曲本汇刊〉[18]56和〈横滨市立大学纪要:子弟书集〉[19]影印均为百本张抄本);(2)首都图书馆编《清车王府藏曲本》[20]51所录抄本;(3)《俗文学丛刊》[21]396-405所录抄本;(4)《故宫珍本丛刊:岔曲秧歌快书子弟书》[22]290所录抄本,此曲开篇处均作“芸窗下”。但值得注意的是,《遣晴雯》中的“空留下一抔净土伴秋林”句,以上四个版本分别抄写为:“空留下一坏净上伴秋林”“空留下一盃静土伴秋林”“空留下一坯净土伴秋林”“空留下一坏净土伴秋林”,竟然无一不讹。再看“蕉窗人”句,四种抄本及《子弟书选》均同,只有《红楼梦子弟书》为“蕉窗氏”;“剔缸”句四抄本相同,《子弟书选》和《红楼梦子弟书》为“剔烛”。《红楼梦子弟书》收录的此曲标注“据北京大学藏车王府抄本迻录”,对照后与车王府抄本不尽相同,《子弟书选》与《红楼梦子弟书》所收的版本差别更大,不仅词句有别,前者比后者还多16句出来,《子弟书选》录入的傅惜华藏本(或为别埜堂本)也非上述四种抄本之一。《遣晴雯》当至少另有两种抄本曾传世,也即是说,诗篇中的“蕉窗下”的别本多半是存在过的。
八、“窗”在子弟书中的含义
崔蕴华在《书斋与书坊之间——清代子弟书研究》[23]68中对“窗”的意向叙述颇有道理,其认为窗具有三重含义:隐署作者名讳;营造创作意境;透窗以观万千。
子弟书《一顾倾城》结尾有句:“伯莊氏小窗无事闲中笔,这就是一顾联姻子弟文。”[5]2491这里的“小窗”到底是哪一种含义呢?
陈锦钊辑录《子弟书集成》[5]2484中,《一顾倾城》注“伯莊氏作”,显然是把小窗当成了创作情境,并没有因为小窗作品颇多,且是知名的子弟书作家,伯莊氏又同样“迄尚未多见”,而将这段子弟书标记为韩小窗作。那么,在伯莊氏和小窗同时出现时,确认伯莊氏为作者;芸窗下和蕉窗人(氏)共存的作品中,为什么只认可名气更大的芸窗呢?
九、初考子弟书作者之情形
黄仕忠撰《车王府钞藏子弟书作者考》一文对最初车王府曲本的整理情况有回顾:“〈车王府曲本编目〉只是一个目录,虽间或标明作者为谁,却没有说明所据;从其题署看,一部分是文内嵌有作者名字,其作者可以得到旁证的;一些则是据本文而作的揣测,颇有可商议者;另有少量题称,颇不经见,细加考察,疑为附会或误题。笔者曾询及当初参与编目的先辈,当时他们尚是在校学生,以数十人之众,在大跃进的背景下,在短时间内完工,未敢谓翔实;兼以原始资料早已散佚,今已不复记其所据。”[14]414
据此看来,因最初匆忙的整理工作,看到诗篇中有“芸窗”二字,即将《遣晴雯》记录为芸窗所作,也是有可能的;后又有研究者看到尾句,遂改录作者为蕉窗。而芸窗认定之影响久未消除。
十、结语
对于在同一篇子弟书中,有多处疑似嵌名的,不同抄本所记有出入的同一曲目,作者归属的考证,不能根据作者的知名度和作者留有作品数量来推断,应根据曲中语境、抄本时间、版本差异、题跋记载、知情者口述和相关文献综合考虑才显客观。
综上,笔者认为《遣晴雯》作者为蕉窗的可能性非常大,起码不能仅仅从诗篇来断定作者是芸窗,更无法从现有资料否认蕉窗的存在。也有人猜测“蕉窗人”为芸窗自称之偶题。芸窗家的窗棂外蕉树绰约,他写到尾处,抬眼一看,窗景入词,即蕉窗便是芸窗,芸窗就是蕉窗。芸窗为北京作家,窗外应不生芭蕉树。《武陵源》前后提及芸窗二字,何苦在《遣晴雯》中避讳重复,凭想象随意偶题呢?然此猜测虽牵强却无法排除。即便为偶署,作者在不同时期署名有本名、字、号、笔名等亦司空见惯,实不影响将《遣晴雯》作者标注为“蕉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