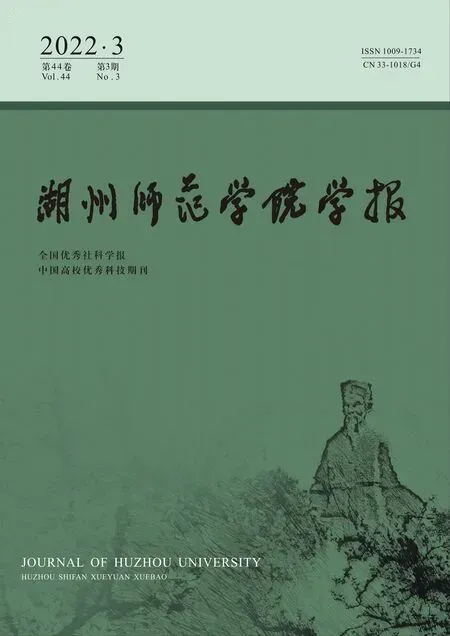阳羡词派接受“稼轩风”的词史契机与多元观照*
支小蓉,杨许波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恰如严迪昌所言,阳羡词派是“崛起于沧桑巨变、风云诡谲的历史时期的文学流派”[1]8。该派是在明清易代之际,以陈维崧为中心形成的一个包含有上百人之多并取得了丰硕成果的创作群体。其中除了宗主陈维崧的《湖海楼词》外,又有数十家词人有传世词集,如史惟圆之《蝶庵词》、任绳隗之《直木斋词》、曹亮武之《南耕词》、万树之《香胆词选》等。另外,该词派还编有《今词苑》《荆溪词初集》《瑶华集》《名媛词选》等词学总集与选本,这种宏大的创作数量和规模在清代词学史上可谓寥若晨星,阳羡词派也因此奠定了在清代词坛上的地位。在宗主陈维崧的带领下,阳羡词派诸词人在理论与创作中都表现出了对“稼轩风”的推崇,他们以“存经存史”、崇“情”主“意”为词学主张,敢于将意义重大的内涵体现在词学实践中,以慷慨豪迈之声抒发悲痛深沉之思,这种直抒性情、张扬豪放的创作风格背后,隐含的正是以稼轩豪气为内在特质的词学思想。目前学界多关注“稼轩风”对阳羡宗主陈维崧或其他个别词人的影响,但缺少对阳羡词派整个群体接受“稼轩风”的系统研究和整体观照。本文将立足于阳羡词派的词人、作品及词论,从该派接受“稼轩风”的表现、原因及影响三方面为基础进行多元观照,层层递进地剖析这种接受的全貌及其对清初词坛嬗变的推动作用。
一、阳羡词派对“稼轩风”的接受表现
中国古代文学浩如烟海,包括多种不同形态的文学体裁。其中,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对文学现象的独特见解、主张和观念,被称之为文学思想。词学思想隶属于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它是词人在时代环境的影响下,为实现某种功能或者目的,通过作品、词学批评、词学理论等形式表现出来的具有一定文学特质的思想或观念[2]2-8。在南宋国运日衰的时代背景下,辛弃疾悲慨雄壮的豪放词风应运而生,雄踞于南宋词坛,不仅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词学风格,并以其独特的情志风貌折服了同辈后继,使南宋词坛表现出“歌词渐有稼轩风”的盛况。明末清初,“稼轩风”随着词学复兴再一次走进了词学创作的中心,其中以抒情达意作为词的表达功能、以经史子集作为词的内容来源、以词人本身作为词的抒情主人公、以雄大气魄和沉郁意境作为风格特征,为清初阳羡词派的词学创作带去了新的方面。清初词学虽有中兴之势,但也正如陈廷焯《白雨斋词话》所言:“自国初诸公出,如五色朗畅,八音和鸣,备极一时之盛。然规模虽具,精蕴未宣。”[3]3775针对词学矜弱的问题,阳羡词派以辛词为师法对象,通过理论探索和创作实践给清词发展带来了新方向。
阳羡词派对“稼轩风”的接受首先表现在词学理论上。辛弃疾的门人范开在《稼轩词序》中说:“公一世之豪,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4]50词作为辛弃疾政治失意时的“陶写之具”,是其气节、人格与心志的集中体现,其词学思想包含着以气入词、抒情言志的词学主张,以文为词、标举风骚的词体意识,以及语拙意真的审美原则等方面,这在明词“音律失谐”“语句尘俗”的创作状况下,为阳羡词派提供了创作的方向。正如陈维崧在《词选序》中所言:“而东坡、稼轩诸长调,又骎骎乎如杜甫之歌行与西京之乐府也。盖天之生才不尽,文章之体格亦不尽。”[5]54词人以歌行与乐府为例,阐释了文体变化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多样性与包容性,并由此肯定了词体文学产生的必然性。又说:“要之穴幽出险,以厉其思;海涵地负,以博其气;穷神知化,以观其变;竭才渺虑,以会其通。为经为史,曰诗曰词,闭门造车,谅无异辙也。”[5]54陈氏认识到了清初词坛“矜香弱为当家,以清真为本色”的主流词风对词学发展的不利影响,提出词应与经、史一样具备“思”“气”“变”“通”四个方面的文化功能,不应该局限于闺房情爱等俚俗狭隘的表现范围,而应该反映深刻的思想内容,洞察事物的流变规律,承担起经、史所具有的社会功效,这一表达不仅明确了词的具体内容,更是将词与诗、经等严肃的文学体式相等同,在丰富词学功能的同时也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陈维岳评价其兄时有言:“先伯兄中年始学为诗余,晚年尤好之不厌,至于赠送应酬往往以词为之。或一月作几十首,或一韵叠十馀阕,解衣盘薄,变化错落,几于昔人所谓嬉笑怒骂皆成文者,故多至千余。古今人为词多,未有过焉者也。”[5]53陈维崧从中年开始作词,直至晚年仍醉心于此,他对词的钻研和坚持更加证明了他对词这一文体地位的认同。另外,陈维崧在《蝶庵词序》中有一段引自史惟圆的话,可以看作是阳羡词派对词“存经存史”功能所做的拓展和努力,其有言:“夫作者非有《国风》美人、《离骚》香草之志意,以优柔而涵濡之,则其入也不微而其出也不厚。人或者以淫亵之音乱之,以佻巧之习沿之,非俚则诬,故吾之为此也,悄乎其有为也。”[5]49词人并不否定温、韦、周、秦一派的创作风格,但更主张词应该像《国风》《离骚》一样,能够借用美人、香草等意象,或咏叹高尚的人格、气节及人生感受,或表现深厚的社会内容和深微的忧愤心理。可见,以陈维崧为代表的阳羡词派不仅将稼轩词的理论内涵深入到了词的地位、社会功用、内容意义等各方面,更是追求在词作中抒发真实情感与意志,其将词与“存经存史”的功能紧密联系的创作特征,可以说是对辛弃疾以词为陶写人生之具的延续和传承,这给阳羡词派甚至是整个清初的词学思想发展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可能。
阳羡词人体现在作品中的稼轩豪气,是该派接受“稼轩风”的实践表现,其中以辛弃疾为对象的次韵词又是其主要表现方式。次韵作品是我们观照一个作家及其名篇杰作在历代被接受、传播状况的重要来源,我们不仅可以通过词人的次韵作品考察其创作风格与喜爱倾向,还可以了解到词人与前代作家的渊源关系。仅就词学创作来说,南宋以后的词学创作中,能经常看到次韵辛弃疾的作品。而阳羡词派作为一个庞大的创作群体,他们次韵稼轩词的数量更是在清初遥遥领先。其中陈维崧14首,分别是:《鹧鸪天》7首,《水龙吟》3首,《贺新郎》2首,《永遇乐》1首,《满江红》1首;曹亮武4首,分别是:《念奴娇》1首,《贺新郎》1首,《沁园春》1首,《摸鱼儿》1首;万树6首,分别是:《水龙吟》2首,《归朝欢》1首,《满江红》2首,《贺新郎》1首;周在浚2首,分别是:《永遇乐》1首及《西河》1首[6]351-372。阳羡宗主陈维崧的作品在历代次韵稼轩词的数量中位居前十,相对于其他词人分散少量的次韵作品,阳羡词派诸词人对稼轩词的频繁唱和,证明了该群体对“稼轩风”的认同,而这种认同也清楚地体现在该派的词学风格中。以陈维崧这首《贺新郎·冬夜不寐写怀,用稼轩同甫倡和韵》为例:
已矣何须说!笑乐安,彦升儿子,寒天衣葛。百结千丝穿已破,磨尽炎风腊雪。看种种,是余之发。半世琵琶知者少,枉教人,斜抱胸前月。羞再挟,王门瑟。
黄皮裤褶军装别,出萧关,边笳夜起,黄云四合。直向李陵台畔望,多少如霜战骨。陇头水,助人愁绝。此意尽豪那易遂?学龙吟、屈煞床头铁。风正吼,烛花裂。[5]1539
上片词人感慨自己身世坎坷、怀才不遇的人生遭际,下片以边关萧瑟、胡笳四起的悲凉氛围,凭吊过往的战场与古人。最后以雄健遒劲的笔力为全词深沉低昂的情感作结。陈廷焯将陈维崧词中的豪放之气评价为:“真稼轩后劲也。”[3]3837可以看出,这首词从词牌到题目,再到情感气势和引经据典的手法,都能让人感觉到辛弃疾张扬豪放、摇撼山河的词风。除此之外,阳羡词派其他词人如曹亮武《贺新郎·月夜舟发九江,用迦陵韵》有乘风破浪、龙跃天门之势,《念奴娇·病中庭梅盛开,同其年用赤壁词韵》更是笔力劲健,豪壮激慨;再如“著有《梧月词集》,为词场家所传诵,与陈其年诸君旗鼓颉颃”[7]83的蒋景祁,其《念奴娇·赠曹荔轩,用东坡赤壁词韵》等作亦追步稼轩豪放雄健的词风;其他如史惟圆《贺新郎·江上旧感》、万树《贺新郎·三野先生传赞》等词也都有豪气冲天、雄健苍茫之感。
总之,阳羡词派不仅从理论上接受了辛稼轩的词学内涵,更是在创作风格中表现出了清初词坛少有的豪迈奔放之气,可以说这是对“稼轩风”的一种有目的、全方位的接受过程。
二、阳羡词派接受“稼轩风”的词史契机
严迪昌曾在《“稼轩风与清初词”——兼论稼轩风的独异性与时代性》一文中提出:“在一定程度上说,词人的审美情趣的自我选择以致艺术风格的形成,既是自由的又是并非绝对自由的,有时甚至是很不自由的,此中有着俗称的‘身不由己’的微妙而复杂的潜在关系。”[8]阳羡词派接受“稼轩风”除了受词人审美情趣的主观影响之外,更是词人在政治环境、地域文化、词学发展规律等多重因素影响之下做出的选择。
首先,明清易代之际,时局政治的变化作为外在动因,引发了文人士子内在心态的变化。阳羡词派所处的时代,适逢满洲统治者入主中原,乙酉年(1645)夏,清军攻破南京,屠杀城民,宜兴地区的有志之士在极为频繁激烈的抗清活动中伤亡惨重。随着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并通过一系列政治手段,达到了文化统治和打压遗民文人的目的[9]。战火和严酷的政治手段给文人带来的心悸,淋漓尽致地体现在他们的作品中。曹亮武的《贺新郎·陈卫玉舅以事徙塞外二十年矣,弓治表弟曾万里省亲。闻有损赎之诏,复破产而行,词以送之》[10]7197是仅存不多能够反映科场案之残酷的作品,上片“辽海银州都历遍,相见悲酸难画。争拥抱,泪如波泻”,写其舅陈卫玉流放宁古塔之艰难凄苦,以及家族子弟探亲之万分艰辛的境遇。下片寄希望于捐金救赎,又恐“怕金尽、事难凭把!”表现出词人当时战战兢兢的心理变化,此词从受害人、叙述者等不同角度直接表现出科场案对当时文人士子带来的心理创伤和严重影响。另外,清初三大案中“奏销案”对江南士子的打击最为严重,阳羡词派重要词人徐喈凤为此丟官,任绳隗则因此失去进士考试资格,诸如此类的情况俯拾皆是。文人士子一边对清政府接连加科、召试进士的科举制度而心存希望,一边又面临清初三大案的步步紧逼,如履薄冰。在这种矛盾困惑的心理之下,被剥夺入仕权利甚至受到威胁的江南士子只能将这种不堪、心悸、无奈与愤懑全部付诸词。表现在阳羡词人身上,则是用极其豪放的词风来陈述身世家国之悲,在词中揭露时代的黑暗浑浊、力陈心中的悲慨愤懑。与此相同,辛弃疾亦是在国家屡遭侵犯,豪情壮志无处可发的境遇下形成了豪迈奔放的词学风格,这一共通点也是促使阳羡词人选择学习 “稼轩风”的重要原因。
其次,社会环境和文人心态的变化,促使词体文学本身也亟须变革。满目疮痍的国家现状和严酷残忍的清初三大案给江南地区的文人士子带来了心灵上的沉重打击,这种悲痛感慨已经不能为“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委婉表达所包容,更不是“懒起画峨眉”的闺中女子所能承受。因此,改变词学风格和内容成了当务之急。例如余怀,早在明清易代之际就在创作中实践辛弃疾豪放词风并产生较大影响。吴伟业在《玉琴斋词序》有云:“词大要本于放翁,而点染藻艳,出脱轻俊,又得诸金荃、清真,此缘学富而才隽,无所不诣其胜耳。”[7]122读余怀词可以发现,其填词不仅学习温庭筠、周邦彦等人的婉约之风,更是在词中表现出对辛弃疾豪放词风的偏重。另有明末进士金堡,其坎坷的生活经历使其词摆脱了浮艳绮靡的词学风格,转而偏向豪迈之风,有次韵稼轩词作品19首。再如清人邹祗谟,作为阳羡宗主陈维崧来往紧密的好友,也早已在其词论中表现出了对词风变革的见解,其在《倚声初集》序言中说:“揆诸北宋,家习谐声,人工绮语。……而辛刘陈陆诸家,乘间代禅,鲸呿鳌掷,逸怀壮气,超乎有高望远举之思。”[11]字里行间透露着对以辛弃疾为首的南宋豪放词风的赞赏,他“非前工而后拙,岂今雅而昔郑”的观点更是主张应从风格体式等各个方面拓宽词的表现领域,体现出词人对兼容并蓄的词学风格的认同,这种求变的词学思想与陈维崧的词学观不谋而合,二者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明末清初词坛上几次重要的唱和活动(即扬州江村唱和、广陵唱和以及秋水轩唱和)也是将“稼轩风”推向复兴必不可少的环节。这三次活动所唱和的词牌分别为《满江红》《念奴娇》《贺新郎》,皆为辛词常用词牌,并且就词牌所属声情来说,《满江红》激昂慷慨,《念奴娇》响遏行云,《贺新郎》洪畅浩荡,多用来表达豪迈奔放的思想情感。由此可见,这三次唱和都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改变词坛上趋向香艳柔婉一类的词学风格,转而将更加深沉悲慨的情感赋予词作,增添了一丝别样的豪迈风采。蒋景祁在《陈检讨词钞序》中说:“先生内联同郡邹程村、董文友,始朝夕为填词。”[7]93创作群体与唱和活动对以“稼轩风”为主导的豪放词风的推广,影响了参与其中的阳羡词人,这也为后来阳羡词派接受“稼轩风”做了铺垫。
最后,“稼轩风”成为阳羡词派的显著标志并且成功走向复兴,离不开陈维崧强大的领导力量。从陈维崧的活动轨迹来看,崇祯末年到顺治十年左右的这段时间,陈维崧及其周围词人还以“花间”“云间”等婉约词风为宗尚。直至顺治十三年(1656)陈维崧之父陈贞慧亡故,其词风才开始发生变化。康熙八年(1669),陈维崧结束如皋、广陵等地的游历,受到在广陵游历时期所参与唱和活动的影响,回乡之后也开始了频繁密集的唱和活动,这种具有引领性的创作活动使陈维崧成为“学者靡然从风,即向所等夷者,尚当拜其后尘,未可轻颉颃也”[12]卷首的对象,这带动和影响了周围一批文人的词学活动。阳羡词派的鼎盛时期虽然与陈维崧定居故乡潜心写词同步,但也离不开阳羡词派诸词人的鼎力唱和。任绳隗较早与陈维崧结识,早在“天下填词家尚少”之时,就已经与其进行填词唱和了。他早年词风绮丽,以索香、索镜等“十索”艳词闻名。在经历了“奏销案”之后沉迷道术、潜心著述,词风也趋向苍凉轻峭,多书写失意人生。如《白苧·隔墙闻弦索声》下片:“堪惜。家人敛黛,才子搔头,横吹一曲,拨尽琵琶残拍。频呼酒,按不住青衫湿。”[10]2928此词中,词人失意之悲与愤懑之气喷涌而出,苍凉之中又颇有稼轩豪气。除此之外,阳羡派健将徐喈凤、蒋景祁等人也在与陈维崧的长期交往中耳濡目染、专注于作词,并出现了“人各有作,家各有集,即素非擅长而偶焉寄兴,单辞只调亦无不如吉光片羽,啧啧可传”[12]的盛况,集体创作活动中形成的“稼轩风”清晰地表现在阳羡词人的词论以及作品风格中。
三、“稼轩风”对阳羡词派的影响
阳羡词派对“稼轩风”的接受实际上是对彼此双方的共同成就:一方面,辛弃疾的词学理论与豪迈词风影响着当时词坛上主流词人的创作方向,并为清初词坛开辟出了一条全新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阳羡词派诸人的推崇唱和使得豪迈奔放的“稼轩风”在数百年之后重新获得生命力,并成功回到了词学创作的中心。
阳羡词派对 “稼轩风”的接受呈现出由个人到群体的特征,“稼轩风”首先对阳羡宗主陈维崧的词学风格产生了巨大影响。陈维崧在《上龚芝麓先生书》中回忆道:“向者粗习声律,略解组织,雕虫末技,猥为陈黄门、方检讨、李舍人、诸公所品藻。”[5]87可见其早年与云间词人陈子龙等人交往密切,所以其早期词作颇有云间习气,表现为婉丽香艳的词风。且看其《阮郎归·咏幔》一词:
鲛绡微皱忆潇湘,风吹红线凉。算来只在红垣傍,教人愁断肠。 笼宝篆,暖银釭。流苏无限忙。知他何处费思量,霏霏春昼长。[5]1777
陈维崧这首小令表面是在吟咏微风中精致的幔帘,其实字里行间透露的是女主人公在漫长的春昼里思而不得的悲伤情感,她的孤独寂寞与满腹愁苦恰如摇晃的流苏,日复一日,无穷无尽。这种创作手法与云间词人陈子龙颇为相似,词风尽显纤弱鲜妍、婉媚含蓄之感,所以被王士祯评为:“以拟大樽诸词,可谓落笔乱真。”[11]269然而在遭遇了巨大变革之后,这类早年所作的闺情词却使陈维崧头颈发赤、悔恨不止,甚至在后来的《乌丝集》中删除了大量娇柔软媚、吟咏闺情的词作。其后期词作正如陈宗石在《迦陵词全集跋》中所说:“或孤蓬夜雨,轗轲历落……酒棋歌板,诙谐狂啸,细泣幽吟,无不寓之于词。”[5]1830曲折坎坷的人生经历使得陈维崧的词学内容与风格也表现出了明显的变化,且看其《醉落魄·咏鹰》:
寒山几堵,风低削碎中原路。秋空一碧无今古。醉袒貂裘,略记寻呼处。 男儿身手和谁赌?老来猛气还轩举,人间多少闲狐兔?月黑沙黄,此际偏思汝。[5]1066
同样是咏物之作,与前期吟咏闺中之物不同,词人以雄鹰自比,以狐兔比喻残害人民的贪官污吏,借荒凉的环境氛围抒发其激奋昂扬的情感,将狼狈落寞的处境与稼轩豪气融二为一,抒发出虽老之将至,但意气犹存的感慨。再如其《满江红》词有云:“雨覆云翻,论交道、令人冷齿。告家庙、甲为乙友,从今日始。官笑一麾君竟罢,病惊百日余刚起。问乾坤、弟畜灌夫谁,惟卿耳。”[5]1211谢章铤在《赌棋山庄词话》中评价此词为“哀啸狂吟,无非跋扈。竹垞以比青兕,岂过誉哉”[3]3379。可以说在陈维崧心态转变之际,“稼轩风”不仅适时地为陈维崧提供了一个可以承载其思想与情感的表达方式,更是使得稼轩豪气成了阳羡词派词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鲜明标志。
清初阳羡词派对“稼轩风”的接受使词的文学地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明末陈子龙在《幽兰草题词》中评价明词创作状况时曾说:“此非才之不逮也,巨手鸿笔既不经意,荒才荡色时窃滥觞。”[13]26有明一代词学创作队伍呈现出式微的特征,当时文人既不屑于创作词体文学,又囿于腐靡浅显的表面无法深入,使得词学从根源上缺乏活力。针对这一现象,明末云间词派首先进行了积极的改变。该派倡导词学复古,回归本色,以晚唐五代之温、韦、二李为圭臬,追求由俗趋雅的词学特征,为词坛带来一股雅正之风。但由于该派末期对婉约形式的固执追求,终究未能给词体带来根本改变。相对而言,阳羡词派与辛弃疾如出一辙的尊体理论,从根源上给词体文学带来了变化。除宗主陈维崧外,阳羡词人任绳隗在《学文堂诗余序》中亦有言:“夫诗之为骚,骚之为乐府,乐府之为长短歌,为五七言古,为律,为绝,而至于为诗余,此正补古人之所未备也,而不得谓词劣于诗也。”[7]98他认为词的出现弥补了古人文体发展中的空白,坚决反对将词视为卑劣低下的文体,并且非常重视词人的创作手法及品质能否写出好的词。对待词体文学的不同态度导致了词体功能观差异,朱彝尊在《紫云词序》中认为:“大都欢愉之辞工者十九,而言愁苦者十一焉耳。”“词则宜于宴嬉逸乐,以歌咏太平,此学士大夫并存焉而不废也。”[7]240朱彝尊视词为小道的观念,使其明确地将诗和词的表达功能完全区分开来,认为词为娱宾遣兴,歌咏太平而作,而诗则为言胸中志向,谈家国大事而作。阳羡诸词人则不然,如徐士俊在《荫绿轩词序》中所言:“词与诗虽体格不同,其为摅写性情,标举景物,一也。若夫性情不露,景物不真,而徒然缀枯树以新花,被偶人以衮服,饰淫靡为周、柳,假豪放为苏辛,号曰诗余,生趣尽矣,亦何异诗家之活剥工部,生吞义山也哉?”[7]116一方面批评了当时词坛上的弊病,另一方面又说明了阳羡词派诸人在继承稼轩豪风的基础上融入了新的时代因素和感情意志,他们将自我的真性情不加掩饰地全盘付诸词作,从而避免了枯树着花的弊病。可以说对词体地位的推尊是“稼轩风”对阳羡词派之影响的深刻表现。除去理论上的推崇,该派在实际创作中的尊体倾向则表现在以真情入词。徐喈凤是以真率语力陈心中意的词人之一,蒋景祁在《荫绿轩续集词序》中评价其词时说:“词,诗之余也,其入人之深,移情动魄之致,则又妙于诗,故作者往往寄焉。”[7]117这表明词不仅同诗一样可以抒情达意,而且在动人心魄上更胜于诗。值得注意的是,清初阳羡词派推崇以稼轩为代表的豪放词风,却并不被豪放所困囿,他们所积极倡导的是词风的多变与兼容,多变的题材和词风才能容纳不同的情感表达。蒋景祁认为陈维崧词“取裁非一体,造就非一诣”[7]93,即言陈维崧词并不拘泥于豪放一派,他在取材、用意上博采众长,豪迈奔放可比苏辛,清丽工致可比周、秦,婉约香艳则可比温、韦,可见其纵横变化、丰富多彩的词学风格,这是该词派在推尊词体的基础上所做的开拓和创新,是对“稼轩风”另一种意义上的延续继承。
综上所述,阳羡词派对“稼轩风”的接受不仅促使阳羡词派本身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词学风格,而且也让以“稼轩风”为代表的豪放词风重新风靡于词学舞台。这二者的良性互动一改明末婉丽香艳的词风,使词体创作逐渐摆脱低微的文学地位,为清词的中兴提供了重要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