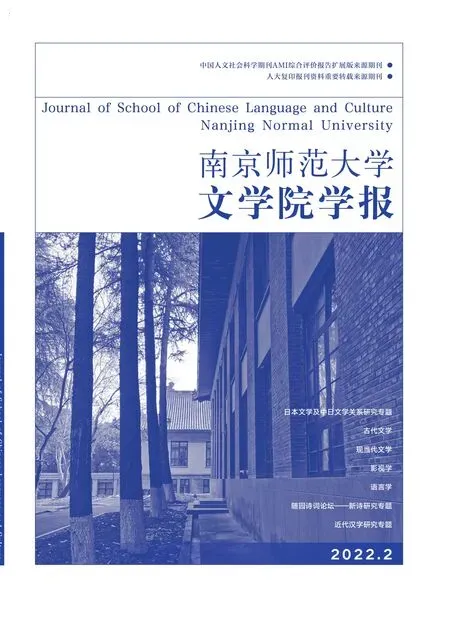日本汉诗的双语性特征探讨
严 明 梁 晨
(上海师范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036;上海师范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036)
溯源于中国古典诗歌而开枝散叶的东亚各国汉诗历经千余年,成为世界文学史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其中日本在诗作质量、留存数量和推陈出新等方面,都堪称东亚汉诗之典范。日本汉诗人长期处在双语读写的复杂环境中:一是身处东亚汉字文化环境中,中国古典诗歌成为日本汉诗创作的长期学习典范;二是日本汉诗人的母语环境,日语的发音、语法、表记等方面与汉语皆有根本性的差异。这种双语环境纠缠一体,长期影响着日本汉诗的发展。汉文典籍作为日本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占据主导位置,影响遍及日本诗文经史的书写。而双语环境对日本的儒官、僧人、诗人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使得日本汉诗创作及评论或隐或现地带上了双语特征。学界对日本汉诗的双语特征已有所关注,主要从两个角度出发:其一强调汉字这一视觉语言符号的跨文化功能;其二从训读法入手,分析日本汉诗人对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接受。归结到一点,就是以汉字、汉文为中日两国跨文化对话的共通性为前提。(1)陆晓光的《最早的双语诗歌集〈和汉朗咏集〉跨文化特色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1月)一文首次明确地提到了日本汉文学的双语性。然而,这篇文章仅略带过对汉字、假名两种书面表记系统的介绍,并未对双语性创作现象作深入探讨。吴雨平《橘与枳 日本汉诗的文体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从文体学角度对日本汉诗进行研究,亦关注到了作为汉诗物质载体的汉字。她强调了汉字和日本口语实际分属两个不同语言系统,并且用大量例证指出,在日本汉诗的发展历程中,汉诗人会写诗而不会汉语是一个普遍现象。她的研究进一步明晰了日本汉诗的双语特性。而这种文学生产机制之所以能够运作,其核心原因正在于汉诗的物质载体汉字是一种视觉语言的表记。马歌东的《训读法:日本受容汉诗文之津桥》(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首次以日本汉文学生成的角度,系统介绍了作为一种语言转换机制的训读法,并认为训读法同时影响了日本对中国文学的接受,以及本国汉文学的创作。辛文的《日本汉诗训读研究的价值与方法论前瞻》(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7月)一文是以训读法和日本汉诗之关系为中心最为深入和全面的论文。该文将日本对汉诗的训读从广义上的训读法中凸显出来,认为应当以“诗家语”为本位进行研究。而西方的日本文学史书写,则是以西方文学的话语观念统摄日本文学中的诗歌(poetry)传统。在西方视域下,中日两国之间看似不可逾越的语言差异,可以被整合进单一的民族文学传统中。这种处理方式意味着日本汉诗被明确划归为日本文学,它不再是“以唐诗为代表的中国古代诗歌影响并繁衍到海外的最大一脉分支。”(2)马歌东.日本汉诗溯源比较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1,第13页。这样的处理方式取消了两种语言文字、文化系统之间所存在的异质性,日本汉字作为日本民族语言书面表记的核心部分,也脱离了“汉字”这一暧昧表述,而成为了本民族文学的语言载体。可以看到,对日本汉诗双语特征的探讨,牵涉到对汉字的跨文化功能、中日文学关系,以及日本民族文学等重要问题的思辨,而这些思辨都关乎对日本汉诗本体的认知。因此,本文推进对日本汉诗双语特征的探讨,意在从多个角度深化对日本汉诗本体特征的认知。这种双语因素存在于东亚各国汉诗乃至汉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所以本文以日本汉诗为中心的研究,包含着对东亚汉文学具有双语特征的价值探讨。
一、日本汉诗双语特征的产生环境
汉字并非日本固有文字,在汉字传入前,日本没有自己的文字系统。日本语学者沖森卓也(おきもり たくや,1952- )区分了汉字在日本的“存在”与“传入”的不同。他认为,来自中国的早期移民或者外交使者等母语为汉语的渡日者,只是给日本带来了汉字的“存在”。因为这一存在并没有和日本语言发生关系,也没有影响日本文字的产生,因此不能认为是汉字真正“传入”日本。直到五世纪初,《论语》《千字文》等汉文文献经由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国内有记录和撰写文书的需要,而汉字在此过程中发挥了注音训读的作用,汉字才算是真正进入了日本。(3)沖森卓也.日本の漢字1600年の歴史[M].東京:ベレ出版, 2011,第16页。
王朝时代汉文典籍的阅读在日本皇室持续进行,对汉籍中意象、主题、思想的解读,形成效仿隋唐律令制国家的基础,另一方面也构建出日本汉诗产生之初的语境。以日本宫廷诗宴为例,最早记录是《日本书纪》所载:“显宗天皇元年(公元485年)三月上巳,幸后苑,曲水宴。”《日本书纪》是日本最早的正史,成书于养老四年(720),其记事从神话时代直到持统天皇让位(697),构建了七世纪以前的日本历史。这段补记的日本最初曲水宴,已经被染上了六朝文化的色彩。因为“上巳祓禊”和“曲水宴”均是从中国六朝时代舶来的仪式,进入到日本宫廷生活后成为贵族文学重要的场所。(4)林晓光.东亚贵族时代的曲水宴与曲水文学[J].学术月刊,2013(3),第132-139页。此外以唐朝开元礼为原型的释奠礼,也成为日本汉诗创作的重要场合。在释奠礼上,文章博士从《论语》《毛诗》《史记》《汉书》等儒家经史典籍中选出题目,让参礼者写诗。(5)菅谷车次郎.日本汉诗史[M].东京:大東出版社, 1941,第9页。除了皇室举办的各种宴会,亦有公卿在私人场合举办诗会,进行探韵、和韵等诗作游戏。
考察《怀风藻》、敕撰三集等王朝汉诗总集,可以发现日本汉诗人在早期写作中就受容了中国的时间观(千古)和空间观(天地、万国),将本国历史的构建置于与中国王朝平等的基础之上。如《怀风藻》中大友皇子《五言侍宴》:“皇明光日月,帝德载天地,三才并泰昌,万国表臣义。”(6)与谢野宽、与谢野晶子、正宗敦夫.日本古典全集:怀风藻、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本朝丽藻[M].日本古典全集刊行会,1925,第10页。阿倍仲麻吕《五言春日应诏》:“天德十尧舜,皇恩霑万民。”(7)与谢野宽、与谢野晶子、正宗敦夫.日本古典全集:怀风藻、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本朝丽藻[M].日本古典全集刊行会,1925,第15页。藤原不比等《五言元日应诏》:“正朝观万国,元日临兆民。”(8)与谢野宽、与谢野晶子、正宗敦夫.日本古典全集:怀风藻、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本朝丽藻[M].日本古典全集刊行会,1925,第19页。美努连净麿《五言春日应诏》:“此时谁不乐,普天蒙厚仁。”(9)与谢野宽、与谢野晶子、正宗敦夫.日本古典全集:怀风藻、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本朝丽藻[M].日本古典全集刊行会,1925,第17页。息长臣足《五言春日侍宴》:“帝德被千古,皇恩洽万民。”(10)与谢野宽、与谢野晶子、正宗敦夫.日本古典全集:怀风藻、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本朝丽藻[M].日本古典全集刊行会,1925,第25页。这也就是说,日本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对汉文化的全面吸收,使得日本汉诗自发轫便处在双语环境中。日本汉诗在承担了王朝时代儒官贵族言志抒情的同时,也成为了日本早期国家形成中政治文化话语的有机组成部分。来自中国的文章可以经国的观念,成为发轫期日本汉诗的认知底线。正如日本文化史学者池田源太在《文章的经国性格》一文中写道:“(文章的经国性格)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文化现象。从八世纪晚期到九世纪前叶,对国家的文化、文明的思考成为一种独特的思想立场。而这在日本文化发展历史的其他时代是没有其他类似的例子的。”(11)池田源太.平安初期における文章の経国的性格[G].古代学协会编.桓武朝の诸问题,1962,第9页。
而在王朝时代之后,中国传统的诗学话语作为日本汉诗生成、演化的重要动力,持续发挥着深刻的影响,其中以汉字为载体的东亚汉文化圈的向心力是至关重要的。日本汉语史学者平田昌司曾经提到汉语的核心特点:“汉语很突出的特点可能仅有一个:坚持全用汉字书写的原则,拒斥其他文字进入中文的体系里,正字意识十分明确。”(12)平田昌司.文化制度和汉语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第1页。而具体到汉字作为汉语书面表记的特征,他又指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事实:正字、韵书、科举功令严密地覆盖汉语基层的多样性,稳固地控制书面语言的单一性,甚至还给东亚汉字文化圈不断提示了中国语言的典范。”(13)平田昌司.文化制度和汉语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第9页。确如平田昌司所言,以汉字为载体的东亚汉诗,是围绕着中国古典诗歌典范而生成的。经典汉诗文作为中国汉字文学的典范,在东亚汉文学创作中不断地被模仿,而东亚汉文学的发展则不断加固着汉字的典范性。
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范式,以汉字为载体,包含了声律规范、用典、诗学观念等重要因素。东亚汉诗人在创作时,其学习的正是以汉字为核心的这一整套话语体系。而这种话语体系被东亚汉诗人接受,并不断创作出新的作品之后,其影响便超越了中国,具有了跨国界、跨文化的东亚性格。
日本汉诗人特别关注汉诗范式中的声律规范。江户后期的大江玄圃就认为,古今诗歌的联系就在于诗格,即作诗的法度和准则,这是古今诗歌的不变本质:“格者何也?法准之义也。法准者何也?必有法准焉。……格之既设矣,格诸开天而施于今,今之诗犹古之诗乎。瑕犹可磨,质岂可变焉?”(14)大江玄圃.盛唐诗格[M].赵季、叶言材、刘畅.日本汉诗话集成.北京:中华书局, 2019,第952页。日本第一部汉文诗话——平安中期空海的《文镜密府论》即将四声谱、用声法式、用韵等内容放在开篇。可见当时的汉诗人继承唐人认知,对于诗的用韵和平仄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将这一部分的内容视为学诗的首要根基功力。此后,韵语和平仄的问题一直是日本诗话始终关注的对象,如《诗家声律》(宇野士朗)、《诗律兆》(中井竹山)、《诗律天眼》(熊阪台州)、《社友诗律论》(小野泉藏)等诗律专论的层出不穷,显示出声律探究在日本汉诗创作中的重要地位。进入江户时期后,集中出现了一批专门的音韵学研究。如《古诗韵范》(武元质)、《磨光韵镜》(释文雄)、《汉字三音考》(本居宣长)等。这些著作对汉字的字音、作诗用韵采用示例、韵图等方式进行考辩。而到了明治年间,随着西方语言学相关理论的输入,后藤朝太郎、大岛正健等人对汉诗的音韵、四声、古韵等作了系统梳理。至此,古代日本的音韵学研究以汉诗为起点,完成了到汉语史的跨越。
二、日本汉诗双语特征的张力冲突
日本古代汉诗人用非母语进行汉诗创作,在两种语言的差异张力下,必然会产生与中国古典诗歌创作范式及汉语典范性的难以融合,乃至发生冲突。在这些张力冲突中,最明显的就是汉诗声律。日语和汉语属于不同的语系,发音和语法等有着较大差别。这就导致日本汉诗人在汉诗创作中经常出现声律不协的困境。赤泽一堂《诗律》指出日本汉诗人不明四声,漫口作诗的现象:“今世作者不谙诗律,漫然任口缀述,未尝知四声为何物也。”谷斗南的《全唐诗律论》也指出,江户汉诗人中真正能辨清诗律的并不多。这反映出江户汉诗创作的真实状态,对汉诗声调、平仄之类诗律的掌握,很难达到纯熟程度。野口苏庵的《诗规》探讨其中的原因:“我邦平入二声皆能记认焉,上去二声易混,故少留意下仄处,欲其不为皆上皆去,是可耳。”这说明日本汉诗人并不是完全不领会四声,而是因为受母语发声的影响,能够记认古汉语的平声和入声字,对于上声和去声字则容易混淆。这种双语冲突的识别规律反映到日本汉诗创作中,则表现为对仄声部的上去两部分字易混淆,所以须特别注意,尤其要避免上声和去声字混用。
大多数日本汉诗人,并没有和中国诗人直接交往切磋的机会。光绪七年(1881),嘉兴诗人陈曼寿为日本人小野泉藏的《社友诗律论》作序,指出了这一因素对日本汉诗人创作的不利影响:“所惜当前东道未通,不得与吾邦人时相讨论,以致疑无不质,难无不问,以传误,不可救药。”可见由于缺乏与中国诗人的交流反馈,日本汉诗中一些声病的产生,是在失衡的双语环境中的无奈现象。
对于日本汉诗中普遍存在的声律不谐的现象,日本人有一个专门名词来形容——“和臭”(或名“和习”)。如果说声律的不协调是双语性语言环境对日本汉诗创作的影响结果,那么汉诗中用典的选择,则涉及到两种语言文化的冲突和协调,这首先表现为汉诗中日本的人名、地名,其命名规则都与中国有所不同。
日本汉诗人为追求风雅,往往将本国汉诗人的双字姓改成中国的单字姓,这种做法可以上溯到平安时代。从平安时期的说话集《江谈钞》中可看到,贵族庆滋保胤被称为“庆保胤”,同时期的贵族大江以言则被称为“江以言”。(15)江村北海.日本诗史[M].富士川英郎, 松下忠, 佐野正巳.词华集日本汉诗(卷二).东京:汲古书院,1983,第17页。对于这种改姓风气,从“是编多完录姓氏”的做法可以看出,江村北海是倾向保留原来的日本复姓的。只是由于改汉化单姓的做法已经蔚然成风,北海对汉诗人改汉姓的做法采取两可的态度。
如果说人名姓氏更改尚不足以形成激烈的争议,那么地名的汉化改动,则直接影响到了汉诗的解读。《日本诗史》就提到:“远江州称袁州,美浓州称襄阳,金泽为金陵,广岛为广陵之类,于义有害,是以一概不书。”《夜航诗话》也提到上述例子:“美浓为襄阳,伊贺为渭阳,播磨为鄱阳,相模为湘中……”(16)津阪东阳.夜航诗话[M].赵季,叶言材,刘畅辑.日本汉诗话集成.北京:中华书局, 2019,第1582页。这些日本的地名改头换面之后,变成了中国的地名,这让读者感到疑惑。对于汉诗中的这种地名更改风气,《夜航诗话》指出了根本原因:“我邦凡百称呼多不雅驯,而地名特甚也。先辈病其难入诗,往往私修改之。”(17)津阪东阳.夜航诗话[M].赵季,叶言材,刘畅辑.日本汉诗话集成.北京:中华书局, 2019,第1582页。可见,日本汉诗人对人名、地名改造的风气,实际上是以汉文化为雅驯,以本民族文化为俚俗的认同结果。
到了明清时期,日中间的人员及书籍往来增多,很多中国文人接触到了日本汉诗作品并进行评价,这对日本汉诗创作带来直接影响。十六世纪,侯继高的《全浙兵制考》中有《日本风土记》,其中收录10余首日本汉诗。进入江户时代,以长崎商贸港为据点的日中书籍往来更为频繁。《竹田庄诗话》记录了随货船来到长崎的清朝商人中也有不少能文识诗者,他们与日本人谈诗论画,对长崎的文教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长崎镇,华夷通交转货处,故士民富饶,家给人足,治平日久,渐向文教。加之清商内崇尚风雅,善诗若书画者往往航来,沈燮庵、李用云、沈铨、伊孚九辈不遑搂指,故余习之所浸染,诗书画并有别致。”(18)田能村竹田.竹田庄诗话[M].赵季,叶言材,刘畅辑.日本汉诗话集成.北京:中华书局, 2019,第2036页。
西岛兰溪(1780-1852)的《弊帚诗话》也提到了中日交往对本国风土之雅化的影响。他引述了《孔雀楼笔记》中记载的一则故事:天皇曾派当时的弹正大弼仲国连夜追捕一个逃跑的妾。而这则故事的作者,将“弹正大弼”(从五位上,弹正台,负责监察中央行政)写作“御史中丞”。尽管在职责上两个官职的范围是相当的,但弹正大弼只是“散官”(弹正台到后来只是一个名存实亡的机构),受天皇私命是正常的。然而在中土人士看来,仲国位居“御史中丞”,居然受皇命做追捕逃跑的小妾这样的事情,会觉得可笑。因此《孔雀楼笔记》的作者认为,应该将日本的官职名称直接保留,不应换成中国的官职名,以免产生误解。西岛兰溪举了一首诗中的例子:“摘菜公卿设春宴”。“摘菜”本是公卿姓名,但如果给中土人士看这首诗,则会觉得诗的描写对象身居要职却以采摘蔬菜为游戏,造成误解。从中日名称更改的事例中可以看到,随着中日交流空间的扩展,日本汉诗的接受范围逐渐从本国扩展到了中国,其名称的雅化、借用、更改等,会造成一些有趣的误读。而产生误解冲突的根本原因,是日本汉诗中的汉字名称,表面看是在东亚汉诗共同表意系统中运行,彼此都明白语义,但实际上却暗藏着两套不同的话语体系,即双语交缠并产生了差异张力,其真实语义难以彼此都明了,这便是日本汉诗中产生所谓“和习”的内在动因。
三、日本汉诗双语特征的展开路径
(一)训读:阐释汉籍经典的双语方式
日本汉诗人对人名、地名的汉化改造,源于身处外来语的汉字系统中,但实际上还受到母语的潜在影响。对这种中日双语使用乃至特征展现,须考虑到其内在的发生机制,即日本人是如何接受和解读包括中国诗歌在内的汉籍经典的?这就涉及到汉文训读法。
汉字是最初记录日本文学的书面语。日本文学的产生,从一开始就涉及对汉文典籍的解读。探讨日本汉诗创作的双语特征,对其解读汉诗文方式的考察就非常重要。
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佛教、基督教的典籍翻译是在两种定型而成熟的语言系统之间进行的,因此可以从一种语言文字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文字。而汉诗文经典进入日本之初,日语还没有形成独立成系统的文字体系,所以不可能用日语直接翻译汉语文献,只能采用在汉籍文献文本上标注符号的方式,来完成汉籍的阅读和理解。这其中就包含着后来学界对训读本质的争论:它到底算一种翻译,还是只是“阅读汉文的方法”?所谓“训读”(くんどく),是指在汉文字一侧用符号进行标记,说明汉文中词语的发音、词性和阅读顺序。随着汉字的广泛使用且汉字与当地语音的对应关系趋于稳定,日本人得以借助训读法直接理解汉诗文,并按照日语句式将其朗读出来。
汉文训读保留了汉文中的文字和语法,但不是用一套全新的符号系统进行翻译替代。由于训读符号的加入,日本人在理解汉诗文时,其文本的语法句式发生变化,出现了两种语言系统的并置。值得注意的是,训读只是一种汉诗文解读法,并没有一种官方的统一规定。在江户时代以前,对汉籍文本的训读是在各家博士、学者的流派内进行,通过老师和弟子口口相传流通的。
释大典《诗语解》云:“虽然倭夏异语,环逆异读,即有丁尾鱼乙,代之象胥,乃谓能会,亦即隔靴,而况其不会者乎?且夫行文之间斡旋之要多在助字,而助字固难以一定论矣。”这里所指“丁尾鱼乙”的异读,就是指在汉文原文一侧随行标注的训点,按照日语的语法顺序进行理解阅读,也就是训读法。释大典认为,通过训读来解读汉籍最终还是如隔靴搔痒。训点的位置、读法并无定法,这也容易造成对同一汉籍文本的不同解读。他从诗语言的特殊性出发,论述了训读法的不可取却又不可弃:“华之与倭,路自殊者乎。又况诗之爲言,含蓄而不的,错综而不直,加之音节,不容一意训释者乎?……故倭读之法不可取,不可舍,其说在于筌蹄也。”(19)释大典.诗语解[M].赵季,叶言材,刘畅辑.日本汉诗话集成.北京:中华书局, 2019,第5523页。
正因为诗歌的语言婉转含蓄,所以才可以有多种意义诠释的空间。也因为有了双语的背景,由于训读而产生的新的解读意义,自有其合理性。从平安时代到室町战国时代,处于私传状态下的训读方法,就如同律令制国家的汉字、汉学,是一种被权贵阶层垄断的知识体系。进入江户时代之后,印刷术的大量使用使得汉籍得以普及并向更多阶层传播,对于训读法的知识垄断才逐渐消除。对于日本汉诗的发展来说,作为知识的训读法的普及,促进了日本儒学者、汉诗人乃至市民百姓对日中两国汉诗经典的接受和吸收,不同的解读观点以结社、诗话等媒介进行传播,促成了日本汉诗创作及本土诗学理念的成熟。
(二)和文诗话:日语书写中的诗学自觉
无论是将语言和性情对立,还是将汉诗与和歌区别,从中都可看到对汉字乃至汉诗文体特殊性的认识。汉诗的文字及形式,都迥异于日本的母语及和歌。日本汉诗人的创作,其发生机制是在操作两种语言互补的艺术,其核心机制在于调和这两种诗歌语言,使之合乎日本汉诗规范,以便抒发感触性情。围绕着调和双语策略的展开,日本诗学中的本土理念也逐步发展成熟。
日本本土诗学理念成熟的标志之一,在于和文诗话的大量出现。江户时期出现了一大批和文诗话,这些诗话是为了帮助日本汉诗人及读者更便捷地了解汉诗和汉文诗话。这反映出日本汉诗的双语性不仅影响到了汉诗创作,还影响到了对汉诗的批评。而和文诗话的出现,更便于表达日本诗坛的本土诗学意识。
和文诗话大致分为以下四种:对中国诗歌的注释、品评:如衹園南海的《明诗俚评》;作诗法的说明:如川合春川的《诗学还丹》;对韵格规范的系统阐述:如武元登登庵的《古诗韵范》;整理解释汉诗创作中的常用诗语:如藤良国的《诗语金声》。和文诗话发挥的重要功能,是帮助汉语水平不高的日本汉诗人更好地理解汉诗经典及诗学理念。正如南海衹园《明诗俚评》跋语自言,体恤时人解读汉诗艰难,就撮钞明诗绝句,以国字(日本语)加以解释。日中语言文化的差异使得日本人对汉诗的理解有着较大困难,而和文诗话则可在很大程度上纾解这种双语间切换的解读困难。川合春川也认为,用日语解汉诗,有益于初学者深入理解汉诗意境:“其为书也,以国歌为诗句,以和言为诗语之事,将俾初心易人于学诗之境。”江户和文诗话的产生,满足了日本汉诗创作主体扩大后的学诗写诗的社会需求。而江户诗学批评的繁荣,也推动了大量汉语诗话的刊行,和文诗话可以发挥训解普及作用,因此应运而生,比如《诗语金声》便是其中之一,“宜且择其所由近时诗学之书,亡虑数十百种,率皆以国字训释,使初学有所措手。”(20)川合春川.诗学还丹[M].池田四郎次郎,国分高胤.日本诗话丛书.东京:文会堂书店,1921,第5335页。有了和文诗话,日本汉诗及诗话的传播范围更趋宽广,受众也愈加增多,这就大大拓展了日本汉诗意义解读的本土空间。日本汉诗人在和文诗话的表述中,逐步建立起有着本土意识的诗学理念。武元登登庵《古诗韵范》是一部专论汉诗用韵的诗话著作,其言“夫人之性情固不以域异,而音韵则以地殊焉。不以域异者,虽深远而可辨,凡说诗者是也。以地殊者,或浅近而难明,如古诗韵脚是也。彼诗法传于我尚矣备矣,而未尝有论古诗韵脚者也。”(21)武元登登庵.古诗韵范[M].赵季,叶言材,刘畅辑.日本汉诗话集成.北京:中华书局, 2019,第5372页。可见武元氏已经意识到汉诗创作涉及到不以域异的人之性情,也涉及到因域而异的诗体韵律,他看到了日本汉诗的双语性质,中日汉诗人的性情可以不因地理空间的差异而不同,但中日汉诗的音韵则会随着母语的转换而发生改变。因此,日本汉诗创作的用韵,有必要从本国语言文学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一些变化改革。可以认为,江户时代的日本汉诗人开始萌生自创一体的意识,即突破单一汉语的局限,兼采本土语言,从双语的角度展开对日本汉诗的论述,最终建立起具有本土特色的诗学叙述。
(三)双语对译:跨语言、跨诗体的诗学对话
江户汉诗人开始有意识构建日本语境下的诗学阐释,包括和文诗话的写作,达到对中国诗歌经典、诗学论著的独特解读。江户诗坛同时展开的,还有汉诗和歌之间的对译,其诗学意义及价值则超越了古已有之的训读法。江户时代汉诗与和歌的对译,产生了两方面的作用,一是通过双语对译,加深了对中国诗歌经典的理解,使之成为提升日本汉诗乃至和歌创作的重要因素;二是借助和译推广汉诗,也通过汉译沟通和歌,这样的双语对译有效降低了日本人汉诗解读及创作的难度。
日本早就有对汉诗的和译本,如镰仓初期歌人源光行(1163—1244)编著的句题和歌“三部曲”,分别译自唐人李瀚《蒙求》为题的《蒙求和歌》十四卷、初唐李峤《百咏》为题的《百咏和歌》十二卷,以及中唐白居易《新乐府》为题的《乐府和歌》五卷(后散佚)。源光行对三部唐代诗选的和文译作,是日本汉文学史上对汉诗、和歌两种诗体进行密接对译的成功尝试。
江户前期的古文辞派汉诗人是汉诗和译的积极实践者,他们主张直接阅读中国经典,不重视古已有之的训读法。荻生徂徕《译文筌蹄》明确反对训读,认为阅读经史典籍就要遵循汉语的语序:“但此方自有此方言语,中华自有中华言语。体质本特,由何吻合。是以和训回环之读,虽若可通,实为牵强。”(22)荻生徂来.译文筌蹄[M].须原屋书店,1908,第3页。太宰春台也认为,日本人之所以难以理解汉诗文,是因为被训读语序所混淆,所以训读有碍于解读汉诗文义理。(23)太宰春台.倭读要领(卷上)[M].嵩山房,1728,第12页。传统训读法是用混杂汉语与和文特殊表记来解读汉诗文文本,古文辞派则主张直接阅读汉语文本。也就是说,古文辞派倾向于将汉语视作纯粹的异质文化的语言。基于这样的主张,古文辞派汉诗人成立了译社,直接进行汉文和译,并重视“活的”中国语,邀请长崎的唐通事冈岛冠山传授汉语口语。
古文辞派诗人有尝试将汉诗译成日本俗谣体,如服部南郭就翻译了唐朝诗人郭震(656—713)的《子夜春歌》。原诗为:“陌头杨柳枝,已被春风吹。妾心正断绝,君怀那得知。”译成日语歌谣为:“道のほとりの青柳をあれ春风がふくわいなワシが心のやるせなさ思ふ殿御に知らせたや。”(24)日野龙夫.日野龙夫著作集〈第3巻〉近世文学史[M].东京:ぺりかん社,2005,第464页。江户后期的汉诗人大江玄圃(1729—1794)也曾译过这首诗:“往き返る、ちまたの柳、枝垂れて、春のあらしに吹かるめり、心乱れしこのうさを、恋しき人の知るべくもがな。”(25)日野龙夫.日野龙夫著作集〈第3巻〉近世文学史[M].东京:ぺりかん社,2005,第464页。
而到了1774年,田中江南刊行译诗集《六朝诗选俗训》。此书翻译了中国六朝时约三百首恋爱诗。如萧衍的《子夜歌》:“恃爱如欲进,含羞未肯前。朱口凳艳歌,玉指弄娇弦。”,译为:“少し甘えてどうか そばへよりたさうで、臆面してようより添はぬ、美しい口で『メリヤス』を歌ひ、きゃしゃな手で三味線·琴を弾く。”(26)日野龙夫.日野龙夫著作集〈第3巻〉近世文学史[M].东京:ぺりかん社,2005,第466页。江户时代日本汉诗人的汉诗经典和译,多选恋爱诗作,这一选诗倾向与日本文学的传统直接相关。古今和歌多以男女恋爱为题材,如《万叶集》中的恋歌发源于歌垣这一上古时代的民俗活动,并集中在“相闻歌”这一分类中(27)远藤耕太郎.万叶集の独咏的恋歌の生成 : 歌垣歌からの连続と飞跃 (山田直巳教授退职记念号)[J].成城大学社会イノベーション研究,2019(2),第1-14页。;《古今和歌集》则第一次将“恋歌”作为单独的分类。在中国,《诗经》、六朝诗以及中晚唐诗是古代爱情诗发展的三个重要阶段。随着两汉文人逐步接受和参与创作乐府歌曲,原先集中在民歌中的爱情表现进入到雅诗中,成为六朝诗歌的重要题材。(28)杨新民.试论中国古代爱情诗创作的三次高潮[J].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6(2),第36-44页。
而在早期和歌集中,亦能观察到恋爱题材的和歌与中国六朝诗的密切关联。日本学者辰巳正明总结了《古今和歌集》与《玉台新咏》的联系,发现两者的共同点在于男性诗人以思妇身份进行抒情。上述《六朝诗选俗训》选译的诗体,显示出编译者田中江南特别关注六朝时的清商曲辞。曾智安的《清商曲辞研究》注意到,清商曲辞并不纯粹是俚俗的民歌,而是同时包含了文辞典雅的文人雅歌,显示出了文人雅诗创作与民歌清商曲辞的双向互动。田中江南对清商曲辞的译作,则是以这些经由文人加工雅化的六朝诗为对象,用日本的语言和诗体进行文学表达,这一双语对译过程被称为“俗训”。
从六朝诗到和歌俗训,意味着中日两种语言诗歌背后的艺术对话和文化转化。比如萧衍诗中的“艳歌”被译成“メリヤス”,后者是日本民族音乐的一种,多用于歌舞伎和净琉璃的演出。另外,译后的和歌中也出现了三味线这一日本本土的乐器名称。可见在俗训时,译者所做的不仅是努力保持原诗的含义,更重要的是对其中内容进行本土语境化的处理。田中江南的汉诗和译,与传统的汉诗训读法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训读保持汉诗原样书写,只是对其中部分汉字的位置进行返点标识,阅读时调整语序以符合日语的语法习惯,但不改变汉诗的书写顺序。而江户汉诗人对汉诗经典的和译,则是在中日两种语言诗歌之间的对译,并涉及汉诗与和歌两种诗体之间的交汇互通。江户汉诗和译之作大都涉及爱情婚姻及现世人情内容,大量汉诗和译本的刊行,贴近了日本读者的阅读习惯,也提供了更为丰富多彩的中国诗歌经典。
江户中期后的汉诗人,有意通过汉诗和译来普及汉诗知识,降低汉诗创作的门槛。1801年,柏木如亭选择五山时代流行的《联珠诗格》中130余首汉诗,译成《联珠诗格译注》刊行。(29)日野龙夫.日野龙夫著作集〈第3巻〉近世文学史[M].东京:ぺりかん社,2005,第469页。《联珠诗格》全称《唐宋千家连珠诗格》,南宋蔡正孙(1239—?)选编,以七言绝句为主,罗列唐宋诗人诸家诗格。其编撰意图,据蔡氏序曰“凡诗家一字一意可以入格者,靡不具载,择其尤者,凡三百类,千有余篇,附以评释,增为二十卷,筹诸梓,与鲤庭学诗者共之。”(30)于济,蔡正孙.唐宋千家联珠诗格校证(上)[M].南京:凤凰出版社, 2007,第50页。可知蔡氏选编此书是为童子学诗之需。此诗选在中国刊行后不久失传,但传到朝鲜和日本后却长期流行,对东亚汉诗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联珠诗格译注》是用当时的日本语进行翻译的,为了便于初学者的理解而加了注释。比如其中贾至《巴陵夜别》:“柳絮飞时别洛阳,梅花落后在潇湘。世情已逐浮云散,离恨空随流水长。”译为:“柳の絮の飛時、洛陽で别れてきて、梅の花の落后は 潇湘の川のあたりに在た、世情は已浮云を逐て散たが、いま別る恨は 空にこの流水に随て长。”(31)日野龙夫.日野龙夫著作集〈第3巻〉近世文学史[M].东京:ぺりかん社,2005,第469页。这种译注式的诗选文本,其功能类似于前一节所说的和文诗话的创作,即用日本的语言阐释中国诗作经典,降低本国人学作汉诗的门槛。
川合春川《诗学还丹》的做法则更进一步,探讨了直接取材和歌的汉诗写作法,使日本汉诗人能借助日语及和文学直接进行汉诗创作。川合氏认为,和歌是本朝俗歌,而汉诗是中土声诗,因此对日本人来说,和歌容易明白,汉诗却难以解读,更难创作,所以由翻译和歌入门进入汉诗创作有其便捷性。川合氏还提出和歌译汉诗的具体步骤:先了解汉诗的基本知识,比如汉诗的各类诗体,包括律诗绝句的平仄声律要求等;然后是和歌译汉诗的几种具体方式;最后是关注和融汇和歌及汉诗中的使用典故。这样可以帮助日本汉诗人将汉诗写出含蓄绵延的风格。(32)川合春川.诗学还丹[M].池田四郎次郎,国分高胤.日本诗话丛书.东京:文会堂书店,1921,第194页。
川合春川以能因法师(中古三十六歌仙之一)的和歌为例,进行和歌汉译的尝试。比如“嵐吹く三室の山のもみぢ葉は龍田の川の錦なりけり。”(后拾遗集·秋)这首和歌译成汉诗则是:“御室山头枫叶秋,秋寒玉露染红愁。请看吹尽西风色,总入龙江作锦流。”另有《后拾遗集·羁旅》中的一首:“都をば 霞とともに 立ちしかど秋風ぞ吹く 白河の関。”其中“秋風ぞ吹く 白河の関”一句译作汉诗句,则为“白河关外是秋风”。还有《新古今和歌集》中的:“山里の春の夕暮来てみればいりあひの鐘に花ぞ散りける。”其中“いりあひの鐘に花ぞ散りけ”名句,译作汉诗句子“百八钟声催落花”。
日本和歌有着鲜明的季节感,川合春川所选这三首和歌也都突出描写了秋天景物和歌人的感受。特别是最后一首歌,不论是夕暮,还是钟声和秋日的组合,所突出的寂寥惆怅之感成为了日本文学的重要母题。川本皓嗣的研究指出,这一意象组合在《万叶集》中就已出现,而从《新古今和歌集》开始,秋夕之歌作为单独一类被收入和歌选集,频繁出现在羁旅题材和歌中。这类和歌中独具特色的意象,使得译出的汉诗句也具有了了浓厚的季节感、色彩感和忧伤感。这些从和歌译成的汉诗句,并没有因两种语言诗歌对译而产生违和感。其原因在于中国诗歌传统中本来就有“自古逢秋悲寂寥”的主题,这一点与和歌悲秋基调大致吻合。再加上和歌采用五七调,翻译成汉诗的五言、七言体,大致可以通过字词音节的对应完成韵律的互换沟通。
明清文献中也有对和歌汉译法的记载,比如明代李言恭《日本考》卷三将和歌汉译的过程分为五个部分:真名假名体对照、呼音、读法、释音、切意,并以天智天皇一首和歌的汉译为例加以展示。(33)书影来自于: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26179&page=12
“真字”即汉字,“草书”即假名,“呼音”则是用较大的字体书写和歌中的汉字,旁边用较小的字体书写这一汉字的读音。其标记读音的方式,是用发音相近的汉字组合进行表示。如“秋”(あき-aki),写作“阿气”;“田”(た-ta),写作“塔”。(34)李言恭,郝杰.唐大和上东征传·日本考[M].汪向荣,严大中校注.北京:中华书局, 2000,第103页。在完成了对和歌中汉字的读音标记后,“读法”的步骤中,将和歌中所有汉字、假名的读音使用发音相近的汉字连缀起来,构成完整的“读法”。“释音”是将述的读音分为几类:汉字词与汉语义同的,保留汉字词原来的写法,曰“正音”;如“の”(的)一类的助词,则曰“助语”;至于假名词语,则用汉语进行翻译,如“革里复”(かりほ,刈穂),意思是割稻穗。最后的“切意”,则是和歌的汉诗译作,其诗多为四言、五言体。如此译作“秋田收稻,结舍看守。盖荐稀疏,我衣湿透。”由上可知,《日本考》记载的和歌汉译方法,保留了和歌的书写原貌,而其明确的译诗步骤和举例,则为译诗者提供了可实操的参考。
《日本考》与《诗学还丹》都记载了和歌汉译法,在译诗目的、翻译方法上存在着一些差异。《日本考》所涉内容除了日本语言文字、文学的介绍,还包括日本的自然地理和物质文化,其记载的和歌汉译方法,是作为明代对日本整体认识的一部分而存在的,并不像《诗学还丹》是指导日本人写汉诗的诗话。《诗学还丹》沟通和歌与汉诗,其推行和歌汉译的目的是为了让日本人能够便捷掌握及创作汉诗;而《日本考》记载的和歌汉译,其目的是为中国读者了解日本和歌,并无指导和歌创作的目的。
关于具体的译法,《日本考》涉及到写法、语音、语义诸方面,在译成汉诗时,以字字对应的方式,尽可能地切合和歌原意。而《诗学还丹》侧重于从形式和表现方式上模仿汉诗,并不注重字义的完全对应。如“嵐吹く 三室の山の もみぢ葉は 龍田の川の錦なりけり。”这首和歌,其中并没有“愁”字,但作者根据文本的意境翻译成了“秋寒玉露染红愁”,强调了歌人面对秋日红叶所含有的物哀之感。还比如“秋風ぞ吹く 白河の関”一句,作者将“白河の関”译成“白河关外”,则是强调了中国诗歌传统中“关外”边塞意象的苍凉,替代了和歌原作中描述秋风的动态之感。
总的来说,相对于《日本考》追求原文与译文对应,《诗学还丹》以和歌为切入点帮助日本读者入门汉诗创作,其最终目的是要从本国语言出发,创作出符合汉诗范式的汉诗,因此更强调汉诗与和歌两者的差别,继而突出汉诗特有的风格。可以说,川合春川探究译歌入诗之途径,开启了日本人学习汉诗的方便之门。更重要的是,从和歌汉译创作实践中可以看到一种新的可能:不同于以往从中国诗歌、诗学文本出发建立起本土的诗学话语,日本汉诗人也可以直接从本民族语言文学传统入手,逆向构建起跨语言及跨民族文化的诗学对话。
四、结论
通过对日本汉诗人阐释中国诗歌、诗学文本方式的考察,可以看到在同一性与差异性并存的双语环境下,日本汉诗及本民族诗学理念的生成,皆有赖于对中国诗歌经典、诗学论述的传承解读。这种生成机制既说明了日本汉诗传统的构建受到中国诗学影响的客观现实,同时也凸显出日本汉诗人阐释主体的作用,进而确认日本汉诗在日本文学传统中的重要位置。
日本汉诗的双语性特征对日本汉诗乃至东亚汉诗的研究来说是重要的。从日本汉诗的双语性特征切入,我们可以观照日本汉诗创作语言及诗体的两重路径,进而探究日本汉诗乃至东亚汉诗创作过程中的双主体性特点。
首先,汉诗双语特征的形成,是以汉字文化圈为基础的,因此日本汉诗创作受到汉文经典传承的深刻影响。日本汉诗被纳入隋唐以来的东亚文化共同体中,共享了汉字汉籍及汉文化的丰厚知识体系。特别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范式,直接开启和深刻影响了日本汉诗的发展。日本汉诗发展的每个阶段,都可以清晰地看到日本汉诗与中国诗歌创作、诗学观念的对应关系脉络。
其次,汉诗双语特征的另外一面,是日本汉诗人在接受汉诗文的时候,采用训读、互译的方式。其中受到本民族语言文化的影响,必然反映在日本汉诗的创作与诗学观念评论中。积淀久之,就会出现兼取和歌写法,摆脱中国诗歌经典范式的一面。汉诗双语特征的生成,有赖于日本汉诗人创作过程中的跨文化对话机制。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视域下,两种异质文化的交流,本质上是对话双方携带自身话语体系和特征在意义层面上进行的接触。具体来说,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在跨文化文艺创作中的实践可分为独白、协商与争论三种模式。(35)冯伟.独白、协商、争论:当代跨文化戏曲的中外“对话”模式研究[J]. 中国比较文学,2020(4),第15-27页。其中,协商被视作跨文化对话中的创造性转化的核心力量,体现了求同存异的诗学立场。从这一角度看,日本汉诗是日本汉诗人进入汉字文化场域,化用中国古典诗歌创作范式,并融入本民族语言、情感之后生成的。
从日本汉诗创作看,日本汉诗人对中国古典诗歌创作范式的态度,基本以尽可能接近中国诗人的理解为目标。中国古典诗歌作为汉字文化圈中的共同规范保持着崇高地位,中国诗歌经典随着汉籍在东亚的流转而被东亚各国汉诗人长期阅读与改造。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古典诗歌创作范式与东亚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并非征服与顺从,而是相互激发。中国诗歌范式的影响,不仅关涉日本汉诗创作,也关乎东亚各国本土文学样式的变化发展。比如和歌的意象、主题、歌体乃至歌论,皆充满中国古典诗学影响的痕迹。
然而,汉字文化圈和本国语言文字双向作用下形成的汉诗双语环境,使得江户汉诗人趋向于兼顾本土文学文化的实况习惯,对舶来的汉诗经典范式进行改造。这种接纳和改造,发挥出了日本汉诗人的主体能动性。如上文提到的对人名、地名的改造,就体现了日本汉诗人在汉诗创作中的能动性。而在这种发挥能动性的背后,则是对大和民族文化主体意识的彰显。
在巴赫金对话理论的基础上,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提出了“互文性”的概念。在互文视域下,每个文本不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存在于文本的网络之中,其构建有赖于对现存文本的回溯。(36)李明.文本间的对话与互涉——浅谈互文性与翻译之关系[J].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2003(02),第5-9页。就日本汉诗而言,它存在于以中国古典诗歌为中心的东亚汉诗文本群中。它的发展,是历代日本汉诗人与中国古典诗歌经典对话的结果。特别是日本汉诗人对汉诗声律的讨论,在促进日本汉诗声律范型成熟的同时,也引入了域外视角的多元理解,丰富了东亚汉诗中以声论诗的审美观念。
日本汉诗作为本民族文学的一部分,意味着日本汉诗也处在日本文学文本的网络之中,并与和文创作产生互文的关系。早在《和汉朗咏集》早期汉诗和歌选集中,就可看到汉诗与和歌唱和、竞赛的现场。从日本汉诗文本的双语特征,到日本汉诗创作的双主体性质,使得诗、歌互文关系在促进两者审美观照相互激发的同时,也促进了和歌的经典化历程。当汉诗进入到日本本土文学的互文性网络中,也加强了这一网络中主要文本的双语特征。双语特征是考察日本汉诗民族性的重要途径,也成为日本汉诗发展动力的重要来源。在世界文学史上,这种以双语特征为切入,观照异质文化互动对文学影响的例子并不少见,以下试举两例。
第一个例子是后殖民视域下的非母语写作研究。非母语写作这一概念通常被用于分析少数民族文学、离散(流散)文学(diasporic writing)等主题。“diaspora”这个词来自希腊语,意思是“分散和播种”,最初是指巴比伦流亡后巴勒斯坦境外犹太人的分散和定居。而在后来,这个词被广泛用于形容犹太人流亡各地的灾难性历史。其流散想象的关键部分是寻求回归巴勒斯坦和建立犹太国家的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全球化现象中人口流动带来的“边缘——中心”关系的重组,使得流散现象及对流散现象的理论分析成为了文化研究的重要方面。(37)王宁.流散文学与文化身份认同[J].社会科学,2006(11),第170-176页。应该注意的是,“流散”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人类历史上由来已久。但作为后殖民批评话语的“流散”的成立,则是基于全球化的特殊语境,这与东亚汉诗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异质文化互动而出现的双语特征,有着本质的不同。
第二个例子是拉丁语与欧洲各民族语言文学的互动关系。古罗马帝国的扩张使得拉丁语成为欧洲各国的通用语言。拉丁语在中世纪广泛运用在欧洲的宗教、教育等活动中,其对欧洲文化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瑞士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 特(Jacob Burckhardt)在《历史的反思》中将其概括为 “国家权力、教会权力和文化权力”(38)唐晓琳.语言的权力——拉丁语对欧洲统一的影响与作用[J].社会科学家,2011(11),第148-150页。。以文化权力为例,在《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Europäische Literatur und Lateinisches Mittelalter)一书中,德国语文学家库尔提乌斯(Ernst Robert Curtius, 1886—1956)就指出,德意志民族对拉丁语文化的接受,使得拉丁语成为该民族文化的锚点,该影响一直持续到十八世纪,才被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竞争所压制。(39)Ernst Robert Curtius, Colin Burrow. European Literature and the Latin Middle Age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p26.而欧洲近代各国的民族语言中,也有直接源自于拉丁语的。例如,西班牙语的元音发音、词性变化、时态、句法等内容,都与拉丁语有着紧密的事实联系,被认为是拉丁语的变种。(40)卢春迎.西班牙语诞生于拉丁语与西班牙帝国的崛起[J].外国语文.2020(03),第14-19页。拉丁语同欧洲地方方言也有着互动。比如从高卢地区挖掘出来的陶器上的文字是拉丁字母,但其实是高卢语言,使用了拉丁语的框架来排列,并且用了拉丁文的数字。这说明两种文字之间的混淆(41)James Clackson. The Blackwell History of the Latin Language[M].Hoboken: Wiley-Blackwell, 2010, p232.或许受到出口贸易等因素影响,其文字书写形式就可能有差异。此外,拉丁语和欧洲各地方言的使用语境也有区别,继而造成了事实上的双语现象。例如,在男性占主导的教育、军队、法律、行政和公共生活等领域,使用拉丁语就多一些;相对而言,女性书写中就贴近日常口语,用当地方言较多。这些差异分布,与东亚汉字文化圈中的双语现象,也是同中有异,值得在更大的历史文化范畴中进行比较分析。
作为欧洲通用语的拉丁语与欧洲各地方言的互动,以及后殖民文学中的非母语写作,这两种现象都诞生于西方文化的话语体系中。那么对以日本(包括朝鲜、琉球、越南)汉诗为代表的东亚汉文学双语性特征的研究,则是立足于探讨东亚汉文化的传播与接受路径,融汇本土语言及文学因素,并形成一种以双语性特质为重要基面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其特殊的理论价值及东亚实践意义无疑是值得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