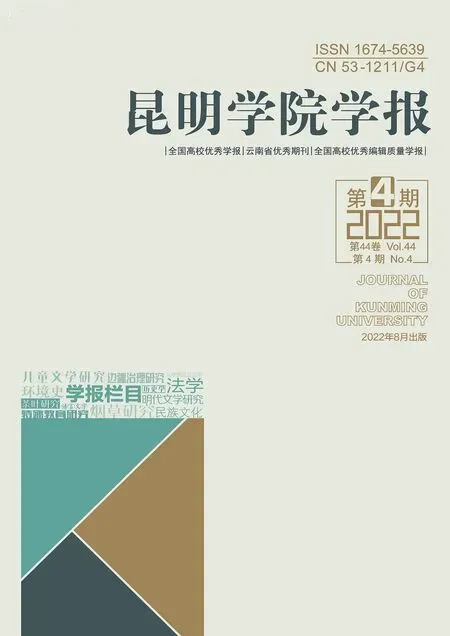扬弃私有财产与批判抽象思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感性解放”
于子然
(云南大学 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1844年4—8月,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完成了关于古典经济学、共产主义和黑格尔(G. W. F. Hegel)著作的笔记[1]98,这些文献于1932年全部出版,并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标题为人熟知[2]21。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出版以前,学术界对马克思在1844年春夏所进行的研究不甚了了,即便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梅林(Franz Erdmann Mehring),他也仅通过卢格(Arnold Ruge)写给费尔巴哈(Ludwig Andreas Feuerbach)的信得悉马克思在1844年春夏的大致情况。[3]97-98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发表后,学术界对此极为关注,并形成了对此手稿的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以朗兹胡特(S.Landshut)、迈耶尔(J.Mayer)、德曼(Henry de Man)、弗洛姆(Erich Fromm)为代表,他们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思想的顶峰,并提出了“两个马克思”的理论,主张“回到青年马克思去”;第二种观点以科尔纽(Auguste Cornu)、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巴日特诺夫(L.N.Pajitnov)为代表,他们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一部过渡性的著作,其中带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理论痕迹,但彰显了一定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倾向;第三种观点以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为代表,他们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一部不成熟的著作,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之间存在认识论的断裂。[2]31-41
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麦克莱伦指出,类似《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般格言式的叙述会造成制造体系的外表[1]99。换言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书写方式有利于开展思辨的批判,但不利于理论的阐述,更不利于读者的理解。或许,这也正是学术界对此手稿提出大相径庭的理解和阐释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此而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内容并不是完备的思想体系,而是尽显锋芒、引人深思的洞见,其中的真知灼见有赖基于不同的问题阈开展进一步的阐释。
杨适先生曾指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形成自己世界观时期的一部关键性作品,是马克思哲学的秘密和诞生地。”[4]学者朱立元也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5]。可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虽然马克思并没有关于美学的专门著作和系统理论,但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仍将马克思喻为现代化时期最伟大的三位美学家之一[6],这并非空穴来风,而是马克思的思想中本就包含了指向其后某些革命性美学讨论的向度。从西方19世纪末反形而上学的理论思潮以来,美学出现了以“感性”之名向“身体”回归的“感性解放”思潮,如: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福柯(Michel Foucault)、德勒兹(Gilles Louis Rene Deleuze)、桑塔格(Susan Sontag)、伊格尔顿、舒斯特曼(Richard Shusterman)等均对“感性解放”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而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感性解放”的讨论则在其中具有承前启后的特殊作用,并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7]
一、从私有财产到异化劳动:“感性解放”的具体语境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TheEconomicandPhilosophicManuscriptsof1844)的第三篇笔记中写道:“对私有财产(privateigentums)的扬弃(aufhebung)是人之感性(sinne)、本性的彻底解放(emanzipation)。”[8]269
马克思在手稿中谈到的感性解放问题是从其对私有财产的批判而引申出来的。马克思将私有财产与人的感性联系起来考察后指出:私有财产是人成为陌生的(fremder)、非人的客体后的感性表现[8]268;私有财产将人的感性异化(entfremdung)为以享受作为目的之于事物的占有[8]269;基于私有财产对感性的异化,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也对应异化为占有[8]268;而人的生活方式也对应异化为劳动和资本化[8]268。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思想不但受到黑格尔异化理论的影响,而且还借鉴了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理论,更重要的是,马克思的“异化”思想不再局限于德国古典哲学中“异化”概念的传统[2]118。对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思想,弗洛姆曾做出较为精当的总结:异化(alienation)或者疏远化(estrangement)是人在把握世界时并没有将自身感受为行动的原动力,那么世界(其中包括自然、他者和人自身)对人保持陌生;虽然作为客体的世界(其中包括自然、他者和人自身)可能是人的创造物,但世界仍旧高于并反对人自身;当主体从客体中分离时,异化就是被动地、接受地感受世界和自身。[9]37
考察马克思对私有财产批判而引申出的感性解放问题,需重返手稿对私有财产的具体讨论。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私有财产始于封建社会时期的土地占有,土地占有是私有财产的基础。”[8]230但封建社会时期,作为土地占有者的领主与土地之间还存在占有之外的关系,即“土地显现为其领主的无机身体”[8]230,亦或是领主对土地还存在感情。但土地成为商品后,土地所有者与土地、土地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感情的、人性的部分被抹除,而成为纯粹的占有。从“nulle terre sans seigneur”(没有土地无领主)向“l′argent′a pas de matre”(金钱没有主人)的转变[8]231,表明在封建社会中,“人是土地的主人;而资本主义社会中,金钱没有主人”。在这两句谚语中,人与土地、人与物之间主仆关系的消失,其根本是人与土地、人与物之间情感的抽离;金钱进而替代了情感,成为人与土地、人与物之间的中介。
私有财产不仅抽离情感,甚至扭曲了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劳动行为之间的关系。在私有制的统治下,个人从社会中获得的利益与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成反比。[8]211这种私有制原则在资本主义社会具有更显著的表现:劳动者生产的产品越多,那么劳动者自身就变成更廉价的商品。[8]235自然界为劳动者提供劳动生产的原料,同时也为劳动者提供生存供给。[8]237当劳动者以劳动的方式与自然界发生联系时,劳动者却无法掌握自然界为劳动生产提供的原料,甚至其付出更多的劳动却只能获得更少的食物。
在此需明确,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国民经济学理论中的“劳动”并非真实劳动,而是固化在客体中的劳动,是劳动的物化(vergegenständlichen),此时劳动被衡量为“物”,即劳动产品。劳动者不再对劳动产品进行占有和享受,甚至劳动行为本身也成为异于劳动者存在的客体。劳动行为的客体化以劳动产品衡量劳动行为,甚至劳动行为也不能被劳动者自由地掌握,劳动行为反而控制着劳动者。这类似马克思所举出的例子:从“领主占有土地”到“金钱没有主人”的变化,对物、对身体具有支配权的劳动者逐渐丧失了这种支配权。异化就是劳动者与劳动行为、劳动产品之间关系的疏离。劳动行为、劳动产品不再受劳动者支配,相反,劳动产品、劳动行为却掌控、支配着劳动者。
马克思在手稿中就劳动问题而反复提及的“客体化”(gegenstandes)、“物化”(vergegenständlichung)实际上就是工人在劳动过程中,汗水、精力、智慧、情感凝结在“物”——劳动产品中。即,使无形的、运动的劳动行为以客体化呈现的过程。所以,马克思所说的劳动的物化(vergegenständlichen)也可以理解为劳动使(ver)其客体化,即劳动者的劳动转化为劳动产品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劳动者丧失了对劳动产品、劳动行为的支配权[8]236,劳动者只有通过不断地劳动才能维持自己的身体所需,而劳动者维持自己的身体是为了更好地劳动。所以,劳动者陷入不断劳动的重复中,劳动者运用“劳动”这一人的功能时,却成了不自由的动物。[8]239
马克思认为,私有财产从其主体存在(subjektive Wesen)、主体活动的层面而言就是劳动。[8]256同时,私有财产、私有制就是人的一种自我异化(selbstentfremdung)。[8]263所以,私有制(privateigenthum)是迷惑的、被剥离的异化劳动的结果[8]241,异化劳动导致了私有制、私有财产的出现。表面上看,私有制、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原因,实际上私有制、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结果。当劳动者不占有劳动产品、劳动行为和自我意识后,对应产生了私有制,而并非私有制确定后才出现异化劳动。毕竟,劳动者只有在劳动之后才产生了劳动产品,而劳动者自身之外的他者占有了劳动产品,这时才出现了私有制。劳动者生产出的劳动产品反过来束缚劳动者,完整的真实劳动仅仅以劳动产品的形式衡量劳动,劳动者之外的他者对劳动产品进行私有制的侵占,这将劳动者与劳动行为、劳动产品之间原本亲密的关系进行异化(entfremdung),即异化劳动。
马克思所谈到的异化劳动具有四个层面的内容:第一,劳动者无法支配劳动产品是物的异化(die entfremdung der sache);第二,劳动者无法支配劳动行为是自我异化(die selbstentfremdung)[8]239;第三,劳动者失去对自我的独立认识,导致类存在(gattungswesen)的异化;第四,人与劳动产品、劳动行为、自我认识的疏离,最终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其中,马克思所提出的类存在的异化不易把握,需进一步探讨。
当对“gattungswesen”(类存在)的通行英语翻译为“species being”时,马克思在此借“gattungswesen”所赋予的人与动物之间的对立被忽视。动物是臣服于、被支配于“gattung”(类)之下的奴隶,而人则是具有某“gattung”(类)自然属性而不断丰富自身的存在物。[10]8“gattungswesen”所蕴含的人与动物之间的对立实际就是,人是一种自由的存在,而动物不是。作为“类存在”(gattungswesen)的人将自身的“类”与其他存在物的“类”作为认识的客体,作为“类”的存在原则将被人所认识,那么人可依凭对“类”原则之认识以把握其可能性,并进而开发、改变、塑造、对待任何一种存在物,所以人具有自我创造、自我实现的可能,因此人是自由的存在。[11]107
当“gattungswesen”被翻译为“类本质”时,不仅人与动物之间的对立被忽视,甚至于存在相关的意义也被一同忽视了,因为在德语中,“wesen”这个词具有三种含义:“存在”“个体存在”“本质”。当《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wesen”被理解为“本质”时,马克思对于“人之存在”这一古老哲学命题的见解被一定程度的忽视。[10]1所以应将马克思在此所说的“gattungswesen”理解为“类存在”。
马克思认为,作为个体的人在实践中、认识中将个体自身作为类存在(gattungswesen)。[8]239换言之,人的认识、行动往往根据其对作为类、作为属的“人”之认识而展开。马克思还认为,人会将自我视为一个客体,这是自我意识与生存的抽离,但正是由于这种抽离,人依靠自我意识支配行为,所以人的行为是自由行为。[8]239但劳动者的异化劳动却扭曲了、劫掠了自我意识,将自我扭曲为不占有劳动产品、劳动行为的劳动工具,从而陷入无休止的重复劳动。
人对于类、属的认识就是一种普遍意识,而马克思认为,普遍意识(allgemeines bewußtsem)是真实的共同体、社会存在这一鲜活形式的理论形式,并且这种抽象的意识与真实存在之间还是敌对的[8]267,即这种类、属的普遍意识与真实存在之间形成了敌对。
马克思指出,人的类意识(gattungsbewußtsein)使其不断确证其真正的社会生活,并仅在其思想中重复地活跃存在。[8]267苏联和民主德国于1982年合作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中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写作时间、写作顺序编排的原始顺序版[8]267与根据逻辑结构、思想内容编排的逻辑顺序版[8]391在此处存在较大差异。原始顺序版在此仅指出了“类意识”在人的思维、思想领域的意义,尚未直接说明类意识对人之实践层面的意义;但逻辑顺序版及相关的英译版[12]、中译版[13]均在此句话之后具体说明了类意识对类存在的引导。这表明马克思或许并未在手稿中直接说明类意识与类存在的关系,或者现存手稿中此处的内容已经亡佚。但逻辑顺序版在此对“类意识”和“类存在”的说明并非空穴来风,因为无论原始顺序版还是逻辑顺序版,其在说明“类意识”后,二者均有“反之亦然”(wie umgekehrt)的表述。可见,“类意识”并非与存在完全割裂,而是反过来作用于人的存在。在此也表明,异化对人之类本质的疏离即是对人的自我意识中作为人类该如何存在的思维方式的改变,进而以这种思维改变的结果束缚了人的具体存在方式。
所以马克思认为,人在加工、创造客体化世界的过程中,凭借对类、属的人之认识从而在其创建的世界中确证自我、认识自我。[8]241但异化劳动抢走了劳动者的劳动产品,劫掠了劳动所创造的劳动世界,剥夺了其创建世界的客体形式、物质形式,即,夺取了劳动者确证自我、认识自我的物质载体,劳动者也因此失去了对自我的认识。私有财产对劳动产品的占有导致了物的异化,物的异化促成了劳动者对劳动行为的失控,即自我异化。基于物的异化和自我异化,劳动者失去了对自我的认识,同时也失去了对他人的认识,最终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异化。
二、对私有财产的扬弃:“感性解放”的具体方案
马克思明确指出,异化劳动实际上就是一种占有、侵占(aneignung);占有、侵占就是异化劳动。[8]246如将妇女以及自然物作为满足肉欲的客体是人之自我存在(existirt)的无限退化,这也表现在类关系(gattungsverhältniß)的形成上,即表现在某种概念、观念的形成上。[8]262换言之,将自然界作为满足欲望的思维方式、感知方式与人对自然界的概念认识、观念认识紧密关联。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又表现为感性的、感官的(sinnlich)[8]262。而这种感官的、感性的感受方式又反映出人如何理解作为类存在(sattungswesen)的人[8]262,即作为类存在的自身。同时,人对人之类存在的理解、认识又反过来影响、建构了人那感性的、感官的感受方式和体验方式。
人通过感官感受到的自然,是人之精神层面的非自然世界。[8]239作为类、属的人,首先是将整个自然世界作为直接的生存供给,其次才将整个自然世界作为客体(gegenstand)或者物质。[8]239这意味着人之感官与自然世界发生关联时,具有实践在先、认识在后的特质;人总是先在世界中生存,其次再展开认识活动。所以类本质的异化是存在于人之生存后的一种认识,人之生存先于人之认识。但根据马克思所观察到的劳动者生存现状,这种类本质的异化却反而约束了劳动者的生存。这也就是马克思提出的作为类、属的人之抽象生存方式与作为个体的人之生存的异化和疏离。
劳动者生产出的劳动产品对劳动者的控制进而导致了感官对自然界的异化,感官所感受到的自然不再隶属于人,而是成为异于人而存在的部分;而劳动行为对劳动者的控制则导致了劳动者自我行为的异化。劳动者不再占有劳动产品、劳动行为和自我意识;劳动者的异化劳动创生了不用劳动的资本家;资本家占有了劳动者的劳动产品、劳动行为及其客体化的世界、自我意识。[8]241所以,资本家占据劳动产品、劳动行为以及劳动者的自我意识的私有制是异化劳动的必然产物。[8]241
私有财产的运动就是对所有先前生产运动和人之现实存在地感性揭示。[8]264私有财产可以通过感官直接感受到,同时私有财产又是人异化后生命的感性表达。[8]264那么,私有财产是一种感观表征,具体表现为:人对其自身而言成为陌生(fremder)且非人的客体(gegenständlich),其生命表征为其生命的疏离和异化,现实的人成为不现实的人,现实因此变得陌生。[8]268私有制将人之于客体的感官感受方式异化为占有和拥有,所以人的肉体和精神之感觉(sinne)被异化(entfremdung)为占有的感觉。[8]269那么,私有制之于感官的异化在于将感官片面化、狭隘化,将原本具有多种可能的感官体验狭隘为占有。
所以,对私有制的扬弃就是对异化劳动的扬弃,对异化劳动的扬弃就是将劳动产品、劳动行为以及自我意识归还给劳动者自由地拥有。伴随劳动者自我意识的复归,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问题也得以解决。马克思所说的“感性解放”就是将劳动产品、劳动行为和自我意识复归于劳动者、复归于人,那么人的感官才会从被他人占有的不自由状态中解放出来。
人通过感官所感受到的客体是人之感官的客体化,这些客体属于人自身,那么人就在客体世界中确证自己的存在。[8]270人通过感官对世界进行客体化的感受时,客体实际上仅仅是人那存在力量之存在(wesenskräfte sein)的确证。[8]270当人以人的感受方式感受客体时,那么人就不会在客体中失去自身。[8]269这种人的感受方式就是以完整的感官感受方式去感受物、他人、世界。
针对私有制之于感官、之于人的异化,马克思提出,要对私有制进行积极(positive)扬弃,而私有制的积极扬弃需要改变感官占有的方式,即不再将人的存在、物、他人作为以享受为目的地占有;而是以完整的、全面的状态成为人。[8]268那么,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positive aufhebung)就是以人之方式对人之存在(wesens)、客体化的他人、人之劳动产品的感官占有,而并非以片面获取愉悦为目的之感官方式占有、拥有其自身存在、他人以及劳动产品。[8]268马克思反对以占有、拥有的方式看待人与物、人与自身、人与他人的关系,而要求以人之方式对待物、自身、他人。但马克思在此所说的人之方式又是什么呢,这种人之方式,即人全面存在(allseitiges wesen)于全部本性中,亦即作为一个完整的人。[8]268
针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完整的人、全面的人,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进行过精彩的总结。他认为人的完整性、全面性在于人与客体对立并克服这种对立而成为有生命的主体,人克服了碎片化的行为和规定,成了行为的主体,又是行为的最后客体。[11]197打破了主客体之间的对立,实际上就是打破占有思维所划定的主客体之间的鸿沟,伴随主客体之间鸿沟的消弭,人将作为完整且全面的人。消弭主客体之间的对立具体到行动层面,马克思仍然提倡对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
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就是人占有自己的生命,即对异化的积极扬弃[8]264。对私有财产、对异化的积极扬弃就是人向人的存在(sein menschliches),即社会存在(gesellschaftliches dasein)的复归[8]264。马克思在此对人之社会存在的强调,实际上是强调我为别人而存在,别人为我而存在。这种存在方式才是马克思认为合乎人性的存在(sein menschliches dasein)[8]264。也只有处于这种社会存在的存在方式之下,人与自然实现了存在层面上的合一(wesenseinheit)[8]264。
基于异化劳动形成私有财产的结论,马克思认为废除私有财产即可消灭异化劳动。异化劳动本身就是劳动者对其劳动产品、劳动行为和自我意识的自主占有,那么对异化劳动的废除就是将劳动产品、劳动行为和自我意识复归于劳动者,从而实现感性解放。而解放(emancipation)正是把人的世界、人的关系复归于人[8]162。所以,扬弃私有财产就是扬弃异化劳动,扬弃异化劳动就是实现感性解放,实现感性解放就是将人的感官感受方式复归于人。卢卡奇(György Lukács)认为,马克思区分了劳动的客体化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所导致的自我异化。[2]281作为现实存在的人,客体化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马克思所要扬弃的并不是作为人之基本存在方式的客体化,而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所导致的自我异化。这也就是马克思提出“感性解放”的具体方案——对私有财产的扬弃、对异化劳动的扬弃,将人的劳动产品、劳动行为、自我意识以及同他人的关系复归于人。
三、对抽象思维的批判:“感性解放”的深层意义
马克思指出了私有财产的运动就是生产和消费[8]264,其运动的三个阶段为:第一阶段,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统一;第二阶段,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对立;第三阶段,劳动与劳动自身的对立,资本与资本自身的对立。[8]255-256在第一个阶段中,劳动产品归劳动者所有,劳动者付出的劳动越多,他就占有越多的劳动产品;在第二阶段中,劳动产品不归属于劳动者所有,劳动者劳动得越多,其占有的劳动产品不一定越多;在第三个阶段中,劳动产品归属于资本家所有,劳动者劳动得越多,其劳动行为就更加贬值,其占有的劳动产品就越少。这是马克思所总结的私有财产运动所经历的三个必然阶段,其最终结果是,敌对的相互反对[8]256。这种敌对不仅是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敌对,还是工人与工人之间的敌对、资本家与资本家之间的敌对。
如何解除私有制、私有财产运动的必然结果(即敌对的相互反对)呢?答案是需要扬弃(aufhebung)私有财产。扬弃一方面具有废除、消灭的含义,另外一方面还包含了超越的意义。如马丁·米利根(Martin Milligan)便将“扬弃”翻译为“超越”(transcend)。但鉴于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对费尔巴哈(Ludwig Andreas Feuerbach)辩证法的继承以及马克思哲学自身的发展,“aufhebung”并不是简单的废除,而是辩证法意义上的“扬弃”。
马克思认为,黑格尔辩证法从抽象的异化(entfremdung)出发,进而取消抽象以肯定实际,最后又取消实际以再次肯定抽象(abstraktion)。[8]277这也就是黑格尔辩证法中否定之否定(die negation der negation)的过程,但黑格尔的辩证法并不是对真正存在的确证,而是对假象存在进行否定以对假象存在进行确证。[8]411那么,黑格尔的辩证法就是肯定哲学对立面(如神学超验性)而与哲学自身相矛盾的哲学。[8]277
相较于黑格尔,费尔巴哈则区分了作为绝对肯定(das absolut positive)的否定之否定(die negation der negation)与基于自身且肯定自身的合理肯定(begründete Positive)。[8]276绝对肯定(das absolut positive)与合理肯定(begründete Positive)之间的区别在于:第一,肯定的范围、程度不同。绝对肯定是对事物进行全面、彻底地肯定;而合理肯定则是对事物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上地肯定。第二,合理肯定基于事物自身,绝对肯定基于事物的对立面。在此,马克思赞同合理肯定,批判绝对肯定,即马克思赞同基于事物自身进行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地肯定。
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哲学成为包含其曾经的对立面(即神学)的一种新哲学,但这种哲学并不是通过对自身肯定而获得肯定,而是通过肯定其对立面而获得一种扩充进而肯定自身。那么这种否定之否定后而获得的肯定就与基于自身的肯定是对立的,即:绝对肯定(das absolut positive)与合理肯定(begründete Positive)的对立。
包含在否定之否定中的自我肯定(selbstbejahung)与自我确证(selbstbestätigung)并不是对自我的肯定,而是受其对立面影响后怀疑自身,试图重新证明自身。那么否定之否定的自我肯定与自我确证就不是对此在(dasein)、当下存在的肯定和认可,而是直接或间接地对立于那基于自我立场的感性确证。[8]277这仍然与绝对肯定与合理肯定对立。所以,马克思一再强调否定之否定后的肯定已不再是对自我的肯定,而是类似于对自我对立面吸纳后新的建构,所以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具有抽象性,且还具有否定自身的特质。
马克思在对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进行批判时,主要表达了对黑格尔否定之否定中部分肯定的不满,黑格尔借以否定之否定的扬弃并未肯定真正的人之存在,而是肯定了宗教、神学等假象存在;而马克思所力求肯定的乃是人之存在,人之感性地、全面地存在。所以,马克思赞同费尔巴哈的观点:辩证法要从肯定的(positiven)、明确的感性出发。[8]277
另外,马克思所提出的感性解放命题不仅基于对私有财产的扬弃、对异化劳动的扬弃,还基于马克思对黑格尔抽象性主体思维的批判。黑格尔认为,如果将人等同于自我,那么自我是抽象理解的人,自我是抽象所产生的人[8]406。在黑格尔看来,人的存在(wesen)等同于自我意识(selbstbewußtsein)[8]406;存在(wesen)不过是人之真正存在、自我意识(selbstbewußtseins)异化后(entfremdung)的外观[8]406。
黑格尔所设定的主体,如自我意识(selbstbewußtsein)、哲学精神等,在马克思看来就是对自我的客体化(selbstvergegenständüchung)和对自我的异化(selbstentfremdung),黑格尔试图利用抽象的自我来把握世界。[8]277但黑格尔所设定的抽象自我与真实世界是不相干的,这进而导致了黑格尔对存在的取消。[8]277黑格尔所设定的主体与真实存在之间的断裂造成对自然的、鲜活的人之存在的抽象,即抽象思维(das abstrakte denken)。[8]277黑格尔并没有将真正的人、自然的人作为主体,所以黑格尔的主体是自我意识,即,抽象的人[8]407。
但是,马克思认为,人的存在是异于、对立于抽象思维的[8]403,并且抽象思维与感性现实(sinnlichen wirklichkeit)或现实感性(wirklichen sinnlichkeit)之间是矛盾的[8]403。现实的感性意识(sinnliche bewußtsein)并不是抽象的感性意识,而是人的感性意识[8]404。人感性地客体性存在,即人能够对真正的感性客体进行生命表征[8]408。
人之真正地存在就是感性存在,就是在自身之外拥有感性的客体并感性地拥有客体。[8]409然而,对异化后客体非感性的占有仅作为一种在意识、思维中的占有。[8]403对异化后客体的占有带来了异化统治之下对客体性(gegenständlichkeit)的扬弃(aufhebung),但对异化后客体的占有必然带来从互不妨害的异化向真正敌对的异化的转变。在黑格尔看来,提出客体性(gegenständlichkeit)的主要意义并非在于给定客体特性,而是以客体的特性对自我意识(selbstbewußtsein)进行攻击和异化(entfremdung)。[8]410
占有那作为意识对象的客体带来了非对象性的客体存在状态,此处的占有不再是一种抽象思维上的占据,而是人与物、肉体与物之间在手的、实践的状态。意识对象并未以思维的方式觉知,而是以在手的实践状态而成为非对象性的整一。
倘若没有占有意识对象,那么对客体的意识与对自我的意识之间是互不妨害的,但是倘若占有了意识对象,那么对客体的意识与对自我的意识之间就是真正敌对的。因为对意识对象的占有会导致意识对象直接成为自我意识的组成部分,那么对客体的意识与原本的自我意识会组成新的自我意识,其中客体意识与原本自我意识的矛盾会在新的自我意识之中形成直接地对抗。倘若不占有意识对象,那么对客体的意识与自我意识之间并不会发生直接地对抗。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提出客体性是为了通过客体的某些特质以改变、异化自我意识。
所以,黑格尔的思路可以总结为:存在与思维之间的对立成了存在的缺陷,所以存在必须向思维所设定的抽象靠拢,进而以对存在的扬弃实现向抽象思维的趋近。那么,黑格尔哲学就是否定此在(dasein)的哲学,就是以否定此在的方式向虚妄的抽象思维靠近的哲学。黑格尔赋予了这种抽象思维以另一个名称——精神(geist),精神在此要实现存在向抽象思维的同一,其所谓的同一就是否定之否定,就是绝对否定(absolute negativität),就是否定存在自身的否定。[8]418
基于对黑格尔绝对肯定的辩证法和抽象性主体思维的批判,马克思的“感性解放”命题显现出扬弃私有财产之外的维度,即否定以抽象思维制导人之存在,强调先于抽象思维而存在的感性的人,进而以肯定、确证人之此在。
亚当·沙夫(Adam Schaff)严肃地区分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异化”(即“物的异化”)与“自我异化”的不同,并强调“异化”问题才是马克思关注的重点。或许,从马克思整体思想的把握而言,沙夫的观点是合理的,但沙夫的区分也恰恰体现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内容上的两个维度,即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和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这两部分的内容之间几乎出现了认识论的割裂。
而这种内容上的割裂直接体现在不同版本的内容编排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中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写作时间、写作顺序编排的原始顺序版[8]278与根据逻辑结构、思想内容编排的逻辑顺序版[8]403在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批判处的编排具有较大差异。原始顺序版的编排为:在马克思整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主要观点后,并未接续马克思对黑格尔双重错误的说明,而是接续笔记本(三)中第14页至第17页的内容,即马克思在私有财产和需求方面的思考;在笔记本(三)中的第十七页内容结束后,原始顺序版又继续编排了笔记本(三)中第13页的内容,即马克思对黑格尔双重错误的说明;之后,原始顺序版编排了笔记本(三)中第18页的内容,即马克思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继续批判;在笔记本(三)中第18页之后,原始顺序版编排了笔记本(三)中第22、24、28~34页的内容,即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相较于原始顺序版的编排,逻辑顺序版则将马克思对黑格尔批判完整地放到一起。
原始顺序版与逻辑顺序版编排的不同,涉及研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文献问题的重要讨论,即马克思在手稿中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能否作为单独的一篇笔记。实际上,无论是否将其单独筛选出作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笔记本(四)”,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与手稿中其他内容相比,其所具有的独立性和批判内容本身的逻辑性都显示了这一部分内容的特殊。从马克思在手稿序言部分表明这一部分应作为单独章节[8]326,到马克思、恩格斯遗稿专家梁赞诺夫率先发表的手稿局部本,再到MEGA1中标题、编排顺序的特点,最后到学者奥古斯特·科尔纽、T.B.波特莫尔对“笔记本(四)”的认定[14],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在手稿内容中的独立性是呼之欲出的。
但在这种独立性之外,也应该注意《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政治经济学部分与哲学部分的联系,例如卢卡奇特别强调其中经济学部分与哲学部分的关联。卢卡奇的观点可以简要地概括为:无论是国民经济学理论,还是黑格尔哲学的思辨,他们均将非存在的人之抽象概念作为人的存在。[2]275-276对此,阿尔都塞讨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观点亦可做进一步佐证:“经济学中的‘抽象’(abstraction)批准了(autorise)哲学中的‘抽象’,而哲学中的‘抽象’则受雇于(employer)经济学中的‘抽象’并作为其基础(fonder)。”[15]无论国民经济学还是黑格尔哲学,其根本问题均在于,抽象思维对真实存在的统摄和戕害。而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中抽象思维批判的根本原因,可以借用弗洛姆对马克思的关于人之意识问题的总结:不是人之意识决定人之存在(being),而是人之社会存在(social being)决定人之意识[9]18。
四、结语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感性解放”的命题具有两个维度的意义,分别是扬弃私有财产和批判抽象思维。扬弃私有财产是马克思提出“感性解放”的具体语境,也是马克思“感性解放”思想中带有实践性、方法论色彩的理论主张,其对应的笔记内容是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批判抽象思维则是马克思“感性解放”思想的隐匿维度,马克思正是要打破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哲学中所划定的抽象主体,并以人之感性存在取消抽象主体对人之此在的忽略和轻视,从而给予人之存在这一古老哲学命题以新的答案。当然,扬弃私有财产与批判抽象思维两个维度的“感性解放”并不是割裂的、断裂的,而是恰恰处于隐匿之中那关于抽象思维的批判构成了马克思“感性解放”的前提和基础,毕竟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反思时,也对其理论中所设定的抽象主体进行了反思。不过,马克思思想中鲜明的实践倾向使其不会在纯粹的思辨中耽搁太久,毕竟对于感性存在的过多思辨难免会陷入重新建构抽象主体的窠臼,马克思强调的是解决问题,而不是纯粹的思辨。所以,马克思认为:人之感官的解放只有通过实践的方式[8]271;社会主义不需要再抽象地假定人之此在(das dasein des menschen)这一概念性的中介,社会主义是以实践的感性意识(sinnlichen bewußtsein)着手于人和自然之存在(wesen)。[8]2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