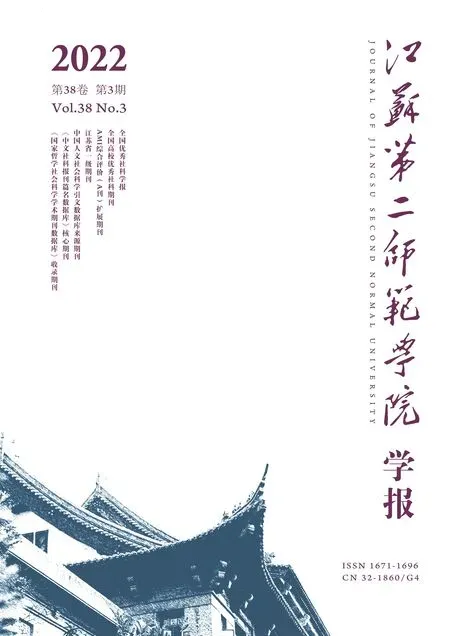刘勰三教观研究*
谢 渊
(1.南京大学哲学系, 江苏南京 210023;2.江苏第二师范学院美术学院, 江苏南京 210013)
刘勰是南北朝时期具有儒佛道兼容思想特质的典型代表,其在三教关系上的观点是南北朝时期三教关系的重要分支,亦是该阶段关于三教关系的代表性观点。佛教进入中土后,就致力于对以儒道两家为代表的本土文化的渗透,并积极寻找中国化的契机。历经两汉的主动依附谋求发展与魏晋时期的冲突、融合,发展至南北朝时期三教鼎立的局面正式形成,为后期三教的深层次融合提供了基础,以刘勰为代表的文人阶层,对于三教观的思考推动了三教关系及相关理论朝向更完善、科学的方向发展。
刘勰三教观的形成与其生平及家世密切相关。其父刘尚早亡,20岁前相依为命的母亲亦离开人世,遂南下定林寺,随僧祐学习佛儒经典十余载。后得学士沈约举荐步入仕途,曾官至六品太子府机要秘书、东宫一通事舍人。但随着沈约与僧祐的相继离世,仕途之梦破灭。其后奉敕回定林寺整理僧祐经藏,垂暮之年皈依佛门燔发出家,一年后黯然离世。门第观念盛行的南朝,刘勰仕途不畅或与其家族的衰败有直接联系。名门贵族把持着整个社会的发展与仕途的晋升,十分注重品阶门第,寒门出身的学子面对的是难以逾越的身份鸿沟,即便才能卓越,勋劳卓著,若没有家世背景,断然不可能与权贵精英交游并列。另一方面来看,家世亦决定了家学的传承,这对于个人思想的形成有着重大影响。刘勰虽出身东莞刘氏,但传承至刘勰时衰败萧条,几乎于庶族无异。关于其是“士”或“庶”历来争论不休,笔者认为,刘勰一支虽没落至与寒门无异,但其士族家学并未丢失,其父曾任越骑校尉,其堂叔刘岱于句容出土的墓志上记载亦可佐证,刘氏这一支至少到齐梁之际,尚能保持家风不坠。因此,单凭朝野高官斥其为寒士为依据,将其归为庶人似有不妥。
南朝儒释道鼎立的背景,少年时期佛学浸润的经历,加之士族家学的传承,对刘勰三教观的形成起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亦决定了其儒佛道思想兼容并包的特征趋势。
一、立足儒家、融涉佛学
永明二年(484年),刘勰因家庭变故南下定林寺,追随名僧僧祐儒佛并学。这一阶段是刘勰三教观的形成初期,家学的熏陶让其立足于儒学视角,身处佛门则让其开始融涉佛学思想。因此展现出以儒涉佛的思想特征。
“齐高帝少为诸生,即位后,王俭为辅,又长于经礼,是以儒学大振。”[1]382在其后的三年之中,齐将儒学立为国学,并下诏“修建教学,精选儒官”。故在永明元年后形成了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永明文学时期”,此时的社会各基层几乎进入了家家寻孔教、人人诵儒书的局面。此时正值刘勰迈入青年阶段,人生观思想观树立之际,故自幼聪慧、笃志好学的刘勰,在二十岁前学习内容以儒家思想为主是无疑的。另一方面,家风使然,也决定刘勰初期的思想必然不离儒家,这些都让儒学之风在刘勰思想成长过程中留下了深刻烙印。从主观方面来看,以没落士族自居的刘勰亦不可能主动涉及佛教经论的学习,更没有机缘接受佛学的改造。这种情况至刘勰进入定林寺后发生了改变,父母离世的变故,促使刘勰南下谋求生活,委身于受皇家认可的定林寺谋求日后发展。此时江左释风日盛,佛教得到帝王的重视是客观事实,佛学与佛教对于早孤而失去依靠、入仕无门的刘勰存在巨大吸引力。
“(永明)五年,正位司徒,给班剑二十人,侍中如故。移居鸡笼山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讲语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2]473文士萧子良首开鸡笼山是南朝学术思想领域的大事。他于建康西邸广泛召集文人学士,名士名僧,“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高祖与沈约、谢眺、王融、萧深、范云、任防、陆锤等并游焉,号日八友。”[2]473形成了“竟陵八友”。由此可见“道俗之盛,江左未有”,此言绝非虚言。在此处集道俗于一邸,如此盛况一定程度上对于佛学的盛行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彼时身为竟陵王的萧子良,看似与佛教与儒学,并不相关。但以萧子良的社会地位,以及基于此社会地位所接触到广泛的社会影响,都决定了佛风的盛行必定对自身及对他人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彼时的南朝无论统治阶级还是平民百姓,可以说从文至武、从士到庶,出入佛老者甚多。而皇家寺庙定林寺更是香火鼎盛高僧辈出,佛法受到上层统治者的尊崇,达官贵人、鸿儒俊彦经常是座上宾客,文人名士趋之若鹜,在此谈佛论道,宛若高级佛学沙龙。刘勰南下初入定林寺时,当时僧祐已经接下法献衣钵,成为定林方丈,僧众繁多,盛况空前,连贵为临川郡王的萧宏亦常出入其间。在这样的皇家寺庙中寄身佛门的经历,为刘勰从根本上认识佛学与从思想上接受佛学浸润,提供了天然的沃土。入寺的前六七年时间中,刘勰整理定林经藏,为佛经编排目录、撰写序跋,并负责处理日常与僧祐往来之书信,在这些看似琐碎与经书相伴的几载中,令他有机会充分学习佛学理解佛经。与进入定林寺前相比,刘勰的思想从根源发生了变化,佛学已经牢牢地占据了一席之地。
南北朝时期盛行的佛学实质已经是玄学化了的佛学。此时经学的地位有所下降, 玄学的地位逐步上升,思辨的玄风盛行于南朝各个阶层,佛学通过与玄学的相互吸收,进入了思想界,借由玄学来格义,利用玄风的盛行不断发展自身。如此以玄解佛促使了玄与佛趋于合流。此时的佛学实质上已经大量地吸收了老庄的道玄思想,其本身已具足道家部分思想作为成长的细胞。在此阶段的刘勰,虽然没有直观地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但大量融涉了玄学化佛学决定了刘勰在思想上大量吸收佛学思想的同时,道玄亦在佛学思想的包裹下,渗透于刘勰的思想大厦之中。
从初上定林寺整理佛典,到随僧祐编排目录,都是刘勰在自身纯粹的儒学血脉中不断融释佛学因子的过程。“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3]1859亦是刘勰从实践中体会佛学理解佛学的经历。无论自觉抑或非自觉,这对于刘勰三教观的构筑起着重要作用。立足于儒家视野,广泛接纳佛教的思想改造,为其三教观的发展与成熟提供了充足的养料,云集佛儒经藏的定林寺是刘勰的思想发展的天然温床,也为在《灭惑论》中从义理层面调和儒佛关系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立足于儒的视野接受佛学的沐浴,这时期的刘勰已向儒佛兼用的道路踏出了坚定一步。
二、弥合佛儒,批判道教
佛教在中土站稳脚跟后,与儒道形成鼎立的态势,这期间三教不可避免地展开了正面交锋。刘勰于建武四年(497年)撰写了《灭惑论》,从义理、源流、人伦等多重方面将佛与儒进行全方位的调和,把道家与道教相分的同时,将道教定义为神仙方术。定林寺长期接收到的佛学熏陶,使佛学的种子在刘勰的思想中开始生根发芽,在这一时期展现出强烈的弥合儒佛批判道教的思想倾向。《灭惑论》代表性地反映了刘勰这一阶段的三教观,展现出以儒护佛的思想特征。
儒佛并修使刘勰开始以儒学的视角理解佛理问题,在义理层面,刘勰提出佛教以二谛法让世人辩明三空扫象破执,弘法传道的过程本身就是教化众生救人脱离苦海的大德大善之举,因而“功立一时,而道被千载”。“至道宗极,理归乎一;妙法真境,本固无二。”[4]则指明佛和儒两家所说的“至道”,本质上是一样的,“菩提,汉语曰道”,佛教里至高的菩提智慧就是汉语中所说的“道”,所以“孔释教殊而道契”,儒、佛的根本思想是一致的。同时“异经同归,经异由权”又指出儒道和佛道是并行不悖的,只因语言各异而言论不一。
在人伦方面,他强调佛教的德行与儒家的基本原则相通,“孝理至极,道俗同贯”。出家在家仅有形式上的区别,都能阐发德行。甚至提出在家奉养双亲是一时之孝,学习佛法才能永久地让家人脱离苦海的大爱大孝。故儒佛之间是“玄化同归”,所追求的理想殊途同归。关于二者谁先谁后以及夷夏之辩的争论,刘勰指出《老子化胡经》为道教徒伪造,老子传道西方没有根据,且佛教本身并不是为了教化蛮夷而设立,极力证明佛教与儒家的根本一致性。
关于教化功能方面,刘勰提出“殊教合契,未始非佛”,认为受教化的不同是由众生不同的机缘所决定。有佛缘,就接受佛教的教化,如有俗缘,那就接受帝王的教化,甚至认为世俗的教化也是佛法的体现。因而,儒佛二家在思想层面是完全可以相融合的,实质可以称得上是殊途同归。之所以显示出不同,只是两家思想在不同地域不同文明背景下生长绽放出的文化表象。
《灭惑论》是刘勰回应将佛教全盘否定的《三破论》而撰写出的,其根本立场是为佛教辩护。《三破论》由道教提出,其对于佛教破国破家破身的指责不留余地,彼时刘勰仍寄居于寺中,依靠佛门的同时仕途上仍待机而动,如果真将佛教定义为亡国之教,岂不是前程尽毁。于定林寺十余载深谙佛理的刘勰用《灭惑论》为武器尤其是针对指责佛教的道士群体,组织起言之有据的反击,故刘勰对其的批判上不遗余力。南北朝时期,道家作为一个学派已经失去了其独立形态,往往与道教混合在一起。刘勰首先将道教从道家剥离,指责道教为神仙方术,道人也为愚狡方士。又从南朝佛教的真神论出发,指出道教修炼的永生追求“形器必终”,但佛教所修行的脱离苦海涅槃之境才是“神识无穷”,这就是所谓常住不灭的泥洹妙果。同时又肯定老子学说为导世良方,是“非出世之妙经”,但语下之意,仍隐有治世之道不如救人之佛的意味。
《灭惑论》中弥合儒佛关系拉拢道家排斥道教的倾向,是刘勰三教观发展阶段中对儒佛道三教关系的重新思考与定位。但刘勰对于儒佛道的三教关系的认识,略显暧昧。虽然在儒佛关系上刘勰极力弥合,但关于出世与入世的追求二者又是必然不可调和的,刘勰本人也在数年后用行动做出了选择,甚至对道家为未必是一味地批评。所以这一时期刘勰对于三教观的认识,弥合佛儒批判道教的同时,实际趋于三教思想的调和与吸收。这时期的激烈思考,为其后期趋于稳定兼收并蓄的三教观铺平了道路。
三、兼收并蓄,三教并用
中兴二年(502年)刘勰完成鸿篇巨制《文心雕龙》的撰写,兼收并蓄的三教观在50篇的论文中展露无遗,刘勰以三教并用的手法,高于儒释道的角度阐发思考问题,展现出三教和合的思想特征,也标志着刘勰三教观步入三教汇通的成熟阶段。
文心雕龙序志即言,刘勰夜梦手捧红漆礼器,随孔子向南走,遂决定撰写文。“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旦而籍,乃怡然而喜,大哉圣人之难见哉,乃小子之垂梦欤!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孔子者也。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一……脚详其本源,莫非经典。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丝悦,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异,宜体于要。于是据笔和墨,乃始论文。”[3]1862刘勰梦见的是孔子而非如来,也说明其梦中所追随的圣人,是儒家圣人,所求为孔孟之道,这也是刘勰从内而外的尊崇儒学的外化表现;同时以梦的形式展开又充满着老庄的道玄色彩;以心为题命名是遵循佛学著作命名的惯例,单从表相来看,文心雕龙三教熔于一炉的特征显然易见。
关于内里的融合,从《原道》篇来看,提出“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5]1强调人能立言也是顺乎天道的准则。“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采; 有心之器,其无文欤?……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 ”[5]1万事万物于人世间都具备文采,圣人所立之言自不必说,古今先贤所留的济世之文诚然是天地的主宰,在诵读学习圣人之文时,对于个人心灵与社会风气有着教化之大功效。另外在《文心雕龙.原道》篇中提及“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壁,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如此强调无为正是取自于老庄学说,是为老庄论道; 此后又提及“道心惟微,神理设教。光采元圣,炳耀仁孝。龙图献体,龟书呈貌。天文斯观,民胥以效。”[5]1此强调神理设教正是出自《周易》的卦辞,是为易传论道。同样,在此《原道》篇中多次提及神理一词,从刘勰协助僧裕所编撰的《出三藏记集》一书中来看,明确言辞表达所说的“神理”其“理契乎神”,这样几处很明显指佛之理,是为佛学之神理解。全书中这样由表及里的对于三教兼用的例证多不胜数,在这样50篇大论文的合著中,立足于三教并蓄的视域下著述,足以说明这一时期刘勰三教观已趋于成熟,真正达到兼收并蓄,三教并用。“勰撰《文心雕龙》五十篇,论古今文体,引而次之。……既成,未为时流所称。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约,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令者。约便命取读,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3]1867《文心雕龙》得到沈约的好评,为刘勰扣开了仕途之门。兼收并蓄,三教并用的三教观经过撰写《文心雕龙》的洗礼,已成熟稳定融汇一炉。充分吸取了三家学术之精华,从形而上之体到形而下以致用,为后期刘勰开创经藏目录,创建名实相符的目录学思想,形成兼顾内容形式的文体起了指引方向的作用。
四、“儒学为本”的三教观倾向
刘勰三教观三个向度的演变与其个人发展自洽且相适。不管是以儒涉佛、以儒护佛还是三教和合,不难看出尽管是一个动态变化逐步成熟的过程,但思想是常常随着时代的发展、个人的遭遇而有所变化。因此,厘清其三教观展开的根源尤为重要,直接关乎于分析刘勰看待三教问题角度,对其思考问题方式的探讨及对其利用三教观处理事物切入点的研判。
一直以来最大疑惑是,笃信佛教的刘勰为什么要坚守儒家立场呢?
首先,从动因来讲,刘勰始终以儒士自居。《文心雕龙》中的《宗经篇》中充分肯定了儒家的地位。虽然自我的评定可能出现偏差,而自身的行为也可能与自我的定位产生背离,但其初心落于儒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如前文提及的其原生家庭而言,刘勰家世虽没落,但家学传承仍在,其祖父、堂叔以及父亲都是士族出身。南北朝时期虽然儒学消沉导致佛道并兴,但儒学在世家的家学传承中仍是占据主导地位,即便是梁武帝时期佛教被推行为国教风光一时无两之际,儒学仍不可撼动地根植于士人血脉中。从个人发展而言,父母双亲的过早离世,让刘勰想要再度跻身士族已经相当困难,其父离世之前曾官居四品秩二千石,本身是无须纳课服役的,到建康定林寺依沙门僧祐更多的可能是考虑避免四处流落寄人篱下之苦,从而安心学业。同时僧祐为其进入仕途也提供了可能性。栖身于作为南朝的皇家寺院的定林寺,亦有为日后谋求政治资本之意。于此看来,他似乎并不是纯粹出于佛学的感召而拜服于高僧遁入释门。
其次从动机来谈,刘勰完成《灭惑论》的写作后构思《文心雕龙》,也是出于在同一时代的文士之中未有鸿篇巨制的著作诞生的考量,写旷世之作《文心雕龙》以期立言;反响未达到预期后,反思认为或是自身影响力不够,著书不能达到广泛认可,求见沈约后步入仕途,求功名以期立功;得沈约举荐后更有恩师僧祐为其仕途保驾护航,胸怀“纬军国任栋梁”之志以期立德。最终虽抱负未成,但究其动机仍不离儒家“立德、立功、立言”思想。“穷则独善以乘文,达则奉时以骋绩”是刘勰为自身设定得人生信条。后期出家为僧,是因对其有知遇之恩的沈约与仕途上为其保驾护航的恩师僧祐离世,从而政治幻想的破灭,而本身的奋斗终其一生也只得到梁武帝萧衍对其“高级文学侍从”的评价定位,心灰意冷之下的无奈之举。
如此对自身“树德立言”的期许,其出家之际仍不忘上表朝廷的行为,也足以证明刘勰的思想剥去外相,本质上仍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笔者认为,刘勰的一生“出世”是为了“入世”,“入世”无果后才选择了“出世”。关于刘勰在儒佛道三教中的偏向问题中,王元化先生做了简明准确的概括:“刘勰的一生经历正表明了一个贫寒庶族的坎坷命运。怀着纬军国、任栋梁的入世思想,却不得不以出家作为结局。”[6]31当然,其中关于庶族的定位仍值得商榷。但总体来说,刘勰的三教观是一个融涉儒佛道的动态过程,虽然历经了三个阶段的动态发展,总体呈现儒佛道三家合流汇通的趋势,但本质是以儒学为基点而展开的,其以儒为本的思想取向从未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