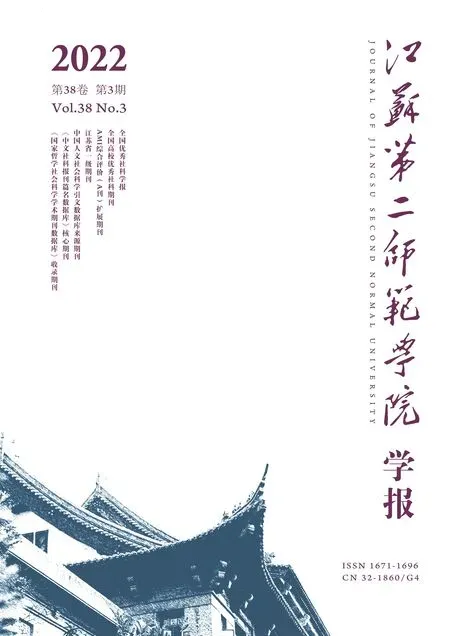文学地理学视域中《红楼梦》与《儒林外史》空间比较研究
李忠明 吴张慧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7)
作为文学创作的主体,作者个人生存空间的自然特征、文化传统以及转换迁移,都会在其作品中留下深刻的印记,构成作品的独特的空间特征。六朝古都南京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传承,是明清时期许多著名作家的居留之地。特别是《红楼梦》《儒林外史》这两部最伟大的小说作品,其创作空间均与南京密切相关。《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自其曾祖父曹玺开始,三代四人先后出任江宁织造,曹氏家族在南京享受了半个多世纪的荣华富贵。作者少时在南京锦衣玉食的生活以及在此经历的丧父、抄家等重大变故,对《红楼梦》的创作影响巨大;曹雪芹十年辛苦不寻常,著书黄叶村,身在京城,心系金陵,书中贾府表面上在北京,实际上真正的空间落脚点是江南甄家,形成了结构上明暗对比的空间张力。《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在青少年时期饱受家乡全椒士绅白眼之后,愤而举家迁往南京,耗时十年,创作《儒林外史》;南京的文化传统、风土人情、都市气息,既是吴敬梓精神创伤的疗伤圣药,也是创作《儒林外史》不可或缺的文化资源,让南京成为与以全椒(小说中化名为五河县)为代表的恶俗文化对抗的精神栖居之地,成为小说的空间结构的核心汇集地域。
一、作者生存空间的自然风貌与人文传承
从时间上看,两部杰作均诞生在十八世纪中叶,正值康雍乾盛世的顶峰,政权不断巩固,生产不断发展,明末以来破烂不堪的社会经济得到了极大的恢复,尤其是商人阶层积累起了巨大的商业资本。生产的不断发展也促成了当时城市经济的空前繁荣,位于东南沿海的大城市南京,更是“人烟凑集”,但是既得利益者大多数是官僚、地主和商人,劳动群众的生活依旧困苦,城市的繁荣之下掩盖的是农村的贫苦;文化发展方面,清朝统治者为了笼络知识分子,消除敌对情绪,采用多种方式网罗知识分子,对于不愿在朝廷做官的有影响的文人,利用编纂图书的办法加以联系,大量的古代典籍由此得以保存流传,但在编辑的过程中,统治者对于古籍进行了大量销毁;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方面,统治者一方面通过怀柔政策笼络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大兴文字狱。“盛世”的景象中包含着矛盾,隐藏着诸多动乱的因素。从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来看,当时正处于清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期,也是封建社会的末端,是封建文化的回光返照。
从空间上看,两部作品均将感情集中灌注于南京。《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的作者,都有移家、迁徙的经历,因此就其生活的自然空间而言,均有两个空间。
1.吴敬梓——全椒与南京
吴敬梓康熙四十年(1701)出生于安徽全椒,33岁移家南京,自称“秦淮寓客”。全椒和南京是研究作者生平的两个重要空间[1]。明清之际的全椒吴氏极为重视科举,并取得了巨大成功。自吴敬梓曾祖吴国对这一辈以来,代代都有进士,并出现了榜眼、探花各一名。吴敬梓在诗文中也常以自豪的语气提及“五十年中,家门鼎盛。陆氏则机云同居,苏家则轼辙并进。子弟则人有凤毛,家巷则人夸马粪”。[2]40到吴敬梓这一辈时,全椒吴氏逐渐由盛而衰,吴敬梓在《移家赋》中发出“君子之泽,斩于五世”[2]41的感慨。吴敬梓在全椒的生活并不如意,生父与继父相继病故后,族人争相夺取他的财产,“兄弟参商,宗族诟谇”[2]41,诸如此类的事件对吴敬梓产生了极大的思想刺激,吴敬梓与族人以及故乡的士绅关系不睦,对故乡的社会风气十分厌恶,其在《移家赋》中以“昔之列戟鸣珂,加以紫标黄榜,莫不低其颜色,增以凄怆,口嗫嚅而不前,足盘辟而欲往。念世祚之悠悠,遇斯人而怏怏”抨击全椒的世态炎凉[2]41。
与全椒相比,青年时期几次游历南京都给吴敬梓留下了良好印象。南京风光绮丽、依山傍水,山水城林相互映衬。城内外水系发达,玄武湖、莫愁湖、秦淮河等纵横交错;名山众多,钟山、鸡笼山、牛首山、幕府山等交相辉映。吴敬梓在《移家赋》中称赞南京“景林佳丽,黄旗紫气,虎踞龙盘,川流山峙,要栏花砌,歌吹沸天,绮罗扑地,实历代之帝都,多昔人之旅寄”。[2]42因而在33岁这年,吴敬梓怀着漂泊的悲情与新生的期盼,举家迁往南京,“偶然买宅秦淮岸,殊觉胜于乡里”,由此开始在南京长达21年的寓居生活。移家后由于其不善经营,生计窘迫,迫使吴敬梓走出文人圈与市井小民来往,由此作者对于现实人生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来到南京之后,吴敬梓不可避免受到南京文化的影响。南京优越的自然环境以及人文景观,六朝古都的历史积淀、短命王朝的悲情色彩以及作为陪都的政治氛围等,均对其创作有所影响。
首先,南京是六朝古都,遗迹甚多,人文荟萃,具有独特的厚重感。中国古代文人历来对南京都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许多文人墨客在其作品当中都用大量的笔墨对南京的自然风光、人文景观进行描述。例如袁枚在《随园诗话》卷二:“佳辰结良觌,言采北山杜。鸡鸣古埭存,登临浑漫与。萧梁此化城,贻为初地祖。六龙行幸过,金碧现如许。欲辨六朝踪,风乱塔铃语。江南山色佳,玄武湖澄澈。豁开几盎间,秀出庭木末。延陵敦夙尚,藉以纾蕴结。山能使人澹,湖能使人阔。聊共发啸吟,无为慕禅悦。”吴敬梓对魏晋风尚有极大的兴趣,《金陵景物图诗》中近一半是凭吊六朝古迹的内容,且每组诗之前都有诗序介绍此地的历史背景或特色。
其次,南京是当时的文学中心,有“天下文枢”的美誉。南京刻书业发达,朱元璋曾将南方各地的书版集中于南京国子监,刻印“南监本”。到了清代,南京涌现出一批私家书坊,三山街、内桥成为书坊聚集地,南京是全国的图书和众多书商云集之地。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提及:“今海内书,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阊阖也、临安也。”[3]41刻书业的兴盛使得南京成为图书汇集之地,有“图书之府”的美名。曹寅在南京时为南京文化的繁荣做出过极大贡献,包括刊行《全唐诗》和《佩文韵府》,演出名剧《长生殿》等。刻书业的发展也推动了南京教育事业的发展,书院的设立使得南京人才辈出,据陈美林先生研究,吴敬梓在移居南京之后,与不少文人、学者交往,感受新的社会思潮和学术风气的熏染。
再次,南京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为商业的兴盛创造了优越的条件,作为东南沿海的大城市,人口众多,商业、手工业发达,娱乐文化兴盛。《松窗梦语》中写道:“(金陵)乃圣祖开基之地,北跨中原,瓜连数省,五方辐辏,万国灌输……南北商贾争赴焉。自金陵而下,控故吴之墟,东引松常,中为姑苏,其民鱼稻之饶,极人工之巧,服饰器具,足以眩人心目,而志于富侈者争赴效之。”商业的繁盛吸引了各地豪商、巨贾来此进行商业贸易,也为文化和娱乐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在繁荣的南京城,戏曲文化十分繁荣,南京素有江左风流之称。明清时期南京是江南地区的戏曲演出中心,戏班众多,名伶云集。明代南京的戏曲表演活动十分活跃,在当时享有“金陵歌舞诸部甲天下”的美誉,出现了以南京为背景的戏曲,例如《秣陵春》《桃花扇》等。商业的繁荣,使得市民阶级扩大,符合市民阶级消费需求的世情小说在此有着广阔的消费市场,书坊主出于追逐利润的目的,也助推了世情小说在江南地区的流行。
明成祖迁都之后,南京成为留都,在明清文学作品当中,南京的都城地位一直都被人们所强调。东鲁古狂生在《醉醒石》当中第一回便强调了南京不仅是南方地区的政治中心,也是经济中心,“南京古称金陵,又号秣陵,龙盘虎踞,帝王一大都会……其壮丽繁华,为东南之冠……真是说不尽的繁华,享不尽的快乐”。清朝时,南京相对宽松的文化氛围,被当时的文人所追慕。从六朝至明清,南京始终处于政治的风雨飘摇之中,作为六朝古都的历史地位,并不是仅仅说明南京曾作为都城的辉煌,同时也使南京的文化含义之中自带了历史兴衰变化的悲情色彩,这里上演了太多的历史更迭。这种历史的变更,使得南京自带一种悲情色彩。
2.曹雪芹——南京与北京
虽然对曹雪芹生活在南京的具体时间范围尚有争议,但是他从小居住在南京直至雍正五年曹家被抄才搬迁到北京这一判断,基本得到了学界的公认。有些学者认为曹雪芹在南京生活的时间长达十几年,比如吴新雷[4]94;也有的学者认为曹雪芹在南京只生活了短短的三四年,比如周汝昌[5]91。
自曹雪芹曾祖父曹玺开始,曹家三代四人历任江宁织造,曹氏家族在南京度过了极为显赫的半个多世纪的时光。[6]曹家身为内务府包衣的特殊身份,注定了其与皇权的纠葛。曹玺之妻孙氏是康熙儿时的保姆,康熙称其“此吾家老人也”;康熙六次南巡,曹家接待四次;康熙帝御赐曹家匾额“萱瑞堂”以及御书题词等等,凡此种种,足见其恩宠异常。曹家多次接驾一方面令曹家风光无限,另一方面接驾时花费的银两如同淌海水一样,这也为曹家的衰败留下了隐患,曹家之后被抄家与款项亏空不无关系。曹雪芹出生之时曹家已经不及之前那样兴盛,但此时的织造局仍能维持着荣华的排场,祖辈曹寅等人营造的书香门第的艺术传承和文化氛围仍在,祖辈曹寅的文学事业以及爱才惜才的文学风尚,给了曹雪芹极大的影响。曹雪芹的童年时期便是生活在这样一个钟鸣鼎食之家,鲜花卓锦,烈火烹油。
雍正时期,由于曹頫与康熙政敌的交往,再加“织造款项亏空甚多”,最终于雍正五年被抄家。由此,曹家败落,曹雪芹随家人前往北京。据有限的诗文记载,在北京曹雪芹过着“举家食粥酒常赊”的窘困生活,他自评“富贵不知乐业,贫困难耐凄凉”,昔盛今衰的强烈对比,使得曹雪芹常常追忆过去丰衣美食的金陵生活,“衡门僻巷愁今雨,废馆颓楼梦旧家”,敦诚《赠芹圃》云“燕市哭歌悲遇合,秦淮风月忆繁华”,“梦”“忆”足可见曹雪芹对曹家过去辉煌的追忆,这种追忆在《红楼梦》中也如实反映了出来。[5]298+276
在明清时期的小说中,很多小说作者都会在作品中对金陵籍贯有意无意地突出,例如《南朝金粉录》便是金陵诸位名妓的故事;《绘芳录》:“却说我朝鼎盛之时,金陵出了两个名妓”。这在《红楼梦》和《儒林外史》中也有所体现,梅新林将其提炼为“金陵情结”[7]。两位作者虽都选择将南京作为情感寄托之处,在其中灌输的情感却不尽相同,吴敬梓是逃离家乡之后来南京寻找新的希望;曹雪芹则是在穷困潦倒的现实之中,追忆过去在南京的繁荣。南京在两部作品中的具体描写,以及作者“金陵情结”的具体内容,留待下文具体讨论。
二、作品描写空间的结构特征与文本意义
吴敬梓因讨厌家乡全椒而移家自己向往的六朝古都南京,由科举世家的既得利益者转变为科举弊端的猛烈批判者,其南京生涯自然与青少年时期沉醉于科举的全椒生活构成反讽;曹雪芹少年时期生活在花团锦簇的南京,后来因为抄家被迫迁徙北京,相对于童年时期美好的回忆,穷困交加的当下生活同样构成了巨大的落差。《儒林外史》《红楼梦》虽然描写是几乎同一历史时期的南京,但由于作者的不同的人生经历,构成了他们对南京不同而同的印象,呈现出丰富多样的文本意义。
1.以南京为松散枢纽、内在核心的全国性地理布局
《儒林外史》中作者所叙述的空间在不断的变化之中,从《儒林外史》全篇来看,全书五十六回的内容跨越了多个地区,涉及浙江、山东、广东、江西、安徽、陕西、四川、贵州、江苏等地。全书五十六回中提及江苏五十一回之多,浙江次之,共有二十七回。在江苏各地之中,南京被提及的频率最高,直接间接共有三十回。[8]由此可见,江苏尤其是南京,是《儒林外史》的叙事的核心地域。
吴敬梓对南京有特殊的情感,对于他而言,南京风景秀丽、文化繁荣、名士聚集且是文化、礼乐中心,是追求礼乐兵农社会理想的理想之地。在南京,吴敬梓与不少文人、学者交往,接受新的社会思潮和学术风气的熏染,如颜李学说以及当时一些文人重视科学的风气。同时由于生活困苦,作者也与形形色色的市井小民有了更密切的接触,这些对他思想转变有积极的影响。明代特殊的政治地位也使南京成了与仕宦保持疏离的那些士人的情感寄托与精神家园,南京为吴敬梓这些功业未建的名士,提供了安身立命之所。
《儒林外史》中南京是文化的中心、礼乐规范的中心,一个具有强大辐射力的文化场,全书呈现以南京为中心,向四周扩散的文化辐射结构。第三十二回娄太爷去世前嘱咐杜少卿“南京是个大邦,你的才情,到那里去或者还遇着个知己,做出些事业来”[9]。在扬州活动的一些名士也提出“我们同在这个俗地方,人不知道敬重,将来也要到南京去”。沈琼枝也想到“南京是个好地方,有多少名人在那里,我又会做几句诗,何不到南京去卖诗过日子;或者遇着些缘法出来也不可知”。作者借书中士人之口,阐明当时南京在群众心中的重要地位,字里行间流露着作者对南京学术文化中心地位的推崇。
除了通过人物语言直接表述,作者对不同地区人物形象的塑造,也足以看出作者对南京文化的认同与推崇。刚开始的山东、广东以及江西地区,除王冕之外,基本以反面人物为主,作者对其多持否定态度。到了浙江、南京地区,作者塑造的人物逐渐正向,全书正面人物的两大代表虞育德和庄绍光,一在南京任国子监博士,一是江宁府属上元县人。全书还塑造了许多南京的文士形象以及众多在南京进行的学术交流。如第三十四回,杜少卿大谈《诗经》,赢得金东崖、迟衡山、马纯上、萧柏泉、季苇萧、余和声等人纷纷称赞。
除了文化中心,小说中也重点描述了南京礼乐规范中心的地位,祭泰伯祠这一全文情节的重中之重,便发生在南京,各类士人不约而同地往南京聚集,有分量的人都参与了这一次典礼。晚辈读书人中,比较有分量一点的,不少人也来凭吊过、瞻仰过泰伯祠。“我们生长在南京,也有活了七八十岁的,从不曾看见这样的礼体”,借百姓之口,表现当时礼乐制度的崩坏,这场祭祀便显得更为珍贵。
南京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为其文化扩散提供了动力。明清时期,由于独特的政治、经济、人文与自然风光等条件,南京的文化集聚与辐射功能得以实现。在当时,悠久文化传统的积淀以及文人学士的大量汇集,使得南京文化氛围极浓,从而促使南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景观,文化事业繁荣,戏曲表演活动十分活跃。文集和时文刊刻的需要,促进了南京刊刻业的发展,使得南京成为当时的图书中心,成为许多人向往之地。例如文中第四十八回提到,“老哥要往南京,可惜虞博士去了。若是虞博士在南京,见了此书,赞扬一番,就有书坊抢的刻去了”。
吴敬梓人在南京,同样难舍家乡情结,而他青少年时期在家乡遭遇的难堪经历,成为创作儒林形象尤其是恶劣的士绅群体的内在动力与生活来源。《儒林外史》中作者借写五河县的势利熏天、重利轻义表达其对全椒的讥讽,塑造了一批趋炎附势的五河县人,更是通过余家葬礼一事表现五河县人的崇尚迷信、礼乐尽失。“五河县发了一个姓彭的人家,中了几个进士,选了两个翰林,五河县人眼界小,便合县人同去奉承他”。对这种趋炎附势的风气,作者极为不满,给予了辛辣讽刺:“问五河县有什么山川风景,是有个彭乡绅;问五河县有什么出产稀奇之物,是个彭乡绅;问五河县那个有品望,是奉承彭乡绅;问那个有德行,是奉承彭乡绅;问那个有才情,是专会奉承彭乡绅。”吴敬梓《移家赋》中曾以“假荫而带狐令,卖婚而缔鸡肆。求援得援,求系得系。侯景以儿女作奴,王源之姻好唯利。贩鬻祖曾,窃赀皂隶。若敖之鬼馁而,广平之风衰矣”,讽刺族人不顾门第,正与小说的描写构成了直接的呼应。因此,小说中南京与五河县的空间反衬,与作者生活实践中南京与全椒的巨大反差是正相关的。
2.真假大观园的空间布局
《红楼梦》叙事以大观园为核心空间,故事主要发生在大观园之中,从修建大观园开始,大观园就逐渐成为联结故事的重要地点,文章借元妃省亲对大观园的园内建筑进行了赞美和歌颂,突出表现了大观园的建筑美。文章中的主要人物也都居住在大观园之内,薛宝钗住蘅芜苑,林黛玉住潇湘馆,贾宝玉住怡红院,迎春住缀锦楼,探春住秋爽斋等等,以大观园的院子的特点暗合人物的性格特点。从文章的结构看,《红楼梦》以大观园作为叙事核心。但是大观园的故事原型究竟是在北京还是南京,学术界有不同看法:俞平伯[10]116-126和周汝昌[6]111-119两位前辈学者都认为大观园在北京;吴新雷等人认为大观园在南京[11];周思源等学者认为大观园融合了南北园林的特点,是曹雪芹虚构的空间[12]269-278。我们倾向于认为,创作《红楼梦》时,曹雪芹人在北京,心系南京,地域上看贾府属于北京、甄家属于金陵,心理上甄家为真、贾府为假,地理上、心理上交相辉映,青少年时期的南京富贵、温馨生涯的回味,成为在北京艰难困苦的生活中创作《红楼梦》的精神支撑与素材来源。曹雪芹对小说五易其名,其中《石头记》《红楼梦》和《金陵十二钗》三名均与南京有着深厚的渊源。
《红楼梦》将故事的发生背景设置在北京,但却又不时写及南京的甄家以及贾府在南京的房产,文中江南甄家有很多情节与曹家吻合。例如,在第十六回借刘嬷嬷和王熙凤之口追忆当年甄家四次接驾,这与当年康熙帝南巡六次,有四次驻跸曹家的史实相吻合。第十八回元妃省亲的盛大排场是当年康熙南巡接驾的艺术重现。正如脂砚斋评本所说“借省亲事写南巡,出脱心中多少忆惜感今”。曹雪芹写荣宁二府的衰败处处暗合金陵曹家的败落,最后的抄家单子所列名目,与当年金陵曹家被抄家的理由何其相似。
此外,发源于南京的云锦在《红楼梦》中多次出现:王熙凤出场时“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褃袄”;贾宝玉出场时“穿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北静王水溶“穿着江牙海水五爪坐龙白蟒袍”;薛宝钗穿着“玫瑰紫二色金银鼠比肩褂”;史湘云穿的“一件水红装缎狐肷褶子”;晴雯带病为宝玉修补的雀金裘,这些都是云锦的成品,曹家三代四人先后出任江宁织造,年幼的曹雪芹自然也非常熟悉这些花团锦簇的服装。[13]
文中对“金陵”的正面描写不多,南京对曹雪芹来说更像是一种寄托与归宿,一种美好的象征符号,在《红楼梦》中,人物遇着不如意之事,开口便是回金陵去,凤姐等人最后葬在了金陵,大观园中美好纯洁的女子也与“金陵十二钗”对应。文中多次强调对于金陵的旧礼仪的尊重,贾宝玉和薛宝钗成婚礼“俱是金陵旧例”,贾母也曾提到“咱们都是南边人,虽在这里住久了,那些大规矩还是从南方礼儿”。
《红楼梦》中的金陵意象是富足的,“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真珠如土金如铁”。这仿佛是当年曹氏家族在南京的显赫、富贵生活的真实写照。作者不断地回忆和追思南京的繁华与富足,过去的繁荣与现在的潦倒不断交织,今昔强烈的对比更加衬托出今日的潦倒和没落。同样在南京,曹雪芹经历了丧父、抄家,因此《红楼梦》一再提及“末世”,那种留恋和感伤始终贯穿小说,整篇笼罩着过去的巨大忧患与恐惧。
对于曹雪芹而言,南京和北京有不同的含义:南京在时间上属于过去,在空间上指向南方,南京代表着锦衣玉食,北京代表着贫困潦倒。他身在北京,写作时念念不忘的是南京,《红楼梦》由“现在的北京”追忆“过去的南京”,在文中重构金陵的生活,通过现实时空与金陵虚幻时空的相互交融,重构金陵这一虚幻时空,因此《红楼梦》中的南京不免有一种虚幻、朦胧之感。
3.虚实相生
《儒林外史》与《红楼梦》都对南京进行了描写,却因为作者写作时处境的不同,采取了不同的呈现方式,呈现虚实的对比。《儒林外史》以实写为主,真切展现南京生活的自然风光与世俗风情;《红楼梦》以虚写回忆为主,将南京置于背景之中,时隐时现,展现作者美好的情感寄托。吴敬梓对南京的特殊感情以及他当时正寓居南京的现实背景,促使作者在《儒林外史》中对南京进行了正面、全方位的描写,构建了一个具有强大文化辐射能力的现实南京。而创作《红楼梦》时,曹雪芹已经离开南京几十年了,作者在穷困潦倒的现实中一次次追忆南京,因而《红楼梦》中的南京是虚幻的、繁荣的。
吴敬梓写《儒林外史》重在写实,从“所记大抵日用常情,无虚无缥缈之谈”的现实主义视角出发。创作此书时,作者正寓居南京,《儒林外史》中很多重要素材取自于作者的南京生活,卧闲草堂第三十回回末总评称“明季花案,是一部《板桥杂记》;湖亭大会,又是一部《燕兰小谱》”,《儒林外史》可与记录南京的专门典籍媲美[14]218。纵观全书,作者对南京的自然景观、社会风情进行了真切的描写,洋溢着浓郁的文化气息。如第二十九回,写雨花台的风光,“走到山顶上,望着城内万家烟火,那长江如一条白练,琉璃塔金碧辉煌,照人眼目”,第五十五回写雨花台风光,“望着隔江的山色,岚翠鲜明,那江中来往的船只,帆樯历历可数”。《儒林外史》中,描述了很多南京的地方礼俗,诸如第四十一回,描写了南京七月晦日清凉山地藏会,“到七月二十九日,清凉山地藏胜会——人都说地藏菩萨一年到头都把眼闭着,只有这一夜才睁开眼,若见满城都摆的香花灯烛,他就只当是一年到头都是如此,就欢喜这些人好善,就肯保佑人。所以这一夜,南京人各家门户都搭起两张桌子来,两枝通宵风烛,一座香斗,从大中桥到清凉山,一条街有七八里路,点得像一条银龙,一夜的亮,香烟不绝,大风也吹不熄。倾城士女都出来烧香看会”。其他还有婚礼、葬礼、祭祀礼仪以及中元节点河灯等。吴敬梓《儒林外史》中的描绘士人的境遇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是契合的。《儒林外史》虽然假托写的是明代成化末年至万历二十三年间的历史,但实际上却处处可见清初南京社会生活的影子。文中出现的很多地名,例如三牌楼、内桥、水西门、利涉桥都符合明清时期南京实际情况。
《红楼梦》是意象化的写作,其表现的重要特点就是幻想和非写实性。作者除了在文章中虚构出大观园这个理想空间之外,还多次提及“金陵”,南京对曹雪芹更像是一种美好的象征符号,并不是指代南京的实际意义。《红楼梦》对于南京的描写更多是一种内在的意绪,南京“作为一种精神和心理氛围弥漫于整部《红楼梦》中,又似乎作为一种与现实隐然相对并可以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精神象征高悬与《红楼梦》的时空之上。有时你虽然未见‘金陵’一词,但你却同样可以在‘金陵’与‘金陵’的间隙中强烈而真切地感受到它的存在”[15]425-426。
无论是《儒林外史》的实写还是《红楼梦》的虚写,都是对南京形象的典型塑造,对于南京所带有的变迁与流逝的一面进行了呈现。《红楼梦》与《儒林外史》的小说都以空幻结局收束全文,似乎都体现了南京变迁和流逝的一面,“六朝往事随流水”,南京见证了历史上无数盛衰荣辱、悲欢离合。两部作品都借南京表达一种盛衰交替之感,《红楼梦》中女子生命的消逝,大观园中众多人物富贵之后逐步走向衰败的命运,宁荣两府的败落。《儒林外史》开篇便以“百代兴亡朝复暮,江风吹倒前朝树。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感叹风流云散。结尾以“江左烟霞,淮南耆旧,写入残编总断肠。从今后,伴药炉经卷,自礼空王”,与开头形成前后呼应,感伤情绪贯穿始终,表达对真名士的老去及风物的消歇幻灭与追忆。
三、读者重建空间的人文解读与精神寄托
一部作品的价值、影响和文学内涵在同时代或者不同时代的读者是不同的,通过不同时空读者的不同解读可以不断赋予作品新的意义。“文本空间”的意义是生生不息的,读者对此的阐释也是永无止境的。
1.读者的重新认识
南京是六朝古都,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地位突出,是南朝民歌、六朝文学、明清小说诗歌散文的重要发生地。南京文化流传至今,不仅是源自南京本身独特的自然空间景观,更重要的是蕴含于其中的隐喻意义,南京的优越自然环境与历史的沧桑变化是文学作品创作的素材来源。后来人将《红楼梦》与《儒林外史》视为研究南京的两部重要作品,认为在两部作品中南京均是经过作者主观美化的一种理想状态。
对于两位作者选择将南京作为情感灌输之处的原因,不同的学者提出了自己不同的观点:余英时先生等人曾提出“汉族认同感”的说法,认为曹雪芹在经历过抄家的磨难之后,意识到清代统治的腐朽,所以选择南京这个汉人故都,实际上是曹雪芹民族意识的觉醒[16]149-158;周汝昌等认为曹雪芹童年时期在江宁织造局的生活给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算之后抄家北京,也必然听说了很多曹氏家族在南京的故事,所以选择将南京作为自己的情感寄托之处[5]。对于吴敬梓选择将《儒林外史》的故事核心放在南京,学界的意见较为统一,《儒林外史》将背景设置在明代,南京是明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不写南京难以描绘当时儒林的实貌,而且作者在33岁迁家南京,作者对于南京是认可和欣赏的,寓居南京的现实背景也使得其能够以客观冷静的态度去审视这个城市[17]214-236。
《红楼梦》作为一部写封建家庭生活的小说,在其文本中塑造了两个典型空间:一个是以大观园为代表的理想的空间;另一个是大观园外的贾府以及贾府以外的污浊的现实空间。作为核心空间的大观园的究竟在何处,学界有三种不同的观点。红学界最有影响的俞平伯和周汝昌两位前辈学者都认为大观园在北京;赵冈等人认为大观园在南京,早在两百多年前,诗人袁枚就在他的《随园诗话》卷二中提道:“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中有所谓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他认为曹雪芹《红楼梦》中所写的大观园是他所居住的随园。周思源等学者认为:“大观园综合了我国北方皇家园林和南方私家园林的共同特点,是二者结合的典范。”[12]269-278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大观园实际是曹雪芹为了给笔下的人物提供一个理想的活动空间,融合南北园林特点所虚构出来的一个园子。小说正是通过大观园的荣衰来隐喻这个世家大族逐步由富贵走向衰败的命运。部分学者将研究的眼光投向了大观园中的园林艺术,认为《红楼梦》在通过大观园的环境,显示了人物丰满的形象和鲜明的个性,显示了作者满腔的情愫,创造了充满理想的文化氛围。
关于《红楼梦》到底是双重空间还是三重空间,也吸引了包括宋淇、余英时、王彬等一批研究者的目光。有研究者认为《红楼梦》虽然写的是南京,但是背后隐藏着的是更为广阔的地域空间,甚至可以与时代背景相结合。二知道人在《红楼梦说梦》中提到“太史公纪三十世家,曹雪芹只纪一世家。……然雪芹一世家,能包括千百世家”。曹雪芹写宁、荣世家,无异就是解剖了封建社会的一个活体细胞,通过这个细胞,就看到了整个封建社会,看到了这个社会的最终趋势。
《儒林外史》是一部根植于当时社会现实的小说,对于《儒林外史》的解读注重情节本事与人物原型的探究,陈美林先生在着重研究《儒林外史》与南京的历史勾连,刘红军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儒林外史》人物原型和情节本事的考论文章。除南京之外,《儒林外史》中的五河县也吸引了研究者的目光,最流行的说法是五河县的原型,就是作者家乡安徽省全椒县,作者描写五河县的恶赖风气,暗喻的是明清时期社会充满不良的风气:读书人只想求功名而忽视礼义道德、毫无真才实学;百姓多趋炎附势、唯利是图。正如《儒林外史》天二评本中所说的:“遍地如此,岂特五河。”
《儒林外史》中涉及的地名很多,研究者对其空间叙事是否有内在逻辑、地域出现的前后顺序是否是作者的有意安排争论颇多,胡适、鲁迅、陈美林、杨义等学者均从文学的角度对其结构特点进行了研究,叶楚炎从地域叙事的角度研究《儒林外史》中的结构特点[18],史俊超结合文学地理学的理论,提出《儒林外史》就“空间而言各大地域叙事有严密的圈层结构。在各大板块内部,从外围到中心的叙事趋势逐渐加强,但又并非单向的线性集中,而是一种聚焦——离散——再聚焦的圈层结构”[19]。
二十一世纪以来,一些学者将《红楼梦》和《儒林外史》放在空间叙事的视角下,探讨两部作品中的南京叙事,提出《儒林外史》中的南京充满了六朝烟火气,是对南京的纪实性描写。《红楼梦》中的南京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呈现在作品中就是一方乐土。梅新林首次提出曹雪芹这种对于南京的特殊感情可称之为“金陵情结”[20];葛永海紧随其后,在自己的论著中指出从广义的含义上看,吴敬梓同样怀有一种“金陵情结”,在《儒林外史》中对南京进行真实、全面的大段描写。[21]从时间的角度来看,《儒林外史》与《红楼梦》都创作时,两位作者都选择了隐喻,《儒林外史》假托是明朝时的南京,《红楼梦》中作者将真事隐去,把故事聚焦在大观园之中。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不难看出,两位作者的选择时均为了规避当时严苛的文字狱。
综观各种对《儒林外史》《红楼梦》空间解读的文字,毫无疑问,绝大多数阐释者同样带有自己的地域视角。偏爱南京的学者当然更愿意把金陵理想化,把全椒、北京作为理想空间的对立面,反之亦然。比如安徽(尤其是全椒)的学者当然更愿意探讨当地文化对吴敬梓的哺育,有意无意地淡化吴敬梓对家乡的敌视与批评;南京的学者当然更愿意论证大观园的原型主要是金陵随园,有意无意地强化金陵意象在《红楼梦》中的重要价值。
2.传承
在文学作品构建出的想象空间中,“因文设景”具有较高的审美意义,即实现“因文成景,文传景名”的效果。《红楼梦》《儒林外史》作为我国古典文学名著,在当代传播过程中产生了诸多独特的文学景观:曹雪芹主题纪念馆、重建的大观园以及红楼文化艺术博物馆、吴敬梓纪念馆和秦淮水亭。纪念馆的建设主要是对存疑的故居地址进行保护,虽然对于故居的真假还有所存疑,但是首先得保护,不然关于真假的讨论将毫无意义。后人参观这些重现的文学景观,所抒发的感慨是读者与作者跨越时空的对话,诸多文学景观的建立,是读者基于文学文本进行空间重建的结果。
综上所述,《儒林外史》与《红楼梦》中“南京”之“文本空间”既是南京的,因为它源于南京,以南京为现实依据;同时它又是非南京的,因为它虽然写的是南京,同时又是融合了记忆南京与当下南京、实体南京与梦幻南京、物态南京与精神南京、个性南京与共性南京的集合体。虽然写的是南京,但是背后隐藏着的是更为广阔的思维空间,与作者的主观想象以及读者的文本构建直接相关。
四、总结
文学作品产生于特定的地理环境之下,也受限于一定的地理空间,这里的地理空间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景观两个方面,作者生存空间自然环境与文化传承不仅是创作者的描写对象,反过来也会影响创作本身,《红楼梦》《儒林外史》都明显受到南京地域文化的影响。两位作者的生平,都有移家、迁徙的经历,因此就其生活的自然空间而言,均有两个空间,吴敬梓是逃离家乡之后来南京寻找新的希望;曹雪芹则是在穷困潦倒的现实之后,追忆过去在南京的繁荣。《红楼梦》《儒林外史》两部作品对于南京的选择带有一定的必然性。南京的优越的自然环境和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对于任何一个文人来说,都有着独特的吸引力,六朝文化深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南京人的生活。
其次,文学作品是作者的主观创作的过程,作者在进行文学创作时,由于作者主体生活境遇、情感寄托的不同,选用不同的呈现方式,相同的地理空间呈现出来的文本空间会有所差异。《红楼梦》和《儒林外史》描写的几乎是同一时代的同一城市,但两者选用了不同的呈现方式,《红楼梦》虚写为主,以“北京”追忆“南京”;《儒林外史》则以实写为主,展现南京的自然风光和世俗人情。不同的呈现方式,所传达的文本意义也有所不同:吴敬梓因讨厌家乡全椒而移家自己向往的六朝古都南京,青壮年以后的生活、创作中,自然对青少年时期生活的全椒构成反讽;曹雪芹少年时期生活在南京,后来因为抄家逼迫迁徙北京,青壮年时期在北京生活、创作,不断追忆童年时期美好的生活,对当下的精神空间构成了反讽。
再者,读者在对文本空间进行人文解读时,又会产生新的文化空间,读者的每次阅读都是一次“精神探源”,或许每次阅读都会比之前破译更多的隐喻,但却是永远无法企及“终极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