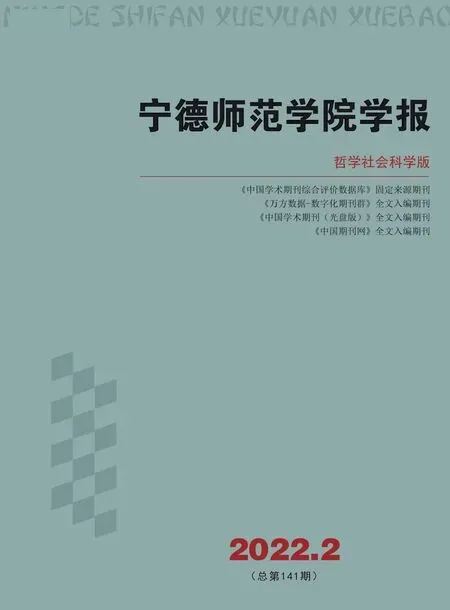习近平治水理念在福建省的实践
陈凯伦 高 峻
习近平同志从事基层治水实践以来多次就系统治水与科学治水做出重大决策部署,催生了新时代水利精神财富。[1]在福建省工作的17 年半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在厦门、宁德、福州履职,期间他立足福建省省情,结合本地区域山水优势,推进了一系列甚至在全国具有前瞻性和开创性的的治水实践。那么,习近平同志在闽17 年半年期间具体开展了哪些治水实践?这些治水实践与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提出的“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16 字治水理念有怎样的联系?习近平治水理念是习近平同志在不同时期躬行调研,致力谋划改革发展,高度概括形成的科学理论,是新时代水利实践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2]为福建省的水利事业绿色发展发展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一、治污实现节水优先与开源并重
福建省森林覆盖率居全国前列,是我国降水量、水资源量最丰沛的地区之一,也是我国水源涵养重点保护区。习近平同志率先启动了福建的生态省建设,他在1999 年1 月千里江堤建设暨水电局长会议上讲话时强调:要统筹兼顾经济、社会、生态三大效益,建立一个开源节流并重的供水供电体系。[2]虽然节水观念在当时福建省群众的认知中早已不陌生,但在水量颇丰的福建省倡导节水是难能可贵的,即便当下在水量丰富的区域普及节水新技术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习近平同志在当时就已形成居安思危的节水观念,可见其高瞻远瞩的超前意识。
如果说千里江堤建设会议上的讲话是习近平同志在闽节水的思想萌芽阶段,那么厦门筼筜湖的治污实践则为节水优先与开源并重的思想提供了理论来源。1988 年2 月,厦门市政府办公地点搬迁到湖滨北路,湖滨北路毗邻厦门臭水湖——筼筜湖。过去筼筜湖是市区的最大地表水面,每到夜晚华灯初上,停泊在湾内的渔船享有“筼筜渔火”的美誉。[3]然而,1970 至1971 年期间,厦门为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实行围海造地,在湾口修建了筼筜海堤,致使海水交换的路径被截拦,从此筼筜湖成为一个封闭的内湖,同时也成为全市一半以上污水和城市垃圾的容纳所。据统计,筼筜湖的污染源主要来自周边125 家工业企业,这些企业每年排放的近七百万吨的污水占每年全市污水的四成以上,此外全市生活废水近一半约五百万吨直排该湖,还有六家医院污水也直入此湖,[4]恶劣的水环境不但危害厦门市民的身心健康,还阻碍了厦门经济的发展,[5]时任厦门市副市长的习近平同志为此殚思极虑,采取截污措施迫在眉睫。1988 年3月30 日,他召开专题会议正式启动了厦门水质污染的整顿工作,明确把“治理筼筜湖,保护西海域”作为目标,为筼筜湖制定了一套完整的综合治理机制,与此同时厦门市的污水处理项目也伴随着筼筜湖的治理有序展开,1989 年,在厦门市政府的大力推动下,福建省第一座污水处理厂在厦门落地,原本直接排入筼筜湖的废水全都汇集到污水处理厂,排入大海或者用于绿地浇灌,[6]实现了节水的目标与污水优化再利用。此外,习近平同志亲自主持制定了厦门市第一个发展战略——《1985-2000 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他在战略中特别强调要集中当时现有的财力、物力、科研力量等各方力量积极治理筼筜湖,不能以破坏海洋生态系统为代价来发展特区经济。[7]
习近平同志来到厦门开启了在闽工作的第一站,迎着改革开放的东风首次对沿海发达地区的城市建设和管理做出指导。他秉承“节水即治污”的理念,将污水资源优化再利用作为节水与开源并重的核心内容,筼筜湖循序渐进的治理经验也为全国其他省市关于如何整治城市内河污染问题,实现治水事业的开源及节流提供了宝贵经验。直至2000 年底,筼筜湖治理工程基本竣工,整治成效卓著,[8]如今,碧波荡漾的筼筜湖已成为厦门中心城区一颗闪亮的明珠。筼筜湖治污实践表明,通过“节水即治污”“节水与开源并重”的实践是行之有效的,这段经历为习近平之后从区域性水污染的综合治理到加强沿海城市治水问题与经济建设的演变积累了宝贵经验,为后来以更广阔的视角探索生态问题奠定了基础。
二、闽江调水实现空间均衡
水资源空间均衡指的是区域水资源和水生态承载压力与承载支撑力之间的协调程度,结合当地实际用水量和人均需求,从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实现满足人民生活保障的需要与水资源承载之间的内在关系。习近平同志来闽工作后的经历,使他对江海山林的发展,区域水资源空间均衡形成了独到的见解,为响应改革开放的号召,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同志结合福州市的发展,因势利导亲自主持并编订了《福州市20 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即福州“3820”工程),他在其中首次提出“城市生态”的概念,[9]闽江调水工程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3820”的要求,福州市还将进一步加快水资源的跨区域平衡。[10]福清市是全国农业城市化首批综合改革试点之一,但由于福清市内河溪数量寥寥无几,且水量不丰,导致福清人均水资源仅占全国人均水平的1/3,缺水的窘境严重影响了福清人民的生产与生活。20 世纪90 年代福清市经济发展日新月异,带动了需水量成倍增长,现有的水利基础设施早已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11]为解决水资源匮乏问题,习近平同志在主持省政府工作期间,果断启动并大力推行了闽江调水工程。该工程北起乌龙江的闽侯祥谦镇峡南村,东至福清市城头镇岩兜村,南抵三山镇的北林水库,输水线路横穿闽侯、福清两县市10 余个乡镇,主要建设项目包括:(1)取水工程。取水口选在乌龙江桥下游530m 处,取水工程包括总装机容量8800kW 的取水泵站工程和取水头部工程、取水管道工程;(2)输水工程。涵渠包括“一条主干线”,即闽侯县峡南至福清阳下酒店的分水枢纽处,再分出3 条支线分别将水引到福清城头、龙高和江阴地区。[12]习近平曾多次到施工现场指挥,适时提出意见和改进方案,推动工程顺利发展。在一次调研中,习近平同志亲自坐施工车进入青圃岭隧洞察看工程进展情况。[13]该工程于2003 年11 月顺利竣工,此后每年可调水约1.5 亿m3,灌溉耕地38.74 万亩,为周围104 万群众解决了燃眉之急,[14]扭转了福清市常年以来水资源短缺的困境,为城乡居民的供水和工农业生产提供了基础保障。此外,习近平同志在福州执政期间,于1993 年在闽清县推进建成了华东最大的水电站——水口水电站,这是福建省第一个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兴建的能源工程,不仅有效地缓解了福州水电能源紧张的问题,[15]还拉动了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的进一步腾飞。
水的空间均衡受到地形地貌、降水特征、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的动态影响,水资源在不同区域分布不均是客观存在的规律。尊重自然规律实现经济与环境之间协调可持续发展,达到人水之间和谐共处,这是习近平关于水利论述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福清市水资源短缺的现象,他采取坚决果断措施进行顶层设计,抓住了解决水资源困境的“牛鼻子”——量水而行,将福清市区域水资源的承载力划为一条不可触碰的“高压线”,为实现水资源绿色发展打开了新进路,这是习近平同志底线思维在水利领域的探索与实践。2019 年9 月习近平同志亲临黄河视察指导工作,在座谈会上他生动地将空间水资源合理布局形容为“有多少汤泡多少馍”,坚持以水来约束城、地、人、产四项发展,正是对闽江水调工程精髓的进一步阐释。
三、厘清规律实现系统治理
系统治理的内涵旨在对水资源的变化规律和趋势进行一线排查,坚持全流域综合治理,同时对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的水生态以修复为重点工作,协同水资源水环境保障流域健康高质量发展。对此,习近平同志在整治内河、根治水患与治理水土流失方面率先做出了示范。
在整治福州的内河问题上,习近平同志将治水事业建设提高到城市发展目标的高度,通过完善体制改革系统治理高位推动,实现内涝、污染、绿化、水土流失四项措施有序展开。[16]首先,对于内涝问题。习近平同志多次携水利技术人员亲临现场指导工作,最终决定对闽江153 公里的防洪堤采用钢筋水泥进行加高加固。同时经勘察人员验证,在当时内涝最严重的地区铜盘路附近开挖河道,[17]彻底解决了千百年来洪水泛滥的问题。其次,对于城区污染问题。习近平同志通过推动出台《福州市城区内河污染综合整治规划》,强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城市发展目标之一,并开创福州污水治理先河,规划兴建了福州第一个城市污水处理厂——祥坂污水处理厂。同时,每年投入一定资金在内河两边腾出通道做绿化带,做到“一河一带”,[18]并提出“全党动员、全民动手、条块结合、齐抓共治”的十六字内河治理原则,[19]摸索出了一套适应福州内河治理之道。此外,对于水土流失问题。针对闽江口以南的平潭和长乐水土流失问题采取专项整治,习近平同志于1996 年3 月13 组织召开农业工作会议,强调落实“三五七”造林绿化工程和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通过发展林果生产控制水土流失。[20]最后,对于景区西湖污染问题。2001 年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同志强调要统筹好开发和保护的关系,要求真抓实干马上行动,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和扩大西湖。[21]
木兰溪水患治理是习近平同志继福州内河治理实践之后又一聚焦系统施治成果。木兰溪水患经历二十多年的持续治理,总体的治水理念逐步上升到水生态、水经济、水文化“三位一体”的全流域系统治理的科学发展理念。[22]木兰溪下游由于地形破碎,纵坡较陡以及溪流弯曲排洪不畅等自然因素导致木兰溪水患频频。[23]习近平同志坚持亲自擘划,对如何将木兰溪变害为利,统筹兼顾进行科学论证和充分研讨。1999 年10 月在第14 号超强台风的影响下,木兰溪转瞬成灾。面对灾情肆虐,习近平同志庄严承诺:要彻底根治木兰溪水患。[24]此后,习近平同志四次亲临木兰溪指导工作,并强调要牢固树立“科学治水”的发展观。在习近平同志的倡导下,国内水利专家窦国仁院士主持攻关,研发了全国首创的物理模型,解决了“裁弯取直”[25]对水生态环境带来的直接负面影响,并由习近平同志亲临考察,证实了这项试验效果的可行性。如今,曾经让当地人“谈溪色变”的水患之河,已然成为首批水利部示范的生态之河,实现了变害为利、为民治水的目标。[26]
长汀水土流失的成功治理是基于习近平同志躬行实践,在实地勘察、收集详实数据的基础上,最终根据分析结果在关键节点进行重要部署,围绕分流域、分阶段、循序渐进的方案,治理水土流失创造的奇迹。长汀县曾是全省水土流失程度最为严重的地区,习近平同志在闽执政期间5 次出行长汀调研并亲自题词力图彻底治理长汀水土流失。1999 年11 月27 日,习近平同志提出要与水土流失问题作斗争,要有“滴水穿石,人一我十”的使命感。[27]2000 年1 月8 日,习近平同志同意上报长汀县为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县。2001 年10 月13 日习近平同志听取水土流失治理的情况汇报时说:“要将治理重点放在土流失特别严重的区域,这项工作要持之以恒地落实下去,认真总结经验以点带面覆盖到全区域。”2002 年为进一步压实水土流失治理责任制,习近平同志进一步提出在闽建设生态省的战略设想。[28]2012 年初,已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依旧格外关注长汀县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现状,两个月内分别两次派调研组实地考察并做出重要批示,其中2012 年1 月8 日习近平在调研组上做出批示:长汀县水土流失治理正处在关键期,此时的战略布局事关水土流失治理成败,[29]应牢牢抓住主要矛盾率先治理水土流失最严重的三洲镇,把治理水土流失与发展地方经济相结合。在习近平同志的部署下,长汀县明确发展思路,打响了长汀水土流失治理攻坚战,彻底改变长汀县生态现状,森林覆盖率提高到79.4%,[30]实现了“荒山—绿洲—生态家园”的历史性转变,圆了当地百姓的百年绿色之梦,[31]“长汀经验”也为我国其他地区水土治理提供了实践范本。
习近平同志在坚持完善水资源全过程管理方略的实践中,牢记为民治水、科学治水的系统治水观。他在基层期间对治水事业的探索是形成生态文明思想的奠基石,如今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体系的构建,正是习近平同志对当前经济发展格局和趋势的深刻洞察。将水利事业的发展与城市发展、民生工程、基础设施建设相结合,为认识当下、规划未来、制定政策找到客观基点,提高了水利工作的科学性。在习近平同志任党中央总书记后,在更宏大的历史和地理背景下将这些治水战略构想置于一个更加广阔的框架,上升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32]使之施展空间更大,未来的作用和带动的效益将更加深远。
四、守护绿水青山实现经济效益
两手发力指的是联动市场和政府将水资源管理置于社会经济发展大系统中,在开发、利用、保护、节约、配置等问题上充分发挥政府以及市场为抓手的指导作用。山海兼备的福建地区是习近平同志治水实践重要的练兵营,也是习近平在闽接触山海发展的开始,习近平同志在闽履职期间的治水实践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重大理论提供了探索平台。[33]
习近平在宁德履职时期对林业建设和库区的治水实践,不仅是绿化荒山和改善民生的考虑,更是闽东人民摆脱贫困的重要出路,从发展经济建设时兼顾生态效益,到把生态效益转化为经济效益的过程,实现了绿色经济新发展模式。到宁德上任初期,习近平同志就开始了对闽东九县市的调研,在调研中他发现闽东许多荒山具有宜林的优势。[34]为了改变闽东地区的绿化现状,1989 年1 月习近平同志提出“三库”绿色生态理论,即森林是“水库、粮库、钱库”,[35]强调政府要合理开发利用好山林优势。[36]据宁德市林业局数据显示,目前宁德全市森林覆盖率达69.98%,实现了以生态发展带动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37]同时,习近平同志还高度重视宁德古田县库区建设,1989 年7 月10 日,当时国家“七五”计划提出要建设水口水电站,在建设库区的过程中古田县部分村庄被淹没,习近平沿途视察水口水电站的建设和库区移民情况时提到:要充分发挥山区经济特色,利用水库的防洪、灌溉、发电、水产养殖、旅游开发等多种用途实现经济效益,[38]使库区经济实现自我发展的需要。
此外,在习近平同志的倡导下,三明经济社会建设在厚植山水优势的基础上力争做好山水文章实现生态和经济效益的统一,最终实现了三明人民从守护青山绿水间捧出金饭碗,让荒芜的土地变为绿色“聚宝盆”的美好愿景。六年时间里习近平同志先后十一次遍访三明的山山水水,始终把改善民生,为民治水当成头等大事。习近平同志于1997 年4 月13 日在调研时提出:要充分挖掘三明天然的山水优势,画好“山水画”,促进山区经济的迅速崛起。[39]1999 年7 月6 日,他在调研泰宁老区工作时指出:三明未来要因地制宜挖掘山区的生态优势并将之转化为经济效益。[40]2002 年6 月26 日,他在三明视察洪涝灾情时的讲话中提到:三明是福建母亲河——闽江的源头之一,具有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优势,现在看似没有价值的绿水青山,未来将会成为无法估量的无价之宝,要严肃认真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41]这一阶段的治水实践是习近平同志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识在省域层面对市级工作做出的,是基层治水履历走向成熟的阶段做出的,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萌芽的产物。[42]
新时代习近平同志提出“两手发力”的治水理念,是正确处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平衡的又一次升华。水资源利用属于公益性较强的行业,在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的条件下应该以水资源创造的价值规律为基石,在市场供求以及价格机制的推动下,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大化。同时,政府部门应该以宏观调控的形式,通过制定相关法规、指示等行政措施,对水资源市场化进行调整和适当干预,多渠道解决水资源问题。
五、结语
治水兴,百业兴。在闽工作的17 年半期间,习近平同志在躬行实践中一步步探索优化科学系统的治水观。从区域层面治理筼筜湖过程中提出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兼顾生态效益;到市域层面的“城市生态建设”,提出要保护利用好生态资源将生态资源转化为经济效益;再到省域层面的“生态省建设”,强调要科学治水,实现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协调统一;延续至中央层面的16 字新时代治水工作的新方向。福建省独特的山水优势为习近平同志的治水实践提供了一个设施完备的练兵场,他离开闽到浙任职并正式提出的“两山”的理论精髓,在福建省的治水实践中皆有了初步体现。新时代治水理念既承载着时代使命又为推进我国治水事业的蓬勃发展谱写了新篇章,从要让福州成为清洁、优美、舒适、安静的沿海开放港口城市,到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美丽中国的新夙愿,[43]丰富的基层治水经历见证了习近平总书记政治事业的每一个新的台阶。要建设好美丽中国必须打好碧水保卫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治水兴水作出详细论述,每次出行考察调研必心系祖国的大江南北,考察足迹遍布祖国各大水利工程。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江河之行,所到之处留下的江河之策,无不体现了他心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江河之情。在习总书记内心中,全力保护水环境、严厉整治水污染,事关民生福祉,让祖国的水更清、更绿、更美,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回顾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时期和地域作出的治水思想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论述,也是新时代我国水利事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历史缩影,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万法归宗、一以贯之,却又鞭辟入里、气贯长虹的博识生态学说。[44]
注释:
[1]鄂竟平:《弘扬新时代水利精神汇聚水利改革发展精神力量》,《学习时报》2019 年9 月16 日。
[2]姜文来、冯欣、栗欣如、刘洋:《习近平治水理念研究》,《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0 年第4 期。
[3]谢小青:《厦门市筼筜湖综合治理工程介绍》,《厦门科技》2003 年第5 期。
[4]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习近平在厦门》,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0 年,第27 页。
[5]卢振彬、杜琦、黄毅坚:《厦门筼筜湖综合治理的生态效果》,《台湾海峡》1997 年第3 期。
[6]厦门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办公室:《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1985 年-2000 年》,福州:鹭江出版社,1989 年,第347页。
[7]卢昌义、谢小青:《从筼筜港到筼筜湖》,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254 页。
[8]庄世坚:《厦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发祥地》,《厦门特区党校学报》2019 年第3 期。
[9]习近平:《福州市20 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福州:福建美术出版社,1993 年,第146 页。
[10][15][17][18[32]]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习近平在福州》,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0 年,第16、18、97、162、439页。
[11][13]康辉平:《福清市闽江调水工程简介》,《水利科技》2014 年第2 期。
[12]康辉平:《福清市闽江调水工程》,《水利科技》2007 年第3 期。
[14]严顺龙:《解了“近渴”解“远渴”》,《福州日报》2008 年1 月14 日。
[16]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习近平在福建(上)》,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1 年,第283 页。
[19]胡熠、黎元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福建的孕育与实践》,《学习时报》2019 年1 月9 日。
[20]戴斯玮、林善炜:《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思考与实践》,《林业经济》2017 年第4 期。
[21]《习近平要求不惜代价根治福州西湖污染》,中国新闻网,2001 年2 月4 日,https://www.chinanews.com/2001-02-04/26/68317.html。
[22]林爱玲、林剑冰、林国富:《木兰溪治理:变害为利 造福人民》,《福建日报》2021 年8 月12 日。
[23]朱波:《绿色发展理念在治理木兰溪中的生动实践》,《区域治理》2019 年第9 期。
[24]林国富:《木兰溪建设美丽中国的生动范本》,《中国水利》2019 年第19 期。
[25][26]朱远、陈建清:《生态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要素与实践逻辑——以福建木兰溪流域治理为例》,《东南学术》2020 年第6期。
[27][31]陈丽珠:《习近平同志五次长汀行》,《福建党史月刊》2015 年第8 期。
[28]陈振明、吕志奎:《<摆脱贫困>中的地方治理思想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 年第1 期。
[29][39]阮锡桂、郑璜、张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近平同志关心长汀水土流失治理纪实》,《中国水土保持》2014年第12 期。
[30]段蕾:《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态政治学阐释》,《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6 年第3 期。
[33][35][38]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习近平在宁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0 年,第79、342、250 页。
[34]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86 页。
[36]陈锦芳:《<摆脱贫困>中的生态文明思想及闽东实践》,《山东党校报》2021 年第7 期。
[37]张云:《宁德市森林资源变化的灰色预测》,《华东森林经理》2004 年第4 期。
[40]张林顺:《青山绿水真的成了人民群众的无价之宝》,《福建日报》2019 年3 月2 日。
[41]涂大杭:《习近平在闽工作期间对三明重要指示精神研究》,《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 年第2 期。
[42]中共三明市委办三明市档案馆:《习近平在三明资料汇编》2007 年第1 期。
[43]李捷:《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问答》,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 年,第15 页。
[44]黄承梁:《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历史自然的形成和发展》,《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9 年第1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