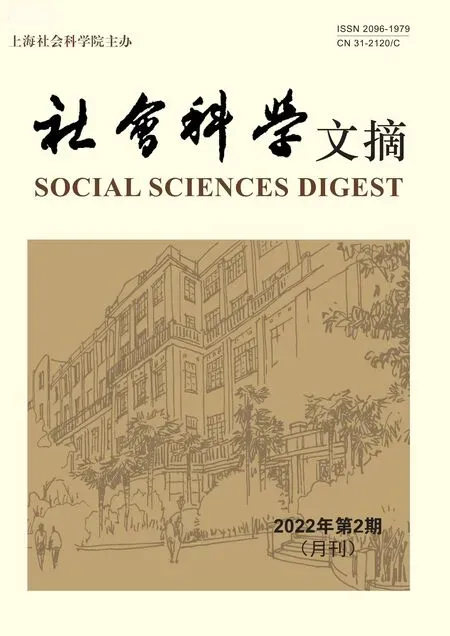后现代叙事的建构:“重写现代性”及其方法论意涵
文/王依娜
20世纪80年代后,叙事分析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后现代哲学、社会学、语言学等学科视角的基础上,逐步转向了后现代叙事分析。助推这一转向的代表人物——法国哲学家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的“重写现代性”不仅为后现代叙事提供了一个建构性的分析视角,还为后现代叙事塑造了一种具体性、可资借鉴的方法论准则。
为什么是“重写”?
“重写现代性”是20世纪80年代后法国社会兴起的一种理解“现代性”的视角,也是一种关于差异、回忆、分析的叙事视角。利奥塔早在1979年的著作《后现代状况》中初步展露了此视角,但他当时并没有提出“重写”这一概念,而是在1986年的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演讲中正式提出了“重写现代性”,他认为“重写现代性”比“后现代性”更贴切地表达了后现代的核心思想,“重写”既表明了“后现代性”的非延续性与非继承性,也表达出一种新的视角与姿态。
“重写”并非意味着一种“前进姿态”。“重写现代性”(Rewriting Modernity)以前缀“re(重)”替换了“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的前缀“post(后)”,这一用词变化体现了利奥塔对于那种以“前”“后”来划分历史时期做法的厌恶。他认为划分历史时期的做法实际上暗含了一种“超越自我”的承诺以及“变成非我”的现代性冲动,而无论是现代性还是后现代性,两者都不能被划分为一个范围清晰的历史实体;另一方面,他试图消除“后现代性是对于现代性的取代或批判”的观点,强调“重写”是一种在现代性事业展开之前人们应当保持的姿态——不仅是要悬置那些被规划的思想,还要保持一种对于未来可能发生事物一无所知的开放姿态。这与西方哲学的后结构主义有所不同,后结构主义认为“后现代性”是与“现代性”所延续的某些传统进行分离或对其进行批判的过程,“重写现代性”并非是简单延续或取代了现代性,也并非是建立一个新的时代,而是在现代性事业展开之前的一种清醒意识、反思精神与开放姿态。
“重写”也并非意味着一种“后退姿态”。利奥塔认为弗洛伊德早期陷入了一种“原始场景”的还原主义,例如,弗洛伊德将神经官能症还原为儿童受到成年人诱惑的场景,而“重写”一方面试图避免这种还原主义,即避免一种无休止的回忆分析过程;另一方面保留了还原主义的无目的性指导过程。“重写”不是对于回忆的无休止分析或对于现象的简单还原,而是基于无意识与感觉的内省和“清算”——以“抵抗那种想象中的后现代性的写法”来重新认识、阐释或解构现代社会的既有特征。研究者需要在此过程中,通过回溯现代性事业中那些不加以区分的、理所当然的诸种理想主义,唤醒那些被遗忘的、潜存在人们无意识之中的“他者”。
综上,正如利奥塔所言,最贴切的“重写”概念就在于前进和后退之间的“双重姿态”。“重写”既不全面否定或取代现代性的“前进姿态”,也不主张进行无休止回忆分析的“后退姿态”;“重写”既不会刻意划分历史时期或推崇某一阶段,也不倡导将当前现象被动地“溯源”为系列的古老情感与原始情境,更不会陷入一种基于现象还原主义的逻辑循环陷阱;而是在无目的前提下重新反思和理解现代性,逐步培养出一种不进不退、时刻内省的反思精神与清醒姿态。
为何重写“现代性”?
“现代性”通常指18至20世纪西方工业社会中的基础主义、普遍主义和本质主义;“后现代性”通常指20世纪末西方后工业社会中的反基础主义、反普遍主义和反本质主义,即对“现代性”的质疑。而“重写现代性”提供了另外一种理解现代性、具有解构主义和建构主义双重特征的视角——以“重写”为准则解构“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并在“重写”方法论指导下反思、批判和重塑“现代性”的特征基础。
利奥塔认为前现代社会的“关系结构”包含一种关于过去与未来的“聚合状态”——不同叙事主体在相同意义结构中共享同一事件及其发生过程,叙事者、听者、故事中的主人公被附着于具体情节之上,因此无论是过去的故事,还是未来的预言,均在当下构成了叙事者当下生命的全部。不同身份的人物通常通过创立、见证、传承等具体过程来建构“神话叙事”的合法性。这种“自我合法化”不仅建立在“讲故事”的基础上,还建立在“讲故事的人”与“听故事的人”的关系基础上。不同成员通常会与“神话叙事”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关联,部落的重要事件(如出生、死亡、婚姻等)在这种关联作用下被不断地复述和记忆,部落内部构建起一种成员之间相互理解、共同生活与集体记忆的“关系结构”。
基于对前现代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叙事结构比较,利奥塔认为前现代的“关系结构”已逐步变成一种“非人”的现代叙事结构。现代叙事崇尚一种去主体化、抽象的、指向未来的理想主义,这不仅构筑了总体性的理想,还要求人们付诸当下行动。现代叙事不仅消解了主体间的关系性,还将叙事者、听者、主人公等主体排除在外,并竭力将不同的主体统统容纳和整合进一个预测和避免未来风险、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系统,现代主体面临着一种被消解并最终完全消失的危机。可见,现代叙事的基本特征可以“重写”为一种总体支配个体、未来支配当下、去主体化的“非人”趋势。作为现代社会最为核心的特征之一,“非人”一方面指资本主义商品化的危机,另一方面指主体心中的“无人之地”,即人们以往依赖于一种基于内心认同感的、让人们成为叙事主体的“共享文化”,而“非人”的现代社会却消解了这种“共享文化”,也正如利奥塔在《非人:漫谈时间》中所指出的“非人”特征:时间的失调、活动去物质化、共同体失稳。
现代社会的“叙事危机”不仅表现为一种“非人”特征,更为关键的是,宏大、统一的现代叙事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转型社会的流变性。现代社会以来的叙事结构愈发地趋向于异质化和多元化,这些新变化不仅表现为一种内部分化、各自分割的趋势,还表现为系统间相排斥、侵蚀与吞噬的割裂关系——“语言孤岛”,其呈现出各语言系统间缺乏共识的现状。而面对日趋复杂和多样的实际变化,现代叙事却并没有适应且难以适应这些新变化,现代叙事既没有通过“关系结构”来自证合法性,也难以通过其他途径来证明其合法性。
利奥塔认为后现代叙事是基于语言异质性和多元性的系统分化,而非基于理性和规则的系统整合。后现代叙事的核心是差异性和谬误性,而不是一致性和系统性,所谓的“共识社会”其实是一场“语言游戏”——各个系统之间既有相互的争夺和冲突,也有形式化、非本质的共同规则。相比于达成一种形式化的规则,那些由于形式化规则所导致的无主体社会往往会更加恐怖——不仅会催生出压制不同意见的恐怖主义,还会形成以理性为基础的西方中心主义视角。
“重写”还意味着后现代叙事是对于现代叙事的质疑。利奥塔认为后现代叙事仅仅呈现了后现代叙事结构的一些新变化以及“现代性”在面对这些新变化的诸种不适应情况,由此后现代叙事表达了一种质疑现代性的需要,如“应当重新反思那些基于普遍理性与规则且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但后现代叙事始终没有回答应当“如何反思”或者应当“秉持什么样的方法来反思现代性”等实际问题,利奥塔认为“重写”可以针对上述问题提供一些更具备建构意义的回答。
综上,利奥塔在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社会中找到了一条叙事结构的逻辑链条,他认为相比于前现代叙事结构,后现代和现代叙事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而现代社会以来的叙事结构不仅脱钩于实际、脱离于主体性,还可能借助纷杂多样的语言系统达成一种包揽所有的、形式化的西方中心主义,导致人们深陷于一种“非人”危机。基于此,利奥塔提出了“重写”的方法论原则。“重写”不仅为质疑和解构现代性的一体性、封闭性和规范性提供了一个较为明确的方法论视角,也为建构现代叙事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考,即如何建构新的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以适应后现代叙事的新变化。
“重写现代性”的方法论原则
“重写”不仅为社会科学提供了一条反思现代性的研究视角与方法路径,同时也为构建一种具备合法性、开放性、反思性和技巧性的后现代叙事方法论提供了一些新的准则。
首先,“重写”是重新确立叙事合法性的基础性前提。利奥塔认为在叙事知识与科学知识的演进过程中,两者呈现出一种源头和派生的关系,即叙事知识是源头,是用客观描述来解释物理世界的话语,科学知识派生于叙事知识,叙事知识是群体对其自身存在、历史与未来所讲述的故事;另一方面,两者也在关系变迁中相互影响、相互建构,随着科学知识越来越脱离于叙事知识,叙事知识沦为权威、成见、公认等观念的“剩余物”,这个变化不仅导致科学失去了社会性的基础,还导致社会关系朝着“外在化”方向发展。因此,“重写”意味着叙事知识作为科学知识的源头和基础,其基础性地位与合法性基础需要被明确、被着重。
其次,“悖谬逻辑”是“重写现代性”的核心准则。“重写现代性”主张从非先验的特殊性上升到普遍性的路径,但拒绝将差异归纳为单一、可被加总的系统,也拒绝将普遍法则应用于特殊个体。利奥塔认为知识的合法性并不来源于共识、标准,而来源于呈现差异、悖论、突变等现象的“悖谬逻辑”,这不仅暗示了一种基于差异的非线性、反身性或递归形式的导向,也暗示了一种非本质主义、去中心化、非统一性的视角。基于这种逻辑,研究者应当跳出普遍性和必然性的陷阱,转向关注对大叙事构成冲击的、具有节点性质的历史记号,以及不确定、超出预测的现象,关注这些记号和现象对于社会的激活作用,发展一种突变、非连续和开放的理论体系。
再次,“反思性”是“重写现代性”的重要指向。利奥塔认为“重写现代性”必须进行反思性判断,这既是因为反思性判断适应了后现代叙事的诸种新变化,也是因为反思性判断能避免“为创新而不断创新”或刻意制造出某些模仿性、外在性的实体。具有“反思性”的“重写”意味着研究者把“解构”作为“建构”的基础,关注事件破坏既定法则所呈现的可能性,寻找新的规则和行动方式,更重要的是排除现代人对于普遍理性的欲求,避免人们对差异做出过早判断。
最后,“重写现代性”还意味着一种基于技巧和艺术的叙事取向。利奥塔借鉴了弗洛伊德的“修通”方法——通过对于个体联想和记忆的修正过程,发掘被某种普遍主义叙事所抑制的个体性差异叙事,从而找到主体的不同行动意义并由此呈现问题的本质。这意味着研究者需要始终关注那些不能被总体同化的个体行为,让研究对象进行积极地自我呈现和自我剖析,同时意味着“重写式”的分析并不依靠于既有的知识,而是依靠于技巧、艺术与场景,正如利奥塔所言:其结果不是给一个过去的要素下定义,而是给思想营造一个场景要素。因此,“修通”不仅像是一个永无终结的任务,还像是一本可以被重复阅读并不断从中获得新体会的名著。可见,“重写”既不是刻板的“默写”,也不是忽视宏观历史和具体情境的“改写”,而是一种基于情境再现的真实记录。
综上,“重写”并不旨在抹掉“现代性”的印记,也不旨在发掘出一套新的体系或工程,而旨在开拓出一种思维方式、研究准则与分析视角——尊重主体间的差异性,培养主体的反思意识与批判精神,培育研究者的分析能力与技巧,由此唤醒更多类型的主体参与到“重写现代性”事业中去。
结论与讨论
在严格意义上,试图超越现代理想主义、建构新的后现代叙事方法论的“重写现代性”并没有提供一套成型的方法论体系,也没有提供一套成熟的行动计划。“重写现代性”经常被批判为一种虚无主义、相对主义或无政府主义,批判者认为利奥塔的“悖谬逻辑”不仅不能帮助群体从“自在”转向“自为”,还会助推学术与政治领域中的无政府主义;“重写现代性”过分看重了差异性,因此它不仅轻视了不同群体和文化间达成一致的努力,还否定了批判家能够创造一个关于社会公正的共识,但正因为“悖谬逻辑”处于既有的知识系统内而不是系统外,人们才能得以认识和理解它。这些批判均表现了对“重写现代性”作为一种方法视角的质疑。
但毋庸置疑,“重写现代性”作为一种思维方式、表达方式与研究准则,为当下理解与分析“现代性”提供了一个新颖视角:坚持具体事件分析、差异分析和类型分析,采取修通、多元话语分析等混合方法探索行动、机制与结构的状态,这些视角不仅对于捕捉流动性社会特征、解释转型机制、分析社会变迁史更具有实用价值,也在解释新现象、保持理论开放性、推进理论创新等方面提供了颇多的建构性启发。
后现代叙事常被理解为一种缺乏建构性的批判主义,而“重写现代性”却提供了一个理解后现代叙事方法论的建构性视角。“重写”意味着“后现代”不是与“现代性”截然对立的一种批判主义,而是糅合了解构主义和建构主义双重意涵的视角;“重写”以差异性、突变性、多元性为基本原则,以关注特殊历史事件、探索多元的解释框架为主要过程;“重写”既能在继承中解构既往的、不符合实际的现代叙事结构,也能在某种程度上建构新的后现代叙事方法论准则。因此,有必要重新理解“重写现代性”的多重意涵,以“重写”为视角探索更为具体、变化且鲜活的社会事实,以“重写”为准则深耕更为广阔、切实且人性的后现代叙事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