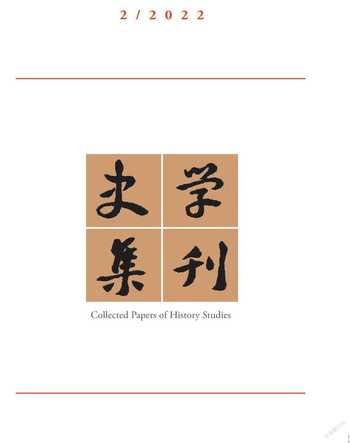20世纪美国残疾人就业权利的缘起、制度化与困境
摘 要: 在某种意义上,20世纪的美国历史也是一部残疾人的民权运动史。如果说经济大萧条初步唤醒了残疾人的就业权利意识,两次世界大战开启了美国伤残军人康复与就业援助的机制建设,第三次科技革命则加速了残疾人就业权利保障的制度化进程。从公共就业计划、残疾人社会保障保险计划、补充收入保障计划,到《1973年残疾人康复法》,再到《1990年美国残疾人法》,残疾人的就业权利经历了被漠视、依附于福利救济、向实现平等权利转变等阶段,给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领域留下了诸多挑战和值得思考的问题。由于法律在解决社会问题上存有局限、残疾人对各种福利保障资助的依赖、根深蒂固的偏见等因素,美国残疾人争取平等权利之路仍任重而道远。
关键词: 就业权利;职业康复法;残疾人社会保障保险计划;补充收入保障计划;美国残疾人法
美国残疾人就业难的问题由来已久。作为一种民权诉求,残疾人就业权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引起社会的关注,而其得到制度保障的历程更加漫长,直到《1990年美国残疾人法》的颁布才实现了残疾人就业权利的制度构建。正因如此,美国学界对残疾人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直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残疾人民权运动的发展,学者们才真正聚焦残疾人及其追求权利的历史。①
至21世紀初,美国学者依然认为,由于“社会否认残疾人的价值”,使其与任何少数群体一样被视为“他者”,也由于历史常常只是成功者的历史、英雄的历史,“我们在书写历史的时候故意将他们(残疾人)抹去了”。②因此,有必要对美国残疾人争取平等就业权利的运动、残疾人就业权利制度化等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本文拟以残疾人就业权利意识的觉醒为切入点,分析20世纪残疾人就业权利制度化的进程及困境,以期深化相关领域的研究。
一、经济大萧条与残疾人就业权利意识的觉醒
20世纪以前,美国在社会和政府层面对残疾人问题不甚关心。在殖民地时代,“残疾人被禁止在13个殖民地的城镇和村庄定居,除非他们能证明有能力独立养活自己”。不同时期的移民政策“实际上禁止身体、精神或情感有缺陷的人进入美国”,“由于流行‘残疾等同于无能’的观念,残疾的存在似乎足以剥夺一个人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在家庭中,残疾人被隐藏起来,不被承认,甚至通过不提供生活支持的方式任其死去”。 Frank Bowe,“An Overview Paper on Civil Rights Issues of Handicapped Americans:Public Policy Implications,” in Civil Rights Issues of Handicapped Americans:Public Policy Implications,Washington,D.C.:U.S.Commission on Civil Rights,May 13-14,1980,pp.8-9.在残疾人的内心,其自我认知不可避免地反映了普遍的社会态度,使他们甚至不敢尝试自力更生。即使在20世纪初,对于身体残疾的人来说,外出就业、在社会上有所作为也不是其核心诉求,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最渴望得到直接的物质支持。直到经济大萧条和罗斯福新政时期,美国人对世界和自身的认识发生了深刻变化,对人权意识的强调尤为突出,使残疾人的就业权利问题浮出水面。
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几乎横扫美国所有经济领域,导致失业人口激增。美国在1929年春季的失业人数为280万,1931年春季达到800万,1933年春季则达到1300万至1500万。 William P.Quigley,“The Right to Work and Earning A living Wage,”New York City Review,Vol.2,No.2(Summer 1998),pp.144-145.同时,在岗工人的工作量和实际收入大幅缩水,例如西弗吉尼亚煤矿每吨煤卖75美分至1.25美元,而矿工每周工作2天至4天,每天净收入从80美分到1美元不等,其工资经常低于生活成本,入不敷出的状况比比皆是,以至于矿工联合会的领袖约翰·刘易斯痛陈工人及其家属的生活还不如家畜。 Irving Bernstein,The New Deal Collective Bargaining Policy, Berkeley:Publishing House,1950,p.16.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和社会上众多有识之士认识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与民众的就业权益紧密相关,严重失业会使经济形势更加恶化,也会危及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宁。罗斯福总统推出公共就业计划,以保障美国有就业愿望和能力的人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赚取一份“体面的工资”,使自己及家人过上“体面的生活”。 高嵩:《“体面的工作”:富兰克林·罗斯福就业权利思想与实践》,《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第44-50页。就业权利成为与生命、自由、财产等美国人奉为圭臬的人权紧密相连的一部分。
随着整个社会对就业权利的重视,残疾人也开始为自己的就业权利采取联合行动。30年代于纽约成立的残疾人联盟(the League of the Physically Handicapped)及其活动引起了媒体、社会和政府的关注。该联盟的大多数成员遭遇了因儿童脊髓灰质炎、脑瘫、心脏病、肺结核以及意外事故而导致的各种残疾。他们确信,身体残疾是他们求职时遭到拒绝的原因。尽管工程进度管理局(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实施了公共就业计划,但是由于残疾人的记录被盖上了“PH”(physically handicapped,身体残疾)的印章,因此无法获得进入公共就业领域的资格。这种困境让残疾人觉得自己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少数人。为了主张残疾人的就业权利,他们发起两项活动,引发了社会关注。首先,联盟六名核心成员于1935年5月29日至6月6日进入并占领紧急救济署(Emergency Relief Bureau)驻纽约办事处负责人的办公室,静坐抗议并提出如下要求:必须立即向联盟成员提供50个工作岗位,以后每周再提供10个工作岗位;已婚人员的月工资不得低于27美元,单身不得低于21美元;残疾工人必须与非残疾工人在一起工作,而不是被隔离开来。 Doris Zames Fleischer and Frieda Zames,The Disability Rights Movement:From Charity to Confrontation,Philadelphia,PA:Temple University Press,2001,p.5.该组织及其示威、静坐和绝食等行动得到《纽约时报》等媒体的报道, “Crippled Pickets ‘Torture’ Harris,” New York Times,June 21,1935,21.激励了他们的后续努力,最终成功消除了“PH”类别标签,为该组织成员及纽约市其他残疾人争取到了工程进度管理局提供的工作。
其次,联盟成员于1936年和1937年两次前往华盛顿,使更多的人关注到全国范围内残疾人遭遇的就业歧视现象。1936年5月,在与工程进度管理局局長哈里·霍普金斯(Harry L.Hopkins)会面时,他们坚持要求为残疾人制定一个永久性的就业计划,进行全国性的人口普查来验证联盟的论点,即存在许多身体残疾但可以胜任某种工作的潜在劳动者。《华盛顿星报》在当时的报道中认为,联盟成员寻求的“不是同情,而是一个具体的计划,以结束工程进度管理局项目对残疾人的就业歧视”。 Frances Lide,“Girl Leader of Cripples Asks Plan to End ‘Discrimination’,” Washington Star,May 11,1936.美国学者认为,该联盟及其活动“打破了关于残疾的固有观念。他们不是要唤起人们的怜悯,而是受愤怒的驱使,冒着不被社会认可的风险,秉持与其他失业残疾工人团结在一起的理念,与不公正的限制其工作机会的歧视做斗争”。 Doris Zames Fleischer and Frieda Zames,The Disability Rights Movement:From Charity to Confrontation, p.7.
由于联盟的很多成员解决了就业问题,加之社会上关于残疾人联盟受到社会主义者的控制等不利舆论的出现,1938年该联盟解散。尽管残疾人联盟存续的时间较短,残疾人主张就业权利的呐喊和运动也未能触及制度构建的层面,但是它通过行动展示了残疾人联合起来争取就业权利的意义。因此,20世纪30年代成为美国残疾人就业权利意识觉醒的时代。
二、两次世界大战与促进伤残军人康复就业的机制建设
两次世界大战为美国残疾人就业权利的发展提供了契机。美国政府努力为残疾军人谋福利,出台了伤残津贴、康复和就业援助等政策,为20世纪下半叶残疾人就业权利的制度化提供了必要准备。
伤残军人的安置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既包括赋予他们荣誉,竭尽全力医治他们身体上和心理上的创伤,又要为其重返就业领域做准备。陆军部卫生局局长威廉·戈尔加斯(William Gorgas)将军根据战时调查,于1917年底指出,伤残军人的康复包括“培训他们,使其尽管身体残疾,也能再次成为生产者”。他建议所有伤残军人在退伍前留在军队,完成身体功能的完全恢复;为他们建立职业学校、工厂、训练营地,根据伤残的性质对其进行必要的职业训练。1918年6月3日,他在新拟定的伤残军人康复计划中进一步指出,士兵的康复应是一种包括手术和术后功能恢复的过程;伤残军人在医院接受疾病和损伤的物理治疗(physiotherapy)的同时,由教育部门开发“治疗性职业”(curative occupation),让他们“以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形式从事治疗性职业”。 William Gorgas,“Report of the Surgeon-General(United States Army,1917),”reviewed by A.D.Hiller,in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Vol.8,No.3(March 1918),pp.242-243; A.G.Crane, The Medical Depart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the World War,Vol.XIII,Part One:Physical Reconstruction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Washington,D.C.:Office of the Surgeon General,Department of War,1927,pp.28-30,39-40,PDF be available at Hathi Trust Digital Library,https://babel.hathitrust.org (2018-08-01).戈尔加斯将军没有具体定义何为“治疗性职业”,只是提出教育部门应该按照“现代路线”开发治疗性职业,提供必要的人员和设备。通过“物理治疗”和“职业治疗”(occupational therapy)相结合的方式,帮助伤残军人恢复身体功能,重新回到常人的生活状态。如此复杂的工作需要政府采取行动,戈尔加斯将军的计划和建议对陆军部和国会相关部门产生了影响,相关法律得以制定。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联邦政府采取的影响较大的相关政策有四项:第一,1918年6月27日通过的《1918年职业康复法》创造了一个新理念,即联邦政府不仅要向残疾军人提供生活费,而且要为他们提供培训,帮助他们克服伤残造成的就业能力的不足,获取新技能,以期退伍后找到新工作; U.S.Congress, Public Law 65-178,S.4557,Vocational Rehabilitation of 1918(June 27,1918),in United States Code,Congress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News,Vol.1,65th Cong.,2nd Sess.,St.Paul:West Publishing Co.,1918,pp.617-620.该法又被称为《史密斯—希尔斯士兵康复法》(The Smith-Sears Soldiers Rehabilitation Act)。第二,由政府向伤残军人提供就业援助的做法,在战后惠及非军人群体。《1920年平民职业康复法》授权联邦政府推出第一个全国性残疾人就业援助计划,联邦政府以50%的配比向各州康复机构提供联邦资金,为那些非战争原因致残的残疾人提供咨询、职业培训和就业安置服务等援助; Employer Service Strategies in Rehabilitation:New Approaches to Placement,Eighteenth Institute on Rehabilitation Issues Memphis,Tennessee October 1991,Arkansas University,p.8.《平民职业康复法》(Civilian Vocational Rehabilitation Act)又称《史密斯—费斯职业康复法》(The Smith-Fess Vocational Rehabilitation Act)。第三,《1943年职业康复法修正案》扩大了职业康复服务的范围,将患有精神疾病和智力迟钝的群体纳入其中,以解决因战时劳动力严重短缺而出现的非技术岗位劳动力不足,同时规定只要伤残退伍军人还能胜任入伍前的工作,企业必须重新予以雇用; Hellen Baker,“Industry’s Plans for Absorbing the Disabled Veteran,”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Vol.239,May 1945,p.128.《1943年职业康复修正案》又称《巴登—拉福莱特康复法》(The Barden-LaFollette Rehabilitation Act)。第四,1944年11月27日,罗斯福总统发布9503号行政命令,在伤残退伍军人中实施公共就业计划,完成职业培训的伤残军人依据培训内容可以在政府中得到相应的工作,并鼓励更多的培训合格的伤残退伍军人加入公务员队伍。 Franklin D.Roosevelt,Executive Order 9508 on the Seizure of Montgomery Ward Co.Properties (December 27,1944).Online by Gerhard Peters and John T.Woolley,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node/210609(2017-06-01).
重新雇用伤残军人并非易事,对参与各项康复计划的机构和企业的业务培训、安全设施、员工管理等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学者認为,大机构、大企业由于实力雄厚更容易满足上述要求,而一些小企业在执行这些法律方面的确面临着严重困难。 Hellen Baker,“Industry’s Plans for Absorbing the Disabled Veteran,”p.128.此外,雇用伤残军人还面临着许多问题:企业仅需要雇用负伤归来的老员工,还是需要对其他伤残军人敞开大门?在伤残军人的培训上,政府和企业各自应承担什么责任?用什么标准考核伤残军人的工作?日后在调岗、裁员时如何处理伤残军人?如何在实施优待政策的过程中维护伤残军人的尊严?对此,企业和政府进行了诸多探索,美国伤残军人就业权利在实践中得到不断重视。
伤残军人是残疾人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和公众对伤残军人就业权利的讨论,不可避免地推动了对整个残疾人群体的关注。因此,其他残疾人的就业权利也逐渐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所接受。
许多归国的因伤退伍军人和战时填补劳动力空缺的残疾人,因二战结束后军人回归工作岗位而陷入了失业困境。在美国就业服务局登记的残疾退伍军人约22.5万人,其他残疾工人7.5万人,都在寻找工作机会。为了主张和维护就业权利,残疾人再次联合起来游说总统和国会,迫使杜鲁门总统于1946年9月宣布,10月6日至12日为“全国雇用残疾人士周”,旨在为残疾退伍军人和其他残疾工人寻找合适的就业机会。他指出,“尽管许多政府机构和私人组织参与了这一活动,尽管我们所有人都很关注,但只有这个国家的雇主才能应对这一挑战”。杜鲁门要求每一位雇主提出就业需求清单,就业服务局为残疾退伍军人和其他残障工人提供咨询并推荐给雇主,通过雇主和就业服务局的合作,“将有用的公民推荐到工作岗位上,残疾人可以做得像健康人一样好,甚至更好”。 Harry S.Truman,Statement by the President on Employment of Disabled Veterans and Other Handicapped Persons (September 12,1946).Online by Gerhard Peters and John T.Woolley,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node/232077(2018-07-01).“全国雇用残疾人士周”(National Employ the Physically Handicapped Week)于1988年改为全国残疾人就业意识月(National Disability Employment Awareness Month)。“全国雇用残疾人士周”的设立,标志着残疾人的就业问题终于成为美国政府和社会重视的全国性议题。尽管大多数美国人将20世纪六七十年代视为民权运动和女权运动的时代,但是实际上,在30年代残疾人权利意识开始觉醒,到50年代系统性的残疾人政策开始逐步制定与实施。1973年,《残疾人康复法》得到实施,真正成为一项残疾人就业援助政策,发挥了保障残疾人就业权利的作用。
三、科技革命后工伤事故的增加与解决残疾人就业问题的不同路径
尽管第三次科技革命极大地解放了劳动力,改善了工作条件和生产环境,但工作中各种意外还是不断出现,许多从业者不幸落下残疾。美国工伤致残现象增多,工伤人口翻倍增加,使因工伤残和伤残劳工成为不容忽视的问题。
美国政府统计数据显示,第三次科技革命初期,因工受伤的美国人在1945年约为202万,1946年约为206万,1947年约为206万,1948年约为202万,1949年约为187万。 数据根据美国政府资料统计,下文同。U.S.Bureau of the Census,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1950,Washington,D.C.:GPO,1950,p.206.这组数据说明,20世纪40年代后期美国每年出现两百万左右的伤残劳工。第三次科技革命基本完成后,工伤事故是否减少?答案是否定的。1970年至2000年间,美国每年新增工伤人数,除1985年有过短暂的小幅下降之外,一直保持稳中有升的态势。1970年至1985年,每年工伤新增人口保持在200万至220万之间;90年代以后,迅速飙升至360万至390万,较之前增长了接近一倍。 U.S.Bureau of the Census,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2006,Washington,D.C.:GPO,2006,p.433.通过两个时期的数据对比不难发现,20世纪中期以后,科技进步没有阻止工伤事故和工伤人数的增加,反而加剧了工伤问题的严重性。
无疑,工伤事故的飙升与美国经济和就业形势的变化有密切关联。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经济长期萎靡不振,就业率不高,在岗劳动力数量少,因此工伤事件及受伤人数相对较少。而1990年以后,美国经济重新焕发活力,就业率大幅提高,在岗劳动力数量随之增加,工伤事件和受伤人数相应增多。
比较分析20世纪下半叶工伤人数在不同行业的分布与变化,可以窥得工伤事故的行业特征。1949年到1999年,全美新增工伤人数不断增长的同时,不同行业的受伤人口呈现大相径庭的变化。首先,建筑业、制造业、交通和公共服务业、贸易行业的工伤变化,与全国总体趋势保持一致。建筑业1949年新增工伤人数18.3万,1999年新增47万,同比,制造业工伤人数由38.1万增至63万,交通和公共服务业工伤人数由19.9万增至38万,贸易行业工伤人数由32.9万增至75万,都增长了一倍左右。其次,农业和采矿业工伤人数的变化与整体趋势背道而驰,不增反降。1949年农业新增工伤人数34万,1999年锐减至13万,同比采矿业工伤人数由7万降至2万。最后,受伤人口的大幅增长主要集中于服务业和政府公职人员中。1949年,服务业与政府公职人员的工伤问题相对较少,因此统计部门将它们与其他行业归为一项,统称为“服务业、政府公职人员、其他行业”,工伤人数共新增36.8万;但是到1999年,服务业和政府公职人员的工伤统计被单独列出,分别为94万和58万,合计152万,是1949年数据的4倍有余。 U.S.Bureau of the Census,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1950,p.206; U.S.Bureau of the Census,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2002,Washington,D.C.:GPO,2002,p.408.这组数据说明,在20世纪下半叶,尽管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生产自动化水平的提高,一些传统行业如农业和采矿业的工伤事故和工伤致残人员大幅减少,但随着一些新兴产业,特别是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和政府机构、职能的扩大,工伤事故大增,因工致残的人数急速飙升。
因工伤事故而致残的人口大量出现,逐渐成为引人关注的社会问题。以1945年为例,工伤事故中死亡和永久性完全伤残的人数新增1.8万,永久性部分伤残的人数新增8.8万,暂时性完全伤残的人数新增191.4万。由于很多工伤事故发生在伤者的青年时代,伤残带来的问题会持续困扰其数十年。在工作中遭遇永久性部分伤残的人口,1945年新增8.8万,1946年新增9.2万,1947年新增9.0万,1948年新增8.7万,1949年新增8.0万, U.S.Bureau of the Census,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1950,p.206.美国劳工部进行工伤数据统计时使用如下概念:“永久性完全残疾”指的是受伤的人将永远丧失工作能力;“永久性部分残疾”指的是受伤的人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休养将恢复工作能力,但会留下终身残疾;“暂时性完全伤残”指的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病人有希望完全康复,但在治疗期间会丧失工作能力。 5年时间累计新增43万多。无论是永久性完全伤残还是永久性部分伤残,都会导致残疾人数不断增加。暂时性完全伤残虽然有希望得以痊愈,但也会让伤者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过上与残疾人相似的生活,使他们切身感受到残疾人的痛苦。残疾人及其亲人的遭遇,使社会上同情残疾人的力量不断增强,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
严重的工伤事故和劳工伤残现象,以及20世纪五六十年代残疾人权利运动的发展,令美国学界不得不关注残疾人问题。围绕残疾人问题的属性和解决途径,逐渐形成两种对立的观点。第一种观点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认为残疾是一种客观的疾病或缺陷,即“个人问题”和“医学问题”;由于残疾人和健康人的区别在于前者存在身心障碍,因此解决残疾人问题的关键是康复,通过医疗手段最大限度地治疗残疾人的疾病,恢复其工作能力,帮助残疾人最大程度地向健康人靠拢。如果这一目标达成,所谓残疾人的问题就不再是问题。 Harlan Hahn,“Civil Rights for Disabled Americans,” in Alan Gartner and Tom Joe,eds., Images of the Disabled,Disabling Images,pp.181-203.第二种观点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后,认为残疾既不是“个人问题”也不是“医学问题”,而是一种“社会问题”。他们的依据是,在美国社会,残疾人占总人口的1/5,许多人在过去并不被认为是残疾人,但是后来被定义为残疾人,说明残疾并不是殘疾人的一种客观状态,而是一种社会的主观认知。美国第一所为残疾人设立的大学——加劳德特大学的汉娜·乔纳从历史的维度,分析美国旧南部严格的等级制度和人身依附文化,指出尽管残疾人已经成为公众心目中的累赘,但一部分南方聋人拒绝接受这种观念,他们深信自己是有能力和完整的,为自己感到骄傲,通过不断奋斗在各自领域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在汉娜看来,残疾不是人的一种缺陷,而是人的一种“特征”(characteristic),与“胎记、疤痕、酒窝或身体上的其他标志”一样,与“不寻常的服装、典型的举止”一样,是社会中的一种普遍现象。 Hannah Joyner,From Pity to Pride:Growing Up Deaf in the Old South,pp.6,39.与汉娜的观点相接近,致力于帮助残障儿童的社会活动家凯西·斯诺认为“残疾是人类经历的自然组成部分”,“与性别、种族和其他特征一样,残疾只是人类的许多自然特征(natural characteristics)之一”,“残疾是自然的(disability is natural)”。 Kathie Snow,Disability is Natural:Revolutionary Common Sense for Raising Successful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Woodland Park,Colo.:BraveHeart Press,2001,p.1.PDF be available at http://www.disabilityisnatural.com/(2020-08-01). 她们的观点在美国影响广泛,美国国会在修订《2004年残疾人教育法》时明确宣告“残疾是人类经历的一个自然组成部分”,“残疾决不会削弱一个人参与社会或为社会做贡献的权利”。 U.S.Congress,The 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Act of 2004.Be available at https://sites.ed.gov/idea/statute-chapter-33/subchapter-i/1400/c/1(2018-08-01).
以上两种观点,分别将残疾与医学、残疾与社会紧密联系起来,对于理解残疾人的就业权利具有不同的影响。如果残疾是一个医学问题和个人的问题,政府就只需要采取福利性的救济措施,帮助残疾人进行康复,残疾人福利政策的制度化因此成为必要之举。如果残疾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是人类的自然特征之一,政府就有责任在政治、思想、教育等各个方面进行全面改革,以实现残疾人的一切平等权利,因此主张和维护平等就业权利的制度构建就变得不可或缺。虽然在美国社会的争论中,残疾与医学、残疾与社会分别是两种解决残疾人就业的思路,但是在美国的实践中,残疾与医学、社会的关系交叉而行、相互影响,不同时期各有侧重。
四、福利模式的制度化与残疾人就业权利的有限性
有美国学者将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残疾人政策称为“医疗模式”或“康复模式”,即通过医疗手段最大限度地治疗残疾人的疾病,帮助他们尽可能地恢复身心健康,使其尽量接近健康人的状态。 Susan Burch and Ian Sutherland,“Who’s Not Yet Here? American Disability History,” Radical History Review, Vol.2006,Issue 94(Winter 2006),p.128.而笔者认为,无论是从医疗福利的视角,还是从就业权利的角度看,20世纪中叶之前,美国政府对残疾人的康复、救济与就业一直持漠视态度,尽管美国政府对残疾军人的康复和就业施以援助,但是其政策目标不是为了主张他们的就业权利,而是为了补偿他们战时的牺牲和荣誉。20世纪中叶后,美国的残疾人就业政策经历了两个阶段,其中1954年至1990年之间为第一阶段,美国政府实施以救济为主、救济与就业兼顾的福利性政策,使残疾人获得了有限的就业权利,是残疾人就业的福利模式制度化时期。
在这一阶段,残疾人就业政策及其福利性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项政策中。
第一,根据《1954年社会保障法修正案》和《1956年社会保障法修正案》,实施“残疾人社会保障保险计划”(Social Security Disability Insurance), U.S.Congress,Public Law 880,H.R.7225,Social Security Amendments of 1956 (August 1,1956),in United States Code,Congress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News,Vol.1,84th Cong.,2nd Sess.,St.Paul:West Publishing Co.,1956,pp.807-856.由社会保障局负责,对因工伤事故致残的人群提供一段时间的经济保障。该计划最开始只为50~64岁因工致残的人,以及有未满18岁残疾子女的退休、生病工人提供残疾福利。1956年至1960 年,有约559 000人领取残疾福利,平均福利金额约为每月80美元。 U.S.Congress,Public Law 84-880,H.R.7225,Social Security Amendments of 1956(August 1,1956),p.807;John Bound and Richard Burkhauser,“Economic Analysis of Transfer Programs Targeted on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in O.Ashenfelter and D.Card,eds.,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Vol.3,Chapter 5,1999,pp.3417-3528.根据《1960年社会保障法修正案》,“残疾人社会保障保险计划”的受益群体得到扩大,任何年龄因工致残的工人及其家属都可获得残疾福利。 U.S.Congress,Public Law 86-778,Social Security Amendments of 1960 (September 13,1960),pp.924-925,PDF be available at https://www.ssa.gov(2018-07-01).
该计划在实施中遵循一个原则——申请者工伤时的年龄、工龄、工伤前的就业状况、参与社会保险的情况都与残疾福利挂钩,要求申請者曾经的就业状态必须在一定期限内符合社会保障覆盖的范围。 Richard V.Burkhauser and Mary C.Daly,“U.S.Disability Policy in a Changing Environ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16,No.1(Winter 2002),p.215.也就是说,该项目的受益者必须曾经有稳定工作,长期缴纳保险,且因工作而致残。同时,残疾福利的多少因人而异。以往工作的时间长、曾经的收入高、缴纳的社会保险金高,获得的资助力度便相应较大。例如,1996年因工致残且年满50岁的人,如果他自22岁起一直处于就业状态,并且收入等于联邦最低工资,便可以获得一年6828美元的残疾福利金,即每月569美元。如果他有妻子和一个孩子需要抚养,则福利金为一年9828美元,即每月819美元。 John Bound and Richard Burkhauser,“Economic Analysis of Transfer Programs Targeted on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pp.3446-3447.
从资助情况看,该计划似乎仅仅是一个针对伤残工人的救济项目,与他们的就业权利关系不大。实际上,这恰恰体现了美国早期残疾人政策的特点:救济与就业兼顾,但以救济为主。这一政策对伤残工人再就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疾病治愈后的持续资助上。根据规定,即便受助者的伤病已经治愈,残疾人社会保障保险计划的资助也不会立刻停止,而是会维持一段时间,帮助他们度过再就业初期充满不确定性因素的阶段。例如,1998年,该计划向受助人提供长达45个月的过渡期,其中前9个月是无条件试验期,即便受助人能够立刻融入新工作,资助也不会停止。在无条件试验期结束之后进入观察期,如果受助人工作状况良好,每月收入在联邦担保收入之上,资助将停止,否则资助还将继续。 John Bound and Richard Burkhauser,“Economic Analysis of Transfer Programs Targeted on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p.3448.
这种持续资助的福利政策,在伤残劳工治疗——基本治愈后走出病房走向社会、适应身体改变后的自己和全新的工作环境——这一充满不确定因素的过程中,为他们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免除后顾之忧、帮助其再就业,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二,根据《1972年社会保障法修正案》,实施“补充收入保障计划” (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由社会保障局负责,授权联邦和州政府为低收入人群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 U.S.Congress,Public Law 92-603,H.R.1,Social Security Amendments of 1972 (October 30,1972),p.1465,PDF be available at https://www.ssa.gov(2018-05-01).
美国学者研究发现,残疾人社会保障保险计划的受助人整体上具有以下特征:年纪较大、男性、非西语裔白人、已婚,至少具有高中以上学历等。 John Bound,“Richard Burkhauser and Austin Nichols,” Tracking the Household Income of SSDI and SSI Applicants,Michigan Retirement Research Consortium Working Paper,2001,p.11.那些被社会保障保险计划拒之门外的申请者,由于受教育水平更低、更缺乏资金积累等原因,在遭遇伤残时的境况更为悲苦。而“补充收入保障计划”就是要弥补残疾人社会保障保险计划覆盖范围不足的问题。这两个计划的不同在于,社会保障保险计划的福利资助以曾经缴纳社会保险金为前提,而补充收入保障计划不以缴纳社会保险金为前提,主要提供现金福利。
补充收入保障计划与残疾人就业的联系,集中体现在给付标准的计算上。该计划现金福利的标准是帮助受助人和受助家庭的收入达到联邦担保收入的标准。以1999年为例,个人最高联邦担保收入为每月500美元,夫妻两人每月769 美元。在实际执行上,发放金额不对所有受助人“一刀切”,不是直接发放500美元或者769美元,而是根据受助人的收入确定资助金额,联邦发放的福利金额等于联邦担保收入减去受助人的可计算收入。一个人的收入分为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两部分,非劳动收入主要指从政府或其他机构获得的福利与资助。该计划规定,在核算联邦福利金额时,每一位受助人皆可以享有收入计算减免额度,即每月20美元的非劳动收入和65美元的劳动收入不计算在其月收入中;
当受助人的收入超出这个减免额度时,其非劳动收入如实计算,而超出的劳动收入按照50%的比例计算。Arthur Jones,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 and Its Noninstitutional Recipients:July 1997 and 1999,Issued August 2003,U.S. Census Bureau, Washington,D.C.,p.2,PDF be available at http://www.census.gov/prod/2003pubs/p70-90.pdf(2018-09-01).联邦担保收入政策的本意是由联邦政府设定一个能保障公民基本生活水平的固定收入标准,当受助人的收入没有达到政府规定的标准时,其差额由联邦政府予以补全,使个人收入和各项福利之和至少达到联邦担保收入的标准。但是该计划计算收入和发放资助的方法实际上使联邦担保收入的标准动态化了,使个人收入和各项福利之和超过了联邦担保收入的标准,以1999年为例,相当于将其上限由500美元提高到520~1085美元之间。
这意味着,受助人如果在接受“补充收入保障计划”资助期间积极参与工作,他的收入不仅完全可能超过联邦担保收入,而且他越努力,收入就会越高。
因此,“补充收入保障计划”是一项奖勤罚懒、激励残疾人就业的福利政策。它体现的是政府对社会成员的救助义务,帮助每个人在遭遇伤残时仍然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由于其计算收入和福利金额的方法鼓励残疾人的再就业,故其体现的就业权利属性较为明显。
2000年,共有770万人获得了联邦政府的伤残资助,其中50%的人仅接受残疾人社会保障保险计划的资助,37%的人仅接受补充收入保障计划的资助,13%的人同时接受两项计划的资助。为实施这两项计划,联邦政府共投入760亿美元,其中560亿用于残疾人社会保障保险计划,200亿用于补充收入保障计划。 Richard V.Burkhauser and Mary C.Daly,“U.S.Disability Policy in a Changing Environment,” p.216.
第三,制定《1973年残疾人康复法》,在全国实施“全面的、持续的”职业康复服务计划,帮助残疾人,特别是那些处于最“严重伤残”状态的残疾人,为他们重新走入就业领域做好准备。 U.S.Congress,Public Law 93-112,H.R.8070,Rehabilitation Act of 1973(Original Text),September 26,1973,Washington,D.C.:GPO,pp.2,7,PDF be available at https://www.gpo.gov/fdsys/pkg/STATUTE-87/pdf/STATUTE-87-Pg355.pdf(2015-08-01).“严重伤残”包括截肢、失明、癌症、脑瘫、遗传性胰腺病中的囊性纤维化、耳聋、心脏病、偏瘫、精神发育迟缓、精神疾病、多发性硬化、肌肉萎缩、中风、癫痫、四肢瘫痪以及其他脊髓疾病、肾功能衰竭、呼吸和肺功能障碍等。这是以救济为主、救济与就业并重的残疾人政策福利模式制度化的最后一个重大举措。
前文提到的第一项与第二项举措,是在涉及老年人、妇女、儿童等社会福利的改革中,因触及残疾人的利益而诞生的。这种局面随着《1973年残疾人康复法》的出台而结束。从名称上看,这项法律的关键词是“康复”,但其帮助残疾人再就业的指向性十分明确。该法授权联邦拨款,支持各州政府、企业、非营利性组织为殘疾人提供各种诊断、治疗、教育、培训、生活辅助等方面的设施和服务。尽管该法授权卫生教育福利部部长负责全面工作,但是也要求劳工部等部门配合。 U.S.Congress,Public Law 93-112,H.R.8070,Rehabilitation Act of 1973,pp.37,40.劳工部在美国各地设置了为数众多的就业服务机构,既为残疾人提供咨询和培训,又为雇主提供支持,帮助他们改善企业的环境和设施,以便于招募残疾工人、推动残疾工人就业工作的开展,同时还负责监督承包政府工程的企业是否按照法律规定雇用残疾工人。
1974财年国会为此拨款6.87亿美元,1975财年国会拨款7.19亿美元。到1975财年结束,共有90万名残疾人向地方就业服务机构递交或者更新申请资料,其中15.7万人获得了咨询帮助,5.15万人进行了测试以明确个人的特殊才能以及能够适应的工作岗位,19.1万人找到了工作。伤残军人也是就业服务机构重点帮扶的对象,1975财年共有31.4万名伤残军人报名,其中5万人获得了咨询服务,7.6万人找到了工作。 U.S.Department of Labor,and Department of Health,Education,and Welfare, Employment and Training Report of the President,1976,Washington,D.C.:GPO,1976,p.126.可以说,这项政策对残疾人的康复和就业起到了重要作用。
综合上述残疾人康复、福利救济和就业政策,这一阶段美国残疾人就业权利福利模式的制度构建主要有两个特点。第一,将救济和就业融合在一起,并把救济作为工作的主要方面。在时间上看,越是早期的政策,越是强调救济;第二,将治疗和培训相融合,将治疗作为工作的“重头戏”。之所以有如此特点,与当时政策制定者和美国社会对残疾人的认识密切相关。一方面,残疾一直被视为一种疾病或人的生理不足,在本质上美国人仍存在对残疾人的偏见,“残疾等于无能”,因此通过治疗难以恢复到普通人健康水平的残疾人,仍然是民众眼中的“异类”;另一方面,政策制定者将残疾人的权利保障问题,简单化为个人的医疗问题,而以治疗为中心、康复为目标的政策,没有看到残疾人问题与政治、法律和文化之间的紧密联系,忽略了社会上对残疾人的偏见。而仅治疗残疾人的身心障碍,无法消除残疾人面对的就业歧视,无论如何都是治标不治本。
由于强调救济和治疗的政策导向,这一时期美国残疾人的权利被置于救济性福利政策之下,残疾人行使的就业权利是受到限制的权利、有条件的权利,而不是作为一个人的天然权利的组成部分。残疾人要想获得与普通人同等的就业权利,尚待时日。
五、《1990年美国残疾人法》与残疾人平等就业权利的确立
美国残疾人就业政策的第二个阶段以《1990年美国残疾人法》的颁布为标志。该法确立了残疾人平等就业权利的法律基础,号召全社会建设一个无障碍社会,以保障残疾人的平等就业权利,由此美国进入残疾人就业权利获得制度化保障的时期。
作为美国民权运动的成果,《1964年民权法》第七条规定,在就业领域,禁止以种族、性别、宗教和民族为由侵害人与人的平等权利。 U.S.Congress,Title Ⅵ of the Civil Rights Act of 1964,PDF be available at https://www.eeoc.gov/statutes/title-vii-civil-rights-act-1964(2018-05-01).但是,该法没有对残疾人的就业权利予以明确保护,残疾人在就业领域遭受歧视的现象依然被漠视。
虽然《1973年残疾人康复法》的实施效果显著,但由于社会偏见和歧视的存在,残疾人的就业状况和工资待遇仍然不容乐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1990年以前,残疾人的失业率在15%以上,而美国整体失业率为5%左右; Melvin Brodsky,“Employment Programs for Disabled Youth:An International View,” Monthly Labor Review,Vol.113,Issue 12(December 1990),p.50.第二,残疾人的工作收入低于健康人。如1984年男性残疾劳工平均工资仅为健康人的54%; Robert Haveman and Barbara Wolfe,“The Economic Well-Being of the Disabled:1962-84,” The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Vol.25,No.1(Winter 1990),p.41.第三,青年是劳动力的主力军,青年残疾者的就业状况是残疾人整体就业状况的风向标。遗憾的是,青年残疾者的就业环境变得更差了。绝大多数残疾青年一跨出校门就陷入失业困境,如1986年残疾青年高中毕业后即失业的比例高达90%以上,只能依靠政府救济和家庭帮助维持生活。
不仅如此,美国学者研究发现:在收入水平上,伤残不明显的劳工的工资比非伤残劳工低17%,而伤残明显的劳工的工资比非伤残劳工低41%;在就业机会上,非伤残劳工的就业机率为93%,伤残不明显的劳工仅为75%,伤残明显的劳工低至62%。 Marjorie L.Baldwin and William G.Johnson,“Labor Market Discrimination against Men with Disabilities in the Year of the ADA,”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Vol.66,No.3(Jan.2000),pp.557,559.伤残被分为两类:一种是不明显的伤残,包括骨折、疝气、高血压、肾结石、胃病、肺病、心脏病、四肢畸形等;另一种是明显的、严重的伤残,包括四肢缺失、失明、耳聾、中风、瘫痪、癫痫、大脑瘫痪、语言功能障碍、酗酒、药物成瘾、精神疾病、艾滋病等。也就是说,残疾人的工资水平和就业机会,并不是按照他们对社会和企业贡献的大小来确定,而是受到伤残的严重程度及其是否容易辨认的影响。
在此情形下,美国残疾人组织行动起来,要求国会颁布保护残疾人平等权利的法律。1989年末,一些议员向参议院提交了保护残疾人权利的议案,经过国会两院的辩论、修改和表决,1990年6月,《1990年美国残疾人法》得以颁布。老布什总统称它是“世界上第一部全面保护残疾人权利的平等宣言”,它的通过使美国成为此项人权事业的“国际领导者”,使美国4300万残疾人“融入主流社会”。 George Bush,Remarks on Signing the 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of 1990 (July 26,1990).Online by Gerhard Peters and John T.Woolley,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node/264870(2018-08-01). 十余年后,有美国学者评价该法是一个“全新的”“以就业为导向”的法律。 Richard V.Burkhauser and Mary C.Daly,“U.S.Disability Policy in a Changing Environment,” p.214.
《1990年美国残疾人法》共分五条。第一条为“就业”,规定美国各级政府和所有雇用25人以上的企业,都不得在招聘、录取、培训、晋升等方面淘汰条件合格的残疾人。在招聘阶段禁止体检,如需体检,可安排在招聘结束后。体检的结果仅可以用于岗位的合理调整,并且不得外泄,以免暴露残疾人的个人隐私。用人单位需要提供方便残疾人进出的通道、适宜残疾人开展工作的各种设施,并按照残疾人的特殊需要调整工作时间表和培训政策等。只有在雇用残疾人将给其他人带来“直接的健康和安全威胁”时,企业才可以拒绝雇用。具体而言,对于一个食品企业,在招聘食品加工工人的时候,可以拒绝雇用艾滋病和肺结核患者,因为病人身上的疾病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将直接威胁食品安全。但是,该企业在招聘会计、出纳人员时,不可以拒绝一个条件合格的艾滋病或肺结核患者,因为他们与食品生产环节没有直接联系。该条款还规定,不得歧视残疾人的亲属,不得强化残疾人是社会和家庭“累赘”的负面形象。该法对残疾人家属的保护性规定,体现了保护残疾人权利的全面性。该法强调,其各项要求是通行全国的最低要求,各州可根据自身情况,进一步加强对歧视的限制。 U.S.Congress,Public Law 101-336,S.933,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of 1990,July 26,1990,in United States Code,Congress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News,101st Cong.,2nd Sess.,St.Paul:West Publishing Co.,1990,pp.330-337.PDF be available at https://www.govinfo.gov(2020-10-01).
第二条为“公共服务设施”,第三条为“私人运营的公共场所与服务设施”,规定公私建筑、设施都要适宜残疾人自由进出和使用,以保证残疾人能够获得“完全和平等的快乐”;第四条为“通信服务”,规定所有电信运营商都必须改进设备和服务,以便使聋哑人能够有效、及时地享受通信服务; U.S.Congress,Public Law 101-336,S.933,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of 1990,pp.337-369.第五条为“其他事项”。
分析《1990年美国残疾人法》的条款内容,第一条是该法的核心,禁止就业领域对残疾人的歧视,旨在建立一个公平的就业环境,让有能力的残疾人公平地参与竞争。其他条款是对第一条的保障,为确保残疾人享受公平的就业权利而减少障碍。举例来说,一个失去双腿的残疾人,通过学习取得了会计师资格证。在第一条的保障下,他可以与其他具有同样水平的人公平竞争,最终找到一份会计的工作。但是,如果地铁和公交车没有为残疾人提供特殊的辅助设施,他就无法从家里到公司去上班,如果公司附近的咖啡馆、饭店缺少方便轮椅进入的通道,他就无法解决午饭和休息的问题。而《1990年美国残疾人法》要做的就是扫清残疾人在平等就业道路上的障碍。在它的保护下,只要残疾人有工作能力,他就能像其他健全的人一样找到工作。只要能找到工作,从家里到工作地点,从工作地点到休闲娱乐场所,从一个工作地点到另一个工作地点,残疾人都将畅通无阻。所以,建立一个无障碍社会,特别是交通无障碍的社会,是残疾人就业权利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和保障。
在实践中,多个联邦机构负责监督落实残疾人的就业权利。受到歧视的残疾人可以向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公平就业实践办公室等联邦机构投诉,联邦機构会根据调查情况,或者要求企业整改,或者在受歧视的残疾人与企业之间进行调解,甚至到各地联邦法院对企业发起诉讼。 David M.Studdert,“Charges of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Discrimination in the Workplace:The 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in A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Vol.156,No.3(August 2002),p.220.美国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是联邦政府打击就业领域歧视的一个主要机构,其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在美国设有53个地区办公室,管辖范围包括性别歧视、种族歧视等问题,对于与残疾人相关的歧视,打击力度也很大。例如,1995年至1997年,每年每1000名残疾人劳工中约有12人向该委员会提起投诉,案件累计24.5万件,其中14%的投诉在该委员会内得到解决,雇主为每项投诉支付的赔偿金额都超过15 000美元;23%的投诉提交到联邦法院审理,平均每个案件的涉案金额为21万美元左右。其余的投诉或者撤销,或者准备起诉到联邦法院。 Daron Acemoglu and Joshua D.Angrist,“Consequences of Employment Protection? The Case of the 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09,No.5(Oct.2001),p.939.联邦机构监督、保障残疾人就业权利的工作对残疾人的帮助不可忽视。
总之,《1990年美国残疾人法》的颁布与实施是美国残疾人民权运动史的里程碑,意义重大。首先,它标志着美国残疾人平等就业权利的确立。该法构建了残疾人就业权利的法律框架,完成了保障残疾人就业权利的制度构建;其次,由于就业权利是残疾人人权的核心,而建立一个无障碍的社会以保障残疾人的平等权利是残疾人法的核心精神,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该法相当于残疾人的人权法,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残疾人民权运动的重要成果;最后,该法的革命性变化在于,它并不是把残疾人作为“病人”,而是把他们视为一个具有独特性的少数群体,他们的伤残不再是疾病而是一种“特征”。政府的职责就是将具有“不同‘特征’的残疾人”从受歧视、被隔离的困境中解放出来,让他们享有同等的就业权利。通过该法,美国政府将就业权利政策和福利政策组合在一起,并将保障残疾人就业权利的政策重点由福利救济向平等就业方向转变。
余 论
总括前文,美国残疾人就业权利的缘起与制度化经历了漫长的历程,依据美国政府政策的变化,可以将其分为三个时期:20世纪中叶之前是美国政府漠视残疾人就业权利的时期。尽管伤残退伍军人获得了来自政府的就业援助,罗斯福新政时期一部分残疾人获得了公共就业计划的援助,但都不是出于就业权利视角的举措;1954年至1990年之间是残疾人就业权利的福利模式制度化时期。由于美国政府实施了以救济为主、救济与就业兼顾的残疾人就业政策,其福利性质决定了残疾人获得的就业权利是有限的;1990年以后是美国政府将就业权利视为残疾人的一项基本民主权利,并努力使其获得制度保障的时期。在法理上,残疾人获得了与其他美国人一样的平等就业权利,残疾人政策的重点由救济为主向平等就业为主的方向转变。在政策保护之下,美国残疾人的就业环境大为改善。
美国政府之所以在20世纪中叶后对残疾人就业权利给予积极回应,主要有以下四个原因:第一,工业革命后,由于安全生产水平不高,大量工人在工作中受伤。这种局面贯穿了整个20世纪,即便在第三次科技革命兴起后,伤残劳工仍大量出现。这些劳工拥有工作经验,对工作环境十分熟悉,对自己的能力也有客观评价,他们在康复后渴望重返职场,自力更生,实现个人价值;第二,20世纪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美国都参与其中。在战争中,大量士兵受伤。他们中许多人在战前都从事着自己喜欢的工作,在康复后渴望返回原来的岗位就业。即便身心上的伤残使他们无法胜任原来的工作,许多人仍希望另谋职业,不想成为社会和家庭的负担。对于这些为国征战、英勇负伤的军人,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去维护他们的就业权利;第三,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发展,社会生产对于体力的依赖大大下降,聪明才智、意志品质成为雇主最为重视的素质。在这些方面,很多残疾人不逊于健康人;第四,残疾人获得就业权利是残疾人民权运动与全国范围内民权运动互动的结果。
然而,《1990年美国残疾人法》的颁布并未使美国一劳永逸地解决残疾人问题。首先,该法并没有赋予残疾人与健全者竞争时的优先权,仅仅是给了他们与健全者同台竞争的机会,这只是法律上的公平,在实践上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在它鼓励一部分残疾人谋求就业和经济独立、由资源消耗者变成财富生产者的同时,还有一些残疾人由于身心障碍较为严重,对就业漠不关心。1990年以后,许多永久性残障者表示,对他们影响最大的仍然是联邦政府的收入补贴,而不是就业保护。很多残疾人离不开各项福利保障计划的资助。 Richard V.Burkhauser and Mary C.Daly,“U.S.Disability Policy in a Changing Environment,” p.214.相当一部分美国学者研究认为,1990年以后残疾人的就业率不升反降,因此对政府政策的评价不高。 Daron Acemoglu and Joshua D.Angrist,“Consequences of Employment Protection? The Case of the 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pp.915-957; Marjorie L.Baldwin,“Can the ADA Achieve Its Employment Goals?”,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Vol.549,Jan.1997,pp.37-52.
其次,民权法、残疾人法和其他法律的实施,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社会对残疾人的偏见与歧视,因为这种偏见与歧视不仅来自殖民地时代就存在的对残疾人的隔离、移民政策中对残疾人的排斥,更重要的是,它来自20世纪这样“一个对残疾人的偏见和歧视愈演愈烈的时代”, Frank Bowe,“An Overview Paper on Civil Rights Issues of Handicapped Americans:Public Policy Implications,” p.9.来自美国人发自内心的顽固认知,即认为权力与残疾是相互排斥的。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末,“残疾等于弱点”“残疾等于无能”的观念左右着社会对残疾人的态度和残疾人的命运。当残疾人的价值和能力被否定,他们无法像常人一样享受平等的权利。以至于有美国学者认为,“在今天这样一个已无法利用电视报道制造精彩骗局的时代,像罗斯福那样有严重缺陷的人不可能当选总统”。 Doris Zames Fleischer and Frieda Zames,The Disability Rights Movement:From Charity to Confrontation,p.5.
因此,美国更需要的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政治革命,以消除残疾人行使作为人的平等权利的真正社会障碍——公众的偏见与歧视。残疾人最迫切需求的是没有偏见、没有污名、没有歧视、没有因行动不便而带来的艰难。他们渴望可以像其他大多数人一样,有足够的资源来认识和实现自己的潜力。
责任编辑:宋 鸥 郑广超
The Origins,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Dilemmas of Employment Rights for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20th Century
GAO So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Jilin,130024,China
)Abstract:In a certain sense,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20th century is a history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for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If the Great Depression initially awakened the awareness of the employment rights of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and the two World Wars initiated the policy construction of rehabilitation and employment assistance for disabled American soldiers,the Thir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ccelerated the process of institutionalizing the employment rights of 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From the Public Works,the Social Security Disability Insurance,the 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to the Rehabilitation Act,and the 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the employment rights of the disabled have undergone a transformation from being disregarded,to being dependent on welfare assistance,to realizing equal rights,and left many challenges and questions to ponder in American politics,economy,society,and ideology.Due to the limitation of laws,historical legacy,and deep-rooted prejudice,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still have a long way to go to fight for equal rights.
Key words:Employment Rights; Vocational Rehabilitation Acts; Social Security Disability Insurance; 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 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DOI:10.19832/j.cnki.0559-8095.2022.0023
收稿日期:2021-02-25
基金項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庆祝建党100周年预立项课题“中共中央东南局与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在浙江的传播研究”。
作者简介:宫兰一,东北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导师为王占仁教授。
① 中共中央东南分局(1937年12月—1938年10月),是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领导南方各游击区组织开展工作的派出机构,受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双重领导。项英任东南分局书记,曾山任副书记,陈毅、方方、涂振农任委员。
② 根据抗日战争形势的变化,中央决定撤销长江局,在长江局领导区域内设3个中央局:以大后方的广西、四川等地为基础,设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长江以北陇海铁路以南地区设中共中央中原局;在长江以南的东南地区,将原东南分局改为中共中央东南局(1938年10月—1941年5月),项英任书记,曾山任副书记,后又增任饶漱石为副书记。
③ 龙跃:《坚持浙南十四年 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苏多寿主编,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史略》,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中共中央东南局》编辑组编著:《中共中央东南局》,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
22705011863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