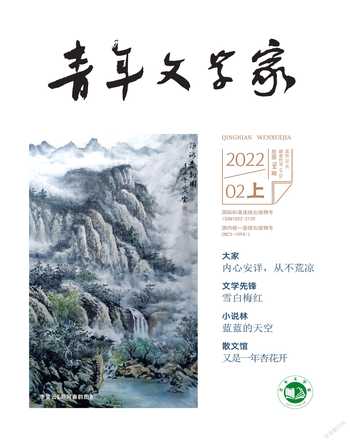论中国现代诗化小说
李慧敏

文学进入现代后,许多传统模式被打破,但是传统文学的抒情性格却一直在延续。中国文人骨子里的“诗性”依然存在,这表现在小说创作中,就是语言诗化、结构散文化、情节弱化、追求意境美、具有传统审美倾向。这种小说告别传统经典小说模式,横跨诗、散文、小说三种文体,将叙事艺术与抒情艺术相结合,我们称之为“诗化小说”。本文选取中国20世纪30年代这个诗化小说发展最为繁盛的时期作为观察对象,翻阅废名、沈从文、萧红等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尝试梳理中国现代诗化小说的特征、源头与发展。
一、20世纪30年代诗化小说总体状况
(一)时代背景
20世纪30年代,紧张的时局、现代文明的侵入,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得人们急于求成,追逐现实利益。文坛上也出现了许多都市小说,大多描述上海这个现代文明都市下男男女女纸醉金迷的生活。一些前期创造社的成员为了获得销路,不惜放弃文学的高度,而写一些充满肉欲的、迎合大众口味的低俗文学。许多没有艺术性、奢靡、矫作的文章也因此流出,朱光潜在《谈美》中将这些现象归结为“大半是由于人心太坏”。
面对“人心太坏”,有的作家走左翼路线,积极入世,这些作家自觉肩负着历史重任,走在时代的前端,成为当时的主流思想与文化。例如,鲁迅、茅盾、蒋光慈等人,文坛上也出现了左翼作家联盟这样与时代挂钩、与政治紧密联系的文学团体。这些作家以笔为戎,金戈铁马,似有无穷的力量和勇气去彻底展示这个时代、社会、人情、人性的巨幅画卷,想要谱写这一时期史诗般的巨作。他们的作品因切合时代主题,有着鲜明的革命旗帜与强烈的斗争性。在当时的文坛中,也出现了京派小说家这一群体。林徽因在《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的《题记》中的两句话可以概括这个文学派别的创作特征,认为他们“趋向农村或少受教育分子或劳力者的生活描写”,“诚实的重要还在题材的新鲜,结构的完整,文字的流丽之上”。京派小说将平民世界和乡村总体叙述全部包容进来以示其文化的保守主义,他们的情感是内敛的、节制的、理性的,与当时的时代主流思潮相背离,不参与政治斗争,也不强调文学的功利作用。中国现代诗化小说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成长起来并形成当时一道独特的风景。
(二)代表人物
1.废名
废名的文学创作在当时远离时代潮流,是一座“永久孤绝的海岛”。他在《说梦》中写道:“字与字,句与句,互相生长,有如梦之不可捉摸。然而一个人只能做他自己的梦,所以虽是无心,却是有因。结果,我们面对他,不免是梦梦。但依然是真实。”
可见,废名的文学观点围绕“梦”展开。
废名是一个重视“梦”的文学创作者,他“梦”的气质出现在作品里,形成了一种恬淡、清新、宁和的文风,表现在语言文字上,则有一种朦胧美、意境美,再加上他喜好晚唐“温李”诗词,作文也犹如古人作绝句的韵味,这也是废名诗化小说最显著的特征。早先,胡适提倡“作诗如作文”,而废名却反其道而行之,作文如作诗。例如,小说《桃园》里王老大闩门:“王老大一门闩把月光都闩出去了。”就很有些“闭门推出窗前月”的意思;再如《菱荡》里描写女人洗衣服的场景:“洗衣的多半住在西城根,河水渴了到菱荡来洗。菱荡的深这才被他们搅动了。太阳落山以及天刚刚破晓的时候,坝上也听得见她们喉咙叫,甚至,衣篮太重了坐在坝脚下草地上‘打一栈’的也与正在捶捣杵的相呼应。野花做了他们的蒲团,原来青青的草她们踏成了路。”
這段文字极富画面感,不仅如此,似乎还能从这清逸的语言中听到浣衣女的嬉笑声。很容易让人想到王维的《山居秋暝》:“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废名自己也说,写《菱荡》是有唐人绝句的特点的,事实上他的小说创作“实是用绝句的方法写的”。
《桥》是废名作于20世纪30年代的长篇,说是长篇,因为其片段性的结构,却“颇同短制”,随便抽出一个章节都能当作短篇来阅读,只是主人公并不众多,主要是小林和琴子二人。小说写两人的两小无猜,其间穿插了唱命画、送路灯等民俗,极富情趣。作品延续之前冲淡平和、恬静的文风,文体简洁,语言上用词险僻,致使喻义晦涩。从《桥》的篇目中便可看出废名的“诗性”与审美—“金银花”“井”“落日”“杨柳”“清明”“箫”“桥”“梨花白”“枫树”“荷叶”“萤火”,这些都是古诗词中的常用意象。废名这种将古诗词因素融入现代小说里的本领堪称了得,丝毫不矫揉造作,从表面上看似乎有旧文章的痕迹,但是在他之前,没有人这样写作小说,这实在是他的创举。
可以说,废名是诗化小说的先导,其诗化小说风格简约幽深、古朴拙讷。其于20世纪30年代创作的作品中,渗透的佛法理趣更多,但因为用词生辣奇僻,较为晦涩难懂。
2.沈从文
沈从文深受废名20世纪20年代小说的影响,并且继承延续废名的文体实验。他的诗化小说美丽却有一层淡淡的忧愁,似无意与当下工业文明对立,但是对古老灵魂的描述,对初民淳朴而又健康的生活方式的赞美无处不体现在文中作为一种与“现代中国”相对立的乡土文明而出现,少了废名文章中的归隐气质与以冲淡为衣的外貌特质,而是多了一份倔强的以乡下人的眼光看城市中人的态度,作品以原始、野蛮的乡土人民的生命张力为外在表现。
沈从文所提倡的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他所供奉的是“人性”。他所创造的乡村世界是一种“理想化的现实”,他的乡村叙述总体是美的、善的,而构建起这个“希腊小庙”最重要的基石,就是沈从文心中那些美丽、活泼、纯情、诗意的女子。这些十三四岁的女孩子形象天真烂漫、淳朴动人,一如《竹林的故事》里的“三姑娘”,他们没有强烈的情感起伏,仿佛一曲清新、舒缓的牧歌。沈从文笔下的三三、萧萧、翠翠、夭夭都是美好的女孩子形象,都被他敬奉在“希腊的小庙”里,是他专注人情美、人性美的所在,也是他所构筑的湘西世界的美的所在。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故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心机后,就又从从容容地在水边玩耍了。
通过这一段对翠翠的外貌和性格描写,我们可以看出沈从文对女子淳朴、活泼性格的喜爱,他所崇尚的是那种原始的、发自人本性的力量。这一段的文字排布上也是错落有致,长短句交叉,三个“从不”连用,读来跌宕起伏,顿生节奏之美。
从沈从文的《边城》中看得出他与废名的师承关系,他在文体上的实验与废名颇为相似,都是用近乎散文的笔触描写一个个动人的故事,整篇文章情调切合文章内容充满美感,氤氲着诗意。但是,他与废名最大的不同就是他对城市文明犀利的、审视的眼光。他的作品追求一种边地民谣的意境,渲染湘西独特的风情风貌,将湘西作为一个整体的叙述总体,以及巨大的象征意象与同时期的都市生活和现代文明作对比。他不喜欢现代文明下产生的“社会”和秩序,向往古朴、纯粹的人性的美好,并且以边地人们这种性格作为衡量一切人和事物善恶的标准。正如他在《水云—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中所说:“一切来到我命运中的事事物物,我有我自己的尺寸和分量,来证实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我用不着你们名叫‘社会’为制定的那个东西,我讨厌一般标准,尤其是什么思想家为扭曲蠹蚀人性而定下的乡愿蠢事。”沈从文对世俗世界的疏远与隔离使得他的小说自成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纯净且充满人性美,这也为以后的诗化小说奠定了基调。
3.其他
除了废名与沈从文外,20世纪30年代诗化小说的创作者还有萧红、芦焚、艾芜等人。《生死场》《谷》《南行记》都以散文的笔调、诗的语言来谱写平民世界,或忧忿,或凄怆,或哀凉。他们的创作各有特色,但都具有诗化小说的特征。
萧红笔下的东北黑土地、芦焚作品里北方废园阴冷的景象、艾芜文中蕴藏着神秘内核的边地风情民俗也让人产生无限遐想。如《南行记》中提到的克钦族妇女的头饰,还有《山峡中》《松岭上》的奇遇冒险和边地奇异风光,“两岸蛮野的山峰,好像也在怕着脚下的奔流,无法避开一样,都把头尽量地躲入疏星寥落的空际”。萧红、芦焚的诗化小说已没有废名、沈从文的那种追寻化外之境,尝试挖掘古朴、本真的人性美,也缺少一切应该回归自然、本于自然的向往憧憬。相反,他们写出了乡村愚昧、麻木、可悲可叹的生活境况,以及工业文明侵入宗法制乡村带来的激烈震荡与破坏。虽然所表露的思想情感并不相同,但是他们与废名、沈从文一样,打破严格的小说传统模式,将小说、诗歌、散文融合在叙事艺术中,以抽象性思维、诗意性思维整合意象,作为一种象征表述。
(三)总体特征
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诗化小说总体上淡化情节,诗化小说没有传统小说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情节张力,但是注重意境的体现。小说多以乡土为背景展开。例如,废名的湖北黄梅、沈从文的湘西世界、萧红的东北黑土地、师陀的果园城、艾芜的荒山边地……诗化小说作者将他们生活过的乡土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意象渗透进小说中,风俗民情、日月江河、山村野店等都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将乡村叙述总体作为一种与现代都市以及都市文明的鲜明对照而出现。
1.思想内容
内容上或是追求古老的初民之风,描刻化外之境;或是写现代文明侵入下,宗法制农村的崩塌;或是写在现代文明的对照下,农村的愚昧、陈腐与必然灭亡的趋势;或是迫于生活的压力逃入少是非、少现代文明的少数民族边地地区,但都是以一个乡村叙述总体来对照现代文明。
思想上既有保守的一面,以及先民古朴、纯真人性的情感流向,如废名、沈从文;也有保持客观态度,描绘被现代文明所影响下的农村,如芦焚;也有抨击乡村落后、停滞的状态,批判乡民愚昧、麻木的萧红等。个人因自己的生活处境的不同而造成叙述情感的差异,导致思想情感的倾向也不尽相同。
2.艺术表达
叙述手法上,将叙事艺术与抒情艺术两相结合,更加突出抒情艺术,营造意象,追求意境。这一时期的诗化小说与它在20世纪20年代的萌芽状态不同,有别于郁达夫的内心独白,它突出情节以外的“意境”。语言表达上注重语言的诗化,句子长短有致,具有节奏性。例如,废名绝句诗的语言,凝练且有美感。沈从文的语言“较为奇特,有真意、去伪饰、具个性,追求纯和真的美文效果”,并且“长句精确、曲折而富韧性,短句重感兴,活泛有灵气”。
模式上告别小说的经典模式,结构散文化,情节弱化。有的诗化小说仿佛喃喃自语,支离破碎的、跳跃性的语言以及作者独特生命体验的含蓄表达都讓人产生阅读障碍,毫无章法可循,也毫无情节可读。
二、中国现代诗化小说溯源
现代诗化小说可追溯到鲁迅。1921年,鲁迅先生所写的《故乡》不仅开创了“乡土文学”这一母题,带动了一个群体的写作—“乡土小说”作家群,而且还启发了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诗化小说作家。如《故乡》中“深蓝的天空”“金黄的圆月”“碧绿的西瓜”俨然一幅色彩浓厚的水彩画。《朝花夕拾》中的乡土题材,《彷徨》《野草》中的诗化语言,都充满了诗意。
郁达夫的小说也可算作一个现代诗化小说可追溯的源头。他的小说情节弱化,以情绪结构全文,心理描写充分且满含作者或悲愤或落寞的强烈情绪。这一点上,郁达夫的小说似乎与西方诗化小说更为靠近。他不似鲁迅的小说如《故乡》《社戏》《在酒楼上》构成一种诗情,而是由大量的内心独白构成。比如《沉沦》中的“他”,故事本身没有多少故事性可言,但时时、处处又能感受到作者及主人公强制闷在胸腔中,一触即发的激动情绪。行文间带有强烈的抒情色彩,具有明显的抒情性格,这也是日后诗化小说的一个重要外貌特征。
20世纪20年代初的鲁迅与郁达夫的小说并没有20世纪30年代已成气候的诗化小说的“小说艺术思维的意念化、抽象化,以及意象性抒情、象征性意境的营造等诸种形式特征”。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鲁迅作《野草》集,学界有学者认为这是一本散文诗集。鲁迅在这部集子里已经打破小说、散文、诗的界限,他并不是刻意如此,而是其艺术创作思维模式已经转变得抽象化、意念化,这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却为诗化小说的诞生起了一个引导的作用,集子中诸多的象征形象,如“影子”“雪”“火”“夜”,以及象征性表述为诗化小说的酝酿、发生甚至发轫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三、中国现代诗化小说发展
废名作为诗化小说的创作先驱,1924年,《竹林的故事》以其清新隽永的文笔为当时苦闷的文坛吹进一阵轻柔的风。小说并没有像乡土小说群作家那样描绘乡村的愚昧、封建宗法制度的残酷,而是用一支温柔的笔写出“以慈悲之心写人间悲苦,在美好的人性人情中得到解脱”。“诗笔”充满了“禅趣”,女人失去丈夫,女儿失去父亲都是世间悲惨的事情,但是小说中却没有这样的哀叹或呻吟,而是以一种冲和平淡的调子进行着、描绘着三姑娘母女依然澄净且宁静的生活。在这篇小说里,废名创造了一个十二三岁纯洁的小女孩形象,清澈得如同泉水,淳朴得仿佛还是婴儿般那样。这为后来的沈从文、汪曾祺在他们的诗化小说中所创造的一系列小女孩形象开了先河。
这种语言的诗化,结构的散文化为小说文体创新开辟草昧,为还在懵懵懂懂探索中的诗化小说奠定了最有力量的基础,他说:“写小说,乃很像古代陶潜、李商隐写诗。”无疑废名的文体实验是成功的,影响是惊人的。他为下一个时期诗化小说大家沈从文的出现埋下了重要的一笔。
20世纪30年代诗化小说达到了一个顶峰,这主要是由于废名和另一诗化“小说重镇”沈从文。
沈从文以他的故乡湖南湘西为背景谱写了一曲曲美丽却又哀愁的乡间民谣。他的诗化小说代表作《边城》被称为“七万字的长诗”。随之而来的萧红、芦焚、艾芜等,他们的内容无一不指涉自己曾经生活过的家乡、农村,并且创作思维已经完全转变为抽象与意念的模式。尤其是萧红,作为一名女性作家,有着女性作家独特的敏感而细腻的笔触,钱理群先生说她的作品“风格明丽、凄婉,又内含英武之气”,萧红已经完全打破传统小说的经典模式,创造了一种介于散文和诗的文体。她的小说意境也不似废名和沈从文追求那种古朴、健康自然、充满生命力的意境。她把曾经生活过的乡下生活的土地比作“生死场”,整篇小说弥漫着一种压抑的灰色的死的气氛。
20世纪30年代后期20世纪40年代,多变的时局让文人们辗转各地,生活不得安宁。废名更加虔诚地研究佛理,大有归隐之趣,其《莫须有先生传》因阅读时对作者所要表达的东西模糊不清而变得复杂,用词的晦涩使人不能很好地理解;沈从文的《长河》从外貌上看似乎还是对前期湘西民歌式小说的继承,但其内在的对乡村生存方式的理解已经改变;萧红的《呼兰河传》完全是对童年生活的一种追忆;师陀的《果园城》则透露出诡异与阴冷;何其芳的散文《画梦录》也极具诗的气质,幽谧的梦幻思维也给他的小说带来诗性,他于20世纪30年代创作的《老蔡》《王子酋》等都属诗化小说的佳作。20世纪40年代出现的冯至的《伍子胥》则是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对前期诗化小说的继承,虽然还有前期的意境與情致,但是内容已不再是叙述古朴乡镇上古朴乡民们古朴的美德了,也不再见那些纯美的小女孩形象,而是像20世纪30年代何其芳《王子酋》那样在历史中盘亘,回顾往昔岁月,不理会纷扰的现世,“躲进小楼成一统”了,内容进入我国古代历史,以伍子胥的际遇为主线,发挥诗人的想象力与语言表达力,勾画了一位古代贤人形象,以史刺今。文人们回到古代的历史、传奇中,看似一种逃脱的态度,其实是对这个时代最有力的声讨!
从废名到沈从文,再到何其芳、冯至,这是中国现代诗化小说完整发展的一条线索。20世纪30年代的诗化小说背离主流却自成话语,恪守自己的创作原则,追求人性美与意境美。在当时,他们并未结成团体或彼此互通有无,他们也并没有鲜明的文学标语与共同的创作原则,在当时不被人所理解。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小说与诗歌创作力的重新勃发,他们的价值被重估,他们的文学成就也被重新定义。诗化小说作为现代文学的一支,它的发展既承继了中国传统抒情性,也容纳吸收了现代语境中的时代性与个体生命经验,是文学史上不可忽略的一种文学现象。
2045501705212
——一本能够让你对人生有另一种认知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