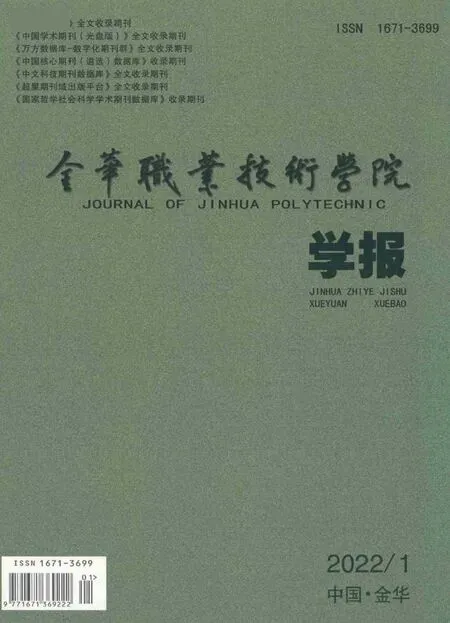“氧化”与“新生”
——论《木箱深处的紫绸花服》的隐喻叙事
甘传永
(中国海洋大学,山东 青岛 266100)
《木箱深处的紫绸花服》是王蒙于1983年发表在《花城》的一部短篇小说。小说写作缘起于一件紫绸花服,这件紫绸花服是王蒙的妻子收到的朋友赠送的新婚礼物,可惜没穿几次就被压到了箱子底,待到妻子想再穿时却发现款式已落伍了。王蒙惋叹于这件衣服的历史和命运,于是借助童话的笔法创作了《木箱深处的紫绸花服》这篇小说。王蒙透过一件衣服的“眼睛”去观察时代的变迁,从一件衣服的命运去体会人生沉浮的滋味,运用隐喻式的叙事使小说达到了意在言外、旨趣深远的效果。
一、主流之外的寂寞之音
小说的主要情节并不复杂:1957年,丽珊在结婚前夕收到一件苏绣的紫绸花女罩服,但因为政治形势的变化,她只穿了一次这件紫绸花女罩服,就将其放进了箱子,直到二十六年后,这件衣服才被重新拿出,可这件重见天日的衣服被年轻一辈所厌弃,因为它的样式和风格已远远落伍于时代潮流,最终衣服重回丽珊手中,坦然接受衣服被“氧化”的结局。
在韦勒克和沃伦看来“文学的意义与功能主要呈现在隐喻和神话中。人类头脑中存在着隐喻式的思维和神话式的思维这样的活动……一切意象都是对人类思维中无意识活动的揭示”[1]219-220。从社会历史层面看,王蒙把中国当代社会近三十年的风云变幻浓缩在一件衣服上,用这件一直不合潮流的衣服隐喻逝去的青春。从个体生命具有普遍性的层面看,王蒙用这件衣服的命运隐喻了难以言说的人生寂寞感和错位感。
丽珊的紫绸花服是纯手工缝制的苏绣风格,上面有凤凰和竹叶的图案,饱含爱情美满、吉祥如意的美好寓意,小说中对衣服的描写是这样的,“既柔和、又耀目,既富丽大方,又平易可亲”[2]390。这样一件纤细柔软具有中国古典美学意蕴的衣服,受1957年“反右”政治形势的影响而无法被衣服的主人穿着。小说中写道,鲁明和丽珊在婚后不久就去了农村。我们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可知他们是被当作“右派”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改造的。此时的知识分子已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学习启蒙者,而成为接受农民改造和教育的对象,由于他们在农村要参加务农劳作,而这件紫绸花服仅适合城市生活方式,不符合农民的审美习惯和体力劳动对穿着的需要,因此身份的特殊性和从事工作的性质注定了丽珊只能把“原来珍贵地放在她的樟木箱子里的许多衣服都丢掉了,像那件米黄色的连衣裙,像鲁明的一身瓦灰色西服,像一件洁白的桃花衬裙……它们都是紫绸花罩服的好同伴”[2]391,取而代之的是把羊皮背心、防水帆布做的大裤脚裤子、连指手套、厚棉帽子等适合农村居住和劳作的服饰装进箱子。
如果说此时紫绸花服是因为实用性不强及丽珊因生育出现身材变化而无法穿着,那么到了“文革”时期,这件衣服因为其象征的政治身份而列入被淘汰甚至销毁的行列。反“四旧”是“文革”时期的重头戏,在日常生活方面表现为不顾一切、不分优劣地反对代表传统文化的衣食住行各方面,在服饰方面表现为反对古典美学风格的衣服,如旗袍、罩服等,它们被认为是封建思想的残留物,因此要被禁止。同样,在小说中,面对误带来的一条领带,丽珊和鲁明更是如临大敌,因为领带、西装在此时被认为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服饰。由于紫绸花服承载着丽珊的青春和爱情记忆,在她的坚持下,紫绸花服最终被留了起来,丽珊也期待着“也许”和将来。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这件衣服因为不合时代主流在二十六年间一直被压箱底。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新质料、新风格的服饰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人们除了追求舒适,更加追求时尚,而这体现了多元、个性、自由的时代主潮。随着新时期的到来,紫绸花服被重新从箱子中拿了出来,本想能被认可,但没料到被儿子儿媳嫌弃老旧、落伍,不肯接受这件紫绸花服。此时的紫绸花服虽不再因为政治意识形态被压抑,但因被年轻人认为其落后于八十年代特有的凹凸花纹毛线衣、喇叭裤等流行衣服,再一次被摒弃在主流之外。
两个时期,不同的社会背景,紫绸花服却摆脱不掉无法进入主流的命运,它似乎永远是不合时宜的。这种借衣服命运诉说“弃妇”心绪的手法正是古代文人借“香草美人”抒内心情志这种表达方式的重现。紫绸花服的经历和遭遇也是王蒙那一代人的经历和遭遇,他们有理想、有能力,可惜还没来得及充分发挥,就遭遇了政治局势动荡的影响,被各种斗争甩出时代中心,流落边缘,等到重新回归时却忽然发现自己早已是时代的陌生人,原有的经验与现实不匹配,令他们生出一种“文化休克”感。而这种感觉难以直接表达出来,只能借一件衣服的命运来抒发自己的情怀。
王蒙在谈到《木箱深处的紫绸花服》时曾说:“人生当中有很多这样的故事,有些事走得靠前了,你做不成,等到你觉得你能做了的时候,你走得已经不是靠前的了,不前卫了,你已经落后了,已经是老一辈的了。因为世界与时间是不待人的,世界本身也不断地发展变化。”[3]时代造成的人生的错位,永远处在时代边缘的人生苦味,努力想要进入主流却不得的悲哀与无奈,这些正是王蒙要借由一件紫绸花服要揭示的人生矛盾。“好的隐喻使用‘可感知事物’来暗指‘纯理性的事物’”[1]227,王蒙借一件衣服隐喻了社会的变迁以及发生在社会变迁下的人们的思想、精神、情绪、心理的变迁。这种内敛含蓄的写作风格让小说的意境悠长绵延,达到了余音绕梁、回味无穷的效果。
二、走出“归来”困境的智者选择
王蒙通过小说表达的人生寂寞感和命运错位感在社会历史层面指向了八十年代,指向了从被极左政治压迫下归来的这群“文化英雄”面临的新时期困境以及走出困境的不同选择。这是小说在社会历史层面的隐喻。王蒙并不像这一时期的许多作家,仅把小说创作停留在“伤痕”“反思”这类主题上,而是开始指向未来,从而获得一种更具前瞻性和深远意义的书写眼光。
面对迅速出现的各种样式的新衣服,紫绸花服作为“归来者”,无论是款式、气派、质料,都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虽然表面上新时期的衣服对有二十六岁高龄的紫绸花服尊敬有加,但实际上内心里瞧不起它。当它满心期待能在年轻一辈中重焕光彩、展现青春时,却被认为是“老掉牙”的物件而遭嫌弃。紫绸花服虽然以英雄身份归来,享受到了尊敬的地位,但实质已经疏离于时代潮流,它的内心因此充满了落伍与过时的迟暮之感。
王蒙通过紫绸花服的命运隐喻了一批“文革”后归来作家(复出作家)的命运。八十年代中国作家的主要类别之一是从五十年代起因政治或艺术原因而受挫的作家,他们中的一些人刚刚在文坛崭露头角就被迫放下了手中创作的笔。这些被放逐的作家,在八十年代获得了“重生”,作为复出作家进入新时期。“归来”意味着回归中心轨道,回到目的地,并自然而然地获得“文化英雄”的荣耀身份,同时他们的内心存有一种“弃民”身份意识,因而令“归来”更增添了一份悲壮感和崇高感。
然而,事实上,“归来者”们并没有获得如大部分人所想象的价值多元化、理想化的“创作自由”的文学环境以及进入文学核心权力机构的地位。新时期初期,国家意识形态与知识分子进入了一个“蜜月期”,文学创作开始有了较为宽松的环境。虽然执政党层面此时掀起并支持否定“文革”、反思建国以来问题的潮流,但文学界中却出现了质疑、动摇“体制”本身合法性的发展可能。因此,八十年代初出现了一系列或大或小的从官方层面对触犯禁忌的作家的作品进行批评或批判的事件。除了文学环境,复出作家的文学地位也并没有如所想的那样再次占据时代主流,成为“弄潮儿”。这一点从新时期初几次作家协会理事会上就可看出。正如小说中的紫绸花服,无论它底蕴如何深厚,但它从内到外都已无法与新流行的丝袜、带拉链的裤子、有凹凸花纹的毛衣相提并论,它即使重见天日也不能被年轻一代所接受,注定是被氧化的命运。
同样是作为“归来者”,王蒙以文学创作的活力和为人处世的练达,展现出了一个智者的姿态,并在八十年代的文坛占据一席之地。王蒙在复出后同样以“文革”和建国后系列事件为题材发表了许多作品,如《最宝贵的》《风筝飘带》《布礼》《蝴蝶》《夜的眼》《海的梦》《杂色》等,与其他“归来者”不同的是,他一开始就与流行的揭露、控诉的题材和激烈的情感方式保持距离。虽然有的作品依然采用了以当代历史事件为结构框架的方法,但他在作品中表现出一定的思想深度、艺术控制力,以及重视心灵成长变化、重视历史理念的思辨倾向。他没有留恋于“伤痕”“反思”这类主题,而是竭力地从混乱中寻找秩序重建的可能,从负有责任者那里看到了可以谅解之处,从被冤屈和受损害者那里看到了弱点和需要反思的“国民劣根性”。他的作品最终都落脚于呼唤人们要为建设四个现代化、建设富强民主的国家而努力,令作品充满着理想和信仰的底色,符合“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主流话语规范。
除了做到主题的控制和情绪的矜持,王蒙在小说艺术方面也做了更多探索。他的许多小说主要写了人物意识的流动,对人物的心理、情绪、印象进行分析,并采用了联想式叙述,让作品有一种流动之感。王蒙这些游离于写实规范路径的小说在一段时间内引起了“现代派风波”,很快在文学界成为其他作家学习的前沿的艺术范式,并在八十年代中期成为流行手法,王蒙也自然成了文艺“先锋”,有批评家指出,王蒙创造了“东方艺术流”的表现手法,这也成为他在主流站稳脚跟的重要原因。除了写作上的突破,王蒙的务实、包容的政治智慧也让他在官方层面得到认可,而这种政治经验又影响甚至补充了他的写作体验。八十年代以来,王蒙担任过《人民文学》的主编,作家协会的常务副主席,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文化部部长,这些政治身份更让王蒙始终处在时代潮流之中。
王蒙的这种双重成功,得益于他较一些复出作家有一种建设性的意识与行动力,符合了时代主题和历史发展趋势;更得益于王蒙这代人未被磨灭的理想主义情怀和革命信仰。他的“桥梁”和“界碑”心态,让他做出了智者的选择,走出了“归来”的困境。八十年代的王蒙因双重身份充当了作家和官方之间的“桥梁”,他自认为充当着“一个减震减压的橡皮垫”,他明白自己要做的事就是促进沟通、照顾大局,缓解矛盾、增进团结。这种智慧的来源,王蒙认为是自己比纯粹的政治家“多了一厘米的艺术气质与包容肚量”,比纯粹的作家“多了一厘米政治上的考量”[4]175,比知识分子们、行业精英们“多了也许多于一厘米的实践”[4]175,比激进的“左派”“多了好几厘米的理解、自控与理性正视”[4]175。虽然王蒙被认为是左右逢源,也受到过左右夹击,陷入类似“有点发胖的界碑”的尴尬处境,但是王蒙始终坚定的革命信仰和建设性的努力让他与时代达成了和解,也与自己达成了和解,即使此时这种和解背后的裂隙被暂时遮蔽。“被泪水与时间高高兴兴地氧化了吧。别了,我的,我们的五十年代的美丽的紫绸花服”[4]173,这是王蒙对《木箱深处的紫绸花服》这篇小说的解说,更是对自己的期待与告诫。
三、寻求超越的逍遥姿态
小说中的紫绸花服除了隐喻逝去的青春、归来者的困境,还暗含小说在个体存在层面的深层隐喻。小说通过叙述丽珊和鲁明对紫绸花服的价值判断和意义期待隐喻了个体如何突破命运错位的悖论,超越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实现自由和逍遥,这也是王蒙小说具有普世性价值的原因所在。
莱考夫和约翰逊认为“隐喻是我们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它帮助我们部分理解那些无法完全理解的事物,如我们的情感、审美经验、道德实践、思想意识。这些想象的尝试并非没有理性,因为使用了隐喻,它们采用的是富于想象力的理性”[5]。与他们的观点相似,王蒙借助隐喻手法,在丽珊和鲁明对紫绸花服的不同处理上,暗含了个体不同的思想意识和文化实践。
信念、理想、希望是精神生命的根基,一旦人意识到自己的信念、理想、希望的无用性,精神生命就会跌入虚无的深渊。在这深渊中,如果生命的思与情找不到超越深渊的路径,生命自身的热情就会焚毁生命自身。丽珊把紫绸花服的重生寄希望于“也许”“以后”,意思是期待政治动荡结束那一天的到来。她知道自己无法再穿紫绸花服,于是想把这件衣服传递给儿媳,把自己年轻时未能实现的愿望寄托在年轻一辈身上,通过子辈之身再次焕发紫稠花服的光彩,她希望以这种方式把自己逝去的青春在子一辈身上重新“找回”。可丽珊没想到的是,儿媳用一句“谁穿这个老掉牙的”,坚决地拒绝了她,并用有着令人眼花缭乱的无数个小拉链的新衣服令五十年代的紫绸花服“目瞪口呆”,截断了它“真正的青春是在八十年代”的幻想。丽珊就是在紫绸花服会在新时期重生的期待中,陷入失望乃至绝望的“深渊”。
丽珊对紫绸花服价值的执着追求是拒绝承认它已是过时之物,拒绝承认它在新时期“无用”的真相。这背后是她对自己这辈人在新时期价值的思索,她有满腔的热情和理想,以国家民族的命运为自己的命运,富有价值自居的道德精神。所谓价值自居,就是把超越个体需要的某种更高价值内化为自身的感性生命,与古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气节相似。这同时也是王蒙的思索,当个体面临壮志难酬、生不逢时的局面,如何生存和超越这种困境。
面对得不到说明的人间苦楚、难以理解的生命无常、令人恐惧的精神荒漠和骇人可怕的价值荒谬,个体消除此种绝望感往往只需要认识的转变,即突破紫绸花服有用论和无用论的二元对立观念。与丽珊相比,鲁明对紫绸花服的态度是“你给出去,我还舍不得呢”,他清楚这件衣服只能属于历史,只能作为回忆过去的纪念物,不可能在新时代再次焕发“第二春”,必定不会被潮流容纳。因此,他没有陷入执念和纠结之中,他知晓该过去的就应承认是过去。这样,陷入失意困境的灵魂经过艰难的摸索、怀疑、拒绝和辨认,重新确立了精神方向,终于找到了一条充满逸情的出路——逍遥。
丽珊和鲁明对紫绸花服的当代价值的不同认定,隐喻着不同个体面对同样的不幸、荒谬时的不同认知。他们同样在复杂的感受中认识了世界和人生,并带着紫绸花服跨入新时期,然而他们却走向了不同的道路,有着截然不同的肯定自我的方式,重新确立了判然有别的信念。不同的信念源于不同的内在感受,因此首先必须清楚他们是如何感受人生和命运的无常与残酷。根据现象学的原则,我们事先不是关注他们内心做出的存在判断,即他们对世界和人生的认识,而是应考察作为存在判断依据的精神意向性结构,从心理意向的本原性入手,分析和描述意向心理的种种特质。不同的判断正是由这些不同的精神意向构造出来的。人的存在与世界具有一种共在的关系。作为个体的人在世界中虽然与外界事物的关系是偶然的,但与作为整体的世界的关系则不是偶然的,而是物质的客观性与主观能动性相交织的结果。在以丽珊为代表的一类人眼中,世界包含着恐惧、困惑、怀疑,而在以鲁明为代表的一类人眼中,世界却包含着无限的适己性,呈现出意趣盎然的恬然生机。这与不同个体的精神方式、内在意识中的精神意向是有关的。
如果以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结构区分这两种精神意向,我们可以把鲁明的精神意向的基本要素称为“乐感”。乐感是把现世生命的快乐感受作为精神在世的基础,与道家的超道德、超历史,与自然宇宙相契合的清虚恬然之乐是相关的。它追求的是超越外部事物的限制,转向主体的情态本身,达到个体自足心态的盈盈之乐。快乐情态超越了伦理秩序和自然宇宙,就成为了终极性的存在。快乐感受的首要性质是保持心意上的愉悦状态,个体此时的主观能动性主要用于消除内部和外部刺激形成的张力,造成心态波动,以求得心态上的平衡快适。乐感在根本上就是个体在满足求乐需要时对自身心意的调节和把控,以及对心理情愫本身的自怡满足。因此,当鲁明看到子一辈不接受紫绸花服,看到丽珊的努力失效后,他并没有陷入失意的情绪,反而“爽朗地大笑着说:‘你给出去,我还舍不得呢。’”[2]396。鲁明知道强行进入这个时代只会是徒劳,顺其自然才是最佳选择。
与之相对,丽珊面对紫绸花服带有一种深深的忧患之情,她担心自己被时代遗忘,从中我们可看到她的精神意向的基本要素是一种“忧感”。只有当个体自身感觉缺乏某种东西时,精神世界才会有忧感。如果精神意向的目的指向心态之外的对象,就像丽珊对紫绸花服寄予了太多希望,势必造成内心需求的张力不断扩大,心态的剧烈波动导致紧张感的产生,如忧愁、焦虑。忧的本质是对尚不存在的东西的渴求,渴求本身是自身缺失的一种表现,没有缺乏感也就不会渴求,因此渴求的本质就是填补欠缺。在自身欠缺的状态下,人的精神意向不得不把内在驱动力指向自身以外的对象,忧感由此产生。忧感的实质就是自足与缺失的矛盾,是人面对不协调局面时产生的紧张。
面对现实的发展,小说中丽珊与自己达成了和解,紫绸花服也与自己达成了和解。紫绸花服是丽珊与鲁明爱情的见证,它承载着他们二人饱含温馨、艰难和执着的回忆。最终,丽珊从它身上期待的将来也变成了现实,他们一起度过了那段苦难的岁月,迎来了人生新的春天。丽珊与自己达成了和解,她懂得了属于过去的、历史的记忆就应该沉淀到心底,而自己要用不变的信仰去坦然接受时代的变化,只有向前看才能建设美好的未来。岁月的试炼和内心的平静,永恒的理想和执着的信念正是丽珊拥有的宝贵财富。紫绸花服也与自己达成了和解,它明白了自己在新时期应处的位置,不再执拗于不切实际的幻想。自己承载着历史的记忆,是历史的见证者,这就是自己的价值。顺应时代发展,虽然紫绸花服必会逐渐“氧化”,但是它的精魂,它背后的经验、教训、理想、信仰都已经深深烙印在人们的心里,是永不会“氧化”的。
这种和解背后是对忧感的超越,是追求逍遥的人生姿态,是中国精神意向结构的最佳和理想形式。逍遥即生命意向在尽情的自我表现中乐然自得、恣意摇情,既无待于外,又不拘于己,超脱外部世界和内在自我的局限。王蒙非常清楚知识分子追求逍遥的必要性。这是适应并融入新时期的前提,更是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的前提。王蒙在本篇小说发表的当年写了一篇散文《清明的心弦》,以此回应他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所面对的境况,事隔多年之后回忆那段历史,他依然在理解和反思自己是否做到了“清明”。王蒙自言“我追求的我向往的是清明。清就是清楚与清纯,明就是明白与明朗”[4]187,要“保持一种静谧和理性”[4]187,懂得“独立地负责地面对真实,面对别人,更敢于面对自己的良知”[4]187。《木箱深处的紫绸花服》这篇小说带有的逍遥意味也暗含了王蒙思想中的道家情怀,多年后的他在谈论庄子时曾说:“庄子一生论述的主旨就是指出通向逍遥之路,实现个人的与内心世界的超脱解放。”[6]内在精神世界的自由与独立是庄子式的逍遥,木箱深处的紫绸花服在人心的深处慢慢氧化则是王蒙的逍遥,二者此时恰不谋而合。
四、结语
王蒙在五十年代确立的知识结构和精神气质,并不意味着进入八十年代后会完全“氧化”,他与大多数复出作家一样在八十年代与现代左翼文学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话语,存在“既即又离”的复杂关系,这在他的小说中就有所体现。干预生活、写真实、人道主义等在王蒙八十年代的小说中仍是隐含的主题,只不过这种具有启蒙性的话语逐渐成为幕后底色,离开了宏大叙事,更注重个体对人的存在状况以及对人与世界复杂关系的探索。因此越来越强调文学的“个人性”是王蒙小说越来越突显的特质。
王蒙在作品中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某些“越轨”可谓是气质使然,就像他的个性无法使他成为一位“合格”的政治家,他自己也承认:“与一个真正合格的中央委员的素质保留着差距。我太迷恋文学,迷恋想象和修辞……我实在缺少杀伐决断的雄心、壮心、决心和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斗争永无穷期的狠心和韧性……压倒对手而不被对手压倒的英雄主义。”[4]186正如小说中的紫绸花服的“氧化”就是个缓慢的过程,王蒙自己“弃旧”和融入新潮流的“重生”也是个曲折探索的过程,他在八十年代末的经历或可看成“旧残余”和曲折探索的具体表现。对王蒙来说,或许这种“氧化”和逍遥的姿态到了九十年代之后才彻底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