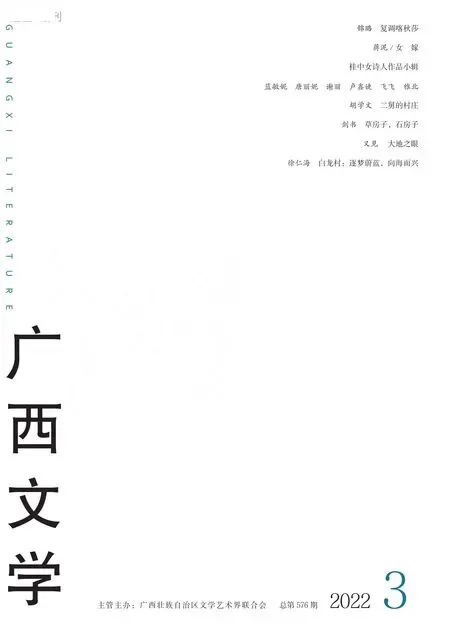墙上的父亲(创作谈)
剑书
一直在心里提醒自己,父亲是不可以书写的。
有什么好写的呢?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一个湮没在乡村人群中的泥腿子,既没有干出令人侧目而视的大事业,也没有德泽乡野的美誉流传八方。
事实上,父亲身上有很多毛病。比如他很固执,我们家族的人不论是谁,不论有多么德高望重,也劝不动父亲改变他的脾性和已经决定了的事情。比如他酒量不大声音大,两杯酒喝下去酒劲慢慢发作,嗓音大得声振屋瓦,令全家人不得安生。再比如他不是一个好庄稼汉,没有操持出一个家里有余粮、银行有存款的家。
这样的父亲,有什么好写的呢?
父亲,在他的有生之年,从来就不是我的书写对象。
我想写的,是慈爱的母亲,是内化于心的山水图景,是一个人奔走的呼喊与挣扎。在我过往的文字里,父亲偶尔露出头来,面目模糊不清,形如远远走来的人,只听见咳嗽声,难辨真容。
直到父亲停止了呼吸,躺到棺材里,埋身黄土之下。
直到我坐在空空荡荡的堂屋里,看着墙上父亲的遗照,再看着母亲的遗照,他们都用包含千言万语的目光看着我。我自言自语:“我现在没有爹,也没有妈,我现在是一个孤儿……”
直到这个时候,我方才感觉到父亲对我如此重要。
这个家,如果没了父亲将会是什么样子?可以想见的是,我的人生轨迹一定会改写,不会深切感知到父亲这个称呼的重量,更不会领悟出岁月长河处处有父亲支撑的真味。
于是,我就开始酝酿写父亲。
第一稿,我只写了一个开头就没有办法写下去了。
书写骨肉至亲,有一种撕开伤口再次缝合的剧痛。
解决这个剧痛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回忆,不去书写。
书写,有时候是一种残忍。
那一段开头我是这样写的:“我的身影像寒夜刺骨的风。刺骨的风裹挟雨水、草叶、泥沙,翻山越岭向百里之外的老家扑去。那雨水、草叶、泥沙不是真实的物质存在,是我内心卷起的波澜,如石头、如生铁、如干枯的河。”标题也不是《草房子,石房子》,而是《风吹散》。
这样的调式,起得像在陡坡上行走,攀山而上,阻隔重重。
最好的办法,就是立定,转身。
就这样,稿子一丢,就丢了大半年。
直到有一天,我又坐回冰冷的板凳,重新敲打起了键盘。
不继续写,我无法越过内心的高山。
这一写,就从早晨八九点写到深夜十二点。中间没停过吃个饭,打个盹。
那一天,我仿佛是个长跑运动员。
可以想見,那些倾泻而出的文字带有强烈的个人情感,汹涌得像刚下了一场暴雨之后的河流。这些个人情感是一个儿子对父亲的喃喃自语,抑或是在旷野无人处的倾诉。写到激越处,我甚至在恍惚中想把农民的父亲,被太阳晒老的父亲,叫成儿子的英雄。
请原谅我的趔趄和冲撞。这只是把父亲比喻为一座大山的另外一种叫法,这只是一个儿子在追忆父亲的路上发出的长长叹息。
18935005113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