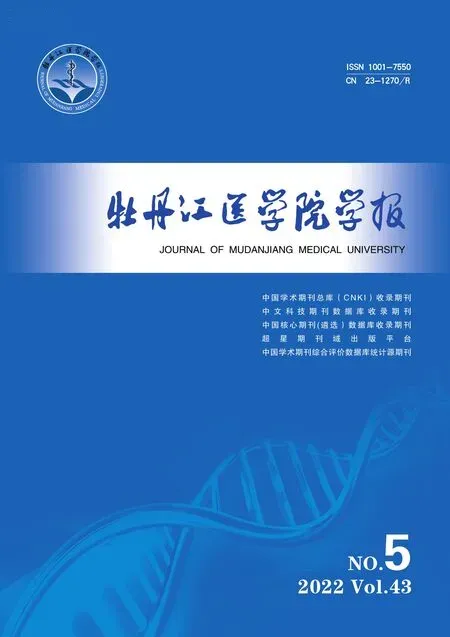肺部微生态在肺免疫炎症活动中的作用及研究进展
朱子晗,李晴晴,熊心雨,徐梦宇,马鸿宇,李 静
(1.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检验科;2.蚌埠医学院,安徽 蚌埠 233000)
众多免疫性及胃肠道相关疾病的病理变化过程都被发现与肠道菌群有关,因此恢复肠道菌群平衡、重建免疫环境就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对于菌群的研究不断深入,目前临床上细菌产物、细菌毒素、益生菌等微生物制剂已经用于免疫耐受的重建[1]。菌群也已被证实可促进对自身抗原的耐受,并且可以调节肠道运动和分泌,维持肠粘膜屏障的完整性,维护免疫系统的正常活动等[2]。本文将从肠粘膜免疫耐受的建立机制、肠道菌群调控免疫系统在肠粘膜免疫耐受形成中的机制、共生菌群诱导免疫耐受等方面作一综述。
1 肺部微生态概述
人类自出生开始,肺脏就通过呼吸作用不断接触空气中的微生物群。但是,基于呼吸道黏膜免疫系统具有物理屏障作用和清除病原体能力,学术界一度认为健康机体的肺脏是无菌环境[1]。随着二代基因组测序等非培养细菌鉴定技术的出现,使得在种属水平鉴定细菌存在成为可能。自第一份关于健康受试者的肺部微生物组的独立培养报告发表以来,已有多项研究使用分子生物学技术进行肺脏细菌的检测与鉴定,证实健康人肺脏中存在常驻微生物群[2]。尽管肺脏微生物群的数量和多样性不及肠道,但其在生理及病理过程中对肺部免疫系统的调控具有重要作用。研究表明肺部菌群主要来源于上呼吸道定植菌及空气中的细菌[3]。因此,肺部微生物群具有个体差异及空间差异,在个体内呈现出持续更新的特点。为了更好地了解肺部微生物区,Dickson等人提出了“适应性岛屿模型(adapted island model)”假说[4],在健康状态下,呼吸系统是一个连续、动态的生态系统,并且其微生物群组成随着来源于上呼吸道并向下呼吸道迁移的微生物而变化。Dickson等人验证了该模型,证明肺脏中的群落丰度随着其离上呼吸道距离的增加而减少。健康人下呼吸道菌群种类与上呼吸道极为相似,但是相对丰度略有差异。健康肺脏中的微生物主要包括厚壁菌门、拟杆菌和放线菌等[5]。
影响肺部微生态组成的因素多样,其中细菌的迁移和细菌被清除出气道的速度起决定作用[6]。此外,肺内环境的变化也可能会影响细菌的组成。这些变化包括pH值、相对血液灌注、吸入颗粒的沉积、氧张力、相对肺泡通气、上皮细胞结构、温度以及炎症细胞的浓度和活性等[1]。综上所述,肺部微生物群主要来自上呼吸道并且菌群数量和丰度相对较少,具有动态变化的特点。肺部微生物群在塑造与调控免疫系统发育、维持肺稳态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受重视。
2 肺免疫系统概述
肺泡主要由覆盖着粘液的单层上皮细胞组成,其表面积约为70平方米,通过呼吸作用与外部环境直接接触。因此,肺免疫稳态是在一个充满微生物和吸入颗粒物的开放环境中建立。肺脏防御体系包括物理屏障和免疫系统,免疫防御体系又分为固有免疫系统(第一道防线)和适应性免疫系统(第二道防线),对抵御有害物质的入侵发挥重要作用。肺脏中居留大量的免疫细胞,包括肺泡上皮细胞、肺泡巨噬细胞、树突状细胞(DC)等,还包括循环单核细胞以及淋巴细胞等[5,7]。少量的病原菌经物理屏障即可快速清除出气道,然而部分病原体可突破物理屏障,进入肺泡内部。因此,就需要启动免疫系统来清除这些进入肺泡内部的有害病原体。固有免疫细胞中如单核吞噬细胞等可直接吞噬并清除病原菌,树突状细胞等抗原提呈细胞通过与外来的病原体(抗原)的结合,进一步激活适用性免疫反应,将T细胞聚集到肺部,负责识别、杀伤感染的细胞。此外,固有免疫系统还具有调节适应性免疫系统的特征,包括在宿主防御中激活抗原特异性免疫反应[8]。肺免疫系统的稳态与微生物群的相互作用是动态的,且受遗传、年龄、生活方式和环境影响。当免疫系统—微生物群处于动态平衡状态时,肺脏对无害抗原具有免疫耐受性。然而,当微生物群失调紊乱情况下,会直接影响肺部的免疫功能,对自身免疫性疾病及肺炎症性疾病的发生或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3 肺部微生态失调对肺局部炎症的影响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9],肺微生物群发生缺陷或失调会对肺的局部免疫细胞产生显著影响,形成局部免疫细胞和微生物区系相互交织的反馈回路,并且可能与肺部各种慢性炎症性疾病的易感性和严重程度密切相关。
3.1 肺部微生态失调对先天免疫的影响肺泡上皮细胞是保护肺脏免受外界病原体入侵的第一道屏障,表面覆盖着一层薄而可移动的粘液。肺部粘液屏障的完整性对肺脏具有重要的保护作用。研究发现,无菌小鼠的肺脏中粘液量显著低于无特定病原菌(SPF)环境中饲养的小鼠,将乳酸杆菌移植至无菌小鼠肺部,其粘液产生量恢复到SPF小鼠的水平[10]。另一项研究表明,在SPF小鼠的肺中,Muc5ac基因高表达,该基因受炎症因子IL-17A和IL-17E等的调节,促进粘液的产生[11]。另外,在多种慢性肺部炎症性疾病中,肺部微生态失调可影响粘液产生。因此,肺微生物群可能通过调节粘液的产生来调节局部粘液屏障功能。
肺泡巨噬细胞对维持肺的正常功能也发挥重要作用,其通过清除外界有害物质、碎片、表面活性物质和凋亡细胞等发挥保护作用[12]。当肺部发生炎症时,肺泡巨噬细胞可以介导细菌清除和启动中性粒细胞募集。金黄色葡萄球菌是导致肺部感染的常见机会致病菌,主要定植在上呼吸道和下呼吸道中。研究证明,金黄色葡萄球菌可募集外周血CCR2+CD11b+单核细胞至肺泡,并诱导其向M2型肺泡巨噬细胞极化,从而显著减轻流感病毒感染引起的肺损伤[13]。此外,有研究表明,肺移植中的肺微生物群失调可能引起巨噬细胞的炎症反应,导致移植失败[14]。
树突状细胞(DC)是肺粘膜系统中固有免疫和适应性免疫的桥梁,肺脏中常包含两种功能不同的DC亚群:常规DC(CDCs)和浆细胞样DC(PDCs)[15]。与肠道内一样,肺内的DC常暴露于外界环境,包括共生菌和病原体。另外,CDCs和PDCs表面存在大量的模式识别受体(PRRs)[15],其与微生物的相互作用可调节肺脏的免疫稳态。在慢性炎症性肺部疾病,如哮喘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中,发现气道粘膜DC数量增加,功能异常。另一项研究表明,肺部共生菌和病原体对体外培养的DC影响不同,病原体可刺激DC表达高水平的炎症因子,包括IL-23、IL-12p70等。因此,肺微生物群可通过调控DC的功能调节局部免疫,参与维持肺脏正常免疫防御体系。
3.2 肺部微生态失调对适应性免疫的影响肺内定居的γδT细胞是维持肺内稳态的重要效应细胞和调节细胞,对肺癌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在内的多种肺部疾病的进展有重大影响[16]。有研究表明,肺微生物态失调会激活居留的γδT细胞,从而促进肺腺癌的发展。此外,肺部共生菌可通过MyD88信号通路刺激髓系细胞产生IL-1β和IL-23,进而诱导γδT细胞的增殖和激活,从而促进肿瘤相关炎症[17]。Yadava等人利用LPS/弹性蛋白酶鼻腔给药诱导COPD小鼠模型,并探究微生物失调与COPD进展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COPD模型小鼠肺部的微生物丰度和多样性均显著低于对照鼠,将LPS/弹性蛋白酶处理的小鼠鼻内移植正常微生物群可诱导γδT细胞的发育,进而加重小鼠COPD慢性炎症等症状。因此,γδT细胞在介导肺微生物群失调对慢性炎症性肺部疾病进展的影响中起着重要作用。
Th17细胞是IL-17A和IL-17B等促炎细胞因子的主要来源。在特发性肺纤维化小鼠研究中发现,该小鼠存在肺微生物群失调,进而诱导白细胞介素-17B(IL-17B)的产生。通过调控肺微生物群或中和IL-17B均可改善疾病进展。进一步研究发现,拟杆菌属(Bacteroides)和普雷沃氏菌属(Prevotella)中的部分共生菌可促进纤维化发展[18]。提示Th17细胞及其分泌的促炎因子可导致菌群紊乱加重肺纤维化等疾病进展。
调节性T(Treg)细胞在维持肺脏免疫耐受中具有重要作用,可抑制过敏原和异种抗原等有害免疫反应。肺微生物群可调控DC表达PD-L1促进Treg细胞发育,加强其免疫抑制作用[19]。研究发现,在多种慢性炎症性肺部疾病中,如囊性肺纤维化(CF)和COPD,Treg细胞数量减少,且与疾病进展有关[20]。我们推测,肺微生态失调可导致Treg细胞受损,使其免疫抑制能力减弱,从而加重炎症性疾病的进展。
4 肺局部炎症对肺部微生态的影响
肺部微生物群的平衡和失调对肺局部炎症有着重要作用。同样,炎症在肺部微生物群的形成中也起着关键作用。炎症环境下,上皮细胞损伤暴露出基底膜基质,从而促进细菌粘附。受损的上皮细胞还产生关键的细胞因子,如胸腺基质淋巴细胞生成素(TSLP)、IL-25和IL-33,来应对细菌成分[21]。这些介质可激活2型先天淋巴细胞(ILC2s)产生IL-5和IL-13,从而导致其它的炎症反应,例如嗜酸性粒细胞与杯状细胞的增殖[22]。研究发现,在过敏和其它慢性IL-13产生状态下,杯状细胞增生会导致气道深处粘液水平过高,从而抑制吞噬作用并进一步增强细菌定植[23]。另外,炎症细胞是儿茶酚胺的来源,而儿茶酚胺可以调节细菌的毒力[24]。此外,研究发现一些菌群会因炎症反应的副产物,如活性氮等物质而受益。有研究证明,在低氧及慢性炎症等条件下变形杆菌门可以利用活性氮物质(许多炎症细胞的副产物)作为末端电子受体,支持炎症条件下的生长[25]。炎症与变形杆菌门的关系在肠道中研究的更为深入,其相互作用的机制对研究肺部疾病具有参考价值。
5 展望
综上所述,学术界在肺部微生物群对肺部免疫的调节的研究领域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阐明了微生物群在肺脏建立局部免疫平衡和抵御外部病原体方面的关键作用。肺的双向和地理隔离结构赋予了肺微生物区系的脆弱性和动态性,因此在各种有害因素的作用下会发生微生态失调,加重肺部疾病的进展。另一方面,肺部微生物区系丰度相对较低,对微生物的分离、培养和鉴定带来了挑战。大量的研究证明了肺部微生物群对呼吸道免疫稳态有重要的调节作用。同时,肺部微生物群的结构失衡与多种肺部炎症性疾病有着密切关系。因此,进一步深入研究肺部微生物群与宿主及肺部炎症性疾病之间的相互关系,使调节肺微生物群成为治疗肺部疾病的一个潜在靶点,对防治肺部疾病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