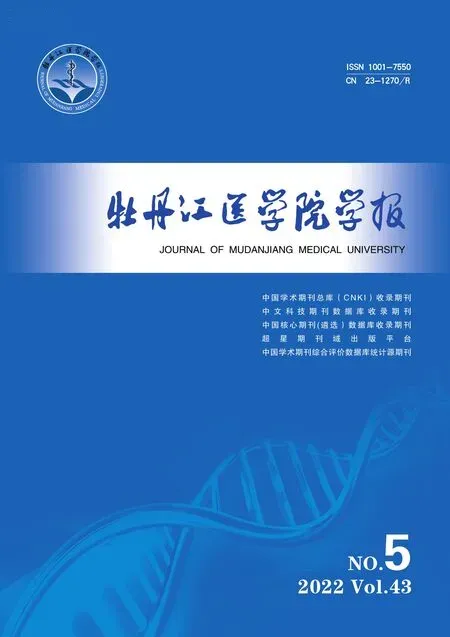肠道菌群和结直肠癌关系的研究进展
王天正,李 琳,何池义
(皖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安徽 芜湖 241000)
结直肠癌作为一种恶性程度极高的肿瘤,随着对其致病机制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发现肠道菌群在结直肠癌的发生、发展及治疗过程中有着重要作用。本文主要选取几类具有代表性的肠道菌群,通过阐述它们的致病机制、代谢产物与结直肠癌之间的联系、肠道菌群在结直肠癌治疗中发挥的作用,为进一步揭示肠道菌群在结直肠癌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及临床应用方面提供参考。
1 结直肠癌概述
结直肠癌是当今世界上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由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于2020年发布的全球癌症数据报告显示,中国新发癌症人数和死亡人数均居全球首位。结直肠癌现作为世界发病率第三的癌症,死亡率高居第二,较往年有持续上升趋势,已成为一种严重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疾病[1]。
2 肠道菌群概述
在人体的肠道中存在着数量庞大的微生物菌群,驻留的细菌数量是人类体细胞和生殖细胞的十倍,由于其代表的微生物基因组也远远超过了人类基因组,因此有学者将人体和寄生在人体内的微生物共称为“超级有机体”(superorganism)[2]。面对如此繁多的菌群,人们通常将它们划分为有益菌、有害菌及中性菌三大类。常见的肠道有益菌包括乳酸杆菌和双栖杆菌,它们可以通过降低肠道pH值、减少病原微生物的定植与入侵以及改变宿主免疫反应等途径发挥有益作用[3]。目前已知的肠道致病菌(即有害菌)包括牛链球菌、幽门螺杆菌、脆弱拟杆菌、粪肠球菌、败血梭状芽孢杆菌、具核梭杆菌及致病性大肠杆菌等。
肠道菌群在人体中发挥着重要的生理作用,它们的某些成分能够产生多种短链脂肪酸(SCFAs),如丁酸、琥珀酸、丙酸等,这些SCFAs在调节结肠上皮细胞的生长和分化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三种SCFAs也是结肠细胞重要的能量来源,包括丁酸酯(BT)、丙酸酯(propionate)和乙酸酯(acetate)[4]。肠道内的某些菌群也可以参与机体营养物质的合成和代谢过程,如双歧杆菌可以从头合成维生素,其中包括B族维生素、维生素K、泛酸、烟酸等,这些维生素在人体的生长发育中起重要作用[5];此外肠道菌群还可以促进肠道上皮的形成、影响肠道上皮的通透性,因此当肠道内缺乏相应菌群时,肠道的形态、结构和细胞更新特性会受到极大损害。除了上述生理作用外,特定的微生物菌群在肠道定植会刺激肠道黏膜层淋巴组织的成熟,如果在此阶段无法形成适当的肠道菌群,肠道的免疫系统功能将会受到损害,从而引起某些肠道疾病的发病率上升,如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和大肠癌等疾病[6]。
在正常情况下,肠道内的各类菌群相互制约和影响,共同构成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处于一个相对平衡状态。当这种平衡被打破时,肠道内菌群的多样性就会发生变化,从而引起各种肠道疾病的发生、发展,如炎症性肠病、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肠易激综合征、结直肠癌等。饮食、年龄、药物等多方面因素均会影响人体肠道菌群的平衡,比如人们普遍认为食用高纤维食品可以预防结直肠癌,而食用大量的红肉、饱和脂肪和加工食品则会促进结直肠癌发展;促炎症反应能够破坏肠道屏障、降低肠黏膜免疫功能,并使得细菌移位、加强炎症反应、激活某些致癌物质,从而引起肠道内微生物群落失调,进一步诱发癌症;衰老也会对人体肠道内的微生物群的组成、多样性和功能产生负面影响,原因可能与老年人饮食习惯改变、机体免疫反应发生改变,以及增加了对某些药物的接触有关[7]。
3 肠道菌群和结直肠癌致病的相关性
3.1 肠道有害菌与结直肠癌致病的联系近年来研究发现,一些肠道有害菌可能对结直肠癌的发生发展起着促进作用,其中包括大肠杆菌、产肠毒素脆弱类杆菌、粪肠球菌、牛链球菌等。下面便针对这几种常见有害菌与结直肠癌可能的致病关系进行简述。
3.1.1 大肠埃希氏菌和结直肠癌的联系 大肠埃希氏菌(E.coli)通常被称为大肠杆菌,是一种常见的机会致病菌。致病性大肠杆菌能合成细胞毒性坏死因子、循环抑制因子以及大肠杆菌毒素等物质,从而诱导内毒素的产生和慢性炎症的发生。
E.coli中存在着聚酮合成酶(pks)基因组岛,其编码合成的大肠杆菌蛋白是一种基因毒素,可引起DNA损伤、细胞周期阻滞、染色体结构不稳定等结果,与结直肠癌的发生、发展有着密切联系。近年来由Iyadorai T等[8]学者研究发现,结直肠癌患者与非结直肠癌患者相比,结直肠癌患者体内的大肠杆菌所占比例更高,且pks基因组岛呈阳性的E.coli也更加多见。
3.1.2 产毒素脆弱类杆菌和结直肠癌的联系 脆弱类杆菌(Bacterooides fragilis,BF)是一种专性厌氧杆菌,分为产肠毒素脆弱类杆菌(Enterotoxigenic Bacteroides fragilis,ETBF)和非产肠毒素脆弱类杆菌(Nontoxigenic Bacteroids fragills,NTBF),其中ETBF可以引起人类炎性腹泻并促进结肠癌的发生。
研究表明,ETBF能够增加结直肠癌细胞在体内和体外的干细胞数量,在干性调节中起重要作用。ETBF激活的Toll样受体4(TLR4)通路通过活化T细胞核因子5(NFAT5)促进组蛋白去甲基化酶2B(JMJD2B)的表达,而JMJD2B正是参与胚胎干细胞转化和调节肿瘤干细胞特性必不可少的成分[9];此外ETBF分泌的脆弱类杆菌毒素(Bacteroides fragilis toxin,BFT)还会触发由结肠上皮细胞IL-17R、核因子κB(nuclear factor kappa-B,NF-κB)和Stat3信号转导介导的炎症级联反应,从而诱发粘膜炎症和癌症[10]。ETBF还可以裂解肿瘤抑制蛋白E-钙黏素、激活Wnt/β连环蛋白信号通路,促进结肠上皮细胞增殖从而诱发癌症[11]。根据Butt J等[12]流行病学研究显示,E.coli和ETBF共同感染可能与结直肠癌的发生、发展也有着重要关联。
3.1.3 牛链球菌和结直肠癌的联系 牛链球菌(Streptococcus Bovis)是食草动物肠道中的正常菌群,多见于牛的胃肠道和粪便,也是人体胃肠道中的常见菌群。牛链球菌感染是链球菌引起的心内膜炎的第二大病因,在所有细菌性心内膜炎的患者中占10%~15%,而牛链球菌性心内膜炎与菌血症也是结直肠癌存在的早期线索,25%~80%的牛链球菌菌血症患者伴发结直肠肿瘤,因此牛链球菌和结直肠癌的发生有着不可忽视的关系。牛链球菌促进产生的一些炎性细胞因子可以参与一氧化氮和自由基的形成,如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1β(IL-1β)、白细胞介素-6(IL-6)、白细胞介素-8(IL-8)等,它们会损伤正常细胞的DNA。牛链球菌提壁抗原还能够在体外诱导COX-2过表达,通过合成前列腺素促进细胞增殖、血管生成以及抑制细胞凋亡从而促进结直肠癌发生发展。最近有研究表明,牛链球菌能够通过招募肿瘤浸润性CD11b+、TLR-4+细胞诱导肿瘤抑制性免疫过程,这在结直肠癌的发生过程中也有重要作用[13]。
3.1.4 粪肠球菌和结直肠癌的联系 粪肠球菌(Enterococcus Faecalis)是一种广泛分布于自然界的兼性厌氧菌,属于机会致病菌,多存在于人和动物上呼吸道、消化道、生殖道内。研究显示,与健康对照组相比结直肠癌患者粪便中的粪肠球菌水平显著增加[14]。粪肠球菌致癌的主要原理是诱导超氧化物的产生,损伤肠上皮细胞的DNA从而破坏细胞染色体的稳定性;此外粪肠球菌也可以通过产生金属蛋白酶直接破坏肠上皮屏障,进而引起肠道炎症。最近有学者分离并测序了抗粪肠球菌噬菌体EFA1的基因组序列,证实EFA1在HCT116结肠癌细胞共培养系统中能够破坏粪肠球菌的生物膜,从而对粪肠球菌的生长繁殖起调节作用[15]。
3.2 肠道代谢产物与结直肠癌的联系肠道细菌在人体内活动往往伴随着诸多代谢产物的产生,这些代谢产物在结直肠癌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可起重要作用。常见的代谢产物如SCFAs在调节结肠上皮细胞的生长和分化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它也是结肠细胞重要的能量来源。有学者发现丁酸盐能够起到抑癌作用,原因可能与丁酸盐抑制了肠道内促癌活性的酶如组蛋白脱乙酰酶有关[16]。一些学者研究了SCFAs在大肠癌治疗中的应用,认为综合利用SCFAs、肠道微生物群及天然化合物在临床上对结直肠癌进行化学预防具有一定的应用前景[17]。
胆汁酸也是一种重要的代谢产物,根据其来源不同分为初级胆汁酸和次级胆汁酸两大类。初级胆汁酸是由肝细胞直接合成而来,包括胆酸和鹅脱氧胆酸;次级胆汁酸则是经过肠道菌群的分解及肝肠循环后形成,包括脱氧胆酸、石胆酸、甘氨脱氧胆酸、牛磺脱氧胆酸、甘氨石胆酸、牛磺石胆酸。与结直肠癌发病有密切联系的是次级胆汁酸,在肠道微生物影响下形成的次级胆汁酸可以促进活性氧自由基形成,从而破坏细胞膜和线粒体,引起DNA损伤、减少细胞凋亡、增加细胞突变,最终使正常细胞转化为癌细胞;高脂肪饮食会导致大肠中次级脂肪酸如脱氧胆酸和石胆酸浓度增加,这是结肠炎症和癌症的危险因素,相比之下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量能够起到抗炎和抗癌作用,这可能与结肠膳食纤维发酵过程中增加了醋酸、丙酸和丁酸等SCFAs的产量有关[18]。
除了SCFAs和胆汁酸,蛋白质最终代谢产物硫化氢也与结直肠癌有所关联。有研究表明,硫化氢能够触发促炎症和高增殖途径,且自身具有遗传毒性物质的作用,因此可能与大肠癌的发展相关[19]。
4 肠道菌群和结直肠癌治疗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肠道菌群和肿瘤关系研究的不断深入,有学者发现肠道菌群和不同的抗癌治疗方式间存在着双向的相互作用,即不同的治疗方法可能会导致肠道菌群发生不同的改变,而肠道菌群的这些改变反过来又有助于人们选择不同的治疗手段进行抗癌治疗[20]。有研究表明,在肿瘤的化疗和免疫治疗中,肠道细菌在调节宿主对抗肿瘤药物的反应中起到关键作用[21]。
临床研究表明,化疗会导致肠道中微生物组成发生变化,如乳酸杆菌和双歧杆菌减少、大肠杆菌和葡萄球菌增加,并且还会因损伤肠道上皮导致微生物群易位,在肠系膜淋巴结等外周淋巴器官促进免疫细胞成熟和干扰素γ等分泌因子的产生,这些变化有利于粘膜的愈合和抗癌反应。同时一些口服药物和注射药物也需要依赖肠道菌群转化为活性形式发挥抗癌作用。此外,肠道菌群也可以促进某种药物代谢物的产生,抑制用于另一种药物解毒的关键酶,从而增强药物的副作用,如拟杆菌属可以将索里夫定转化为溴乙烯尿嘧啶,从而抑制5-氟尿嘧啶(5-FU)的降解,导致5-FU在体内毒性增高[22]。最近有学者研究烟酰胺单核苷酸(NMN)对小鼠肠道微生物群和代谢产物的影响,发现NMN能够增加肠道酪酸产生菌以及某些益生菌的数量,减少嗜胆杆菌和口腔杆菌等几种有害菌的数量,降低肠粘膜通透性从而对肠道产生保护作用[23]。
肠道菌群的组成可能也影响到癌症免疫治疗的功效和毒性。一项对小鼠的研究表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抗pd-1/PD-L1或抗ctla-4可能受到肠道菌群组成的影响,给肠道菌群生长不良的小鼠口服含双歧杆菌的益生菌制剂,反过来会增强PD-L1的抗肿瘤效果[24]。近年来还有学者发现维生素D对肠道菌群的稳态有显著的调节作用,维生素D缺乏症与大肠癌的高发生率密切相关,补充维生素D有利于维持粘膜嗜酸链球菌介导的结肠屏障完整性,从而达到抑制大肠癌发生、发展的目的[25]。这些发现给治疗结直肠癌提供了广阔的思路,通过抗生素、益生菌、益生元或粪便移植等方法对肠道菌群进行调控,以提高抗癌药物的疗效或减轻其毒性。
5 结语
结直肠癌是当今世界上恶性程度极高的肿瘤,发病率正在持续上升,有大量的研究证据表明肠道菌群在结直肠癌的发生、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有的菌群可以分泌毒素、炎性细胞因子引起细胞DNA损害,有的菌群能够通过激活信号旁路等其他途径促进细胞增殖;同时肠道菌群的代谢产物如短链脂肪酸、胆汁酸在结直肠癌的发生、发展中也起到重要作用。通过调控肠道菌群来预防和治疗结直肠癌是时下研究的热门问题,但目前的研究大多还缺少相应的临床试验,随着人们在肠道菌群方面研究的不断深入,一定能够寻找到副作用更小、治疗效果更佳的治疗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