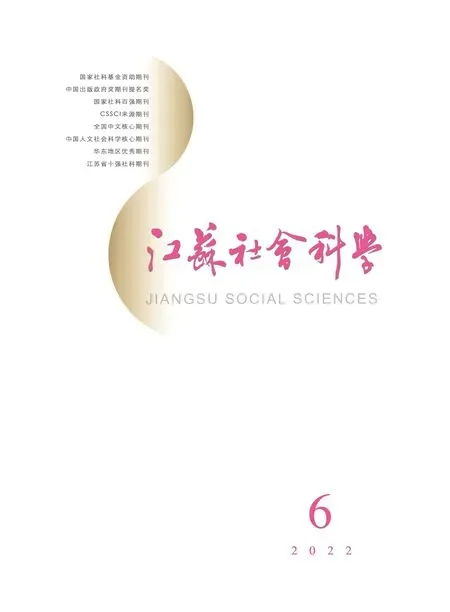中华美学精神及其诗学基因探源
张 晶 刘 洁
内容提要 中华美学精神的研究是对当前坚定民族文化自信这一理念建构的积极参与和理论支持,其方法论具有独特性。与中国美学思想的研究相比较而言,它更加注重中华民族精神活性的描述和阐释,具有明确的当下性和实践性。文化自信的基础是对本民族文化基因的明确认知与认同,中华美学精神的人文智慧包蕴着根本性的文化生成与精神创化的活性基因,醇厚深邃的诗学诗教传统是其中活性力量最为强盛的精神元素。对这一诗性基因的发掘并不限于追溯源动力和原形态,更在于内部精神构成的准确分析和当代意识形态的有效提取,因此极具中华美学精神独特气质的审美感兴论便是这项诗性基因研究的落脚点。审美感兴论的核心价值在于,由触物起情与“持人情性”两大诗学命题共同创化,中华民族无论个体还是集体都在人与自然、人与历史、人与世界的和谐共存与持续流转中获得了精神生活的成长与完善。
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美、追求美的民族,中华文化是一种创造美、弘扬美的文化。中华美学精神,就是建立在这样的民族本性和文化基因之上的关于美与审美的文明表征。正是这个作为存在之生命境遇的美的文化精神,一直引领着我们从日常生活到灵性境界的身体实践和心灵归属。中华文化的美学精神,以它独有的诗意特性,开启、引领、推动、更新着中华民族的感性、理性乃至灵性的各类智慧。
宗白华先生曾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痛切地发问:“我们丧尽了生活里旋律的美(盲目而无秩序)、音乐的境界(人与人之间充满了猜忌、斗争)。一个最尊重乐教、最了解音乐价值的民族没有了音乐。这就是说没有了国魂,没有了构成生命意义、文化意义的高等价值。中国精神应该往哪里去?”[1]宗白华:《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往哪里去?》,《宗白华文集》第二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03页。而如今,我们的民族历经百年沧桑,我们的文化精神已经回归家园,审美价值观的重新树立正在成为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标志之一。我们不仅要民主与科学、真理与良知,我们还要美丽与繁荣、理想与境界。中华美学精神从哪里来?我们要追溯到传统的诗教礼乐中去,更新它,重塑它,发扬它,创造它,使它成为与时俱进的先进文化和自强不息的时代精神。当下我们党的文化战略更是旗帜鲜明地指出了精神文明的发展方向,“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1]《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文艺报》2015年10月15日。,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2]《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国艺术报》2016年11月30日。。坚守中国精神、坚定文化自信,这正是中华文明发扬光大的基本要求。中华美学精神的研究,也必须从此出发,深入到民族文化精神之高等价值的挖掘中,以守护国魂、捍卫人文。
一、中华美学精神研究的方法论意义:精神活性
中华美学精神的研究,在方法论上是有别于中国美学思想研究的。首先是“中华”与“中国”的区别。很显然,“中华”比“中国”是更具有文化共同体意义的概念,因为我们的精神文明、我们的文化传统从来不是单一独行、一成不变的,而是多元并行、与时俱进的,“中华”二字更能彰显中华民族所独有的“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生生不息”的文化特质,即巨大的包容力和强大的传承力。其次是“精神”与“思想”的区别,这里需要更为清晰地加以说明。
我们认为,美学“精神”研究与美学“思想”研究的对象、范围、重心有所不同。精神研究应更加关注“落实”的文明与“持续”的文化,它不必像思想研究那样,追求全面、翔实,以及对历史语境的还原,即它不必关注那些无法复活的死的意识形态,而应重点关注那些依然活跃在民族生命中的或有极大可能被再次激活的传统,即那些可以“落实”到当下现实的实践性的精神文明和能够“持续”生成理想世界的恒久性的意识形态。所以,美学精神的研究相对于美学思想的研究,应该格外强调对文化实力的真实性、可行性和续航性的科学论证。而对文化基因进行深刻而精细的探测、分析、编辑与重组,应该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工作。对此我们党也已作出明确的指示:“中华美学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强调知、情、意、行相统一。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3]《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文艺报》2015年10月15日。这里指出的三个“讲求”,高屋建瓴地概括了中华美学精神的文化基因所在。具体说来,“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是中华民族审美运思方式的独特性,“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是中华民族审美表现方式的独特性,“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是中华民族美的存在形态的独特性[4]张晶:《三个“讲求”:中华美学精神的精髓》,《文学评论》2016年第3期。。中华美学精神研究必须在这些文化基因上进行层层探测与分析,科学地把握自身文化的生成轨迹与发展方向,才能真正地坚定中华文化立场,自信地展示中华审美风范。
同时,我们也应该领会一个“强调”,即“强调知、情、意、行相统一”的方法论意义,即当前对中华美学的研究,不应该只是思辨性的研究,它应该是情感性、意志性、实践性的美学意识形态研究。这正是我们所主张的美学精神研究不同于美学思想研究的根本所在。“精神”不止形成于“知”,它还传承于“情”,发扬于“意”,更要凝结于“行”,成为真正的民族灵魂。这其实也是一种方法论的传统回归与文化自信,即回到“经世致用”的信念中去,使我们的美学研究不回避现实,不固守理论,而是同民族情感、文化意志、艺术实践相结合,落实到精神文明的创造中,使中华审美文化散发历久弥新的文化魅力,从而成为世界文明进程中的重要力量。
当下学者们对中华美学精神的研究,在方法论上已经不约而同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尤其自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发出明确指示以来,关于中华美学精神的研究方兴未艾,很多成果明显突破了以往的思想研究,凸显出美学作为意识形态的当代性与实践性。比如,董学文对“精神活性”的强调。他认为,“即便是在‘中华美学精神’中寻找某种‘不朽’的因素,那这种所谓‘不朽’,也不是一种凝固僵硬的东西,而是指它在当代乃至未来仍有一种精神活性。而且这种活性,又可以优化当代的美学生态,使得当今的文艺和审美更加具有朝气与活力。所以说,‘中华美学精神’是存在于时间之中的,只是这个时间不能被解释为一种静止的时间,而应当被解释为像真理一样是个流动的过程。……从传统的实在自身出发所能够发现的包括‘美学精神’在内的‘精神’,只是‘精神’的古董和‘精神’的化石。它是‘精神’失去精神活性后的残骸,不是精神本身。只有那些既能存在于传统中又能超越传统,在现时代仍具有活力的东西,才属于精神性的存在”[1]董学文:《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中国艺术报》2015年1月21日。。再比如马龙潜对中华美学精神在当前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强调也是一种共识。他认为,“中华美学精神并非一种抽象的理论规定的结果,而是具体存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整体结构中,存在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是通过它所发挥的独特功能和作用得以确认的。从意识形态在文化整体结构中的核心地位看,作为意识形态诸形式的艺术、道德、政治和法律思想、哲学和宗教等,是这种功能结构的最集中、最深刻、最全面的表现”[2]马龙潜:《“中华美学精神”的理论定位及其功能特性》,《文艺报》2015年4月15日。。
由此可见,中华美学精神的研究,与以往的中国美学思想研究有所不同。它在方法论上更加注重美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建构力量的当代文化实践,它的研究对象、范围以及重点都有新的规定。简言之,这种研究就是对文化基因的激活,即对“精神活性”进行“持续”创化,使其“落实”于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现实中。
事实上,就中国传统意义的“精神”观念来说,它本身就是“活性”的。《淮南子·精神训》曰:“夫天地之道,至以大,尚犹节其章光,爱其神明,人之耳目曷能久熏劳而不息乎?精神何能久驰骋而不既乎?是故血气者,人之华也;而五藏者,人之精也。夫血气能专于五藏而不外越,则胸腹充而嗜欲省矣。胸腹充而嗜欲省,则耳目清、听视达矣。耳目清听视达,谓之明。五藏能属于心而无乖,则勃志胜而行不僻矣。勃志胜而行之不僻,则精神盛而气不散矣。精神盛而气不散则理,理则均,均则通,通则神,神则以视无不见,以听无不闻也,以为无不成也。是故忧患不能入也,而邪气不能袭。”[3]刘文典撰,冯逸、乔华点校:《淮南鸿烈集解》,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66—267页。显然,“精神”是人于天地间恒久生存的一种力量,其活性不仅表现于生命机体的活跃,更表现于它能通过超越机体而凝聚全部宇宙秘密于人心的盛大。对于中国人,这种活跃盛大的精神活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属性,是人以生命的整全性即形体、脏器与神理、天道的圆融一体的境界来实践创化不已的伟大智慧。因此,中华美学精神研究,必须以捕捉“活性”为构架、为线索,在尊重历史、尊重发展的前提下,精准提取文化基因,清晰阐释美学内涵,从而将文化创新的理论实践持续下去。
二、文化基因路径的中华美学精神研究:人文智慧
所谓文化基因,就是指民族精神的内核,是一直存在于民族本性中的始终没有磨灭的文化特质,它更多是一种精神文明形式的存在,往往在社会环境发生巨变后仍然显现于民族文化生活的诸多方面。尤其是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民族,这种基因在个体和群体中的文化建构力会格外坚韧和强大。中华民族是人文觉醒极早、文明传承连贯、文化辐射广远的民族,我们的文化基因非常强大,它持续性地生成着和创化着民族自身的精神力量。从文化基因入手的精神研究,就是对精神的内在原力的追索,这一路径不仅要梳理出精神是什么,更要探测这些精神的原形态和源动力,要对“精神活性”再探测、再分析、再检验、再创化,搞清它们“从哪里来”,把握它们“往哪里去”。就中华美学精神而言,文化基因的路径探讨格外必要,美学本身的意识形态属性和文学艺术的人文本质,是重要的决定因素。而更为重要的是,中华文明的“诗性智慧”发达而持久,同时我们这种智慧又与强大的“诗教传统”并行不悖,因此,诗词曲赋、琴棋书画等文艺及其美学精神,本质上都是诗学基因的生化。作为中华美学精神的原形态和源动力,诗学基因就是我们民族独有的诗智(诗知与诗情)与诗教(诗意与诗行)的根本合一。中国诗学的“学”不是学科、学问,而是“智慧”与“教化”的传承和实践。所以,我们所说的诗性智慧就不是西方知识体系中的关于诗的艺术或诗的思辨的学问,“中国诗学”所展现的诗性智慧有着自己的文化命脉和精神特质,它与中华美学精神的基因式关联也具有自己独特的链接类型和黏合方式,这也正是本文最核心的研究问题。
如果从严格的现代学科角度看,中华文化本无美学。众所周知,美学学科是现代中国西学东渐的重要成果之一。但是就民族精神的成长来说,美学学科的引进激发了一种利用原有人文资源进行全新知识生产的热潮,这不仅使一个新的学科诞生了,更重要的是激活了一大批沉睡已久的智慧,使它们以新的知识形态出土,以新的话语方式言说。这就是长期以来所谓现代转换的研究路径。它严格按照西方思辨哲学的知识生产方式,即从范畴的界定到命题的论证再到体系的建构这一清晰路径,将中国智慧重新阐释,以达到同西方学术在同一种话语系统下进行有效对话的目的。尽管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这种现代转换,但同时也引发了严重的失语焦虑。我们的文化精神进展,需要这个过程,但不能完全依赖于此。摆脱失语焦虑的方案之一就是回归中华家园,带着游走四方的生命体验,重新观察故土的一草一木,发现它的特别与珍贵,爱护它、滋养它、培育它,使这安身立命之所更加丰饶与美好。如今这种研究方向应该也是一种共识了。中华美学精神的诗性基因研究,其实就是中华民族诗学化的人文智慧的研究,我们的诗教也是包含在这种智慧中的教化,它不是与智慧相分离的。我们要诠释自己的诗学术语,梳理自己的文化命脉,言说自己的人文情怀,推行自己的美丽精神。总之,我们要“强调诗知、诗情、诗意、诗行统一”的全美智慧。
我们认为,中华美学精神的诗学基因研究,首先应该强调“智慧”观念的回归。关于这一点,已经有学者提出过一些看法(甚至试图建构所谓中国智慧美学的理论体系),比如郭昭第就认为:“西方美学充其量只是知识美学,中国美学则根本上是智慧美学,其学术宗旨不是建构概念范畴和知识谱系,而是追求圣人人格理想。”[1]郭昭第:《智慧美学:中国美学精神及当代价值的重新发现》,《当代文坛》2013年第4期。“西方所谓智慧常常是一种知识和德性,而且总是与善相联系。但中国所谓智慧并不仅仅是一种知识乃至德性,而且往往体现为对知识的中止乃至否定和超越,这是因为知识往往依赖经验的积累和增益,智慧却常常并不依赖经验的积累和增益,甚至体现为对经验的削弱和减损,是将经验减损到极致而生成的本心的自然呈现。”[2]郭昭第:《智慧美学:中国美学精神及当代价值的重新发现》,《当代文坛》2013年第4期。“最重要的是,中国智慧美学拥有西方美学所没有的周遍无碍的学科优势,及统一世界美学的基本思维方式和世界精神。”[3]郭昭第:《智慧美学:中国美学精神及当代价值的重新发现》,《当代文坛》2013年第4期。尽管我们并不赞同所谓“统一世界美学”的说法,但是把中国美学精神的特质落脚于超越知识与经验的“智慧”层面上,这确实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观点。
所谓智慧,其实就是一种不断实现生命“超越”的能力,不仅要超越知识,还要超越情感、超越意志、超越经验,即超越一切当下的知、情、意、行的单一维度,而以它们的整体面貌即完整自然的人格或人性理想,跟世界、跟宇宙、跟自然进行多维度的有效交往。正如有学者所言:“智慧是在对前人的知识和经验总结基础上的创造性思维,是人类辨析判断、发明创造的一种能力。在一个个体与另一个个体或群体相对应时,智慧是这个个体超越另一个个体或群体的能力;在今天和昨天相对比时,智慧是今天超越昨天的能力。”[1]王世梅:《智慧与智慧场》,西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页。所谓创造性思维,核心就是“超越”,超越旧的,创造新的,走出已知,走向未知,在有限的时空中向无限的宇宙超越。因此,智慧不只是知识的增量,更是从知识的束缚中挣脱出“自在的精神”来;智慧不只是情感的深厚,更是从情感的负累中生长出“空灵的精神”来;智慧不只是意志的坚定,更是从意志的执着中领悟出“广大的精神”来;智慧不只是行动的精进,更是从行动的切实中通晓出“和谐的精神”来。可以说,智慧就是一种超越的精神,就是一个民族文化恒久弥新的活性基因。事实上,就人类总体来说,智慧本身并没有什么东方西方之分,“超越”精神是整个人类文明得以生存发展的原动力。但是,就“超越”精神的具体形态来说,东方和西方确实存在差异。仅就古希腊哲学智慧和中国先秦儒道智慧而言,前者可以说是在“灵肉”“人神”关系中思索有关“人性”的超越智慧,而后者则是在“性情”“天人”关系中思索有关“人格”的超越智慧,于是,前者将智慧凝结于“神”之“理式”,后者则将智慧凝结于“圣人”之“道”。所以,前者在“灵魂”升华的“迷狂”中获得“神谕”之智慧,而后者则于“人生”在世的“和乐”中获得“心灵”之智慧。
从智慧的层面,即从超越之精神的层面,而不是从单一的知识或经验的层面去探寻中华美学精神的文化基因,这将使中华智慧的诗性特征凸显出来。我们的智慧类型,就像泰戈尔所言,它“不是科学权力的秘密,而是表现方法的秘密。这是极其伟大的一种天赋”[2]转引自宗白华:《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往哪里去?》,《宗白华全集》第二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00页。。宗白华认为这天赋就是“中国民族很早发现了宇宙旋律及生命节奏的秘密,以和平的音乐的心境爱护现实,美化现实”的“文化的美丽精神”[3]《宗白华全集》第二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02页。,宗白华把这“乐教”即尊重“宇宙旋律和生命节奏”的文化传统,称之为“国魂”。中国的“诗”“乐”本就一体同源,皆为人心之所出。《毛诗·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礼记·乐记》曰:“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所以根本上,我们文化的美丽精神就是“人心”之智慧,我们的国魂就是“人文”之精神。《文心雕龙·原道》曰:“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为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道心惟微,神理设教。光采远圣,炳耀仁孝。”[4]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页、第3页。中国人的智慧正在于此,以“人”为天地之心,以“文”明自然之道,以“圣”立世间之德,以“理”传生命之神。方东美在《中国人的智慧》中明确论述过,中国人是通过“人文的途径,透过生命创进”而获得智慧,“整个宇宙,无论它被分割成多少领域——自然界或超自然界,现实界或理想界,世俗界或神性界,在中国人文主义看来,都是普遍生命流行的境界,这种大化流衍,范围天地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而人类承天地之中以立,身为万物之灵,所以在本质上便是充满生机,真力弥漫,足以驰骤扬厉,创进不已”[5]方东美著、李溪编:《生生之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4页。。
我们认同这样的观念。中国“智慧”的核心就是以“人文”之途径去“创进”去“超越”的精神,而这种人文精神却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更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以人心映照宇宙、以人生顺应自然、以人情寄寓万物的“广大而和谐”的精神。中国智慧的超越性、创造性,实现于无限的生命流转中、绵延的人文教化中、坚定的精神传承中,它从不拘泥于一人、一物、一世、一代,而是永远要把这一人、一物、一世、一代放回到人生在世中、生命流转中、宇宙大化中,去见证价值与意义。“数千年以来,我们中国人对生命问题一直是以广大和谐之道来旁通统贯,它仿佛是一种充量和谐的交响乐,在天空中、在地面上、在空气间、在水流处,到处洋溢着欢愉丰润的生命乐章,上蒙玄天,下包灵地,无所不在,真是酣畅饱满,猗欤盛哉!”[1]方东美著、李溪编:《生生之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0页,第105页。但同时,“在自然的大化流行中,中国哲学认为人应体广大和谐之道,充分实现自我,所以他自己必须殚精竭智的发挥所有潜能,以促使天赋之生命得以充分完成,正因自然与人浩然同流,一体充融,均为创造动力的一部分,所以才能形成协合一致的整体,如果有人不能充分实现自我而有遗憾,也就是自然的缺憾,宇宙生命便也因不够周遍而有裂痕”[2]方东美著、李溪编:《生生之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0页,第105页。。的确如此,“广大和谐”的中国智慧,最终会形成一种人格理想,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乃至民族整体,都将以实现这一理想为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就人格形象来说,这种领悟且践行了“广大和谐”之道的人,就是圣人、真人、神人,而就人格特征来说,他们智慧充盈,能以超越的精神进入全美境界,他们的“知、情、意、行”统一而完整,充实而包容。正如《孟子·尽心》曰:“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由“美”及“大”及“圣”及“神”,人格一步步成长超越,最终凝结为一种文明之秘密。
总之,我们只有回到“广大和谐”的智慧层面去追索中华美学精神的文化基因,它的人文创化、诗性超越的特征才会浮出水面。由此,我们再精进,诗性基因的内核也会有目共睹,而我们也能够充分证明,正是因为诗性基因(即诗学诗教并行不悖的人文智慧)的存在及其不断地变异和创化,才有所谓的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中国智慧、中国精神。
三、中华美学精神的原形态与源动力:诗学教化
如果说,我们中华民族有一种精神活性,那就是人文智慧,即把人当作宇宙之心、万物灵长,人与宇宙万物和谐共处的智慧,那么,与诗教美育并行不悖的人文诗学就是这广大智慧始终保持活性的原形态和源动力。我们认为“中国诗学”不同于西方诗学,它不是纯粹思辨的学科体系,而是“智慧”的和“教化”的,是对人生境界与人格理想的建构与实践。从“诗经之学”到“诗品之学”“诗体之学”“诗式之学”“诗格之学”再到“诗话之学”“诗理之学”“诗评之学”“诗艺之学”等,中国诗学在两千余年的人文传统中,始终没有脱离“以智慧求境界”与“以教化树人格”的精神式晋级路径。无论哪种诗学,它都要展示自己的智慧发现和境界追求,也都要表达由己及人的教化意志和人格向往。中国古代士人首先是“诗人”,即在诗教中成长的正人君子,“诗性”是他作为文明之人的本色、底色,然后才是旁及各类学术、艺术而生成的其他身份。没有诗学参与的学术和艺术,没有诗学教养过的书家、画家、乐者、论者,在中国传统世界中是无法想象的。但我们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一度不仅将诗教剔除于诗学,而且也将诗学剥离于美育,似乎中国文人挥洒画笔、抚琴笑傲时,便是跟赋诗寄情、属文说理的自己毫无干系。事实恰恰相反,不仅诗学与诗教并行不悖,美学与美育亦是并驾齐驱。《论语·季氏》曰:“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论语·阳货》曰:“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这是中国最著名的诗学命题“兴观群怨”说的出处,可它难道不也是诗教和美育的命题吗?诗学,对于一个中国人的成长来说,它就是生命能力逐步养成的整体智慧,它是对万物的感应与际会(兴),是对世事的观察与应对(观),是对他人的接纳与交往(群),是对人生的体味与思量(怨)。这其实就是把认识的(知)、情感的(情)、意志的(意)、实践的(行)智慧全部安排在一场诗性的生命进程中,以学而养、教而化的人生,超越个体与当下,趋向生生不息之至境。
诗学,是中国人表达智慧和实现教化的重要方式,智慧在“诗言”与“言诗”中被整体性内化和外显,内化为个体的修养与灵智,外显为超越于个体的经典与文章。在内是学而养的生命历练与体味,在外是教而化的精神播撒与传承。但这内修外化不是两个分裂的过程,而是从生到死的并行与交融,甚至可以说,“诗”几乎是一个中国人终生的信念。这个“诗”当然不是专指诗歌这种文学体裁,而是指人文化育之下的全美智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诗性基因。吟诗、作诗,此为“诗言”,评诗、论诗,此为“言诗”,这根本就是文人、学人的一种日常生活,甚至“诗言”与“言诗”也不是那么界限分明,甚至以诗言诗,这于中国诗学也并非罕见。更重要的是,我们几乎把所有的智慧都以“诗言”或“言诗”的方式来呈现,诗论与乐论、书论、画论、曲论等文章的书写方式、思考方式、传承方式等,无不相似而共通。这是因为,中国诗学的“诗”是“诗者持也,持人情性”的“诗”,这个“诗”是中华审美文化的总出发点,是在所有学术和艺术中最为流通无碍的人文精神,我们甚至要说,“持人情性”就是中华美学精神的一号基因。
《文心雕龙·明诗》曰:“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1]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5页。刘勰于此表达的诗学观念,有一种智慧的推进。他从汉代纬书中借来“诗者持也”的说法,把“诗言志”“诗缘情”推进到“持人情性”的层面,这是中国诗学的一次智慧性飞跃。之所以说它是智慧的,是因为“持人情性”不仅将“言志”“缘情”这两个有内外偏重的表达进行了统一,而且也将“持人”即人文教化的含义继承下来结合进去,从而使“诗”作为人文智慧的特征得到了极大突显。“诗者持也”本自《诗纬·诗含神雾》,其曰:“孔子曰:《诗》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万物之户也。刻之玉版、藏之金匮。集微揆著,上统元皇,下叙四始,罗列五际。故诗者,持也,以手维持。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2]赵在翰辑:《七纬·附论语谶》,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53页。这里的“持”显然不是刘勰的“持人”之义,而是“持德”“持君”之义,即承天地之德、佐君主之政的意思。而刘勰提出的“持人情性”的“持”,则是扶持端正[3]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附语词简释》,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56页。、培养教育[4]陆侃如、牟世金译注:《文心雕龙译注》,齐鲁书社2009年版,第139页。的意思,“持人情性”就是通过诵诗、学诗、作诗、论诗而能持存“圣人性情”(人格理想)、体悟“自然之道”(生命境界)的诗学实践。很显然,对于一种精神文明的传承来说,“持人”比“持君”、“持人情性”和“维持君德”更具有超越和创化的积极意义。
众所周知,西方美学最初是作为感性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的,其核心研究就是对美的本质、对艺术美的本质和形态、对美感的本质和心理机制进行连续而深刻的追问。在这种知识体系中,人格理想和生命境界并非它的核心议题,至少不是学问的根本目的。但是,在中国的人文智慧中,思辨追问最终总要落到如何抵达人格高度和生命广度这样的问题上,我们对美、美感、艺术与诗的本质思考必须与这个问题相关联才能获得答案。所以,从学科角度附会的话,我们似乎应该把中国美学视为“性情学”而不是“感性学”,把中国诗学视为“人文学”而不只是“诗艺学”。当然,我们的研究其实是要打破中国美学与中国诗学之间的学科界限,把它们看作一体,即“性情”教养与“人文”智慧的不可分。如果说,西方美学最终要在“艺术之诗”中抵达“感性的灿烂”与“人性的深邃”,那么中国美学便是要在“人文之诗”中抵达“性情的和谐”与“生命的广大”。我们特别将“持人情性”当作中华美学精神的一号诗性基因,意义也正在于此。而且我们必须看到,这个命题的“精神活性”非常强大,从古到今,多重延异多次激活,形成了中国人文诗学最灵动的一条精神线索,它跨越“言志”与“缘情”,走向“神理”与“神思”、“物色”与“体性”,最终又走向“神韵”与“性灵”,此中皆是“圣人性情”与“自然之道”并行不悖合二为一的诗家“本色”。
作为中华美学精神的诗性基因,“持人情性”所包含的诗教美育内涵并非等同于“维持君德”之“风下刺上”的政治教化。我们要的是这一诗学命题的当代性和实践性,也就是所谓的“精神活性”,即每一个文化共同体的成员都能拥有“温柔敦厚”的“圣人性情”、领悟“天地之心”的“自然之道”这样的诗学实践。这个活性隐藏在原初语境中,它需要一个全新的激活和创进。这是一种不同于政治教化观的“人文教化观”,确切说,它始于刘勰。《文心雕龙》所言的“神理设教”“温柔在诵”,正是以“原道”“征圣”“宗经”“明诗”为先导的“自然之学”“性情之学”“人文之学”“神理之学”。它其实是一个“广大和谐之智慧”的演进历程,人从天地中来,创化以理、精进为心,又返回天地中去,生命便是这无碍流转的天人合一、人伦承续的“神理”教化,这才是中华文明的根本教化,它不是一君一朝之教育,而是精神传承的整体生命实践。《文心雕龙·原道》曰:“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1]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3页,第15页,第22页,第65、68页。《征圣》曰:“陶铸性情,功在上哲。夫子文章,可得而闻,则圣人之情,见乎文辞矣。先王圣化,布在方册,夫子风采,溢于格言。”[2]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3页,第15页,第22页,第65、68页。《宗经》曰:“诗主言志,诂训同书,摛风裁兴,藻辞谲喻,温柔在诵,故最附深衷矣。”[3]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3页,第15页,第22页,第65、68页。《明诗》曰:“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民生而志,咏歌所含。兴发皇世,风流二南。神理共契,政序相参。英华弥缛,万代永耽。”[4]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3页,第15页,第22页,第65、68页。这些论述显示了一种生命整体性的教化智慧,“道心敷章”为源、“神理设教”为流,“陶铸情性”于内、“温柔在诵”于外,“神理共契”在此、“万代永耽”在彼,中国诗学之诗教正是这种整体性、超越性人文智慧的核心所在。所以我们要明确提出,人文诗教的核心正是中国诗学与西方诗学的本质差异。相对而言,西方诗学的发展路径是一条少数人的冒险之旅程,而中国诗学的绵延承继则是一片祥和安然的生活世界,前者为思辨之学,后者为教化之功。我们美学精神的研究应该比美学思想的研究更加关注这一点,即诗教美育作为诗性基因原形态和源动力对中华美学精神的生成与创化所具有的根本建构性。
关于诗教美育与中华美学精神的关系,有学者已经关注到并试图进行深入的揭示。比如陈望衡就提出,“教化与审美统一的理论,是中华美学的核心精神,这一精神在唐代基本上达到完善地步,此后,教化与审美两者要不要统一的问题似乎不再突出,如何统一的问题则更为文人所重视”[5]陈望衡:《教化与审美的统一:中华美学精神论之一》,《长江文艺评论》2016年第3期。。这个说法的具体细节虽然还需进一步考察,但他对“核心精神”的强调却是我们赞同的。再比如金雅提出,“与西方美学精神突出的理论旨趣相比,中华美学精神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其鲜明而强烈的实践旨趣”;“中华美学精神的实践旨趣,指向人的生命和生活,具有突出的人文意趣、美情意趣、诗性意趣。这也构筑了中华美学最为重要的理论内核”[6]金雅:《中华美学精神的实践旨趣及其当代意义》,《社会科学辑刊》2018年第6期。。这个观念显然与我们所强调的中国诗学的诗教核心以及人文智慧、精神创化等观点深度契合。与上述研究有所不同的是,我们将摆脱一般性的范畴或命题性梳理,把最具有精神活性的那部分人文智慧,从遮蔽或隐藏的状态中激活,使其中的诗性基因能够创化出新的审美精神、新的审美文化,并流行于当下生活与未来文明的建构中。
四、诗性基因与美学精神的生成与创化:审美感兴
中华美学精神的生成与创化源于它的诗性基因,即以人文智慧的诗教美育为原形态和源动力的中国诗学,而这一基因如何能够滋养这种精神文明不断生成与创化即它具体的运行机制是怎样的,是需要继续深入讨论的问题。我们说中国的诗性智慧是“持人情性”的诗学、是“神理设教”的诗教、是“自然之道”的美学、是“温柔在诵”的美育,但其实它们根本上是一件事,它们都由“持”这一具有文化传承意义的精神实践贯彻着、落实着、推动着,即持于人、持于理、持于道、持于文。我们必须超越语义学来了解这个“持”作为精神力量的独特性。
司空图《二十四诗品·雄浑》曰:“大用外腓,真体内充。返虚入浑,积健为雄。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荒荒油云,寥寥长风。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持之匪强,来之无穷。”[1]司空图撰、郭绍虞集解:《诗品集解》,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3页,第19—20页,第24页。此中所谓“持之匪强,来之无穷”之“匪强”“无穷”,便是这“持”的力量,自然而然而又恒常不朽,这是一种了解自然而后顺应自然进而利用自然的博大恒久、既温柔又劲健的精神之力。那么,如何才能“持”呢?或者说,如何才能“持之匪强”而“来之无穷”呢?《自然》曰:“俯拾即是,不取诸邻。俱道适往,著手成春。如逢花开,如瞻岁新。真与不夺,强得易贫。幽人空山,过雨采苹。薄言情语,悠悠天钧。”[2]司空图撰、郭绍虞集解:《诗品集解》,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3页,第19—20页,第24页。如此“持新”便能“匪强”。《精神》曰:“欲返不尽,相期与来。明漪绝底,奇花初胎。青春鹦鹉,杨柳楼台。碧山人来,清酒深杯。生气远出,不著死灰,妙造自然,伊谁与裁。”[3]司空图撰、郭绍虞集解:《诗品集解》,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3页,第19—20页,第24页。如此“持初”便能“无穷”。这是一种世界观和价值观的独特坚守,它是以“岁新”“初胎”为意义持存的基本意象。对于生活世界在生命个体(包括人与物)上的首次敞开,中国的人文诗学给予了无限的关注,因为它就是“持”的起点和“周而复始”的一个全新过程。我们的精神文明从未将“终”或“死”作为思想的核心,因为“生生不息”才是终极理想。尤其在诗学中,“生气远出,不著死灰”这几乎是一种最直截了当的批评话语了。中国诗学无论儒还是道,都是从这“生生”思维中创化出根本的精神来。“持”就是“生生不息”,“诗者持也”就是“文之不朽”,“持人情性”就是守持本性与真情,也就是初心与本色。好的诗书画乐,从来都是与生气充盈的大自然同在,它是“生生不息”的“自然之道”在人文世界中一次又一次敞开的“众妙之门”,它就像自然“岁新”、人类“初胎”一样持续不断地发生、消逝、重来,人文智慧就在生命的流转、绵延、来往之中深刻体验到孕育的张力与重生的惊奇。所以,“持”根本上也是“返”,回到初心,回归自然,在一切尚未生成的时空里即在“虚静”“澄明”的境界中,从头再来、重新推演。这就是老子所说的“游乎太初”与“涤除玄鉴”,也是孔子所说的“思无邪”与“绘事后素”。所谓“返”,不是在原初不动,而是周而复始,必先有“周”而后有“复”,所以“持”与“返”都是一种“周行”的运动,只是这运动总要有静止的瞬间,由此构成一种生命的节奏,那个瞬间就是“萌新”与“初始”,它不是绝对的始终,而只是无始无终的宇宙节律的一次更停与止息。
可以说,没有哪一种诗学或美学比中国诗学更加关注这个周行的运动和重启的止息,这就是中国人的天赋,即对宇宙节奏的秘密了如指掌的智慧。如果说,人的精神活性之核心在人文,人文之核心在诗性,那么,诗性的核心就在这个伟大天赋上,而我们的研究将把这天赋锁定在“感兴”这个只在中国诗学里才大放异彩的美学精神形态上。审美感兴的诗学实践,是最具中国特色的美学原则,也是最具精神活性的诗性智慧,它是最中国的而同时也是最美学的,或者说,是中国美学精神中最有可能将某种知识美学转化为智慧美学、将感性美学转化为性情美学、将思辨诗学转化为文化诗学的基因性内核。因为审美感兴是流通于中国诗书画乐等全部文艺类型及审美文化中的普遍性观念,而且它有着绵长、丰沛、广泛的理论形态,而审美感兴论的开启与延宕,正是在“持新”“守初”的独特精神成长轨迹中实现了自身的积淀与成熟。所谓感兴,就是感于物而兴于诗,“感”是人与世界的基本交往方式,它既是感觉、感知,也是感动、感慨,还是感想、感悟,而“兴”则是人文之首启的显现方式,是以心灵的应答跟宇宙大化交谈的第一种姿态,是人作为天地之心萌发的初次诗意,它既是兴发、兴奋,也是兴趣、兴味,还是兴致、兴意。但同时,“感兴”不是简单的“感”与“兴”,它们的黏合性表达精准描述着甚至规定着“持人情性”的精神起点与生长轨迹,即“感物而动”“兴来如答”这样周行止息的生命节奏。可以说,“感兴”的精神形态,就是生命不断重启众妙之门、重辟自然之道的智慧,它一次次开启人心、引领人文,并指向一切显现之外的无限境界。中国的审美感兴论,既不能拿西方古典诗学的灵感论也不能拿现代诗学的惊奇论来诠释,因为它不是非自主的、一次性的、不可捕捉的,更不是效果性的、情感性的,审美感兴是可以在诗学实践中控制自如的心灵技术,也是可以在诗教美育中被学习、被传承的灵性训练,而且它贯穿在诗性智慧成长的全过程,因此根本上,审美感兴是贯穿感性、理性与灵性即整个精神成长过程的一种内在文化机制,是与宇宙节奏根本契合的生命图式。它是“持人情性”这一文化基因生成创化的运动轨迹和精神落实。
《论语·泰伯》曰:“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正是“持人情性”的基本步骤。皇侃《论语义疏》曰:“此章明人学须次第也。兴,起也。言人学先从《诗》起,后乃次诸典也。所以然者,诗有夫妇之法,人伦之本,近之事父,远之事君故也。又江熙曰:览古人之志,可起发其志也。”“学诗已明,次又学礼也。所以然者,人无礼则死,有礼则生,故学礼以立身也。”“学礼若毕,次宜学乐也。所以然者,礼之用和为贵,行礼必须学乐,以和成己性也。”[1]皇侃撰、高尚榘校点:《论语义疏》,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93页。这也是中华文明教化之道的一种具体程序,学诗以培育丰富而真挚的情性、学礼以训练规范而节制的理性、学乐以养成仁和而文明的心性,它们是一个在自然、自律、自在中人格得以完善的旅程。我们所说的审美感兴,首先指的正是这种诗教、礼教、乐教中的“持人情性”之进程。“兴于诗”是一个起始训练,“立于礼”是一个中间过渡阶段,“成于乐”则是一个情理和合之人生境界的抵达。而且这个过程并非只有一次,它可以像四时流转一般周而复始,只要一个人掌握了回归自然与重启世界的技术,即懂得审美感兴的适时发动,那么他便是在“持”守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可以说,所谓“兴于诗”,便是不断回到诗性的世界里,每一次都仿佛“初”生一般地去发现世界的“新”,陶冶性情、澡雪精神、涅槃重生。《二十四诗品·流动》曰:“若纳水,如转丸珠。夫岂可道,假体如愚,荒荒坤轴,悠悠天枢。载要其端,载闻其符。超超神明,返返冥无。来往千载,是之谓乎。”[2]司空图撰、郭绍虞集解:《诗品集解》,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42—43页。诗是流动在宇宙之中的一种精神,其可“超超神明”,亦可“返返冥无”,这是周行不已的有无相生。如此再想“兴于诗”这一教化之始,便能领悟在中华人文智慧的教化传承中,诗既是起点也是顶峰,而所谓“兴”其实既是一种起始也是一种止息,是起止之间的刹那觉醒与转变,精神于“流动”中重回“雄浑”之“真体”。
历来学者讨论中国美学中的审美感兴论都格外强调“触物起情”的基本内涵,但是这会把审美感兴论局限于审美发生学意义,而掩盖了这一思维机制在个体审美经验的全过程中和在文化共同体的美育训练中的丰富意义,或者简单说,以“触”掩盖了它的“持”,即对“持人情性”之含义的忽视。我们认为,审美感兴论必须同时强调“触物起情”与“持人情性”这两条原则,才能真正体现出中国诗性智慧的独特性,才能跳出灵感论、移情论、惊奇论、偶然论等解读,回到更为浑然流通的中国人文精神中。具体而言,“持人情性”是“触物起情”的先决条件与推行机制,感兴的发生与持续,必然是在一个“性情之人”的生命经验中的事件性存在,而这个“性情之人”即诗人,是首先存在于诗教传统中的,即“兴于诗”的人文启蒙中。我们说,“诗”并不是“文”之起源,而是“文”之“心”,是人文觉醒之后的“圣人性情”所领悟“自然之道”的一种高级形态,它把宇宙的神秘节奏吟咏出来,成为族群中人人共通的精神载体,因此是最早的文化共同体的意识形态。因此,“兴于诗”所教化的正是“人文之心”即“圣人性情”,“触物起情”所触之“物”和所起之“情”,皆是人文之物、人文之情,而非无心之物、无文之情。正是“持人情性”的人文内涵,把审美感兴论与西方的神谕式灵感论区分开,同时也不会将诗性智慧简单地归结为原始的巫术思维,而是更加强调人类自身的心智与灵性,这恰恰就是中国人文智慧的基本特色。
在历代的审美感兴论中,《文心雕龙·物色》中的两个命题应该格外加以关注,即“入兴贵闲”和“兴来如答”[1]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94—695页。,这两个命题非常精准地概括出审美感兴内在机制中“触物”与“持人”的根本关联。“闲”是一种人心的止息状态,却又是“入兴”的最佳时机,性情返回到虚静澄明、浑然天真的初心中,这是一种积极的闲适,在无所为中蕴蓄映照万物、容纳万有的一片胸襟。“答”则是心灵迎来了“万有”入心之后的透彻明了,人心与自然有来有往地持存着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兴来”便是自然入心之后以神思意象显现出生命答案的一种觉醒和领悟。所以,对于一个中国诗人或艺术家来说,诗以及其他所有艺术,是一种通过审美感兴的文化机制去寻求生命答案即生命的价值与意义的活动。甚至可以说,没有“兴于诗”这一文化机制的运行,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文人的精神世界将无法建构起健康积极的价值观、人生观乃至世界观,因为以感兴论为根本特色的中国诗性智慧,是给出生命答案的最直接方式。吟诗作画是传统中国文人几乎贯穿一生的修身养性之术,因为这是直接在“闲”中,与自然、与天地进行直接的对话,是使心灵自由敞开并顺应宇宙的节奏从而聆听到生命根本意义的回答时刻,“兴于诗”不只是幼童之学,而是赤子之心的一生持存与时刻复观。审美感兴论在这个更大更深的层面上去思考,从生命价值与意义的整体智慧中去思考,才能使其文化基因的特性得到更具活性的挖掘和发扬。
中华美学精神的诗性基因研究,是一次探寻民族根基的旅程,我们希望从“精神活性”中发现这个基因的具体编码和文化能量。在这个起点上,中华文化深厚的“人文智慧”慢慢滋养出一棵挺拔茂盛的精神之树,它的枝叶不断超越着原有的时空,一直繁衍生息着诗意和合的新世界。我们的文化基因,是人文的,更是诗性的,它在“持人情性”的诗学诗教中孕育生长,也在“审美感兴”的诗理诗智中成熟再生。
综上,在方法论上,我们首先试图将“持”与“兴”无穷循环的诗性特征以精神现象学的方式尽可能地描述出来,因为只有对“中华美学精神”做现象学式的精确描述,其内在的活性基因才能清晰可辨地被分离出来,才能被当作一种可再生的力量进行创造性的重组与编辑。同时,我们的研究不仅要回归精神现象学的准确描述,还要由此出发进行创造性的阐释,即以中国或现代阐释学的方法进行独树一帜的理论创新,冲破传统束缚,激活那些独有的美学概念和命题,使它们在多种可能的路线上获得精神成长的自由。精神研究必然是更加倾向于阐发和推扬,因为它重在对文化活性基因的探索,它必须是生成式的研究而不能仅仅是回归式的复古,必须在我们的研究中有新的精神可以落实的关键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穿凿附会,我们要在中国阐释学的根本原则基础上自由发挥,在尊重意义相对性原则的同时,守护意义确定性的界限。正是在这样的方法论之下,我们对中国诗学中“持”与“兴”的回环并进特征格外地关注和强调,因为中华美学精神的内在机制依然有着“未发之语”“未竟之意”,每一代人都将探测出自己的一片全新领地,实现解蔽之梦与开辟之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