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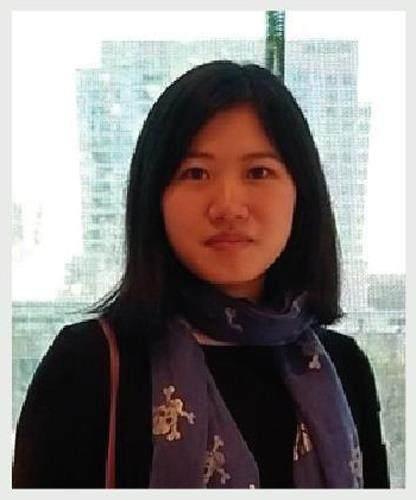
向湾硚
“2021年5月至今,一个名为《芬芳一生》的摄影作品在多座城市展出。照片的主角是旧屋和遗物,观众们却驻足良久,甚至流下眼泪,这些亲切的画面,让他们想起了自己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最近,一篇名为《近8000张让人落泪的照片,是我见过人生最好的告别》的网文配着照片和视频,在网上流行了很长一段时间,前面引号内的文字就是这篇文章的开头。
本来,从出生到今天的二十几年,还不足以撑起“我的生活”,但生活就是点滴积累,不是末了的总结,也不妨眼下就写起。
看着她的嘴唇我感到十分痛苦。
两片嘴唇并不闭合,凹凸着,艳红如血。牙齿上沾染了口红,崎岖相向。一厘米长的睫毛和紫色眼影,一头花白爆炸发过肩,一顶碎花小毡帽。巨大斜挎包在肩上,皮肤黝黑,几抹散布未均匀的粉在两颊。
我们站在一起排队,等待入场。这是伯克利每周三中午的音乐会,免费对所有人开放。那天中午是爵士乐队,热情的节奏音符比往常的“高雅”交响乐更受大家欢迎,等候的队伍绵长。
我偷偷看了她太久,不打招呼实在不好意思。
她五十多了。一个人住。每周来伯克利的图书馆上课。那是专门为成人提供的,类似于“扫盲”的基础课程。她吐字不清晰,但是悠悠的,眼睛还有神。
我不小心问到了她的女儿。她的目光就游走了。
“I usually don’t like to talk about my daughter.” (我一般不想聊到我女儿。)
二十多年前,她的女儿不到二十岁,已出落标致。她每天工作,挣钱,不怎么关心女儿日常。女儿稀里糊涂怀孕了,对方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
她已经太久没跟女儿说过话。女儿现在是一名妓女。她说,挺后悔当初没有花费足够的精力在女儿身上。
口红还粘在她的牙齿上。看着她的双唇,我感到一些痛苦。
小的时候,我是待在外婆家里的,和表姐表弟一起。当我后来回到妈妈爸爸身边的时候,他们已经永远缺席我的童年了。在我上大学之后,假期回到家,妈妈经常会想教育我。她说:“这就是你最大的缺点,都怪我当初没有好好教你……我现在跟你说,你改……”
她說,“最大的缺点”……仿佛,她万分了解她的女儿。她说,“都怪我当初”……仿佛,如果她曾经在我身边,就能把我教导成完美的模样。
但我是,一个有些恶毒的女儿。
我会对她说:“你也知道,你永远没有那个机会了。”
摸着我的嘴唇,好像,有一个词,叫“痛苦”。
疫情以来,崩溃的时刻更加明显了。
疫情之前,再怎么崩溃,也需要在周一早上打理好自己,穿上一身正常的皮相去学校,做一个专业的老师,做一个认真的学生。疫情之后,一旦崩溃,就躺在这张床上,像麻薯一样,越躺越瘫,越瘫越大,越大越起不来。
和心理咨询师的会面更加频繁,一周一次。她总是问我——你所说的“崩溃”是什么意思?有哪些表现?
来到美国之后,这是我的第五个心理咨询师。和心理咨询师的关系非常微妙——这必定涉及偏见——因为你只能在一个完全信任的人面前剥开结痂的伤口——所以你要遇上一个让你舒服的人,符合你所有偏见喜欢的人。
在这一个之前,四个中有两个是我喜欢的,但两个是我不喜欢的。不喜欢的那两个,一个是一位咨询时候嚼口香糖的姐姐,她认真地做笔记,给我要看的资料,但我却感受到了一种轻视,一种——“你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并不值得这些沉重的苦痛”的轻浮。
另一个是一位老爷爷,跟他的会面其实很愉快,他说他去过日本,也对中国文化感兴趣,还会一点中文。他的眼里有爷爷一般的慈祥——我也很希望可以认识他。可是,在他最后要跟我约后面的会面时,我还是表达了自己的偏见——我说,对不起,我希望是一个女性咨询师。
喜欢的人,倒都是相似的。她们不会让我觉得压迫,她们倾听,但是又会给出聪明的提问,让我注意到我自己在刻意掩饰、无意忽视的地方。
我总结了一些会让自己崩溃的“小事”。
一是关乎贫穷,当我发现我花费了不应该的钱;一是关乎自卑,当我看到同辈人令人艳羡的生活;一是关乎价值,当我没有做到自己理想中的样子。
这三件事都直指我成长过程中盘根错节而成的锁链——总是没有课外书读的贫穷童年,靠“成绩”来保护自己不受伤害的学校生涯,靠“优秀”来证明自己是个值得爱的、一点不比男孩子差的女孩阶段。
那么,什么能让我走出低迷呢?一是接触我感兴趣的话题,开始思考;一是被人肯定我的价值;一是让我看到对未来的希望;一是天上掉红包。
我依然像我大学时第一次心理咨询一样把问题和解决办法梳理得头头是道,然后等待着发掘更深的,被我掩埋的小伤口。
我也试图依照这些发现来规避崩溃瞬间,事先安排,然而生活总是先于预测。
最近的一次崩溃来自于课程论文压力。读硕士的时候我总是“提前”的,我会在学期过半时候已经决定选题,后半学期就不断添加素材资料,绝不拖到最后来赶。读到博士,却更多被“不会写得好”的恐惧给抓住了。
这一次崩溃时,我又想到了“放弃”。我总是想到放弃,这个借口越来越无力,因为放弃并不会让我真正快乐,我其实就是过着我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
那个高中时候读伍尔芙《一间自己的房间》时的幻想现在已经实现了。我住在自己布置的精致果壳里,捡来树叶涂鸦,做成李灯,我到校园挖土,在窗台上种青绿的葱和最爱的变色木,我有自己一张安静的书桌,有小巧的厨房,有完整的镜子,有整墙的空白等我贴上诗句,还有音乐——买来一个二手电钢琴,一个朋友线上教我,而我则陪他练习中文。
而这一切,是我自己挣来的。
很多个晚上,我会惊慌自己以后不会再有这样的自在生活,当我只需要养活自己,当我只需要面对自己。
但真正让我惊慌的是,若我再度选择放弃自己。
相信,不会再有了。
再过几个月,我会满25岁,这个数字听起来那样成熟,像个大姐姐一样。
昨天,弟弟跟我说,谢谢你,每次跟你聊天都让我感到舒服。我很心疼我的弟弟,希望以后他有困惑的时候,也都愿意来找我,而对他的每一个困惑,我都有让他感到有帮助的答案。
“独立”的口号喊了很多年,依然身处象牙塔中的自己仿佛并没有底气说出这个字眼——只是,这一路上,也已经做了好多令自己感到骄傲的事情,那么,就继续走下去吧。
大学毕业以来,我一直有一种挫败感。很多同行过一段路的人早已在他们的专业领域成为前列,我就那样看着他们从默默无名到如今,而我似乎还一直是这样暗淡着,裹在未来堪忧的文学专业里,挣扎在总也读不完的书本和令人头痛的论文写作里。
不过还好,我度过了过去三年的低潮期,现在大约走出来了,愿意走起来了,哪怕是蜗牛,也慢慢走起来,心中依然为自己点起烛火的希望。
想在这里简单分享最近这半年让我走出来的三件小事。
很多人用西西弗斯比喻自己的生活,日复一日地将石头推上山顶,循环往复。但这并非是完全绝望的——西西弗斯的希望就在每一天開始推石头时,而他的成就感萌发于每一天结束时候,将石头推至山顶之时。
这就是活着,日复一日,或重复,或看似广义无望,但实则蕴含细小希望的劳作生活。
坦白说,过去三年的读书生涯里少有感到希望的时刻,总是孤独,总是挫败。叹自己英文不够好,一周五百页读得坎坷,而一看芝加哥大学的同行一周页数2000;叹自己读书太慢太少,好多“应该”读的书还未读……总有一种声音在告诉我:你太菜了。
我仿佛,从来没有推动过那一块石头。
一方面,我非常希望自己做一个精准的写作者,写出清晰而深刻的文章;一方面,学业繁重、我总是挣扎着,鲜有能挺直腰杆说“我真不错”的时刻。
这三年,我时常为这样的挫败感笼罩,无数次地想要休学退学,甚至也在硕士毕业时延迟博士入学,来体验“工作生活”。那之后,再回来,则真的是想象的更好的某种生活的借口也没了,只能硬走下去。
这种情况,直到今年夏天才开始好转。
一是我找到了适合自己兴趣的研究议题。
夏天开始读中国现代女性文学,探讨的问题都是我所关心的;秋季学期我继续修人类学系的性别中国课,各种讨论也总让我激动。也正是为这两门课写论文的时候,我真正地感受到我是“有话要说”,而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
我这才懂得,研究必须是自己真的感兴趣,探索问题,否则就只是折磨。而去找到这个兴趣点的路程,就是需要不断阅读那些可能“无味”的资料。
二是我开始主动寻找同路人。
寒假的时候,为了准备综合考试,我组织了线上的生命政治读书会,与其他学校的同仁一起探讨我们关心的议题,既让我感到了并非孤独,而是有同行者,也让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好多。我这才明白,我从来都不必将自己限制在此地,自怨自艾不过是作茧自缚,网络时代,可以四处寻找同路人。
三是论文写作能力的进步。
我的论文写作也有了进步。我终于开始体验到一种如同建筑师般的快感:一砖一瓦往上砌、一字一句的雕琢,直至最终打磨出自己设计的形状。这种极致的精准感和掌控感,是在初期接触这一工具时所无法做到的,因为那时能力有限,眼界有限,想象有限。我终于在接近一个更自如的状态了。
到现在写研究计划,我好像终于找到了一个自己可以发力并愿意努力的位置,这才终于走出了心态上的低谷,回到了充满困惑却兴奋的状态。
这种困惑不是对于自己的人生,而是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种想要一探究竟的力量。
这种好奇让我不再害怕自己此刻的渺小,而是可以感受到自己一点一滴的进步。
那些空大的、与他人比较的目光,都暗淡下来,与我无谓了。
我终于幸运地找到了自己感兴趣的事,更幸运的是,我的工作便是要去做好这件事。
于是,我也可以是勤劳的西西弗斯了。
这是开学的第一周,也是我满25岁后的第一周。生日当天,我告诉自己“珍惜”,而今天,我想告诉自己,我不想再浪费此后人生的一分一秒在抱怨和可悲的顾影自怜中,我只做一个勤劳的耕作者,在思想和文字的天地中,笔耕不辍。
长到25岁,才真的开始懂得“珍惜”二字。珍惜每一天醒来的阳光,珍惜这张安静的书桌,珍惜身边的陪伴,珍惜呼吸。于是最重要的事只是认真活着,认真过每一天,注意睡眠,好好吃饭,做好眼下的一件一件小事。
五月底结束了比较文学硕士第一年的探索,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熬了过来,又知道自己即使叫苦不迭也不舍得真正放弃。
在期中的时候,由于沉重的阅读任务和应试教育竞争体制下力争上游的惯性心理,我几乎想要休学。又在一周一周的挤压里,努力把自己从黑洞里逼出来,继续。
直到期末时候,做西方经典文论课的两道考试题,一到纸上下笔,才察觉出自己的提高——对英语的掌握,逻辑的梳理,理论的把握都进益了。
这个时候,既是挺过来的开心,又有一种落寞:可能,在山下的时候,只能以仰望姿态,对山顶不是向往便是被荆棘扎破吓怕;而只有到一个小山顶时,才能体会短暂翻越的成就感。
开学时候无限激动——终于可以接触这些人类历史上闪闪发光的大脑了!慢慢的,日常的琐碎消磨着思想的光,递增的难度和受挫打压着最初的热情,眼睁睁看着自己疲软下来,越来越拖累。
原来,最大的敌人,不是什么大灾大难,而是日复一日琐碎日常对于最初那份炙热的消磨啊。
我甚至怀疑自己是否适合这个专业了,我甚至开始缜密计划,如何休学开始一种新的可能,给自己注入另一罐鸡血了。
然后看到英国读博的前辈和我一样的“熬”,看到一直认为最适合学术研究的学霸挚友吐露出同样的挫败感,甚至说出同样的“放弃”的话语,我才想到,可能,这一条路,就是这样的,要在无数次打磨一个人的自信心后,坚定一个人的上进心——即使是注定了你会无数次受挫,无数次焦头烂额,无数次临近溃败边缘,你依然没有崩塌溃败,你依然在痛哭之后选择前行——这样的人,才能够承受之后要袭来的更加狂暴的风雪。
苦难是一种双向选择。我选择理想,理想也筛选配得上它的战友。
终于明白了里尔克这句话:“哪有什么胜利可言,坚持意味着一切。”
這个题目看起来好老套,像是小时候老师让我们写“我的梦想”一样。不过小时候写作文就是为了讨老师开心,现在写是一种建立自我秩序的必要——写作是清晰的,说话次之,只有透过写作,想法才成为思考,耗在脑子里的就不过是一团乱麻。
现在要写写这个题目,是因为好似猴子掰苞谷一样,我渐渐忘记了一些曾经就明白的道理,忘记了二十多年来发生的一些珍贵事情。
遗忘是人类致命的缺点,它让一代人不断重复老一代人的错误,又让一个人不断重复自己的错误。
我记得自己在七年前就说“命运是一枚苦果,生活是咽下去的过程”,也可一个人自城区骑行搭车盘山路回乡,如今,却有些怯了。最近看完《指环王》系列,被送上九死一生之路的两位小霍比特人,身兼重担,无甚武功,最后还是完成了使命。
但如若换成两个武功绝顶的人,危险就会少几分吗?成功率就会大一些吗?或许并不会,因为在面对一段无法预测的长远路途时,唯一能凭借的,只能是一腔孤勇,如少年时候的一腔英勇,可螳臂当车,也“泰山石敢当”,在百转千回的磨难中,坚韧,不放弃,出击。不在于能力,更在于意志。
一个人年岁渐长,少了年少的英勇,这种遗憾让人难堪。但也可笑笑说无所谓——因为没有几个人逃得过这股少年气消磨殆尽的过程。
因为小时候的经历,我自以为是个能吃苦的人,如今这读博种种,我这些年来性情的变化,都在质疑这个论断——小时候能吃苦是因为没有其他选择,如今有选择了,为什么还要吃苦?
你可以拿着硕士学位回家找一份还算可以的工作,在小城结婚生子,为什么还要煎熬着读博?如果读博是你想要的,你为什么还会煎熬?
你理想的生活到底是怎样的?
一张安静的书桌,书写的自由,空间,时间。
一群志趣相投的朋友,我们信仰美和真理,在言语照亮的世界里互相依偎;时常散步,时常思索,时常歌唱;是孔子所说“莫春者,春服既成……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我曾经拥有过这样的生活,两次,都因为那个时候我周围有“同类”。
越来越理解《聂隐娘》电影中侯孝贤的描述——她是一个人,没有同类。聂隐娘被送去习武,去社会化,也是异化,不再是一个标准社会规训下的人,长成后回家,却也再回不了家。所有的情感再无处安放,所有的罪过都被迫深埋。此后只有一条路,不回头地走下去。
我理想的生活并不难获得,我现在就有一张安静的书桌,只是我的朋友们四散着,在各自的生活轨道里,我们时常忘记了相互探望。
如果你读到这里,希望你给远方的朋友发去问候,或是,抱一抱你身边的朋友。
你们从不曾分离——
相信我。
(责任编辑:庞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