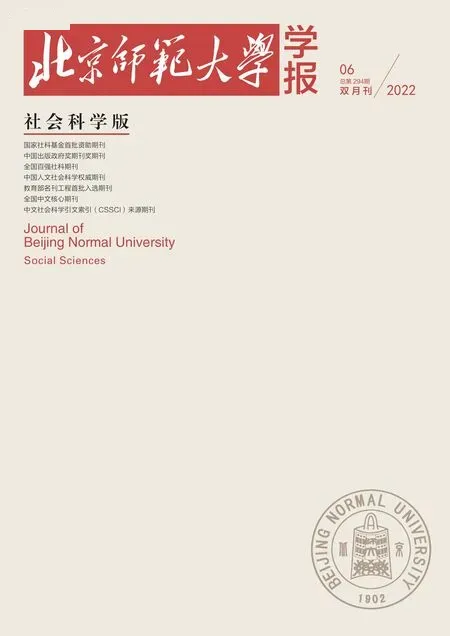新诗标题的现代变革
王泽龙,崔思晨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诗歌研究中心,武汉 430070
现代诗歌标题千姿百态,丰富多彩,是现代诗歌意义的重要元素,在诗歌创作中为诗人所普遍重视,在诗歌鉴赏时被读者首先关注。而中国古代诗歌标题在诗作中的存在感较弱,古代诗歌标题形态在漫长的诗歌史中相对稳定,在逐渐强化的辨体意识下,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制题的固有模式。新诗标题在诗歌现代转型中逐渐摆脱了古诗制题的传统定式,标题与诗人个性和作品风格特点发生了紧密的关联,标题的意义被大大强化。然而,诗歌标题的现代变革这样一个饶有兴味的话题,却较少被学界关注。有学者从古代文体学、诗歌历史变革、副文本等视角探究古代诗歌制题的特点(1)这方面代表性的成果有:吴承学:《论古诗制题制序史》,《文学遗产》,1996年第5期;陈向春、姜国梁:《论中国古典诗歌的“标题”问题》,《作家杂志》,2008年第1期;何砾:《中国古典诗歌的隐含叙事:诗题、诗序和诗集系年》,《中华文化论坛》,2016年第6期;石建初:《我国诗文标题发展史概论》,《中国文学研究》,2001年第1期。。而现代诗歌与古代诗歌标题相比发生了怎样的变革,现代诗歌标题的形态与功能特征如何,标题与诗人创作个性、风格、时代语境有怎样的联系等,均少有涉及,上述问题的研究对新诗的理论探讨与创作实践不无启发意义。
一、诗歌标题形态的现代变革
五四以来,新诗标题打破了传统诗歌标题固定的话语体系后,呈现出自由开放的形态。在制题上或以中心词表明抒情主旨突破诗体辨识范式,或以意象性隐喻超越事实性陈述,以形态的开放性替代传统的封闭性的程式化命题。标题形态的转变成为新诗变革的一个特点,标题的千姿百态增添了新诗的表现力与艺术感染魅力。
(一)从古诗范式性命题到现代诗歌中心词制题
古代诗歌标题的形态变化总体上较为稳定,呈现出历代诗歌制题范式的延续性特点。古诗标题的范式在汉代开始出现,乐府诗以“辞”、“曲”、“歌”、“行”等为题,初步形成了有诗体辨识性的标题范式。在乐府诗的发展中,汉魏古乐府诗题被六朝诗人以拟乐府的形式保留下来。初唐的歌行“题目也仍属古乐府范围”(2)③ 葛晓音:《新乐府的缘起和界定》,《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第165、168页。,盛唐诗人则吸收了古乐府以“三字题概括篇意的特色”(3)② 葛晓音:《新乐府的缘起和界定》,《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第165、168页。。两汉时期的制题意识较弱,偶有沿袭《诗经》中取诗句中若干字为题的制题方式,如《上邪》、《有所思》、《十五从军征》等。至魏晋时期,诗歌标题范式基本形成,出现了大量以“酬”、“赠”、“答”、“和”等为诗题的交际性表述,对后代诗题的拟作有深远影响。唱和、即席赋诗、分题分韵、赋得限韵等交际性的活动盛行,强化了诗歌标题的范式。如魏文帝曾赋诗,命王粲、刘桢、阮瑀、应玚同题共作(4)夏传才、唐绍忠:《曹丕集校注》,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231页。;至唐朝,唱和诗成为了一种流行的风尚,韩孟诗派唱和及元白集团唱和等风靡一时。唐代诗歌在继承前人制题经验的同时,创作出大量新题乐府诗,形成了“××歌送××”、“××行赠××”等标题范式,如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孟郊《新平歌送许问》、杜甫《入奏行赠西山检查史窦侍御》等,皆为诗人行卷和唱和的流行诗歌标题。在唐代行卷诗中,同题之作便于分出诗人之高下(5)王立增:《论唐代乐府诗的交际功能》,《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科举考试也影响了诗题范式的形成,命题限韵出题方式要求考生围绕诗题进行创作,追求“一题到手,必观其如何是题之面目,如何是题之体段,如何是题之神魂”(6)刘逸生:《诗话百一抄》,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6年,第175页。的审题命意效果。“明诗其复古也”(7)沈德潜、周准:《明诗别裁集·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清代 “溯三唐之元本,上窥六朝、汉魏,以无失三百篇遗意”(8)王兵:《清人选清诗与清代诗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62页。。宗唐宗宋思潮助推了复古之风,这一类传统的制题形式至崇圣尚古的明清诗坛,并没有大的改变。
到五四白话文运动时,诗歌接受西方诗歌的影响,诗歌标题打破传统诗歌命题的规制,出现多元自由的命题样态。其中,标题以中心词制题的形式成为较为普遍的形态。中心词制题是诗人对诗歌所关联的时间、场所、事件、情感等多个因素进行综合考量之后提炼的与主题相关的指示性命题。可以说,中心词制题是新诗最早显露出的特征。在胡适早期的白话诗中,已经体现出中心词制题的意识。如《蝴蝶》、《老鸦》、《人力车夫》、《鸽子》、《孔丘》、《寒江》等诗,诗人在中心词的提炼过程中,注重诗题与内容间存在的直接联系,抒写对象成为命题中心。像胡适的《蝴蝶》:“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诗中每一句都以诗题蝴蝶为中心展开描述或议论。古人写蝴蝶则通常不见于诗题,杜甫所写“穿花蝴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所拟诗题为《曲江二首》;杨万里的诗“儿童急走追蝴蝶,飞入菜花无处寻”的诗题为《宿新市徐公店》,两首诗均不以中心词或意象为题目,古诗中这类写景诗的地点性命题多为程式化的。西方诗歌大多选取作品中关键词作为诗题,五四时期新派诗人在对西方诗歌的翻译过程中,受到其中心词制题方式的影响。胡适早期翻译的诗歌《老洛伯》、《关不住了!》等,就是中心词命题。王独清曾翻译诗歌《流光》(龙沙)、《云雀歌》(雪莱)、《纪念》(缪塞)、《心愿》(皮耳士)等,在他的创作《花信》、《春愁》、《埃及人》等诗中都选择了中心词制题的方式。王独清曾直言自己非常喜爱法国诗人拉弗格的那首L’hiver gui vient(《来临的冬季》),他的《最后的礼拜日》“更是Laforgue所爱用的题目”(9)穆木天:《王独清及其诗歌》,《现代》第5卷第1期,1934年5月1日。。
新诗标题在打破古代诗歌制题范式的同时也接受了传统诗歌制题的影响,有的诗题呈现为中心词制题的变体。新诗题中有的选择与古诗题中“歌”、“行”、“曲”等结合,在变化后突出诗歌的中心词意识。现代诗歌标题在中心词和修饰性词语的组合中模糊古代诗歌标题中的文体特征。《梅花树下醉歌》(郭沫若)、《画者的行吟》(艾青)、《生命的哀歌》(冯乃超)等诗题已经很难看到乐府诗题的直接影响,呈现出古今融合的制题特点。早期的新诗标题也呈现出明显的过渡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自觉保持了古典因素的延续。苏曼殊在1914年出版的《拜伦诗选》中,将原题为THE ISLES OF GREECE(希腊的群岛)译为《哀希腊》,“哀”、“赠”、“寄”等诗题在马君武、梁启超、胡适、杨德豫、闻一多等诗人的翻译中,均有沿用这一类诗题的诗歌。胡适《尝试集》中的诗题《赠朱经农》、《哀希腊歌》(译诗)、《水龙吟》、《去国行》、《大雪放歌》等就保留有新旧过渡的鲜明痕迹。
(二)从事实性陈述到意象性命题
古代诗歌标题常常以创作时间、地点、缘起等记事性因素拟题。诗题中保留的创作背景表现出古代诗歌标题的记事功能。如公宴时作诗《皇太子宴玄圃宣猷堂有令赋诗》(陆士衡)、《应诏宴曲水作诗》(颜延年);饯别时作《送应氏诗》(曹子建)、《邻里相送方山诗》(谢灵运);游览时作《泛湖归出楼中玩月》(谢惠连)、《行药至城东桥》(鲍明远)等。记事性标题在古诗长题中得到充分显现,常有数十字或上百字的诗题,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诗歌的序言。古诗长题在魏晋就已有较多出现,诗人“以标出引起诗兴之本事”(10)吴承学:《论古诗制题制序史》,《文学遗产》,1996年第5期。。《昭明文选》中所收记事性诗题数十首,如《古意酬到长史溉登琅邪城诗》(徐敬业)、《从冠军建平王登庐山香炉峰》(江文通)等。新诗标题中,相当一部分诗题延续了古代诗题实用性的形式,即将标题作为记录诗歌创作信息的载体。如《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胡适)、《深秋永定门城上晚景》(傅斯年)、《抱和儿浴博多湾中》(郭沫若)等。以事实性陈述的方式拟题,很难与诗歌整体意境呼应,诗歌标题与诗歌内容往往呈现出断裂的关系。因此,随着现代诗人的审美意识增进、现代诗歌的逐步成熟和表现题材的变化,传统的事实性陈述诗题对新诗的影响逐渐减弱(11)闻一多曾说,“近来新诗里寄怀赠别一类的作品太多。这确是旧文学遗传下来的恶习。……甚至有时标题是首寄怀底诗,内容实在是一封家常细故的信。”(《闻一多全集》第3卷,孙党伯、袁謇正主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第342页)。
真正改变古代诗歌命题固化形态的,是标题中大量出现的现代意象。古代诗歌标题中的意象“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12)⑥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256、290页。,意象的编码在长期的创作中逐渐被固定为一套对应性模式。如以杨柳、长亭、酒等意象喻送别,以鸿雁、双鲤、捣衣等喻思乡,以梧桐、芭蕉、流水等意象喻愁情等。这些趋同的意象选择弱化了诗人的创作个性,限制了诗歌的活力。自晚清诗界革命起,大量新名词出现在黄遵宪等人的诗作中,而新名词进入诗歌标题则成为现代诗歌转型的标志之一。诗人主体在意象的创造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意象复杂、多重的隐喻功能开发与诗人的艺术感觉和表达能力相关。如《立在地球边上放号》(郭沫若)、《我从café中出来》(王独清)、《火车擒住轨》(徐志摩)等诗题,以现代世界的陌生化感受更新了诗歌的意象。标题中新意象的出现带来了现代气息,意象的隐喻重建了诗歌的符号世界。
五四以来,现代诗人尝试以具体的意象展现抽象的题目,让“复杂的情感”能“跑到诗里去”(13)胡适:《谈新诗》,《星期评论》,1919年10月10日。。如胡适的《“威权”》,将“威权”拟人化,以思辨性的隐喻关系透出现代性的思维特征。“威权”高高在上的发号施令与最终被“奴隶”推翻,其中的反抗色彩与胡适挣脱文言桎梏的决心相互映衬。戴望舒的《雨巷》的标题暗示了“五四后”一代知识分子理想失落、人生迷茫、寻路求索的心理意绪。“雨巷”与“姑娘”同属虚拟的象征性意象,被赋予多重现代情绪内涵。艾青曾说,“我认为诗人应该比散文家更化一些功夫在创造新的词汇上……新的词汇,新的语言,产生在诗人对于世界有了新的感受和新的发现的时候”(14)艾青:《我怎样写诗的》,《学习生活》第2卷第3、4期合刊,1941年3月。。受象征主义诗潮影响,现代意象不完全是美的、优雅的、高尚的,甚至是灰暗的、丑陋的。现代诗歌标题的意象体现出日常化、现代化的色彩,一改“深文隐蔚,余味曲包”(15)③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256、290页。的审美追求,转而形成一批传递现代情感和时代精神的创造性意象。李金发的《弃妇》的命名,就是哀怨孤独、绝望无告的身心漂泊者的象征性符号。穆旦的诗题《我歌颂肉体》,将“肉体”置于与“思想”相同重要的地位,被思想禁锢的肉体是“自由而又丰富”的生命根基,“我歌颂肉体:因为它是大树的根,/摇吧,缤纷的树叶,这里是你坚实的根基”,诗歌标题,是对肉体作为生命意义存在的崇高礼赞。
(三)从文体标识到形态的自由开放
古代诗歌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一套结构模式,诗歌的各部件在结构中各司其职。标题在诗歌中多承担着单向的指示作用,其中文体标识是古代诗歌命题中最常见的形式之一。诗题的不同后缀对应着一定的表现范围,同时对应着一定的体式。如乐府诗标题中有“引”的诗歌与琴曲有关,而“曲”、“怨”类诗题则与闺情、宫怨等内容相关,如李白《玉阶怨》、王维《秋夜曲》等。标题中的文体标识体现出古人强烈的辨体意识,辨体反映出古代典章制度的影响,辩体宗经维护了文学领域的等级秩序。“文章以体制为先,精工次之。”(16)陈梦雷等:《古今图书集成·文学典》第六二一册,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第38页。辨体就是等级与秩序的区分和确立,正如曹丕所言:“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17)萧统:《昭明文选》,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1年,第529页。黄侃认为《文心雕龙》中的“文能宗经,体有六义”,“六者之中,尤以事信、体约二者为要”(18)④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第19、32页。,可见辨体是文章规范的重要准则,鲜明的文体对创作提出了形式的要求。同时,辨体也影响着文体的风格,“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19)③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第19、32页。。辨体成为古诗制题长期遵循的模式。
如果说,古代诗歌的发展逐渐将符号的意义固定化,那么现代诗歌则尝试恢复词的多义性,以此激发语言的活力。开放性诗歌标题的出现较多受现代译诗影响,现代诗人在创作中有意识地吸收西方诗歌异质化的词语和形式,并在创作中将其本土化。诗人在译诗中学习诗歌的命题的突出形式之一,就是在诗题中加入标点符号。柳无忌将莎士比亚的诗歌Blow,Blow,Thou Winter Wind译为《号鸣,朔风呀号鸣》,Take,O Take Those Lips Away译为《取去呀,取去那对唇樱》,译诗既保留了原诗题中的标点,又将英文句意融入现代语法,为新诗拟题提供了参考。而另一些翻译则显示出对外语诗歌的改造,如胡适译蒂斯代尔的诗《关不住了!》(原诗题为Over the Roof),诗人为凸显情绪,在标题中增加了“!”。徐志摩译弗莱克的诗《“有那一天”》,注意保留了诗题中的引号。新诗标题采用标点符号成为了一种流行的现代命题形式,如《地球,我的母亲!》(郭沫若)、《大堰河——我的保姆》(艾青)、《我归来了,我底故国!》(王独清)等。标点符号用语气停顿凸显情感表达,增添了诗歌的表意功能。
美国意象派和法国象征派诗歌对中国的现代诗歌形式的影响甚深。五四时期大量意象派和象征派诗歌译介对新诗文体的影响,便是自由体诗的流行,自由体诗追求的正是语言的自由和题材的自由。新诗人吸收了自由体诗灵活的句法,在诗歌命题中得以大量运用。戴望舒早期在创作《自家伤感》、《残叶之歌》时,诗题语言仍然是中国传统式的;到翻译了洛尔迦的诗后,诗题已经离开了古典的诗歌意境,诗人对于诗性语言的提炼,在西班牙谣曲中得到升华。《对于天的怀乡病》、《我思想》、《我的记忆》、《白蝴蝶》等诗题展现出诗人自如的现代表达。诗歌命题不再受创作范式左右,而是以“诗的情绪”(20)戴望舒:《诗论零札》,《望舒诗稿》,上海:上海杂志公司,1937年。为中心,实现诗题的自由收放。长题如《教我如何不想她》(刘半农)、《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艾青)、《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何其芳),情绪舒展自如,情感鲜明饱满;短题如《毁灭》(朱自清)、《偶然》(徐志摩)、《葬我》(朱湘),主旨精炼,节奏紧促。甚至亦有打破规范的语法结构,出现成分缺失的情况,如《我用残损的手掌》(戴望舒)、《半夜深巷琵琶》(徐志摩)、《在不知名的道旁》(徐志摩)等诗题。
现代诗题形态的自由开放,是五四新思想、新思潮对传统文化思想禁锢的冲决的产物,也是对古代诗歌规制突围的收获。新诗标题的转型,是现代思想文化转型的一个成果,是诗人与诗歌新生自由的一个典型标志。
二、新诗标题的现代功能
现代诗歌标题的开放形态,为标题现代修辞、抒情、叙述与意蕴召唤等功能的实现提供了新途径,为现代诗歌自由丰富的表意打开了新空间。五四白话新诗运动的近期目标,达成了白话对文言地位的取代,自由体对旧格律的转换,这样一个新旧转变只是新思想新形式建设的开端。如何在新的文学地基上重建新诗精神品质、美学形式、艺术风格,需要全方位的诗歌元素的创新与探索。可以说,诗歌标题的变革,是实现新诗现代性转化与现代功能开发的一个重要元素与路向。
(一)突显语言符号的修辞作用
新诗标题充分利用修辞的作用,以比喻、夸张、设问、感叹、省略等多样化的修辞格拓展表意空间。修辞的运用与“语言观念的进步有着血肉的关系”(21)陈望道:《关于修辞》,《中学生》第56期,1935年6月。,语言符号的修辞蕴含着多重内蕴与色彩,聚集于标题中时,常常可释放出丰富的艺术张力。比如,艾青的诗题《透明的夜》中,具有色彩感的“透明”酒杯与黑暗的“夜”相组接,语义场形成对比反差意蕴空间,与“酒徒”们在夜的狂欢中展现出野蛮强悍的生命力互相彰显,“透明的夜”把社会边缘人的“痛苦,愤怒和仇恨的力”在灯光下聚焦,夜色掩盖不了“酒徒”们的愤怒,也压抑不住原始的活力。废名的《宇宙的衣裳》语义场中的“衣裳”被诗人寄予了众多的希望,穿透了“人类的寂寞”,是照亮世间的灯,也是庇护人类的寄托。新诗标题的修辞将审美的时空改变,也颠覆了既有的阅读经验,赋予现代诗歌崭新的审美体验。
新诗标题修辞的丰富与新诗题旨的复杂化相关,当表达的时空受到限制,语言表达的修辞性引申或化用成为突破限制的一种有效选择。俞平伯认为“雕琢是陈腐的,修饰是新鲜的”(22)俞平伯:《白话诗的三大条件》,《新青年》第6卷第3号,1919年3月。,新诗标题的修辞常常帮助诗人在标题有限的容量中表现复杂的题旨。徐志摩的《海韵》戏剧性地描述单纯的年轻女郎向往大海,追寻自由,却被大海吞没的悲剧。诗题“海韵”是一曲为女郎献上的大海挽歌,是诗人告别自我早期单纯追寻爱、美、自由理想唱出的一首忧伤惜别心曲。标题的修辞风格与内容相关,或刚健冷峻或柔婉明媚。冯至的《蛇》以标题的借喻暗示了诗歌的整体意蕴。蛇意象在中国文化中有着丰富复杂的意蕴,冯至另辟蹊径,将自己的寂寞与相思比作静默蜷伏在草丛中的长蛇,它表面漠然冰冷,却藏有万种柔情,对姑娘梦中的静默访问,表达的是寂寞之苦,相思之切,体贴入微的满腔痴情。蛇之意象作为标题,完全褪尽恐惧可怕的意象内涵,呈现的是无比温柔缠绵的美好情感意蕴,成为了现代诗歌修辞性命题彰显现代诗意的佳作。
现代诗歌标题的修辞风格的形成与远取譬的方式相关,如《铜像底冷静》(刘延陵)、《小舱中的现代》(朱自清)等,将异质的喻体相关联,陌生化修辞更加凸显诗歌标题的审美效果。因此,来自于不同语义场的词语搭配,传达的并非词语简单组合相加的意义,而是词与词、物与物之间的重组的意义。标题词语的这种修辞性组合寄寓着的关系,是来自于我们熟知的世界、却又难以用既有经验道出的关系。它体现出诗人在创作上的整体性构思,诗歌标题不再独立于文本之外,而是作为文本的一部分,共同实现诗歌内蕴的建构,标题因此实现了功能的拓展,超越了指示性的实在含义。
(二)叙述与抒情的参与
传统诗歌标题具有抒情功能。古诗标题的抒情往往是封闭的,个人心境化的,这一点与现代诗歌追求的社会传播接受意识明显不同。现代诗歌标题较多直接展现出诗人的社会观察与生活的态度。五四时期白话新诗派中的大量写实诗歌标题,像刘大白的《卖布谣》、《田主来》、《割麦插禾》,刘半农的《学徒苦》、《相隔一层纸》、《一个小农家的暮》,沈尹默的《三弦》、《耕牛》、《人力车夫》等,诗题直接呈现日常生活对象或场景,与诗歌文本具体描述形成互文对应,表现出五四新文学面向大众、面向民间、面向现实的启蒙主义立场与诗歌价值取向。另一路浪漫主义诗歌的浓郁抒情意味在诗题中一目了然。郭沫若的《我是一个偶像崇拜者》、《地球,我的母亲!》、《匪徒颂》等诗题的宏大话语与夸张性修辞,毫不掩饰诗人自我情绪,诗歌题目中传达的是那个时代青春昂扬的激情,让我们感受到五四破旧立新的强大气息。湖畔派诗人汪静之的《过伊家门外》诗题直白,是年轻一代大胆率真爱情的心灵告白。也有形象含蓄的爱情诗命题,像徐志摩自喻为纯洁轻盈、潇洒飞扬的爱情诗题《快乐的雪花》,林徽因的《你是人间四月天》的节制委婉又清纯热烈,典型地呈现了“五四后”一代具有现代浪漫主义品格的唯美诗风。象征主义诗人王独清的《悲哀忽然迷了我的心》、《失望的哀歌》、《颓废》等诗题另成一派,诗题成为了现代都市心灵流浪者感伤迷惘情绪的象征符号。新诗标题注重叙述与抒情的平衡,常以虚词的使用调节抒情与叙事的关系,帮助完成情感的抑扬。像朱自清的《“睡罢,小小的人”》、王统照的《烦激的心啊》、朱湘的《你何必啼呢》、戴望舒的《回了心儿罢》等标题,以语气词的介入传递了更为细腻、迂回曲折的心理与复杂情绪。
新诗的成熟在标题上的表现,是在叙述中延续了日常语言的逻辑,但在意义上却超越了日常的表达。叙述性诗歌标题尝试在个性情感的显露中,纠正抽象诗歌语言的疏离感,返回语言的自然场域,唤醒日常经验的共鸣。何其芳的《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田间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刘半农的《教我如何不想她》等标题,虽然标题的语言接近口语,但诗人在叙述中或是以叙述者的身份进入叙述语境,或是以虚拟的抒情对象完成平等的交流,传达着同时代人的普遍情感,这类标题引领诗性的话语逻辑,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三)诗歌标题的意蕴召唤空间
在读者进入诗歌之前,标题常常制造一种引人入诗的语境,这是传播中的一种阅读契约。诗歌标题作为语言符号具有构建特有意蕴召唤空间的功能。召唤空间概念的最早提出者是沃尔夫冈·伊瑟尔,他在演讲《文本的召唤结构》中提出作品与读者之间存在着相互建构关系,并在其理论著作《阅读活动》中进一步深化了其观点。诗歌的召唤空间是诗人以语言构筑的思想情感表达的空白,在语言之外的丰富含义则由读者参与破解。诗题中的召唤空间由作者创造出一个解读范围,诗人的创作意图是确定的,而诗题的含义在读者的诗歌阅读参与中得以补全。标题中空白的出现在于表达逻辑的截断,或是以显在的姿态制造未完的对话,或是以隐在的视点呼唤想象的加入。诗题以特有的形式引起读者的注意,期待在解读的过程中共建诗歌的内涵。
现代诗歌标题的开放性与自由化,赋予了诗人在表达上有着较大的主动性。诗人常常借对话形式,采用人称代词实现诗题的召唤意蕴,诗题中常出现“你”或“你们”,是作者眼中的理想读者,而“我”则成为现实作者传递意义的虚拟作者的代称。应修人的《妹妹你是水》、汪静之的《伊底眼》等诗题传达出清新自然的五四气息,诗人们将天真烂漫的情感表达诉诸于“你”和“伊”,专注于内心感受的抒发,抒情对象更多是虚指,诗题纯粹的青春话语引领读者的想象,完成爱情的书写。对话预示着双向关系的产生,“我”在对话中期待得到一个回应,一种共生。在这里,“你”的地位和“我”一样,是平等的,同时,“我”的表达并不会左右“你”的思考,“我”和“你”都是独立的,体现了五四以来尊重人的自身、尊重个人情感表达的时代特征。
现代诗歌标题,常常通过语言组合的陌生化,在语言组合之间产生跨越性空白,其深邃的意义在读者的解读中得以显现。如卞之琳的《雨同我》:“天天下雨,自从你走了。/自从你来了,天天下雨:/两地友人雨我乐意负责。/第三处没消息寄一把伞去?”解诗过程中的滞涩延长了读者的审美感受,诗题既言“雨”又言“我”,却又未说明二者间的联系如何。对于“我”来说,“雨”令人苦恼,但若是友人相伴,那“雨”似乎也不那么恼人。“雨”又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苦恼,外界的阻塞与个人的意愿之间永远难达成统一。诗题所言的《雨同我》又何止诗人眼下这一种情感,“我”所感怀的,正由一点推演及万事之忧思。新诗标题在此基础上的发展和继承延续了美学上的正向意义,以空白与语言的相互补充完成诗歌的主题。卞之琳的《古镇的梦》,也是语言的奇异组合,瞎子的白天的算命锣、更夫夜里的梆子,“敲不破别人的梦”,连自己每天也是“做着梦似的”在街上走,生命的寂寞与人世间的隔膜正如千年不变的“古镇的梦”。卞之琳的这类诗题还有《距离的组织》、《圆宝盒》等。
三、新诗标题与表意互动
现代诗歌标题与内容之间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关系,新诗标题在诗歌表意中,以独立的姿态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诗歌的整体结构中,标题与内容各有其意义传达的价值,现代诗歌标题所具有的现代功能恰恰成为了标题与内容之间共生、互动的前提,为新诗表意的丰富和意蕴的深化提供了基础。诗人将诗旨前置以展现个人的创作意图,以标题与内容之间的审美缝隙实现互文性阐释,扩大和丰富了诗歌的内蕴空间。
(一)诗旨前置意识
现代诗歌多以整首诗的圆满性、完全性来表现多变的情感和丰富的思想。新诗标题常作为“诗眼”,将诗旨置于诗歌首位,诗旨是诗人情感或思想的凝结。胡适所言的“须言之有物”(23)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第2卷第5号,1917年1月1日。倡导的就是诗歌情感或思想优先的原则。古代诗人多以形式优先,正如废名所言,古代诗歌形式是诗的,内容是散文的;新诗内容是诗的,形式是散文的(24)废名:《谈新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5页。。古代诗歌讲究诗句炼字,古代诗歌多有名句传世;古人的炼句炼字并不出现在诗题中。诗旨前置意味着诗人创作观念与创作机制的现代转变。郭沫若的诗歌具有代表性。郭沫若的诗《地球,我的母亲》源于诗人突然袭来的情绪冲动,情感的爆发让他“赤着脚踱来踱去,时而又率性倒在路上睡着,想真切地和‘地球母亲’亲昵,去感触她的皮肤,受她的拥抱。”(25)郭沫若:《我的作诗的经过》,《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216页。以“地球母亲”为抒情对象,诗歌每节第一句重复,正呼应了诗歌的题旨。又如其《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以夸张的姿态在诗题中展现出宏大开阔的胸怀。《炉中煤——眷恋祖国的情绪》则以副标题的形式抛出诗人的情感归属,与主标题形成表层与深层阐释的呼应。《凤凰涅槃》是一个神话故事的现代翻新,诗旨象征着古老中国、诗人自我在时代的巨变中涅槃新生。《天狗》的狂啸与奔放,也是对全诗五四破坏创造精神和时代颂歌的大写意。
诗题中题旨的点明更有利于读者对于诗歌的理解。李金发《温柔》中所写,“我以冒昧的指尖,/感到你肌肤的暖气,/小鹿在林里失路,/仅有死叶之声息。”诗人将爱情的感觉诉诸于语言,在整体柔和的色调之中,闪现出些许浓烈的笔墨,“死叶之声息”与爱人之气息或许在诗人耳中被一同捕捉。情感的流露不尽是婉转低回,而诗题《温柔》却正说出了诗人感情的克制,“我奏尽音乐之声,/无以悦你耳;/染了一切颜色,/无以描你的美丽。”这样展露心迹的诗句,异于李金发神秘、深幽的象征诗风,将诗歌终章的内涵前置于诗题之中,为读者的解读提供了意蕴的指引。汪静之的诗将“所要发泻的都从心底涌出”(26)汪静之:《蕙的风·自序》,《蕙的风》,上海:亚东图书馆,1933年。,他的《蕙的风》、《愉快之歌》、《忠爱》、《恋爱的甜蜜》等诗题都鲜明表达出诗人纯洁、真率的爱情体验,诗题的明了直接,呈现了新生一代思想解放、个性自由的时代新气息。艾青则常常在诗题中以“土地”的意象艺术化地表达对于祖国的深爱,将个人情感与时代使命感联系在一起。《我爱这土地》在诗题中便宣言主旨,“土地”联系着诗人对于祖国的忧思,诗人自比飞鸟,生在这土地、葬在这土地,“土地”成了我们理解艾青诗歌主题的关键词。
(二)互文性意义生成
现代诗歌标题是浓缩了的诗歌语言,标题与诗歌内容在意义的传达上二者相互指示,又互相生发新的内涵,标题与内容之间呈现互文性关系,互文体现在文本的内部和外部。现代诗歌标题和诗歌内容在彼此的吸收和转化中,既保持了二者的独立性,又实现了融合与意义的再生。
互文的意义的生成需要一定的语境。现代诗歌标题与内容构成的隐喻结构使得二者的相互指涉成为一种必要的存在。标题的语义集合所代表的情感色彩、语言基调与诗体、句法等因素都发生关联。卞之琳在《距离的组织》中,充分发挥了标题与内容之间的互文性。诗中构筑的梦境与现实之间的交错,给人抽象、繁复、扑朔迷离的审美印象,诗句中交错的典故如“罗马衰亡史”、“盆舟”等结合一句一跳跃的意境转接,恰好印证了标题中所说的“距离”与“组织”。诗中“一千重门外”的声音、“远人的嘱咐”以及 “友人带来了雪意和五点钟”,指向着现实中的距离以及意象关联的距离,而这些又被诗人巧妙地“组织”在一首诗中,诗标题道出了诗人对现实和梦境曲折表达的用意。穆木天《苍白的钟声》则以诗歌形式的变化呼应诗题中“苍白”的意义:
苍白的 钟声衰腐的 朦胧
疏散 玲珑 荒凉的濛濛的 谷中
——衰草 千重 万重——
听 永远的 荒唐的 古钟
听 千声 万声
诗歌以词的间隔代替标点,既形成了语感的停顿,在视觉上也完成了钟声顿挫的美感。诗中词语的重复、交叠,正呼应了钟声不断、绵延的声音表现。
新诗标题互文性的另一种表现在于以直接或间接引用诗句为题的情况,如朱自清《“睡罢,小小的人”》、吴兴华《“当你如一朵莲花”》、戴望舒《我用残损的手掌》、闻一多《忘掉她》等诗题。这些从诗中摘取出来的诗句,一方面是诗中的话语焦点,另一方面蕴含引语对正文的引申。当诗句作为标题的形式出现,参与到诗歌意义的构建时,作为直接引语的诗句,在语气、用词上暗含着诗人的期待用意。成为话语焦点的词或短语或句子,体现了诗人对诗歌内涵的强调和提点。如“我用残损的手掌”在诗题和诗歌的开头、中间两次出现,诗人对“永恒的中国”充满同情与期待的同时,也以“摸索”、“触到”、“蘸着”、“轻抚”等词的引导,让人感受到整个中国经受的沧桑和苦难,标题与中国、希望、诗人的忧思联系在一起,负载了更加厚重的意义。
(三)形象化表意
标题是读者接收信息的第一窗口。形象化表意诗题是诗人思想情感表现的一种外化,意象与思想情感巧妙融合,诗人将要展现的抽象题旨形象化,打通诗歌空间与现实空间,唤醒读者的生活经验。新诗标题是解诗的入口,为诗歌内涵的解读提供视点。闻一多以《死水》为标题,在与诗歌中反复出现的相关意象呼应,以对“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的“死水”的繁复修饰,衬托压抑着的“没有爆发的火山”,让读者感受到了诗人心中被压抑的光和热。周作人的《小河》也为诗歌的解读提供了视点,“小河”不仅是流动的河流,它象征着斗争的过程,伴生着忧郁和光明的产生和角逐,标题“小河”隐含着反抗的意识,紧扣着时代的脉搏,将无数个意象组成意象群,共同指向一个语义场。
我们无法将标题从诗歌中拆分出来,也不能将诗歌分割于标题来理解。卞之琳《圆宝盒》中的“桥”是诗人反复提醒大家关注的意象,“搭在我的圆宝盒里”的“桥”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媒介,而“圆宝盒”才是诗人所寄寓的,诗题在形象化处理中委婉传达诗人对于人生这一抽象命题的具象化理解。“至于‘宝盒’为什么‘圆’呢?我以为‘圆’是最完整的形相”(27)卞之琳:《关于〈鱼目集〉》,《大公报·文艺》第142期,1936年5月10日。。不然,我们很容易在欣赏经验的影响下误读,就像李健吾说的那样:“要不是作者如今把‘圆’和‘宝盒’分开,我总把‘圆宝’看做一个名词。”(28)李健吾:《答〈鱼目集〉作者——卞之琳先生》,《大公报·文艺》第158期,1936年6月7日。
形象化诗题为诗歌的表意提供了多重思路,形象化的表意与诗人思想的直接连通才使形象化的表达具有血肉。在形象化的表意中,诗人思想情感的贴切表达常常靠诗题中部分的形象暗示。郑敏《金黄的稻束》通过诗题与诗歌中“疲倦的母亲”、“远山”、“雕像”等意象相对照,“金黄的稻束”寄寓着诗人的多重情感,以多种意象和修饰实现情感的具体表达,其审美效果超过了在诗题中意象的简单罗列。因此,“金黄的稻束”不仅是“疲倦的母亲”的“养育”精神的缩影,也是“远山”和“雕像”无言奉献的写照,诗人将对见证、哺育人类成长的人和物的感激之情,浓缩于诗题之中,形象化诗题的魅力在与诗歌内容的补全中得以体现。郭沫若将热情澎湃的自我形象化为诗题《天狗》,诗人喷涌的热情和对于个体生命的自信以“天狗”的形象展现出来,他“飞奔”、“狂叫”、“燃烧”,体内充满着无限的能量,甚至要超越肉体的界限,传达出极端的狂热。“天狗”是浓缩了诗人的所有澎湃情感的来源,“天狗”既是诗人自身,也是五四时期无数渴望表达个性、尊重个体的人的时代缩影。
四、新诗标题的个性化与时代性特征
新诗标题呈现出鲜明的个性化风格与时代性特征。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曾大力标举摩罗诗人“率真行诚,无所讳掩”,“掊物资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现代精神,批判旧礼教强调的情不能逾“礼”,诗要止乎礼义的传统(29)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84、47页。。个性之解放,人格之独立是五四新文学的现代思想灵魂。科学民主的思想旗帜,把中国文学引向了关注人生现实与时代变革的方向。新诗标题个性化的表达与时代性彰显就是新文学现代性变革的突出文学现象,现代文学的个性化书写与时代变革可以在诗题古今变革中一目了然。从古代诗歌的歌赋行吟,题赠颂和之类的标题中,我们是难以看到诗人的个性风格与时代特征的。
(一)自我意识与标题的个性化
新诗标题以自我意识的彰显表现诗人的创作个性。我们翻阅五四时期白话新诗集,就能从不同诗歌标题中感受到色彩鲜明的个性化特点。胡适的《尝试集》中的诗题有《希望》、《乐观》、《上山》、《一念》、《一笑》、《一颗星儿》等,透露的是这位首倡新诗改良者清新温和的改良态度。刘半农的《扬鞭集》的诗题,《学徒苦》、《老牛》、《铁匠》、《织布》、《老木匠》、《相隔一层纸》、《一个小农家的暮》等,彰显了这位诗人主张平民主义路线、民间诗风的诗学个性。俞平伯的《冬夜》诗集中,《孤山听雨》、《春里人底寂寥》、《无名的哀思》、《别后的初夜》、《破晓》、《风尘》、《夜月》等,较多保留着新旧转换时期,对古代诗歌抒情传统与写景意境的改造与留念的痕迹。李金发的《微雨》给人们吹来的是异国怪异诗风,《弃妇》、《死者》、《自剖》、《琴的哀》、《夜之歌》、《希望与怜悯》、《寒夜之幻觉》、《假如我死了》、《你可以裸体》等,尽显象征主义诗歌“对于生命欲望揶揄的神秘及悲哀的美丽”(30)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新派诗人有着自觉的标题意识,大多重视诗歌的标题。汪静之在1922年3月4日《晨报副刊》发表了一首题为《短诗·十一》的诗,待到1922年8月出版诗集《蕙的风》时将其更名为《过伊家门外》;刘半农在1923年9月16日《晨报副刊》上发表的《情歌》被收入《扬鞭集》时,改为《教我如何不想她》。闻一多收录在《死水》中的《心跳》,在之后被改为《静夜》。修改后的标题,既贴合着诗人的语言风格,也体现了诗人当时的心理意绪。
往往在表现相同题材中,不同的标题较明显带有不同的诗人个性。如20世纪20年代描写爱情的诗歌中,康白情的《窗外》淡雅而细腻,郑振铎的《云与月》柔和而明朗,应修人的《妹妹你是水》活泼而清新,冰心的《相思》沉静而端庄,徐志摩的《偶然》精致而飘逸,穆木天的《落花》幽远而朦胧,冯至的《我是一条小河》舒缓而低沉。20世纪30年代开展的关于晦涩诗风的论争中,朱光潜、邵洵美、周作人、沈从文等诗人都认为创作要遵从自己的内心运用譬喻(31)朱光潜:《心理上个别的差异与诗的欣赏》,《大公报》,1936年11月1日;邵洵美:《诗与诗论》,《人言周刊》第3卷第2期,1936年3月7日;周作人:《关于看不懂(一)》,《独立评论》第241号,1937年7月4日;沈从文:《关于看不懂(二)》,《独立评论》第241号,1937年7月4日。,使作品“有他自己表现的方法”(32)沈从文:《关于看不懂(二)》,《独立评论》第241号,1937年7月4日。。李金发曾对自己诗歌的难解作出回应,“我的诗是个人灵感的记录表,是个人陶醉后引吭的高歌”(33)李金发:《是个人灵感的记录表》,《文艺大路》第2卷第1期,1935年11月29日。,诗题《一瞥间的灵感》即是诗人创作观的注解,看重感官在瞬间留下的印象。《为幸福而歌》是李金发最为满意的诗集(34)李金发:《李金发回忆录》,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第68页。,诗题《红鞋人》、《叮咛》、《枕边》等在爱情的描写中收束了以往的幻想,代之以浪漫缠绵的意蕴。
标志着个体身份的“我”与五四自由解放的时代精神相呼应,诗人在读者面前得以树立起一个充分表现自我的形象。“他们最称心的工作是把所谓‘自我’披露出来,是让世界知道‘我’也是一个多才多艺、善病工愁的少年”(35)闻一多:《诗的格律》,《晨报·诗镌》第7期,1926年5月13日。。郭沫若的诗题在标题上张扬着个体的独立、自主,《我是一个偶像崇拜者》中的“我”是秩序的破坏者,是对自然、万物的崇拜,甚至也崇拜“破坏”,“我”肯定自己的价值,“我”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我们在赤光之中相见》则兼具大气与婉约,既有诗人对于自然、宇宙的渴望追求,也以群体的呼唤应和了诗歌中低回的情绪。这样丰富、饱满的自我形象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读者曾说,“沫若诗即如此雄放、热烈,使我惊异,钦服”(36)谢康:《读了女神以后》,《创造季刊》第1卷第2期,1924年2月28日。。
(二)新诗观念与标题的风格
现代诗人的诗歌观念直接联系着诗歌创作。闻一多在《律诗底进化》中主张诗歌语言凝练和形式紧凑的必要性,“以最经济的方便,表现最多量的情感”(37)闻一多:《律诗底进化》,《闻一多研究四十年》,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47页。。《死水》诗集中的诗题多二字题目,《口供》、《春光》、《黄昏》、《末日》、《发现》、《死水》、《也许》、《心跳》、《荒村》、《祈祷》等,诗题体现出诗人精心的推敲,突出拟题形式的匀称和情感节制。诗人的创作风格常常在标题上体现为意象的类型性和特征化,意象的稳定预示着诗人创作风格的形成。比如,艾青在20世纪30、40年代创作成熟期的代表性诗歌,《太阳》、《向太阳》、《给太阳》、《太阳的话》、《土地》、《我们的田地》、《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我爱这土地》、《复活的土地》等标题,以具有原型意义的“太阳”和“土地”意象展现对人民苦难生活的关注和对祖国的深沉挚爱。臧克家的《泥土的歌》、《烙印》、《歇午工》、《生命的零度》等诗题,显露出诗人平实朴素的艺术风格的逐步形成。在拟题上具有辨识度的风格,意味着诗人诗艺的成熟。
徐志摩的拟题与诗歌创作一样,展现出浪漫主义诗人的自由潇洒和不拘一格的“体制的输入和试验”(38)陈源:《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西滢闲话》,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第207页。。徐志摩在标题中广泛尝试多种词语、句子和组合形式,在相对稳定的个人风格中实现创新性探索。自由俏皮的表达诗题如《不再是我的乖乖》、《再休怪我脸沉》、《你是谁呀》、《沙扬娜拉十八首》;对话性表达的诗题如《“他眼里有你”》;延续古诗标题范式的诗题如《常州天宁寺闻礼忏声》、《再别康桥》;融合欧化词语而又显出清丽本色的诗题如《雪花的快乐》、《草上的露珠儿》等。此外,在标题的形式上,徐志摩通过标点符号截断或强化了情绪书写,如《别拧我,疼》、《我不知道风——》、《“先生!先生!”》等,这类创新性诗题,丰富、提升了新诗的美学境界,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卞之琳曾提到,徐志摩“为表现方法开了不少新门径”(39)卞之琳:《十年诗草·题记》,桂林:明日社出版部,1942年。,《志摩的诗》在他新诗的阅读中“是介乎《女神》和《死水》之间的一大振奋”(40)卞之琳:《徐志摩诗重读志感》,《诗刊》,1979年9月。。可以说,徐志摩对于诗题风格变化的尝试与成就,充分显示了他在与西方文化融合之后表现出来的实践热情与才华,成为了他对中国现代浪漫主义诗歌的一个艺术奉献。
(三)时代语境与标题价值取向
20世纪科学与革命两大世纪变革之潮流,无不在人类一切社会领域与文化活动中发生影响。中国诗歌的现代转向,突出体现在对时代生活与现实变革的关注。20世纪动荡的社会生活与时代语境不同程度地影响着诗人心境、语言修辞与艺术形式的选择,现代诗歌标题与传统诗歌比较,具有较鲜明的时代色彩。当诗题中传达出来的情感不仅仅代表诗人自身,而且与广泛的同时代读者产生共鸣时,诗歌标题在一定意义上就成为了一个时代精神取向与审美时尚的标记。
五四时期,中国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影响着新诗人的取材和命题,启蒙成为新诗人创作的一种价值导向,许多新诗表现出现实主义关怀,新诗在标题中便直接显露出诗人对于底层人民的关注,如《学徒苦》(刘半农)、《两个扫雪的人》(周作人)、《卖布谣》(刘大白)、《女工之歌》(康白情)等,甚至出现了“人力车夫派”(41)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晨报副刊》,1926年3月27日。。同时,诗歌创作被一些诗人视为他们“对于时代的使命”(42)成仿吾:《新文学之使命》,《使命》,上海:创造社出版部,1927年,第4页。,郭沫若的《笔立山头展望》被闻一多称作是代表着“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43)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创造周报》第4号,1923年6月3日。。其他诗题如《匪徒颂》(郭沫若)、《胜利的死》(郭沫若)、《海上的悲歌》(成仿吾)等都表现出五四浪漫主义思潮的反抗精神。
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上半期,新诗在自我反思中转向中国古典诗学传统中寻找突破,如闻一多提倡新诗创作应“取其不见于西诗中之原质,以镕入其作品中”(44)闻一多:《律诗底研究》,《闻一多研究四十年》,第58页。,古典诗歌的意境影响了新诗标题的面貌。现代派诗人戴望舒、何其芳、林庚、废名的诗,青睐于晚唐诗歌中常见的意象,他们以群体的面貌营造同色调的语义空间,追求一种“晚唐的美丽”,将古典的意境融于新诗之中,诗歌内在精神上透露出20世纪30年代一代知识分子理想迷失中的忧郁与感伤。戴望舒在《残花的泪》、《游子谣》、《雨巷》、《烦忧》等传统气息浓郁的诗题中,显示出内心的忧郁与精神的迷茫。何其芳的诗题如《梦后》、《扇》、《休洗红》、《罗衫》等从古诗词中化用的词句,渗透着古典的韵味,表现出感伤、灰暗的情绪色调。废名的《灯》、《妆台》、《掐花》等诗题,投射出鲜明的佛理禅宗虚幻神秘气息。而坚持大众化诗歌路线的左联诗歌,其诗歌标题现实生活气息浓厚,或政治色彩鲜明,如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吹号者》、《手推车》,殷夫的《血字》、《别了,哥哥》,蒲风的《茫茫夜》等诗题,较典型地代表了左翼现实主义诗歌的主流表达。
抗战时期展现革命主题和书写战争的大量诗歌标题,体现了国防诗歌命题的时代特征,留下了特有的历史印记。其中,相当数量的现代诗歌选本以抗日和救亡为编选题材,选本中的诗歌标题,在关键词的选择上以吸引大众的关注为目标,考虑到鼓动救亡的效果,多以口语化、大众化的语言为主调,体现出国防诗歌“必须采用人民大众所能了解的言语”(45)林林:《诗的国防论》,《质文》第2卷第2期,1936年11月10日。的要求。抗战时期的诗歌标题以简洁明了的艺术特色,促进了抗战诗歌在短时间内及时传播,引起国民的广泛关注。
新诗标题在经历了传统命题范式突破和诗体解放之后,实现了表达空间的拓展、内涵的丰富、形式的自由开放,是诗歌现代性转变的一个突出的形式标志。新诗标题与古代诗学传统有着众多复杂的联系,这种联系仍然会长时间存在,我们主要讨论的是现代诗歌标题对传统诗歌标题的革新与突破。现代诗歌标题的开放性形态与特征,决定了诗人诗歌标题样态的丰富性、复杂性,甚至矛盾性,我们讨论的新诗标题特点与诗人个性化特征等问题,是从现代诗歌标题,包括诗人个体的整体面貌与倾向来立论的。新诗的变革与标题的现代性探索并没有止境,需要我们继续关注与思考。
——评王泽龙《现代汉语与现代诗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