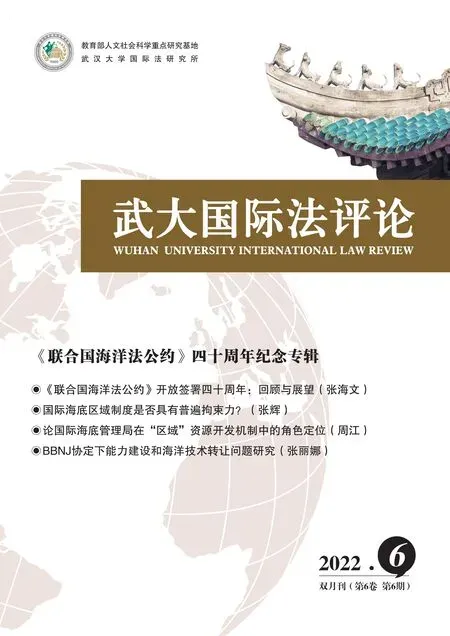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国际法规制的碎片化:现实成因、法律困境与解决路径
蒋小翼 高天义
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是国际海洋法的热点问题,目前,国际社会正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称《海洋法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以下称 “CBD” )两个不同的框架下推进国际造法新进程。①参见郑苗壮、刘岩、徐靖:《〈生物多样性公约〉与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洋生物多样性问题研究》,《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第40页。根据《海洋法公约》进行的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Marine Biological Diversity of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以下称 “BBNJ” )养护和可持续利用问题的国际谈判已历经特设工作组、筹备委员会和政府间会议阶段,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是其核心内容。与此同时,部分CBD 缔约方在谈判中提出,通过 “2020 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海洋目标” 将CBD 的适用范围扩展至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以下称 “ABNJ” )。这无疑将与BBNJ 协定产生一定的交叉与重叠,其工作成果可能导致潜在的法律冲突,进而影响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效果。
BBNJ 协定与CBD 缔约方会议之间的职权冲突反映了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领域的国际法规制碎片化困境。截至目前,国内外学者已经就国际法碎片化和全球海洋治理的碎片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系统性成果。然而,专门聚焦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领域国际法碎片化的研究仍较为有限。碎片化的国际法律机制会对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造成怎样的影响、如何完善相关机制等问题仍不明确。本文试图梳理当前涉及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的国际法律机制,阐明相关国际法规制碎片化的成因,并明确国际法规制碎片化造成的法律困境,最终为完善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机制提出一定的路径选择。
一、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国际法规制的碎片化表现
国际法的碎片化是指国际法体系内部各分支之间缺乏有机联系与统一性,导致相关的原则、规则、制度在适用时产生不协调,甚至相互矛盾、冲突的现象。①参见莫世健:《国际法碎片化和国际法体系的效力》,《法学评论》2015年第4期,第120页。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的国际法律文件缺乏统一性与联系性,海洋生物养护主体多元且分别独立运作,多种养护对象之间相互割裂,这些都反映出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相关国际法规制的碎片化。
(一)相关国际法律文件缺乏统一性与联系性
长期以来,国际社会在渔业、航运、气候变化等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相关领域进行了分散的立法活动。各部门的法律体系分别独立运行和发展,在不违背国际强行法的情况下往往排除其他条约的适用,导致相关国际法律文件数量日趋庞大且不成体系。②参见刘晓玮:《全球海洋治理架构的碎片化:概念、表征及影响》,《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第26页。目前,涉及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的国际法律文件主要有以下几类:
1.全球框架性公约。全球框架性公约的缔约方具有全球性,往往就某一问题提供了包括基本原则与具体措施在内的综合性法律框架。目前,与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直接相关的全球框架性公约主要为《海洋法公约》与CBD,二者是分别独立设计并发展的法律机制,具有不同的目标和宗旨。其中,包括执行协定在内的《海洋法公约》体系建立了系统的海洋环境保护制度,而CBD 则明确了缔约方对其管辖海域生物资源的主权权利,并建立了包括就地保护、移地保护、公众教育等在内的健全的保护机制。此外,《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以下称 “UNFCCC” )目标中的 “增强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 揭示了其与生物多样性养护之间的联系。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 条规定: “本公约以及缔约方会议可能通过的任何相关法律文书的最终目标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少人为活动对气候系统的危害,减缓气候变化,增强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确保粮食生产和经济可持续发展” 。然而,由于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养护长期以来都被视为两个问题,目前UNFCCC是否属于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领域的框架性国际公约仍存在争议。
2.区域性海洋环境保护条约。区域性海洋环境保护条约一般旨在保护特定海域生态环境,其制定者或缔约方主要集中于某特定地理区域。涉及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的区域性海洋环境保护条约主要有《保护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公约》(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Marine Environment and Coastal Area of the North-East Atlantic,以下称 “OSPAR 公约” )《东南大西洋渔业资源管理和保护公约》(Convention on the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of Fishery Resources in the South East Atlantic Ocean)、《防止北冰洋中部公海无管制渔业协议》(International Agreement to Prevent Unregulated High Seas Fisheries in the Central Arctic Ocean)、《中西部太平洋高度洄游鱼类种群养护和管理公约》(Convention on the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of High Migratory Fish Stocks in the Western and Central Pacific Ocean)等。由于区域性海洋环境保护条约的缔约方数量相对较少,且在地理上相对集中,所以各缔约方较容易就特定环境下的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问题达成共识,区域性海洋环境保护条约也往往采取比全球框架性公约更为具体的措施。②See Jeff A. Ardron et al., The Sustainable Use and Conservation of Biodiversity in ABNJ: What Can be Achieved Using Existing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49 Marine Policy 98(2014).
3.特定类型的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条约。特定类型的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条约主要包括 “约束特定人类活动” 和 “保护特定海洋物种” 两类。其中, “约束特定人类活动” 的条约主要规范海洋捕捞、船舶航行等特定人类活动,如《控制和管理船舶压载水与沉积物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Control and Management of Ships’Ballast Water and Sediments)、《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Pollution from Ships)、《防止倾倒废物及其他物质污染海洋的公约》(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of Marine Pollution by Dumping of Wastes and Other Matter)等。而 “保护特定海洋物种” 的条约主要规定了对特定物种的养护机制,包括《国际捕鲸管制公约》(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Regulation of Whaling)、《保护南极海豹公约》(Convention on the Conservation of Antarctic Seals)、《南方蓝鳍金枪鱼养护公约》(Convent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Southern Bluefin Tuna)、《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等。由于相关国际立法呈现分散化态势,危害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人类活动的管制范围与应受保护的海洋物种范围存在交叉,并且二者很难被穷尽列举,因而在各种特定类型的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条约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法律冲突或空白。
4.其他软法性文件。软法性文件多以宣言、指南等形式存在,虽不具有强制性的法律拘束力,但其内容显示了缔约方的主观倾向,具有一定的实际影响力。①参见何志鹏、申天娇:《国际软法在全球治理中的效力探究》,《学术月刊》2021 年第1 期,第103页。目前,涉及海洋环境保护的软法性文件有《世界自然宪章》(World Charter for Nature)、《关于人类环境的斯德哥尔摩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Human Environment)、《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热内卢宣言》(Rio Declarat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等,专门适用于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的软法性文件如《关于海洋生态系统负责任渔业的雷克雅未克宣言》(Reykjavik Declaration on Responsible Fisheries in the Marine Ecosystem)。这些软法性文件明确了国际社会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采取预防措施养护生态环境等共识,并为有拘束力法律文件的出台提供了一定借鉴。
(二)养护主体多元且分别独立运作
随着国际社会的演变,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对海洋生物多样性进行养护的主体十分多元,按法律地位可分为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国家三类。其中,政府间国际组织又包括全球性国际组织、区域性国际组织两种,政府间全球性国际组织有联合国、国际海事组织、国际海底管理局、国际捕鲸委员会等,政府间区域性国际组织则有OSPAR 委员会、中西部太平洋渔业委员会等。涉及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包括世界自然基金会、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绿色和平组织等。除此之外,沿海国对其管辖海域享有排他的管辖权,可自行制定适用于其管辖海域的生物多样性养护措施,各国对其航行在公海上的船舶也享有管辖权。上述多元主体的职能与管辖范围存在一定的交叉与重叠。多元主体分别独立运作并代表不同的利益,在推动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混乱。②See Elisabeth Druel & Kristina M. Gjerde, Sustaining Marine Life Beyond Boundaries: Options for an Implementing Agreement for Marine Biodiversity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49 Marine Policy 91(2014).
(三)各种养护对象之间相互割裂
在现有机制下,整体的海洋生态系统被人为进行了分割,这使得各种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对象之间相互割裂。一方面,目前的海洋空间划分导致了养护对象的空间性割裂。《海洋法公约》将整体的海洋划分为内水、领海、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公海和国际海底区域等海域。各海域适用不同的法律制度,且各种法律制度之间并不完全兼容,从而导致了海洋物种、种群和生态系统的空间性割裂。另一方面,受技术条件等因素的限制,实践中,各主体往往根据经济价值、丰富度、生存的危险性等标准对海洋物种进行区分,针对不同的海洋物种制定差别化的养护措施,而缺乏针对非目标物种的保护措施。①See Robin M. Warner, Conserving Marine Biodiversity in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Co-evolution and Interaction with the Law of the Sea,6 Frontiers in Marine Science 4(2014).因此,作为养护对象的鱼类、珊瑚、水鸟、鲸类等海洋物种是相互割裂被单独保护的,而不是充分考虑各海洋物种间的相互作用,将该特定物种作为整体生物多样性的一部分采取保护措施。各种海洋物种、种群和生态系统被人为割裂,也是相关国际法规制碎片化的重要表现。
二、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国际法规制碎片化的现实成因
(一)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问题具有复杂性与交叉性
生物多样性是生物及其与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的总和,由遗传(基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三个层次组成。②参见生态环境部:《生物多样性概念和意义》,https://www.mee.gov.cn/home/ztbd/swdyx/2010sdn/sdzhsh/201001/t20100114_184321.shtml,2022年9月14日访问。CBD 明确了生物多样性养护的三大目标,即保护生物多样性、持久可持续利用其组成部分以及公平合理分享由利用遗传资源而产生的惠益。③参见《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条。生物多样性养护问题本身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交叉性,这是相关国际法规制呈现碎片化特征的现实原因。
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问题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海洋空间广阔,物种丰富且各种海洋生物及海洋生态系统间的相互作用极其复杂,但人类对海洋的认知相对于陆地而言较为有限。海洋约占地球表面积的71%,最深处可达11000 多米,广阔的海洋孕育了多样的海洋物种、种群与生态系统,目前有记载的海洋物种共有20 多万种。④See UNESCO, Ocean Life: The Marine Age of Discovery, https://www.unesco.org/en/articles/ocean-lifemarine-age-discovery,visited on 22 November 2022.然而,由于自然、技术等因素的制约,人类对海洋生物多样性的认识,尤其对深远海生态系统的探索仍面临巨大挑战。其次,海洋是一个相互连通的整体,受洋流运动与海洋物种迁徙影响,海洋生态系统间的连通性较陆地生态系统而言更为明显,这要求将海洋环境视为一个整体加以保护。然而,国家间的利益冲突导致各国很难接受统一的海洋环境标准,各国的海洋环境治理立场也存在差异,因此,很难在国际社会形成海洋环境治理合力。海洋环境保护还受到经济成本和科技条件的限制。这些都加剧了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问题的复杂性。
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问题还具有交叉性,涉及渔业活动、船舶航运、气候变化等多个相互交叉的领域。例如,海洋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渔业活动存在密切联系。渔业活动可能会直接影响海洋物种的分布情况及种群结构。大多数渔业活动都具有选择性,这可能会在数量、大小和年龄分布等方面改变物种特征,导致其遗传基因库或种群结构变化,从而影响海洋生物的长期可持续利用。①See George W. Boehlert, Biodiversity and the Sustainability of Marine Fisheries, 9 Oceanography 28(1996).同时,气候变化是影响海洋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因素,即使平均温度的微小变化也会对海洋生态系统产生重大影响。②See Robin Warner, Oceans in Transition: Incorporating Climate-Change Impacts into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for Marine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45 Ecology Law Quarterly 31(2018).海洋生物多样养护还与航运息息相关。船舶在航行过程中的污染物和压舱水排放、噪声污染和抛锚行为都会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影响。此外,海洋基础设施建设、国际贸易等相关领域也与海洋生物多样性存在相互作用。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问题涉及多个不同的领域,而这些不同领域之间的法律机制分别独立发展且缺乏协调,这是造成相关国际法规制呈现碎片化特征的重要原因。
(二)《海洋法公约》存在一定的时代局限性
《海洋法公约》为人类的海洋活动提供了基本的法律框架,但该公约在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方面存在一定的时代局限性,这是相关国际法规制呈现碎片化特征的主要原因。
首先,《海洋法公约》关于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的规定较为原则和模糊,且在公平合理分享海洋遗传资源惠益方面存在空白。《海洋法公约》本身并未明确提及 “生物多样性” 的概念,仅在专属经济区、公海、海洋环境的保护和保全等部分有若干适用于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的原则性规定。在专属经济区部分,《海洋法公约》概括性地规定了对专属经济区内生物资源,以及跨界海洋种群、高度洄游鱼种、海洋哺乳动物、溯河产卵种群、降河产卵鱼种、定居种生物的养护和利用制度;③参见《海洋法公约》第56、61、62、63、64、65、66、67、68条。在公海部分,《海洋法公约》明确了公海自由原则,并在第二节规定了公海生物资源的养护和管理制度;④参见《海洋法公约》第87、116、117、118、119、120条。在海洋环境的保护和保全部分,《海洋法公约》明确了 “防止和减少海洋污染” “不将损害或污染转移或将一种污染转变为另一种污染” 等原则,并规定了全球性和区域性合作、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援助和优惠待遇、海洋活动环境影响评价等内容。⑤参见《海洋法公约》第十二部分。此外,《海洋法公约》中还包含一些涉及海洋环境保护的原则性规定,这些规定对于保护海洋物种、种群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具有一定的影响,但仍然较为抽象。①如《海洋法公约》第192 条规定, “各国有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义务” ;第195 条规定, “各国在采取措施防止、减少和控制海洋环境的污染时采取的行动不应直接或间接将损害或危险从一个区域转移到另一个区域,或将一种污染转变成另一种污染” 。总体来说,《海洋法公约》中关于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的概括性规定加剧了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领域的分散化立法活动,进而导致相关国际法律文件不成体系。
其次,《海洋法公约》采取了 “分区主义管理机制” ,将整体的海洋划分为具有不同法律地位的海域。然而由于立法技术的有限性,加之自然条件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国际社会在缔结《海洋法公约》时并未充分认识到对海洋环境进行整体治理的必要性,因此《海洋法公约》本身并未建立一套完善的协调机制,导致实践中各种养护机制无法充分兼容。根据《海洋法公约》,领海、专属经济区等国家管辖海域由沿海国专属管辖,而各国在公海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多元养护主体没有强制性义务去兼容其他主体制定的养护机制。尽管《海洋法公约》在序言部分规定 “各海洋区域的种种问题都是彼此密切相关的,有必要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考虑” ,但是各种机制的协调效果往往依赖于国际法主体相互配合,因而《海洋法公约》中的 “分区主义管理机制” 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一定的碎片化后果。②参见郑志华、宋小艺:《全球海洋治理碎片化的挑战与因应之道》,《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20年第1期,第175页。
(三)现有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机制的合作与协调效果不佳
在《海洋法公约》 “分区主义管理机制” 下,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主体呈现多元化,同时存在大量的机构和条约同时为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提供规范,各类全球性机制、区域性安排以及各国单独制定的机制共同发挥作用,但其相互之间合作与协调的效果并不理想。实践中,上述各种机制的目标和宗旨存在差异,多元养护主体间的利益和诉求也存在冲突。尽管在不同机制间已经建立起一定的协调与沟通机制,如CBD 第九次缔约方会议决定同UNFCCC 下的技术转让专家组交流信息。③See CBD, Report of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to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on the Work of Its Ninth Meeting, https://www.cbd.int/doc/meetings/cop/cop-09/official/cop-09-29-en.pdf, visited on 8 December 2022.目前各项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公约的秘书处负责人也正通过一个正式的联络小组定期举行会议,以加强执行工作的协调与合作。④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https://zh.unesco.org/themes/biodiversity/governance,2022 年11 月20 日访问。但是,目前不同机制间的协调安排仍不够普遍和完善,各种机制间的合作与协调往往依赖于各方自发进行。各类碎片化的机制共同发挥作用,而理性行为体倾向于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或自身宗旨目标的实现,导致实践中各主体规避治理成本、以全球风险的复杂性特征模糊治理责任。①参见王亚琪:《后实证主义视角下的全球治理机制碎片化及其管控》,《国际论坛》2022 年第2期,第144页。在国际无政府和行为体自利的前提下,多元主体利益和诉求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着各类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机制的合作效果,因此,建立行之有效的协调和沟通机制仍任重道远。
三、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国际法规制碎片化的法律困境
(一)全球框架性公约的适用范围存在交叉和争议
为了弥补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领域国际法的缺失,目前国际社会正在《海洋法公约》和CBD下推进国际造法新进程。然而,《海洋法公约》与CBD是独立运行并发展的框架性公约,其中,《海洋法公约》适用于整体的海洋空间,而CBD 则适用于包括海洋物种在内的生物多样性养护事项,两者的适用范围在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问题上存在交叉,进而引发了框架性公约的适用范围争议。
根据《海洋法公约》进行的BBNJ协定谈判被视为当前海洋法领域最重要的立法进程。目前BBNJ 第五次政府间会议第一阶段会议已经结束,其谈判议题涵盖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的主要方面。然而,CBD 作为生物多样性管制的基本国际规范,其缔约方会议内容同样涉及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事项,这与BBNJ 的相关工作存在交叉,特别是CBD 框架下 “具有重要生态或生物学意义的海洋区域” (ecologically or biologically significant marine areas,EBSA)的适用可能与BBNJ 划区管理工具制度产生冲突。此外,除到2030 年止保护30%海洋的数量目标外,各方对CBD 的适用范围也存在分歧。CBD 第4 条规定了两种适用情形:一是缔约方管辖区域,二是受缔约方管辖或控制的活动,而不论该活动发生在国家管辖海域还是ABNJ。在谈判中,部分缔约方以CBD 适用于缔约方管辖或控制的活动为依据,要求通过海洋目标将CBD 的适用范围扩展至包括ABNJ 在内的全部海洋,其他缔约方则要求将CBD 适用的空间范围严格限制在国家管辖区域,这反映出关于《海洋法公约》和CBD 两个全球框架性公约的适用范围争议,即ABNJ 生物多样性养护应优先适用《海洋法公约》体系还是CBD 体系。对该问题处理不当可能导致更严重的国际法碎片化问题。
(二)多元主体对部分规则与原则的解释与适用存在较大主观性
目前涉及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的各种法律文件不成体系,其缔约主体和管辖事项存在交叉和重叠,同一事项可能会涉及多个相互冲突的法律文件。然而,在各个法律文件间往往缺乏明确的位阶关系,并且由于涉及多个不同的部门和领域,不能简单地适用 “新法优于旧法” 的原则,这导致实践中多元国际法主体对各项法律文件的解释和适用存在分歧,从而对相关国际法的确定性构成挑战。①See Robin M. Warner, Implementing the Rule of Law for Nature in the Global Marine Commons:Developing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Frameworks, https://ro.uow.edu.a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2057&context=lhapapers,visited on 15 December 2021.多样化利益和诉求的存在则导致各主体易选择适用相互冲突的法律文件,并且对同一国际法律文件的解释也可能存在差异。实践中,部分国际法主体通过碎片化的法律依据论证其主张的合法性,已对部分机制的有效实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例如,日本在退出《国际捕鲸管制公约》后援引《海洋法公约》下的专属经济区条款支持其捕鲸主张,阻碍了鲸目哺乳动物养护机制的有效实施。根据国际捕鲸委员会通过的《全球禁止捕鲸公约》与《南大洋海域禁止捕鲸公约》,全世界范围内的商业捕鲸都被禁止。日本作为传统的捕鲸大国,在2014年南极捕鲸案后要求恢复商业捕鲸未果。②参见刘恩媛:《从日本退约谈鲸鱼法律保护问题》,《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4期,第59页。2019年6月30日,日本宣布退出国际捕鲸委员会,并提出恢复在其领海和专属经济区内的商业捕鲸。③参见人民网,http://industry.people.com.cn/n1/2019/0705/c413883-31215121.html,2022 年12 月8日访问。日本宣称此举符合国际法,其依据是根据 “条约的相对效力原则” ,在日本退出《国际捕鲸管制公约》后,该条约就不再对日本具有法律效力,日本也就不再受 “禁止商业捕鲸” 的限制。④See International Whaling Commission,https://iwc.int/permits,visited on 8 December 2022.日本认为,根据《海洋法公约》下的领海和专属经济区制度,日本享有对其管辖海域内生物资源的主权权利,包括其中的鲸鱼种群,因此其可以在管辖海域从事商业鲸鱼。⑤See China Daily, https://www.chinadailyhk.com/articles/240/132/198/1545810349286.html, visited on 8 December 2022.然而,《海洋法公约》第65条规定,在专属经济区内 “各国应进行合作,以期养护海洋哺乳动物,在有关鲸目动物方面,尤应通过适当的国际组织,致力于这种动物的养护、管理和研究” ;第120 条规定,《海洋法公约》第65条的规定也适用于养护和管理公海的海洋哺乳动物,因此,各国应合作养护位于其专属经济区内的海洋哺乳动物,尤其是鲸目动物。日本对其管辖范围内鲸目动物的主权权利与《海洋法公约》的哺乳动物特别保护规定产生了冲突。而日本对《海洋法公约》部分条款的不当解释与适用,阻碍了鲸目动物保护国际法律机制的有效运行。
(三)有损海洋生物多样性整体养护目标的实现
《海洋法公约》在序言部分规定, “各海洋区域的种种问题都是彼此密切相关的,有必要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考虑” 。海洋生态系统具有很强的连通性,对海洋生物多样性进行养护要充分考虑海洋环境的整体性。⑥See Konrad Jan Marciniak, New Implementing Agreement under UNCLOS:A Threat or an Opportunity for Fisheries Governance?,84 Marine Policy 326(2017).然而,碎片化的国际法规制现状有损海洋生物多样性整体养护目标的实现,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多元主体所采取的生物多样性养护措施易相互干扰。海洋生物多样性受气候变化、渔业捕捞、海洋排污、海底矿产资源开采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这些因素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现有的专门性养护机制仅对其中某种或某几种特定的人类活动进行规制,在减少某因素对环境破坏的同时,可能会加重其他因素对海洋环境的不利影响,从而与整体的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目标背道而驰。
其次,完整的海洋被人为地分割为适用不同法律制度的海域,也阻碍了对海洋环境的整体养护。目前的海洋区划并没有充分考虑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要求,各种海域之间的界线仅是一条人为的政治边界,并不具备生态学意义,流动的海洋生物往往不会去遵守人为划定的政治边界。①参见王建廷:《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国际法的新发展》,《当代法学》2010年第4期,第143页。在碎片化国际法规制的背景下,各区域和部门养护机制并不完全兼容,对于海洋生物的养护也存在监管技术和治理能力等方面的差距。在OSPAR 委员会建立查理·吉伯斯南部海洋保护区(Charlie-Gibbs Marine Protected Area)时,冰岛曾反对将其外大陆架区域及其上覆水体纳入该保护区的范围,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减损了该保护区的实际执行效果。②See Charlie-Gibbs Marine Protected Area, http://charlie-gibbs.org/charlie/node/71, visited on 9 December 2022.
最后,特定物种养护机制的适用往往缺乏对生物多样性的综合考量。现有的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机制多根据物种的经济价值、丰富度、危险性等,分别制定差别化的养护措施,往往专注于对特定海洋物种进行保护,并缺乏针对非目标物种和完整生态系统的保护。然而,现实中海洋物种并非独立存在,而是往往依赖于其生存环境与其他相关物种。③参见张晏瑲:《国际渔业法律制度的演进与发展》,《国际法研究》2015年第5期,第24页。因此,当特定养护主体实施单一海洋物种养护措施,以达到该物种的最大可持续产量时,可能会干扰其他物种养护机制所采取的行动,进而对其他海洋物种甚至完整的海洋环境产生消极影响,阻碍海洋生物多样性的综合养护。④See Robert J. Hofman, Stopping Overexploitation of Living Resources on the High Seas, 103 Marine Policy 91(2019).
(四)多重国际争端解决机制间存在管辖权冲突
随着国际法的碎片化发展,当前国际社会已经建立了基于不同法律体系的多种国际争端解决机制。涉及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的国际争端首先是一个涉海争端,《海洋法公约》第287 条规定了国际海洋法法庭、国际法院、仲裁法庭以及特别仲裁法庭四种争端解决机制。⑤参见蒋小翼:《〈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涉海环境争端解决程序之比较分析》,《边界与海洋研究》2018年第2期,第68页。同时,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问题还涉及国际贸易、渔业等领域,因此还存在世界贸易组织、区域一体化机制、区域渔业机制等争端解决机制。各种争端解决机制在管辖范围上存在重叠。在当事方不能就争端解决方式达成共识,或几个争端解决机制同时主张专属管辖权时,就可能引发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管辖权冲突,其结果是使原本的争端更加复杂,相关情况在MOX Plant 案中得到了集中反映。
MOX Plant 是英国位于爱尔兰海沿岸的一个核燃料厂,英国未就该厂向海洋排污对其邻国爱尔兰披露相关信息,爱尔兰政府遂将该争端提交至国际海洋法法庭,要求国际海洋法法庭依照《海洋法公约》附件七规定,采取仲裁庭组成之前的临时措施。①See Request for Provisional Measures and Statement of Case of Ireland, in the Dispute Concerning the MOX Plant(Ireland v.United Kingdom),9 November 2001,paras.149-150.同时,爱尔兰还以英国违反OSPAR 公约第9 条的信息披露义务为由,②OPSAR 公约第9 条第1 款规定:缔约方应确保其主管机构根据任何自然人或法人的任何合理要求,在无须其证明具有相关利益,不收取不合理费用的情况下,最晚在2 个月内尽快向其提供本条第2 款所描述的信息。第2 款规定:本条第1 款所说的信息,是指任何可获得的关于海域状况、对海域产生不利影响或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的活动或措施,以及关于依本公约采取的行动或措施的书面、可视、口头或者数据库形式的信息。主张由依据OSPAR 公约第32 条组成的仲裁庭审理该案件。③OPSAR 公约第32 条第1 款规定:缔约方之间关于本公约的解释或适用的任何争端,当不能通过协商途径解决时,例如委员会主持的调查或调解的方式,应在任一争端方的请求下,根据本条所列条件将争端提交仲裁。英国则提出欧洲法院对MOX Plant 案拥有专属管辖权。在后续审理中,国际海洋法法庭组成的特别仲裁庭鉴于欧共体是《海洋法公约》缔约方,认为当事国应首先确认此案是否属欧洲法院专属管辖,并指出依OSPAR 公约所组建的仲裁庭不是《海洋法公约》所规定的享有强制管辖权的特别法庭,不享有对本案的管辖权。④See MOX Plant Case (Ireland v. United Kingdom), Order of 24 June 2003,Arbitral Tribunal under Annex VII of the UNCLOS,para.20.而OSPAR 仲裁庭主张拥有本案的管辖权,并根据OSPAR 公约第32 条规定主张本案应适用OSPAR 公约进行审理。⑤See Ireland v. United Kingdom (OSPAR Arbitration), Award of 2 July 2003, OSPAR Arbitration,para.185.同时,欧洲法院主张对本案拥有专属管辖权,其依据是欧共体与其成员国都是《海洋法公约》的缔约方,因此《海洋法公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欧共体法的一部分,而欧共体条约第292 条制止其他国际条约修改欧洲法院在共同体法解释和适用问题上的专属管辖权。⑥See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v. Ireland, Judgment of 30 May 2006, the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para.121.
在该案中,作为争端当事方的英国和爱尔兰选择适用不同的争端解决机制,而这些争端解决机制之间缺乏协调,导致欧洲法院、国际海洋法法庭下的特别仲裁庭、OSPAR 仲裁庭之间发生了管辖权冲突,使得争端更加复杂,进而阻碍了争端的解决。
(五)BBNJ国际造法新进程受到不利影响
目前涉及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的重要国际造法新进程即为依据联大决议在《海洋法公约》下进行的BBNJ 协定谈判。国际法规制的碎片化导致BBNJ 协定谈判的立法障碍,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大各缔约方之间的分歧。因此,受国际法规制碎片化的影响,相关国际造法新进程的成果可能无法达到国际社会在谈判初期的预期。①See Efthymios Papastavridis, The Negotiations for a New Implementing Agreement under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concerning Marine Biodiversity, 69 International &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585(2020).
一方面,国际法碎片化现状在技术上加大了新条约的立法难度,影响BBNJ协定的订立进程。涉及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的国际法律文件之间缺乏协调,其中,各类区域条约与专门条约间彼此割裂,拥有差异较大的指导原则、目标物种与养护措施,很难进行协调并制定统一的全球生物多样性养护措施与标准。以划区管理工具为例,现有的海洋划区管理工具主要是单一部门为实现特定目标而采取的措施,包括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划定的渔业管理区、区域海洋组织制定的有限的海洋保护区与海洋空间规划、CBD 缔约方会议所提出的EBSA、联合国粮农组织设立的脆弱海洋生态系统(vulnerable marine ecosystem)、国际海事组织为减轻航运对海洋环境影响而划定的特别敏感海域(particularly sensitive sea area)、国际海底管理局划定的特殊环境利益区域(areas of particular environmental interest)和保存参考区(preservation reference zones)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正考虑在ABNJ 指定世界遗址。总体来说,各类海洋划区管理工具的概念不尽相同,使得当前涉及划区管理工具的各种术语并不被普遍理解,实践中各主体易使用同一术语指代相互冲突的概念。②See Konrad Jan Marciniak, New Implementing Agreement under UNCLOS:A Threat or an Opportunity for Fisheries Governance?,84 Marine Policy 322(2017).然而,联合国大会关于在《海洋法公约》下设立BBNJ筹备委员会的第69/292号决议明确提及,新协定不应破坏现有文书、框架和机构。因此,BBNJ协定谈判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构建新协定,使其在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上实现有意义的改变,但不会颠覆现有的海洋治理体系的关键挑战。③See Nichola A. Clark,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for the New BBNJ Agreement: Moving beyond Global,Regional,and Hybrid,122 Marine Policy 1(2020).如何处理BBNJ 协定与现有的碎片化国际法律体系之间的关系,在全球与区域、部门法中找到平衡,成为BBNJ协定谈判的挑战。
另一方面,碎片化的国际法律体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各国在BBNJ 协定谈判中的分歧。国际法主体是国际法律规范的制定者。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各主体倾向于积极推动相关国际造法进程向符合其利益与诉求的方向演进。碎片化的国际法现状使得各国或国家集团往往通过解释,从碎片化的法律机制中寻求支持其利益的法律依据,而BBNJ 协定的缔结将对海洋生物资源进行重新分配。在现有碎片化法律体系中占据优势地位的主体为实现其自身利益,更倾向于以现有的国际法律文件为依据,拒绝支持新的BBNJ 协定,因而将延缓BBNJ 协定谈判的进程,并限缩新公约的适用范围与国际影响力。①See Anne Peters,The Refinement of International Law: From Fragmentation to Regime Interaction and Politicization,15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titutional Law 679(2017).
四、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国际法规制碎片化的解决路径
碎片化的国际法现状导致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相关法律机制间存在冲突,对海洋环境的完整性养护构成挑战,但也为国际法的变革提供长久动力。为了应对上述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国际法规制碎片化的法律后果,笔者提出如下解决路径:
(一)构建有效的国际法律协调机制
不成体系的国际法律体系给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规则的确定性带来挑战,导致部分养护措施相互干扰,影响部分养护机制的实施效果。为了更好地对海洋生物资源进行养护,单纯分散地执行现有的条约是不够的,还需要在各部门和各保护制度间进行更有效、更充分的协调,以促进不同层次国际法律文件之间的有效互动。②See Jeff A. Ardron et al., The Sustainable Use and Conservation of Biodiversity in ABNJ: What Can be Achieved Using Existing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49 Marine Policy 106(2014).
在法律文件的订立和修改程序中,应注意建立一定的法律协调机制。衍生于法律文件本身的协调机制有两种情形:一是在立法时尽量考虑周全,为该法律文件与其他相关法律文件的合作与协调做出明确的规定;二是在法律冲突发生后,通过修改条约或订立新条约来明确不同法律文件间应如何相互协调。虽然国际社会已经在部分法律机制间建立了一定程度的协调机制,但相关的协调机制并不完善。面对碎片化的国际法现状,未来的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国际造法新进程应放在现有规范的背景下进行,在订立和修改条约时尽量建立完善的协调机制,避免潜在的法律冲突。
在法律文件的解释和适用中,应当以条约法为基础协调各层次法律文件之间的冲突,并充分发挥联合国及其相关部门的协调作用。一方面,各种国际法主体应坚持并完善以《维也纳条约法公约》(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 VCLT)为基础的国际条约法,对各类国际法律文件进行合理解释。VCLT 第31 条规定, “条约应就其用语按照上下文并参照其目的和宗旨所具有的通常意义,善意地予以解释” 。在对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相关国际法律文件进行解释时,应当综合运用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等多种方法得出合理结论,避免片面解释给相关法律的确定性带来冲击,使各种国际法主体的权利和义务边界更加清晰化。另一方面,作为成员分布最广泛、国际影响力最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及其相关部门在协调各种国际机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联合国及其相关部门已经建立了一定程度的海洋法律协调机制,如联合国在法律事务厅设立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司;联合国定期举行海洋和海洋法问题不限成员名额非正式磋商,以协调各方意见。①See United Nations Open-ended Informal Consultative Process on Oceans and the Law of the Sea,https://www.un.org/depts/los/consultative_process/consultative_process.htm,visited on 22 November 2022.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涉及全人类共同利益,未来应更充分地发挥联合国及其相关部门的国际影响,充分协调各种法律机制的适用。
(二)促进养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国际合作
目前涉及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的各类全球、区域、专门机制数量繁多,相关的国际主体也十分多元。虽然单一主体的措施能做出相应的贡献,但最终只有多元主体充分合作才能确保海洋生物多样性的长期可持续利用。在区块割裂的治理现状短期难以改变的前提下,国际社会应不断推进海洋生物多样性跨领域、跨区域国际合作。
首先,涉及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的多元主体应积极寻找共同利益,开展多种形式的务实合作。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关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实践中养护义务也由多元主体共同承担。因此,在全球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中应强调多元主体间的共同责任,贯彻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尽可能在充分考虑各方利益的基础上形成共同的价值诉求,减少多元主体间的海洋环境治理分歧。②参见何志鹏、高潮:《国际法视角下的公海海洋保护》,《甘肃社会科学》2016 年第3 期,第179页。具体来说,可以建立各公约秘书长的定期会晤机制,以加强不同领域机制间的信息共享与合作;管辖海域在地理上相邻或生态连通性明显的区域海洋环境机制也应该加强对话与合作。同时,海洋环境具有较高的整体性与连通性,多元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是导致相关国际合作不畅的原因之一,而《海洋法公约》所确立的适当顾及义务提供了一种平衡各方海洋权利的思路。 “适当顾及” 是指各主体在行使自身的海洋权利时,应合理地考虑其他主体的海洋权利,在不同的权利之间相互协调,尽可能地不损害其他主体的海洋权利。③参见张国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适当顾及” 研究》,《中国海洋法学评论》2014年第2期,第53页。不过,在适用适当顾及义务时,应明确对其他主体权利的 “适当顾及” 以不损害其海洋权利为限,并不意味着为维护其他主体权利而放弃自身的权利。
其次,国际社会尤其应进一步加强国际海洋技术合作,以海洋科技共识推动各主体在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事项上的共识。国际社会越来越注重科学信息对海洋环境保护的指导价值和意义。实践中,各国在海洋环境保护问题上存在分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各国的海洋科学技术水平差距以及技术标准不统一所导致的。国际社会可在联合国、CBD 等国际机制下搭建具有公信力的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提供现有最佳科学证据,为影响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决策提供信息,从而理清各主体所管辖事项的边界,凝聚共识,指导多元主体在充分认识海洋环境问题的科学基础上展开深层次合作。
(三)明确《海洋法公约》和CBD的适用范围
国际社会正在《海洋法公约》和CBD 两个全球框架性公约下共同推进国际造法新进程。在CBD 框架下的 “2020 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海洋目标” 制定过程中,大部分缔约方并未明确 “至2030 年保护30%海洋” 的目标是否涵盖缔约方管辖海域与ABNJ,其结果可能会为ABNJ划区管理工具设置一定的数量标准。为避免加剧相关国际法的碎片化,应明确《海洋法公约》和CBD 在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方面的适用范围。
首先,CBD 适用于缔约方管辖海域及缔约方管辖或控制的活动,其在ABNJ 的适用不得抵触海洋法。CBD 第4 条规定了两种适用范围:一是空间意义上的缔约方管辖海域;二是行为意义上的缔约方管辖或控制的活动。①参见《生物多样性公约》第4条。CBD 并不因其适用于缔约方 “在ABNJ 有可能会影响生物多样性的行为” 而获得对ABNJ 空间的约束力,因为ABNJ 是严格的空间概念,其与主体标准之间在逻辑上为并列关系。同时,CBD第22 条第2 款明确规定在海洋环境领域,缔约方在适用CBD 时不得抵触各国在海洋法下的权利和义务。②参见《生物多样性公约》第22条。此处的 “海洋法” 是有关各海域法律地位及在海域中从事活动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称,其中最主要的条约即为《海洋法公约》。因此,从CBD体系看,《海洋法公约》在ABNJ生物多样性养护上优先于CBD适用。CBD框架下的海洋目标不应抵触《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的BBNJ协定。
其次,《海洋法公约》适用于整体的海洋,包括沿海国管辖海域和ABNJ。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是《海洋法公约》的长期议题之一,国际社会已经在《海洋法公约》体系下通过《关于执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的协定》《联合国鱼类种群协定》等建立了一定的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机制。依据《海洋法公约》编制的联合国大会海洋和海洋法秘书长报告大多涵盖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事项,相关内容包括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现状、近期措施和未来规划等。此外,国际社会正积极通过BBNJ协定谈判进一步完善ABNJ生物多样性养护机制。《海洋法公约》第311条第2款规定, “本公约应不改变各缔约国根据与本公约相符合的其他条约而产生的权利和义务,但以不影响其他缔约国根据本公约享有其权利或履行其义务为限” 。①参见《海洋法公约》第311条。即《海洋法公约》规定了在与其他条约冲突时,其应当得到优先适用,《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的BBNJ协定优先于CBD 体系下的海洋目标,CBD 关于ABNJ 的生物资源养护规划应与BBNJ协定保持一致。
(四)在《海洋法公约》框架下完善ABNJ生物多样性养护机制
ABNJ 占据了整体海洋的大部分,其中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受到人类活动的严重威胁。ABNJ 的生物多样性养护面临着比沿海国管辖海域更为复杂的局面,养护主体多元、相关法律冲突、养护对象割裂等问题更加明显。同时,相较于支离破碎的沿海国管辖海域,ABNJ的法律地位相对一致,并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和独立的海洋空间。完善ABNJ养护机制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涉及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的国际法规制并不是一套静态的规则,而是逐渐发展的开放性国际法体系。在《海洋法公约》下订立的BBNJ 协定有望缓解ABNJ 生物多样性养护的国际法碎片化困境,建立更加一体化的ABNJ法律制度。②See Robin Warner,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High-Seas Biodiversity: Steps towards Global Agreement,3 Australian Journal of Maritime&Ocean Affairs 221(2015).
未来的BBNJ 协定谈判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应当明确《海洋法公约》是BBNJ 协定谈判及将要达成的协定的法律基础,BBNJ 协定对现有国际法规制的吸收不能与《海洋法公约》产生冲突。同时,在新旧法律文书间的关系问题上,BBNJ 协定应积极纳入现有的国际法律机制,以避免新旧法律文书之间的不协调与冲突,并确保不降低现有的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的环境标准。③See Genevieve C. Quirk et al., Cooperation, Competence and Coherence: The Role of Regional Ocean Governance in the South West Pacific for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Biodiversity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3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ne and Coastal Law 672(2017).其次,BBNJ 协定应尽量与现有的专门性和区域性机制实现相互兼容,为专门性和区域性养护机制发挥作用提供法理支撑。各种专门性和区域性养护机制在BBNJ协定未出台时弥补了法律的空白,并且为ABNJ 环境治理提供了经验。例如,OSPAR 委员会已经在东北大西洋海域建立了网络化的海洋保护区体系,这为BBNJ 划区管理工具机制的建立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然而,各类专门性和区域性机制的职权范围和实际执行力相对有限,并且各区域机制的发展并不均衡,通过BBNJ协定在全球层面整合各种专门性和区域性养护机制十分必要。在可预见的未来,制定统一的、具备强制执行力与明确具体措施的国际法律框架难度较大,由区域机构采取具体的养护措施,仍将是主要的养护机制。为了避免不同机制间的冲突,BBNJ 协定应明确各种专门性和区域性养护机制的管辖范围、作用和效力等级,建立部门内和跨部门的合作与协调机制。最后,BBNJ 协定还应充分考虑海洋生态系统的连通性,将海洋视为一个相互连通的整体加以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问题具有复杂性和交叉性,这是导致相关国际法规制碎片化的重要原因。BBNJ 协定不仅应将海洋环境的整体治理视为基本原则,还应制定涵盖海洋遗传资源及其惠益分享、包括海洋保护区在内的划区管理工具、海洋能力建设和技术转让、环境影响评价等主要领域的具体制度与规则。
结语
国际社会已充分认识到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并在多个法律框架下推进国际造法新进程,但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领域国际法规制的碎片化现象严重。碎片化的表象不仅源于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本身的自然特性及其分散的国际法规制状况,还归于现有法制的时代局限性。该困境已对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带来负面的法律后果,影响养护措施的实施及实践效果。尽管如此,应对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国际法规制碎片化问题依然有章可循,合理解释和充分协调现有冲突,明确各方权利义务及适用范围是可行的解决路径。在该路径下,即使不同国际法律文书的目标和宗旨存在差异,其所规定的具体养护措施也可能相互冲突,但是这些法律文件在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事项上存在共同的价值追求。同时,虽然在多元养护主体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利益和诉求差异,但在各主体之间也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即全人类都将成为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的受益者,这为构建有效的国际法律协调机制提供了可能性。未来只有充分践行海洋环境综合治理的理念、强化责任共同体意识,才有可能促进制度间的有效互动,确保海洋生物多样性的整体养护与长期可持续利用,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