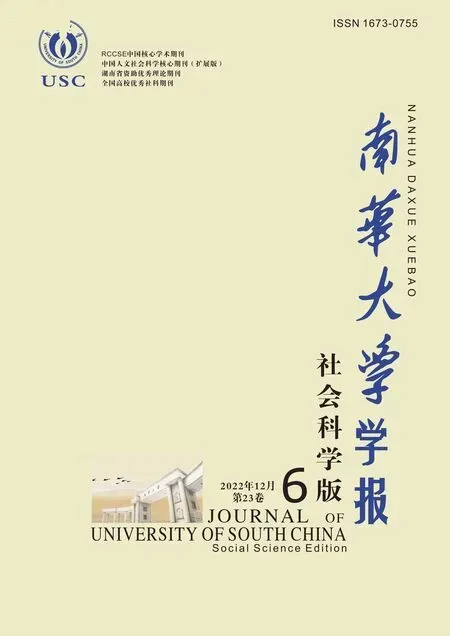论表意汉字在文化记忆的保存与传承中的影响
张 东 赞
(外交学院 基础教学部,北京 100037)
一个时代跟过去的关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与记忆媒介的关系。人们通过一些媒介来处理日常生活中的记忆问题,从而形成媒介记忆。所谓媒介记忆是指人们通过对日常信息的采集、理解、编辑、存贮、提取和传播,形成一种以媒介为主导的人类记忆的平台和核心,并以此影响人类的个体记忆、集体记忆和社会记忆[1]。对自己以及群体过去的感知与诠释是人们着眼于未来,决定采取何种行动的出发点,也是个人与群体赖以设计自我认同的出发点[2]。过去不可能完全消失,总会以某种不同于“今天”的典型形式留存于世,承载过去信息的媒介则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中,文字作为文化记忆的媒介在指涉过去以及文化传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拼音文字因其高度抽象化的特点而以文本作为记录过去的手段,其可靠性已经受到人们的质疑,它不能保证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的有机结合。历史学家们也开始怀疑文本的可靠性,甚至质疑其描述传统[3]207。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始终保持着文字与语言早期的关联,字形存储了大量过去的“痕迹”。大量文化信息通过汉字“形体”得以保存与传承,汉字无疑是华夏文化记忆的重要承载物。
一 经验的积累与文字的产生
交际是人类的生存本能,是人类在相互交往中使用符号创造意义并且运用符号进行意义反射的动态过程。个体需要同其他群体成员进行交际才能完成自我认知与群体身份的认同,二者均按照文化预先设定的轨道进行,个体无法脱离文化为群体所设定的生产生活的轨道。随着社会生产活动以及交际的不断扩展,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增强,动物的群居本能逐渐隐去,代之以群体有意识的聚合行为。为了更好地从事生产活动,成员不断分享群体经验,逐渐形成趋同的心理期待与行为空间,德国文化学者扬·阿斯曼将这个空间称之为文化的凝聚性结构。在这个空间里,人们共享象征意义体系,成员之间通过凝聚性结构而聚集在一起,并且接受具有趋同行为模式的影响[4]207。
约翰·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中指出,新生的人就像一块空白的石板,个人变成什么样,都由其生活经历写在这块石板上,后天经验对个人的成长以及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5]。没有经验积累的野蛮人处于一种原始的自然状态。在这种自然状态中,没有教育,没有经验的积累,人类一代一代毫无意义地繁衍下去。每一代都从起点重新开始,可能还会不断重复着前人的错误。若干世纪都在原始时代中度过,人类虽已古老,却依然处于童年[6]。随着经验的不断积累,共享经验为群体成员所设定的时间与空间层面上的行为模式,即生活轨道也逐渐形成。人们在处理一些问题上不至于从头开始,而是在过去经验的基础上向前推进。爱德华·埃文思·普里查得曾这样解释时间结构,“站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上,他都知道之前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并能够预测及计划以后的生活。一个人结构性的未来就好像已经被安排好了”[7]。这是强调过去经验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古者无文字,其有约誓之事,事大大其绳,事小小其绳,结之多少,随扬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春秋左传集解》)“结绳记事”是人类的第一个记忆工具,也是人类文明史的重要前提条件。“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易·系辞下》)上古华夏及秘鲁印第安人都有这样的记事习惯。直到近代,在某些尚无文字的部族或地区,仍然采用结绳记事的方式来记载和传达消息、情报。除了结绳记事之外,人们还可以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进行信息存储与传承,最典型的形式就是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
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体现了人类所特有的历史感。人们将过去重大的事件和人物形象以某种形式固定保存下来,给现实生活提供一个参考框架,从而可以将过去某个时间段中的场景和历史拉进到“当下”的框架里,让人们产生希望和回忆[4]62。神话传说是一个民族童年时代的歌谣,它保存了一个群体早期的生存智慧、经验以及对外在世界最原始的看法,它们将以参照物的身份存在于人们的社会实践中,为人们的行为活动提供价值和道德的评判标准。先民所建构的英雄事迹在讲述者的不断讲述中,不断被重复而得以现时化。在不断地讲述中,诸神慢慢失去了玄奥的神话象征意义,却获得了现实的道德教化功能。民间故事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能表现和阐释民俗事象的内涵,又影响并促进民俗事象的传承。人们从民间故事这一“魔镜”中透视社会秩序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家庭如何组成,政治结构如何运转,人们如何捕鱼,男人和女人如何分权,食物如何制作等等[8]。
当人们的社会交往活动出现过渡膨胀时,单凭人类自身生物学上的记忆能力已经不能满足信息存储的需要,这就要求产生起中转作用的外部存储器。这个存储器可以使需要被传达的、文化意义上的信息和资料转移到其中。结绳记事以及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这些口耳相传的记录方式随着人们交际范围的扩大已无法满足人们经验不断积累的需要,故“易之以书契”。正所谓“夫文象列而结绳移,鸟迹明而书契作。斯乃言语之体貌,而文章之宅宇也”。(《文心雕龙·练字》)文字作为重要的信息载体就应运而生了。
文字的产生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伯益作井,而龙登玄云,神栖昆仑……”(《淮南子·本经训》)。相比结绳记事而言,文字的产生克服了结绳记事在表声方面缺乏可读性、表意方面缺乏直观性以及记事容量小的缺点;相比较口耳相传的记录方式而言,文字克服了知识传承的媒介仅靠讲述者的记忆来传承的局限,它使人类记忆的外化成为可能,群体经验得以顺利传承,大大提高了人们重新吸纳以及处理现有信息资料的能力,扩大了人类活动的时空维度。文字的力量来源于它同知识的联系,而知识却来自祖先,生者须借助文字与祖先沟通,它连接过去和现在,从而为人们在将来的生产活动提供经验指导。史前文字做为“族徽”的事实表明,知识往往由死者掌握,死者的智慧则通过文字的媒介来显示于后人。华夏民族推崇的“慎终追远”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祖先是经验的持有者和传承者,只有将祖先的经验传承下去才能更好地进行社会实践。
文字作为存储媒介的独特性在于它通过树立一个对手而得到巩固。这个对手就是图像、雕塑和建筑,而它们都会被时间侵蚀。文字则会被时代所传承下去,能够克服时间的侵蚀,具有超时空性。哲学家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在其著作《真理与方法》中关于文字的存储力量这么写到,“来自过去的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流传没有一样能与之相比,过去生活的残留、建筑的剩余、工具、坟墓的内容都被从它们上面吹过的时间风暴侵蚀了,而文字的流传则相反,他们被破译、被解读,是如此纯净的思想,就像在眼前一样同我们讲话”[3]213。由于文字的产生,文化中的凝聚性结构的发展历史也因此从主要依靠仪式化的重复到文本阐释的转移。在没有文字之前,承载文化象征意义体系的凝聚性结构主要通过仪式的不断重复来实现其现时化。文字产生之后,伴随着凝聚性结构内容文化化的过程,凝聚性结构的现时化完成了从仪式关联到文本关联的过渡。人们也从依靠仪式的重复来传承文化意义而产生的压力中解放出来。
二 汉字的表意属性与图式认知
世界上现存大约5千多种文字,根据其构形依据大体可以分为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两大类。作为信息存储的物质载体,二者在信息存储时所依托的单位有所不同,这与理据载体的形成途径有关。以组合理据为编码基础的语言重听觉,重时间,其文字主要采取表音的方式。以成分理据为编码基础的语言,主体在认知方式上往往重视视觉、空间组合,文字体系采取表意方式[9]79。汉字作为表意体系的文字,始终保持着与语言早期的关系,没有走向跨语言的道路,这与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密不可分。冯友兰在深入研究中西哲学的差异后指出,“对于概念形成的途径,中国哲学主要依靠直觉的方法获得,表象在概念的形成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西方则是用假设的方法获得的,抽象思维起着重要的作用”[10]。这种差别也造成了中国人整体性思维与西方人分析性思维的不同特点。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认为不同的语言标明了不同的观念体系,文化行为上的差异是在语言意义的结构中传递和编码的。语言不是简单地反映世界,而是对世界实施范畴化的同时给世界进行一定建构,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客体世界。因此,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客体世界的认知。汉字作为表意体系的文字,造字之初就是人们生活导向以及经验的一种反映,也正是基于其表意的特点,汉字成为华夏民族在处理指涉过去以及文化传承问题上的一个重要工具。汉字作为始终未与汉语脱离的表意文字,从字形上可以折射出华夏民族的思维特点。
中国哲学对于概念的形成所采取的直觉方式与汉字形体所体现出的图式认知具有内在一致性。图式是人脑已有知识经验的网络,它融合了三种最基本的陈述性知识元素,即命题、表象和线性顺序,是陈述性知识的一个整合单元和综合表征形式。皮亚杰用图式这一术语描述人们表征、组织和解释经验的模式,人的大脑不仅可以按照逻辑顺序存储抽象的信息,还能以动态的三维信息存储形象信息,从而凸显信息的空间属性,这与表象记忆有关[11]。表象的感知是人类经验积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空间和时间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两个基本维度。空间主要表现为名物的大小、高低、宽窄,离合等状态,具有离散和直观性。时间主要表现为事物的发展变化,呈现出连续和无形的状态。以成分理据为编码基础的语言,其认知现实的途径偏重视觉、重直觉的把握,因而编码体系中重名物,会基于名物的基础上进行编码,因名物的离散和有形的特点,可以成为临摹取象的依据[9]73。就汉字来说,字意的取象是根据构形系统和与之有关的历史文化推测出来的。汉字的形体与认知主体的视觉感知密不可分,同时又融合了人们的主观认知。以“教”字为例。《说文解字》:“教,上所施下所效也。从攴从孝。凡教之属皆从教。”“攴”,小击也。“教”从形体上基本把这一行为的图式给勾勒出来了,这种“观象取类”的方法是拼音文字无法实现的。人们对表象的感知成为汉字、汉语以及中国哲学思维特点的一种内在联系机制。
表象作为感性的形象是认知主体接受刺激时信息对自我的一种呈现方式,具有一定的直观性和概括性。这与中国哲学重视视觉以及整体性思维具有内在一致性。整体性思维从与它事物或它方面的关系和比较中来认识、把握和评价认识对象,不把认识对象看成是孤立的或分隔的,常常会把人以为二元的事物对立统一起来,它强调认识对象的时空连续性与系统性,在概念、范畴的界定方法上,采用“观象取类”的方法,而不是事物属性抽象法。“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说文解字序》)古人在造字的时候是基于事物整体特点而采用“观象取类”的办法,重视图式认知。
汉字不同于拼音文字的重要方面在于汉字在形体上以一种图式的形式直观地呈现于人们面前。“仓颉之初作书也,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说文解字·序》)汉字的造字大体分为“文”和“字”前后两个阶段。所谓独体为文,合体为字。“文”的本义是画画、纹画,是基于实物基础上的“依类象形”,字则是在“文”的基础上的进一步跳跃式发展。图式描述的是整合性的知识,有利于个体经验的获得与检验,更接近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现实。汉字这种“方便他人”的图式设计很容易让人接受和识别。
三 文字形体所负载的文化信息与阐释
文字是语言的视觉形象载体,透过它理解语言是人类交际的重要途径。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在存储人们的生存经验、智慧信息时所采用的基本单位不同。拼音文字是跨语言的,在指涉、记录过去时主要依靠文本。文本通常是具有完整、系统含义的一个句子或多个句子的组合,文字之间通过组合形成文本来表达传递某种语义信息,单个文字本身没有意义。文字的形体一旦形成就不会轻易地发生变化,而社会却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这样就会造成一成不变的文本与不断变更的现实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距离,这种差距需要解释来进行弥补。然而文本一旦停用,就不再是文化意义的承载体[4]95。同时文化意义的载体从依靠仪式的重复到文本的转变本身就隐含着文化意义被遗忘的可能。因此,对于一些文本来说,只有借助注释者的注释手段才能让其复活。
对于表音文字而言,有些文本随着语音的变化而无法进行解释。尤其是当大量不计其数的文本出现超出了一个时代所能记忆和铭记的限度。有些文本将被尘封在资料库而变成了空壳,有些文本因无法解释而成为陌生的、遗忘的角落,文字所记录的文本几乎与未知的东西没什么两样[4]103。另外,由于拼音文字字形本身并不承载一定的信息,所以文本的阐释也就会出现不同的版本,会造成文本的原始义和阐释义差别越来越大,在保持文化一致性上会有比较大的分歧。
汉字是世界上现存唯一的连续六千多年而没有间断且日益成熟了的表意体系的文字。汉字在记录汉语的时候,始终保持着与语言的联系,字形本身就承载着文化信息,虽然经历久远的时间,但其原始的信息仍然负载于其字形上。“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不由字,道则不达。”(戴东原《与是仲明论学书》)戴震(字东原)明确地指出汉字与“道”之间的关系以及汉字在阐释文本时的作用。其深层原因在于汉语社团的认知途径以视觉为基础,着眼于空间,而空间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哲学家叶秀山认为,“中国文化在其深层上是以字学为核心的,字学似乎是中国一切传统学问的基础。”[12]汉字以其表意属性成为汉民族的群体记忆的物质载体,负载着人们对过去的回忆结构。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包含了人们回忆结构的客观部分,也承载了回忆结构的主观部分,即生活的导向,意愿和希望。
四 汉字作为凝聚性结构与文化的传承
过去总是由特定的动机、期待以及目标所主导,并且依照当下的相关框架得以建构,它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一旦无法再现,过去就变成了历史。汉字在造字之初就反映了古人观察世界的独特视角,正所谓“近取诸身,远取诸物”。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语言文字的演变,汉字的音形义等方面需要做进一步解释。基于汉字的表意属性,在对汉字的解释中就造成了群体对过去的再一次重塑,同时完成对自身连续性的虚构。德国著名学者扬·阿斯曼指出,在促成文化一致性的过程中,重复与解释两种方式具有大致相同的功能[4]87。仪式的重复是文化意义现时化的重要手段,文字的出现逐渐替代了仪式对文化的传承功能。汉字的表意属性使其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在人们日常生活的使用中得以现时化,不断塑造着群体特征。汉字的表意属性进一步打破了信息传递的时间和空间局限,汉字所承载信息的阐释就是在重现古人观察世界的视角与认知方式,拉近了人们与古人之间的距离,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文化记忆的保存、现时化与传承的问题。
文字的出现让人类社会的凝聚性结构的演变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以仪式为基础不断重复的阶段和基于文本进行解释的阶段[4]96。对于拼音文字而言,仪式的一致性逐渐过渡到文本的文本一致性,通过文本来解释仪式的具体流程,意义因为传承而具有保持鲜活性。文本是传承意义的一种重要形式,因此,只有当人们传播文本的时候,意义才具有现实性,而文本一旦不用,文本就成为意义的坟墓。对于拼音文字而言,文本的可靠性是值得怀疑的,在文字的形与意之间没有关联,人们在解释文本的时候带有较多的主观性,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某些文本已经无法解读。反观汉字,汉字通过字形创造了一种文化信息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古人观察世界的视角得以呈现在人们面前。人们使用汉字的时候其实就进入到一种文化信息空间,在这种抽象的文化信息空间中,个人通过共享古人观察世界的视角而成为一种参与者,从而有利于集体身份的认同。一位埃及学者默罕默德·侯赛因·海卡尔说:“只有使过去复活,一个民族才能存活。”汉字的表意属性承载了华夏民族关于过去的集体记忆与社会经验,对于整个民族的发展至关重要。汉字所承载的文化信息是民族的财富,这个财富越巨大,集体的观念就越稳固也越深入人心[4]90-136。
五 余 论
文化作为国家的精神名片,透过它可以看到一个群体的生活方式与精神面貌。只有当过去进入到一定的历史框架中才会成为人们所去理性思考的东西。这些被装入一定框架的过去,同时又要借助一定的外部存储媒介和文化实践来组织回忆,从而实现文化意义的现时化。古人的生存经验和智慧可以通过汉字存储并传承下来,汉字所蕴含的独特的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值得每一个中国人骄傲和自豪。可以说,每个汉字都有一个故事,讲好汉字的故事,对于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增强华夏成员的身份认同感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