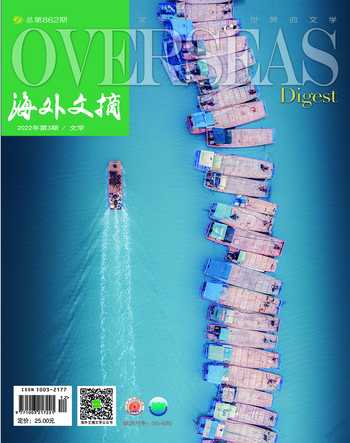砂罐子记
张强勇

一
在毗邻资水的山坡上,有一处隆起的土丘,土丘上有五孔烧窑遗址,从上到下,由小变大。
我隐约看到了制坯的作坊,煤矸石堆积的黑土层,废弃、破碎的砂罐瓦片。我看到这些遗址呈大大小小的土丘状寂寞地蹲在土地上,看到很多的碎片在脚下堆积,这是漫长而沉重的历史挤压。我想象着这里制造砂罐的窑炉、碾槽、水井和灰坑,还有堆放着亮光闪闪的煤炭,松树毛尖。我至今都难以言说我获得这一信息时,这块土地带给我的艳羡和惊喜。碎片在土丘上星星般散落,人踩在上面,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有时感觉着一种神秘而令人心醉的声响。
三月的阳光,明亮而温暖。废弃的窑址,深陷于山谷间、山丘上,深陷于时间。黄土夯成的低矮房屋,依山而筑,这是工匠歇憩的地方,手工作坊和窑炉散落在此。多少年前,这里还亮着灯火。我随手捡拾起一枚碎片,小心翼翼地抚摸着遗留在土地上的文明,碎片上没有文字,灿烂的阳光映照着砂罐的纹路,发出耀眼的光芒。我抬起头来望天望云,倏忽,我敬重的一位文化学者的声音,开始在这片遗址的废墟上弥漫——废墟是毁灭、是葬送,是诀别、是选择。烧造制作砂罐的手艺濒于失传。有多少人知道祖先是何时开始了泥土与火的烧造?又有多少人知道祖先何时完成了由砂到陶到瓷的进化?
二
老人带我来到曾经烧制砂罐的作坊,用颤抖的手从怀中拿出一串钥匙,打开了一把锈蚀的铁锁。
老人的脸涨得通红,原来呆滞的目光就像被什么点燃,他看起来好像有点激动,就像正在完成一件期待已久的事情。一扇制作粗糙的木门用了很大力气才被拉开,其实这更像是栅栏,几根粗大的木头横竖交叉,木质干燥后收缩的力量,使木板之间留下很多窄缝。我注意到老人拉门时的手势,那么敏捷、迅速,仿佛急于进入一处秘密的藏宝地。
木门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慢慢张开,一个尘絮飘动的暗淡空间出现了,几束激情四溢的光芒发自同处钉满木板的窗户上的缝隙,那是这个屋子里的唯一光源,仿佛一面墙壁上的灯隐藏在一些看上去凌乱的木板后面。中央是一团很大的泥坯,裂开着无数的叉痕,好像一行行干枯的泪珠在等待着主人的到来。几条矮小的凳子凌乱地摆放在四周,凳子上仍然有泥土粘在上面,工尺、转辘、刀具等撒了一地。老人将一把尺子从地上捡了起来,眯着眼睛看了一阵,好像是要努力看清楚上面的刻度,他的目光在某一个刻度上停住了。说,现在一切都没有用处了,大家都不需要砂罐了,这么好的泥土都没有用处了,它们都是我挑选的,唉,我曾经制作了多少砂罐子啊!
几片蛛网缠绕在木料上,上面的蜘蛛却不知去向。它们为什么在这里结网?在光线灰暗的屋子里,它们究竟能够捕获什么飞虫?这些小小的精灵,是不是一直都守在这里,一直都在等待着原来的主人?这里曾经是多么的热闹,蜘蛛是知道的,或许是已经发现了曾经的热闹。
老人将凳子搬了出来,并没有去擦拂凳子上的灰尘和泥土,径直地坐了上去,我看到老人提起烧制的砂罐,堆满沧桑的黝黑脸庞顿时泛起了亮光。
三
一对父子正在取土,儿子看上去四十好几了。我问老人多大?老人伸出右手,朝我做了一个手势。“七十了?”老人点点头。
砂罐厂依山而建,隐匿着手工老作坊。老人说有一百多年了,上世纪曾辉煌过。古朴简陋的土墙,垒满砂罐的储藏室,烧窑的土坑……眼前的景象与鳞次栉比的农家新屋格格不入,它更像是一个记忆的符号,作为砂罐厂最后的注脚……老人说,山上全是制作砂罐的天然优质泥土,大家都以制作砂罐为生,大大小小的手工作坊,有十几家。
老人十来岁就跟着大人制作砂罐,快五十年了。
做了多少砂罐子,也已经记不清了。最辉煌的时候,有好几个商贩在他家等货。现在,随着各种塑料、金属用具的使用,砂罐子已慢慢淡出了人们的生活。不过,还是有不少人喜欢用砂罐,他现在制作的砂罐还是能卖出去,老人说着,露出了满足的笑容。
为什么五十年能坚持下来?老人笑了笑,说自己没有什么爱好,就喜欢做这个,那样子,十足一个老顽童。这么多年过去,砂罐已和老人的生命紧紧融为一体,传统民间手艺不能在自己手中失传……谈起制作砂罐,这位不善言辞的老人却说得头头是道。
“你不是在看我取土吗?”老人咧着没了牙齿的大嘴,“取土很关键,泥土要有黏性,要干燥,要是那种粉末状的泥土最好。取来的土,要用米筛筛一遍,去掉里面的砂石和杂质,再配入煤灰等原料。坯料配好后,就开始揉泥了。”老人并不是用手揉,而是用脚去踩,一直把泥巴踩“熟”。怎样才算踩“熟”呢?这就得凭眼力、凭经验了,一般得踩一个上午。用双脚揉土,揉“熟”泥巴,泥土踩好后,就可以开始拉坯了。
老人踩几圈就要休息一会儿,撩起衣角擦擦汗,背上都湿透了。光着双脚在翻打的泥团上踩,一问才知道,这也是祖辈传下来的检验方法——制罐的土质非常细腻,容不得半点杂质,脚板的皮肤较为敏感,有硬的东西能瞬间察觉,可以保证成品质量。
老人在作坊里忙碌着,说是“作坊”,其实也只有七旬的老人和他的儿子二人。在一张直径大约50 厘米左右的圆盘前,老人一边用脚轻轻拨动圆盘旋转,一边熟练地捏塑着圆盘上的泥土,用竹板轻轻地拍打,就像一位母亲拍着婴儿。不多久,罐坯初具雏形。老人将罐坯放入另一个稍大的模具里面,加上沿口。老人将泥巴捏成长条,与原来的罐坯沿口接合,在老人的巧手之下,兩块泥巴接合得天衣无缝。接好之后,用毛刷对沿口进行打磨。老人告诉我,刷子是用长头发制作的,打磨出来的泥罐特别光滑。我看到老人聚精会神的样子,对老人来说,土和水的混合有着神奇的魔力,充满着劳动的乐趣。
“泥沙入手经抟埴,光色便与寻常殊。”在转盘的模具上拍打成型,加上沿口,用毛刷打磨,不紧不慢、轻轻柔柔地屈伸收放,一边用脚拨动着转盘,一边用手打磨,老人享受着赋予泥团新生命的惬意,每一件砂罐制品背后是爱的积累和延续,更是手艺人的匠心和传承,那娴熟的动作就像一位舞台上的艺术家。老人对于自己的手艺,有着一份发自内心的骄傲。
望着老人略显苍老的脸庞和那一双布满老茧却灵巧的双手,回味着老人用砂罐熬出的浓酽山茶的余香,所有话题和思绪都被一缕缕温暖的记忆围拢了起来。一排排整齐而又精美的罐坯,盛放着多少光阴?又留存了多少往事?它们像极了一颗颗跌落人间的星星……
窑里的火生起来,青蓝的浓烟冒出来,老人的眼睛有一丝湿润,老人看见了泥土和火焰的舞蹈。
四
“卖砂罐子咯——卖茶壶噢——”卖砂罐人走乡串村,挑着根长扁担,扁担上挂着大大小小、各种形状的砂罐制品。
地处资水中游的沙塘湾,盛产砂罐,迄今已有八百余年的历史了。民间陶器——砂罐不仅让沙塘湾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集镇声名鹊起,而且也使砂罐深入祖祖辈辈居于资水沿岸的群众生产生活之中,成为一段温暖的历史、民俗、文化记忆。
砂罐子品种多,有砂火锅罐、药罐、焖肉罐,烧热水的高罐,煮饭的瓮口罐、篱耳罐,炒菜用的横柄扁罐,炒瓜子花生用的敞口罐,烧甜酒用的翘嘴罐,烧茶用的牛头罐,还有茶壶、钵头、碗碟、漏斗、香炉、灯盏、筷子筒、火熜钵。砂罐又有单耳孔、双耳孔、三耳孔、四耳孔,甚至还有五耳孔、六耳孔,用一根或者几根竹鞭穿入砂罐的耳孔,方便提、拿。当然,耳孔越多,砂罐的体积就越大,能盛的东西和作用也就越多。
砂罐子表面和内壁显得很粗糙,像细小的沙砾粘在上面,新出炉的砂罐子大多为银灰白色,闪着金属的光泽,经过柴火和木炭的烘烤与煅烧,沙砾慢慢变成漆黑色,有一种黑不拉几的感觉。而那新买的砂罐子,在洗干净之后,第一次是要用来熬粥的,把粥煮成糊糊。砂罐子壁在窑里烧制时,也许有些细小的漏洞,经过熬粥的过程,熬烂的米粒或米汤糊糊把这些细小的空隙填充、堵塞起来,砂罐子就不再渗水或漏水了。
砂罐子,砂罐烧水、煮饭、热菜、熬药……每家每户都有好几个,即使破了,也舍不得丢,会用来装东西。人们会把每天鸡下的蛋放到旧砂罐里,等到攒满一罐,再拿到集市上去卖,旧砂罐俨然成了聚宝盆。
穿过万年的风沙,依稀可见砂罐子在熊熊的灶火上进行着自己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