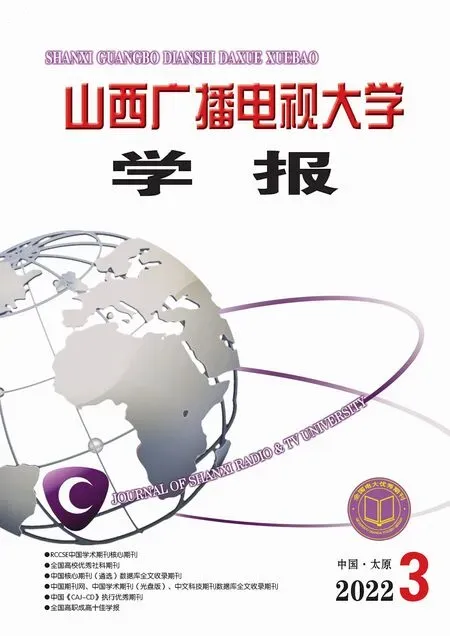试析荧幕中的声音景观及听觉建构
□王泽宇 李雪枫
(山西大学,山西 太原 030006)
声音景观(soundscape)描述的是以听觉主体为中心的声音环境,谢弗(Schafer)将其定义为“可研究的任何声音领域(Acoustic Filed)”。[1]自有声影片诞生以来,人们对于电影、电视中的声音现象一直处于听觉失谐的感知状态,声音仅提供着补充性和感觉性的说明。随着荧幕声音技术日渐成熟,声音蕴含物质性与艺术性交融的魅力被创造出来,扩展了声音与影像的关系,激发出听者与荧幕声景之间感官和文化的全新共鸣。
一、荧幕声景三大构成元素
音乐是一门抽象的艺术。参与荧幕叙事的音乐并不是独立存在的,需要配合荧幕中的人物、物体、情节、主题深化影片的主题思想,表现人物的心理活动,推动故事叙事发展,从而达到增值、赋义的艺术效果。人声制作是视听媒介再创造的重要手段,它以语音为载体将文字所传达的二维信息转化为三维的有声语言,在传递信息的同时也塑造着真实可感的人或物的声音形象。音响是声音景观中最独特的元素,它不仅能展现时代变迁、空间变化、地域文化色彩,还能够给予那些熟悉的声音以感情投射或附加象征性价值。音乐、人声、音响作为荧幕中的三大声音元素以多维、立体的叙事手法和对时空维度的重置,呈现出独具音韵美与艺术美的媒介景观。
(一)音乐
背景音乐确定一部影片的基调,发挥着“调性”(keynote)的作用。声音景观中的“调性”指的是听者所处声音环境的“基础”(base)或“背景”(fond)。[2]不同的声音景观提供着完全不同的调性,许多影视作曲家会利用主旋律音乐来深化整部影片的主题思想。在《海上钢琴师》《天堂电影院》《小妇人》等剧情类电影中抒情是背景音乐的主旋律,优雅、温暖又不乏激情的弦乐和充满追忆感的铜管乐营造出一种浪漫主义的美好幻想,以此来缅怀美好岁月中的爱情、友情、亲情。而诸如《蜘蛛侠》《复仇者联盟》一类英雄主义式科幻类电影,则大量运用恢宏、史诗感的低音管乐和充满能量、叛逆的电子音乐演绎出英勇、无畏、自我牺牲、首创等精神。除乐器的选取之外,曲式类型、演奏方式、和声结构等亦是烘托主体的重要元素,依循振幅、强度、频率、时值等客观物理属性,使得音乐产生的艺术效果与场景情绪协调统一,以音乐独有的情绪感染力和听觉层次感参与影片的叙境状态,渲染场景气氛、强调故事情节,深化不同题材影片的主题思想。
在参与叙事过程中,音乐增值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其与情感表达间的对应关系,生动地刻画人物形象,展现人物的心路历程。“音乐信号负责表现人物的心理活动”[3],以舒缓、悠扬、急促、连续重音、反复等音乐形式配合角色的神态、动作,来揭示人物的精神状态和思想感情,来展现这一声画结合的艺术形式。同时,音乐还是荧幕外观众情绪的发动机,塑造着影片故事的快乐、悲伤、激动、愤怒等情绪,作用于观众的潜意识而不被察觉。多样的情感转移产生于音乐中,它建构了影视艺术与观众体验的积极联系,是渲染营造画面丰富情感氛围的核心所在。
音乐在影片的场景转换中,以其占据领先地位的及时性表达给予受众心理预期。例如,低频的音乐预示着危险或厄运即将来临;急促、渐强的和弦伴随着镜头的快速推移暗示着故事即将发生转折;舒缓且减弱的音乐则代表事件的落幕或者故事达到尾声……“音乐的力量,就在于从感性上表现出来的时间运动,就在于表现为节奏的时间”[4]。音乐确定了影片同步、分割、拉伸等节奏形式,以“标点符号”的形式把控时间节奏,勾连视听整合从而推动着故事的叙事连贯性与完整性。
(二)人声
声音是诉诸听觉的,在有声语言的运动形式上,各语言元素之间的相对性和统一性是极为重要的。目前国内多采用后期配音,不同的视觉形象需适配质感、类型相近的声音形象以补全视听和谐的效果。在影视剧中,高大威猛的男性形象多采用力量型男声以带来稳重、大气之感;温柔恬静的女性形象采用中性女声或轻柔型女声给人以舒适感;刁蛮任性的人物形象多采用高亢型男女声营造出放荡不羁之感;父母、长辈形象则运用均质型男女声给人亲和、信赖之感……当然,影视人物声音形象的塑造还需分析人物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等因素,再结合配音员情、气、声等有声语言特征来展现特定场景下人物的高尚情操或特定阶级的思想感情。
针对产品声音形象的建构标准更为苛刻,通常需要运用配音员个性化的声音形式和独特的声音质感来形塑消费者的听觉标识,这种再创造“不是简单地出声念字,而要赋予稿件以音声化的加工创造”,[5]达到传播广告意蕴和价值的目的。中国著名配音演员孙悦斌是典型的浑厚型和低沉型男声,其最著名的配音代表力作《剑南春标志篇》:“这个标志,概括了酿造高品质白酒的必经之路,2005年5月13日,国家首次颁发此标志,颁发给剑南春,视为中国高档白酒,身份证。”低频的声音属性以及配音员对力度的虚实把控,完美塑造了酒水产品声音形象,胸腔共鸣与鼻腔共鸣刚柔并济,清晰而深邃。另一位著名配音员徐东宇的声音则风格迥异,他的《BMW3系》汽车广告:“是什么成就了运动王者,是平衡、是力量、是灵动,更是自始至终的激情!新BMW3系,擎动·心动。”相比于孙悦斌的浑厚低沉,他更倾向于“力量型男声”,他对声音力度的把控精准明确,充满磁性的男中音配合稳健的语调,极好地凸显了汽车类广告的严谨轻奢的产品特点。
人声所传达的信息远大于文字,它还包括音高、音色、强度、节奏等有声语言元素。人们在谈话时,“传达一项信息的总效果=言词7%+声音38%+面部表情55%”[6]。而影视艺术的出现,放大并唤醒了人类听觉中对于声音物理层面的感知。米歇尔·希翁[2]提出了基于声学、医学的“耦合振荡”概念,“耦合振荡是指我们身体的一部分会随着声音,尤其是低音频以及一部分喉咙补位的嗓音,而带有‘善意’(sympathie)的耦合振荡”[7]。低频的波状物从耳廓始入,再由鼓膜、小骨骨链传至内耳引起淋巴液振动或通过骨导传播进而将声波振动辐射至身体各部位引起振荡。例如广告《国窖,1573》,孙悦斌以其醇厚饱满的声线,中低音区扎实的胸腔共鸣技巧娓娓道来广告背后的故事,此时由听觉神经感知到的声音与身体的耦合振荡,形成了听觉与知觉两度叠加的联合共振,观众会在潜意识中产生肯定性心理共鸣,带来极强的听觉信服力和情绪感染力。
(三)音响
音响是荧幕声景设计中的重要一环,也是对声音叙事方法的探索,指明了声音创造性实验的路径。音响风格多样,这里将其分为自然音响和渲染音响两个部分。自然音响是指将自然景观与社会景观中具备自然、社会环境特征的音响,通过间隔式传声器拾音(spaced microphones)、重合式指向性传声器(coincident directional microphones)、双耳拾音技术(binaural recording)、点传声器近距离拾音(Close mic’ing)等多种拾音技术拾取同期声或采集拟音(Foley)音响,将其纳入影片的声音景观中。自然音响是为影片的写实性与客观性所创作,为其所传达的信息能达到最大程度的真实化而服务,对还原时空场景、增强真实感、在场感发挥着巨大作用。在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第三集中,我们可以听到徽州人在木榨榨油时,撞锤敲打木楔子沉闷的“咚咚”声、手艺人挥动撞锤时具备地域文化特色的吆喝声、炸膛与坯饼挤压导致油脂渗出的声音……这些音响的固有物理形式与当地文化紧密相连,“作为语言的‘第一能指’决定了它的永远在场”[7],再现了那个年代血肉与草木碰撞出的生命活力,成为了历史长河中最好的声音印记,传递出这道传承一千多年的古老工艺的文化意蕴。
渲染音响指的是通过现代声音技术渲染、重构的非自然音响。自然音响的核心是重现(reproduction)以增强真实感,而渲染音响的关键则是逼真(verisimilitude)。声音设计师将自然音响、拟音音响、自动对白替换(ADR)等采集到的声音素材经由后期变形、放大、遮蔽等技术处理,以达到与声源听感相近或超越客观声源的声音艺术效果。例如在电影《泰囧》中,主人公王宝给客人按摩发出的声音,是由我国著名拟音师龙岚通过揉捏猪肉录制而成;《霸王别姬》中程蝶衣火烧戏服的声音,是打火机燃烧粉丝产生的“啪啪声”;电影《星球大战》中光剑撞击的音效是由闲置的电影放映机和旧电视发出的声音后期配对而成……拟音师将不同混响、不同材质的声音持续混合、交汇,还原声源的物理属性或渲染(rendering)出一种熟悉的听觉综合,哪怕是最简单的声音片段,经过放大、减速都能展现出丰富的层次和声音细节,并将听觉场景引向具体化、物质化和真实化。观众所听到的音响将继续与原初声源保持高度的相似性,带来亲切感和在场感,或与声源摆脱原有的因果关系与画面以一种崭新的方式重新组合,调动、提升观众感知活力的同时为影片内容赋值、赋意。独特的音响效果设计更是扩展了影视创作的深度与广度,塑造出独具想象力的听觉形象带来更具艺术魅力的视听效果。
二、荧幕声景重构听觉方式
声音是具备时代属性的,1892年至1927年无声影像一直占据着唯我独尊的统治地位,直到20世纪初前后母盘复制技术逐渐发展成熟,电声录音时代的到来才正式拉开人类探究声音领域的序幕。21世纪声音技术迭代更新,数字声音制作技术、多声道立体声、杜比SR-D数字音轨、声音混录技术、THX(Tomlinson Holman Experiment)、数字立体声系统等新时代数字声音技术的入驻,激发了一种声音和影像之间的概念共鸣,重塑了观众的听觉方式和听觉经验。
(一)荧幕声景重置听觉时间
声音不存在停顿,它是瞬息的、易变的、一次耗散的。而在声音固定、变形技术出现后,人们倾听的时间和声音本身时间之间的同步性与紧密性逐步消解,荧幕中的时间不具有现实中的时空统一性,而是在画面和声音的交汇与离散之间灵活转换。
以声音的规律性建构时间感知。声音设计师通常会根据声音的波长、音色等声音内部特征的发展变化驱动或抑制时间节奏。在纪录片或公益广告中,以舒缓、平滑的配乐和低频、温和的男声为背景声,以及自然环境中均质的音响效果,此类声音相对于波动、不规律的声音具备的“时间活力”(temporal animation)较少[8],将对影像的时间感知带来缓慢、放松之感,从而通过声音的介质波动延长观众的听觉印象。
以声音强度、频率建构听觉敏锐度。在荧幕中存在着不同程度影响听觉时间的因素,通常强度越高、频率越大的声音最能影响听觉的警觉程度。例如悬疑、恐怖影片中经常突兀地出现快速且高音的声音现象,此类不具备规律脉动且不可预见的声音会立刻使观众的耳朵和注意力处于警觉状态,其强度、频率的含量决定了观众投射注意力的程度,声音的物理节奏超越了人体感知声音流的节奏,以将时间节奏点化、断裂的形式驱动观众在当下时空的实时倾听。
以声音持续方式建构听觉印象。现代录音载体带来了声音的复现,使得声音运作客观化,因此我们可以对声音进行再倾听。著名广告经纪人布罗姆曾说:“广告必须要不断重复,这就是全部秘密”[9]。首次听见一句广告语或广告音乐会产生即刻印象,消费者可能会对声音进行一定取舍。听觉作为被动的存在使得反复倾听得以成立,广告影片的反复播放使得更多的声音细节、信息被输入听觉窗口之中扩展了消费者的听觉阈限,最终形成高度凝练的听觉标识带来熟悉感和确认感,以声音的重复精确、延长着消费者的听觉印象,华为手机的提示音和麦当劳的五连音——“balabababa”等耳熟能详的品牌标识音便是最好的例证。
以均质的声音拆解时间节奏。均质的声音在荧幕中一般充当背景音或画外音角色,具有超脱时间线的非现实化特征。例如潮汐的流动声、山风呼啸声、街道的喧嚣声、催眠音乐等。由于此类声音个频段功率谱密度相近、能量分布均匀,因而很难参与生动的情境刻画和影片叙事,阻碍了观众对于荧幕时间节奏的感知。一些喜剧片、写实片常用此种视听失调(dissonance)的声音技巧造成声画间离的效果,以达到讽刺、批判、反思或揭示其背后话语及权力关系等效果。
(二)荧幕声景重建听觉空间
“每一个声音,当它实际发生在某一地点时,必然便具有某种空间特质,如果我们想利用声音来再现环境,就必须注意这一非常重要的特质。”[10]电影、电视所记录的立体空间是需要通过光与声音来构建的,荧幕画框作为影像的“容器”划定了观众的视觉边界,但在荧幕中为人耳所捕捉的声音依旧呈现流动、扩散的物理属性,那么在荧幕空间中能否提供一个听觉场景框架呢?
米歇尔·希翁[8]基于影视声音的空间特征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空间视角,将其分为“画内音”(onscreen sound)、“画外音”(offscreen sound)、“非叙境音”(nondiegetic sound)三种声音空间地带。“画内音”指的是可识别声源出现在荧幕中的声音,并且可视声源与声音二者同时存在于荧幕的叙境时态之中。画内音所表现人或事物是具备从属关系的,通常以视觉为主导并附加声音信号协助倾听。当我们在荧幕中听到声音时,镜头会充当我们的“眼睛”锚定声源位置给予视觉再投射,通过特写、放大等景别转换的视觉效果“磁性地”引导着观众定位画面中的声源位置,从而完成声画同步的视听效果,达到“在场”倾听的现实效果。
与“画内音”相反,“画外音”则代表着荧幕中不可见的声源所发出的声音,是影视艺术中拓展画外空间的常用技法。声音设计师通常会根据声音与影片角色或物体的关系设置画外音的传播范围、形式以营造某种情绪,达到某种叙事目的。例如,门外的脚步声、远处不可见的车鸣或是屋外教堂的钟声以延展观众对画外空间的想象。另一种情况则是心理画外音(mental offscreen sound),在荧幕中表现为声音场域缩小到观众或某位角色才能听到的声音,例如以配音展示角色内心诉求、想法的声音,并且观众只能从心理或逻辑层面推断其声源的无形。画外音与画内之间也存在着重叠、交替或转换,在电影《生化危机:终章》中,当主人公在光线暗淡的环境下打开一扇铁门时,铁门发出的刺耳音响引发了回声效果,观众所感知到的声音“体积”由薄增厚并具备了混响的重叠效果,以可见声场到无声源声场的对比、变化暗示了荧幕中实际空间的宽广度。
在荧幕视听关系中“非叙境音”是指不存在于荧幕叙境时空中的声音,我们最常遇到的非叙境音便是旁白、解说和背景音乐。“非叙境音”虽不参与荧幕叙境,但相比于其他声音元素它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界限,拥有独特的“话语权”。配音和音乐赋予了观众“穿越时空”的能力,它们可以由个体到整体,从伴随一个画内角色的具体时空场景游移到另一个特定时空,又或是瞬间推动整部影片的故事走向,以人声中心和音乐形式占据影片的主导地位,锁定、凝固或压缩时空场域,带领观众穿梭于“时空轮回”之间。
(三)荧幕声景观重塑听觉“真实”
正如本雅明对于现代科技的描述:“技术复制能把原作的摹本置入原作本身无法达到的地方。”[11]荧幕声景以现代化声音、听觉技术将声音“客体化”并与现实声源分离,形成了谢弗所说的“声音分裂”(schizophonia)[12]。声音编码使得听觉主体摆脱了与原初声音环境的因果关系,制造出一种“非在场”的声音景观。这种听觉主体、现实声源的不在场与声音真实的缺席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媒介听觉文化,以强硬的姿态“征服”或“霸占”着听者的听觉自由,并重塑了听觉经验与听觉方式。
真实和逼真(verisimilitude)永远是两个概念,在被中介化的听觉环境中,声音不是事物本身的忠实传达,而是一种违背“在场性”规律的听觉“真实”。荧幕中大海的流动声、骨头断裂声、汽车碰撞声、枪声等音响效果均是经由声音技术“染色”“加工”的听觉产品,很多观众并未在现实生活中拥有此类自然的听觉体验,而经过渲染、重构的声音拥有比直接感知更为丰富的听觉效果,无论是在物理层面声音的振幅、频率、强度、方向、速度等声音发生的方式,还是其所带来的临场感与震感力均取代了观众原初的听觉经验,并逐渐成为听者实用的聆听标准,试想一位从未去过海边的人描述潮汐的涨落声时,岂不沦为一种“声音幻觉”?
在听觉主体与声音环境的交互关系中存在着“埃尔格听觉”[2],即听者既是声音的发出者也是声音的接收者。例如,当我们在倒一杯茶水时,可凭借水在杯中所发出的声音谐波判断茶水是否倒满;转动车钥匙时汽车发动的轰鸣声;自身走路的脚步……一系列“在场性”的行为均会引发这种特殊的听觉形式。在同一物理空间中声音会给予听觉反馈,听者可以根据声音的音量、音色等物理属性判断声源的位置、方向、声环境或其他有效信息。在逼真甚至“超真实”的荧幕声景重构了听觉对声音时间顺序和空间组织形式的感知,以一种抽象、模糊、不可预见或跨越式的形式重组时,听觉将无法调动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去完成视觉与听觉一直以来的互补、对照关系,同时也瓦解着“埃尔格听觉”的反馈作用。
三、结语
荧幕声景是一种中介化的媒介景观,重构了声音的组织形式,拓展了崭新的听觉领域。数字化、电子化的声环境改变了听觉主体未经调和的听觉方式,带来了听觉文化的转向,由自然倾听转为非自然、技术化的倾听。同时,荧幕声景依托媒介技术打破了人们原初积累的听觉经验,以技术化声音编码的方式重塑了听者的知觉“完整”和感官“均衡”。